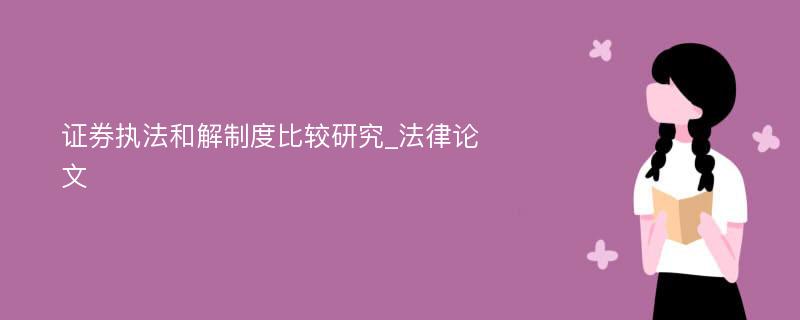
证券执法和解制度的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制度论文,证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F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788X(2009)04-0020-10
证券执法以授予证券监管机构之行政权为基础,体现的是行政权对证券市场之被监管者的权威,因此通常表现为具有阻遏、惩罚等性质的行政处罚。但是,面对证券行为的日益复杂化、专业化以及证券执法资源有限性的挑战,证券监管机构不得不寻求更快捷、高效的执法方式,以便集中精力处理严重性、影响性较大的其他案件。证券执法和解制度是指在证券执法过程中,证券监管机构采用与被监管者协商的方式,就特定的被调查行为达成和解,以被监管者自愿作为或不作为的方式代替形式上的行政处罚从而终结案件的一种执法机制。在证券执法和解机制中,民事领域中的平等协商理念被引入证券执法实践,并转化为证券监管机构与被监管者之间通过自愿协商而就被调查之证券市场行为达成和解,以此代替行政处罚或者取得等同于或超越行政处罚之效果,并因和解的达成和执行而终结案件。不管以何种性质来解释这种执法行为,它都以节约或者更有效地配置证券执法资源为初衷,以自愿和解代替行政处罚为本质,以实现证券执法目的和效果为保障。
一、证券执法和解机制的合法性基础
证券执法和解制度以证券执法权为基础,但有特殊之处,因此需要立法授权作为法律依据。纵观各国的证券执法和解立法,主要有三种立法授权模式:
第一种是行政程序法明确授权的立法模式,以美国、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为典型。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第554条第3款规定:“行政机关应对一切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提供机会:(1)使他们在时间、诉讼性质和公共利益允许时,能够提出和考虑问题、论点、和解请求和调整建议;(2)在当事人之间不能依协商解决争端时,根据通知和该法第556条及557条的规定,举行听证并裁决。”德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第54条第2句规定:“行政机关尤其可以与行政行为将要针对的人,缔结公法上的契约,以代替行政行为的实施”。第55条规定:“如果行政机关根据合乎义务的裁量,经过明智地考虑事实内容或法律状况,认为对存在的不确定性能够通过彼此让步(和解)得到消除时,就可以签订这种公法上的契约。”我国台湾地区“行政程序法”第55条规定:“行政机关对于行政处分所依据之事实或法律关系,经依职权调查仍不能确定者,为有效达成行政目的,并解决争执,得与人民和解,缔结行政契约,以代替行政处分。”这种授权模式既尊重了证券执法和解与证券执法之行政权相联系的特性,又因其明确授权而使证券执法和解之法律根基更加牢固。
第二种是金融立法概括授权的立法模式,此以英国为典型。英国《金融服务与市场法》授予金融服务监管局广泛的证券执法权力,包括但不限于制定规则、准备和公布法则、做出一般指导、决定基本政策和原则、行政处罚权力等。这使金融服务监管局可以根据证券执法实践的需要,在自行裁量的基础上确定和解结案的执法方式。第三种是金融立法明确授权的立法模式,此以新加坡和我国香港地区为典型。新加坡《证券及期货法》第232条第(5)款规定,不管是否承认责任,都绝不能将本条解释为阻止金融监管局与任何人达成在本条第(2)款或第(3)款关于违反本部分规定所指限度内支付民事罚款的协议的权力。香港《证券及期货条例》第201条第3款规定,证监会如在任何时间考虑根据第194(1)或(2)、195(1)(a)、(b)或(c)、(2)或(7)、196(1)或(2)或197(1)(a)或(b)或(2)条就某人行使权力,并认为就维护投资大众的利益或公众利益而言,作出以下作为是适当的,则可与该人达成协议……从而在金融立法层面上明确确立了证券执法和解的合法性。
可见,证券执法和解制度的合法性的直观表现,是行政立法或者金融立法等的授权性规定,或者明确授予和解的权力,或者概括授予自由裁量权,从而为执法和解提供合法性依据。我国《行政程序法》尚在起草中,《行政处罚法》并未为行政和解制度预留空间,证监会于《证券法》修改过程中提出的增加监管和解的建议也未予接纳,因此,我国在行政立法和证券立法层面上均未提供和解的合法性依据。这就需要我们从行政法或证券执法的理论层面挖掘现行立法的缺陷和认识的不足,并在理论上提供合法性依据的基础上酝酿其法定化的目标。
证券执法和解制度的最大障碍在于行政权的非处分性,行政权的非处分性与以协商、妥协为内容的契约式和解是根本对立的。然而,有关不得和解的主张之所以能够成立,是以“其应履行的义务”明确、合法、合理为前提的,但其忽略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前提:行政过程中存在着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只要法律、法规赋予行政主体一定幅度或范围的行政裁量权,那么,所谓的“其应履行的义务”就有变动的可能性,就应该是可以“和解”的。只不过这里的和解要受到更加严格的限制而已。[1]在美国行政法中,自由裁量权不仅存在于行政机关对事实的判定、规则的理解和适用、决定的作出等环节,还表现为“指控自由裁量”(prosecutor discretion)——行政机关对某个行为是否进行指控并采取行动属于自由裁量权范围,以及“选择性执法”(selective law enforcement)。指控自由裁量权和选择性执法之所以存在,主要是因为任何执法机关都受制于有限的资源。行政机关拥有的执法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执法者始终会面临“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情景。面对有限资源的事实,如何配置这些资源,就属于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属于一种行政技术。行政过程中自由裁量的广泛存在与行使,表明行政过程中不仅存在协商妥协的可能性,而且这种可能性几乎无处不在。既然自由裁量权的行使是一个事实,那么,与其让行政机关基于单方面的判断和斟酌而行使这种权力,显然还不如鼓励行政机关在通过协商对话获得合意的基础上行使这种权力,因为后者更有助于自由裁量的理性化,有助于“以权利制约权力”。[2]对行政机关而言,建立在通过对话、协商方式而获得的共识基础上的行政和解也更容易得到执行。因此,行政权包含的自由裁量权的授权或性质提供了以和解解决纠纷的空间,也为证券执法和解制度提供了合法性依据。
在我国,立法上尚未提供证券执法和解(或行政和解)的授权性规定,在解决行政纠纷过程中,却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协商、谈判等体现和解因素的情形。例如,在行政处罚过程中,相对人与执法机关之间就违法情节、处罚种类和幅度等问题进行交涉,这实质上反映了行政处罚机制存在协商机制的运用空间。在行政诉讼中,居高不下的撤诉率也间接反映了这一点。有数据表明,《行政诉讼法》实施14年间,全国一审行政案件撤诉率从未低于1/3,最高时达到57.3%[3],而根据《行政诉讼法》第51条,行政机关改变其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且行政相对方同意,这是撤诉的原因之一。这说明,行政相对方的撤诉相当一部分是由于与行政机关达成某种合意——行政机关改变具体行政行为。这些情况虽不能作为行政和解之直接法律依据,但却表明行政权行使过程中实际上存在协商的情形,如果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存在协商的事实,也就存在本文所指证券执法和解的上位制度(行政和解)的可能性。在我国,证券执法和解的合法性存在实践基础,但只有上升到立法尤其是行政立法层面,证券执法和解的合法性才是完整和坚实的。派生于此,我国在确立证券执法和解的法律机制时,必须充分考虑证券执法和解的适用条件、基本程序、和解内容和效力等问题。
二、证券执法和解的适用条件
证券执法和解只有一定的前提条件下才具有可实施性,但因为和解的相互妥协性、自愿协商性,和解适用条件的设定等原因,证券执法和解也呈现了多样性和不统一性。在总体上,行政执法和解的适用条件分为三种:
(一)适用和解的积极条件
适用和解的积极条件,即明确规定证券执法案件只有在满足一定条件的基础上,证券监管机构才能与相对方进行和解。其中又有两种条件设定模式:一种以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为典型,二者均将事实或法律关系或状况经合理调查而仍不确定、相互让步之和解同样能达到行政行为目的作为适用和解的积极条件。另一种以香港地区为典型,即证监会只在被告配合调查、事实相对清楚以及可能的处罚相对可预测的情况下,才选择和解。
比较分析来看,前者将和解限定在事实与法律经过合理调查仍无法明晰的复杂疑难案件,源于证券执法资源有限和执法效率的考虑。其中存在一个问题,即在事实与法律调查不清的情形下进行和解,容易对证券监管机构的执法权威产生消极影响,使公众对其执法权丧失信任,而证券监管机构本身也不愿意承认对证券违法行为束手无策,尽管行政权不是万能的,但此种和解的达成就意味着承认了行政权面对违法行为的无能或无奈。因此,这种和解前提的设定可能是证券执法机关以及社会公众都无法接受的,我国台湾地区和德国证券执法中鲜有成功和解的案例,恐怕与此有关。如果稍微转变一下立法技术和措词,如授予自由裁量权,或者将承认违法行为作为和解的附加前提条件,证券执法机关可能更愿意采用和解,社会公众也更容易接受这种和解,执法行为的相对方也可能基于利益衡量而作出适当选择。后者的和解条件与前者正好相反,为事实与适用法律完全确定的、相对简单的案件,且以配合调查为辅助条件,有重罪重罚、轻罪轻罚的味道。通过和解简单案件,有利于集中执法资源于更严重、影响更大的案件,尽管初衷与前者类似,但因兼顾了证券监管机构的自尊和自信,也迎合了公众的认识,因而得到了积极的使用。
(二)适用和解的消极条件
适用和解的消极条件即禁止和解的情形,其既可以是从反面对积极和解条件的明确化,也可以是对积极和解条件的进一步限定,还可以是对证券监管机构概括的和解授权的限制,因而具有其他方式所不具备的价值。然而,适用和解的消极条件必须与积极条件或授权立法相结合使用,否则容易造成反向推理的谬误。
如美国的《联邦行政程序法》和1934年《证券交易法》均未明确限定SEC采取和解程序的条件,这与SEC的广泛授权有关,但并不意味着SEC在所有情况下都可以选择适用和解。美国《行政争议解决法》对此做出了限制。当一个行政争议的解决可能涉及行政先例的确立、公共政策、公共利益、信息公开的必要性等因素时,SEC就不得以ADR程序替代正式的行政程序。
(1)遵循先例的价值观念要求提出确定的或权威的解决方案,而ADR程序不可能被普遍接受作为权威的先例;(2)当涉及或者影响政府政策的重大问题,进而要求在做出最终决定之前引入额外程序时,ADR程序无助于为行政机关创设建设性的政策;(3)坚持既定的政策对于确保不增加个案决定的偏差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而ADR程序不利于保持个案决定的一致性;(4)事件对未参与ADR程序的个人或组织影响重大;(5)有关该程序的充分公开的记录有着重要意义,但ADR程序不能提供这种纪录;(6)行政机关必须保持对事件的持续管辖权,并有权根据变化的情况而改变处理方法,而ADR程序将妨碍其实现上述要求。① 香港的纪律处分规则规定,以缴款代替纪律处分在以下情况并不适用:①失当行为涉及不诚实行为;②有关人士有很大可能再次作出类似的失当行为;以及③有关人士的失当行为非常严重,须及时令该人离开业界,因为如他留在业界,会危害投资者的利益和市场操守。②
(三)授权证券监管机构自由裁量
授权自由裁量是指既未规定和解的积极条件,也未限定消极条件,而由证券监管机构根据个案情况自由裁量。如新加坡金融监管局认为,设定和解的标准既不切合实际,也不令人满意,英国在立法上也持这种态度。然而,英国执法机关通过执法实践活动,也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参考因素,如违法行为的严重性、被调查者是否合作等。必须看到,完全的授权性立法通常只能在特定的判例法体系中才能有序地运作,不宜机械地模仿。
如此介绍三种和解条件的设定方式,仅是基于区别上的考虑,在实践中,有的国家使用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和解条件设定方式。在我国,香港在立法上即将三种方式结合起来,既有积极条件和消极条件,还有一个兜底性的授权规则,即证监会有权在其认为就维护投资大众的利益或公众利益而言是适当的情况下,借协议而就纪律处分程序达成和解。但证监会是否会就某宗个案进行和解将视乎个别个案的事实及情况而定。应当说,和解条件设定方式的不同以及内容的差异都与所在国不同的法律文化和证券执法背景密切联系,因而需要在国际经验的基础上进行本土化的处理,即根据本国证券执法环境、目标、公众认识等确定适合且易于接受的和解条件设定方式,而且,具体和解适用条件的设定也许随着上述因素的变化而变化。
三、证券执法和解的工作程序
工作程序是和解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及执法效率与公平的衡量,甚至一些敏感的问题,如行政权属性、利害关系人保护、平等协商在和解制度的体现等等。因此,各国关于和解工作程序的设计存在一定差异,这是因为法律文化和法律环境不同而带来的问题。
(一)和解谈判的启动
和解是为了解决证券监管机构正在调查的证券违法案件,因此,启动和解程序至少应在启动调查程序之后进行。然而,和解不是没有预设条件的任意和解,无论证券监管机构还是被调查者,都必须在衡量是否符合和解前提的基础上决定是否启动和解程序,这样,至少在理论上,唯有经过必要的调查,才有启动和解的可能。但是,关于和解前提的不同设计以及和解中相应的惩罚性机制的存在使谈判的启动阶段相应地推延。一般来说,和解前提设定得越严格、和解内容中的惩罚性越严重,和解的启动阶段可能越往后推迟。
美国的证券执法和解一般以SEC掌握了一定的证据及线索,开始调查程序为起点,但是无论在调查阶段还是调查完毕以后的诉讼或行政审裁阶段,都可以进行和解。即任何被通知可能或将要对其启动行政审裁(调查)程序的人,或者已经处于审裁(调查)程序的一方,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提出书面的和解申请。③ 而像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一样以事实与法律调查不清为前提,则其和解程序的启动相对其他国家则通常表现为证券违法行为的处罚阶段或可处罚阶段。英国FSA则针对和解程序启动的不同阶段设定了不同的罚款折扣率,而且,较之之前30%、20%、10%和0的折扣,现在的折扣30%、15%、5%和0。通过降低中间两个阶段的折扣率而实际上传递着鼓励尽早和解的政策倾向。其他国家虽未设定如此明确的鼓励措施,但和解的不同阶段通常包含在和解中罚款等处罚措施的程度的考量因素中。如何设定和解的不同阶段以及相应的和解处罚力度,可能需要仔细地、全面地斟酌。
关于和解谈判的启动者,则或者为证券执法行为的对象,或者证券执法行为的对象与证券监管机构二者兼而有之。在前者,和解谈判的启动权专属于证券监管机构调查之对象,如果以契约来解释,即只有该调查行为之对象有权提出和解的要约,证券监管机构拥有承诺或提出反要约或者拒绝的权利。在后者,证券监管机构有权根据其执法需要决定是否主动提出与被调查方和解结案。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即使证券监管机构没有被赋予和解谈判的启动权,但和解的授权性规定以及其关于鼓励和解的态度、与相关通知书一同送达的可申请和解的暗示等,实际上仍然使监管者掌握着和解程序启动的一定程度的主动权。而且,和解并非单纯的民商事合同,虽其宣称平等协商,但行政权力的影响必然渗透于谈判的全过程,监管机关也在谈判的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即使在事实与法律经相当调查仍无法查清的情况下同样如此。在对和解设定前提,尤其是授权监管机构裁量设定个案中和解的可行性的情况下,被调查方对于能否寻求和解解决实际上有一种不确定的态度,监管机构主动和解或提供和解的机会有利于消除这种不确定性。因此,不管是否明确规定行政机关主动启动和解,其实际上都拥有这种权力,仅是直接或间接、明示或默示的差异而已。
(二)和解的谈判与决策
和解的谈判由双方在自愿的基础上协商进行,根据法律的特别规定,有时会加入听证程序。在美国法上,当委任听证官时,负责谈判的部门和提出和解请求的一方可以要求听证官就和解申请的适当性发表意见,但要求听证官对和解表达意见或者参与和解会谈意味着提出和解请求者放弃了根据听证官表达的意见而主张偏见或者擅断的权利。④ 而在台湾地区,听证的主要目的尽管也是确定和解是否合理以及商定和解内容,但并没有因听证而导致申请者某些权利的丧失。
关于和解谈判与决策的合一抑或分离,既有将二者分离的做法,也有主张二者合一。美国法上采取二者分离的做法,和解申请由SEC委任的利害关系部门予以考虑。该部门将附带其意见的和解申请呈递给委员会,如果其提出的是反对和解的建议,那么,除非提出和解者要求呈递,否则,该和解申请将不会呈递给SEC。⑤ 英国在形式采取的也是和解谈判者与决策者分离的制度。英国SFA根据《金融服务与市场法》关于执行与决策分离的规定,在《2005执行文件》中设置了由两名FSA董事组成的执行案件处理组作为和解决策者,而原来设定和解的标准和批准和解条件的RDC不再参与和解,但在和解失败的情况下针对被调查事项作出行政处罚。从而实现了FSA内部和解与行政处罚之决策者的形式分离,并在此基础上通过无论FSA职员还是被调查者都不能向RDC披露相对方做出的任何承认或陈述的规定实现了实质上的分离。
证券执法和解不仅要实现执法效率,也要兼顾和解的公平性。而在和解失败的情况下,证券监管机构要做出行政处罚,但和解谈判过程中以和解为目的而做出的某些承诺、自认等是不能作为行政处罚的依据的,如果和解的决策者与行政处罚的做出者在证券监管机构内部是合一的,那么,很难保证行政处罚不受上述承诺和自认的影响,相对方提出和解申请就可能给其带来不利后果——加重处罚或者施加处罚。因此,为了保证相对方的合法权益,同时维持其和解的积极性,和解的决策者与行政处罚的决策者首先应当在形式上实现分离,即分别由证券监管机构内部的不同部门来执行。其次要在实质上实现分离,即决策者获得的以和解为目的的承诺、自认等信息不能传递给行政处罚的决策者,但前者经调查而掌握的违法行为事实则应及时提交给后者,以使其做出公正的行政处罚决策。
(三)第三方的参与
和解是针对行政处罚所作用之证券违法行为,而证券违法行为所侵害的不仅是证券市场秩序,还有具体的证券市场参与者,包括证券投资者、其他证券中介机构等。尽管在行政处罚之外还有民事赔偿、刑事诉讼等责任机制对受害者提供保护,但就该违法行为达成的和解内容的广泛性以及和解目的中的效率性考虑等使之不可避免地涉及上述人的利益。第三方利害关系人如何参与到和解程序中来是证券执法和解机制中不可回避的问题。
由于和解在代替行政处罚的同时往往不具有违法或责任承认的效果,并且也不记入和解相对方遵守法律的档案资料;在信用制度较发达的证券市场,这无疑起到激励和解的作用。因此,一些国家在和解决策之前引入了第三方的参与制度,如台湾地区金管会于行政和解契约协商过程中,应就所欲和解之内容征询利害关系人的意见或举行听证,但金管会不受利害关系人意见或建议的拘束,其仅作为和解决策的参考。参与权超越了知情的范畴,使利害关系人能将其意见反映给和解决策者,即使不对后者产生拘束力,但如果在之后的和解公开中详细说明对该意见的采纳情况及是否采纳的理由,那么,第三方权益就可在和解中得到较为充分的体现。
四、和解的内容
证券执法机构接受和解的目的在于确保在和解中实现的对当事人的制裁,真正能对违法者本人造成损害,而不会仅被视为一种业务成本。因此,和解的内容除一般的行政处罚措施,如罚款、禁止或限制从业资格等之外,还包括对违法行为受害者的赔偿、放弃其他诉讼权利、保险补偿或者税收扣减等。
(一)是否承认违法或责任
证券监管机构对证券违法行为者作出行政处罚是从监管机关的角度作出的关于行为违法和承担责任的判断,如果该行政处罚最终生效,那么,不管被处罚者是否承认违法或责任,其当然具有此种效力,或者可以说违法和责任是行政处罚的当然含义。但证券执法和解制度关于违法或责任的承认上却有不同规定。如在美国法上,一旦否认关于违法行为的指控,SEC就不会同意或批准和解,因此,几乎所有公开的和解决定中都使用“既不承认也不否认违法行为之指控”的措辞,即和解不具有违法行为之推定功能。台湾地区金管会“处理原则”也做出“既不承认亦不否认”之类似规定,但以经相对人之请求为前提。与之相反,英国FSA的相关执行规则规定,任何和解都必须包括相对方所承认的关于事实和任何违法行为的陈述,即承认违法或责任是和解的必备内容。而香港地区证监会和新加坡金融监管局的执法和解既可以在承认过错的基础上作出,也可以在不承认过错的基础上作出,但香港证监会的不承认过错的和解需要征询受该和解决策影响的相关部门的意见,实务操作上取决于针对个案的具体判断。从和解制度的整体框架分析,违法或责任承认与否的制度设计同样取决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如和解前提、执法状况、法律文化、违法行为的严重程度、和解中涉及之处罚的严重程度等,只要与特定的证券执法和解环境相适应即可,不必追求统一的标准,但仍可由立法或监管机关提供参考性指标。
(二)民事罚款的对象和程度
民事罚款是大多数证券执法和解的必备内容,但在罚款之对象及数额的确定上却存在一定的争论,美国SEC执法和解实践对此的犹豫表现得更为明显。
确定罚款对象的困难之处在于对公开公司是否适合做出以缴纳罚款为内容的和解。公开公司具有不同于股东的独立法人人格,单从主体资格角度看没有问题,但公司缴纳罚款实际上仍是由股东来承担缴纳责任,而公开公司的股东,尤其是公众股东往往就是和解之公司违法行为的受害者,不但不能获得赔偿反倒承担责任,其合理性似难接受。因此,美国SEC也不愿意向公开公司请求或施加民事罚款,因为在理论上,这种罚款的负面影响最终将落在已经受公司之违法行为欺骗的投资者身上。但有学者认为,随着2002年《萨班斯—奥克斯利法》的通过,其不愿意针对被指控的违法行为之公司积极追究大额赔偿与和解的倾向终于结束。⑥ 之所以如此,与《萨班斯—奥克斯利法》关于将和解之罚款纳入专为受该公司之违法行为侵害的投资者提供赔偿的公平基金制度密切联系在一起,而且,除追究公司之责任外,对公司之违法行为有过错的董事、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也要承担行政处罚,无论是处罚中的罚款抑或和解中的罚款,都可纳入该公平基金,与公司的民事罚款共同作为受害投资者的赔偿基金。尽管如此,如果公司受处罚之行为的受害者是股东,其仍将承担该罚款支付的成本(大多数对公司实施罚款的案件均如此)。因为当罚款最终返还于为该违法行为之受害者的部分或全部股东时,所返还的数额也少于分配的管理成本。因此,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在2006年初做出了一个关于对公司施加罚款的决定,并将以下因素确定为斟酌公司罚款的主要因素:一是公司是否因该违法行为而获得利益;二是公司罚款补偿或者进一步损害受害股东利益的程度。除此之外应当考虑以下因素:阻遏特定违法行为的需要、对无辜方的损害程度、该违法行为的共犯是否遍及整个公司、过错程度、查明特定类型违法行为的难度、公司是否采取补救措施、与证券交易委员会及其他执法机构的合作程度。⑦ 这就为对公司实施罚款以及保护公司投资者提供了较为明确的指引,从而推动投资者赔偿目标的实质性实现。但在仍坚持公司的独立人格而仅对公司施加行政处罚,或者不考虑公司违法行为之受害股东是否实际承担该罚款成本等相关因素即对公司施加罚款等立法下,仍摆脱不了形式上对公司罚款而实质上由公司违法行为之受害股东承担部分或全部支付责任的尴尬。
关于民事罚款的数额,除新加坡《证券与期货法》第232条第(2)款和第(3)款明确规定了罚款的数额外,其他国家大都授权证券监管机构在考虑各种因素后裁量,如美国、英国等。但由于和解的契约性质——自愿和平等谈判,如何确定和解个案中民事罚款的数额,以兼顾行政处罚之功能与保持和解之积极性,也是难点。正如美国SEC本身已经认识的那样,如果金钱惩罚(罚款)不能区分糟糕与更糟糕的情形,不再有导致名誉损害之忧惧的功能,失去了实施“公开处罚”的能力,那么,sEC也将被剥夺重要的投资者保护工具。⑧ 但如果作出过于严格,或者明显超过正常之行政处罚数额的和解罚款,被调查者的和解积极性可能受到影响,或者不申请和解,或者推迟和解提出的时间,而这也与证券监管机构通过和解缓解执法资源紧张以及提高执法效率的目的相悖。在介绍之国家中,只有英国针对和解的不同阶段确定了明确的和解折扣标准,这使被调查者对和解结果有了明确的期待,就此点是值得借鉴的,但由此能否实现其行政处罚的原有功能,恐怕也是借鉴的同时需要保持怀疑之处。总之,和解之民事罚款数额的确定及激励和解的优惠政策的设定也需要权衡和解目的以及行政处罚功能等因素,是一项因地制宜的制度。
(三)涉及第三方权益的事项
证券执法和解以证券监管机构以和解结案以及相对方为或不为特定行为的承诺为主要内容,但在后者的承诺在约束其自身的同时,也可能涉及和解双方之外的主体,从民事契约的相对效力来讲,可谓证券执法和解契约的涉他效力。如所引我国台湾地区“处理原则”就规定,金管会就行政和解契约得视个案情形及利害关系人受损害之程度与范围,要求相对人于一定期间内与经利害关系人授权且设立目的为保护证券投资人暨期货交易人之财团法人、公益信托或其他公益团体进行民事和解。即以相对方与利害关系人之特定授权者就其损害之赔偿达成民事和解作为本行政和解的前提,从而通过行政和解实现了因和解之事项而受到损害的利害关系人利益的救济,但往往以利害关系人或其授权者已经采取诉讼等实际救济措施为前提。而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和解相对方承诺对因其行为而受害者进行赔偿常常作为和解的内容,这就省略了诉讼等程序,而直接实现了相关者利益的保护。但问题在于,如果仅仅是赔偿或和解的简单承诺,而没有具体化,所承诺之赔偿利益的实现将面临执行和监督的难题;而如果将赔偿或民事和解承诺具体化,包括赔偿数额、支付方式等,利害关系人就必须参与和解谈判程序,并就该赔偿或民事和解享有决定权,这样,其对赔偿或民事和解中某一事项的不同意必然影响证券执法和解的达成。因此,通过证券执法的行政和解一并解决利害关系人的赔偿初衷是好的,但实际操作起来可能需要克服很多困难,包括赔偿承诺的监督执行,赔偿或民事和解承诺相对证券执法和解的效力、利害关系人之赔偿权利的保护等等。
除此之外,和解中还会涉及吊销执业资格、暂停执业资格等典型的行政处罚事项,以及承诺改善公司治理、改进风险监控能力、放弃听证权利、放弃诉讼权利等非行政处罚事项。如美国《公平基金和罚没计划规则(2006)》规定,和解建议必须规定,如果和解建议被接受,那么申请人通过提出和解申请而放弃如下权利:根据制定法规范的要求已经或即将开始的一切听证程序;提出所提议的事实认定和法律结论;申请听证官参与,并做出初步决定;所有的听证后程序;以及法院的司法审查。进而,申请人还需要放弃:本规则或其他法律要求中所规定的、可能被解释为阻止SEC的任何职员参与根据和解建议而作出的任何命令、判断、确认事实以及法律结论等的准备过程,或者对此提出建议;以及任何对sEC基于考虑或讨论有关和解的所有或部分事项而主张偏见或妄断的权利。⑨ 从此意义而言,和解的价值超越了一般的行政处罚,也比没有任何法律效力的指导、指引、建议等更强烈,不仅有惩罚和警示作用,更有规范和引导功能。但从美国的经验来看,证券监管机构可能通过证券执法和解协议的形式设定监管权限以外的其他事项,从而规避监管权的法定限制,或者扩充监管权力。对于具有此类性质的和解协议,能否仅以当事人自愿为由而承认其法律效力,关于合同(或契约)的法律评价的一般规则(即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的解释能否适用也还是问题。
五、证券执法和解的效力
证券执法和解产生的法律效力主要表现在行政程序上的结案效力。而达成和解对于证券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以及和解协议的证据效力等问题也是和解机制需要确定的问题。
(一)代替做出行政处罚而结案的效力
从形式上看,和解针对证券监管机构正在调查之证券违法行为而做出,而且,通常情况下,如不和解,则表现为行政处罚,因而具有代替行政处罚的效力。从实质上看,不管和解是否以承认或推定违法行为或责任为前提,和解中相对方做出的承诺都包含了行政处罚的主要内容,有时甚至超出了相同情形下行政处罚的处罚类型和程度。因此,和解具有实质上代替行政处罚的效力,能够实现行政处罚被赋予的功能。和解具有代替行政处罚的效力,这是域外立法基本一致的地方,但在其他效力方面则存在较大差异。
(二)过错推定或违法行为承认的效力
和解是否具有过错推定或违法行为承认的效力取决于和解前提或内容的立法规定或实践。有的立法明确将承认违法作为和解的前提,如英国;而在有的立法下,承认违法与不承认违法两种和解均可存在,只不过后者的条件更严格,如我国香港地区;台湾地区立法是根据相对方的请求可以在和解中载入“既不承认亦不否认”违法的表示;美国则更为特殊,因为SEC不会同意否认违法的和解,因此,几乎在所有的和解中都加入了“既不承认也不否认违法行为之指控”的措辞。
在将过错或违法之承认作为和解前提的情况下,即使和解内容中不包含此项,其也具有该推定或承认的效力。反之,如果过错或违法之承认并非和解的必要条件,则要看具体个案中的和解是否包含承认的措辞或表示。然而,即使特定的和解并不具有承认或推定违法的效力,不会在其守法记录中体现出来,但其商业信用还是会受到一定的影响。更何况证券监管机关公开的和解决定中关于事实的描述以及处罚或罚款等字眼实质上仍体现出行为违法性,因此,在一般情况下,是否明确承认恐怕没有多大意义,至少在业界而言如此。
然在特定国家,如果证券监管机关之行政处罚被赋予了超越行政处罚本身的意义,那么,是否承认违法就具有重要意义了。在我国,根据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6条的规定,投资人提起虚假陈述证券民事赔偿诉讼,应提交行政处罚决定或者公告。据此,行政处罚决定或公告成为投资者虚假陈述赔偿诉讼的起诉条件之一,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成为民事赔偿诉讼的前置程序。而之所以将其作为民事赔偿诉讼的前置程序,恐怕与行政处罚关于违法行为的有法律效力的认定有关,而一旦以和解代替行政处罚,如果不同时附加违法行为的明确承认,现行法下因虚假陈述而受害的投资者可能根本就没有资格提起赔偿诉讼。因此,是否明确和解具有违法行为承认的效力还是需要认真检讨的。
(三)关于和解对刑事责任的影响
尽管没有明确的立法说明不得就已刑法处罚的案件进行和解,但从许多国家关于和解条件以及和解考虑因素或排除因素的规定来看,就监管机构经调查而确认的刑事案件是不能和解的,反过来说,和解的案件不存在追究刑事责任的可能。但美国在此又表现出特殊性,其将和解与刑事指控视为可以并存的两种措施,但在和解涉及民事罚款的情况下,该民事罚款不能具有惩罚性,而仅以救济为目的。除此之外的非金钱性质的和解处罚,则不排除针对同一和解事项的刑事指控。
(四)关于和解对民事赔偿救济的影响
和解是代替行政处罚的措施,一般情况下与民事赔偿救济无关,因而不排除因该和解事项而受害之投资者在和解之后寻求民事赔偿救济。在证券执法和解的效果完全归属于行政机构(政府),尤其是和解中承诺的罚款上缴国库的情况下,具有行政行为属性的和解行为与民事诉讼是完全独立的,在目的和功能上也有不同定位。因该和解之证券违法行为而利益受损的投资者不能以受害者的身份获得任何利益,必须通过单独的民事赔偿诉讼寻求损害赔偿。
而在美国,和解中的民事罚款与罚没款项要按照一定的标准纳入针对该和解之违法行为而受害的投资者设立的公平基金。基金在优先赔偿投资者损害后,剩余部分专用于投资者教育,而非上缴国库。这样,和解的制度价值已经超越了单纯的行政执法,而具有投资者赔偿的功能。但即使在证券执法和解被赋予投资者赔偿功能的情况下,也不排除受害投资者通过集团诉讼或普通诉讼的形式寻求公平基金赔偿之外的赔偿。而且,在SEC的许多执法和解案件中都可以看到类似的表述,即违法行为者同意放弃在任何相关的投资者诉讼中基于已经支付的罚没款而主张抵消或折扣的权利,而且也不会获得其在民事罚款中已支付部分的抵消或折扣利益。如果法院在相关投资者诉讼中授予这种赔偿抵消,将在授予该赔偿抵消的最终命令后的30天内通知SEC,并按照SEC的指示向国库或公平基金支付同等数量的赔偿抵消金额。这说明,和解中的罚款支付以及随后的公平基金赔偿都不能阻止受害投资者寻求单独的民事赔偿救济。因而,和解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加速民事赔偿的解决。
(五)有时和解还具有扩展证券执法机构处罚权限的效力
自从美国国会通过《证券执行救济与廉价股票法》(Securities Enforcement Remedies and Penny Stock Reform Act of 1990)以来,证券交易委员会就获得了在联邦法院诉讼中针对各种证券违法行为施加民事罚款的权力。但与此相反,在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行政执法程序中,国会则谨慎地限定其施加此种民事罚款的权力。但在Grant Thornton以及少数早期的案件中,SEC已经设计了一个创新性的方法规避对其权力的法定限制,即通过与被调查者签订“自愿”协议的形式支付罚款。再如,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期间,证券交易委员会已经设计出同样的创新性方法禁止证券违法行为者担任公开公司的董事或执行官,而国会直至1990年《证券执行救济与廉价股票法》⑩ 才明确授予SEC执行官一董事任职资格禁止的权力。但那时证券交易委员会已经在至少15起案件中通过和解形式要求并获得了该权力。(11) 如在SEC v.Florafax International,Inc.一案中,在和解协议中达成了一项为期3年的任职禁止措施。(12) 在SEC执法的背景下,这一发展尤为重要,因为SEC职员实际上通常将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和解视为固定的先例以指控和解决随后的案件。(13) 因此,对于通过执法和解的形式扩充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权力或者规避法定的权力限制的实际做法,证券立法必须对此做出明确的反应。
结语
证券市场违法行为本身的复杂性和证券执法资源的局限性增加了调查取证和事实发现的难度,而证券法律相对证券市场行为的不完备性和滞后性,使违法性的判断和执法依据的确定也存在许多模糊之处。更为关键的是,这些困难和模糊之处有时是通过传统的证券执法行为无法解决和克服的。因此,在传统的执法理念下,证券执法或者面临着不能作为和无以作为的尴尬,或者面临违法作为、权力滥用的危险。行政权是现代社会中必不可少,但又是最受争议的一种权力,尽管现代行政权行使的透明度在逐渐增强,但命令从属性质仍使其在许多方面处于私权利之上,从而使公权力与私权利的矛盾时有激化。这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是相背离的,和谐社会并非消灭纠纷,也不可能消灭纠纷,但必须提供纠纷解决的适当机制,尤其鼓励纠纷的一次性解决,鼓励更多的自愿协商以预防和降低纠纷再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等)。和解正是这一要求在证券执法实践中的体现,即将证券监管机构置于与被监管者同等的地位上进行沟通、交流和协商,在相互信任与合作的基础上,以相对快速、低廉和简洁的方式解决执法纠纷,从而实现监管机关与公众及被监管者之间的和谐状态。而且,个案和解的执法方式的价值不仅针对特定案件,还有利于建立监管机构与被监管者的合作关系,有利于形成执法与守法的良性循环。
收稿日期:2009-07-14
注释:
① See 5 U.S.C.§ 572(b).
② 参见《证监会纪律处分程序概览》www.hksfc.org.hk.
③ See SEC,Rule 240(a),Rules of Practice and Rules on Fair Fund and Disgorgement Plans,2006.
④ See SEC,Rule 240(c) (2),Rules of Practice and Rules on Fair Fund and Disgorgement Plans,2006.
⑤ See SEC,Rule 240(e) (2),Rules of Practice and Rules on Fair Fund and Disgorgement Plans,2006.
⑥ Richard A.Spehr & Michelle J.Annunziata ,The Remedies Act Turns Fifteen:What Is Its Relevance Today?,1 N.Y.U.J.L.& .Bus.587 (2005).
⑦ See Statement to the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Concerning Financial Penalties,January 4,2006.
⑧ Speech by SEC Staff at 24th Annual Ray Garrett Jr.Corporate & Securities Law Institute by Stephen M.Cutie,Director,Division of Enforcement of U.S.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http://www,sec.gov/news/speech/spch042904smc.htm.
⑨ See SEC ,Rule 240(c) (4),(5),Rules of Practice and Rules on Fair Fund and Disgorgement Plans,2006.
⑩ 该法案关于公司负责人和董事的任职禁止措施成为1933年《证券法》中的section 20(e)和1934年《证券交易法》中的section 21(d)(2)。
(11) See Russell G.Ryan,"Penalty" Undertakings in SEC Administrative Settlements Deserve a Closer Look,Securities Regulation & Law Report,Vol.36,No.39,10/04/2004.
(12) See,e.g.,SEC v.Florafax International,Inc.,Lit Rel.10617,31 SEC Docket 1425 (N.D.Okla.1984) (three- year bar on consent and without admitting or denying liability,where defendant had previously,and in a separate matter involving a different corporation,been enjoined and criminally convicted for securities violations) See also Stephen J.Crimmins ,Where Are We Going With SEC Officer and Director Bars? ,April 24 issue of BNA's Securities Regulation & Law Report.(available at http://www,bingham,com/bingham/webadmin/documents/radF936 A.pdf)
(13) See Russell G.Ryan,"Penalty" Undertakings in SEC Administrative Settlements Deserve a Closer Look,Securities Regulation & LawReport,Vol.36,No.39,10/04/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