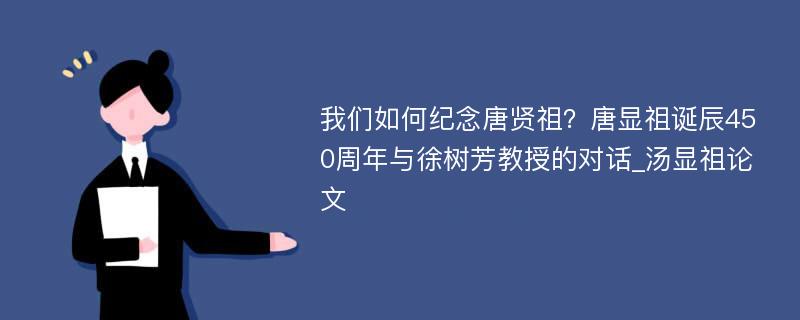
我们该如何纪念汤显祖?——汤显祖诞辰450周年与徐朔方教授对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朔方论文,汤显祖论文,诞辰论文,该如何论文,教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邹:今年是汤显祖诞辰450周年。 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历史事件”。之所以说是“历史事件”,是因为中国戏曲自汤显祖“临川四梦”产生之后,留下了许多值得后人不断思考的问题。
徐:在新千年伊始我们该如何纪念汤显祖,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邹:对!我注意到几件特别有意义的事:一是按汤显祖原本改编的昆曲《牡丹亭》在美国纽约林肯中心上演,引起轰动(准确地说是引起争议);二是您重新校订增补的《汤显祖全集》出版;三是国内关于汤显祖的第一篇博士论文通过了答辩;四是《才子牡丹亭》的最早刻本(影印本)在美国被发现……
徐:还有几件事也值得注意:《牡丹亭》第三种英译全本将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又发现几篇汤显祖的重要佚文;《汤显祖遂昌诗文全编》由遂昌人氏项兆丰先生自费内部出版……
一
邹:关于《牡丹亭》全本上演成了这两年的新闻热点,也成了争议焦点。1998年初夏在上海上演了人们期待已久的55出全本昆剧《牡丹亭》,没料到立即遭到各方面的批评。同样让人关注的是,同年该剧在美国纽约“林肯中心艺术节”(Lincoln Center Festival )上演的计划也被取消了。1999年仲夏,同一台昆剧《牡丹亭》在紧邻林肯中心的拉瓜地亚表演艺术学校演出大厅上演,可知情人都知道,虽然道具、服装及布景仍是一年前在中国精心制作的,但除了少数上海昆剧院的艺术家之外,整个演员阵容已非原班人马。而从大洋彼岸反馈回来的演出评价也与国内的批评形成鲜明对照。排除其它复杂因素,我以为这种在《牡丹亭》400 年演出史上奇特的两班演出人员在中西两个舞台上所产生的两种不同评价,从根本上反映了中西戏剧观的差异。
徐:是这样。从表面上看,“导演”两班人马演出《牡丹亭》的是在中国唱过花鼓戏的36岁的美籍华人陈士争先生,而事实上,这出戏从最初的构想到制作上演都是由西方人和按西方人的艺术感受方式来运用的。1996年初,林肯中心艺术节导演约翰·洛克威尔(John Rockwell)对陈士争先生提及他对汤显祖的巨著《牡丹亭》很感兴趣,他希望能将这出戏完整地搬上美国的舞台。很显然,他需要有十多年戏曲舞台表演经验,又有近十年在美国演艺界导演和制作经验的陈士争先生的帮助。1997年他们两人到中国实地考察经常上演《牡丹亭》折子戏的昆剧团,并拜访了我和其他一些专家、学者。
邹:您1956年完成了《汤显祖年谱》,1959年完成了《牡丹亭校注》,1962年完成了《汤显祖诗文集编年笺校》。 仅《牡丹亭校注》自196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以来,前后四次印刷就高达26万册。您作为国内外汤显祖研究的权威,一定会对洛克威尔和陈士争先生想把《牡丹亭》全本搬上美国舞台感到高兴。
徐:是的。虽然《牡丹亭》在1933年和1935年就由中德人士合作分别在北平和上海上演过,但当时经北京大学德文系洪涛生教授( Prof.Q·Hundhausen)译为德文的《牡丹亭》只是其中的几出戏文。 上演的大概也就是《劝农》、《肃苑》、《惊梦》等这些折子戏。而美国人却要按《牡丹亭》原本上演,这无疑是令人高兴的事。直到现在我也这么想,林肯中心艺术节上演全本《牡丹亭》,对于保持这部旷世杰作的完整性和扩大它的影响范围都具有空前的意义。的确,昆曲象这样规模的演出已经有几个世纪未见过了。不过话又说回来,我并不知道这些人会如何将中国400年前的剧作搬上美国舞台, 他们从我这儿离去后就很少有消息。当然,我也听到一些传闻,但直到最近接到一位在美国的朋友给我寄来的林肯中心艺术节1999年7月份的戏单, 我才知道了他们的一些想法。
邹:我看了这份装帧讲究的戏单,它主要以介绍与上演《牡丹亭》有关的背景材料、导演阐述、演员、音乐以及您和周育德教授的文章为主。我让我的一个研究生将主要内容都译了出来,我作了审校,近两万字。从这份戏单上所披露出的信息看,美国艺术界和中国艺术界对如何面对艺术遗产的态度是有很大差异的。林肯中心艺术节导演尼格尔·瑞登(Nigel Redden)在“欢迎词”中也坦率承认,有关这次演出的一些争论, 的确显示出对于舞台艺术与真实性是有不同的观念(differingconcepts)存在的。他所指的不同观念“争论”就是1998年《牡丹亭》全本在沪上首演所引起的中国艺术界的不同看法。瑞登对1998年《牡丹亭》上海全本演出的态度显然代表了美国方面的一致看法:上海昆剧院的艺术家克服了上演全本《牡丹亭》的各种障碍和困难,已经充分展现出了这部汤显祖写于400年前的名剧的深度(depth)。可沪上一家大报发表的署名文章却不这么看。文章认为这个用西方的视角,去迎合那种对东方文化的浅层猎奇(实际上是故意去展现过去的落后)的搬演,缺乏一种文化和历史的双重准备,变成了一种仪式、一个热闹的炒作。这篇文章的立意显然也是基于东西方戏剧观的差异,用文中的说法就是将中国古典名剧搬演到美国舞台上是否体现了中国传统戏曲中最根本的艺术精神。以这种标准来衡量,《牡丹亭》的上海全本演出则是在一种理论上毫无准备的状态下,去重新解读它的,因而读到的只能是一些浮光掠影的东西。这是其一。其二,从舞台的二度处理来看也捉襟见肘。导演试图用一种现代戏剧观去还原古典艺术的原生态,用开放式的舞台去承载最古老的表演。可是,二度语汇的过分渲染对传统昆曲的艺术品格形成了伤害。导演想要破译历史文化,展现时代氛围,希望展现给观众一幅“清明上河图”式的文化图景。可是,在整台戏中昆曲的本体色彩被淡化了,留下的只是一个文化空壳,里面充斥着种种古风、曲调、世俗、服饰和建筑等等民俗大观式的不厌其烦的展示,因而有人称之为“大杂烩”,隐含着对其整体定位不明的批评。文章还提出了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即《牡丹亭》是否只有折子戏有艺术价值,而演全本则意义不大。按文章的说法,《牡丹亭》在历史上鲜有全本演出是有其深刻的历史和文化原因的。而数百年来象《游园惊梦》、《拾画叫画》等折子戏经历代名家演绎,已形成几乎完美的表演形式,久演不衰,也被公认为是《牡丹亭》的艺术精华,其崇高地位已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某种象征。这就是它的艺术价值,它是文化的积淀,是历史的选择。
徐:《牡丹亭》全本少有演出,原因固然有许多,比如冰丝馆本《牡丹亭》就是进呈给皇帝看的,凡剧中所谓“碍语”都删掉或改写(《虏谍》、《围释》全删,《淮誓》个别句子删掉,《牝贼》中[北点绛唇]、上场诗被改写等)。又如因“填词太长,本难全演”为由而加以改窜,硕园改本变原本五十五出为四十三出,冯改本为三十七出,臧改本为三十五出等。但关键的问题恐怕还在于《牡丹亭》是大诗人的大手笔,“非知音,未易度也”。这一点汤显祖在世时就已感到悲哀:“伤心拍遍无人会,自掐檀痕教小伶。”当然,这不专指演出而言。之所以“伤心”,并不仅仅指象《审音鉴古录》批语所说的“最难于排演者,如《寻梦》、《玩真》”这些单折戏,而在于“小伶”对全剧的主旨并不领会,即汤显祖说的“人知其乐,不知其悲”。因此,只有了解全剧,才能真正认识汤之“曲意”。我们不能脱离全剧而割裂地指认某折某出就为《牡丹亭》之精华。过去不具备全本演出的条件(演员的、场地的、照明的、观赏的等等诸多困难),并不能说明折子戏之外的戏就非精华,折子戏就一定是“历史的选择”,就一定是《牡丹亭》全部的“艺术价值”所在。
邹:我同意您的看法。汤显祖曾说:“知音常苦稀。”我们只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将《牡丹亭》全本搬上舞台,才有可能真正成为汤翁的“知音”。断简残篇是难以窥其郁郁乎之美文的大端的。汤翁在世时就被留都南京太学国子监祭酒戴洵称为“千秋之客”,这是就汤翁的整个生命存在的气象而言的。《牡丹亭》作为汤翁生命历程中的颠峰之作,正可视作他生命辉光气象的全景投射。只有完整地演绎这部旷世杰作,才能真正领悟汤翁无论是其生命境界,还是其艺术创造的真际。不然,“千秋之客”岂不千秋无对乎?
徐:当然,将全本《牡丹亭》搬上舞台不是件容易的事,尤其是搬上西方舞台,面对当代的西方观众。这里自然就存在着与面对中国观众很为不同的处理方式。陈士争先生与约翰·洛克威尔的想法显然是与中国的戏剧观相去甚远的。他们是想将西方关于文本完整性和演出真实性的观念注入主要通过口耳相传而延续的东方戏剧表演风格中。他们一方面认为中国戏曲是世界戏剧的瑰宝,但另一方面又认为在20世纪仍保留下来的戏曲表演传统不足以表现它的影响力或潜力。本来,任何一次排演都是一种新的诠释,是对传统的重新发现,导演按照自己的理解注入自己的意念也无可厚非。但是,任何一种诠释却不能置传统于不顾,甚至象陈士争先生所认为的那样,表演传统也是多余的。这就涉及到对一种文化艺术传统的根本无视和任意割弃的问题。比如中国戏曲并不以真实性的表演为特征,舞台是一个假定的空间。但导演却在舞台上的亭台楼阁制作上下大功夫,由十三位熟练的木匠用木雕手法并按中国典型的建筑技巧加以精细制作。而在表演的过程中,舞台上同时展示演员化妆、换服装、伴奏者的在场及道具、布景的操作过程等这些通常观众看不到的活动……很显然,这是一种自然主义的真实观。这种表现方式有一个很大的危险,即并没有让西方人了解东方戏曲艺术的真正魅力。
邹:这种危险实际上是存在的。在美国演出时舞台前面甚至出现了一个荷花水池,水面上有几对真的鸳鸯和鸭子游来游去,水边树上还挂着鸟笼。鸭子和鸟儿时不时叫上几声,与演员唱腔相呼应。据称这种西方当代舞美设计中最时髦的“发生学”方式临场效果非常好,得到了美国媒体和观众的认可。这就更让人疑惑究竟是什么东西在“引人入胜”了。
二
邹:与《牡丹亭》全本上演闹得沸沸扬扬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先生您却不声不响地推出了新版《汤显祖全集》,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
徐:不要这么讲。这家古籍出版社业务较新,技术力量薄弱,电脑排字,错误较多,达140多处。严格说来, 这个本子是不能留传后世的,但要出订正本恐怕就不知是新世纪何年何月的事了。另一方面,我自己的疏漏也相当多。所以古人说校点一部书不免有终身之忧。现在,我算是相信这句老话了。
邹:我注意到新版《汤显祖全集》是由您一人笺校的,而1962年版《汤显祖集》则是您笺校汤氏诗文集,钱南扬先生笺校汤氏戏曲集。在读了您写的新版“编年笺校汤显祖全集缘起”文后,才知原版洵是一部“奇书”。
徐:有那么一点。1962年的《汤显祖集》,前一年约稿,限定次年出版。我以晚辈身份和钱氏并列,并由我撰写全书《前言》,钱氏不会感到高兴。钱氏《汤显祖戏曲集校例》所说“汤氏尚有酒、色、财、气四剧,今佚”以及他的《后记》所说《牡丹亭》吕家改本就是毛氏汲古阁《六十种曲》本的吕硕园改本等等失误,我也无法同意。按,硕园改本的编者不姓吕。据该剧明刻本序,编者姓徐名日灵,一作日曦,西安(今浙江省衢县)人。见《西安县志》卷二十五。我和钱先生的另一分歧是汤显祖剧作的腔调问题。他的论文见《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1963年第2期,拙作原刊《戏剧论丛》1981年第3期。两人的合作全凭上级的意志,实际上是各管各的,互不通气。拙作《汤显祖集前言》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之后,出版社来信告诉我,“中央负责同志”看了之后不满意,必须修改。我回信说我只能在重新研究以后才可以修改,怕他们急于出版,不能等待。他们又来信告诉我可以参照侯外庐最近发表的汤显祖论文加以修改。侯外庐是当时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多卷本《中国思想通史》的主编,而我当时是不到四十岁的一个讲师。侯氏的论文写得似乎很漂亮,但他引用的汤氏诗文以及对诗文的诠释往往违背原意,无法令人信服。为此我写了一篇批评文章《关于南柯记第二十四出〈风谣〉及其它》,发表在1962年2月18 日的《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上。我答复出版社,根据百家争鸣的原则,我不能按照侯外庐的观点进行修改。权威不可触犯,而编校者的意志也不能随意践踏,亏他们想出一个两全之计,侯和我的两篇《前言》同时采用,都排在卷首。1966年开始的十年动乱结束之后,我写信给那位“中央负责同志”,指出《汤显祖集》采用两篇彼此矛盾的《前言》是出版史上没有前例的事件,我要求得到纠正。果然,后来《汤显祖集》不再按照原样出版,而是分成《汤显祖诗文集》和《汤显祖戏曲集》分别出版。这样就可以删去侯外庐的《代前言》而不至于使他感到不被尊重。据“四人帮”控制下的报刊的揭露,“中央负责同志”指当时中共中央宣传部周扬副部长,他通过前杭州大学林淡秋副校长告诉我同意我的要求。他们和当时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今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前身)李俊民所长都已作古,但是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遵照“中央负责同志”的意旨给我的来信应该归档,万一不归档,当时《光明日报》批判周扬副部长的论文可以作证。十年动乱之后,副部长为本书落实政策的努力令人赞赏。
邹:这恐怕在书籍编校史上也算是“奇闻”了,它也从反面说明《汤显祖全集》应予重新编印的必要。新版《汤显祖全集》在内容上有什么主要特点呢?
徐:除了将汤氏的尺牍重新编排,其可考者都作简单说明和订正过去的错解外,新增了一卷过去没有发现的汤氏的制艺,以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所藏涌泉堂刊本万历癸未《海若先生文》(一名《汤海若先生制艺》)为底本。这是我一二十年前在北京图书馆找到的,但一直没有公布过。这卷制艺共五十五篇,其中《大学》五篇,《中庸》十二篇,(《论语》)“上论”十篇,“下论”八篇,(《孟子》)“上孟”十一篇,“下孟”九篇。
邹:这种“四书之文(‘四书’即《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原于经义,创自荆公”。即由宋仁宗嘉祐朝的王安石创立,王安石正是汤显祖的同乡。到元代,八股文考试程式分为蒙古色目人和汉人南人。后者第一场明经、经疑二问,从《大学》、《论语》、《孟子》和《中庸》内出题,并用《朱氏章句集注》复以己意结之,限三百字以上。后世虽稍有更易,而其大要,俱仍旧制。汤显祖这一卷制艺大体也是这个面貌。这新一卷的增加,将对我们更加全面地了解汤显祖起到重要作用。
徐:的确如此。汤显祖虽以《牡丹亭还魂记》而闻名于世,但他又被清代赵吉士的《寄园寄所寄》列为举业八大家之一。他的没有脱尽稚气的《问棘邮草》中的一些诗,曾使老诗人徐渭为之倾倒。他对前后七子的批判以及他的一些小品文创作比袁宏道早了将近二十年。然而我们应该看到他是理学家罗汝芳的弟子。而罗汝芳则是泰州学派的创始人王艮的三传弟子。东林学派的巨子顾宪成对汤显祖的直率批评心悦诚服。另一位巨子高攀龙读了汤显祖的一些理学著作后颇感意外,说“惊往日徒以文匠视足下,而不知其邃于理如是”。我想,汤显祖如果不是文名太盛,黄宗羲很可以在《明儒学案》中为他立下专门的章节。可惜过去一般论述汤显祖时很少注意及此。最近读到你的大作《汤显祖的情与梦》,感到你在这个问题上有新的突破,特别注意到汤显祖的这些论著,并且作了深入的探索。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大言不惭,我觉得你的大作正好作了拙著《汤显祖评传》的最好补充。当然反过来也可以这么说。不知道你会不会对此介意。
邹:先生奖掖后学,实不敢当。我之所以在拙著中注重分析阐释汤显祖的理学著作,包括他的时文,倒不仅仅因我是研究哲学的,有一种先入之见的哲学眼光,而是在仔细研读了汤氏的全部著作后,发现汤翁并不仅仅是一个戏剧家,虽然作为伟大的戏剧家他是被世所公认的。当汤翁在世时人们就已经不仅仅把他视作戏剧家而论,明万历年间的“学官诸弟子”之所以“争先北面承学”于他,就因为他们认定汤义仍“所繇重海内,不独以才”。即他不仅仅有诗赋灵性、艺术天才,更重要的是有思想,而且其深邃广博为一般学官“闻所未闻”,以至“诸弟子执经问难靡虚日,户屦常满,至廨舍隘不能容”。这都是事实。过去学界最关注的是汤翁的“情”论,而且从明中叶以降的文艺、戏剧理论也确实是围绕着汤翁的情论在转。可问题是“情”之命题并非创发于汤显祖,为何汤翁提出后却有如此大的影响呢?这里有一个关键问题是不能忽略的,即汤翁之“情”论是基于他深刻的理性思考的,是与过去的“情”论有区别的,的确有超越时代处,不然,它是不会也对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想家如黄宗羲、龚自珍、梁启超、严复,以及近代的陈独秀等思想家产生重要影响的。
徐:汤显祖与元明以来戏剧家的最大不同,正在于他是一个有着浓郁的思想家气质的艺术家。回避了这一点,对他的理解往往是不到位的。
邹:可惜,我写《汤显祖的情与梦》时您增加的这一卷我尚未看到,不然,还可以对这方面的探索作得更深入一些。这不仅仅指他的象《阴符经解》、《贵生》、《明复》等理学著作,也包括象《次九曰向用五福》、《策》第三问、《天下之政出于一》论等时文。他的一些没有引起学界广泛注意的赋,如《嗤彪赋》、《庭中有异竹赋》、《广意赋》等也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徐: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赋体和八股文对汤显祖戏曲创作的影响。他二十岁前后开始熟读梁萧统编集的《文选》。《文选》是从《楚辞》到汉魏六朝的一部辞赋诗文选集。据说整部书汤显祖都能一字不差地背诵。辞赋有助于八股文的精进,其骈骊辞藻,对仗工整,奇字难词,都对字、词、句的精炼、准确、脱俗有莫大的裨益。而偶句是作曲填词最常用的修辞形式之一,汤显祖在严格的辞赋、制艺训练中精于此道,自然对其戏曲创作也有莫大助益。
邹:汤显祖被誉为明清举业八大家之一,在过去看来似乎与汤氏成为传奇大家没什么关系,反是一种阻碍。其实不然。虽然我们不必尽信周作人所言“八股文是中国文学史上承先启后的一个大关键”,它“不但是集合古今骈散的菁华凡是从汉字的特别性质演出的一切微妙的游艺,都包括在内”,“它是中国文学的结晶”等等,但八股文也非历代都千篇一律、死气沉沉,尤其是“明人制艺,体凡屡变”,汤显祖所在的隆万间,更是“务为灵变”,其“穷思毕精,务为奇特,包络载籍,刻雕物情,凡胸中所欲言者,皆借题以发之”。方苞的这些看法或有夸诞处,但对汤显祖而言确乎如此。之所以慕名向其求教八股文之作法者会如此之多,以致他弃官回故里临川后,仍有千里之外浙江嘉兴的许重熙和湖广石首的王启茂前来求教,广东的钟宗望为耳濡目染,甚至携家小到临川一住就是三年,关键就是汤显祖不仅仅能给求教者一些八股文作法技巧,也不仅仅止于文章变化之一端,而在于他能将“时文字能于笔墨之外言所欲言”的整体生命气象和诗意地感知世界的方式昭示于人。
三
邹:去年(1999)6月3日,我国第一篇有关汤显祖《〈玉茗堂四梦〉与晚明戏曲文学观念》的博士论文,在北京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通过了答辩,这无疑是汤学研究中一件令人高兴的事。
徐:这的确让我感到欣慰。可惜得很,我带的博士生不少,而且就是元明清方向,可他们或修小说,或修诗文,就是没人修戏曲。戏曲太难,它的藏书北京、上海、南京为多,杭州只有一些一般的古书。
邹:先生培养的博士生虽然没有研究戏曲的,尤其是没有研究汤显祖戏曲的,这虽然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但现在我国毕竟有了第一位“汤学”博士,而且他也是在包括您在内的许多汤学专家所奠定的学术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应当引为中国汤学界的共同骄傲。我在拙著《汤显祖的情与梦》的结语中曾特别提及一件憾事,即日本、德国、美国和前苏联对汤学的研究走在了我们前面,1974年汉堡大学博士论文《汤显祖的四梦》出版,1975年明尼苏达大学博士论文《邯郸梦记的讽刺艺术》出版……可目前国内尚无一部汤显祖研究的博士论文出版。没想到我的这个遗憾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就消除了。周育德教授去参加博士论文答辩时就是带着我这本书去的,他第一句话就是讲我的遗憾已成为过去。尤其让人高兴的是,这位叫程芸的博士才二十八岁,曾在我们武汉大学郑传寅教授门下研读戏曲文学达七年之久,在打下了比较扎实的功底后考入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成为邓绍基研究员的博士生的。
徐:我一向觉得中国古典文学,尤其是戏曲文学领域外国人是很难进入的。我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时也注意到西方学者对中国戏曲的研究,包括博士论文。但多不可征引,也完全不必迷信。因为即便是作为一个中国人,要想真正进入中国古典文学,尤其是极为繁难的戏曲文学领域,没有个十年、八年的基础准备和学术积累,也是难有所见解的。现在相当一些青年人耐不住这个学术积累的寂寞,什么容易,什么出名快就选什么作研究方向,这很不利于学术的发展。
邹:从程芸博士的论文看,他是勤于读书,也是善于思考问题的。这篇论文的最大特点就在于不是泛泛谈论一些人所共知的史实,而是抓住汤学研究中的一些颇有争议的焦点问题展开论析,从中提出自己的看法。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针对包括您在内的汤学专家(包括古代的)提出的问题进行商量辨析。
徐:我注意到学界对我的看法的各种意见。其实1962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的《汤显祖集》中我关于汤显祖《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的笺注是经过深思熟虑而写下的,至今我仍坚持我当初的看法,即“四梦”原不为昆山腔而作。为什么?因为当时水磨调盛行,地方戏为士大夫及传奇作家所不齿,汤氏乃特立独行,宁拗折天下人嗓子而不顾,以其一代才华为江右乡音俗调,不勉强为吴侬软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指责汤翁、改编汤翁剧作的人,如沈璟、臧懋循、冯梦龙都是吴人,他们说汤“生不踏吴门”,所以其词才会“屈曲聱牙,多令歌者乍舌”。说起来令人奇怪,他们精于昆曲,却对《琵琶记》和早期南戏的曲律知之甚少。他们以为汤显祖的用韵是江西人的土腔,其实在早期南戏里早就存在,虽然,它们的作者不是江西人。所以,他们改编“四梦”就是变宜黄为昆山。其实,汤翁曲词不协律处原为便宜伶,而不便吴优也,协宜黄之律而无意协昆腔之律也。汤氏曾说:“不佞生非吴越通,智意短陋。”又说:“不佞《牡丹亭》记,大受吕玉绳改窜,云便吴歌。”都可证“四梦”本非为昆曲而作。
邹:我注意到您1981年在《再论汤显祖戏曲的腔调问题》一文中所作的进一步申论:“汤显祖是否以昆曲作为他剧作的唱腔,至少是疑问。”而这个结论恰恰成为程芸博士论文的起点。他在认同您的这个见解的同时,花了四万字整整一章的篇幅,试图阐述以下两个看法:一、汤氏“四梦”中留有受晚明昆腔唱曲影响的明显痕迹,“宜黄腔”如果存在的话,徐朔方先生对其“乡音俗调”的定性可能有失片面;二、晚明曲家对汤氏“四梦”“失律”的指责并非以“昆腔曲律”相衡他种声腔剧种作品而得出的观察结果。
徐:我非常欢迎年轻的学者能对我的意见提出不同看法。
四
邹:“临川四梦”的版本从明刻本到现在非常多,粗略统计约七十种,仅《牡丹亭》从万历金陵文林阁刻本,到1963年您和杨笑梅校注本就有二十六七种之多。其中一些版本只有善本、孤本,除了简单的记载,学界长期不知其真面目。比如笠阁渔翁刻本《才子牡丹亭》,我们只知“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藏。不分卷。书名标作《才子牡丹亭》,首载笠阁渔翁《刻才子牡丹亭序》”等文字。有意思的是,关于《才子牡丹亭》我们知之甚少,而附刻于该书内的《笠阁批评旧戏目》却因被编入《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而引起研究者注意,但《戏目》作者笠阁渔翁是谁,《集成》编者却谓“不详何许人”。1986年出版的《汤显祖研究资料汇编》,编者毛效同根据《太平乐府》(又名《玉勾十三种》)、《笠阁丛书》、《西青散记》及《才子牡丹亭》批语内容,推论笠阁渔翁即吴震生。又据《西青散记》及《才子牡丹亭》批语,推知《批才子牡丹亭序》为吴震生之妻程琼所作。1987年徐扶明先生出版了《牡丹亭研究资料考释》,认定《才子牡丹亭》,亦名《笺注牡丹亭》,今存有清雍正年间刻本,另有乾隆二十七年刻本。但对笠阁渔翁仍说“不知何许人,待考”,并附有吴晓铃先生给他的信:“此书系两层楼本,上层特长,似高头讲章。其评语极奇,皆联系到‘二根’。如‘迤逗的彩云遍’,评曰:‘彩云二字分开:彩云、肉彩;云,鬓云也。’”
徐:吴梅在《瞿安读曲记》中就提到此书,谓“得批本《牡丹亭》,为清代禁书。所有曲文,皆作男女亵事解。而博综群籍,并书名亦有未知者,可云秘本。阅《牡丹亭》批本,奇诡不可言喻,仅《言怀》、《训女》两折,已匪夷所思,而征引内典,又极精博,洵是奇书。封面书钱塘袁枚子才氏评,恐是假托。余意此评本,或王仲瞿、龚定庵一流人手笔,负才好奇,故作秽亵语,以矜多识。若以笠阁渔翁四字,遂谓李笠翁作,吾知笠翁无此才识也。”
邹:由吴梅、吴晓铃之语可知此书的确是奇书,奇在以独特视角加以批注。批者才识卓异,而且博综群籍,非“淫秽”二字所能涵盖。这些特点近日被您访问台湾时见过的华玮博士的新发现和深入研究得以证实。首先是版本。华博士在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校区东亚图书馆最早见到《才子牡丹亭》影本,经与“北图”、“上图”版本比较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三个版本当系同一个版本。但差别较大,柏克莱本为最早,初刻很可能在雍正年间。乾隆二十七年重刻此版本,印刷时加了题有《乾隆壬午年镌、笺注牡丹亭、本衙藏板》之扉页。这可能是“上图”本的来源。其后,《笺注牡丹亭》又有人增刻了部分,成为今日“北图”本的面貌。而吴梅所见的版本,从“封面书钱塘袁枚子才氏评”看,《才子牡丹亭》在雍正刻本、乾隆二十七年重刻本之外,当另有别的刊本存在。其次是作者。毛效同虽指明此书为吴震生所作,并也指明吴妻程琼写了序,但未加论证。赵山林教授《中国戏剧学通论》大概也据毛说认定安徽歙县人吴震生刻印了《才子牡丹亭》,并说“其妻程琼参加了笺注、评点,也发表了一些可取的见解”。但惜未加论证评说。华博士则将乾隆进士史震林的《西青散记》的相关记载与《才子牡丹亭》加以仔细对勘,以充分的证据断定此书之《牡丹亭》批注部分,确为程琼与吴震生合作,而附录之《戏目》,则大抵为吴震生一人完成。其三是内容。此批本虽然是为满足妇女读者需求而作的《牡丹亭》评本,而且对各出曲文或宾白中许多字辞特意标出引为意涵“性事”或男女“二根”的批语,使此书部分犹如色情辞典,但此书又决非能以“色情”读本涵之。从序中可知,作者的著书“本愿”是“借《牡丹亭》上方,合中国所有之子、史、百家、诗词、小说,为糜以饷之”。因此,其包罗万象,博涉经籍,除子、史、百家、诗词、小说外,还包括理学、佛老、医学、风俗、制度等各方面,俨然中国文化百科全书。且字数超过三十万,远远超出正文,颇有喧宾夺主之势,在戏曲评本中十分独特。从批注视角看,全然摆脱了道德评价模式,而是透过人性自然需求的层面反复辨析情色难以抹杀之理,并解析才、色、情三者之间的错综关系。
徐:看来此书对拓展研究《牡丹亭》的思路将有重要价值。
邹:的确如此。但研究此书困难重重。首要的是此书不易得。我在“上图”善本室见到此书,一如华博士所说的是“乾隆壬午年镌”版本,共八函。一如吴晓铃所说,是两层楼本,上层批注部分几占全页的三分之二强。我粗略计算了一下,全书仅批注部分就约35万字。如欲将此书复制进行研究,需花费重金。有版本保护的原因,也有部分创收的因素,甚至后者的人为因素更重。因而,布衣书生,只能望书兴叹。虽然明知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但部门所有的体制,学术只能困顿停滞。
徐:这也是古典文学研究普遍存在的问题,奈何不得。
五
邹:前边您曾提及,1933年《牡丹亭》被译成德文,并由中德人士合作在北京和上海上演。其实1933年洪涛生所译的只是《肃苑》和《惊梦》两折戏。而早在1931年,洪涛生就已与Dr.Chang Hing 合译了《劝农》一折。1935、1936年洪先生又分别译出了《寻梦》和《写真》两折。到1937年《牡丹亭》才全本译成德文,分别由苏黎世和莱比锡拉施尔出版社出版,书名译作Die Rückkehr Der Seele Ein Romantisches Drama。比德译本要早的是日译本。 宫原平民译注的《还魂记》收入《国译汉文大成》文学部第10卷(1920~1924),铃木彦次郎和佐佐木静光合译的《牡丹亭还魂记》收入《支那文学大观》(1926~1927)。另有1933年徐仲年译的《惊梦》一折法译本及孟烈夫的俄译《牡丹亭》片断。1931年出版的青木正儿的《中国近世戏曲史》首次在国际视野中将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相提并论:“显祖之诞生,先于英国莎士比亚十四年,后莎氏逝世一年而卒(此处有误,当是同年而逝),东西曲坛伟人,同出其时,亦奇也……汤显祖不仅于戏曲上表现其伟大,即其人格气节亦颇有可羡慕者,谱之入曲固为吾党所快者。”如此之高的评价,可知青木正儿是读过“临川四梦”的。
徐:《牡丹亭》的英译本据我所知最早是在1939年,哈罗德·阿克顿译有《春香闹学》一折。全译本最早是在1980年,由美国印地安那大学出版社出版, 译者是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莱分校)的褒奇(CyrilBirch)教授。我惊叹于他的细心,他连曲牌名都加以意译。 但是令人大惑不解的是《牡丹亭》的女主角杜丽娘译成了Bridal Du (杜新娘)。以我浅薄的汉语知识而论,“丽娘”一词和新娘毫无关涉,也许我只能责怪自己想象力太贫乏。1994年中国科技大学张光前教授也在国内出了一个英译本,它不失为补偏救弊之作。当然,作为母语是汉语的张教授,其英语可能不及褒奇那么道地。最近,我有幸拜读了大连外国语学院汪榕培教授的新译本,自然地我想起一句中国的老话:“后来居上。”坦率地说,在我狭小的外语界接触范围内,还没有发现像汪先生那么精通古代文史的学者。
邹:汪教授并不仅仅满足于做一个翻译家,而是要成为一个中国古典文学的独特阐释者。为了翻译《牡丹亭》,他“伏案三四载,两鬓又添霜”。他还亲自去汤显祖的家乡考察了一番。所以,读他的几篇有关《牡丹亭》译后感的论文,感到颇有启人之处也就不足怪了。其中一篇谈《杜丽娘的东方女子忧郁情结》,从女子为性欲和爱情而产生的忧郁情结是中国诗歌的一个永恒主题的大背景上,来看杜丽娘作为典型的封建时代青年女子的忧郁情结特征,认为这种忧郁情结从《诗经》开始就在中国文学中反复出现、不断加深,《牡丹亭》则是我国戏曲中表现这一忧郁情结以及表现如何冲破这一忧郁情结的一个高峰。文中还将杜丽娘的忧郁情结与莎士比亚《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朱丽叶的忧郁情结加以个案比较研究,结论是东方女子的忧郁情结较西方为烈,杜丽娘的忧郁也超过了朱丽叶,原因在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表现在艺术上就构成了中国文化所特有的“伤春”意象。汪教授的另一篇文章是关于《〈牡丹亭〉的“集唐诗”及其英译》。这是一个挺有意思的课题。
徐:《牡丹亭》每出下场诗都袭用唐诗七言成句,而又和剧中情节融合无间。可能这是多余的奢侈之笔,多半无助于作品的提高。然而要做到这一点,却远不是容易的事。曹寅主编的《全唐诗》是1706年才完成的,而《牡丹亭》写于1598年。即使当时有其它《全唐诗》存在,也必定要熟读成诵才能这样断章取义而又运用自如。“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说明高度的文化和文学修养对作家的成长何其重要。然而“无一字无来历”之类的文人习气却又可以使博学成为作家的桎梏,不利于创作。汤显祖在这一点上也未能例外,但是权衡得失,毕竟利大于弊。
邹:的确是这样,汪教授的具体分析最具说服力。他在赵山林教授研究的基础上对《牡丹亭》中根据三妇评本标注唐诗作者的69首276 句(54首以“集唐诗”形式出现的下场诗和剧中的15首“集唐诗”)进行全文检索,结果发现,在《全唐诗》中没有找到的只有3句。 其中两句在下场诗中,第二十七出中的“欲话因缘恐断肠”(天竺牧童)和第三十五出中的“随君此去出泉台”(景舜英);一句在剧中,第五十二出中的“错把杭州当汴州”(林升)。林升是南宋孝宗时人,“错把杭州当汴州”取自宋人绝句,不属唐诗。剩下的两句唐诗则有待学界破解出处了。
徐:……
邹:汪教授还发现了几个问题,一是三妇评本给几句下场诗所注的作者与《全唐诗》的记载有出入,二是下场诗的“集唐诗”文本及剧中“集唐诗”的文本有约四分之一与《全唐诗》的记载有出入。原因是多方面的,有通假字或异文存在,也有汤显祖根据剧情需要而改动的。下场诗是中国古典戏剧的程式,在注重间离效果的戏曲中往往起着画龙点晴的作用。然而对这些“集唐诗”的翻译却让汪教授困难重重,占《牡丹亭》全剧篇幅不到百分之一的集唐诗翻译花费的时间最多,改动也最大。
徐:说到翻译,我觉得真是烦难。以在翻译界享有盛誉的萧乾和文洁若夫妇合译的乔伊斯的意识流小说《尤利西斯》为例,居然在译文中出现“龟甲眼镜”一词。原来在英语中,龟、鳖、玳瑁都是一个词,这“龟甲眼镜”肯定是“玳瑁眼镜”的误译。当然,这只是简单的一种误译。翻译古代作品,难在整个中西文化背景的不同。例如,“梅”译成plum似乎不成问题,然而我在美国吃的plum却无法与梅子认同。梅子、梅花在汉语中所包含的早春或孤高的联想,在英语里是没有的。但是,如果一一加注,我想是很难找到有这样耐心的读者的。汪先生将《惊梦》译为An Amazing Dream信而且达,但在这里实有An Interrupted Dream的意思,近乎意译了。春香取镜台和衣服回来的上场诗说:“云髻罢梳还对镜,罗衣欲换更添香”,用的是唐诗成句。汪先生译为:
Face the mirror when her hair is done,
Add the perfume to the gowns with fun.
前一句信、 达、 雅兼备, 可是我不知道国外读者看了Face the mirror能否理会她虽已妆成,犹觉不放心的感情。 第二句却和原意完全不同了,虽然fun与done协韵是它的好处。
六
邹:汤显祖究竟有多少诗文,这一二十年来随着新的诗文不断被发现似乎越来越难以确定了。1973年上海人民版《汤显祖集》,您在第五十卷补遗了30篇诗词文赋、尺牍、时文,另存目7篇。1986 年上海古籍版《汤显祖研究资料汇编》,毛效同先生收录散佚作品61篇,其中四篇疑为伪作。
徐:我在1998年北京古籍版中除了增加“制艺”整整一卷外,在补遗中另收了诗、文、尺牍、赋、制艺44篇,其中汰去1973年上海人民版收录的七篇:《玉茗堂批订董西厢序》、《艳异编序》、《秋夜绳床赋》、《董解元西厢题辞》、《与汪昌朝程伯书登鸠兹清风楼联句》、《千秋岁引》、《坐隐乩笔记》。增补了佚文十篇:吴书荫教授提供的《溪山堂草序》;龚重谟先生《汤显祖佚文辑注》所收的《华盖山志序》、《黄太次诗集序》、《怀鲁公传赞》、《蕲州同知何平川先生墓志铭》、《何母刘孺人墓志铭》;单松林、程章二先生所辑的《叶梦得像赞》、《题叶氏重修家谱序》;纪勤、松林二先生所辑的《房州尉克宽公像赞》;另有一篇汤翁为老师何镗编《游名山记》所作的序文。这篇名为《名山记序》的序文,江巨荣教授曾撰文加以辨证,可以肯定是汤氏所作。
邹:还有遗漏,如《范濂郑公神道碑》、《故太王事獯鬻勾践事吴》等。
徐:最近江巨荣教授又发现《皆春园集叙》一文。
邹:江先生日前寄给我他新近发现的另一篇汤显祖佚文《虞精集序》。我细读了原文和江先生很有说服力的考证分析文章,可以断定是汤氏的佚文。江先生还告之,另有一篇汤氏佚文在报刊编辑手中待发。由此可推测,还会有汤氏佚文被发现。我觉得,除了发现新的佚文,对已发现的汤氏诗文的甄别认定也是很重要的,比如毛效同先生选录的汤显祖《西厢记序》是从吴震生、程琼合撰的《才子牡丹亭》程琼所作《批才子牡丹亭序》中引录的。汤氏序曰:“余守病家园,傲骨日峭……兼喜浓文艳史,时时游戏眼前,或剪或裁,或联或合,欲演为小说而未暇。”这些话是与汤氏的实际状况相吻合的。您曾多次论及汤氏读过《金瓶梅》、《素娥篇》、《如意君传》等浓文艳史,并确证在汤氏剧作中留下了印记,甚至还引用了原文。由此看来,程琼批注《才子牡丹亭》并非是空穴来风,她是试图引申汤显祖内在隐秘的心理。程琼所引的汤氏《西厢记序》当是可信的。不知先生您如何看。
徐:……
邹:这些新发现的佚文对于更全面地理解汤翁的思想、他的交往对他的影响、他的人生复杂心态等都大有裨益。比如他思想的复杂性,在“儒俭”与“仙游”之间矛盾了一辈子,可他内在心理的主导倾向是什么呢?“儒俭”占上风。即一生都在梦想积极入世,建功、立业、“显祖”,甚至认为诗人也“诚不足为”,“吾所为期于用世”。《黄太次诗集序》所披露出的他的心迹多么直捷醒目!又比如我们很难将一个公认的明清举业大家的汤显祖与一个流芳千古的剧诗大家的汤翁联系在一起。过去学界对他的研究常常回避他是举业大家这一事实,其实这恰恰是不太了解他的举业时文的作法是不同于同时代科场死读儒家经典之人的。“诸生迫学使者,不敢风流;为文词,所记《论语》诸书而止,有不记者焉。”可知他明确反对科考对思想的禁锢,提出要敢于“风流”,即重才情,重个性解放,重创造。《皆春园集叙》这一思想很值得注意。
徐:涌泉堂刊本万历癸未《汤海若先生制艺》虽都是万历十年作于杭州的八股文,但从评批者所指的应予汰除的“禅学中语”以及其它一些“疪谬”看,汤显祖总是偏离正统的八股文格范的。与其说汤氏是以遵循八股格套而称名举业,倒不如说是以其“风流”灵变使窒息人的八股文令人刮目相看而被推重的。
邹:他的八股文《次九曰向用五福》正是因其“有人不及处”的独特的创造性阐释,才被“高荐”为举人之“冠”的。他正是依凭“灵根”、“灵性”、“灵气”之“风流”才情,才能“委弃绳墨,纵心横意”,在“绳墨之外,灿然能有所言”。
七
邹:汤显祖在斗大遂昌县任父母官五年,“一以清净理之。去其害马者而已”,因而赢得万民爱戴,几百年来,口碑载道,颂歌遗爱。明清迄今,遂昌一直有不少人士热心于研究汤显祖。
徐:前边提到的新版《汤显祖全集》所增补的汤氏佚文《叶梦得像赞》、《题叶氏重修家谱序》和《房州尉克宽公像赞》等就采自遂昌县文联、遂昌县汤显祖研究会合编的《遗爱集》。
邹:在这些研究者中,有一些人与汤显祖有一种特殊的关系。比如作有《汤显祖年谱》(未刊)的王权先生,您50年代初曾到他家,甚为欣羡他庭前所种的远近闻名的玉茗树。
徐:王权先生的先祖王镃,是遂昌湖山人,南宋末年的爱国诗人,世代受到人们的尊敬。汤显祖曾为王镃的《月洞诗集》作了序。
邹:或许正因为有这一层历史渊源关系,王先生研究汤显祖达到了痴迷的程度,直到1998年以90余岁的高龄去世。又如项兆丰先生,多年来也致力于汤显祖研究,用他自己的话说:“风风雨雨数十年,至今穷老书生一个。”他节衣缩食,四处查询、搜集汤氏在遂昌的诗文,赶在纪念汤显祖离开遂昌四百周年及《牡丹亭》问世四百周年前夕自费编写内部出版了《汤显祖遂昌诗文全编》。书出来后仍未停顿。又发现了一些佚文佚诗,并感到《全编》注解有失当之处,为此,他去年春天又特地外出访书。回到家又对全书作了较大修订,增加了约两万字,决定重印。现在书稿已在印刷厂排印中,可五千元印刷费只筹集到一半。在紧张校对的同时,还要四处为钱求神拜佛。其情其景,令人感慨。
徐:有意思的是,项兆丰先生的先祖就是与汤显祖曾经有过纠葛的遂昌谏议项应祥。项兆丰先生对先祖与汤显祖的这一段特殊关系是非常清楚的。他既非常钦佩敬慕汤遂昌的道德文章、高风亮节,也对学界对其先祖项应祥的过苛评价有微言,认为他的先祖没有人们说的那么坏。这就涉及到如何评价历史人物的问题。在我看来,项应祥因征赋事件对汤显祖这个父母官怀恨在心,并对汤氏革职为民插了一手,这都是有历史文献可资佐证的。汤翁的《复项谏议征赋书》,项应祥的《柬汤明府》都记录在案。但这并不能因此就推断项应祥对初来乍到遂昌的汤显祖也是虚情假意。他为汤显祖撰写的《尊经阁记》是发自内心赞赏其父母官的。
邹:我同意您的看法。历史研究决不是简单归纳出一个逻辑结论,而是应探寻所下逻辑结论的前提为何。项、汤之介蒂虽“查有实据”,但亦要看到其“事出有因”。即回到事物本身来看,项应祥由赞赏汤遂昌到衔恨汤明府,这是不是历史的真实还是可以加以研究讨论的(近读项兆丰先生《汤显祖的弃官与罢职》、《关于汤显祖在遂昌的征赋》、《论“子不嫌母丑”及其它》等文章,感到学界对汤、项关系的评价恐有失当处)。即便都是历史的真实,恐怕也是属于人之常情的范围,并不一定就适合用人品人格的高尚卑劣等伦理道德标准相权衡。由此而反思拙著《汤显祖的情与梦》中对项应祥的评价,就有明显的情绪化色彩。再翻看最初读项应祥《平昌汤侯新建尊经阁记》的眉批,也多少带有先入之见的成份,缺少同情地理解。
八
徐:说到同情地理解,我想到如何看待汤显祖的死因以及汤氏与色情文学的关系问题。
邹:我知道您早写有一篇考证汤显祖死因的文章,结论是汤显祖死于梅毒。很显然,这篇纯学术性的文章学术界却难以接受。几年前出版《徐朔方集》时,唯有两篇文章以尊重出版社意见没有收入文集,其中就有汤显祖死因考证这一篇。这篇文章寄给京城一家权威杂志,也被退稿。道理似不言自明。人们不愿接受一个有损于汤翁高洁形象的事实,尤其对力倡“情至”论的汤翁来说,这样的死因对我们明清以来就极力褒扬的“情至”思想将是一个隐含讽刺意味的硬伤。
徐:最近,北京这家杂志打长途电话给我,说要将这篇退稿收回,可能要发表。其实,汤显祖死于梅毒,这并不是一件耸人听闻的事,在汤氏的时代,患梅毒而死也是常见的事。在汤氏交往的传奇作家中,屠隆就死于梅毒。屠长卿病重时,汤显祖寄给他十首绝句,《长卿苦情寄之瘍,筋骨段坏,号痛不可忍,教令阖舍念观世音稍定,戏寄十绝》。看了题目,令人失笑。但汤氏却不是中伤友人,那时并不认为这种风流病有损于人的品德。比如汤显祖的友人、《元曲选》的编者臧懋循,在万历十三年(1585)任南京国子监博士(教官)时,因和娈童游乐而被弹劾,罢官回乡。汤氏作诗《送臧晋叔谪归湖上》,其中说:“自古飞簪说俊游,一官难道减风流。深灯夜雨宜残局,浅草春风恣蹴毬。”汤氏不加忌讳,把友人的丑闻略加点缀,写进送行诗中。半个世纪之后,钱谦益《列朝诗集·臧懋循小传》引此诗后说:“艺林至今以为美谈。”现代人可能担忧这首诗会影响两人的友谊,而在当时竟成为佳话。因为社会风尚不同,这一点现在很难理解了。
邹:这就汲及到汤显祖个人的生活经历和对色情文学的态度问题。汤氏曾坦然承认:“吾前时昧于生理,狎侮甚多。”蓄妾、娼游这些当时士大夫的一般风习,汤氏也是染指的。汤氏二十岁时娶吴氏为妻;九年后,蓄赵氏为妾;又九年,娶傅氏为继妻。而按您的看法,这位十八岁的傅氏新妇本是妓女。汤氏对明代大兴的色情文学作品也是最早的阅读者之一。
徐:不仅仅是阅读,而且是欣赏的,这从他的作品中留下的印记可证。《紫箫记》第七出《游仙·前腔》[惜奴娇]说:“还笑,洞房中空秘戏,正落得素女图描。 ”此传奇完成于万历五年至七年(1577 —1579)。万历二十三年(1595)出版的《紫钗记》第二十五出《折柳阳关》,女主角霍小玉和新婚丈夫李十郎告别时预感到今后独寝的情景时说:“被叠慵窥素女图。”“素女图”即被美国印第安那大学金赛性与生育研究所誉为“镇山宝”的明版邺华生的《素娥篇》,它以武则天之侄三思与侍女素娥的艳情作为框架,着重描写行房的四十三种姿式,并配有插图与诗词对照。插图刻工黄一楷正是万历年间的著名工匠。它可能是明代流行的大同小异的多种版本中现今唯一的幸存者。《牡丹亭》第九出《肃苑》春香转述小姐的话:“关了的雎鸠,尚然有洲渚之兴,可以人而不如鸟乎。”最后一句话一字不改地来自《如意君传》。《如》是讲武则天和男宠薛敖曹的色情故事。据考证,这篇近万字的文言小说,当刊刻于正德年间。卷首甲戌秋华阳散人所撰《如意君传序》当是正德九年(1514),而卷末作跋之庚辰年,应为正德十五年(1520)。即汤显祖撰写《牡丹亭》时,这篇小说已流传了七八十年之久。
邹:我细细读了一下《素娥篇》和《如意君传》,发现几个有意思的问题。一是汤显祖爱用的一个词“骀荡”,在这两篇小说中都曾出现。现代汉语中“骀”有两读,读“骀(dài)荡”,指使人舒畅(多用来形容春天的景物),如春风骀荡。读“骀(tài)”则指劣马。而在古汉语中,“骀(dài)荡”则首先指“放荡”。《庄子·天下》曰:“惜乎惠施之才,骀荡而不得”(可惜惠施的才能,因放荡的行为而无所成就)。《如意君传》说:“一日,武后宴,坐融春园。覩风光骀荡,香色旖旎,落花结砌,飞絮霑衣,加以幽禽乱呼,雌雄相敌,蜂蝶侵花,差池上下,感物触情……”此处“骀荡”可解为使人舒畅,也可解为放荡。而《素娥篇》“见杨花之乱飘,感春风之骀荡,适有蝴蝶双来,激动热肠,遂作春风荡一诗以自见”。此处“骀荡”则为放荡意。汤显祖借鉴这个词,恐正是此词所具有的使情畅怀的“放荡”意。二是“牡丹”一词的暗喻性。过去对《牡丹亭》为何以“牡丹”名有过种种解释。但若从汤氏读过《素娥篇》的视角看,汤以“牡丹”名剧,当有所本、所喻。《素娥篇》第十二“推车进宝”就有“卸罗裳,绕遍园寻,拨动牡丹阴,牡丹心”之语。此处“牡丹”当喻指女性生殖器。由此再观程琼、吴震生批《才子牡丹亭》,恐正深得汤显祖之隐秘心理。程、吴正是特意标出“牡丹”喻“女根”。也由此,我们除了从一般政治的、社会的、伦理的角度看《牡丹亭》之外,似还有其它的诠释可能。三是前边提到的《素俄篇》“春风荡”一诗值得注意。“一春花事深无主……知音不逢负肮脏”的无奈心语,与《牡丹亭·惊梦》中“恰三春好处无人见……似这般都付于断井颓垣”的伤春情愫似颇有相通之处。
徐:以“放荡”之本意来解释“骀荡”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世俗以纵欲为尚,人情以放荡为快”。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象晚明这样纵欲放荡的朝代。街市上公开有“淫器”出售,彩色套印的《风流绝畅图》之类的春宫画到处流行,以至日常生活所用的“酒杯茗碗俱绘男女私亵之状”。且不说散文家张岱发表自己的享乐宣言,也不论大诗人袁宏道公开宣布“好色”为人生乐事,就连人们一向推崇的启蒙思想家李贽也将“好货”、“好色”与“勤学”、“进取”等并列,作为人所“共好而共习、共知而共言”的“迩言”。所以鲁迅说《金瓶梅》以降的晚明小说“间杂猥词”在当时“实亦时尚”。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汤显祖、屠隆死于梅毒,臧晋叔“好娈童”、“好美婢”,袁宏道“只愿得不生子短命妾数人足矣”,以维护风化自居的沈璟却有正宫套曲《白练序·咏美人红裩》这样的猥亵之作等,就算不上什么历史事件,这不过是晚明士风和文风而已。当然,对此一无所知,要确当地评价那个时代的文学和社会现象将是困难的。
邹:这确实涉及到如何实事求是地纪念、评价汤显祖的问题。我注意到您写的《汤显祖和〈金瓶梅〉》等文的看法,我觉得先生也有自相矛盾处:一方面先生承认晚明士风和文风“算不上什么历史事件”,但另一方面先生又说“惊梦”等出戏有“瑕疵”(“鲍老催”等)。既然是一种世风,汤显祖也就是合乎常情的存在者,也似乎谈不上他与屠隆、袁宏道等人相比要“正派、严肃得多了”。这是一种道德评价。而从世风时尚的角度,这种道德评价是失效的。这又牵涉到您所说的,汤之“标新立异,不在文字表面,甚至不在于艺术创作形式上的革新,而在于作品的精神实质”。这“实质”是什么?我觉得还是可以再考虑的。汤显祖不会有自觉的反封建意识;而道德评价的尺度在当时的世风时尚下也是失效的,至少是无力的;那么,杜丽娘抗争的意义就既不主要在政治层面,也不主要在道德层面。我觉得应象您所特别注重的那样,对历史要加以还原(以可能寻找到的蛛丝马迹),而不是以今人的眼光任意地加以“拔高”。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人物是不能超越他的时代的,因而他在他的时代也谈不上有“局限性”,他只能如此而已。
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