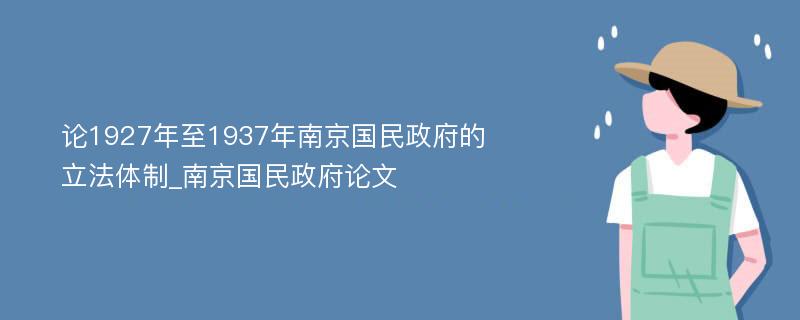
试论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的立法体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民政府论文,南京论文,试论论文,体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06)04 —0035—06
南京国民政府前期(1927—1937年),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党中央常会、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国民政府通过多种途径参与法律的制定,以保障国民党的意志在法律中得到体现,国民党在立法体制中居于重要地位,实质上也就是法从党出。这是国民党立法的初衷。目前,学术界对1927—1937年国民党立法体制的研究是一个空白点。研究南京国民政府的立法体制,有助于从政治制度层面深化和拓宽中华民国史的研究,因而也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本文拟对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的立法体制层次作初步探讨,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
南京国民政府训政时期,在中央一级明确规定以党治政。“本党对于政府,系以整个的党指导监督整个的政府。”[1] 训政时期的立法体制和国民党的以党治国有密切的联系。考察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立法状况,可以看到,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以及由国民党包办的国民会议都参与了立法,下文对此作一分述。
1.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的立法权
在训政时期,按照训政纲领的规定由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行国民大会的职权。关于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法律案,如《确定总理主要遗教为训政时期中华民国最高根本法案》、《确定训政时期党、政府、人民行使政权治权之分际及方略案》,都是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出的。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还对会前其常设机构制定颁布的重要议案采用追认的方式,如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对1928年10月3日第172次中常会制定的《训政纲领》,就是予以追认后生效的。
2.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及中央常会的立法权
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代行其职权,而在中央执行委员会闭会期间,则由中央常会代行其职权,决定国民党的重大方针政策。1928年10月8日颁布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 就是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制定议决的,此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的修订,也都是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中央常会来具体操作的。
3.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的立法权
《中国国民党训政纲领》第5条规定:“指导监督国民政府重大国务之施行,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行之。”[2](P590) 从而使中央政治会议处于领导地位。胡汉民在《训政大纲提案说明书》中更有详细的说明:“政治会议为全国训政之发动与指导机关……政治会议对于党,为其隶属机关,但非处理党务之机关;对于政府,为其根本大计与政策方案所发源之机关,但非政府本身机关之一。换言之,政治会议实际上总握训政时期一切根本方针之抉择权,为党与政府间惟一之连锁,党与政府建国大计及其对内对外政策,有所发动,必须经此连锁而达于政府,始能期其必行……政府一方面,则凡接受之政策与方案,皆有负责执行之义务,有政必施,有令必行。”[3](P304) 蒋介石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才是最高的立法和政治指导机关,而国民政府只是在党的指导下一个最高的行政机关”解释,有助于理解胡汉民对中政会领导地位的定性。蒋介石说:“现在一般人往往对于国民政府五院中的立法院,以为是国家的最高立法机关,无论什么法律,都经由立法院通过后,才能有效,才能由政府去发布施行,不知立法院所通过的重要法律案,更须由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原则,立法院才可通过法律案,所以,‘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才是最高的立法和政治指导机关,而国民政府只是在党的指导下一个最高的行政执行机关。我们如果不明了这一点,就以为国民政府总揽中华民国之治权,一切宣战、媾和、缔结条约以及预算决算,都由国民政府掌理,其实这些问题,一定先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交给中央政治会议去决定原则,待中央政治会议把原则决定以后,才能由国民政府各院部会去公布施行。”[4] 由此可见,中政会实际上是立法的最高指导决策机关。
作为训政时期国民党与政府惟一连锁之机关,中央政治会议总握一切根本方针的抉择权。1928年10月25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79 次常务会议通过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暂行条例》,规定中央政治会议有讨论和议决立法原则的权力,以后修订的政治会议条例,对这一条规定从未修改。通过讨论和议决立法原则,中央政治会议就为即将出台的法律确定了大政方针。此外,中央政治会议还和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会议一道共同参与制定法律。如《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就是由中央政治会议在1928年9月间审查、修订,于同年10月3日上午通过,并于同日下午全案由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72次常务会议照原文议决通过的。 尤其是《训政纲领》还特别赋予中央政治会议修正、解释《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的权力:“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之修正及解释,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议决行之。”[2](P590)
4.国民会议的立法权
这是国民党为应对社会的批评,根据孙中山召开国民会议的遗愿临时作出的决议。实际上1931年国民会议所通过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是由国民党党员参与起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37次常会和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监察委员会一道对草案进行修改的,因此国民会议实质上沦为了国民党蒋介石利用的工具。在国民会议之前,国民党通过《国民会议代表选举法》、《国民会议组织法》,使最后选出的477名代表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国民党党员。所以,从一定程度上讲, 国民会议是变相的国民党的代表会议,只不过是涂上了一点民主的色彩而已。
此外,根据1928年第129次中央政治会议通过的《立法程序法》规定, 参与立法的机关除上述外,国民政府为执行法律或基于法律之委任,须制定法律之细则,这项细则称为条例;国民政府的内政、外交、财政、交通、司法、农矿、工商等部以及最高法院、监察部、考试院、大学院、审计院、法制局、建设委员会、军事委员会、蒙藏委员会、侨务委员会,以及各省政府、各特别市政府在制定条例时,除法令有特别规定外,都须呈经国民政府核准。[2](P254—255)
二
1928年10月8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会议任命胡汉民为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5](P434) 关于立法院院长的职权,1928年10月8日颁布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立法院会议以院长为主席”,[2](P90) 《立法院组织法》规定“院长指挥全院院务及所属机关”,“院长维持院内秩序、整理议事程序”,[2](P162,163) 因而,立法院院长在立法院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一职位大都由国民党中央的要员来充任。关于立法院院长的人选,通常情况是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出,有时也经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议决。国民政府的组织法对立法院院长的任期未作限制,从实际情况看,立法院院长的任期长短不一,如胡汉民在任仅两年多时间(1928年10月8日—1931年2月28日),林森担任院长不足一年(1931年3月—1931年12月),张继在院长职位上仅一个月的时间(1931年12月—1932年1月),而孙科任立法院院长达16年(1932年1月28日[6](P168)—1948年11月26日)之久,掌控立法院时间最长。
根据1928年10月20日颁布的《立法院组织法》,立法院设法制、外交、财政、经济4个委员会,[7] 12月8日增设军事委员会,各委员会委员由立法委员分任,委员长由院长指定;立法院下设秘书处、统计处(1933年修订立法院组织法时将统计处取消)、[8](P197) 编译处。
遴选立法委员是立法院院长的重要职责。立法委员的素质直接决定立法的质量,因此,胡汉民十分重视遴选立法委员的标准。1928年10月24日,胡汉民在中央政治会议上提出立法委员的任用标准:“当首其在党历史,必其人为党国效忠,在革命过程中,未尝有违背党义之言行,而又有相当学识经验始为合格。”[5](P435) 胡汉民后来曾这样解说他用人的标准:国民政府各院部,只要是中华民国的国民,都可以兼收并蓄,甚至学有专长的外国人,也可以请他做顾问……用人的人,也不能以地域为标准。他还举例说,我是广东人,然而,我用人,并不限于广东,也从不敢说,惟有广东人,才最有才具,最可以用。[9] 用人只看学问能力,在这一方面胡汉民是言行一致的,如他在第二届立法委员增补时说:“此次立法院新补八个立法委员,其中为兄弟所素识的只有一个,其余七个,我素未谋面,只看他们的经历与著述,以为相当,便呈请政府简命了。”[10] 惟革命、惟才是举的用人思想,就为高质量的立法提供了重要保证,这已为后来的实践所证明。关于立法委员的任命程序,胡汉民也在1928年10月24日的中央政治会议上提出:“由院长提请国民政府任命、并须经政治会议决定,以符党治精神。”[5](P434)
根据1928年10月8日颁布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 立法委员的任期为二年,不得兼任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各机关之事务官,[2](P90) 虽然任期短暂,又不能在中央及地方政府机关兼职,但还是有不少人心向往之,跃跃欲试,以谋取立法委员职位为快事。蒋介石的谋士、政学系的杨永泰为谋取这一职位就碰了一鼻子灰,胡汉民义正词严地说:“杨某昔曾反对总理及陷害同志,吾焉能用之?”[11](P298) 立法委员之职还引起了社会团体的关注,全国商会联合会于1928年10月26日投票选举10人,以孙中山遗嘱为根据,在1928年11月13日将预选名单开列呈请国民党中央,要求于10人中圈选5人为立法委员,[12](P932) 但国民党中央拒绝了全国商会联合会的要求。胡汉民在复函中认为,按照国民政府组织法,立法院是政府的一个部门,不是代议性质的独立机关,不直接向民众负责,这样全国商会联合会谋取立法委员的职位也就化为泡影。根据1928年10月8日颁布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立法委员由立法院院长提请国民政府任命,1928年10月31日,胡汉民一次向中央政治会议推出48位人选,聘请戴传贤、王宠惠为顾问,[5](P434) 国民政府于11月7日任命胡汉民提出的48人为立法委员。《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为立法院规定的立法委员人数是49位,[2](P90) 11月14日,国民政府又任命钮永建为立法委员。[13] 这样,根据《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的规定,立法委员达到了规定人数的最低指标(为49—99人)。在筹组立法院时,胡汉民严格按照中央政治会议所确立的标准行事,所选委员或是学有专长的法律人才,或是有为国民党奋斗的历史,目的在于使所立之法有助于维护国民政府的稳定。[14]
胡汉民的用人思想,被后任者邵元冲继续贯彻。代理院长邵元冲在选任立法委员时极为慎重,并积极探索选用少数民族的优秀分子为立法委员的路子。如1931年9月29日晚,“约董修甲、王伯秋来谈,征询其对于立法委员之意见”,[15](P778) 邵元冲还在探索使用少数民族优秀分子方面有所创新,1931年10月3日晚, 邵元冲“约张凤九谈对于满、蒙、藏优秀分子加入立法院事”。[15](P780)
南京国民政府在社会的强烈要求下,对立法委员的产生方式也作了调整。从上文中可以看出,立法委员的产生方式从一开始就受到来自社会的挑战,也未得到社会上法律人士的认可:“根据国民政府组织法,立法委员之产生,是‘由立法院长提请国民政府任免之’,而立法院之职权,就同组织法规定有‘议决法律案、预算案、大赦案、宣战案、媾和案条约及其他重要国际事项之职权’,已等于近代各国之国会,而其组成此全国最高立法机关之分子——立法委员的产生,不必经过人民选举或其他选举手续,仅由院长任命,这是目前我国各机关最大之缺憾。”[16] (P437) 1931年12月,由于民族危机的加剧, 民主运动的发展以及国民党内部的争权夺利,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被迫修改政府组织法,把立法委员人数由49—99人增加为50—150人,规定立法委员的半数由法定人民团体选举, 选举方法另行规定。[17]“但选举法迄未颁布,此项规定亦迄未实行。”[18](P346) 1932年12月15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对国民政府组织法作了新修改,立法委员仍定为49—99人,[19] 会议决定召集国民参政会,[6](P180) 以期集中民意,并交中央常务委员会切实执行,这样,原来规定的立法委员的半数,就不再由人民团体选举了。在立法委员的任用方面还是率由旧章,恢复了以前的办法。
从上面分析可以看出,立法院院长拥有立法委员的提名权,维持院内秩序,主持院会,指挥院务,立法院院长在立法院中就有相当大的影响立法的力量,虽然如此,也并不是可以随时决定立法委员的去留,因为根据《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的规定,立法委员的任期为两年,这为立法委员行使其职权提供了保障,即在任期之内委员不能随意免职。由此看来,这与民主的立法制度还是有相近的地方。
从决定立法院院长的人选到中央政治会议决定立法委员的任用,一直都是国民党在发挥作用,因而立法院的组成过程缺乏民主精神,被称为是国民党的御用机关。[18](P219) 在国民党党治的情况下,也有一定的便利,即可避免组织上的纷争:“立法院长、委员,均受命于党,即为党之代表,无所谓地域与职业之区别,亦可免组织上之纷争。”[20](P219)
立法院建立初期,全国商会联合会对立法委员的人选极为关注,曾开会选出10人呈请国民党中央圈定5人为立法委员, 按说作为代表国民的国民党中央是应予考虑的,但还是由胡汉民出面拒绝了这一要求,此后社会在立法委员的任用办法上,一直持有民选代表参与的意见,后来国民党迫于内政外交的压力,在外患日亟的情况下,虽然在立法委员的人数、选举的办法上有所调整,但并未付诸实行,又回复到原来的老样子。这样做从策略上,对于争取民众的支持是不利的,从实际上看其政策的反复无常,也容易导致民众对南京国民政府失去信心,而南京国民政府的最后垮台表明,失去民心是重要原因之一。
三
考察南京国民政府的立法,可以看出一项法律的颁布出台,往往要经过以下几个步骤:提出法律案→中央政治会议确定法律原则→立法院各委员会和院会议决→国民政府最后公布。
1.关于法律案的提出
根据1928年3月1日国民政府公布的《立法程序法》[2](P254) 的规定,享有法律提案权的组织机构和人员有:(1)中央政治会议委员,(2)国民政府,(3)国民政府所属各院部会及各省特别市政府。又根据1928年10月8日公布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第20条、第35条、第39条、第46条,及1928年10月20日公布的《立法院组织法》[7] 第15条、第22条规定,行政、司法、考试、监察各院,各就其主管事项向立法院提出法律案,并可以在未议决之前,随时提出修正案,或撤回原案;至于立法委员提出之法律案,须有5人以上之连署。1932年6月23日,国民党中央第25次中常会通过的《立法程序纲领》规定:(1)国民政府及五院均有法律提案权;(2)国民政府直辖机关得呈由国民政府核准提出法律案;(3)各院之各部会,行政院直辖之省市政府,均得呈由各院核准提出法律案。这一规定的特点是对法律案的提出,增加了相关上级机关核查权。到1933年4月24日,国民党中央第67次中常会修正的《立法程序纲领》除原有提案权的机关外,又增加了中央政治会议有提案权,把原文所定立法院得自提法律案,修改为立法院委员得依法提出法律案。
2.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原则
由中央政治会议决定立法原则,这是训政时期的立法程序。1928年10月25日,国民党中央第179次中常会通过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暂行条例》第5条规定,“立法原则”是政治会议讨论及决议的事项之一。所以,大凡法律案之提出,事实上均先由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原则,再交立法院依据审议。立法原则的决定,是立法院立法必经的程序。1932年6月23日,中央常会通过《立法程序纲领》规定中央政治会议提出法律案,即自定原则;国民政府及五院提出法律案,应拟定原则草案,对核准提出所属各机关之法律案,应审定原则草案,呈由中央政治会议决定。立法院对于中央政治会议所定之原则,不得变更,但可陈述意见。以后,《立法程序纲领》经中央常会加以修正,但对于这项规定并没有变更。中央政治会议所决定的这些原则,包括抽象的和具体的方面,有时是二者兼而有之,有时仅是具体的原则。这些抽象原则,就是指孙中山的遗教,要在立法中贯彻执行。如胡汉民在立法中身体力行,“我们的立法,在根本上,有总理的主义做最高的原则”。[20](P905) 孙科也不甘落后,“一切法制当以三民主义为唯一之中心思想与指导原则,无可置疑”。[21](P388) 具体的立法原则,由“中央将重要之议案发交立法院时, 对于内容之要点,认为不能变更者,列为原则,俾立法时有所遵循。”[22](P25) 中央政治会议所通过的立法原则,实际上往往不只是原则,而涉及许多细节。例如,中央政治会议为《民法总则》决定的立法原则第五项规定,“足二十岁为成年”。这一原则规定与实际条文无异,立法院最后议决的法律案几乎是照抄一遍,只是将“足”字改为“满”字。
3.立法院各委员会和院会议决法律案
1928年10月20日,《立法院组织法》第18条、第19条及第23条对于立法院审议法律案进行了规定。立法院会议之法定出席人数为委员总数的三分之一,表决人数为出席委员之半数,“可否同数时,取决于主席”。[7]“立法院会议须公开之,但经委员7人以上或各院院长、行政院各部部长、各委员会委员长之请求, 得开秘密会议。”根据1929年5月14日国民政府颁布的《法规制定标准法》第1条、第2 条及《立法院议事规则》第10条、第11条规定,立法院通过法律案,须经过三读程序,但院长酌量情形,或全数委员三分之一以上连署请求,得省略之。[23] 一读时,朗读议案标题后,由提案者说明其旨趣,立法委员讨论后议决是否开二读会,否则应交付委员会审查。待报告后,再议决应否开二读会,凡议决不必开二读会之议案,即行作废。二读会朗读议案条文,并逐条讨论议决,其修正之条款及文字得交原审查委员会整理之(《立法院议事规则》第47条),有时可以修正提案。三读时议决全案,除发现与其他议案或法律有冲突时,除提出修正之动议外,仅仅作文字上的修改。关于法律案的议决顺序,《立法院议事规则》第22条专门做了规定:“以中央政治会议交议之事件为第一位,各院移送之事件为第二位,本院委员提议事件为第三位;同等机关移送之议案以到院日期之先后定其次序,本院各委员之提案以先后定其次序。”[24] 这一对交付的议案讨论的先后次序的规定,充分表明了中央政治会议在国民党中所处的领导地位。关于立法院通过决议的表决方法,查阅立法院的机关报《立法院公报》,可以总结出立法院及其各委员会的表决方法有举手、起立、无异议通过、无异议,有时候举手和无异议这两种方式用于表决同一个议案。
4.法律案公布
经过立法院三读的法律案尚不能成为法律,根据1928年10月8 日颁布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公布法律要经由国民政府委员组成国务会议议决,由国民政府主席及五院院长署名。[2](P89) 在国民政府公布法律之前, 如果中央政治会议认为有修改的必要,形成决议案发交立法院依议修正。而被立法院会议否决的法案,如果院长认为有必要,征得中央政治会议同意之后,可以发交立法院会议复议,而且不得再否决。
5.立法院的权限
立法院是在中央政治会议领导下的一个专司立法的机构,根据《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立法院组织法》和《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的相关规定,其权限有四个方面。
第一,同意权。1928年10月8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第25条第2款规定立法院有权议决大赦案、宣战案、媾和案、条约案及其他重要国际事项,这些被称为同意权的职权,在西方三权分立的宪法国家是为议会所拥有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第22条第3款、第4款规定,此等案均由行政院提出并经行政院会议议决,又依同法第3条、第4条、第11条,此等权之行使,属于国民政府并经国务会议议决。又根据1931年12月30日公布的《修正国民政府组织法》,其第8条及第15条规定国民政府以五院独立行使5种治权,并各自对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 则此等权应由行政院单独负责,以国民政府名义行使,立法院议决此等案,行使同意权,其权力与立宪国家的国会没有什么差别。
第二,质询权。这是《立法院组织法》第16条赋予立法院的权力;“立法院关于本院议决之执行,得向各院及行政院各部、各委员会提出质询;前项质询,须经本院议决行之。”[7] 应当指出的是,立法院的这项质询权还是有所限制的:其一,立法院的质询仅限于本院议决案之执行,其非关于本院议决之事项,不得提出;其二,对于各院及行政院各部会提出并且是以文字提出,不得对于其他三院各部会提出;其三,质询案之提出,须经议决,即立法院院长或立法委员联署方为有效。这一质询权在1929年有所调整,根据1929年6月17日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2次全体会议通过的《治权行使之规律案》第1项规定:“一切法律案(包括条例案及组织法案)及有关人民负担之财政案与有关国权之条约案,或其他国际协定属于立法范围者,非经立法院议决,不得成立,如未经立法院议决而施行者,立法院有提出质询之责。”[2](P596) 这样,前后规定的质询权就有所区别:(1)前项质询为关于立法院议决案之执行,后项质询属于立法范围而未经立法院议决公布施行者;(2)前项质询是向各院及行政院各部会提出,后项质询是向公布施行之机关提出;(3)前项为可提出质询,后项为应提出质询,而且是属于职权被侵害所提的抗议。
第三,质问权。这种职权是专门针对监察院所规定的。依据《监察院组织法》第11条规定:“监察委员不尽职时,立法院得向监察院提出质问。”提出此种质问,必须在以下两种情况下:必须是向监察院提出:必须是监察院委员不尽职的情况下。
第四,起草宪法权。1931年6月1日公布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第86条规定:“宪法草案当本于建国大纲及训政宪政两时期之成绩,由立法院议订。”[24](P275) 有中央政治会议决定的立法原则,而拥有这些权力足以使立法院较好地完成各项立法任务。胡汉民之所以愿意走马上任立法院长,也即在于此。“胡汉民看重了立法院的职权,他要通过立法院,制定一整套的资产阶级法令,行之于中国。”[25](P220) 陈公博也曾这样说:“胡先生所要的是立法院, 而把国府主席让之蒋先生。”[26](P184)
综上所论,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立法体制,呈现这样的特点: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常会、中央政治会议及国民政府都享有一定的立法权,真可谓是法从党出了。真正负责从事立法的机关是立法院,却仅享有一定的权限,但立法院不拥有西方三权分立下的国会所具有的对行政的制衡作用,按照首任立法院院长胡汉民的说法,国民政府立法院只是“政治会议下的一个机构而已”,[2](P817) 这是因为对立法院来说,“立法原则都由政治会议决定。政治会议有立法的最高权,我们对政治会议的决议只有遵守”。[21](P816) 由此看来,国民党正是通过多种途径、不同渠道来巧妙地参与立法,从而保障国民党的意志渗透到法律的制定、贯彻和执行之中,这是国民党立法的初衷,也是实质。
收稿日期:2006—02—2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05AZS002)
标签:南京国民政府论文; 国民政府论文; 胡汉民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立法原则论文; 台海时事论文; 立法院论文; 法律论文; 组织法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