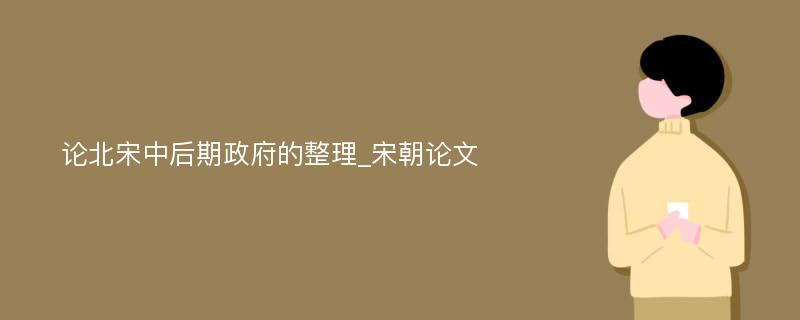
北宋中后期官府校勘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官府论文,北宋论文,后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北宋文化璀灿辉煌,校勘学亦空前繁兴,成就令人瞩目。笔者曾就北宋前三朝(即太祖、太宗、真宗)中央政府组织的校勘活动,撰文予以论述(注:见《宋初官方校勘述论》,载《宋史研究论文集》,河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下同。)。本文即其续篇,所述为仁宗至北宋亡期间的官府校勘活动,所论则涵盖北宋九朝。
本文所述校勘活动的范围与前文相同,仍是朝廷中以校勘为主要目的的文献整理活动,且为皇帝明确下诏或下令进行的。因此诸如景祐修《集韵》、嘉祐编《谥法》等,其间虽确有校勘活动,然因其目的在修纂而非校勘,因此亦不予评述。
以往主要论及北宋官府校勘的论文有四篇(注:四篇为:陈红艳《北宋官府校勘古籍述论》,《津图学刊》1993年第2期;王晟《北宋时期的古籍整理》,《史学月刊》1983年第3期;肖鲁阳《北宋官书整理事业的特点》,《上海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1期;张富祥《宋代校勘学的发展》,载《宋代文献学散论》,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然全面勾勒出30次校勘概貌、并从学术风气与校勘的关系、军政大事与校勘的联系之角度考察者,本文尚属首次。
一
北宋中后期中央政府组织进行的校勘,共计为30次(注:文中校经书与第四次校史书实为一次,第五次校史书与第三次校子书实为一次,本文为撰写之便而分计之,故总次数为30次而非32次。)。为便于观察分析,仍依经、史、子、集之序述之。
仁宗朝以后对经书的校勘,见于史载者仅一次,且为与校史书同时进行的:“景祐二年九月,诏翰林学士张观等刊定《前汉书》、《孟子》,下国子监颁行。”(注:《麟台故事》(以下简称《麟台》。又本文中凡未特指为《四库》本《麟台》者,皆为上海涵芬楼影印《四部丛刊续编》本)卷二。其中“景祐二年”原文为“景祐一年”,据《玉海》(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7年版,下同)卷四三;《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引自上海古籍出版社精装版《四库全书》,前言为1987年8月。以下凡引自《四库全书》者,皆为此版本)卷一一七,景祐二年九月壬辰条改。)
《孟子》在真宗朝曾校勘过,本次校勘的过程则不得其详。校后即颁行。
此期史书之校,则有八次之多。
第一次为校《后汉书》中的志书:“乾兴元年十一月,判国子监孙奭言:‘刘昭《补注后汉志》三十卷……乞令校勘,雕印颁行。’从之。命本监直讲马龟符、王式、贾昌朝、黄鉴、张维翰、公孙觉、崇文院检讨王宗道为校勘,奭洎龙图阁直学士冯元详校。天圣二年,送本监镂版。”(注:《宋会要辑稿》崇儒(以下略作《崇儒》,中华书局1957年版,下同)四之五、四之六。其中刘昭《补注后汉志》原作《注补后汉志》,据《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下同)卷二○三《艺文志》改。)
《后汉志》仅三十卷,校勘却费时一年有余,参加者至少九人,且分校勘、详校两个步骤,可见其认真程度。
第二次为校《天和殿御览》:“仁宗尝谓辅臣曰:‘《天和殿御览》可命校定模本刊行之。’”(注:《玉海》卷五四。)《天和殿御览》是《册府元龟》之精华:“乾兴初……于《册府元龟》中掇其善美事,得其要者四十卷……名曰《天和殿御览》。”(注:《玉海》卷五四。)至“天圣二年五月甲寅,内出《天和殿御览》四十卷……下秘阁镂板。”(注:《玉海》卷五四。)
《册府元龟》本为类书,但“惟取六经、子、史,不录小说”(注:《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三五,中华书局1965年版,下同。),其原名为《历代君臣事迹》,显然偏重于史;此次摘录为《天和殿御览》,仁宗也将它视为史书:“朕听政之暇,于旧史无所不观,思考历代治乱事迹,以为鉴戒。”(注:《玉海》卷五四。)故本文亦将其归入史书。且《册府元龟》“引书近二千多种”(注:见刘乃和先生《〈册府元龟〉新探·序》,中州书画社1983年版。),因而此次“校定”当以他校为主,而非止简单的校对。本次校勘值得注意之处为校新纂之书。
第三次是校《南、北史》、《隋书》:“仁宗天圣二年六月,诏直史馆张观、集贤校理王质、晁宗悫、李淑、秘阁校理陈诂、馆阁校勘彭乘、国子监直讲公孙觉校勘《南、北史》、《隋书》,及令知制诰宋绶、龙图阁待制刘烨提举之……又奏国子监直讲黄鉴预其事。”(注:《崇儒》四之六。又见《麟台》卷二;《玉海》卷四三。)仅此处所载,参与者就已有十人之众。至“(天圣)三年十月,(《隋书》)版成。四年十二月,《南、北史》校毕以献。各赐器币有差”(注:《崇儒》四之六。又见《麟台》卷二;《玉海》卷四三。)。
北宋前三朝已校了正史中的前四史、《晋书》、《唐书》等,本次校勘,显为接续前代之作。其中《南、北史》后又复校之:“景祐元年四月丙辰,命宋祁等复校《南、北史》。”(注:《玉海》卷四三。)
第四次为校前四史与《晋书》:“(景祐元年)九月癸卯,诏选官校正《史记》、前、后《汉书》、《三国志》、《晋书》。”(注:《玉海》卷四三。)其中较为突出者是校《汉书》:“会秘书丞余靖进言:‘《前汉书》官本谬误,请行刊正。’诏靖及国子监王洙尽取秘阁古本对校,逾年乃上《汉书刊误》三十卷。”(注:《长编》卷一一七,景祐二年九月壬辰条。又见《麟台》卷二;《玉海》卷四三。)《宋史·艺文志》中亦明载:“余靖《汉书刊误》三十卷。”参加者还有:“详定官翰林学士张观、知制诰李淑、宋郊。”(注:《麟台》卷二。又见《玉海》卷四三;《崇儒》四之一。)
《前汉书》在太宗淳化年间就曾认真校勘过,至真宗景德元年,又命刁衍等人“复校前、后《汉书》”,结果甚丰:“正三千余字,录为六卷以进。”(注:《麟台》卷二。又见《玉海》卷四三;《崇儒》四之一。)本次校勘“尽取秘阁古本”,历时一年多,且产生三十卷的《汉书刊误》。对一部史书,在约四十年内如此一而再、再而三地雠校,且校勘文字达三十余卷,这在我国两千余年校勘史上亦不多见(注:《长编》卷一一七,景祐二年九月壬辰条下与《麟台》卷二几乎一字不差地有如下一段记载:“至太宗朝,又摹印司马迁、班固、范晔诸史,与六经皆传,于是世之写本悉不用。然墨版讹驳,初不是正,而后学者更无他本可以刊验。”前四史如本文所述,在宋初曾反复认真地校勘过,绝非“初不是正”,故本文不取。此处之“初不是正”,恐为泛指宋代以前所有正史校勘的状况而言的。)。而至“神宗熙宁二年八月六日,参知政事赵抃进新校《汉书》印本五十册,及陈绎所著《是正文字》七卷。”(注:《崇儒》四之十。)即又校出不少错谬,由此亦可见校勘工作是何等艰辛。
此处还应提及的是:在清代钱东垣等辑释的《崇文总目》卷二中,著录有“《三史刊误》四十五卷”,下有:“初,秘书丞余靖上言:‘国子监所收《史记》、《汉书》误,请行校正。’诏翰林学士张观、知制诰李淑、宋祁与靖,洎直讲王洙于崇文院雠对。靖等悉取三馆诸本,及……数百家之书,以相参校。凡所是正、增损数千言,尤为精备。逾年而上之。靖又自录其雠校之说,别为《刊误》四十五卷。”将这段文字与《玉海》、《长编》、《麟台故事》等书的相关记载比照,有四点相同、一点相仿:1.校书皆因余靖进言而起;2.参加者五人中,有四人相同(而不同者,一为兄宋郊,一为弟宋祁,恐为形似之误);3.校勘时间皆为“逾年”;4.均产生数十卷的《刊误》。一点相仿为:余靖进言之内容相近。且从情理上讲,余靖亦不大可能既撰《汉书刊误》三十卷,又为《三史刊误》四十五卷。故此,《崇文总目》所言当即为本次校勘。盖当时进呈者为《三史刊误》四十五卷,而流传于世者仅有《汉书刊误》三十卷。
第五次校《国语》则是与校子书同时进行的:“景祐四年十月十七日,翰林学士李淑言:‘……《国语》、《荀子》、《文中子》……欲望取上件三书差官校勘、刻板,撰定《音义》,付国子监施行。’诏可。”(注:《崇儒》四之七。)本次校勘是为考试出题之需。其结果则不详。
第六次为“嘉祐校七史”:“六年八月庚申,诏三馆、秘阁校理《宋》、《齐》、《梁》、《陈》、《后魏》、《周》、《北齐》七史,书有不全者访求之。”(注:《玉海》卷四三。)至“嘉祐七年十二月,诏以七史板本四百六十四卷送国子监镂板颁行”(注:《玉海》卷四三。又见《崇儒》四之十九。)。(其中《陈书》校定时间为八年七月,详下文)。
本次校勘最值得注意之处是为校勘而搜求书籍,如校《后周书》:“仁宗时,出太清楼本,合史馆秘阁本,又募天下献书,而取夏竦、李巽家本,下馆阁是正其文字。”(注:《郡斋读书志》(引自《四库全书》,下同)卷二上;又见《周书目录序》,引自《周书》,中华书局1971年版。)即募得两种不同版本,才进行校勘工作。其他书亦如是:“臣等言‘《梁》、《陈》等书缺……愿诏京师及州县藏书之家,使悉上之。’先皇帝为下其事,至(嘉祐)七年冬稍稍始集。臣等以相校,至八年七月,《陈书》三十六篇者始校定。”(注:《元丰类稿》(引自《四部备要》,中华书局1989年版,下同)卷一一《陈书目录序》。《郡斋读书志》卷二上载:嘉祐所校七史,“政和中始皆毕”。此说与《元丰类稿》卷一一,《玉海》卷四三、卷五二所载皆异,恐误,本文不取。)从中可看出:当时为校勘而求书,时间上长达一年多,范围远及州县。
第七次为校《后汉书》:“仁宗读《后汉书》,见‘垦田’字皆作‘恳’字,使侍中传诏中书,使刊正之。(刘)攽为学官,遂刊其误为一书云。”(注:《郡斋读书志》卷五上。)《郡斋读书志》卷五上著录有:“《西汉刊误》一卷,《东汉刊误》一卷。右……刘攽所撰也。”《宋史》中亦载:“(刘攽)作《东汉刊误》,为人所称。”(注:《宋史》卷三一九《刘攽传》。)此《刊误》进呈时间为:“治平三年四月……刘攽上。”(注:宋版《东汉刊误》卷一,转引自曾贻芬先生《宋代对历史文献的校勘》,《史学史研究》1992年第3期。)由上述可见,此书为刘攽独立完成的,但“刊正”者似不止刘攽一人。(注:刘攽的著述,《宋史》卷二○三《艺文志》中著录有:“刘攽《汉书刊误》四卷”,又有:“《三刘汉书标注》六卷〈刘敞、刘攽、刘奉世〉。”而《直斋书录解题》卷四载:“《三刘汉书标注》六卷……又本题《公非先生刊误》,其实一书。”(公非即刘攽之自号。)上列三种书与本文所论之《东汉刊误》之间倒底是什么关系?这是研究北宋校勘应回答的问题,然迄未见有论文明白述之。而对此问题清《四库》馆臣曾作过考证,其结论颇合情理,特录于此:“盖于前、后《汉书》初各为《刊误》一卷,赵希弁所说(即《郡斋读书志》卷五上)是也;后以所校《汉书》与敞父子所校合为一编”,即为《三刘汉书标注》;“而《东汉(刊误)》一卷无所附丽,仍为别行”,即我们今天见到的《东汉刊误》(实为四卷);“至别本乃以书为主,而敞、奉世说附入之,故仍题《刊误》之名”,即《公非先生刊误》(见《四库全书总目》卷四五)。)。
第八次为校《资治通鉴》:“哲宗元祐元年三月十九日,宰臣司马光言:‘秘书省校书郎黄庭坚好学有文,欲令与范祖禹及男康同校定《资治通鉴》。’并从之。”(注:《崇儒》四之十。)《资治通鉴进书表》标明进呈时间为“元丰七年十一月”,距校书时间仅一年多,自然也是校当代之书。《资治通鉴》引书数百种,此处之“校定”,当是以他校为主。
子书之校更多达十三次。
第一次为校《内经·素问》等医书:“(天圣)四年十月十二日,翰林医官副官赵拱等上准诏校定《黄帝内经·素问》、《巢氏病源》、《难经》,诏差集贤校理晁宗悫、王举正、石居简、李淑、李昭遘依校勘在馆书籍例,均分看详校勘。”(注:《崇儒》四之六。)至“(天圣)五年四月乙未,令国子监摹印颁行。诏学士宋绶撰《病源序》”。(注:《玉海》卷六三。“宋绶”原为“宋缓”,据《长编》卷一○五改。)其中《素问》后又校之:“景祐二年七月庚子,命丁度等校正《素问》。”(注:《玉海》卷六三。)嘉祐再校之(详后)。
第二次为校“律文及疏”,亦始自天圣四年:“十一月,翰林侍读学士、判国子监孙奭言:‘诸科举人,惟明法一科律文及疏未有印本……’命本监直讲杨安国、赵希言、王圭、公孙觉、宋祁、杨中和校勘,判监孙奭、冯元详校。至七年十二月毕。”(注:《崇儒》四之六。)
北宋百余年间,曾多次删定编敕,如咸平、景德、庆历、治平、熙宁年间等等,然这些整理基本上都是因过去“格敕条目繁多”,而以“删定”、“去其繁密之文”(注:详见《宋会要辑稿》刑法一之一至一之二六;参见《玉海》卷六六。)为主,故本文不论。而这次则明确指出是“校定律文及疏”。《宋会要辑稿》载本次过程颇详:“七年四月,孙奭言:‘准诏校定律文及疏……其《刑统》内衍文者减省,阙文者添益,要以遵用旧书,与《刑统》兼行。又旧本多用俗字,浸为讹谬,亦已详改。至于前代国讳,并复旧字;圣朝庙讳,则空缺如式。又虑字从正体,读者未详,乃作《律文音义》一卷,其文义不同,即加训解。乞下崇文院雕印,与律文并行。’”(注:《崇儒》四之七。)
由此可见,这次整理过程可分为五个步骤:1.减省衍文;2.增补阙文;3.详改俗字、错字;4.恢复前代国讳的旧字;5.作《律文音义》一卷,将俗字与正体加以对照,并对文义不同者加以训解。这五项工作,除“训解”外,皆属校勘范畴,又历时三年多,确为一次较认真的校勘。
第三次是校《荀子》、《文中子》:“景祐四年十月十七日,翰林学士李淑言:‘……有《国语》、《荀子》、《文中子》,……欲望取上件三书差官校勘、刻板,撰定《音义》,付国子监施行。’诏可。”(注:《崇儒》四之七。)这里也提到要撰定《音义》,惜乎结果不详。
第四次为校医书:“(嘉祐二年八月)庚戌,……(韩)琦又言:‘医书……请择知医书儒臣与太医参定颁行。’”(注:《长编》卷一八六。)仁宗接受了韩琦的建议,下诏:“所有《神农本草》、《灵枢》、《太素》、《甲乙经》、《素问》之类,及《广济千金》、《外台秘要》等方,仍差太常少卿、直集贤院掌禹锡、职方员外郎、秘阁校理林亿、殿中丞、秘阁校理张洞、殿中丞、馆阁校勘苏某(即苏颂)同共校正闻奏。”(注:《苏魏公文集》(引自《四库全书》)卷六五《本草后序》,但下诏时间为“八月三日”,恐误。因据《长编》卷一八六,韩琦上言为“八月庚戌”、即六日,下诏时间自当在此之后。又据《玉海》卷六三的两处记载,下诏之日为八月辛酉、即十七日,似得其实。)此后“臣禹锡等寻奏置局刊校,并乞差医官三两人共同详定”(注:《苏魏公文集》卷六五《本草后序》。)。于是“置校正医书局于编修院,命掌禹锡等五人”(注:《玉海》卷六三。)。至“其年十月,差医官秦宗古、朱有章赴局祗应”(注:《苏魏公文集》卷六五《本草后序》。)。至“五年八月,补注《本草》成书,先上之”(注:《苏魏公文集》卷六五《本草后序》。)。本次校勘的最大特点是专门设立“校正医书局”,足见其重视程度。且为任用医官校医书。参加者至少七人。
第五次为校秘阁兵书:“(嘉祐)六年四月,以大理寺丞郭固编校秘阁所藏兵书。先是,四馆置官编校书籍,而兵书与天文为秘书,独不预。大臣或言:固晓知兵法。乃命就秘阁编校,抄成黄本一百七十二册……治平四年六月,以编书毕,迁内藏库副使、路分都监。”(注:《崇儒》四之八。其中“大臣或言”。原为“大有有言”,据《长编》卷一九三,嘉祐六年四月丙子条改。)此文虽未言编校之书及卷数,然历时六年,最后又“抄成黄本一百七十二册”,可见其数量相当多。
第六次为校阴阳之书:“(神宗)元丰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提举司天监所言:‘先被旨应馆阁所藏及私家所有阴阳之书,并录本校定,置库收掌。今编成七百一十九卷,乞上殿进呈。’从之。”(注:《宋会要辑稿》职官(以下略作《职官》)一八之八四。)此为北宋首次校阴阳之书,计七百余卷。
第七次即为校著名的“武经七书”:“元丰三年四月一日,诏校定《孙子》、《吴子》、《六韬》、《司马法》、《三略》、《尉缭子》、《李靖问对》等书,镂板行之。”(注:《崇儒》四之十。)“我国古代兵书著述繁富,种类繁多,然而其精华部分就是‘武经七书’”,“‘武经七书’的颁定,确立了兵书在封建社会的正统地位”,“奠定了中国古代军事学的基础”(注:参见王显臣等《中国古代兵书杂谈》,战士出版社1983年版。)。因此这次校定,意义甚为深远。
第八次为校《道藏》:“宋徽宗初,兴道教,诏天下搜访道家遗书,就书艺局令道士校定。”(注:《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五一,引自(道藏)第148册,1926年上海涵芬楼据明正统本影印,下同。)“我朝崇宁中,再校定《道藏》经典。”(注:《道德真经集注杂说》卷上,引自《道藏》第403册。)本次为以道士校《道藏》。
第九次为校医书:“《和剂局方》十卷大观中,诏通医刊正药局方书,阅岁,书成,校正七百八字,增损七十余方。”(注:《郡斋读书志》卷一五,《中国历代书目丛刊》(第一辑下),现代出版社1987年版。)“库部郎中陈师文等校正,凡二十一门、二百九十七方。”(注:《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三,然著录为六卷。而此书《四库全书》本为十卷,今从之。)本次校医书,任用“通医”、“郎中”校正,“阅岁”而成,正七百余字。
第十次为政和年间再校《道藏》:“(三年)十二月癸丑,诏天下访求道教仙经。”(注:《宋史》卷二○《徽宗本纪》。)至六年校毕上进时,其书序云:“臣于前岁七月,被旨差入经局,详定访遗,及琼文藏经,开板符篆。因得窃览经箓,殆至周遍。”“近又……裒访仙经,补完遗阙,周于海寓,无不毕集。继用校雠密藏,将以刊镂,传诸无穷。”(注:《太上助国救民总真秘要》卷首,引自《道德》第986册。“臣”即洞幽法师元妙宗。)这次校勘,也是访求于前,并任用道士校《道藏》。且其规模宏大,在《道藏》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第十一次为校《证类本草》:“(政和年间)命臣(即提举医学曹孝忠)校正而润色之……诸有援引误谬,则断以经传;字画鄙俚,则正以《字说》;余或讹戾淆互、缮录不当者,又复随笔刊正,无虑数千,遂完然为成书,凡六千余万言。”(注:《政和新修经史证类备用本草》书前序,见《四库全书·子部》。)此书上于政和六年九月。其校勘包括:1.改引语之误;2.正俗字;3.改错字。其纠错“无虑数千”,可谓成果斐然。
第十二次为校《亢桑子》、《文子》:“政和七年八月一日,宣和殿大学士蔡攸言:‘……《亢桑子》、《文子》未闻颁行。乞取其书于秘书省,精加雠定,列于国子学之籍,与《庄》、《列》并行。’从之。”(注:《崇儒》四之十。)《亢桑子》又名《亢仓子》,“唐天宝元年,诏号《亢桑子》为《洞灵真经》”(注:《郡斋读书志》卷三上。);《文子》又名《通玄真经》,二书于《四库总目》中皆入“子部·道家类”(见卷一四六),故此次校勘亦为校道家之书。
最后一次为校《内经》:“(政和八年)五月十三日……诏太医学司业刘植、李庶通、元冲妙先生、张虚白充参校官,大素处士赵壬、明堂颁朔皇甫自收、黄次公、迪功郎龚璧、从事郎王尚充检讨官,上舍及第宋乔年、助教宋炳充检阅官。后又诏刑部尚书薛嗣昌充同详定官。”(注:《崇儒》四之十一。)本次校勘参加人数颇多,且注意任用有学术专长者。
北宋中后期校集部书仅一次:“至天圣中,监三馆书籍刘荣超上言:‘李善《文选》……欲集国子监官校定净本,送三馆雕印。’从之。”(注:《崇儒》四之四。)至“天圣七年十一月板成,又命直讲黄鉴、公孙觉校对焉”(注:《崇儒》四之四。)。真宗时曾校过《文选》,后因“宫城火,二书(《文选》及《文苑英华》)皆烬”(注:《崇儒》四之四。),故有本次之校。
此期综校四部之书有九次。第一次始于景祐元年:“闰六月,以三馆秘阁所藏,有缪滥不全之书,辛酉,命翰林学士张观、知制诰李淑、宋祁将馆阁正副本书看详,定其存废,伪谬重复并从删去;内有差漏者,令补写校对。仿《开元四部录》,约《国史艺文志》,著为目录,仍令翰林学士盛度等看详。”(注:《玉海》卷五二。又见《长编》卷一一四,景祐元年闰六月辛酉条。)
不难看出,这是一次大型综合性整理活动,包括:1.确定各书之存废,删伪去重;2.补写校对;3.编制新目录;4.全面审定。其结果为:“(景祐)二年,上经史八千四百二十五卷。”(注:《玉海》卷五二。)“(景祐三年十月)乙丑,御崇政殿,观三馆秘阁新校两库子集书凡万二千余卷,赐校勘官并管勾使臣、书写吏器币有差。”(注:《长编》卷一一九。)此后校雠工作仍在继续:“(景祐)三年十月甲寅,以知制诰王举正看详、编排三馆秘阁书籍。自是常于内外制中选官充是职。”(注:《玉海》卷五二。又见《麟台》卷二。)且“诏求逸书,复以书有谬滥不全,使命定其存废”(注:《玉海》卷五二。)。而目录进呈时间为:“(庆历元年上十二月)己丑,翰林学士王尧臣等上新修《崇文总目》六十卷。”(注:《长编》卷一三四。)自景祐元年至《总目》上进,整理活动持续十年有余(注:前述校《孟子》和校前四史、《晋书》两次,时间上一为景祐二年九月至三年,一为元年九月至三年,皆在本次校理四库书的时间范围之内。然本次为一般性的编校四馆之书,其中校经史之书八千余卷仅历时一年零四个月;而校《孟子》和前车史等则为别下诏书、专门校勘的,故本文于计次数时分别计之。)。
第二次为嘉祐编定书籍:“嘉祐四年二月〈丁丑〉置馆阁编定书籍官,以秘阁校理蔡抗、陈襄、集贤校理苏颂、馆阁校勘陈绎,分史馆、昭文馆、集贤院、秘阁而编定之。”(注:《玉海》卷五二。其中尖括号内原文为小字,下同。)“六月己巳,又益编校官,每馆二员。”(注:《玉海》卷五二。)参加者还有:“以太子中允王陶、大理评事赵彦若编校昭文馆书籍,国子博士付卞编校集贤院书籍,杭州于潜县令孙洙编校秘阁书籍。其后又以太平州司法参军曾巩编校史馆书籍。”(注:《四库全书》本《麟台》卷二。)至“六年十二月辛丑,三馆秘阁上写黄本书六千四百九十六卷,补白本书二千〈一云一千〉九百五十四卷。二十二日壬寅,遣中使诏中书枢密院合三馆秘阁官属四十一人赐宴,以嘉其勤”(注:《玉海》卷五二。)。可知参与者至少有41人。此后编校工作仍在继续:“七年三月辛酉,诏参知政事欧阳修提举三馆秘阁写校书籍,仍诏两制看详天下所献遗书。六月丁亥,秘阁上补写御览书籍。”(注:《玉海》卷五二。)“十二月,诏以所写黄本一万六百五十九卷、黄本印书四千七百三十四卷,悉送昭文馆。”(注:《玉海》卷五二。)
这次编定群书值得注意之处为:“六年六月,开献书之路,诏诸道搜访。《中兴书目》有《嘉祐搜访阙书目》一卷,首载六年六月求遗书诏书。”(注:《玉海》卷五二。)即为整理政府藏书,特别编制搜访书目,到各道访求。
这次整理的结束时间,《长编》卷二六○载:“(熙宁八年二月四日)丙寅……赐馆阁校勘林希、集贤校理梁焘银绢各三十匹两,以编校四馆书籍毕也。”而且似唯恐人不知,下面特以小字指明:“嘉祐四年二月丁丑,初编校四馆书。”(注:《玉海》卷五二所载编校开始时间与此处完全一致。而《长编》卷一八九嘉祐四年六月己巳条下云:“馆阁编校书籍自此始。”与卷二六○矛盾,疑有误。又《玉海》卷五二载:“以校勘功毕,明年(指嘉祐八年)遂罢局”,但又以小字标明:“或云:……熙宁中罢局。”《崇儒》四之九亦为两个时间并存。而此处上文有六年六月才发求遗书诏书,若八年即罢局,于情理亦不合,故本文从《长编》卷二六○。)即此次编校群书,历时达十七年之久(注:本次校理群书在时间上涵盖了上文所述的校兵书与校七史,而本文仍分别计次。请参见注①。下同。)。
第三次在神宗熙宁七年:“六月二十三日,监三馆、秘阁言:‘……诏书内求访到书籍,只各一部,并未校正,乞行校正……’从之。”(注:《职官》一八之四。)本次为校勘求访所得之书。
元丰元年十二月七日秘阁校理的上言中,提及第四次校勘:“每岁崇文楷书补写四库书……遂命崇文院勘会四馆书籍……”(注:《职官》一八之五。)本次所校则为“四馆书籍”。
第五次始于哲宗元祐二年:“六月八日,秘书省言:‘……乞在省官与供职校理分校秘阁所藏黄本书……。’”(注:《职官》一八之七。)这次校勘延续多年,如元祐五年六月四日的诏书中提及“秘书省见校对黄本书籍未了,可添一员”(注:《职官》一八之一○。),七年三月七日秘书省亦言:“本省节次添差到校对黄本书籍官共五员”。(注:《职官》一八之一二。)至“徽宗崇宁二年五月四日,礼、户部言:‘校〔秘〕书省见誊写三馆书籍充秘阁书,至今一十七年,装褫成书共二千八十二部……犹有一千二百一十三部、及阙卷二百八十九卷未写……’”(注:《职官》一八之一四。)从元祐二年至此,恰为十七年,且此后仍在进行,足见本次校勘历时之久长。校书二千余部,规模亦颇可观。
第六次亦于哲宗朝:“元祐七年五月十九日,秘省言高丽献书多异本,馆阁所无。”(注:《玉海》卷五二。)“诏降付秘书省,仍令本省誊写、校正二本,送中书省、尚书省;及别誊写、校正二本,送太清楼、天章阁收藏。”(注:《职官》一八之一三。)校域外所献之书,这是北宋百余年间仅见的一次。
第七次在徽宗大观年间:“二年,诏大司成分委国子监、太学、辟雍等官校本监书籍。候毕,令礼部复校。”(注:《通考》卷一七四《经籍考·总叙》。)本次校书之具体人数、时间则不详。
第八次始于大观四年:“五月七日,秘书监何志同奏:‘……《(崇文)总目》之外,别有异书……就加校定,上之策府……’从之。”(注:《职官》一八之一五。又见《通考》卷一七四《经籍考·总叙》。)至“政和四年四月十四日……蔡攸……又奏:‘本省官校勘书籍……以经史子集次序成部分校……’”(注:《职官》一八之一五。)可见此次校勘,亦延续了四年以上。
最后一次为:“宣和初,提举秘书省官建言:‘置补完御前书籍所于秘书省,稍访天下之书以资校对。’以侍从官十人为参详官,余官为校勘官。”(注:《麟台》卷二。其中“提举秘书省”之“秘”字原缺,据《崇儒》四之一二补。)后又建局:“宣和四年四月十八日诏……乃命建局,以‘补完校正文籍’名,设官综理,募工缮写。一置宣和殿,一置太清楼,一置秘阁。仍俾提举秘书省官兼领其事……庶成一代之典。”(注:《崇儒》四之一二。)本次校勘之过程虽未见史载,然特为此建局,可见必具有一定规模。宣和六年的一段史料透露出这种规模的概况:“九月十九日,诏减罢校正御前文集〔籍〕官吏,校勘官、校正官、对读官各减一年磨勘……中书省请并补完校正御前文籍并归秘书省,只用馆职校勘,少监充校勘官,校书郎正字充初校正官,丞、郎、著作佐郎充复校正官。详定官十员、管勾一员并依旧。对读官于校正对读官内通留十员。其余合留人数:取押绫纸等使臣四人,点检文字一人,手分五人,楷书六人,专副二人,对算二人,通引官二人,库子库司八人,兵士五十人,和雇人据合用数逐旋和雇。从之。”(注:《崇儒》四之一二。)可见,即使不计兼职的校勘官、初校正官、复校正官与“逐旋和雇”的人员,其他人员总数已达101人!而此前人数还要超出若干。且徽宗时曾多次下诏、极为认真地搜求逸书,并予奖励,如“(宣和)七年,提举秘书省又言:‘取索到王阐、张宿等家藏书,以三馆、秘阁书目比对,所无者凡六百五十八部、一千四百一十七卷,及集省官校勘,悉善本……’诏阐补承务郎,宿补迪功郎。”(注:《通考》卷一七四《经籍考·总叙》。)足见直至北宋灭亡以前,徽宗对校理群书一直是重视有加。《宋史》也注意到这一状况,特别指出:“徽宗时……诏购求士民藏书,其有所秘未见之书足备观采者,仍命以官。且以三馆书多遗逸,命建局……自熙宁以来,搜访补辑,至是为盛矣。”(注:《宋史》卷二○二《艺文志序》。)亡国在即,校理文籍却仍盛况如是,确属鲜见。
二
纵观北宋九朝之中央政府校勘,有如下一些方面值得注意。
其一为将校勘记独立汇编成书。自宋初始,就已出现这种汇编:太宗朝史馆修撰张泌集有《汉书刊误》一卷(注:《宋史》卷二○三《艺文志》。);真宗朝“任随等上复校《史记》勘误文字五卷”(注:《玉海》卷四三。);至景德年间校前、后《汉书》时,又将所校正的“三千余字”“录为六卷以进”(注:《崇儒》四之一。);至仁宗景祐年间校《汉书》后,更产生了多达三十卷的《汉书刊误》,在卷帙上远过前朝,且与张泌书同样具有独立书名。它们标志着到北宋时,校勘记又发展到一新阶段,即已完全独立成书。
自向、歆父子整理群书后,历代中央政府多有校理群籍的活动(注:见《宋初官方校勘述论》。),然皆未将校勘成果单独汇集成书。私家校雠中,亦有不少涉及校勘的名篇名著,如颜之推《颜氏家训·书证》,陆德明《经典释文》等,但也未见有独立的校记汇编。北宋的校记专书,不但标志着政府校勘的一大进步,也是校勘学发展史上一重要里程碑:它标志着校勘学已从以往与目录、版本诸学并行的状态,向着独立方向的重大迈进。
北宋这些校记汇编,是以往校勘发展的必然结果,又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如南宋张淳《仪礼识误》,毛居正《六经正误》,方崧卿《韩集举正》等,都继承光大了这种作法,将校勘成果集为专书。
其二,北宋官府校勘与“小学”的互动,亦颇引人注目。中国古代将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称为“小学”,这三学在北宋之前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它们为高质量的校勘奠定了坚实基础。北宋政府校勘一方面充分运用前代的“小学”成果,一方面又很重视校理“小学”之书。如建国之初就校《经典释文》(其中含大量“小学”资料);太平兴国年间更“详定《玉篇》、《切韵》”,后又雠校《说文》;真宗景德年间则“详定《正辞录》”和“新定《韵略》”,且两次校《尔雅》(注:见《宋初官方校勘述论》。)。这些宋初的校勘工作,伴之以刻板颁行,大大推动“小学”成果广泛传播,为其后的校勘创造了良好条件。可见,政府校勘与“小学”成果两者互相促进,在北宋形成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这无论是对校勘学、还是对“小学”的进展,皆十分有益。
其三是建立专门机构进行校勘。北宋中央已形成校书中心——三馆秘阁,此外还建立一些机构,如仁宗朝的“校正医书局”,徽宗朝置“补完校正文籍局”等。设置这些机构可保证身处其中的人员专心致志进行校勘,且有大量辅助人员协助。这一举措对保证校勘质量无疑具有重大作用。它不但显示出最高统治者对校勘事业高度重视,更是官府校勘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其四为校勘与刻印紧密结合。北宋校勘繁兴,其最直接原因即是刊刻书籍之需;而校勘事业的发达,反过来又推动刻书业发展。二者相互促进,形成空前繁荣的景象。
其五为政府校勘与目录学相辅相成,互相促进。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校勘后编制书目。我国自向、歆父子校理群籍、编制《别录》、《七略》后,代不乏人,如西晋荀勖“复校错误十余万卷书”,编成标志着四分法产生的《中经新簿》(注:《晋书》卷三九《荀勖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东晋李充校理群书后,编成《晋元帝四部书目》,(注:《晋书》卷九二《李充传》。),等等。这一优良传统在北宋得到空前弘扬,如真宗朝的《咸平馆阁图籍目录》、《景德太清楼四部书目》、《(祥符)龙图阁书目》、《祥符宝文统录》(注:《玉海》卷五二。)等,而规模最为宏大的自然是仁宗庆历之《崇文总目》。如此频繁地校书编目,对古代目录学的发展无疑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另一方面的表现是为校勘之广搜异本而专门建立目录,如太宗太平兴国九年正月和真宗景德四年十月就曾两次下诏,为校勘目的而张布阙书目(注:《麟台》卷二。)。至仁宗朝,则更有《嘉祐搜访阙书目》等。为搜求阙书专门编目的作法,北魏就已出现,即“《阙书目录》一卷”(注:《隋书》卷三三《经籍志》,中华书局1973年版。),唐代也曾有《唐四库搜访图书目》一卷(注:《宋史》卷二○四《艺文志》。)。北宋使这一优良传统得到继承和发扬。
其六为对校勘人员赏罚严明。以往各代在校理群书后对参与者进行赏赐的作法,在北宋也得到很好继承。从史书中可见:每次校勘之后皆立即赏赐,或升官晋级,或物质奖励。而对敷衍塞责者亦严惩不贷,最突出一例即在仁宗朝:“(天圣三年六月)丙辰,降直昭文馆陈从易为直史馆,集贤校理聂冠卿、李昭遘并落职。先是,从易等校太清楼所藏《十代兴亡论》,字非舛误而妄涂窜,以为日课。上因禁中览之,故及于责。”(注:《长编》卷一○三。又见《崇儒》四之六。)。这种严厉惩罚前代罕有,实为保证校勘质量的重要手段之一。
其七为注重校当代之书,如真宗咸平年间曾校“太宗圣制”之书,至景德四年,又校理太宗朝所纂之《文苑英华》。仁宗初年,从《册府元龟》中刚刚选编出《天和殿御览》,就立即进行校勘。哲宗朝校《资治通鉴》,距《资治通鉴》进呈时间仅一年多。这四种当代之书中,除“太宗圣制”外,其余三种都是政府组织编修之书。校当代之书实际上是校勘范围的一种扩展,是官府校勘进一步发展的标志。
此外,在任用专家校书方面,北宋也不逊于前代。已有文章论之颇详(注:参见肖鲁阳先生《北宋官书整理事业的特点》,《上海师院学报》1982年第1期。),本文不赘。
北宋馆阁校勘当然也存在一些问题,如神宗熙宁四年宋敏求的奏章中就曾提出锐批评:“今三馆秘阁各有四部书……虽累加校正,而尚无善本。”(注:《职官》十八之三。)然从整体上看,北宋在诸多方面皆超越前代,达到空前高度。且其影响深远:南宋校勘学硕果累累——产生第一部校雠学专著——郑樵的《校雠略》;诞生标志校勘格式规范化的《校雠式》;出现独立完整的校勘学专著——方崧卿的《韩集举正》等,其原因故可列出许多,然北宋校勘的高度发展,显然是最直接而重要的原因之一。总之,官府校勘至北宋已完全成熟,其中有些经验对今天的集体校勘仍是有借鉴意义的。
三
我国历史文献学的实践已有两千余年历史,而历史文献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建立,却仅为近年之事,文献学理论体系尚有待进一步发展完善。对北宋官府校勘进行考察研究,在文献学理论方面也可得到一些重要启迪。
首先是校勘与学术风气的关系。校勘作为文献学应用学科的五大分支之一,必然要受学术风气影响,但这种影响究竟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其程度如何,尚少有人论及。为说明此问题,我们先将北宋各朝的校勘次数列表如下(仅以开始之时计):
太祖1次仁宗
14次
哲宗3次
太宗5次英宗0次
徽宗9次
真宗19次
神宗4次
钦宗0次
从上表可看出:真宗、仁宗两朝是校勘活动最频繁时期:两朝时间跨度为65年,校勘次数为33次,平均频率约为两年一次;其余七朝共102年,校勘次数却仅为22次,平均频率约四年半一次。两相比较,前者为后者的两倍多。
上面勾勒出的校勘频率曲线,与北宋学术风气密切相关。
仁宗庆历前后,恰是北宋学术发生重大变化之时。此前学术思想基本上延续前代,继承者多,创新者少。至庆历年间,学术风气明显转变,疑经惑古思潮大兴,理学迅猛发展,这一深刻变化必然影响到学术界各个领域,从上表看,也极为直接地影响到政府校勘的频率——校勘的对象是古书,目的是扫清古书中的各种错讹,以便更好地向古人学习。庆历前的学风重在继承,自然就要校勘大量古籍;至“庆历之际,学统四起”(注:《宋元学案》卷六《士刘诸儒学案》《四部备要》本。),学者的兴奋点转向创新,校勘的频率亦随之明显下降。
这一影响在经部书校勘方面反映得尤为突出——若以庆历为界,则此前校勘经部书达13次,而其后则为0次!由此可见,一代学术风尚的变化对宫廷校勘的影响是何等迅捷与直接!
史书校勘一直是北宋统治者关注的热点,这与当时史学高度发展的状况是完全一致的。我国史学发展到北宋,呈现极为繁荣的局面:沉寂了数百年的编年史体,因《资治通鉴》的诞生而焕发出勃勃生机;史学领域大为扩展,金石用于考史,方志体例日臻完备;修史机构空前完善,官修史书的品种和数量皆远过前代。史学的繁荣对校勘也产生深刻影响,自太宗朝始,北宋馆阁不但校理了当时几乎所有已成书的正史,而且对前四史更是反复雠校,于刚修成的《资治通鉴》亦立即校定。其校史书的规模、次数与成效皆超越前代,为我国校勘学史增添了灿烂一页。
对北宋校勘的内容进行观察,又可探寻出官府校勘与国家军政大事(及帝王好恶)之间的联系。从四部分类的角度考察,北宋九朝校经部书13次,史部书12次,子部书19次,集部书2次,综校群书11次。其中最突出者为子书。
子书校勘的19次中,竟有8次为道家之书,且仅集中于两朝,即5次在真宗朝,3次在徽宗朝。其原因甚为明显:宋真宗是古代帝王中以尊崇道教著称的皇帝,他曾多次导演降“天书”的闹剧,又曾亲至泰山,举行封禅大典,还大兴土木,修建道观等。徽宗比之更是有过之无不及,连他本人也跻于道教神仙之列。这样的两个皇帝多次校勘道教之书自不足为怪了。而这8次在北宋全部55次校勘中占到七分之一强,由此可见:帝王的好恶对宫廷校勘的影响是何等直接和巨大!(当然,帝王好恶背后的深层原因,仍是当时政治统治之需。)
子书校勘的其余11次中,有5次是校医书。北宋期间曾有多次编修医书的活动,如太祖“开宝重订《本草》”,太宗朝编纂著名的《太平圣惠方》、《神医普救方》,仁宗朝编修《庆历善救方》、《简要济众方》(且专设“校正医书局”),徽宗更“御制”《圣济经》,并亲为作序。北宋统治者为何如此偏爱医书?除学术原因,即中医学经千余年发展、至北宋时需要总结外,是否还有其他原因?
政和八年蔡攸奏章道出了其中奥妙:“窃考《内经》所载,皆道德性命之理,五行造化之妙。”(注:《崇儒》四之十。)重和元年徽宗之诏讲得更为清楚:“朕阅《内经》,考建天地,把握阴阳,其理至矣。”(注:《崇儒》四之一一。)《内经》虽为医书,然古人认为“天人合一”,对人体的辨证也就蕴含着天地阴阳之理,“五行造化之妙”,因此也就包含着治理天下之“道”。夏竦为《天圣真经》所作序曰:“圣人有天下,论病以及国,原诊以知政。”(注:《玉海》卷六三。)这才是统治者偏爱医书的深意所在,即从哲学的高度看待医书医理,并从中体悟治国之道。
至于仁宗、神宗朝之两次校理兵书,显为当时军事之需。北宋至仁宗之时,无大战事已有六十余年,乃至士兵不识战阵,将领不谙兵法。康定年间西夏兵屡败宋军,引起朝廷对军事的重视,故此有嘉祐年间的兵书之校。至神宗朝,开始健全武学制度:“熙宁五年,枢密请建武学于武成王庙,……习诸家兵法”(注:《宋史》卷一五七《选举志》。),同时武举考试以“《孙》、《吴》、《六韬》义十道”为重要内容(注:《宋史》卷一五七《选举志》。)。元丰年间,神宗改制,进一步加强军事力量,因此才有元丰三年之校“武经七书”。
官府校勘集中反映出最高统治阶层的意向,而这些统治者思虑最多的恰是军政大事。他们在遇到疑难时,又总是从以往朝代的经验教训中寻求答案,这种崇尚古人、先哲的价值取向,必然使军政大事直接而深刻地影响到官府校勘的内容。
北宋官府校勘在许多方面都颇为突出,将我国校勘学水平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对其考察分析又可发现:一代学术风气迅捷而直接地影响着官府校勘的频率和内容;国家军政大事(及帝王好恶)也直接而深刻地影响着朝廷校勘的取向。要完善文献学体系,就应回答校勘学与学术风尚、社会状况之间的关系问题,希望上述研究能对此有所帮助。
本文涉及诸多领域,不妥之处在所难免,诚望方家斧正。
标签:宋朝论文; 郡斋读书志论文; 中国古代史论文; 读书论文; 宋会要辑稿论文; 道藏论文; 册府元龟论文; 汉书论文; 西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