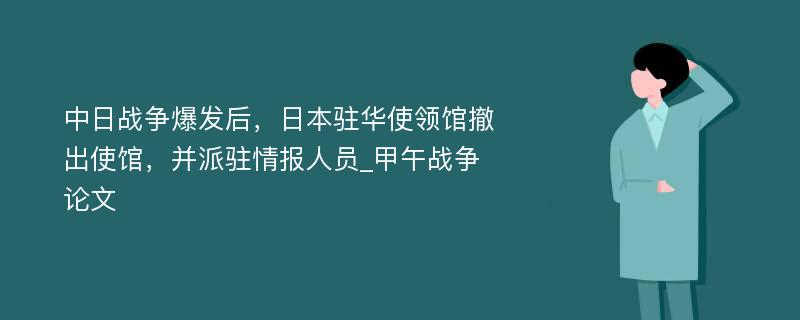
甲午战争爆发后日本驻华使领馆撤使与情报人员的布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使领馆论文,甲午论文,日本论文,情报论文,战争爆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甲午战争爆发后,中日两国各自撤离驻在对方国家的使领馆,一般认为这不过是一项战争爆发后的善后工作。但对于精心策划这场战争的日本方面而言,撤使可谓是其备战的一个组成部分。 1894年7月25日,日本在牙山海面不宣而战,挑起中日甲午战争。但早在一个月之前的6月下旬,日本已着手秘密向美国托付开战后代为保护其在华利益事宜,至8月1日中日两国正式宣战,日本代理公使小村寿太郎一行撤离北京,日本的撤使准备前后长达一个多月。其间,日本为了赢得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支持,精心为战争准备了一套说辞。 日本撤使准备虽早,但战争爆发后日本却等待中国驻日使馆拟正式撤离东京以后才迟迟下达撤使命令。不仅如此,日本还只准备撤离长江以北各大使领馆,试图以局外中立之名保留其上海总领事馆及所辖长江以南大片地区的日本势力。后因清政府强烈要求,加上中国民众群情激愤,在顾虑重重的美国驻华使领馆的敦促之下,日本才不得不撤离所有在华使领人员及重要通商口岸的日本侨民,但仍用各种巧妙的办法在中国各军政要地用心布留间谍人员,继续探查中国军情民情,为战争输送情报。 日本撤使是日本在华势力的大起底。撤使过程中,日本与美国、英国、法国等西方列强多有互动。考察甲午战争爆发后日本复杂的撤使始末,可以揭示日本阁议正式启动战争准备的大概时间、其向国际社会所宣传的战争理由、甲午战争爆发前后日本在华势力的分布及间谍人员的活动等,为我们审视甲午战争开战前后日本备战之精心、中国应战之被动、欧美势力在战争中的复杂立场等提供事实依据。 目前,海内外学界关于这一问题的专题研究还没有看到。日本驻华使领馆撤离经纬史料,中方档案文献虽有一定记载,但主要保存在日本和美国的档案中。本文试利用中、日、英文未刊和已刊档案,结合相关文献,就甲午战争爆发后日本撤使问题做一较系统的考察,以求教于方家。 一、委托美国代为保护在华利益 甲午战争爆发后,日本外务省在致其驻华使领馆的训令中,开篇即称因中国已撤离驻日公使馆,故日本驻中国公使馆、领事馆及邮局也将撤离。日本政府令驻美公使建野乡三“公开”向美国政府提请代为保护在华利益,也是在接到中国驻日使臣汪凤藻致日本外务省的撤使照会之后。① 中国政府正式商讨撤使是在丰岛海战爆发后②,而日本早在此前一个月已通过阁议决定采用秘密方式就撤使问题与美国政府接触,当时中国正在为阻止战争想方设法。 6月28日,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质问朝鲜外署,朝鲜究竟是否中国属国,限次日回复,引起中朝两国极大不安。次日,日本外务副大臣林董奉外务大臣陆奥宗光之命访问美国驻日公使谭恩(Edwin Dun),开始向美国请托日本撤使护侨事宜。林董称,虽然朝鲜的状况没有改变,日本政府也希望以和平方式解决与中国的麻烦,但两国关系非常危急,日本随时可能从中国撤回公使馆和领事馆。他又称,只要与中国的和平商谈仍有望,日本不会向美国提出代为保护的要求,但万一与中国的和平关系中止,请美国保护日本在华利益,询问美国意向。③显然,日本强调的是它正在不断寻求和平方式与中国处理朝鲜问题,向美国提出保护日本在华使领馆问题是在万一和平无望情况下的一种准备而已。林董访问谭恩虽是一次非常私密的行动,但这不仅仅是奉外务大臣陆奥个人的指令,而是日本政府的阁议决定,是日本准备开战的一个环节。④ 林董的要求事关重大,谭恩回称需致电国务卿葛礼山(Walter Q.Gresham)请示。⑤当天,谭恩将林董来访之意简要致电葛礼山。⑥次日,又将会谈情形用信函做了详细汇报。⑦ 如上所叙,林董拜访谭恩前一天,日本逼迫朝鲜否定与中国的宗藩关系,并要求朝鲜外署于次日回复。通过驻朝公使西尔(John M.B.Sill),美国政府已于第一时间获知日本逼朝否定华属消息。当时,朝鲜驻美公使李承寿三访美国国务院,提请美国政府协同其他各国一起出面促使日本从朝鲜撤兵,遭葛礼山婉拒。⑧28日,谭恩也已致电本国政府,告知日本政府和朝鲜政府之间的关系已“非常危急”,尽管谭恩受日本影响,认为日本是期望一个和平的改革的。⑨由此可见,至少在大鸟逼朝否定华属时,日本已有撤使打算,也就是正式启动战争准备。当时俄国和英国先后出面调停拟让中日同时从朝鲜撤兵。7月初,日本被迫接受英国建议,派遣驻华代理公使小村寿太郎来与总理衙门商谈,但事实很快证明小村前来会商完全是应付国际社会的缓兵之计。对此,美国政府也在留意观察。 美国政府接到谭恩有关日本要求委托电报后,告知将会认真友好地考虑,但如果没有获得中国同意,则不能接受这一委托。⑩美国于7月13日较正式地答复日本接受护侨委托。此前这段时间,美国政府一直在观察朝鲜局势及中日关系的走向,进一步确认日本派兵朝鲜的真正原因,且毫不掩饰地向日本指出其在有意引发战争。对此,日本各方准备了一套既定的“美好”说辞来影响美国。 林董访问谭恩后几天,葛礼山与建野乡三会谈,顺便谈到了朝鲜局势。葛礼山表示,美国希望中日共同从朝鲜撤兵。建野则回称,朝鲜内乱的根源在于内政腐败,日本在朝鲜完成必要的内政改革之前不会从朝鲜撤兵。于是,葛礼山表明两点意见:一是希望日本善待这个羸弱无助的邻国,以保持朝鲜局势和平;二是美国“真诚地尊重”中国和日本,但他直截了当地指出,日本显然有意促使中国走入战争。对此,建野表示,日本政府没有侵占朝鲜领土的野心,日本期望朝鲜和平,承认朝鲜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11) 葛礼山也致电谭恩,指示确认日本派兵朝鲜的理由及其要求。7月5日,谭恩回复称,日方称其派兵是根据《济物浦条约》,而增兵是因为中国大量派兵的缘故。至于日本驻兵朝鲜的理由,谭恩据日方说辞,称朝鲜叛乱的根源是政府当局的腐败与压迫,日本提出联合中国一起彻底改革朝鲜行政以确保长久和平,但遭到中国反对而无法推行。日本否认对朝鲜具有领土野心,而决定将无视中国的态度继续推行朝鲜的行政改革。(12)日本竟然将大量派兵与驻兵朝鲜的理由完全归咎中国,而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始终强调它对朝鲜没有领土野心。 谭恩的报告与美国驻华代理公使田夏礼(Charles Denby,Jr.)的报告出入很大。3日,田夏礼在致国务院去电中指出,朝鲜局势危急,中国尽管受到日本步步紧逼,但仍持和平怀柔政策,并已约请英国和俄国出面进行和平调停。(13) 8日,英国驻美大使果然带着外交大臣的命令前来拜访葛礼山,目的是想确认美国是否愿意联合英国一起参与调停以防止中日之间爆发战争。葛礼山婉转谢绝,表明美国将采取中立而不是干涉的立场。次日,葛礼山进而将一份7月7日致谭恩命令的复印件递送英国驻美大使,告知美国政府不会与其他国家连同参与调停。(14)在英国出面约请美国调停的同时,李鸿章也通过美国驻华代理公使田夏礼提请美国协同列强一起促使日本从朝鲜撤兵。(15)美国既已向驻美英国大使表明立场,自然不会答应中国的请求。 11日,谭恩拿着葛礼山7日的命令进一步与日本政府沟通。日本仍然坚持原有说辞,称日本不从朝鲜撤兵并不是为了在朝鲜制造战争,而是为了确保朝鲜的秩序、独立,防止再次出现叛乱。日本希望在朝鲜进行改革,但是中国模棱两可的态度阻止了朝鲜接受必要的改革,继而危及远东和平。日本竟然将破坏和平的责任完全推给中国。日本还宣称,朝鲜的暴乱还没有完全平定,日本在确定朝鲜将来秩序确有保障之时,而不是之前,才会撤兵。(16)陆奥宗光在《蹇蹇录》中曾明确表示,所谓改革朝鲜内政,完全是日本用来挑起战争的手段而已。清政府方面其实并不反对朝鲜改革内政,李鸿章还因此作为促使日本撤兵的“釜底抽薪”之术,令袁世凯“切劝”朝鲜自行改革内政,但朝鲜积弊由来已久,绝非短时间内可一蹴而就。 对此,美国应该还是看得清楚的,但美国所奉行的所谓中立的、不干涉的立场丝毫不为所动。13日,中国驻美使臣杨儒奉李鸿章之命拜访葛礼山,试图继续劝说美国出面调停。访谈中,杨儒提请葛礼山注意朝鲜的现状,指出大量军队驻扎朝鲜,中国提议同时撤兵,但日本以劝诱朝鲜改变内政为由拒绝。杨儒希望美国政府联合各国代表设法让日本放弃向中国挑衅的做法。杨儒进而表明,中国始终坚持和平政策,绝对无意与日本或其他任何国家开战。葛礼山还是重复美国不干涉的立场。杨儒于是指出,日本在实行上述名义的改革之前拒绝撤兵,恐怕战争已不可避免,除非列强对日本施加强大的影响,并询问葛礼山对朝鲜局势的看法,以及改变这一局势的建议。葛礼山以各国调停来安慰杨儒,认为列强已同意出面调停,意味着提供了和平解决争端的途径。(17) 就在杨儒拜访葛礼山当天,日本政府收到美国答复:如果中国政府不反对,美国政府可以接受日本的护侨委托。 日本政府在开始秘密向美国政府委托护侨之初,已向其驻华使领馆发出相关指令。由于美国方面没有在第一时间明确答复,所以日本政府最初在致使领馆密令中,只称中日“谈判破裂”后,日本驻北京公使将托付“外国公使”保护在华日本人,尚未明确指为美国。(18)这里的“谈判”,当指其时在英国调停之下小村与总理衙门的撤兵谈判。谈判自3日开始,7日和9日继续,共进行三次。对于这次谈判,中方充满期待,但小村于会商情节迟迟不予答复,至14日突然向总署发来了一份态度极其强硬的照会,宣称会商失败,且将失败的责任完全归咎于中国。这份照会史称“第二次绝交书”。这一天,正是日本接到美国政府正式同意代为护侨的次日。13日,陆奥宗光第一时间将日本政府托付美国护侨的阁议及美国政府的答复,以训令形式发送驻华代理公使小村寿太郎,令秘密转达驻华各领事。(19)19日,美国政府进而告知日本,一旦战争爆发,美国将负责保护日本的在华利益,条件是中国在日本的利益也将由美国政府负责保护。陆奥随即又将此意致电小村,指示紧急情况下可立即向美国驻华公使提请保护。(20)这样,日本向美国委托护侨的事宜在秘密中基本完成。 20日,葛礼山已经看到战争不可避免。当天,他写了一封长信给美国驻英国大使托马斯·巴(Thomas D.Bayard)。信中,他详细回顾了朝鲜问题之所以发展到如此地步的前因后果。尽管他为此表示一定遗憾,但这封信的主旨显然在于阐明美国政府的立场,即采取不干涉的立场不变。这一天,离日本占领朝鲜王宫仅仅3天,离日本军队在牙山口外率先向中国军队开炮也只有5天。 23日凌晨4点,日本军队攻入朝鲜王官,汉城陷入巨大混乱。情急之中,日本有意为美国驻朝使馆提供帮助,但美国驻朝公使西尔没有坦然接受,他认为此种行为不符合美国政府既定的中立方针。报告中,西尔对于日本挑发战争的侵略行径似也无好感。(21) 美国“中立”的立场未能阻止战争。这一“中立”立场在战争爆发后体现在:美国一方面接受日本请求保护日本在华使领馆及侨民;另一方面则主动向中国表示战时愿意承担相同的委托。 由上可知,日本直到率先开战,在与美国解释朝鲜问题时一直虚与委蛇。撤使意味着认定两国关系破裂,进入战争状态。从日本向美国委托保护准备撤使来看,日本至少在牙山开战前近一个月已进入最后的战备阶段。 美国所答应的“保护”是一个笼统的承诺。为此,美国驻华使领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由于牵涉日本间谍案等复杂情形,与中国政府发生摩擦,因此还就“保护”的性质及权限作进一步补充,详参下文所论。 二、北方各大使领馆的撤离 甲午开战前夕,除北京公使馆外,日本还在天津、烟台(即芝罘)、牛庄和上海设有领事馆,广州、汕头和琼州则由香港领事馆兼辖。战争爆发后,日本外务省并不计划撤离所有在华使领馆,而只准备撤离长江以北的使领馆。上海总领事馆及其所辖长江以南广大地区则拟以局外中立的名义,仿照中法战争时期法国驻上海总领事的做法不撤。撤使工作首先在北方各大使领馆中展开。 (一)驻北京公使馆的撤离 日本虽于6月29日已秘密向美国提请撤使后代为保护,但日本使领馆撤离中国最早的动议却来自中国方面。 7月28日,丰岛海战后第三天,李鸿章连连致电总署,称日本“先开战”,日本驻京公使及各口领事“应讽令自去”。李鸿章的这一建议,一方面是按照国际公法的规定两国开战应令敌国公使、领事限24小时内出境;另一方面也由于日本驻天津领事馆密集的谍报活动令中国方面倍增反感。(22)29日,光绪皇帝谕军机大臣等电寄李鸿章,鉴于日本已绝好开衅,令出使日本大臣汪凤藻即撤离回国。(23)当天,李鸿章即遵旨转电汪凤藻。(24)汪凤藻致日本政府的撤使照会,成为日本政府正式启动撤使的直接动因。 30日,日本获悉中国驻日使团已接奉撤使命令,又据代理公使小村寿太郎的相关电报,断定清政府认为中日之间已开战。(25)当天,陆奥宗光上奏明治天皇,称既已与中国就朝鲜事件开战,日本驻中国的使馆已不得不撤回;拟委托美国驻华公使代为保护在华日本臣民,保存公使馆记录;向临时代理公使小村发送归国训令,请明治天皇裁可。(26)上奏很快获准。 陆奥继而落实请美国保护事宜。他先致电小村令与美国驻华代理公使田夏礼沟通。30日,田夏礼应小村要求致电谭恩,请谭恩通知日本外务大臣立即将保护日本在华利益事宜转交美国当局。(27)但这封电报外务省8月1日才收到。31日,陆奥致电驻美公使建野乡三,令“正式”向美国国务卿提请战时保护日本在华利益。(28)同日,陆奥通过上海总领事大越成德向日本各驻华使领馆转发撤使训令。训令称,因中国已撤离驻日公使馆,故驻中国日本使领馆也将撤回;使馆文件和日本公民请各所在地美国使领馆负责保护;立即撤回驻北京公使馆、驻天津领事、驻烟台领事、驻牛庄名誉领事所有日方使领馆人员及邮局;同时寄送相应撤使费用。训令并不准备撤离上海总领事馆,令只要无危险之忧尽可能不撤,总领馆改挂美国国旗。(29)就在陆奥发出撤使训令的当天,清政府也向日本驻华使馆发出撤离照会,内称: 所有朝鲜一事,中国与贵国意见不同,犹希冀从长计议,无损邦交。乃贵国之兵忽于本月二十三日在朝鲜牙山海口伤我运船,先启衅端,致两国修好之约从此废弃。此后本署与贵署大臣更无商办之事,殊为可惜。(30) 清政府要求小村一行次日离京。在有限的时间内,日本要在东京、华盛顿和北京之间完成正式托付美国代为保护事宜,看似紧张,但由于事先早有准备,与美国的沟通基本是走程序。 当时,驻华的临时代理公使小村寿太郎自东学党起义以来,与驻朝公使大鸟圭介一起一直参与战争过程的策划与实施。7月初,在英国调停下,小村曾奉命与总理衙门进行开战前的最后“商谈”,以为拖延之术。14日,小村又遵奉陆奥宗光之命向清政府发出“第二次绝交书”。当时,小村就时时“参照”在汉城的大鸟圭介“尔时的举动”。当他听闻大鸟在汉城擒拿朝鲜国王时,已感觉和平无望。27日,小村接到丰岛海战电报,明白日本政府已“断然开战”。(31) 如上所述,小村早在7月中旬已接到陆奥委托美国代为保护的密令。接到清政府撤离照会之前,小村已按照陆奥训令与美国驻华代理公使田夏礼沟通。接到清政府撤离照会后,小村第一时间通告了田夏礼。(32) 8月1日,清政府发布宣战布告。当天,小村照会田夏礼,拟于当天下午携同所有使馆人员离开北京,希望田夏礼按照两国政府既定安排,“立即”代为保护日本使馆及在华利益。(33)田夏礼当即回复,将遵从国务卿指令接受小村的要求;他也将致电美国驻中国各领事馆和在华盛顿的国务卿通告实行代为保护事宜;他还将与中国政府立即就此事进行沟通。(34)当天,田夏礼照会总署,表示嗣后居住各口的日本侨民均在他本人及美国驻各口领事保护之下,希望总署即咨行各省转饬各海关地方知照,并希严饬各地方官保护在各口日本侨民。照会最后要求中国政府对于在各省并满蒙地方游历寄寓者,“亦一体保护,使之安稳回到各口”。(35) 同日,小村回复总署照会,称“本日带领随使司员等起身回国”,声明在中国的日本臣民“均归美国政府保护”。(36)小村同时致电外务大臣陆奥宗光报告他即将离开北京,美国公使馆已负责保护日本在华利益。小村这份8月1日下午2点多从北京发送的电报,3日才抵达东京。(37) 8月1日,小村携带国旗、官印及“公秘书类”,率领公使馆二等书记官中岛雄、三等书记官郑永昌、外交官补松方正作、书记生高洲太助及在京10名日本人,从北京出发回国。 其时,可能由于小村电报迟滞的缘故,尚未得到最新情报的外务大臣陆奥宗光仍通过日本驻美国使馆进一步向美国国务卿确认代为保护事宜。4日上午,陆奥收到驻美使馆二等书记官电报,获悉美国驻北京代理公使已奉命保护日本驻华公使馆,且将进一步提供一切合适的友好的帮助。的确,葛礼山是于第一时间命令田夏礼履行代为保护的要求的。2日,田夏礼回复葛礼山,报告已确保承担代为保护之责。次日,葛礼山将其与田夏礼确认保护事宜的来往电报情形电告谭恩。6日下午,陆奥接驻美公使馆二等书记官来电,称美国已落实保护之责。(38) 小村一行2日清晨在通州坐船起航,3日上午到达天津三汊口。从三汊口到大沽,北洋大臣李鸿章派遣亲兵2名士官、40名士兵和2艘炮船前来护卫。途中小村与前来迎接的美国驻天津领事李德(Sheridan P.Read)相会并商谈尚滞留天津的日本侨民事宜。4日,小村一行乘坐小汽船从天津出发,到大沽后换乘英国轮船“通州”号。8日抵上海,与驻上海总领事大越成德、驻天津领事荒川巳次、驻烟台领事伊集院彦吉,及公使馆步兵少佐神尾光臣、海军少佐井上敏夫等相会。12日乘坐法国船“亚拉”号从上海出发,14日到达长崎,15日经神户,17日抵达东京。(39) 日本北京公使馆的撤离得到李鸿章派遣人员的保护,可谓一路顺风,但这个顺利一定程度上是由驻天津领事馆的经验教训换来的。 (二)驻天津领事馆的撤离 日本向来将天津作为侦察清政府军事政治动向的重点。公使馆的武官长期驻在天津而不是北京。天津也是日本侨民的一大集中地区,同时又是战事最敏感区域。丰岛海战消息传到天津后,天津一下子人心激昂。其时,日本外务省致天津领事馆的撤离训令通过上海总领馆转发,由于种种原因,天津领事馆8月2日上午才收悉,所以当8月1日天津领事荒川巳次接到小村一行撤离北京的电报时,尚不确定天津使领馆是否需要同时撤离。可以说,天津领事馆的撤离远没有北京公使馆那么从容镇定,且引发了甲午战争时期影响重大的“重庆”号事件。 7月26日下午,天津传来日本突袭“高升”号消息,大街小巷种种反日传闻一下沸沸扬扬。26日以后,中国电报局已不办理一切暗号电信,领事馆与外务省等的通信完全断绝,中日朝事交涉的前景又无从打听,荒川甚为紧张。31日下午,租界外接近日本领事馆的中国街道还出现数十名清兵,日夜不离;各国人士告诉荒川“危险”正在迫近。其时,美国驻天津领事李德及翻译官,英国驻天津领事窦士德(Henry Barnes Bristow)、工部局书记等在没有接到本国政府指令的情形下,主动给予日本领事馆切实援助。李德于31日夜并与窦士德一同拜访李鸿章秘书罗丰禄,提请清政府此际有必要保护日本官民。清政府因担心出现意外,答应了李德等要求。李鸿章并派遣多名士官、营兵前来护卫领事馆,并答应可随时增添防卫力量。(40) 只是,“高升”号事件点燃的民愤还是影响到了天津的日本侨民。他们络绎不绝前来领事馆询问事态发展趋势及去留。荒川由于尚未接到撤使训令,只能发布安民告示,称形势的发展还难以预测,令先各自安居乐业。尽管如此,从31日开始,天津的日本侨民已陆续开始自发撤离。自7月31日到8月1日,约有30名日本人乘上英国轮船“重庆”号决定离津。其时,荒川也在着手准备紧急撤离,他并经与英国驻天津领事商量,决定先送妻女乘坐“重庆”号前往上海。当天下午5时多,荒川妻子和2个女儿,1名书生,2名婢女在美国领事等护送之下,从天津乘坐汽车前往大沽搭乘“重庆”号。(41) 当天下午4点多,荒川接到小村电报,称当天已从北京出发,令荒川向美国领事请求监护日本领事馆和日本侨民,且令在内地的日本人回到通商口岸。荒川接电后立即拜访美国领事商议,并于当天向日本侨民发布一个新告示,宣称中日两国之间和平已破裂,在华日本侨民从当天开始全部受美国驻天津领事李德的保护。荒川同时发布号外,宣布领事馆当天开始闭馆。然而,荒川至此仍未收到外务省经上海总领事馆转发的撤使训令。其时,李德为使南下中的日本使馆人员安然离津,提议荒川与英国汽船公司太古洋行商议,让当天即将拔锚南下的唯一一艘汽船“重庆”号暂时滞留,等待正在撤离途中的小村一行到达。考虑到天津与上海之间航船较少,荒川接受李德建议,向大沽引船会社办理了约定事宜。(42) 8月2日上午,荒川终于接到了自上海转发的撤离训令,决定与南下途中的小村一行一起经上海撤回,开始着手收拾公用文件及馆内物品准备撤离。正在此际,天津海关雇佣的港长急急忙忙来馆报告中国士兵闯入“重庆”号事件。从后来李德致李鸿章的信函可知,“重庆”号事件其实只是虚惊一场。清兵将“重庆”号上的日本人带离轮船,于当天就释放回船,并没有发生流血事件。(43)但这一事件后来不仅与“高升”号事件相提并论,且直接影响到日本使领馆的撤离。 负责代为保护日本利益的美国领事李德于2日当天照会李鸿章,声称尽管“重庆”号人员被安全放回,但由此表明日本人撤离回国存在很大危险。他尤其提到正自北京南下天津途中的小村一行,认为出于人道和国际法都应给予保护。(44)李德的照会引起了李鸿章的高度重视。小村一行3日上午到达天津三汊口,从三汊口到大沽,李鸿章派遣亲兵一路保护,直到小村一行安然登船,已如上所述。 荒川巳次也得到了李鸿章的进一步照顾。8月2日下午,天津海关长和港长奉李鸿章之命,派遣一艘海关小汽船前来接应。荒川本计划与小村一行一起南下,且在李德的建议下已让“重庆”号多淹留一个潮时。小村一行可能较预期迟到,荒川便向“重庆”号所属汽船公司提出再淹留一个潮时(45),遭到拒绝。洋行代理人在回信中称,“重庆”号最晚必须在次日上午6点离开大沽港,不过该公司另一艘上海汽船“通州”号将于3日早上抵达大沽,使馆人员一行来不及可改乘“通州”号。太古洋行态度的变化,主要是受“重庆”号事件的影响。(46)荒川考虑到3日“通州”号将抵达大沽,未再考虑小村一行是否抵津,先将公私物品分置馆内各室,领事馆房屋一一封印,并与美国领事办理了交接手续。在海关小汽船的接应之下,荒川于2日晚上9点左右,携带贵重物品,与领事馆员、天津邮局人员及美国领事等一起离馆,先于小村一行撤离天津。同船的有公使馆陆军步兵少佐神尾光臣等16人,还有山田要、堤虎吉(海军大尉泷川具和的化名)、石川伍一、钟崎三郎、青木乔、佐伯重太郎。其中,从事摄影业的佐伯未向领事馆备案外出旅行未归。山田要、堤虎吉、石川伍一、钟崎三郎均是大名鼎鼎的间谍。小汽船安然经过大沽炮台等数个炮台,3日上午6点左右到达前一天从塘沽移泊到洋面的“重庆”号,与前来乘坐的其他日本人员相会。同船日本人除16名天桥丸乘组人员外,共48人。曾与荒川一起乘坐海关小汽船离津的山田要、堤虎吉、石川伍一、钟崎三郎、青木乔等均不在名单之中。(47)从后来代理公使小村寿太郎的撤离报告中可知,这些人其实折回天津潜伏了下来。 荒川提到的48人还不是天津日本侨民总人数。4日小村一行行经天津时,李德曾特意建议小村把剩下的日本人全部带离天津。李德主要担心“高升”号的幸存者回到天津后将引发底层人民的暴动,他认为像这种极端的行为远不是中国政府所能控制的。他甚至将这种可能的暴动与1870年的“天津教案”相提并论。(48) 顺便应该说明的是,天津领事馆撤离过程中发生的“重庆”号事件中,虽然荒川夫人在船上,但享有外交保护特权的荒川本人并不在场,不存在外交保护问题。其实,清兵进入“重庆”号并非为了伤害日本侨民,而是为了搜查荒川夫人一行随身携带的文件。(49)的确,这次清政府搜查到了化名为堤虎吉的海军大尉泷川具和致使馆武官海军少佐井上敏夫等的密函(50),进而破获了一起重大的间谍案。中国方面还将“重庆”号事件与“高升”号事件联系在一起,提出按照国际法,“总须日本将高升伤毙人命遗失财务恤偿之后,中国方能将重庆失物一案按照实价赔补。”(51)最后,“重庆”号事件由大沽炮台以二十一响礼炮道歉而结束。 (三)驻烟台和牛庄领事馆的撤离 相比较京津地区,日本驻烟台和牛庄领事馆所在地可谓人烟稀少,撤离问题看似较为简单。不过应该注意的是,这两个地方尤其烟台最靠近北洋舰队基地,烟台和牛庄领事馆的撤离也并非毫无惊险。可以称为日本近代史上最闻名的间谍之一宗方小太郎,就是在领事馆撤离过程中被巧妙而成功地安排潜伏下来的。 丰岛海战爆发后,烟台海关道直接将部下一队海防卫兵布置在外国租界附近,安排四五名士兵昼夜巡逻,当地中国人对日本领事馆并没有过激举动,日本领事可以照旧处理馆务。8月1日深夜,驻烟台领事伊集院彦吉收到驻上海总领馆转发的外务省撤离训令。次日,领事馆下旗闭馆,并通知烟台海关道及在烟台各国领事。(52) 当天,烟台道台通知伊集院,据北洋大臣致总理衙门电报,谕令日本各领事馆出境。(53)对于道台转达的这份通告,伊集院还颇有微词,认为“文句有不妥之处”,但中日既已断交,他无从争辩,但也未予答复,转而着手撤使准备。(54) 伊集院撤离准备的首要之事,是根据外务省指令就侨民和领事馆管理问题与当地美国代理领事商议,但当时美国领事因商务不巧出差。该美国代理领事本是英国人,伊集院于是通过该领事家族与驻烟台英国领事商谈,最后,英国领事馆警部接受了美国代理领事的委托,暂时代为护馆护侨。其次是领事馆房屋继续租赁问题。伊集院与其中一位房主的代理人完成了继续租赁事宜。其他房主虽未联系上,但伊集院据此认为房主应该没有异议。(55)而更为主要的是对在烟台日本人的撤离安排。 当时留居烟台的日本人大致有三种类型,一是领事馆人员,二是一般侨民,还有一种非常特别的就是领事馆指挥下的间谍人员。领事馆人员不多,除伊集院,尚有使馆武官海军少佐井上敏夫。领事馆看守和邮局小使均雇佣中国人,不涉及撤离问题,但正是这些中国人,稍后为伊集院布置间谍人员提供了掩护。日本侨民很少,有一对姓高桥的夫妻及一起居住的2名男女,计4人;另有3名受雇于西方人的日本妇女。(56)这位高桥与使领馆的关系非同一般。间谍人员如天津的青木熊三郎、钟崎三郎等来烟台就住高桥处,还曾与宗方小太郎在高桥寓所“会餐”。(57)高桥一行4人后随同伊集院一起撤离,3名受雇于西方人的日本妇女则各随其雇主住在西山头、崆峒岛和胡矶岛。伊集院以书面形式通知各位雇主,一旦有危险,可托付回烟台的美国领事保护。最引人注目的是对赫赫有名的大间谍宗方小太郎的安排。当时,宗方正奉海军省密令在井上敏夫指挥下潜伏在领事馆内,以侦察烟台附近的中国军事。领事馆撤离后,宗方必须仍留烟台,但烟台地方狭小,潜伏市中终究困难。伊集院经与井上敏夫协商,作了一个非常“巧妙”的安排:宗方伪装成看守领事馆的中国人留在馆内。伊集院并将此意预先“公然”通知中方道台及美国领事,称领事馆撤离后,3名一直以来作为领事馆看守人的中国人及一名邮电局小使中国人共4人将留在馆内。(58)这4名“中国人”中,有一人就是宗方小太郎。 8月4日上午,天津领事荒川一行乘坐的“重庆”号进入烟台港。当天,美国代理领事也从上海回烟台。下午5时,美国代理领事前来与伊集院碰面,将领事馆各屋加上封印,置于其保护之下。伊集院一行,包括井上敏夫及4名侨民同船离开烟台,与小村一行在上海会合后一同回国。(59)留在烟台的日本人只剩宗方小太郎一人。8月6日上午,小村一行乘坐“通州”号南下时途经烟台,宗方将两封有关“北洋之动静”的报告托付书记官中岛雄带到上海。当天晚上,清政府招商局及道台衙门官吏来“似有所探查”,但也没有发现宗方的踪迹。(60) 当时,日本驻牛庄的领事是英国人班迪诺(J.J.Frederick Bandinel)。班迪诺自1876年开始一直是美国驻牛庄代理领事。也就是说,班迪诺其实在代理日本名誉领事的同时,仍是美国驻牛庄的代理领事。由于这种双重身份,牛庄领事馆的撤离较其他各领事馆简单,至少省略了移请美国领事馆代为保护的交接手续。 牛庄领事馆的日本馆员其实只有书记生天野恭太郎一人。班迪诺奉陆奥宗光指令所要进行的撤离工作,首先是如何让天野按时、安全地回国。(61) 班迪诺的撤离准备主要从7月29日开始。为了避免可能的麻烦,他于当天致信当地中国道台,询问是否同意天野乘坐即将开往日本的“飞龙”号轮船,道台次日回复表示同意。(62) 8月1日中国宣战当天,班迪诺收到田夏礼来电,令自当日起将日本在华利益置于美国保护之下。同天晚上,他又收到小村来电,称他将于当天离开北京,令将日本国民转由美国领事保护,并令在内地的日本人回到通商口岸;如果没有别的指令,书记生天野恭太郎需离开牛庄。班迪诺8月2日上午近8点时收到由上海转发、陆奥签署的撤离电令,令将文件和日本国民托付美国领事保护,让天野立即回国。(63) 天野回国较为简单。班迪诺事先已与牛庄的道台顺利沟通,接陆奥电令后,班迪诺安排天野乘坐一早出发开往神户的汽船“飞龙”号直接回国。(64)包括小村一行在内其他日本使领人员均汇集到上海后一起回国,唯有牛庄的天野从当地直接回日本。 当时在牛庄的日本侨民人数不多。除一名三井物产会社员工外,其余均为妇女。其中有3名是海关领航员等西方人的小妾,另有12名卖春女。丰岛海战的消息传到牛庄后,人心不稳,各种传闻纷至沓来。为加强警备,原居住在外国租界外的三井物产会社社员直接转移到了租界内。三名洋妾经与雇主交涉后回国。(65)让班迪诺费周折的还是12名卖春女的撤离问题,班迪诺的撤离报告约用1/4的篇幅来汇报他为此而进行的交涉。这些妇女最后经与雇主协商总算解雇,在宣战前后全部从牛庄出发回国。6日,据班迪诺报告,除一位名叫Shinada的之外,牛庄已无一个日本人。这与稍后田夏礼给的报告一致。留下的这一人,可能是搬迁到外国租界内的三井物产会社的员工。据班迪诺称,这位员工如战时继续留在牛庄,将会搬到他的宅邸居住。(66) 三、上海总领事馆及长江以南地区日本侨民的撤离 根据日本外务省训令,驻北京临时代理公使小村及驻天津、烟台、牛庄领事和名誉领事经上海撤离回国,不包括上海总领事馆。外务省要求上海总领馆在没有危险的情况下尽量不撤,改挂美国国旗。上海使领馆最终撤离,是在中国政府的要求下“被迫”的。(67)上海总领馆拟不撤的安排,并非日本政府一时动议。早在日本秘密托付美国护侨之初,驻上海总领事大越成德就已向陆奥宗光商议不撤细节。大越向陆奥提议,当年中法战争之际,法国公使托付俄国公使保护在华法国人,上海法国领事馆接到开战电报后,即改挂俄国国旗而未撤。中日一旦开战,上海总领馆也拟仿照法国领事馆先例实行。(68) 8月1日下午,大越成德接到外务省宣战训令。大越此前曾接外务省训令,令开战后在留日本人全部托付美国保护。为此,接宣战电报后,大越首先向美国驻上海总领事佑尼干(T.R.Jernigan)通报此意,协商保护侨民及其他善后事宜。2日早上,佑尼干收到驻华代理公使田夏礼的有关保护在留日本人的电报后,将此意直接照会上海道台,并转电南部及长江沿岸各口美国领事。同日,大越向侨民宣布保护事宜已移交美国总领事馆。(69) 大越成德接外务省宣战电报的同时,另接陆奥训令,命将陆奥的撤离训令转电北京公使馆及北方各领事馆。丰岛海战后中国电报局不再办理所有暗号电信,大越也只能通过中国电报局转发,入夜才转发成功。外务省撤离训令不包括上海总领馆所辖地区,大越打算按照与外务省原先商定的方案改挂美国国旗。但美国驻北京公使馆致其上海总领事的电文并未提及变换国旗事,所以美国总领事声称,日本总领馆并无悬挂美国国旗的权利。(70) 其时,上海道台根据总署旨意要求日本总领馆尽快全部撤离。大越考虑到上海其实还不能算是完全的局外中立地,不得已他通过佑尼干回复上海道台,希望等待临时代理公使小村一行抵达上海后一同回国获准,大越并将这一情节向外务省请训。5日,大越接外务省回训,令与小村一行一同回国。7日、8日,临时代理公使小村寿太郎、天津领事荒川巳次和烟台领事伊集院彦吉等先后到达上海。大越向侨民等留下告辞书,于11日随同一起乘坐便船回国。(71)大越及总领馆人员虽然撤离,但上海所辖地区在留日本人远较其他地区复杂。 上海总领事馆辖区不仅包括《中日修好条规》所指定的通商口岸上海、汉口、福州、九江、镇江、宁波、厦门等地,还包括非通商口岸的芜湖,那里也有日本人,加在一起总人数1000多人。其中上海最多,达1000左右;汉口、福州各有20名;九江、镇江、宁波等有一二家杂货店;厦门住着一些日本船夫,人名和人数不详;芜湖有一家日本人开办的杂货店。起初,大越并不打算公然通知侨民回国,以免引起恐慌。鉴于地区分散,自卫不便,不少通商港口尚未设立规范的租界制度,外国领事也多不在其地居住,为此大越计划采取将分散的侨民集中到二三地方的方针。具体而言,以上海、福州、汉口为根据地,如遇危险,日本人就近撤离退到此三处。为稳定人心,大越并没有以公告形式通告这一方针,而是通过上海侨民中与他们有关系者“私下”相告。随着中国各地人心激昂,备战气氛日益浓厚,大越实际上已开始分别布置各大城市附近的日本人展开撤离工作。(72) 大越以个人名义下令在镇江及其他地方的日本人向上海或汉口撤离。对于留居福州和汉口两地的日本人,大越只通告他们举动要更加谨慎。大越认为,日本人在这两个城市安全应该能够得到保障,因为那里的日本侨民当时主要经商,他认为中日开战与两国商人无关,中日商人之间应该不会相互加害。8月1日,大越接到开战布告,他进而电告福州和汉口的日本侨民可以接受美国领事的保护。他相信,福州和汉口居留的外国人很多,留在那里的日本人应该会得到十分周到的保护。(73) 但情形并没有大越想象的那么乐观。丰岛海战日本不宣而战,在李鸿章的建议之下,清政府决定停止在华日本人一切通商。大越也看到此前各地中日商业已完全中止,不少日本人不断撤到上海,在福州的日本人则有直接回国的。这样,在大越撤离前夕,上海总领事馆所辖地内,上海以外,除汉口等地嫁给外国人的日本妇女未撤外,其余留下未撤的,汉口四五人,福州十名。此外还有一些分散人员,但人数“极少”。大越估计,这些人今后应该不会受到什么危害。其余有前往内地经商的,大约认为他们均会回国。大越听说尚有二三名在内地旅游的日本人,对于他们的居住地领事馆不了解,但因为这些人已与中国人很难区别,大越估计应该不会有特别危险。此外,日本人在芜湖开设的杂货店田中号中尚有二三名日本人,开战后,该杂货店遭到当地中国人破坏,于8月1日撤到上海。(74) 上海的情况比较特别。开战前夕上海约有1000人,但回国的却不足300人,主要是妇女及无业的“下等人”。当时中国各地受“高升”号事件影响颇有反日举措,大越认为这些人不如回国为好。这些人员的回国,大越因担心由他本人出面会引起恐慌,而通过上海日本人协会办理。8月2日,该协会依照大越旨意将日本侨民安排得非常有组织,并借船费给那些无旅费者。除上述回国人员,数以百计的日本人开战后仍留在上海。这其中包括相当一批间谍人员。大量日本人包括间谍人员之所以敢于“大胆”滞留上海,重要原因是在这里可以得到列强堂而皇之的庇护。大越成德撤离前,不仅争取到美国总领事强有力的帮助,上海会审衙门及各国势力也均愿意为日本人提供诸多保护。当时在上海港停靠的外国军舰只有一艘法国军舰,法国总领事声明必要情况下将随时提供保护。在上海的日本人社会也相当有组织。大越用心整合了一个叫上海日本人协会的组织,正金银行、三井物产会社和邮船会社上海分店负责人等均是会员。总领馆撤离前夕,该协会曾协助大越成德做了不少工作。正金银行、三井物产会社和邮船会社上海分店负责人等还被大越推选为顾问,拟在要紧关头协同美国总领事保护在华日本人。(75)这里的“日本人”,当然包括那些间谍人员。 南方的广州、汕头和琼州并非上海总领事馆管辖地,由香港领事馆兼辖。外务省训令中要撤离的不包括香港领事馆,广东地区不在考虑撤离范围。但战争爆发后,广东地区的所有日本人几乎与北方各地的日本人同时撤离中国境内。其原因,既不是奉外务省指令,也不是驻香港领事中川恒次郎未雨绸缪,而是由于中国民众的愤怒情绪影响了代为负责保护日本侨民的驻广东美国领事。 7月24日,在广东的各国领事包括美国领事风闻中日开战后,一下子想起了1884年中法战争时广东民众的反应。他们致信在香港的日本领事中川恒次郎,告知中国人一旦获悉中日开战,应该会瞬间群情激昂,对日本人做出“危险举动”。1884年中法开战时,在广东的法国人“仓皇失措”,好不容易才得以撤离。美国领事等指出,如果引发上述这类反日风潮,也将会妨碍在留其他外国人的安宁与利益。在广州的20多名日本人多数是妇女,美国领事提醒中川应切劝这些人尽快安静地撤离。(76) 鉴于情势急迫,29日中川恒次郎派遣书记生白须直前往广东调查。调查表明,当地民风颇为“险恶”,一旦爆发,按照从前的事例来看,不仅外国领事很难给予周到的保护,恐怕还会牵连其他外国人。事实上,在留的26名日本人中,多数是卖春女。中川考虑到让美国领事承担这些人的保护责任可能会有不便,就劝导这些人快速撤离广东。(77) 四、情报人员的布留及其活动 驻华日本使领馆对于日本“洞悉”中国军情起着重要作用。丰岛海战后,有位德国人曾致函李鸿章,提醒应让日本使领馆尽快撤离,因为“中使在倭未能探听倭国军情,而倭人在中竟能洞悉中国军事”。(78)为此,按李鸿章提议,清政府要求日本使领馆尽快撤离中国,尤其京津地区。清政府且“暂停日本通商”(79),所以一般日本人也大都离开中国。 作为代理保护国美国的驻华代理公使田夏礼,为了避免“重大麻烦”,也希望日本人尽量撤离中国,尤其靠近中国军事重地的天津等地。8月11日,小村一行从上海启程回国当天,田夏礼即致函驻日公使谭恩,通报各地日本人撤离情形。报告称,天津差不多是中国军事大本营所在地,民众又因“高升”号事件情绪激昂,经商议,使领馆撤离后,在天津的所有日本人都已离开天津。烟台恰当中国海军指挥部所在地,已无日本人。牛庄除一名日本人外其余均已离去,这名在留人员身份姓名未明说。报告没有提及以上海为中心的南方地区,只谈到上海和芜湖发生了轻微的反日示威游行。(80)日本使领馆撤离后,总理衙门曾特意派人向田夏礼确认有无日本人“潜留京城”。田夏礼面称“并无倭人踪迹”。(81)盛宣怀也向李德面询留津日本人员情况,李德答称“天津人心浮动,诚恐事出意外”,所有在天津的日本人“均已随同小村回国”。(82) 田夏礼等所述,其实只指日本使领馆人员及一般民众。在给谭恩的报告中,田夏礼专门提到在中国的日本间谍问题。总理衙门向他严正声明,中国内地遍布伪装的日本间谍,一旦被抓捕即处以极刑。对此,田夏礼回称,他不赞成任何非法的“暴行”,强烈要求间谍一旦被抓捕,应得到“公正的审判”;若有罪,应送到就近港口遣送回日本。(83)可见,至少田夏礼本人对于滞留的日本间谍态度颇为暧昧,而其所述日本撤离人员中,其实不包括那些伪装潜伏下来的间谍人员。 的确,日本使领馆撤离过程中,有意在中国的军政要地布留下一批间谍人员。这些人员主要分布在京津、烟台和上海等地。 在北京,小村一行刚刚离京,就出现了一位“学生”身份的名叫川畑丈之助的日本人,据称在美国教堂创设的学中西文艺学房学习。两个月前放暑假外出“游历”,于8月30日又回学房,声称“尚不知中日业已失和”,“仍欲入学”。而美国教堂教士鉴于形势特别,不愿留这位日本学生,禀告田夏礼。田夏礼于是致函总署,希望发给川畑“路照”,“遣其回国”。(84)这位“日本学生”其实是一名日本间谍。中方档案作“川烟丈之助”系笔误,真实名字为“川畑丈之助”。日本防卫厅档案中留有一份战时大本营电报,提到川畑等7名翻译官奉命前往旅顺出差事宜。(85) 对于川畑的行踪,总署曾表示怀疑,要田夏礼调查。田夏礼据教士提供的信息回称,这位学生系于当年4月初来京入学,放暑假时出京游历,“经过怀来县及宣化府,至张家口遇雨守候,雨霁过新河站哈拉城至察哈尔,又至苏门哈达,由旧路旋京”,仍希望在学房附学,但教士因恐生事而不愿收留;又称该日本人系“极好学生”,且“甚朴实”。(86)其实,田夏礼这封关于川畑行程的报告完全是虚假的。据宗方小太郎记载,8月1日宗方在烟台领事馆遇见川畑。川畑并非美国教堂的普通学生,而是辞职的陆军少尉,当时刚“经满洲至此地”,在烟台稍作停留后“将去北京”。此次的“去北京”,正是上述田夏礼对总署所称的回学房“附学”。宗方遇见川畑当天半夜,领事馆接到外务省来电,称“上月三十一日已向各国公布对华宣战”。(87)川畑当然也不会“不知中日业已失和”。总之,不是田夏礼和传教士有意蒙骗总署,就是他们受到蒙骗,转而蒙骗总署。总署最终接受田夏礼的调查,让川畑顺利回国。 天津地区情况类似。李德称在天津的日本人已全部回国,但天津撤使后至少有4人是使领馆特意布留的。当小村一行抵达天津三汊口时,李德鉴于中国人对日本人颇抱“敌忾心”,专门致信小村建议带上尚留居天津的日本人。(88)为此,小村提出将陆军省人员山田要和海军省人员堤虎吉继续留在天津,以“保护”租界的安全。也就是说,经美国领事同意,日本以保护租界为由留下了两名军方人员。两人另带来两位间谍人员,石川伍一和被小村称为“钟崎某”的钟崎三郎,当时两人已辫发清服。山田要和堤虎吉为侦探陆海军军务方便起见提出继续滞留石川和钟崎,获小村答应。对于这两位实际上的间谍人员,李德虽劝告此两人不可进入外国租界,但未表异议。(89)而据荒川领事的撤离报告,当时潜伏天津的间谍人员,除上述4人,至少还有青木乔。 使领馆撤离前夕,以使馆武官海军少佐井上敏夫为首,以石川伍一、堤虎吉、钟崎三郎等人为核心的天津地区的情报活动非常引人注目。石川曾奉井上之命前往小站侦察清军派往朝鲜情形,报告极其详实。(90)据传,“高升”号事件就与石川伍一等的情报密切相关。如上所述,清兵在搜查荒川夫人随身行李时,搜查到了堤虎吉致井上敏夫的军事密函。堤虎吉等深感形势颇危,石川伍一和钟崎三郎并于8月6日小村一行刚刚抵达烟台时,曾试图“逃出天津,潜入内地”。(91)最后,石川于当月21日被中国官府捕获,9月20日在天津被枪杀。(92)而天津的其余间谍人员则安然回到日本,继续参加战争。堤虎吉于8月17日石川伍一被捕前夕回到日本(93),钟崎三郎则于9月19日抵达广岛。(94) 烟台虽只滞留宗方小太郎一位日本人,但宗方承担起了侦探北洋海军大本营威海卫的重任。宗方于甲午战争爆发前夕接奉海军军令部密令,从汉口赴烟台,与在烟台的使馆武官井上敏夫会面,以烟台为根据地,侦察北洋舰队大本营威海卫、旅顺口的军情。宗方于7月5日抵达烟台,当时“日中两国之危机愈益迫近,决裂在于旦夕”。宗方抵达烟台后立即开始了对以威海卫北洋舰队为中心的情报侦察活动。他或亲自或派人多次前往威海军港,“冒万险”查点军港内军舰的数量及种类,以及从烟台进入威海卫的要地,其地理位置及与威海卫的距离、住户情况等。(95)使领馆撤离后,宗方组织了好几个中国人部下,“使用清人作探子”,不仅继续探查威海卫港口内北洋舰队情况,活动范围且扩至旅顺、天津,成功送出多份报告。宗方后因送出的两份密函落于清政府之手,行踪暴露,于8月29日奉命离开烟台回到上海。(96) 可以说,北洋舰队最终全军覆没,与宗方探查的情报不无关系。宗方回到日本后,在广岛大本营受到明治天皇召见,召见时明治天皇特令他穿着在中国时的服装。1923年2月宗方病危弥留之际,海军大臣加藤友三郎上奏日本天皇为宗方请求叙位,历叙其一生对于日本海军的“贡献”“不胜枚举”。“功绩尤著者”,则是在“日清、日俄两大战役中的谍报功绩”。而甲午战争中首先被称道的,就是奉命潜伏烟台,“备尝苦心与辛酸,努力探知敌情”、“奉公冒险”的行为,所获情报对于日本海军的作战提供了“很大的便利”。(97) 上海总领事大越成德在撤离报告中,并没有特别提到间谍人员的布留,但“局外中立”的上海,实际上可以说是战争期间日本间谍人员的大后方。 中日宣战前夕,日本参谋本部鉴于在中国的公使馆武官及北京天津间的秘密侦探将校将悉数回国,于7月17日紧急召唤“热心中国内情调查”的根津一东京,派遣前来中国,招募熟悉中文及中国风俗的人员,侦察山海关、鸭绿江以及营口一带中国军队“动静”。根津一到中国后就是以上海为大本营展开新一轮的谍报活动的。(98)清政府破获的三大间谍案,石川伍一案、藤岛—高见案及楠内—福原案(99),后两大案件的主人公,藤岛武彦是应根津一招募随行来到上海的(100);楠内和福原也本拟奉根津一之命,从上海出发前往天津等地探查军情,行前被捕。(101)根津一麾下人员不止以上数人。当时与福原和楠内同行的,就有一名叫景山长次郎的,也准备北上烟台、天津、牛庄一带刺探军情,后趁乱逃走。(102)而与楠内一起曾在上海居住过的,至少有吉原洋三郎、土井伊八,岩本嘉次郎、饭田正吉、白岩龙平、森川省三郎、角田隆次郎和青木乔等人。其中,白岩龙平于9月从上海回到大本营,曾申请由军方支付旅费。(103)拟在上海为楠内和福原转收情报的角田隆次郎及吉原洋三郎等,后来也均安然回到日本。(104)另据楠内供称,有一名叫西村忠一的陆军中佐,曾试图从上海前往天津,所获情报由在上海的楠内转达。(105)可见,当时上海结集的间谍人员,其活动范围辐射日本大本营当时目标所指的东北、京津、山东等北方广大地区。 上海庞大的外国势力与颇成熟的日本人组织,为间谍人员提供了相当保障。影响重大的楠内—福原案就发生在法租界。法方将案犯首先转交给美国总领事馆而不是中方。福原和楠内一度躲在上海的美国总领事馆安然无恙,为此还使美国政府不得不重新申明代为“保护”的权限,详参下文所论。上海正金银行则为福原等人的活动提供接受汇款等方便。(106)藤岛武彦案发生后,上海日本人协会则积极出面与美国领事馆一起试图给中方施加影响。一位在上海寺庙的日本人姓岩本(Iwamoto)的,还直接致函美国驻宁波领事法勒(John Fowler),证明藤岛“无罪”,要求法勒尽力让藤岛获得释放。当法勒向岩本指出中方疑问,即藤岛与声称前去拜访的在普陀山的“友人”高见武夫相互并不认识等种种破绽时,这位神秘的岩本回称他数日内即将离开上海回国。(107)显然,这位上海寺庙的日本人不是一位普通人士。 可以说,分布在京津、烟台和上海等地的日本间谍人员并非各自为战,而是互通声息,相互依托。当时天津与塘沽之间只有2个多小时的火车路程。在石川伍一案发之前,宗方小太郎曾经塘沽前往天津与石川、堤虎吉、山田要等相会,与堤和石川同访陆军少佐神尾光臣,“有所商议”。在天津的钟崎三郎等也曾特意到烟台来看望宗方。其时,宗方在烟台的活动很大程度依托上海。宗方的情报主要通过上海谍报网转送出去。宗方直接与居住在上海美国租界内的医生田锅安之助等联系,再由田锅等将宗方的情报转给同在上海、化名为东文三的海军大尉黑井悌次郎。此外,与宗方有联系的间谍人员如津川三郎、成田炼之助等,均于9月份才离开上海回国。(108)间谍人员之间彼此相当熟悉。如楠内友次郎熟知青木乔在天津“看守领事署”,因在天津“甚险”,听说已回上海。楠内曾在上海与青木一起居住过。楠内对于宗方小太郎的行踪也非常了解,称其在烟台领事馆。(109)福原林平与藤岛武彦、高见武夫均相识。(110) 天津、烟台和上海等地日本间谍人员的活动,因三大间谍案发生,促使美国政府重新申明代为“保护”的性质及权限,而受到相当程度影响。 8月14日,身着中国服装的福原林平和楠内友次郎在上海法租界被捕后,法国领事公然将两人引渡给驻上海美国总领事。(111)上海道台向美国总领事提出引渡遭到拒绝。据美国总领事审讯,福原和楠内是为经商而途经上海前往汉口的,但被捕时中国侦探发现其随身携带有两张文字资料,详细记录了奉天兵营人名、士兵人数及锦州辽阳兵营情形,另有一张暗码电报纸。(112)其实,他们和稍后在宁波被捕的藤岛武彦、高见武夫均为陆军省雇员、大本营雇佣的翻译官,日本官方后来称他们均在“侦察勤务中”被杀。(113)对于这等有着重大嫌疑的人员,美国总领事不另作调查,只将两人留置在领事馆内给予“厚待”。上海道或以两江总督的名义,或以李鸿章名义频频要求引渡,均遭拒绝。上海美国总领事馆之所以敢于公然保护两名间谍嫌疑人员,屡次拒绝中方要求,实因美国驻华代理公使田夏礼的支持。田夏礼曾向在东京的驻日公使谭恩报告称,自己“十分尽力”地“保护”此两人。这样,上海道台与美国总领事馆之间的交涉,遂升格为北京中央政府与美国公使之间的谈判,最终促使美国方面交出两名嫌疑人。(114) 美国领事馆立场的变化,与这一时期美国政府对于“敏感状况”下代为“保护”的权限及性质加以重新确认直接相关。(115) 29日,葛礼山就此向田夏礼发布新训令。训令重申美国当初接受日本委托时的两大条件:一是须征得中国政府同意;二是美国同时保护中国在日华侨的利益,曾获日本政府同意。指令进而就田夏礼所承担的保护职责进行说明,指出美国公使不能正式扮演另外一个国家外交代表的角色,田夏礼的地位是一个中立国代表的地位,在保护其中一方国民利益中,立场须兼顾双方意愿,且所能做的均须与国际法相符合。指令进而就日本在华臣民的法律地位问题进行说明,指出在华日本侨民不能视同美国公民,也不能给予他们治外法权的保护。不能假设他们遵循美国的法律或者遵从美国公使或领事的管辖,也不允许美国公使馆或领事馆成为犯罪者的避难所。在华日本侨民依然是他们君主的臣民,有责任遵从当地法律。另一个国家代为保护他们也不能改变他们的这种地位。(116) 当天,葛礼山以书函形式将这一新的指令精神详细地转告日本驻美公使栗野慎一郎,明确指出,美国驻上海总领事不应该接受那两位有嫌疑的日本人且收容他们,随信并附寄致田夏礼命令的复印件。葛礼山同时也已给美国驻日公使谭恩寄送了一份相同的指令。(117) 在栗野慎一郎看来,葛礼山的新训令主要声明两点精神:一是美国对于在华日本人的保护所抱持的原则与日本政府敕令,即8月4日发布的明治二十七年敕令第一百三十七号有关日本境内居住的中国人的相关旨意相符;二是美国对日本在华侨民的保护与对中国在日侨民的保护遵循完全平等一致的原则,无厚薄亲疏之别。31日,栗野将葛礼山来函报告陆奥宗光。(118) 日本政府的明治二十七年敕令第一百三十七号是完全针对战时在日中国人的新法规。法规第一条规定,在日中国人须服从日本法院管辖;第六条规定,中国臣民有危害日本国家利益者,或犯罪者,或扰乱秩序者,以及有以上嫌疑者,除依照各法令处分外,府县知府仍得将其驱逐到帝国版图之外;第七条还规定,本条令适合于受雇于帝国官厅及臣民的中国人。(119)也就是说在日本的所有中国侨民须完全受日本法律管辖。 9月3日,美国领事馆将楠内和福原引渡给中国政府。当天起,凡是侨居上海的日本人均须受中国法律管辖。(120) 对于美国方面的说明,日本政府当然不能有异议。7日,内务大臣井上馨、外务大臣陆奥宗光联合发布训令,承认在中日开战期间,两国人民虽然共同受美国领事保护,但其保护之旨单止于身体和财产免受非法凌辱,及在侨民和侨居国政府之间起沟通桥梁作用,对于两国人民本无治外法权的审判权。侨居中国的日本国民的民刑事件也须服从中国的审判。(121) 美国驻上海总领事是“遵从美国政府的训令”,应清政府官员的请求,才不得不将两位间谍嫌疑人员引渡给中国官衙的。对于楠内、福原等引渡给中国政府并最后处斩,当时日本驻美国公使栗野慎太郎曾借助媒体的反应,建议拟向美国政府提请由美国公使及领事向中国“抗辩”。对此,陆奥宗光倒看得很清楚。陆奥在回信中指出,在日本的中国人须服从日本法律,在中国的日本人同时受中国法律管制,在法理上难以抗辩。(122) 与福原—楠内案同一时期发生的石川伍一案和藤岛—高见案,美国也均参与其中,但最终还是均按照上述美国政府的新的训令精神实行的。有关石川案学界研究较多,兹不赘述。藤岛—高见案发生时,起初美国驻上海总领事佑尼干曾颇为关切,先致函美国驻宁波领事法勒令用电报汇报此事详情,后又令法勒致电在北京的代理公使田夏礼请示。8月27日,法勒收到田夏礼密电,告知葛礼山明确指示,美国领事不能保护日本犯罪嫌疑人。法勒可以为该嫌疑人得到公正审判提供帮助,但如遭到拒绝,就不要干涉。(123)可以说,美国的上述最新保护政策精神比较及时地影响了法勒。藤岛武彦和高见武夫后被送杭州府斩首。(124) 随着在留的多名日本间谍被清政府逮捕,以及美国亮明“保护”的立场,留居中国的日本人误以为美国政府已经中止保护,人心颇产生动摇,开始陆续回国。(125)宗方小太郎于9月8日离开上海时,同船回国的日本人达150多人。开战前夕奉命前来上海指挥间谍活动的根津一,以及津川、田锅、藤城、成田,包括在上海接受宗方报告、化名为东文三的海军大尉黑井悌次郎,都是在这一当口回日本的。(126)只是宗方等间谍人员对于日本推进甲午侵略战争已提供相当充分的情报帮助。这些间谍人员回国后,还继续为战争推波助澜。如宗方随后参与日本于次年3月攻占澎湖岛、台湾之战,并于12月受大本营派遣再度来到中国,一直为日本军方侦察情报服务长达30余年。(127)从天津逃脱回到日本的钟崎三郎,在日军攻占辽东半岛时承担先行收集军事情报任务。堤虎吉则在日本侵占台湾之初,以台湾总督府参谋海军少佐的身份,参加监察出入淡水港的中国船只是否运送武器弹药等警备工作。(128) 综上所述,甲午战争爆发后日本方面的撤使实质上是其备战的一个重要环节,情报人员的布留及其活动尤其值得注意。(1)撤使即意味着两国进入战争状态。从日本秘密托付美国代为保护在华利益,启动撤使来看,约在6月29日,即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逼迫朝鲜外署回复朝鲜是否中国属国的截止日期当日,日本阁议正式启动战争准备。(2)以秘密委托美国护侨为标志,日本政府早在战争爆发前约一个月已着手准备撤使,但正式下达撤使命令却是在中国驻日使馆送出撤使照会,乃至中国政府下达“驱逐”令之后,且还只准备撤离长江以北各大使领馆,试图以改挂美国国旗为掩护,保留上海总领馆及所辖长江以南广大地区的日本势力。最终促使日本全面撤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代理保护国美国等对于被深刻激发起来的中国民愤的恐惧,他们知道,这种民愤连清政府都难以压制。(3)战争爆发后,尽管清政府要求日本在华使领馆及相关人员全部撤离,但这一旨意其实只在长江以北的京津地区名义上得到不折不扣的实现。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流域及东南沿海,以及中国重要的军政要地,仍然布留了不少情报人员。这些人员的活动有效地协助了日军作战。(4)日本撤使过程中,美、英、法各国驻华使领馆对日态度虽然亲疏有别,美国政府还试图体现中立的立场,但在华的各国使领,尤其美国驻华使领,总体上积极主动给予协助。由此可见,至少到甲午开战前夕,日本已相当程度融入西方在华势力并被接受。各国在京津、上海、武汉等地的租界,乃至个别美国教堂,还成为日本在华从事战争情报活动的庇护所和据点。(5)由于清政府连续侦破三大间谍案,促使美国政府重新界定代为“保护”的权限及性质,包括宗方小太郎在内的不少间谍人员因此纷纷回国,但他们所获情报已足以影响中日甲午战争的进程,这些人员回国后继续为战争推波助澜。(6)中国虽然承受被侵略的沉重代价,但在日本撤使过程中本着国际法原则主动给予郑重保护,使日本使领人员包括普通民众安然离开中国。天津撤使过程中发生的“重庆”号事件,从起因、交涉过程、提出理由等来看,中国方面的处置也有理有据。 ①《参考》,JACAR(アヅア歷史資料センター),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Ref.B07090537100(以下“B”开头者均为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不一一注明)。 ②《发北洋大臣电一》(光绪二十年六月二十五日),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15卷,1932年铅印本,第29页。 ③"Dun to Gresham,June 30,1894," in Jules Davids(ed.),American Diplomatic and Public Papers: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1894-1905,Series Ⅲ,The Sino-Japanese War to the Russo-Japanese War,1894-1905,Volume 2,The Sino-Japanese War I,(Wilmington,Delaware:Scholarly Resources Inc,1981),pp.143—146.按:以下该卷外交文件均简化为ADPP,Senes Ⅲ,Volume 2。 ④《陸奥外務大臣ヨリ清国駐劄小村臨時代理公使宛》(明治27年7月13日),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第27卷第2册,東京,日本国際連合協会1953年版,第424页。 ⑤"Dun to Gresham,June 30,1894," in ADPP,Series Ⅲ,Volume 2,pp.143—146. ⑥"Dun to Gresham,June 29,1894," in ADPP,Series Ⅲ,Volume 2,p.142. ⑦"Dun to Gresham,June 30,1894," in ADPP,Series Ⅲ,Volume 2,pp.143—146. ⑧"Gresham to Bayard,July 20,1894," in ADPP,Series Ⅲ,Volume 2,pp.186—187. ⑨"Gresham to Bayard,July 20,1894," in ADPP,Series Ⅲ,Volume 2,pp.186—187. ⑩"Gresham to Bayard,July 20,1894," in ADPP,Series Ⅲ,Volume 2,p.187. (11)"Gresham to Bayard,July 20,1894," in ADPP,Series Ⅲ,Volume 2,p.187. (12)"Gresham to Bayard,July 20,1894," in ADPP,Series Ⅲ,Volume 2,p.187. (13)"Gresham to Bayard,July 20,1894," in ADPP,Series Ⅲ,Volume 2,p.187. (14)"Gresham to Bayard,July 20,1894," in ADPP,Series Ⅲ,Volume 2,pp.187—188. (15)"Gresham to Bayard,July 20,1894," in ADPP,Series Ⅲ,Volume 2,pp.187—188. (16)"Gresham to Bayard,July 20,1894," in ADPP,Series Ⅲ,Volume 2,p.188. (17)"Gresham to Bayard,July 20,1894," in ADPP,Series Ⅲ,Volume 2,p.188. (18)《当館兼轄地並二其地在留ノ本邦人保方二付北京我公使へ具申二及ヒタル件》(明治27年7月6日),《清国在留帝国臣民ノ保護米国政府へ依托ノ件》,Ref.B07090536700。 (19)《陸奥外務大臣ヨリ清国駐劄小村臨時代理公使宛》(明治27年7月13日),《日本外交文書》第27卷第2册,第424页。 (20)"Mutsu to Komura,July 19,1894,"《清国在留帝国臣民ノ保護米国政府へ依托ノ件》,Ref.B07090536700。 (21)"Sill to Gresham,July 24,1894," in ADPP,Series Ⅲ,Volume 2,p.191. (22)《北洋大臣来电一》(光绪二十年六月二十六日到)、《北洋大臣来电五》(光绪二十年六月二十八日到),《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15卷,第31、35页。 (23)《谕军机大臣等电寄李鸿章》(光绪二十年六月二十七日),《德宗景皇帝实录》第343卷,《清实录》第56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93—394页。 (24)《军机处发李鸿章转汪凤藻电》(光绪二十年六月二十七日),《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15卷,第32页。 (25)《外務大臣陸奥宗光ヨリ在朝鲜特命全権公使大島圭介宛》(明治27年7月30日),《清国在留帝国臣民ノ保護米国政府へ依托ノ件》,Ref.B07090536700。 (26)《奏文》(明治27年7月30日),《在清帝国公使、領事引揚帰朝ノ件》,Ref B07090536200。 (27)"Denby to Dun,July 30,1894,"《日本外交文書》第27卷第2册,第429—430页。 (28)"Mutsu to Tateno,July 31,1894,"《清国在留帝国臣民ノ保護米国政府へ依托ノ件》,Ref.B07090536700。 (29)"Mutsu to Okoshi,July 31,1894,"《在清帝国公使、領事引揚帰朝ノ件》,Ref B07090536200。 (30)《縂署致小村照会》(光绪二十年六月二十九日),《在清帝国公使館撤回始末書》,Ref.B07090536300。 (31)《在清公使館撤回始末書》(按:原题名如此)(明治27年9月3日),《在清帝国公使館撤回始末書》,Ref.B07090536300。 (32)"Denby to Dun,July31,1894,"《日本外交文書》第27卷第2册,第430页。 (33)"Komura to Denby,August 1,1894,"《在清帝国公使館撤回始末書》,Ref B07090536300。 (34)"Denby to Komura,August 1,1894,"《在清帝国公使館撤回始末書》,Ref B07090536300。 (35)《美国署公使田夏礼照会》(光绪二十年七月初一日),《在清帝国公使館撤回始末書》,Ref.B07090536300;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6卷,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2年版,第3376页。 (36)《日本署公使小村照会》(明治27年8月1日),《在清帝国公使館撤回始末書》,Ref.B07090536300。 (37)"Komura to Mutsu,August 1,1894,"《清国在留帝国臣民ノ保護米国政府へ依托ノ件》,Ref.B07090536700。 (38)《在米二等書記官ヨリ陸奥外務大臣宛》(明治27年8月4日、6日),《清国在留帝国臣民ノ保護米国政府へ依托ノ件》,Ref.B07090536700。 (39)《在清公使館撤回始末書》(明治27年9月3日),《在清帝国公使館撤回始末書》,Ref.B07090536300。 (40)《在天津帝国領事館撤回始末書》(明治27年9月12日),Ref.B07090536400。 (41)《在天津帝国領事館撤回始末書》(明治27年9月12日),Ref.B07090536400。 (42)《在天津帝国領事館撤回始末書》(明治27年9月12日),Ref.B07090536400。 (43)"Read to Li Hung Chang,August 2,1894,"《在天津帝国領事館撤回始末書》,Ref.B07090536400。 (44)"Read to Li Hung Chang,August 2,1894,"《在天津帝国領事館撤回始末書》,Ref.B07090536400。 (45)"Read to Li Hung Chang,August 2,1894,"《在天津帝国領事館撤回始末書》,Ref.B07090536400。 (46)"Fisher to Arakawa,August 2,1894,"《在天津帝国領事館撤回始末書》,Ref.B07090536400。 (47)《在天津帝国領事館撤回始末書》(明治27年9月12日),B07090536400。 (48)"Read to Komura,August 4,1894,"《在清帝国公使館撤回始末書》,Ref.B07090536300。 (49)《重慶号暴行始末書》(明治27年9月20日),《日本外交文書》第27卷第2册,第438—440页。 (50)《宗方小太郎日记》(1894年8月4日、6日),戚其章主编:《中日战争》第6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13—114页。 (51)《津海关道盛宣怀致美国李领事函稿》(光绪二十年七月十四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6卷,第3491页。 (52)《在芝罘帝国領事館引揚始末書》(明治27年8月27日),《在芝罘帝国領事館撤回始末書》,Ref.B07090536500。 (53)《道台ヨリ伊集院領事宛》(明治27年7月2日),《在芝罘帝国領事館撤回始末書》,Ref.B07090536500。 (54)《在芝罘帝国領事館引揚始末書》(明治27年8月27日),《在芝罘帝国領事館撤回始末書》Ref B07090536500。 (55)《在芝罘帝国領事館引揚始末書》(明治27年8月27日),《在芝罘帝国領事館撤回始末書》Ref B07090536500。 (56)《在芝罘帝国領事館引揚始末書》(明治27年8月27日),《在芝罘帝国領事館撤回始末書》Ref B07090536500。 (57)《宗方小太郎日记》(1894年7月7日),戚其章主编:《中日战争》第6册,第109页。 (58)《在芝罘帝国領事館引揚始末書》(明治27年8月27日),《在芝罘帝国領事館撤回始末書》,Ref B07090536500。 (59)《在芝罘帝国領事館引揚始末書》(明治27年8月27日),《在芝罘帝国領事館撤回始末書》,Ref.B07090536500。按:据当时也在领事馆的宗方小太郎记载,领事馆撤离人员中至少还有书记生横田三郎(《宗方小太郎日记》(1894年7月5日、8月4日),戚其章主编:《中日战争》第6册,第109、113页)。 (60)《宗方小太郎日记》(1894年8月4日、6日),戚其章主编:《中日战争》第6册,第113—114页。 (61)《参考》,Ref.B07090537100。 (62)"Bandinel to Hayashi,August 27,1894,"《在清帝国公使、領事引揚帰朝ノ件》,Ref.B07090536200。 (63)"Bandinel to Hayashi,August 27,1894,"《在清帝国公使、領事引揚帰朝ノ件》,Ref.B07090536200。 (64)"Bandinel to Hayashi,August 27,1894,"《在清帝国公使、領事引揚帰朝ノ件》,Ref.B07090536200;《参考》,Ref.B07090537100。 (65)《参考》,Ref B07090537100。 (66)"Bandinel to Hayashi,August 27,1894,"《在清帝国公使、領事引揚帰朝ノ件》,Ref B07090536200;《参考》,Ref.B07090537100。 (67)《参考》,Ref B07090537100。 (68)《在上海縂領事大越成德ヨリ外務大臣陸奥宗光宛》(明治27年7月6日),《清国在留帝国臣民ノ保護米国政府へ依托ノ件》,Ref.B07090536700。 (69)《上海総領事館引揚始末書》(明治27年8月23日),《在上海帝国総領事館撤回始末書》,Ref.B07090536600。 (70)《上海総領事館引揚始末書》(明治27年8月23日),《在上海帝国総領事館撤回始末書》,Ref.B07090536600。 (71)《上海総領事館引揚始末書》(明治27年8月23日),《在上海帝国総領事館撤回始末書》,Ref.B07090536600。 (72)《上海総領事館引揚始末書》(明治27年8月23日),《在上海帝国総領事館撤回始末書》,Ref.B07090536600。 (73)《上海総領事館引揚始末書》(明治27年8月23日),《在上海帝国総領事館撤回始末書》,Ref.B07090536600。 (74)《上海総領事館引揚始末書》(明治27年8月23日),《在上海帝国総領事館撤回始末書》,Ref.B07090536600。 (75)《上海総領事館引揚始末書》(明治27年8月23日),《在上海帝国総領事館撤回始末書》,Ref.B07090536600。 (76)《参考》,Ref.B07090537100。 (77)《参考》,Ref.B07090537100。 (78)陈旭麓等编:《甲午中日战争》下,“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2页。 (79)《北洋大臣来电一》(光绪二十年六月二十六日),《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15卷,第31页。 (80)"Denby to Dun,August 11,1894,"《清国在留帝国臣民ノ保護米国政府へ依托ノ件》,Ref.B07090536700。 (81)《总署致美国署公使田夏礼函》(光绪二十年八月初三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6卷,第3539页。 (82)《津海关道代复美国李领事函》(光绪二十年八月初五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6卷,第3547页。 (83)"Denby to Dun,August 11,1894,"《清国在留帝国臣民ノ保護米国政府へ依托ノ件》,Ref.B07090536700。 (84)《美国署公使田夏礼函》(光绪二十年八月初一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6卷,第3535页。 (85)《大本営副官部発宇品運輸通信部宛》(明治28年5月16日),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Ref.C06060914600(以下“C”开头者均为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不一一说明)。 (86)《美国署公使田夏礼函》(光绪二十年八月初六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6卷,第3557页。 (87)《宗方小太郎日记》(1894年8月1日),戚其章主编:《中日战争》第6册,第113页。 (88)"Read to Komura,August 4,1894,"《在清帝国公使館撤回始末書》,Ref.B07090536300。 (89)《在清公使館撤回始末書》(明治27年9月3日),《在清帝国公使館撤回始末書》,Ref.B07090536300。 (90)《清国兵の朝鮮国に派遣始末(2)》(按:原件未标时间),Ref.C08040560200。 (91)《宗方小太郎日记》(1894年8月6日),戚其章主编:《中日战争》第6册,第113—114页。 (92)《荒川巳次領事ヨリ文部大臣西園寺公望宛》(明治28年12月3日),《石川伍一死体取引に関する報告》,Ref.C08040760900。 (93)《海軍大尉瀧川具和帰朝御届の件》(明治27年8月18日),Ref.C10125515300。 (94)《宗方小太郎日记》(1894年9月20日),戚其章主编:《中日战争》第6册,第123页。 (95)《宗方小太郎日记》(1894年6月26—27日,7月5日、7—26日、31日),戚其章主编:《中日战争》第6册,第108—113页。详参馮正宝《評伝宗方小太郎——大陸浪人の歷史的役割》,東京,亜紀書房1997年版,第210—211页。 (96)《宗方小太郎日记》(1894年8月5—28日),戚其章主编:《中日战争》第6册,第115—120页;《海軍大尉黒井悌次郎帰朝御届の件》,Ref.C10125515700。 (97)《宗方小太郎特旨叙位ノ件》(大正12年2月),日本国立公文書館藏,Ref.A11113118300(以下“A”开头者均为日本国立公文書館藏,不一一说明)。亦可参馮正宝《評伝宗方小太郎——大陸浪人の歷史的役割》,第213—214页。 (98)《第6款宣戦前後に於ける我陸海軍中央統帥部の関戦準備業務ノ情况视察員並秘密諜報者の差遣》(按:原件未标时间),Ref.C13110361200;《川上中将発根津一宛》(明治27年7月17日),Ref.C06060705800。 (99)《目次》,Ref.B07090873600。 (100)《根津大尉随行者藤島武彦履歷大略》(明治27年7月21日),Ref.C06061663500。 (101)《福原林平口供》(光绪二十年八月二十九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6卷,第3843页;《上海仏居留地内旅宿二於テ岡山県人福原某、鹿见島県人楠内某ナル者間諜ノ嫌疑ヲ以テ捕缚セテレタリトノ件》,Ref.B07090873900。 (102)《楠内友次郎口供》(光绪二十年八月二十五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6卷,第3837、3842、3840页;《福原林平口供》(光绪二十年八月二十九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6卷,第3843—3844页。 (103)《藤井大佐発大生中佐宛白岩竜平に旅費を支給すべきや》(明治27年9月30日),Ref.C06060825800。 (104)《参日第44号第1》(明治27年10月1日),Ref.C07082019000。 (105)《楠内友次郎口供》(光绪二十年八月二十五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6卷,第3834—3835、3837—3839页。 (106)《福原林平口供》(光绪二十年八月二十九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6卷,第3844页。 (107)"Fower to Jernigan,September 19,1894,"《藤島武彦ナル者上海ヨリ帰朝ノ際鎮海ニ於テ捕縛セラレタリトノ件》,Ref.B07090873800。 (108)《宗方小太郎日记》(1894年7月27日、31日,8月4日、6日、10—11日、17日、19日,9月6日、8日、11日),戚其章主编:《中日战争》第6册,第112—117、122—123页;《海軍大尉黑井悌次郎帰朝御届の件》(明治27年9月18日),Ref.C10125515700。 (109)《楠内友次郎口供》(光绪二十年八月二十五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6卷,第3834—3835、3837—3839页。 (110)《福原林平口供》(光绪二十年八月二十四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6卷,第3827、3829—3830页。 (111)《大本営より楠外3名清国に於て斬殺せられたる件》,Ref.C06022331400;《上海仏居留地内旅宿ニ於テ罔山県人福原某、鹿児島県人楠内某ナル者間諜ノ嫌疑ヲ以テ捕縛セラレタリトノ件》,Ref.B07090873900。 (112)《福原林平口供》(光绪二十年八月二十九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6卷,第3843页;《上海仏居留地内旅宿ニ於テ罔山県人福原某、鹿児島県人楠内某ナル者間諜ノ嫌疑ヲ以テ捕縛セラレタリトノ件》(明治27年9月27日),Ref.B07090873900。 (113)《忠魂史編纂ニ関スル件》(昭和10年6月24日),Ref.B04012569700;《大本営附通訳官陸軍省雇員藤島武彦他清国に於て敵情偵察中死亡の件》(明治28年4月23日),Ref.C10060745200。 (114)《上海仏居留地内旅宿ニ於テ罔山県人福原某、鹿児島県人楠内某ナル者間諜ノ嫌疑ヲ以テ捕縛セラレタリトノ件》(明治27年9月27日),Ref.B07090873900。 (115)"Greshan to Denby,August 29,1894,"《上海仏居留地内旅宿ニ於テ罔山県人福原某、鹿児島県人楠内某ナル者間諜ノ嫌疑ヲ以テ捕縛セラレタリトノ件》,Ref.B07090873900。 (116)"Gresham to Denby,August 29,1894,"《日本外交文書》第27卷第2册,第449—452页。 (117)"Gresham to Kurino,August 29,1894,"《日本外交文書》第27卷第2册,第443—444页。 (118)《米国駐劄栗野公使ヨリ陸奥外務大臣宛》(明治27年8月31日),《日本外交文書》第27卷第2册,第442—443页。 (119)《明治ニ十七年勅令第百三十七号》(明治27年8月4日),Ref.A03020182700。 (120)《宗方小太郎日记》(1894年9月3日),戚其章主编:《中日战争》第6册,第121—122页。 (121)《日清両国各居留民保護ニ関スル井上内務陸奥外務大臣訓令》(明治27年9月7日),《日本外交文書》第27卷第2册,第444—445页。 (122)《栗野慎一郎ヨリ陸奥宗光宛》(明治27年9月10日)、《隆奥外務大臣ヨリ米国駐劄栗野公使宛》(明治27年10月5日),《上海仏居留地内旅宿ニ於テ罔山県人福原某、鹿児島県人楠内某ナ-ル者間諜ノ嫌疑ヲ以テ捕縛セラレタリトノ件》,Ref.B07090873900。 (123)"Fower to Jernigan,September 19,1894,"《藤島武彦ナル者上海ヨリ帰朝ノ際鎮海ニ於テ捕縛セラルタリトノ件》,Ref.B07090873800。 (124)《大本営より楠外3名清国に於て斬殺せられたる件》(明治28年8月31日),Ref.C06022331400。 (125)《日清両国各居留民保護ニ関スル井上内務陸奥外務大臣訓令》(明治27年8月31日),《日本外交文書》第27卷第2册,第445页。 (126)《宗方小太郎日记》(1894年9月6—8日、11日),戚其章主编:《中日战争》第6册,第122—123页;《海軍大尉黑井悌次郎帰朝御届の件》(明治27年9月18日),Ref.C10125515700。 (127)《宗方小太郎特旨叙位ノ件》(大正12年2月),Ref.A11113118300。 (128)《港湾警備》(按:原件未标时间),Ref.C08040581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