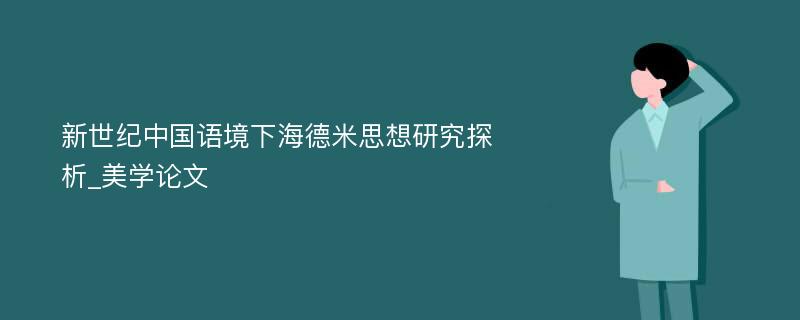
新世纪汉语语境中海德格尔美的思想研究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海德格尔论文,汉语论文,新世纪论文,语境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此凸显汉语语境,意在表明全球视野下海德格尔(以下称海氏)美的思想研究,在汉语学术界的境遇及其原创意味。这种研究不是外来“他者”的简单移植、挪用或“理论旅行”,而是基于本土重新语境化的互动及其创造性生成,在此境域中海氏与中国学者发生了某种深具阐释学意味的多重对话关系。正是在汉语语境下对海氏美的思想研究的互动和视界融合中,生成了中国美学的创造性成果,这些成果使海氏的美之思对中国美学学科的转型、建构,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压迫性“他者”,而是内化为中国本土美学重构的巨大理论推动力及其思想资源,是跨文化语境中一次美的事件的发生。
回顾新世纪汉语学界对西方现代美学的研究,可以说海氏美的思想研究一直备受关注,是汉语美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亦是中国美学转型寻求的“他山之石”。就“美学”这个名称而言,每一个进入海氏存在之思境域发问的人都会有此困惑,在海氏那里有“美学”吗?“美学”作为奠基于现代形而上学之上的一门科学,在海氏看来乃是“行至真理的半途”。他在《尼采》等相关著作中不止一次地指出“‘美学’这个名称意味着对艺术和美的沉思,它的出现只是不久以前的事。它是在18世纪提出来的。”“美学就是对与美相关的人的感受状态的思考;是在美与人的感受状态之关系这一范围内对美的思考”。被海氏从中梳理限定在一定题域中的美学,迥异于学术史和学科意义上的“美学”。但在当前的时代境遇和学科对话交流中,我们又不得不用“美学”这个名称来言说当下对审美的学理研究。尽管“美学”是海氏抨击解构的对象,被他称为“无命运”的家伙、“不是本质性的东西”,但限于学术史及学科分类的强大惯例,人们通常还是把海氏的美之思称为“美学”思想。尽管有些学者对此钩沉索隐、探源辨析,甚至为突出某种特别意味强称之为“美论思想”或“美的思想”,以区别当前现代学科意义上的“美学”。在我们看来,这种辨析的神韵只有还原到海氏审美之思得以可能的境域中才会焕发出强有力生命,从而真正切中“美学”的弊端。一旦回到生活和学术的常态,其特定意味和神韵不可避免地受到遮蔽或跌入存在遗忘的深渊。尽管如此,冠之海氏美学名称的论文仍大行其道。另一方面,“美学”没有因为某位思想家的“否定”而稍有懈怠,而是在强劲发展中顽强地凸显着自我主体意识。因而,“美学”与海氏的审美之思形构了某种别有意味的“罅隙”,学者们的研究无疑是“罅隙”之上沟通的桥梁,二者的互动对话对“美学”产生极大影响并有力地推动着“美学”学科的发展。对于用执着于存在者表象的“现代科学”来概括他的美之思,不知海氏地下有知该作何感想?在人们被迫把海氏美学带出场的研究中,无疑有着研究者独抒机杼的心曲和初衷,可以说,这些研究成果同海氏审美之思形成复调式合唱,一同灿烂了美学的百花园。正是对此的冀望,我们对新世纪汉语学界海氏美的思想研究作简要述评。
一、对海氏存在之思中某些核心概念的阐释,及其美学分期问题研究
新世纪以来,许多学者对海氏存在之思中某些基本问题和核心概念进行梳理辨析,这固然是哲学的研究方式,但这些奠基性和清理地基的工作对于理解海氏美的思想至关重要,甚至有些文章本身就提供了研究海氏美的思想的基本视角。通常的研究都以海氏整体思想为背景来凸显某些核心概念。像彭富春以对东方智慧和西方尤其德语思想的通晓,在《无之无化》中展开对海氏思想的追问,认为“存在作为虚无”乃海氏思想形成的主题。存在“存在着”,凭借于它作为虚无虚无化。以此方式“无”成为海氏观念中的思想的事情的规定。彭富春针对海氏思想道路的不同阶段概括出:“三个语词,凭借于它们的相互取代,同时标明了思想的三个步骤:意义—真理—地方”,这正是海氏所谓的“存在”从世界经过历史到语言的道路。据此他不认同汉语学界海氏思想的前后分期说,认为海氏思想道路的三个阶段即世界性、历史性和语言性,吻合于海氏对自己思想的区分,即从意义(世界)到真理(历史)再到地方(语言)。他还在《西方海德格尔研究述评》(载《哲学动态》2001.5)中就早、中、晚三期的西方研究现状作了述评。受其影响,张贤根在《海德格尔美学思想论纲》(载《武汉大学学报》2001.4)中对海氏美学的哲学基础及分期问题提出看法,认为海氏美学建立在哲学基础上,在对传统美学的超越中完成,其研究艺术的方法具有现象学的解释学循环特征;海氏美学思想的三个时期对应其思想道路的三个阶段,即世界性、历史性和语言性;由此海氏美学思想分为早、中、晚三期,并据此对海氏三期美学思想做了阐释。并进一步在《存在·真理·语言》中,分三篇较详尽具体地研究了海氏美学思想,即存在的追问;真理的显现;语言的倾听。如对海氏早期美学,他认为在海氏基础存在论里审美主体不复存在,而代之以此在,此在是通达存在的必由路径,在本性上,此在即在世界中存在,时间性是此在在世存在的依据,此根据消解于虚无之中。“在之中”整体是一种存在建构,其本性是世界的拒绝,由此规定了存在的悖论,存在即虚无,海氏解构了审美主体论,为美和艺术奠定了存在论基础。
基于对海氏思想的某种理解,俞吾金在《海德格尔的“世界”概念》(载《复旦学报》2001.1)中指出,在海氏思想及其转变中,世界概念起着基础性的、重大的作用。海氏世界概念的演化经历三个阶段:在20年代的论著中,世界归属于人的此在,而且日常此在最切近的世界就是周围世界;在三、四十年代的作品中,艺术作品的真理体现在“世界”与“大地”的争执中,“世界图像”作为现代的本质且技术使世界成为“世界黑夜”;在五、六十年代的著作中,海氏提出世界是天地神和“终有一死者”的四重整体,“终有一死者”在栖居中保护着“四重整体”且上帝是世界的最终拯救者。这里,第二阶段实际是第一阶段和第三阶段之间的过渡,正是有赖于它,海氏才在晚年毅然提出新的世界概念。通过对海氏世界概念演化的解析,可以发现其思想中贯穿着对生存、世界和存在意义的关注。而王庆节在《也谈海德格尔“Ereignis”的中文翻译和理解》(载《世界哲学》2003.4)中,紧紧围绕海氏后期思想的核心主导词“Ereignis”进行阐释,对汉语学界关于“Ereignis”的译名及其基于不同语境的理解进行梳理和辨析,具体分析了此词的难译状况。相比较以前的海氏思想研究,“三阶段说”较为突出。笔者以为,这种基于海氏思想整体洞察的核心词阐释和思想分期,拓宽了领会海氏美的思想的思路和研究视野,给我们很大启发。至于是否一定分前、后期抑或早、中、晚三期,并不是问题的关键,相信惟有学理支撑的创造性成果才有利于研究的推进。
二、对海氏关于美和艺术之思的研究
如何回到海氏存在之思本身,对其美的思想进行洞察,一直是中国学者阐释和理解海氏美的思想的关键点。美是存在之无蔽真理的闪光,亦即存在者之存在的纯然显现。在此意义上美不能作为分析的对象,而只能就美的显现程度进行现象学描述。美生成的场域只能是人与存在者自身原初关联的世界,作为此在的我们只能在世界中追寻美的踪迹。同样,艺术本质上与真理相关联成其自身,其本源意义乃是开启一个世界,而不是以审美对象的方式存在,只是在美学视野(思之下坠的意义上)中它才成为主体体验的审美对象,可此际艺术早已逃离自身世界。艺术作为真理发生的一种方式,是真理进入存在的突出方式,亦即真理历史性显现的方式,而伟大的艺术乃是一个民族世界的开启与民族对自身命运的决断。因而,美学从来不仅仅与趣味关联,以探讨感官的审美愉悦。这些作为海氏美之思的核心内容逐渐被研究者认同,正是在现象学视野中,诸多学者展开对海氏美和艺术之思的研究,并在这种描述性研究中把美学何以可能的问题带出来。
如何让海氏美之思自我显现或出场,是近年来许多学者倾心诉求的意旨所在。在此方面,几位青年学者基于汉语语境对此作了不同研究道路或视角的探索,因视角的不同使研究呈现出某种“对话”特色。范玉刚在《美是存在真理的闪光——海德格尔美的意蕴追问》(载《人文杂志》2004.1)中指出,美是无蔽真理的闪光,它生成于“存在之道作”的裂隙。海氏“返回”思之源头对美的这一根本道说,凸显了美生成的意蕴,它既关乎“存在之道作”的揭蔽,又关联“存在之天命”出场的机缘。这一规定使他不但把美从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获得始源真理的“命运”形态,还使美在存在境域中获得超越的形上价值。对此意蕴的领域只有结合他对“座架”的克服和思之转向,并置于“返回”源头又带向前的存在之思的境域中才有可能。而刘旭光在《“存在”之“光”——海德格尔美论研究》(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4.4)中指出,海氏认为“美”源自审美状态,而审美状态并非是主体的某种精神状态,而是“存在”的本然状态。美是存在者自身的显现,“存在”即美的本质,也是美的功用,美不是显现的结果,而是“显—现”这个动态过程。存在之显现之所以美是因为,人无法在流变的世界中领会与观照存在之本质,存在必然在生活的日常状态中被遗忘,只有打破了这种遗忘状态,人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获得存在之澄明,这种获得存在之澄明状态过程,就是获得美的本质与本源的过程,就是存在者的澄明之光,是存在之光。进一步,刘旭光还在《海德格尔与美学》中对此问题作了多方面阐发,他认为,一方面我们需要阐释和分析海氏关于艺术、美学、诗等的思想,把这些思想与他的整体思想结合起来,去关注他思考这些问题的基本出发点,而不是停留在表面意义上;另一方面,我们必须不断地把这些思想与欧洲的美学传统结合起来看,我们必须弄清这些思想究竟解决了或者提出了哪些美学问题,对于美学的发展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另外,还要说出海氏没有说出却可能说出的话,也就是去思考沿着他所开辟的“思”之路径,可能生发出什么样的美学新观点。范玉刚则在《睿思与歧误——一种对海德格尔技术之思的审美解读》中,从如何理解技术之思对海氏的审美之思、艺术之思进行深入解读。作者认为对于海氏而言,技术—艺术—美与思的关系是支撑海氏思想进路的关键结构,在他看来,我们当下生存的时代在文化上是技术时代,即不但人、物、自然都被坐落于“座架”中,就连艺术和诗以及美都被打上技术的烙印,这是我们直面当下生存困境进行阐释的基点。海氏在对技术—艺术—诗与思的关系进行了切近“事实本身”的详尽分析和论述,不但揭示了技术现象和本性,并对此作了超越常人和时代之思,从而让技术作为存在揭蔽的一种方式回到存在真理的澄明中。就学理意义而言,这一关系结构又是将现行美学—文艺学(含艺术学)提高至现代性背景下,使之获得更为根本性阐释的思路框架。就现实意义而言,他的存在之思远远超越学院之外以“拯救”地球为旨归的绿色环保和生态运动,而指向了未来。
如何深化海氏美的思想研究,有的学者通过比较研究把问题推向深入。如邓晓芒在《什么是艺术作品的本源?》中,通过将海氏的观点与马克思的观点充分比较,对海氏的一般美学思路作了初步分析和评价。在这篇颇有见地的论文中,邓晓芒以马克思历史理性的实践高度批评了海德格尔,“一开始就把艺术问题形而上学化、认识论化了,人的感性的活动、实践、生产和器具的制造在他的美学中只具有次要的、往往还是否定性的意义,而不是用来解决‘艺术之谜’的钥匙……集中到一点,就是他始终没有摆脱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一个幻觉,即认为一切哲学问题都可以归结到对唯一的一个哲学概念的澄清上,由此便能够一劳永逸地把握真理,或坐等真理的出现,至少,也能把可说的话说完,却忘记为自由的、无限可能的、感性的人类实践活动留下充分的余地。在这一点上,马克思的视域至今还未被哲学家们超越,并且往往能使我们深入到这些哲学家们的隐秘的底线。”其观点我们未必赞同,但是推进了海氏思想研究。范玉刚在《“命运”的属意与“境界”的失落——一种对海德格尔艺术之思的解读》中,引入一对价值形而上学概念:“命运”与“境界”作为参照,也对此话题有所推进。正是诉诸“存在之天命”的力量,使他属意“早先的”伟大艺术,把艺术作品的本源追溯到古希腊的“知”,提出对艺术的世界与大地相互争执的真理形态的理解,并从无蔽真理方面来思考艺术的本质。只有从此境域出发,结合思之转向,才能掘发出遮蔽在艺术之思中的底蕴,才能对他艺术之思的形上祈向及其时代忧患意识作出中肯评判,进而对其艺术之思因存在之思“境界”的缺失而丧失本有的人文关怀,并小觑人的心灵对“至善”价值的祈向,作出较公允裁断。就此话题程金生在《论艺术的本源——海德格尔艺术哲学思想探析》(载《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04.3)中认为,艺术本源问题是艺术哲学的前提性问题,它对艺术的艺术性进行追问。传统的艺术哲学把艺术的本源建立在形而上学之上,这是基于主体性视野的艺术哲学,海氏反对这种艺术哲学,而主张基于存在自行发生立场的艺术哲学,它通过“创作”而把天地神人聚合为一,使天地神人在“作品”聚合的世界中自由伸展,由此,艺术通过作品而把存在自行发生的真理设置于自身,人相应地从存在的主人变成存在的看护者。这种思想改变了整个西方文化对艺术运思的方向。
可以说基于对海氏美和艺术之思的现象学领会,海氏美学被带出场,“借对形而上学的反思,海德格尔明确地提炼出美学的感性学性质和美学的形而上学根源,同时美学的发生论上的思想根源也被高屋建瓴地提炼出来”。(《海德格尔与美学》,233页)建基“罅隙”之上的“对话”使学者们在肯定海氏思想达到的时代高度的同时,又关联于美学思想史对其偏颇作了批评。这种对海氏美和艺术之思既有较深入阐释,又基于一定学理和价值参照作出批评的研究,把汉语学界对海氏美的思想研究推进到新层面,就“思的事情”这未尝不是有启发性的研究思路?
三、对海氏存在论诗学的研究
严格地说,海氏视野中的诗学不同于文艺学所讲的“诗学”,海氏诗的思关联于语言、思,意在为现代人寻求“诗意地栖居”之所。海氏被人视为诗人哲学家,其从诗的思走向思本身。对其思诗本源同一的认识,成为大多数学者的共识,只是在具体表述上有些分歧。略可区分的是,孙周兴认为海氏的诗之思绝非通常意义上的“诗化哲学”,其根扎得更深、深远。饶有趣味的是,针对一般意义上海氏的诗意语言观的研究思路,彭富春认为诗意的语言是纯粹的语言,指出在海氏存在之思中语言的本质是诗。而刘方喜在《“大道”在人——言之际的双向运作——论海德格尔语言本体论诗学观》(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9.3)中指出,在语言本体论层面上,海氏从人与自然本体而非人与人之间关系这个角度出发,把语言与人相互作用中的“言”视作本体之“道”。诗歌作为一种本真的语言活动,乃是大道在人——言之际的双向运作,既是大道(言)向人开道成道而由无声之音向人的有声之音转换生成的运作,又是人向大道归本而对道(言)之说做出诗言应答的运作。这一由海氏开启的本体论诗学批评,在现代处境中有重大的生存意义,同时对汉民族古典诗学批评研究极具启发性。张贤根则在《诗的本性与人的居住——海德格尔对荷尔德林诗的阐释》(载《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1)中指出,基于对荷尔德林诗的阐释,海氏揭示了在贫乏时代,荷尔德林诗在克服语言的技术化,把语言保存在纯粹性之中,实现诗与思的合一等方面具有独特的意义。诗作为接受的尺度,意味着思想对语言的倾听。诗人是存在之家的守护人,只有在语言家园中,才能实现诗意地栖居。不同于对海氏诗之思的肯定性阐释,还有学者对其运思方式提出严厉批评。徐岱在《批评游戏:评海德格尔论荷尔德林》(载《外国文学研究》2004.6)中指出,长期以来,德国存在主义思想家海氏对著名诗人荷尔德林诗作的阐释,一直被批评理论界视为文化诗学的一大典范,但事实上这乃是一种粗暴的突出个案。问题主要表现为一种“思”对“诗”的僭妄,而批评主体对诗人的文本缺乏必要的尊重则是症结所在。海氏所谓“诗与思的对话”:首先以“思”为“诗”,尔后以其“思”取代诗人之“思”。这就是海氏以“运思”命名的一种粗暴文学批评的实质,在其对荷尔德林诗所实施的批评实践中,表现出“思”对“诗”的僭妄。从中可见海氏的“借尸还魂”式“批评游戏”,不仅不能与巴赫金对拉伯雷的“我注六经”式研究相提并论,而且与巴特的“批评游戏”也相去甚远。这是一桩典范的以“思”的名分对“诗”实施强暴的批评游戏。我们相信不同视角的冲突和对话,对深化海氏诗学思想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四、对海氏审美之思与传统美学的比较研究
基于像张祥龙、靳希平、陈嘉映、宋祖良、余虹、孙周兴、周宪等还有诸多未在此提及的学者的奠基性研究,学界普遍意识到海氏的审美之思之于传统美学的反动与超越。海氏把美关联于存在的真理问题使其审美之思与传统美学区分开来,在貌似陈辞中为美和美学的何以可能作了奠基。新世纪这一研究立场继续被学者们坚持,并有所深入。如李醒尘在《海德格尔美学思想论》(载《锦州师范学院学报》2000.4)中,通过对海氏美学思想的阐释与分析,指出其不同于传统美学的独特本质,即在对艺术本质的研究中,提出艺术是真理在作品中的自行置入;所谓“真理”就是存在自身的显现,而“自行置入”则是真理稳坐在作品里的一种状态。对于海氏来说,艺术作品的本质不应从存在者角度去把握,而应从存在者的存在去把握;艺术价值体现在世界的建立和大地的显现这两大特征上,其中世界的本质是敞开、开放性,大地的本质是自我归闭、封闭性,作品乃是世界和大地抗争的承担者。海氏的美学思想尽管具有唯物主义色彩,但它对艺术在社会、历史、人生方面所具有的积极意义的肯定,却启人深思。彭富春在《马克思美学的现代意义》中指出,马克思和其他现代思想家如尼采、海德格尔对于近代思想的叛离是颠覆性的。他们不仅将所谓的理性问题转换成存在问题,而且也给真善美、知情意等一个存在论的基础,由此认识论、伦理学和美学作为哲学体系的主要部分已失去根本意义。胡伟则在《走向存在的真理之路——海德格尔的哲学追问与西方美学研究的转向》(载《内蒙古师范高等专科学报》2001.5)中认为,海氏对自古希腊以来的整个西方哲学发动了一场追问与怀疑的革命;对传统哲学的消解和革命,导致呼唤人的“诗意地栖居”成为海氏哲学的中心内容,而这实际上是一个近乎美学的论题,它使人们看到西方美学被遮蔽的部分,扭转了美学的单一阐释方向,为新一代美学家和美学发展注入新的基因。
从以上研究中可以看出,海氏的美之思所达到的历史性维度,既使其与早期审美方式拉开距离,又远远地把基于体验的美学抛在后面,其把美与真理关联起来的美的思想照亮了后来者的研究道路。
五、在跨文化语境中对海氏后期思想的核心主导词——Erei'gnis的阐释,及其在东西方思想会通中的对话
Ereignis作为海氏后期思想的核心主导词,乃是本源性的澄明遮蔽着的显隐运作,它具有多维内涵和意味,又脱出形而上学规定。在Ereignis的源始同一性中,天、地、神、人四方聚为一体,正是在这种镜像游戏中,物成为物,世界成为世界。因而对它的领会及其汉语语境下的阐释,往往成为通达海氏思想的“林中小路”。对此王凯在《海德格尔与老子思想的核心问题》(载《武汉大学学报》2001.4)中强调,东方“道”的概念源远流长,老子对之作了突破性提升,使其成为中国思想中最富想像力的核心语词。老子的“道”对海氏思想的“转向”提供了重要启示,使我们看到了中西思想之间的一个重要交汇点,而海氏在其思想的核心问题及主导语词上,同老子实现了平等“对话”和相互会通;使我们确信中西思想在同等层次、同等深度上进行对话的可能性。无论老子的诗意运思,还是海氏的诗意追问,都体现着对人类生存的真切关切,蕴含着深刻的现代意义,在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下比较研究二者的异同,会给予我们深刻的现代启示。认同这种观点的朱立元和刘旭光在《从海德格尔看中西哲学美学的互动影响》(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3.6)中,具体阐释了海氏在接受老庄“道”的思想影响的基础上提出的“此在在世”的存在论命题,指出它超越西方“主客二分”二元对立的传统;同时指出这一命题反过来对中国当代哲学美学思想发生了重要影响,由此论证了中西文化对话的必要性。作者认为在这场对话中,西方得到了启发,获得了一个参照;中国得到了认同,获得了一条自我再认识的道路。在对话中双方相互启发着、参照着,共同在自我认识的道路上走向澄明,在一种相互推动中完成自身的使命。早对此话题有深入研究的张祥龙在《海德格尔论老子与荷尔德林的思想独特型——对一份新发表文献的分析》(载《中国社会科学》2005.2)中指出,《海德格尔全集》第75卷中有一篇海氏引用《老子》第11章来讨论荷尔德林诗作独特性的文章。以此文献为中介探讨了他对了解海氏与道家关系的意义。认为这个新文献与以前发现的有关材料不同,它不仅出现早,而且是直接针对《存在与时间》的核心思路而引用和阐释《老子》的,同时还涉及他的后期学说。海氏将老子讲的“无”或“扑”解释为一种发生性的“之间”,并认为它是理解“正在来临的时间”和诗人独特性的关键。这种解释既是对他前期“存在与时间”学说的深化,又是对他后期的主导思路——“自身的缘发生”(Ereignis)——的方法论特点的揭示。由此可见,与《老子》的对话是海氏思想本身的内在需要,道家与荷尔德林起码自30年代开始就是海氏哲理灵感的最深来源。范玉刚则在《“之间”的夺出:从Ereignis到Tao——领悟后期海德格尔思想的别一视角》(载《学术月刊》2005.10)指出,后期海氏思想主导词Ereignis的生成受启于多方面影响,在此洞察它与中国老庄之“道”的思之关联,辨析他对“道”之未曾明言意味的“夺出”对其运思的意义,以及以“存在之道作”契合并“夺出”Ereignis中未曾明言意味的合理性。洞悉两种“夺出”的“之间”的丰富内涵及价值意趣的分际,并从对各自文化根性的守护中给当前思想文化建设以启悟。
可以说以上研究虽不限于美学范围,但其成果显然有利于对海氏美的思想的理解和领悟,因而我们在此也捎带述及。
六、对海格格尔美的思想的价值评判
海氏的美之思不仅对中国美学学科建设,而且对整个美学思想的重要性都毋庸置疑,这已成学界的共识,只是对其思想评判的视角有所差异。张公善在《海德格尔美学的历史地位及当代意义》(载《安徽大学学报》2003.3)中指出,海氏美学在存在维度上标志着西方现代美学的完成,而在语言维度上又标志着西方后现代美学的开始。海氏的存在本体论美学与语言释义学美学就像两盏明灯照亮了美学的未来之路。海氏美学以存在为本体,来消解认识论美学分裂的人性,这启示我们未来美学必须以完整的人的存在,即以人的生活存在为本体。而中国主流美学对实践的关注,往往是以牺牲存在、语言的维度为代价的。同时非主流美学如生命美学、超越美学、修辞论美学、否定美学等往往在青睐存在与语言之际,又漠视了实践的基础功能。未来美学应该走辩证综合之途,那就是生存——实践——语言三位一体之美学。同时他还在《海德格尔论美及其现实意义》(载《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2004.1)中指出,海氏论美涉及三大关系,即美与真理的关系:美是真理的一种现身方式;美与存在的关系:一切在者之在就是最美者;美与自然的关系:美的本质是同时的迷惑和出神。海氏将美与真理、存在和自然内在地统一起来,是一种本体论美论,有着巨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此外,还有的学者将其美学观与人学思想关联起来,如吉永生在《论海德格尔的人学与美学观》(《学术探索》2003.3)中认为,作为沉思存在本身、克服形而上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海氏发动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反人道与反美学之思,对形而上学与人道主义、对认识主体与审美主体、对超感性事物与感性事物之间的同源性和演化史进行了极富创见的勾勒。海氏对形而上学与人道主义、对认识主体与审美主体、对超感性事物与感性事物之间深层关系的勾勒,是他就西方哲学和美学的内在规律问题所进行的极富教益的归纳概括。海氏反人道与反美学之思所欲突出的是在存在真理面前人与艺术的仆从身份和恭敬态度,这是克服形而上学狂妄症的关键环节。
新世纪以来,海氏美的思想研究可谓收获颇丰,无论在涉猎的广度还是研究的深度都有相当进展。既有颇见功力的论文,也有深入开掘问题的力作。但在肯定之余,我们也不得不指出相对海氏这座“仰之弥高”的思想的“奥林匹克”,我们汉语学界的研究还缺乏与之全神贯通的系统性、深刻性的力作,在思想的相互关联中对海氏美的思想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尤其是批判性对话还有待加强,海氏美的思想对中国本土美学的建构价值还应成为学者的自觉意识,在这方面还有许多话可以说。当然笔者仅是对汉语语境中海氏美的思想研究的主要倾向作了简要述评,难免挂一漏万,尚有诸多不足和遗漏之处,还望方家教正!
标签:美学论文; 海德格尔论文; 世界语言论文; 西方美学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艺术批评论文; 哲学家论文; 诗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