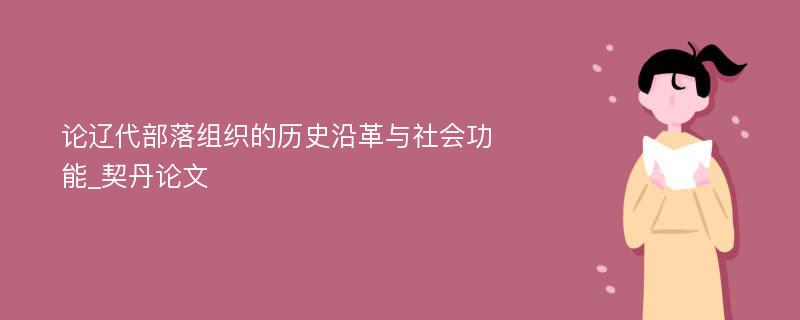
论辽朝部族组织的历史演变及其社会职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部族论文,职能论文,组织论文,社会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部族组织是辽朝在契丹等游牧民族中实行的集行政、生产、军事于一体的制度,贯彻于辽朝统治的始终,构成了辽朝“因俗而治”统治制度的最重要、最基本的内容,堪称辽朝立国之本。虽然《辽史》在历代正史中以其严重疏漏和缺略受到古今学者的批评,其中却保存了辽朝部族组织、部族活动和部族制度的丰富资料,给我们今天讨论辽朝的部族问题提供了便利条件。
一、辽朝部族组织的由来和延续
辽朝的部族组织是以契丹族的部族组织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契丹族的部族活动最远可以上溯到传说中的奇首可汗,由他的八个儿子衍生为在血缘上有密切联系的八个部落。至隋朝开皇年间,契丹族“分为十部,兵多者三千,少者千余,逐寒暑,随水草畜牧。有征伐则酋帅相与议之,兴兵动众和符契”[1](《契丹传》)。可见,此时的契丹族虽然臣属于突厥等强大势力,而为了对付外来势力的威胁,已经形成了最初的部落联盟。
唐朝初年形成的大贺氏部落联盟,就其内部来说,虽仍沿用了古代八部的划分,又继承隋朝时的部落的划分习惯,凑足十部之数。按《辽史·营卫志中》的记载,除八部之外又把松漠都督窟哥和玄州李去闾各算一部。而《新唐书·契丹传》记载:松漠都督府所辖十州,除八部所居九州外,大贺氏自居一州。不论哪一种说法对,此时松漠都督府之下领有的八个契丹族部落则是一致的。在唐朝开元、天宝时期重新形成的遥辇氏部落联盟时期,契丹族再次形成了八个部落,加上被唐朝授予松漠都督的阻午可汗的直属部众和为重建部落联盟立有大功的涅里所在部,共为十部,与隋朝、唐初的部族数是一致的。
此前,契丹族部族联盟的变动和聚散的主要原因是来自外部强大势力的冲击造成的。如在奇首可汗的古八部时期,契丹族为“高丽、蠕蠕所侵,仅以万口附于元魏。生聚未几,北齐见侵,掠男女十余万口。继为突厥所逼,寄处高丽,不过万家。部落离散,非复古八部矣”[2](《营卫志中》)。遥辇氏部落联盟形成的初期,正值“安史之乱”前后,唐朝对边疆少数民族控制能力的衰弱,以及契丹族与周边突厥、回鹘各族在力量对比上的此长彼消,显然使契丹族生存和发展的环境获得了极大的改善,其显著标志是契丹各部族有了各自相对稳定的游牧地和居住地。从此,契丹族部落联盟进入了前所未有的迅速发展的历史时期。
在大贺氏联盟的末期,原有的十个部落仅余五个,遥辇氏阻午可汗时,在涅里的主持下,变五部为八部。具体的变动是由益古、撒里本兄弟分领六营部众,形成后来的迭剌部和乙室部,由涅勒、撒里卜兄弟将一营一分为二,形成后来的涅剌部和乌隗部,由塔古里、航斡兄弟分领三营部众,形成后来的突吕不部和突举部。加品部和楮特部,正是八部之数。从以上八个部落中有六个是三对兄弟所领部众发展而来的史实来看,部落之间的血缘联系还是比较清晰的。
遥辇氏部落联盟内部部族总数,在阻午可汗时期就达到二十个,这也是人为分析的结果,即“分三耶律为七,二审密为五,并前八部为二十部”[2](《营卫志中》)。三耶律指大贺氏、遥辇氏和世里氏(耶律氏),二审密指审密氏族的拔里、乙室已家族。二十部名称除上述八部加右大、左大部外,其余十部已不可考。
辽朝建立以后,以契丹族为主体的部族组织及其制度在新的形势下继续发展、完善,并表现出与部落联盟时代明显不同的特点,主要是部族组织的重新编制和把大量非契丹族人口编入部族。按《辽史·营卫志下》记载,太祖时的部族数仍然是二十个,但由于其中的国舅帐和国舅别部上升为帐分,二十部实际上只有十八部,而国舅别部则是世宗时新增加的。所以,所谓太祖二十部之名,实际上应是世宗时的部族划分状况。上述阻午可汗时代二十部中已知十部除右大、左大二部外的八部被全部继承下来,迭剌部后来分为五院、六院二部,余下的九部则全部是被征服的周边各部族组成。兹列举如下:
1.奚王府六部五帐分。天赞二年(923年),太祖把在奚族故地征服的奚族部众置为堕隗部,合遥辇氏时代征服的五部奚,设奚王府以统领之;2.突吕不室韦部;3.涅剌挐古部,由阿保机收降的大、小室韦部众组成;4.迭剌迭达部;5.乙室奥隗部;6.楮特奥隗部。上述4—6部本为辽朝建立前后所俘奚族族众,太祖时置为部;7.品达鲁虢部,以太祖时所俘达鲁虢部置;8.乌古涅剌部;9.图鲁部,太祖以所俘6000户于骨里部众分置。
辽圣宗时,部族增加到三十四个,《辽史·营卫志下》说“以旧部族置者十六,增置十八”。这三十四部族的来源和组成比较复杂,有的是分析原来旧部族而新置的,如特思特勉部、涅剌越兀部;有的是由太祖以来征服的各族设置的,这一部分从部族名称很容易分辨出来,如突厥、回鹘、唐古等;有的是原来作为著帐子弟而属于宫户或身受横帐大族奴役的奴隶,至此设置为部,如稍瓦、曷术二部。在《辽史·营卫志下》的最后,罗列了所谓“辽国外十部”的名称,并说这“十部不能成国,附庸于辽,时叛时服,各有职贡,犹唐人之有羁縻州也”。尽管在《辽史·百官志二》中,这十部有的被列为“大部”,似乎他们已经与其他被征服的部族具有同样的部族资格,而在事实上并非如此。检索分隶于北、南宰相对的部族名称,可知十部无一名列其中,说明这十部在所有部族中是与辽朝关系是最疏远的。所以,将其比之于“唐人之有羁縻州”,是十分恰当的。
辽圣宗时期是辽朝部族制度进入稳定的巩固发展的历史时期,其主要表现是辽朝对周边各部族的征服战争大体上已经结束,虽然北方的乌古、敌烈部仍然叛服不常,但对辽朝多民族统治的大局已无大影响;辽朝对各部族的划分、编制的过程已经完成。这就是在辽圣宗以后辽朝的部族组织不再扩大的历史背景。
有辽一代以契丹族为主体的部族组织及其制度的长期存在和发展,说到底是契丹等民族游牧生产方式及生产力水平的产物,游牧生产的特定方式比较农耕生产一家一户的个体经营,更具备形成以一定血缘联系为纽带、以家族、氏族乃至部落的社会组织的基础和条件,这也是辽朝建立以前契丹族的部族组织迭经破坏又得以屡次恢复的基本原因。在辽朝,统治者根据现实的政治需要,伴随着部族组织的编制和调整,赋予这种古老的部族组织以全新的意义,使其成为为巩固专制统治服务的得力工具。对于契丹等游牧民族来说,他们的旧有社会结构和习以为常的生产生活秩序仍然被保留下来,可以“各安旧风,狃习劳事,不见纷华异物而迁”。对于广大部众来说可以实现“家给人足”的理想,对于统治阶级来说则达到了“戎备整完”[2](《营卫志中》)的目的。非契丹族的各游牧民族,或被编入契丹族的部族,或在整体上保留了原来的部族组织,并使之具有了与契丹族部族相同的社会地位,其中蕴涵的笼络各部族社会上层、部众,扩大和巩固统治基础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辽圣宗时增置的稍瓦、曷术二部,使这些部众从奴隶上升为具有独立人格的平民,这是辽朝中期以后奴隶制因素逐渐削弱的进程中一个典型事例,其积极的社会意义不言而喻。
二、加强部族制度是辽朝前期政治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
部族事务是辽朝北面官中与宫帐、属国并列的三大职责之一,与朝廷的政治、军事等制度的变化调整息息相关,也与契丹等各族部族权贵的权力、利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说能否处理好部族事务之于辽朝统治者,是关乎安危成败的头等大事亦不为过。特别在辽朝前期,统治者一系列加强和调整部族组织、制度的步骤、措施,是其政治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
(一)迭剌部的一分为二。由于有了涅里的全力支持,迪辇祖里才得称阻午可汗,重建契丹族部落联盟。所以,在遥辇氏时代,迭剌部始终处在十分特殊的地位上。首先,是迭剌部的兵强势众在诸部中独占鳌头。在阻午可汗“分三耶律为七”时就把“大贺、遥辇析为六,而世里(耶律)合一”[2](《营卫志中》)。而上述把世里氏所在部析为以益古、撒里本兄弟为酋长的迭剌部、乙室已部则可能是稍后的事情。“世里合一”是造成迭剌部终“遥辇之世强不可制的”重要的前提条件。其次,迭剌部的部长、权贵们,特别是自涅里迄阿保机的历代部族精英,以强大的部族势力为后盾,长期垄断了部落联盟的军事指挥权,到阿保机叔父述澜时,就任于越,“总军国事”,随后,阿保机继任了以上职务。耶律氏取代遥辇氏已经是势所必然。
强大的迭剌部为阿保机等部族权贵施展才能创造伟业铺平了道路,而在阿保机大功垂成之际,对他形成的最大威胁也是来自迭剌部。由于阿保机有肆无恐的违背传统和愈发不可收拾的专擅行为,引起其他各部“大人”和耶律氏家族成员对他的强烈不满。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随时粉碎对可汗权威的威胁和挑战,阿保机设置了忠诚于自己的腹心部。“时制度未讲,国用未充,扈从未备,而诸弟剌葛等往往觊非望。太祖宫行营始置服心部,选诸部豪健二千充之,以曷鲁及萧敌鲁总焉。已而诸弟之乱作,太祖命曷鲁总领军事,讨平之。”[2](《耶律曷鲁传》)腹心部后来改称皮室军,至太宗时已有三万之众。
在采取什么方式解决强大难制的迭剌部的问题上,追随和反对阿保机的两种政治势力竟然都提出了析分迭剌部以削弱其势力的主张,可见解决迭剌部问题已经尖锐的摆到了部落权贵集团的面前。在《辽史》中被列为逆臣之首的耶律辖底因勾结阿保机的弟弟剌葛等人谋乱,被缢杀,行刑前他对阿保机说:“迭剌部人众势强,故多为乱,宜分为二,以弱其势。”[2](《逆臣传上》)神册三年(918年),太祖甚为倚重的功臣耶律曷鲁在弥留之际遗言:“惟析迭剌部议未决,愿亟行之。”[2](《耶律曷鲁传》)天赞三年(922年),迭剌部被一分为二,分别称五院部、六院部。
(二)部族统领体制的改造。辽朝对部族组织的统领体制的改造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早在契丹族部落联盟时期,由于可汗与联盟内部最有势力的部落权贵之间权力与利益分配格局的制衡关系,形成了把全部部族分成两大系列分别统领的局面。在大贺氏部落联盟的末期,就是由可汗李过折和权势仅次于他的可突于“分典兵马”。当遥辇氏阻午可汗分五部为八部时,又“立二府以总之”[2](《兵卫志上》)。由此奠定了后来以北、南宰相府分别统领各部族制度的基础。
北、南府宰相的职官在阿保机时代之前就已经存在了,《辽史》中或记为北、南宰相,由于这一职官由世选产生,所以被部落联盟中的强有力家族垄断由来已久。从辽圣宗时形成的北、南宰相府分领部族的格局来看,遥辇氏部落联盟的契丹族八部分在北宰相府的有迭剌(后又分为五院、六院部)、乌隗、突吕不、涅剌、品五部,分在南宰相府的有乙室、楮特、突举三部,其中享有世袭宰相特权的分别是迭剌部和乙室部。阿保机取代遥辇氏初年的耶律氏家族的内部难,提供了他对传统的部族统领体制进行改造的契机。公元910年,阿保机“以后兄萧敌鲁为北府宰相,后族为相自此始”[2](《太祖纪上》)。从此,后族萧氏成了世代垄断北府宰相职位的特权家族,形成终辽一代“任国舅以耦皇族”[2](《百官志一》),即皇族耶律氏与后族萧氏相辅相成、共治天下的政治格局。南府宰相“自诸弟拘乱,府之名族多罹其祸,故其位久虚,以锄得部(楮特部)辖里特、只里古摄之。府中数请择任宗室,上以旧制不可辄变。请不已,乃告于宗庙而后授之。宗室为南府宰相自此始”[2](《太祖纪下》)。第一个宗室南府宰相是皇弟耶律苏。辽太祖的这一改革把自部落联盟以来拥有极大权势的北、南宰相的职位从享有世选特权的家族中剥离出来,交到他倚之为心腹的宗室、外戚手中,成为他控制各部族、巩固统治秩序的工具。尽管北、南宰相的选任在辽朝仍实行世选制度,然而却是在政治强权的干预下,完全打破了契丹族自氏族社会以来的历史传统和社会联系之后实行的,从本质上说这种世选已经成为专制集权的附庸。
辽圣宗时期部族统领体制的改造主要是针对奚王府所属六部进行的。奚族与契丹族“异种同类”,由于两个民族比邻为伍,历史上彼此纷争不断,遥辇氏部落联盟的末年,奚族完全役属于契丹族。辽朝建立以后,统治者对于仍统领着广大奚族部众,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的奚王府怀有强烈的戒备之心。后来的事实证明,辽朝解决奚王府问题是有预谋、有步骤进行的。统和十四年(公元996年),奚王和朔奴与东京留守萧恒德共同领兵讨伐东北的兀惹族,不胜,使辽朝解决奚王府问题有了名正言顺的借口。辽圣宗下令奚王府所辖六部改隶北宰相府管辖。这样,奚王府在北宰相府中虽仍然保留着部族的名义,却已是名存而实亡,只剩下了无部众可统的空架子。统和二十二年(1002年),“奚王府五帐六节度献七金山河川地”[2](《圣宗纪五》),辽朝在这里兴建了新的都城中京,标志着奚王府问题的最终解决。
(三)部族长官名称和选任方式的改变。部落联盟时期的部族长官,常见的有夷离堇,《辽史·国语解》释为“统军马大官”,夷离堇一职可能有泛指和专指的两种意义,专指即是部族长官,如阿保机以迭剌部夷离堇即汗位。当时夷离堇的职位,无论是专指还是泛指,被限定在本部族范围之内,由强有力家族世选产生是无庸置疑的。辽太祖时期,把除五院、六院、乙室已部之外的诸部夷离堇改称令稳。会同元年(938年),辽太宗下令改上述三部夷离堇为大王。令稳,《辽史·国语解》释为“官名”,杨树森先生著《辽史简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认为令稳即“令尹”,并据此认为令稳已经是国家官员。统和十四年(996年),辽圣宗改令稳为节度使。以上变化的意义不仅仅在于职官名称的改变,更重要的是反映了以皇帝为代表的专制集权干预部族事务的倾向。在一般情形下,部族长官在本部族内世选产生当无疑问。而这种世选已经迥然有别于氏族社会阶段的世选,除了其过程、结果要受到皇帝、朝廷的制约,享受世选特权的权贵家族受到限制外,新任部族长官的权力也同样受到限制,从《辽史·百官志二》“北面部族官”所见,大部族除大王之外,还有左、右宰相、太师、太保、司徒、节度使、详稳等官员,小部族除节度使外,还有司徒、司空、详稳等官员。
与此同时,包括北、南宰相府宰相和各部族长官的选任也打破了原来的部族界限。如北府宰相的人选已经不限于后族萧氏,还有其他部族的契丹贵族和汉族官员出任过北府宰相。南府宰相的人选似乎更复杂一些,远远超出了皇族四帐的范围,除契丹贵族之外,还有汉族、渤海官员置身其间,甚至包括隶名宫籍的人。即使在实行世选制最典型的五院部和六院部,大王的人选也并非出身本部族的人。
其实,这种突破旧制的做法与皇帝加强对部族事务控制的主观愿望是一致的。统和二年(984年),“划离部请今后详稳止从本部选授为宜,上曰:‘诸部官惟在得人,岂得定以所部为限’。不允”[2](《圣宗纪一》)。划离部不见于《辽史·营卫志》的部族名单,可能是一个无关重要的小部。辽圣宗以次为例,强调部族官的选任不能以本部族为限,可见这在当时部族官的选任中是通行的原则。出于同样的目的,皇帝还特许契丹贵族、宠臣参与另一个部族长官的世选。辽道宗时,右护卫太保、室韦人查剌因诬告知北院枢密使萧速撒等人有功,被允许“预突吕不部节度使之选”[2](《道宗纪三》)。皇帝通过以上方式大大限制和削弱了部族贵族的世选特权,从而达到了控制部族的目的,使部族组织成为贯彻皇帝意志和国家政令的基层机构。
(四)辽朝部族的分类。《辽史·营卫志中》对辽朝部族组织的划分有一段概括文字,从其中的举例来看,所反映的是辽圣宗时期部族组织的状况。“部落曰部,氏族曰族。契丹故俗,分地而居,合族而处。有族而部者,五院、六院之类是也;有部而族者,奚王、室韦之类是也;有部而不族者,特里特勉、稍瓦、曷术之类是也;有族而不部者,遥辇九帐、皇族三父房是也。”这实际上是对辽朝各类型部落、部族的形成渊源及组成情况的概括。“族而部者”,指迭剌部等八个由遥辇氏部落联盟保留下来的契丹部族,他们具有历史悠久、内部血缘联系密切、组织完备稳定等特征,是辽朝部族制度的典范,也是辽朝藉部族组织维护统治秩序的中坚。因此,契丹八部在辽朝所有的部族中地位是最高的,各由一个氏族组成单独的部落。“部而族者”,主要指由太祖时征服的奚族、室韦等部族组成的部,从形式上看,他们被编入契丹族的部族组织,具有了与契丹族相同的地位,而在辽朝统治者的眼里,他们只具有氏族的地位,不能与契丹族八部相提并论。“部而不族者”,特里特勉、稍瓦、曷术三部与契丹八部、奚族、室韦内部各有自己完整的氏族不同,他们最初是因特定的任务而从各部族、斡鲁朵抽出来组成军事或生产单位,因年深日久,户口繁衍而置为部落。这样的部落形成历史短,因来源于不同的氏族所以内部联系松弛。“族而不部者”,遥辇九帐和皇族三父房,一是前世可汗家族的后裔,一是皇族中除去横帐的部分。辽太祖以受位于遥辇氏,所以尊遥辇九帐于皇族之上,而三父房原为迭剌部的一部分,辽朝建立后析出,他们尽管只有氏族的规模,而在辽朝的所有部族中却是最尊贵的。
三、辽朝部族组织的职能
部族组织作为辽朝的主体民族契丹族包括各游牧民族的基本社会组织,承担的职能是至关重要的。尽管《辽史》对部族官的职责的记载失于缺略,但通过对《辽史》本纪、列传、志、表各部分有关部族组织、活动、制度等内容的检索,仍然可以对部族组织的职能做大致的了解。辽朝的部族组织具有军政合一、亦兵亦民的特征,承担着行政、生产、军事三位一体的职能。如果进一步简单概括,即部族组织的职能无论对于辽朝的统治阶级来说,还是对于各部族的长官、平民来说都是全方位的。
辽朝建立以后,统治者继承了部落联盟时代部族制度的外壳,在整顿契丹族部族组织的同时,并以之为典范,把被征服的各游牧民族全部编制在部族组织中。随着对州县占领区的扩大,逐渐形成了北面官管理下的部族制和南面官管理下的州县制两套迥然有别的行政系统。在部族制度下,皇帝主要通过限制部族权贵世选特权,左右部族长官的选任等方加强了对部族组织的控制,通过北、南宰相府对各部族长官和部众发号施令。各部族“分地而居,合族而处”,他们的驻牧地和戍守区都是朝廷划定的,各部族长官和部众不得随便迁徙和流动,而且必须随时听从皇帝或朝廷的调遣。在这里,部族长官对上听命于皇帝和朝廷的北面官,对下统领部众,与南面官下州县长官的作用是完全一致的。
部族还是组织各游牧民族进行畜牧等各业生产的单位,各部族长官既是行政首脑,也是本部族生产活动的领导者和组织者。《辽史》中不乏部族长官因领导生产有方而受到朝廷表彰和受到部众拥戴的典型。如耶律挞烈和耶律海里先后出任南院大王,前者以“均赋役,劝耕稼,部人化之,户口丰殖”[2](《耶律挞烈传》)而闻名,与同时担任北院大王的耶律屋质并誉为“富民大王”。后者“在南院十余年,镇以宽静,户口增给,时议重之”[2](《耶律海里传》)。
部族组织职能见诸文献记载最详细的是军事方面。被编制在各部族中的各族部众,亦兵亦民,“有事则以攻战为务,闲暇则以畋渔为生”[2](《营卫志上》),一身而兼有生活资料的生产者和国家武装力量成员的双重角色,遇战事发生,奉调集结,战事结束,各归驻牧,从事各业生产。此时的各部族长官再次发生角色转换,由平时的部族行政长官、生产活动的领导者转变为由本部族部众组成的军队的指挥者。正是由于部族组织的军事职能,形成了辽朝在军事上的所谓“无日不营,无在不卫”的近乎全民皆兵的局面。
由各部族部众组成的军队称部族军,在辽朝的军队序列中仅次于御帐亲军和宫卫骑军,而在五京乡丁之上。部族军又分为大首领部族军和众部族军两部分,关于大首领部族军,《辽史·营卫志中》说:“辽亲王大臣,体国如家,征战之际,往往置私甲以从王事。大者千余骑,小者数百人,著籍皇府。国有戎政,量借三五千骑,常留余兵为部族根本。”这里的所谓“大首领部族军”,是指部族长官称大王的五院、六院、乙室部和奚王府所属的部族贵族指挥的军队,只有他们才有资格“置私甲”。部族军的主要任务是赴边戍守[3],各部部众“胜兵甲者即著军籍,分隶诸路详稳、统军、招讨司。番居内地者,岁时田牧平莽间。边防纠户,生生之资,仰给畜牧,绩毛饮湩,以为衣食”[2](《营卫志中》)。由此可以断定,各部族的戍守地和驻牧地是分开的,但也不排除有个别部族的戍守地和驻牧地是同一的。在属于前者的情形下,部族又分为戍军和留后户两部分,“凡戍军隶节度使,留后户隶司徒”[2](《营卫志下》)。节度使和司徒的这种职责上的划分,显然赋予了节度使为部族军事长官、司徒为行政长官的意义。
《辽史》中就部族戍边有十分详细而珍贵的记录。耶律昭在统和年间给西北路招讨使萧挞凛的信中说:“夫西北诸部,每当农时,一夫为侦候,一夫治公田,二夫给纠官之役,大率四丁无一室处。”[2](《耶律昭传》)重熙年间,萧韩家奴在应制奏对中说:“乃者,选富民防边,自备粮糗。道路修阻,动淹岁月,比至屯所,费已过半,只牛单毂,鲜有还者。其无丁之家,倍值佣僦,人惮其劳,半途亡窜,故戍卒之食多不能给。求假于人,则十倍其息,至有鬻子割田,不能偿者。或逋役不归,在军物故,则复补以少壮。其鸭绿江之东,戍役大率如此。况渤海、女直、高丽合纵连衡,不时征讨。富者从军,贫者侦候。加之水旱,菽粟不登,民以日困”[2](《萧韩家奴传》)。从上述两段材料中可以得出以下认识:选择富裕部民赴边戍守,是辽朝基本的军事制度,在相当长的时期里都在实行,而且是在部族驻牧地与戍守地分离的情形下实行的,以使部民的防边兵役与“自备粮糗”的能力相适应;耶律昭所指应当是部族的戍守地,同时也是该部族的驻牧地。在此前提下,部民的戍边兵役就不分贫富,成为全体部民共同承担的任务,而萧韩家奴所说则属于部族戍守地和驻牧地互相分离是无庸置疑的。
当然,部族组织的军事职能,尤其是大小部族长官和贵族拥有的私人武装,对于辽朝最高统治者来说是一柄双刃剑,既是朝廷可以倚重的力量,也是贵族、大臣为达到个人目的所最容易找到的支持力量,甚至成为野心家兴风作浪的资本。辽兴宗要发兵联合北汉进攻后周,而“诸部大人皆不欲,兀欲(辽世宗)强行之”[4](《四夷附录二》)。“诸部大人”所以敢于公然和皇帝唱反调,除了契丹族氏族社会原始的民主制的残余仍在顽强发挥作用外,更与此时部族长官、贵族对于本部族的事务仍拥有相当大的自主权以及有听命于自己的武装有直接的关系。辽穆宗在怀州行宫被杀后,耶律贤等人“率甲骑千人驰赴”[2](《景宗纪上》),这里的甲骑很可能就是“私甲”。辽景宗病亟之际,觊觎皇位的野心家们认为有机可乘,蠢蠢欲动,“时诸王宗室二百余人拥兵握政,盈布朝廷”,使“内外震恐”[5](《耶律隆运传》),再次表现出拥兵的诸王宗室在非常形势下是一种极可能造成政局动荡的危险因素。但是,从总体上看,部族组织在辽朝统治中的积极作用是主要的,统治者对部族组织的控制也是成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