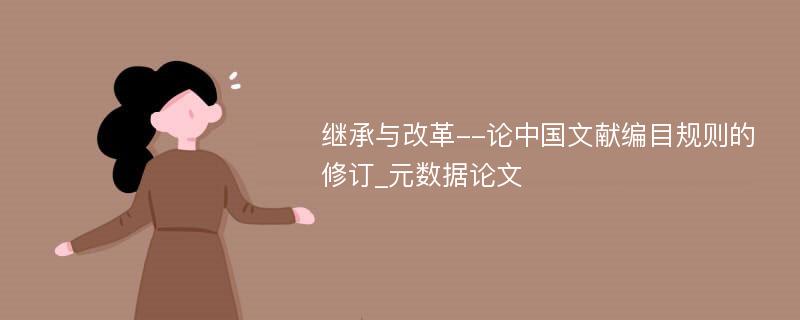
继承与变革——谈《中国文献编目规则》的修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编目论文,中国论文,文献论文,规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由国家图书馆牵头主持的《中国文献编目规则(第二版)》,在图书馆界内专家的共同参与和帮助下,历时两年时间,于2004年12月截稿。这次修订对于我国中文编目工作的实际指导作用怎样?如何评判《中国文献编目规则(第二版)》?终究要由专家和编目工作人员来评估。笔者作为主持这项工作的主要负责人,参与了修订的全过程,这里谈谈修订中遇到的问题和引发的思考。
1 修订的背景与基本情况
1.1 《中国文献编目规则》的作用
由黄俊贵先生主编的《中国文献编目规则》(1996年),是在我国文献标准化工作的推动下,在国家标准GB3792.1《文献著录总则》推广的基础上,结合中国文献编目的实际需要而产生的。在编制过程中,以《国际标准书目著录》(ISBD)为依据,参考《英美编目规则第2版》,充分体现了中国文献和传统书目的编制特点。1996年《中国文献编目规则》出版时,正值我国图书馆界广泛采用计算机编目,推行中国机读目录格式(CNMARC)的初期,应该说《中国文献编目规则》对我国中文文献著录的标准化,对中国机读书目数据编制的规范化,以及中文书目工作自动化起过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国文献编目规则》问世以来,在图书馆等文献机构广泛使用,是编目工作人员进行中文文献编目的主要依据和案头必备工具。可以说《中国文献编目规则》的编制与出版,在我国中文文献编目规则的发展历程中起到了里程碑的作用。
1.2 网络时代编目环境的变化
进入21世纪后,高新技术迅猛发展,尤其是网络环境下信息载体、信息传播方式、信息组织形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对文献机构而言,因文献类型和编目环境的变化,必然带来编目对象、编目载体、编目模式以及编目条例的变化,尤其是数字资源的迅速发展及其编目与整合,对传统文献编目规则提出了挑战。
在网络环境下,文献编目的理论与实践都有了较大的发展与变革,机读目录制作日趋完善。如何在使用机读MARC格式的基础上,改进编目规则不适用的方面,并对新产生的资源进行编目;又如何适应新的元数据处理格式,对数字资源进行编目著录,这是转型期图书馆文献编目工作遇到的新问题,也是急需解决的问题。
2001年前后国内图书馆及文献机构和有关专家呼吁,对《中国文献编目规则》进行全面修订。国家图书馆给予高度重视,牵头组织原撰稿人员和有关专家参与的修订小组,进行《中国文献编目规则》的修订工作。
1.3 《中国文献编目规则(第二版)》的修订原则
参加修订的专家一致认为,编目规则的修订应该面向信息化、面向世界、面向社会需求,实现与国际书目情报交流,使中文书目数据能为全世界所共享。修订要坚持与国际接轨,以ISBD/1992年版、GB3792.1最新版、AACR2R/2002年版等为依据;考虑网络环境下电子资源的特点,注重计算机编目的特点;注意规则的连续性,在修订中尽可能与原结构体例保持一致,在内容上应尽量采纳国际标准。总的修订原则:既遵循ISBD的规则,参照AACR2的做法,又要体现中国文献编目特色,不机械照搬,不被其不合理方面所束缚;既坚持整个编目规则体系的一致性,又要考虑各种文献类型的特殊性;既坚持标准规则的强制性,又保持适当的灵活性;遵循国际通行的方法,在实际编写中确保《中国文献编目规则》的稳定性、连续性和先进性。
这次修订面临转型期图书馆的急剧变革阶段,在把握《中国文献编目规则》的修订尺度上,既要继承传统的精华,又要适应变革的需要,增加新的内容。修改中不仅要对具体规则的微观问题进行斟酌,又要面对编目原则中新旧观念的碰撞。应该说修改的难度较大,遇到的问题较多。修订中我们与具有代表性的文献机构和有关专家进行了多次的讨论与交流,广泛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在一些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对有争议的问题保留了各自的意见,采取了灵活的处理办法。
在著录法部分,把握住总则的修改,原则问题在总则中体现出来。例如:关于信息源的选取、版本信息的选取、分析著录的内容等有所变化。不同文献类型的各章节在总则的指导下,采取适当灵活的原则,保持其特殊性。例如:连续性资源、电子资源、缩微文献等有所调整。
在标目法部分,在整体结构上做了比较大的调整,充实和增加了许多内容。增加了团体标目,例如:中国驻外使、领馆,外交团体,历史上的团体名称等。
2 《中国文献编目规则》修订中涉及的相关问题
2.1 《中国文献编目规则(第二版)》的适用范围
(1)出版发行环节的书目著录需求问题。在修订中有专家提出,本规则应该不仅适用于图书馆和文献机构,还应该适用于文献生产(出版社)传递(书商)与网站等机构。因为这些机构都在做文献编目工作,也都要使用著录规则,从更大范围考虑信息资源共享,还是统一为好。
笔者认为其他(出版社、书商和网站)机构进行文献著录,使图书馆编目工作前移,减轻了图书馆原始编目的工作量,图书馆也可以采用出版机构的书目数据。但出版机构与图书馆编制书目的最终目标不相同,出版社和书商对书目数据的需求侧重在流通环节,著录项目与图书馆有所不同,书目信息的使用周期不同,对许多著录信息原则上也不会长久保存,对书目数据的质量要求也不尽相同。当前,出版社、书商和网站等机构可以参照图书馆文献编目的规则,相同的著录项目尽可能取得一致,不同的著录项目,可以根据出版发行行业的需要设置。这次修订《中国文献编目规则》,出版发行机构的准备不够充分,还不适宜在规则中增加出版社、书商和网站在流通环节所需要的著录项目和内容。
(2)电子或自动编目的书目著录需求问题。在修订中也有专家提出:编目规则不仅涉及文献著录,还应涉及在文献生产过程中的著录。美国国会图书馆从1995年起开始ECIP计划(即自动编目),我国专家在2000年也开始进行ECIP探索,2003年出版了《中文图书ECIP与自动编目手册》,并研制了“自动编目软件”,目前已在一些出版社运行。建议编目规则相应应包括在版编目,避免相互脱节。笔者认为修改后的《中国文献编目规则》,可以指导ECIP编目,但不能替代。关于自动编目的描述性信息提取,究竟采用MARC元数据,还是DC元数据,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摸索与研究,因此时机并不成熟。
2.2 《中国文献编目规则》编制的体例
关于《中国文献编目规则》编制的体例,有专家提出应严格按照ISBD或AACR2的体例和章节顺序,著录法部分应与国际接轨。最新版的ISBD,划分为总则、专著、连续性资源、古籍、测绘资料、非书资料,并增加了电子资源,共计7个部分。新版的AACR2,在著录部分有总则、普通图书、连续性资源、测绘制图、电子资源、非书资料、乐谱、分析;标目部分有检索点的选取、标目的确立、统一题名、参照。但这次修订中没有完全照搬。
在编制体例讨论中,大部分专家认为,原《中国文献编目规则》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比较实用,这次修订在总的体例上应尽可能与原规则保持一致;其次,许多文献类型比较有特点,著录上有其特殊性,应考虑到大型图书馆收藏的丰富性,也照顾到一些专门的图书馆收藏的特殊性。第三,文献机构和编目人员希望对每一种文献类型的著录有一个完整的了解,以便操作。例如:古籍文献、金石拓片、缩微文献、手稿等。
这次修订著录法部分仍然保留了原规则的体例,增加了手稿,修改了分析章节。标目法部分,根据文献机构的实际应用情况做了修改,原标目法有4个章节,包括:款目的构成以及表示、标目范围、标目名称、标目参照。这次修订为5个章节,包括:总则、个人名称标目、团体/会议名称、题名标目、参照。另外,在讨论中对于地理标目是否单列一章有不同看法,通过讨论,多数专家认为在实际撰写中有两个问题不好处理,第一,我国行政管辖权地理名称与非行政管辖权地理名称的区分很难把握;第二,团体名称中的地理名称与主题标引中的地理名称在使用中的区分问题。所以这次修订没有单列章节,仅在团体名称中举例说明。
2.3 编目规则与机读目录著录的结合
在修订中一些专家提出:“在规则中要充分体现机读目录著录需要,反映计算机文献处理的要求,将著录规则与机读格式统一起来,显示格式以机读目录为主,需要统筹考虑手工编目与计算机编目两方面的需求。”在最初的总则修改中,也曾想尝试与机读格式结合。但经过研究讨论,认为不适宜。原因如下:
(1)编目规则与机读格式不同
编目规则包括著录法与标目法两大部分,主要是对文献著录项目和标目选取时的规则。编目规则与机读书目的表现形式和显示格式,以及工作人员操作的工作单格式、检索与使用方法之间有必然的联系,但作用不同,不能混为一谈。有一种观点认为:“机读编目已经成为编目工作的主流,可以不考虑手工编目,因此,著录格式和显示格式也不必考虑卡片格式,以前的编目规则已经没有用了。”
笔者认为,机读编目是继承了传统编目的精华部分,增加了文献描述的范围,增强了目录记忆与显示的能力,书目描述的内容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只是款目载体变化为磁性材料,书目的组织管理由计算机来完成。编目规则是负责文献信息著录项目的选取原则,机读目录格式是负责著录项目的组织与处理顺序。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每个文献机构可以根据编目规则、机读格式、分类法、主题词表,制订本机构的操作手册与细则,但不可能以机读格式替代编目规则。文献机构希望有比较统一的,将编目规则、机读格式、分类法、主题词表相结合的操作手册和细则,国家图书馆联合编目中心正在考虑编制。
(2)关于显示格式的问题
计算机编目的书目数据,可以提供多种显示格式。机读目录继承了卡片目录和书本式目录主要内容与形式,因此,为了照顾读者的阅读习惯,图书馆在向读者提供目录检索时,大部分是按照卡片的形式或者分段形式向读者提供的。有专家提出:“修改后的规则,仍然采用卡片目录格式,没有同时提供网络显示方式,把卡片目录的显示形式当作著录规则,没有将信息著录要求与其显示方式加以区分,传统限制了发展,显示方式也只说明了书目的印刷形式。”
笔者认为,《国际标准书目》(ISBD(M))在范围一节中指出:“在书目记录存储于机读载体的情况下,各种ISBD仅为可直接目读的输出形式,如联机屏幕显示或印刷产品制定了显示规则,而不对机读载体本身的数据结构做出规定。”编目数据的显示格式,现阶段没有明确的规定,编目机构处理书目数据,尤其是向读者提供检索时,可采取不同的方式。目前实际操作中主要有两方面。第一,编目员使用的操作界面和工作单格式,是采用MARC机读格式;也有的操作软件,采用传统的卡片格式。第二,读者检索的显示格式,有MARC格式,也有卡片格式,还有采用主要项目分段格式,或三种方式均采用。那么显示格式是否需要统一?哪一种方式符合读者的需要?是值得研究的问题。笔者认为只要符合读者的检索习惯,满足检索需要,可以不求严格的统一。目前从元数据发展的趋势来看,不同的元数据揭示信息和显示信息的格式是不一样的。
2.4 编目规则兼顾DC元数据编目的问题
DC元数据的出现是为了适应电子资源和网络资源的编目,它可能更适合于数字资源的整合。其主要特点是采用XML置标语言,人和机器均可以阅读元数据,便于元数据在网络上交换。DC元数据目前在实际应用中存在一些问题,还不够完善和成熟。例如:面对不同类型的文献信息和数字资源,15个核心元素远远不够,可以根据不同信息类型扩展,而各个机构没有统一规则,无限制扩展的结果,将导致数据无法交换;15个核心元素,对描述性元数据比较适合,但不能很好地解决揭示结构性元素和管理性元素。为了解决以上出现的问题,适合不同的文献信息与数字资源的处理,美国国会图书馆根据数字图书馆的发展,结合MARC、DC元数据应用,研制了《元数据编码和传输标准》(Metadata Encoding and Transmission Standard),简称METS,它较好地解决了数字资源的创建、对象描述、组织与管理、资源服务、资源长期保存的问题。METS是一个数字对象的元数据编码和传输的标准,适用在一个数字仓储中管理数字对象,以及在多个仓储中或者在仓储和其他用户之间交换对象。可以说METS突破了DC元数据的限制,融合了MARC元数据的结构,提出了一个类似MARC结构的新的元数据编码与传输标准结构。同时创建了《元数据对象描述模型》(Metadata Obiect Description Schema)MODS,用于将MARC21记录中选择的元数据,以及原始资源描述,组成基于XML的元数据格式。不使用MARC字段标识号,而使用易于理解的元素名称,如:“title”、“name”和“subject”等。为书目元素开发了XMLschema“MODS”,选取了MARC21的主要元素,对元素进行了重新组合,MARC的几个元素内容被组合在MODS的一个元素中,字段名采用文字形式。元素比DC多,比MARC少,更加面向用户,适合于图书馆。是一个元素对象集,在METS的框架中使用。
笔者认为DC元数据应用于实际操作,还需有一个发展过程,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改进,DC元数据整体结构和应用还会发生较大的变化。因此,《中国文献编目规则(第二版)》目前不可能解决或兼顾DC元数据的著录。当然在制定DC元数据著录规则时,可以借鉴编目规则,在主要的著录项目上取得一致。
2.5 标目法部分的修订
这次修订对标目法部分改动比较大,原规则中标目法部分内容比较单薄,没有把书目的规范控制置于重要地位,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基于当时处于卡片目录向机读目录的转型过程中,没有考虑到机读目录规范控制的解决办法。二是还没有规范数据制作的大量实践,缺乏对规范数据的认识。但在《中国文献编目规则》问世后的几年,随着机读目录的普及,图书馆编目人员和专家都意识到了书目规范控制的重要性。近年来图书馆书目数据库数据量迅速增加,由于书目数据缺乏规范控制,书目数据库在使用过程中不但没有发挥机读书目查询的便捷和优势,反而给读者检索带来极大的混乱。因此,在机读书目数据的编制过程中,标目的确立就显得尤为重要,在修订中专家们达成共识,标目法部分的修改要结合中文文献编目的特点,系统地制定标目的选取规则。
对标目法的修订,在结构和内容上进行了比较大的补充与修改,对许多规则进行了细化,列举了大量的实例。如果说这次修改能够得到肯定,是因为得益于一些大型图书馆在规范数据库建设中的大量实践。近几年国家图书馆和高校图书馆制作和积累了大量的规范数据,取得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发现了一些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总结了一些典型的个案,为这次修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 编目规则的发展趋势
3.1 新理论框架——书目记录的功能需求(FRBR)
1998年国际图联推出的《书目记录的功能需求》(Functional Requirements For Bibliographic Records),是1961年“国际编目原则会议”以来,国际编目原则和编目思维模式上的重大突破,它从理论上探索编目实体所具有的客观属性,以及实体之间的相互关系,针对编目对象提出了立体化的编目工作模式。它的重要贡献在于:
第一,提出了采用“实体—关系模型”的结构描述信息。
(1)将编目工作分为三组实体:著作、个人与团体、主题。
(2)将第一组著作又分为四个不同层面的实体:著作(Work)、表现形式(Expression)、表达方式(Manifestation)、文献单元(Item)。
(3)第二组个人与团体是第一组实体的责任者,即责任关系。
(4)将第三组主题分为四种类型实体:概念(concept)、实物(object)、事件(event)、地点(place)。同时包含了第一、第二组实体。
第二,从书目记录的功能和目录使用者的角度,提出书目记录应具备发现实体、识别实体、选择实体、获取实体的四个功能。
在《书目记录的功能需求》(FRBR)中,强调面对编目对象的分析与描述,多层面地揭示文献信息,形成一个立体的元数据模型,便于编目人员揭示与处理网络环境下多种媒体信息。这一新理论框架的出现,适应了数字资源编目实践的需要,在理论上突破了原有的文献编目规则理念和编目工作模式,为在网络环境下编目工作的实践提出了理论指导,在建立数字资源元数据描述规则中将发挥指导作用。
3.2 编目规则的突破
国际标准著录规则产生于19世纪70年代,主要适用于印本文献,在21世纪的网络环境中,国际标准著录规则也在考虑如何适合电子文献和网络数字资源。《英美编目规则》第二版(2002年修订版)在这方面作了许多尝试。例如:在对文献书目资源定义中提出:“文献书目资源可分为有形和无形”;以及就电子资源在著录中,遇到的关于信息源的确立、版本项和载体形态项选择等新问题作了修改。《中国文献编目规则》这次修订中也采用了许多新的做法。但是在修订过程中我们感到,只在原有的框架下修修补补,不能适应新的变化。《书目记录的功能需求》(FRBR)的理论框架,将会对未来规则的修订产生主导作用,使编目规则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笔者认为可能会有三方面的变化:
首先,编目规则的框架必然要突破原有的结构,采用《书目记录的功能需求》(FRBR)的结构,对不同编目对象的信息采取不同的描述方法,突破以区分文献类型和载体类型的结构编制著录规则,而注重编目对象的特点,强调编目实体以及之间的关系。
其次,在著录项目的设计上,要考虑文献和数字资源的生命周期,增加文献信息管理性和技术性内容的描述项目,或者元数据元素。
第三,在著录内容上兼顾多种元数据格式,适用于多种元数据著录的要求。
我们希望这次修订后的编目规则,能够适应我国中文文献编目的实际需要,为提高我国文献编目质量,推进中文文献编目标准化,促进国际书目交流做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