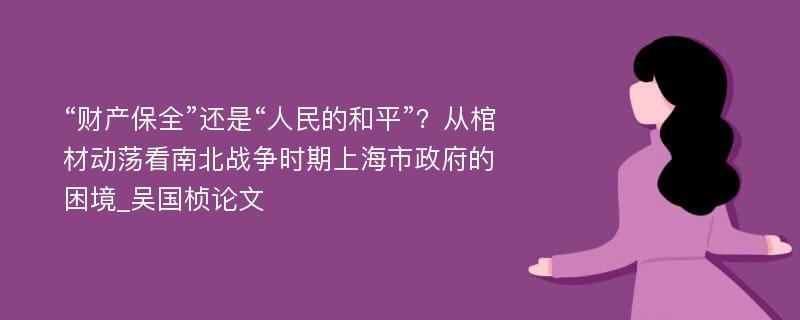
“保产”还是“安民”?——从“寄柩所风波”看内战时期上海市政府的两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内战论文,风波论文,上海市政府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47年10月18日,3000多苏北难民涌进拥有200多间丙舍的平江公所,将900多具带尸棺材移置空地,毫不客气地住下来了。① 此时国共内战重开,大量苏北难民涌入上海,无处栖身的苏北难民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冲击“鬼魂宾馆”——寄柩所。据不完全统计,到1948年底,先后进入上海各大小寄柩所、山庄等居住的难民总数达2万余人,是为“寄柩所风波”。国民党上海市政府从1927年成立开始,即肩负着在中国建立一个现代市政府、“为最终收回租界铺平道路”的重任;也就是说,上海市政府一开始就以建立一个现代政府为己任。② 正如蒋介石在特别市政府成立大会上所说:“若上海特别市不能整理,则中国军事、经济、交通等,即不能有头绪。”③ 承载了如此多厚望的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实际举步维艰,在处理此次“寄柩所风波”中再次陷入是保护私人产业还是救济难民的两难选择之中,再次凸显其角色的无奈与局限。
一 同乡会与市政府的交涉
“寄柩所”又称“殡馆”、“丙舍”、“殡舍”等,是各地同乡会馆设立的专门存放客死异乡的同乡尸棺的地方。近现代上海的同乡组织特别发达,各种各样的会馆、公所、同乡会等,无论规模还是能量,都显得非常突出。④ 会馆公所等同乡组织的首要任务就是帮助同乡寄存、运送灵柩回乡安葬,使其实现落叶归根的梦想,因而大多都设有寄柩所。⑤ 这些寄柩所规模不一,根据各地同乡会实力及其家乡离上海远近而定;当然也有一些丙舍是以营利为目的,更要参照商业活动原则确定规模大小,小者仅有几间丙舍,大者多达数百间,能存放上千具棺材。⑥ 寄柩所拥有大量丙舍房间,对政府而言,它们是受法律保护的私产,不属于公共财产;对同乡来说,它们是属于全体同乡的公产,是公团私产,不容非同乡染指。在近代上海的多次战乱中,同乡团体在救助同乡、救济难民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部分会馆公所也利用空余房屋主动开设难民收容所,收容救济难民等,⑦ 但很少有难民大量冲击寄柩所、直接与死者争地盘的事情发生。
寄柩所等被难民占居之后,各寄柩所、公所、会馆以及同乡会随即要求市政府履行现代政府的基本职能,驱逐非法占据者、保护私人产业不受侵犯。如潮惠山庄在1947年11月21日被难民占居之后,潮州旅沪同乡会理事长郑子良于当日向当地派出所报警;警察随即赶到现场,将六位难民代表带到派出所讯问。难民要求暂借山庄容身,不肯迁出;派出所则因警力有限,无法驱逐,只得向上级嵩山警察分局请示。在此过程中附近难民闻讯而来,加入占居者行列,很快就有210多户1300多人进驻山庄。嵩山分局对于该如何处置占住山庄的难民也一筹莫展,只得将案情汇报给上海市警察局和市政府。⑧
上海市政府此前已经接连收到难民占居寄柩所、殡舍的报告,因而命令上海市警察局“妥慎防范”,警察局在1947年12月9日专门召开会议讨论处置办法。最后要求“社会局会同民政、卫生、警察等局及社会法团与贤达组成统一机构,严格管理,务使井然有序,不使成为社会严重问题。”⑨ 但实际上未能形成任何具体决议,警察局又将难题推给了市长吴国桢。⑩
与此同时,各会馆、公所、寄柩所等迅速动员各种可供利用的关系,向市政当局施加压力。潮惠山庄被占居后,潮州旅沪同乡会致信广东旅沪同乡会理事长、潮州和济医院院长张伉龙求援;张伉龙给同属广东同乡的外交部驻沪办事处主任陈国廉写信,要求陈与市长吴国桢以及警察局长和社会局长等交涉。12月15日陈国廉写信给吴国桢,“勉为恳请勒令迁移”(11)。同日,吴国桢命令“社会局及冬令救济委员会迅予统筹救济”,同时命令警察局“至该民等非法侵占寄柩所,仍仰会同社会局妥为制止”。(12) 12月16日上海市冬令救济委员会拟出方案,要求各寄柩所、殡舍、会馆、山庄等“速将少壮老弱分造名册,投请庀寒所收容编队参加工赈”。吴国桢马上签发了此方案,并命令警察局、社会局通知寄柩所等照此办理。(13) 吴市长本以为认真执行该方案即可万事大吉,因此在回复各寄柩所、公所、会馆的报告以及各关系人等的信件时都信心十足地宣称,“业经本府颁布布告,并通知各该社团等饬各遵照”(14) 云云。社会局、警察局接到命令以后就将任务交给各该管警察分局或区社会行政部门等,然后再分配给各派出所、区公所。然而每一个寄柩所、殡舍内难民动辄成百上千,且难民大都不愿搬迁,因此警、社两局根本无力执行吴市长的命令。(15)
寄柩所、殡舍等则继续向市政府施压。12月21日张伉龙再次致信吴国桢,请求面谈;24日,国民党中央委员、行政院侨务委员会委员长、广东人刘维炽致函吴国桢,请求饬属“迅令该郑维明等众概行迁出、妥护山庄以维原状”(16)。12月27日,大同、沪东两寄柩所联名上书吴国桢,指出此前市府承诺庀寒所成立后于12月20日迁出难民,但“限期瞬即届到,近阅报载各处之庀寒所次第已告完工”,而寄柩所内的难民却“未见有何动静”,要求市府“从速执行迁移,以免事态扩大”。(17) 时隔不久,平江公所、江宁六县会馆、吴江旅沪同乡会、杨属七县旅沪同乡会附设扬州公所、潮惠山庄、通如崇海启旅沪同乡会、大同寄柩所、沪东寄柩所、旅沪湖州会馆、京江公所、浙金嵇善堂等10多个同乡团体和寄柩机构多次联名给市政府写信,要求“勒迁”难民,并要“赴辕请愿”,(18) 京江公所甚至推派王渭滨、陈宗美二代表进京请愿。(19)
到12月底,各个寄柩所、殡馆等给社会局、警察局、警备司令部、上海市参议会的报告,都先后被转送到市政府;各个同乡组织的在沪头面人物也纷纷写信给吴国桢等,要求协助处理被占殡馆、丙舍问题。更有甚者,大同、沪东两寄柩所直接向行政院院长张群求援,“请求钧院迅赐饬查勒令他迁,并作有效之处置而维地方安宁”。行政院批示上海市政府尽快解决。(20) 12月27日,吴国桢给刘维炽、张伉龙、行政院、上海市参议会议长潘公展等回信,仍以冬令救济委员会16日方案答复之,并饬令警察局“严厉执行”。(21)
但冬令救济委员会的方案缺乏可操作性,难民拒绝搬迁;各派出所力劝无效,纷纷要求“强制勒迁”,但市警察局又认为“如强制执行迁让,深恐引起其它事件”,不敢擅作主张,又将皮球踢给了吴市长。(22) 面对众多的报告、各种关系人的信件等,吴国桢只能不断批示“严令社会、警察两局遵照冬令救济委员会办法,严限迁入庀寒所”。(23) 但上海市冬令救济委员会主任委员正是上海市市长吴国桢本人(副主任委员由上海市社会局局长吴开先兼任),面对众多要求“勒迁”的信件、请求、命令等,吴国桢市长全部答复由冬令救济委员会“妥筹”解决办法;而冬令救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吴国桢无法可筹,又向市长吴国桢报告,力陈“本会无法勒迁”。(24) 上海市政府、上海市冬令救济委员会、上海市警察局、上海市社会局等部门在此问题上都没有采取任何有效手段,只是在公函中反复申明其解决方案,以此来敷衍应对各方责难。
正因上海市政当局对难民强行占居寄柩所等公团私产的问题无计可施,随后来沪的难民更是群起效尤,纷纷“通知”市政府各部门,声称准备“借用”某某公所或寄柩所,有些甚至直接强行占据空余寄柩所。(25) 到1948年仍然接二连三地发生寄柩所、丙舍房屋被难民占居事件,而上海市政府却依然束手无策,“长此勒迁,终非良策。”(26) 就在市府左右为难之际,1948年8月南京国民政府社会部为救助难民,决定在苏北、江西等地设立三个难民垦殖区,(27) 上海市政府随即决定将占居寄柩所的难民“并入移垦江西案内办理”,(28) 但此前警察局就无法将难民从寄柩所驱逐出去,现在更无法将其从大上海驱逐出去,此一方案依然难收实效,到1949年解放军进入上海之前,此事都不了了之。(29)
二 “义民”的愤怒
同乡会一方面坚持私有产业不容侵犯、要求市政府予以保护,同时指责难民为“莠民”,名正言顺地将其排除于救济范围之外。潮惠山庄、潮州旅沪同乡会以及广东旅沪同乡会等在向淞沪警备司令部、上海市政府、上海市警察局、社会局等部门报告山庄被占时,一再声称山庄“被流氓用强霸占”、“流氓、乞丐及土老百数十人横施强占”。(30) 在此后的各种交涉中也始终强调山庄被“流氓假借难民名义”霸占,“藉故牟利”等,并声称占居山庄者大多是三轮车夫、黄包车夫、工人、佣工甚至小老板,他们中很多出入山庄“有乘三轮车者、驾驶自由车者;膳食鲜美、衣服华丽者亦不乏人”(31)。也就是说,潮惠山庄方面始终认为占居他们山庄的并非是真正的苏北难民,而是假借难民名义或者说是冒称难民来擅自占据公团私产的地痞、流氓等“莠民”,因此对待他们“实不能稍予姑息,苟不执法以绳,则非唯社会安宁破坏无遗,抑且长恶养奸,致导乱萌……”。(32)
安徽殡馆(皖北山庄)亦多次强调其山庄“被当地流氓自称苏北难民”率众占据,“大有霸山为王之势,且此批莠民及不肖军人奇装异服,进出多搭三轮车,饮食清洁,自外送进,早出晚归,悠游自得。”(33) 延绪山庄、锡金公所等都采用了“自称难民”的称谓,并声称其“恃众强入侵占”山庄、公所,其行为“不似难民之暂借以蔽风雨,而为强有组织之占人产、分间出顶、转租牟利之搭屋党……是可忍孰不可忍?”(34) 各寄柩所、公所、山庄联合给市政府的呈文中虽然也承认“所谓真正难民,固亦有之”,但接着强调“而衣冠清洁、家具整齐者亦复不少,是不啻以难民为职业,甚或拉车负贩,朝出暮归,或顶让原有之棚户而参加占居,或把持现有之占居而私相移替,似又为有职业之难民,职业难民、难民职业,交相为用……”呈文最后更是强调,“值此冬防吃紧,岁暮天寒,设有宵小参杂其间,则社会隐忧何堪设想?”(35)
总之,寄柩所、山庄、会馆、公所等同乡组织认为占据他们产业者并不是“真正难民”,而是地方流氓或者各种以难民之名行窃占他人产业之实的“莠民”。同乡会声称对于莠民的非法行为“本可诉诸法律,诚恐纠纷扩大,社会不安”,才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方式,希望市政当局施加压力,迫使占居者迁走。(36)
面对“莠民”的指责,苏北难民理直气壮地宣称自己是“义民”,是投奔国民党政府而来,理应得到国民党上海市政当局的善待。就在潮惠山庄郑子良向上海市政当局控告“莠民”占据山庄、要求当局勒迁之际,潮惠山庄难民代表也给上海市政府写信求援。难民声称他们“仗义来沪……迫不得已,暂借山庄栖身,与鬼为邻,以求喘息之安,”但郑子良却指使粤籍警官到山庄逮捕代表,并威胁要派警察“将本所避难义民整个逮捕”,因而激起难民公愤,“如照郑子良一意孤行,得寸进尺,势必酿行惨案。咎将谁归?”因此难民呼吁市长“主持正义,该郑子良如有非法异动,请派员警莅临劝阻,以免滋生祸端”。(37)
苏北难民认为他们“素怀忠贞”,因而才“抛妻弃子,追随国军,西撤南来”,是响应国民党政府的号召而出逃的“义民”。(38) 他们辗转逃到大上海,不仅得不到国民党当局的保护,甚至连他们历尽千辛万苦才找到的寄柩所都不能让其容身,因此他们愤怒地质问:难道“苏北义民不及潮惠的死鬼吗?”(39) 外地人死了尚且有个寄柩之处,苏北人活着却找不到安身之所,这种巨大的落差更是强化了苏北难民的愤怒,也强化了他们作为一个集体的意识,因而更加团结起来共同对抗市政府与同乡会的勒迁要求。
为了安置难民,上海市政府在1947年底到1948年初先后开办了3个庀寒所和若干个工赈庀寒所。(40) 1947年底开始出现难民占居寄柩所事件时,上海市政府即要求各寄柩所、会馆、公所等将难民造册登记,其中青壮年难民送工赈庀寒所参加濬河工程,其他老弱病残送第三庀寒所等接受收容救济。但难民认为他们本是“良善公民,均皆小有资产,安分生活”,(41) 他们只是因为不肯“附匪”才逃亡来沪,因此他们不是来上海祈求救济或者乞讨的,政府将他们安置到庀寒所是对他们的侮辱和不尊重。难民在呼吁信中说:“庀寒所是白面鬼、梅毒、砂眼传染病菌媒介所,政府应注意义民的健康,不应叫我们去染恶疾”,“庀寒所是无家无室无兄弟子女关系的场所”,“庀寒所是收容瘪三、小偷的,政府不应教我们义民与他们杂处”。(42) 因此难民普遍拒绝搬进庇寒所。
三 市政当局的“为”与“不为”
处于同乡会与难民夹击中的上海市政当局扮演着十分尴尬的角色,既无法满足同乡会“勒迁”难民的要求,同样无法认同难民的“义民”定位,因而左右为难,处处掣肘。但市政当局对于寄柩所内所发生的事情也并非完全无能为力,而是有选择地进行干涉,力图防止发生其他不测事件。
1948年清明节前,因不满于潮惠山庄被占,陈德业等广东同乡组织了200多人的后援会,并每天在电台广播,号召同乡组织扫墓团和护灵队,准备在清明节“对于护灵行动有所表示”。吴国桢接到郑子良的报告后不敢怠慢,立即批示警察局、社会局“妥为防范”。(43) 上海市警察局卢家湾分局接令后立即派出警察护庄。4月5日清明节那天,陈德业等拉来两大卡车广东同乡,“欲强迁难民”,但被护庄警察和驻庄董事劝阻,未发生大的冲突。(44) 一场酝酿已久的冲突被市政府和警察局明智地消弭于未遂之时。
1948年5月24日,郑子良再给吴国桢写信,申诉占庄难民在庄内“搭盖棚屋,图事久占,有引起火灾,祸延全庄及四邻之虞。”并质问“倘发生火患,危害地方,其责任将归谁负?”(45) 市政府秘书长宗濂和吴国桢随即批示:“令警局严厉制止,并将违章建筑拆除。”(46) 6月8日,嵩山警察分局会同工务局组织拆卸队到潮惠山庄,“当场拆除已建成空棚44间”。(47) 但仍有70间棚屋因住有难民而未拆,市政府对此批示到:“至未拆棚屋,如业主允予缓拆,似可不必勒令拆除,暂缓执行。”(48) 因此市政府对于那些可能威胁到同乡会财产和难民人身安全或可能引起大众恐慌的事件进行了及时有效的处理。
同年8月,占居潮惠山庄的难民向市政府、警察局写信举报难民代表陈光舟等搜刮难民钱财、侵吞救济物资、冒领政府救济款项以及纠帮结伙欺压难民等事。吴国桢马上批示“令警、社两局查明究办!”(49) 警察局调查后发现陈光舟、赵铁军等十余人的确以难民代表的名义“虚报户口,诈领配给品证,并藉故敛财”等,因此将赵铁军等四人抓获并移送地检处法办,同时继续发布通缉令追捕陈光舟等潜逃嫌犯。(50) 10月4日市政府再次命令警察局,要求“严缉该陈光舟等归案究办”,警察局回复称陈光舟“潜赴海门”,并仍在“严密查缉中”。(51) 无独有偶,安徽殡馆管理员唐海珊举报流氓孙步洲等冒称难民占居殡馆馆舍,请求处理。市政府命令警察局、社会局核查上报。警察局调查发现孙步洲等果真是冒称难民,立即“予以逮捕”,交地检处法办。社会局呈文更加意味深长,其文称孙步洲等经警局勒令迁出后,“现居该处者为陈述之等苏北难民三百余人,尚知法纪。”(52) 占居安徽殡馆的难民一度被安徽同乡赶出庄外,但后来更多的难民继续抢占山庄,并且人数一度多达1200余人,使得安徽同乡再也无能为力。(53) 此次警察局调查以后强行赶走了大部分的假难民,对真正的苏北难民却仍未采取强制行动。
市政府除了对占居寄柩所等地方的不法分子予以追究以外,对于同乡会方面对难民的指责,警察局经过调查以后还会予以澄清,肯定其难民身份,并多有袒护之词。如郑子良一再指责“流氓”占居潮惠山庄,擅自移动棺柩,甚至强夺馆丁物品等,但警察局在给市政府的呈文中则称:“……至劫夺私人燃料,强夺馆役炊具,驱逐馆丁等情并未发现”,“该批难民留住处所均系潮惠山庄无人居住之空房,对于该会馆办理殡殓寄柩埋葬等福利善举并无妨碍。”(54) 警察局在回复淞沪警备司令部对难民占居大同、沪东寄柩所一案的质询中说:“该批难民既无违规不法行为,尚能安分守纪,故未严加执行勒迁。”(55) 警察局在调查了占居衣庄公所的难民以后也说“该批难民秩序尚佳……且居处与寄柩所隔绝,不妨碍该所之业务。”(56) 总的来说,市政当局认为占居寄柩所等地的难民中“真正贫苦难民占80%”,“难民中有20%为小贩与苦力”。(57) 也就是说,对于寄柩所等同乡团体声称占据其产业的难民如何横暴、如何无法无天等说辞,无论是警察局、社会局还是上海市政府,并不十分认同,反而对难民多有袒护。
当然市政府对于难民自称的“义民”身份也从未公开认可,更不答应难民要求的各种特殊照顾,但市政府在行动上还是对难民持同情态度。难民占居寄柩所事件发生以后,市政当局即要求难民迁入庀寒所,并声称“如不迁入庀寒所,绝对不予救济”,(58) 但实际上难民占居潮惠山庄以后,“不数日,即有施衣、给米、赐币、赏草及烧饼、馒头等物”,(59) 并且还有“卫生当局派医师及护士至庄内注射防疫针”,不久又有卡车载来“大饼十箩又四布袋等救济品”等等。(60) 吴国桢在批示各难民占居寄柩所等的报告中虽然一再要求“警、社两局勒迁”,同时也不忘强调“并筹救济”、“设法救济”、“随时救济”等。(61)
市政府虽然三令五申要求难民迁出寄柩所等同乡团体产业,对那些尚未正式入住而只是请求暂借寄柩所的“申请”更是批复“不准”、“碍难照准”。(62) 但随着难民越来越多,市政府更加无力安置,因此对难民提出的暂借某某寄柩所或公所的请求表示某种谅解,只是要求“应先征得业主同意,不得擅自强占。”(63) 因为此时市政府已经明白,强制难民他迁并不现实,“迁至何处颇成问题”,而另设难民收容所,则“经费又无出处”,(64) 更何况即使设立收容所,难民也不愿意前往。值此岁末天寒地冻之际,当局亦不能强行将难民驱逐出寄柩所而使其流落街头,“令死人棺柩占居空屋,活人遭冻馁之苦,”(65) 因而只得听任难民自行寻觅暂措之所。
摇摆在安置难民与安抚同乡团体之间的上海市政当局,看似优柔寡断,但在采取措施防止冲突扩大、拆除有隐患的违章建筑以及严厉惩处违法犯罪活动等事情上,却表现积极,这在在说明市政当局并非对难民完全无能为力。国民党上海市政府作为一个“现代政府”不得不承担保护私人产业的责任,同样也必须安置“仗义来投”的难民;市政当局既无法不理睬同乡组织以及其他各种关系人的申诉、请求,更无法不顾难民的实际生活困难,而且衡量之下还得尽可能照顾难民的实际需要,因此市政府不得不周旋于同乡组织与难民之间,尽可能履行地方政府的职责,维持尚未崩溃的地方秩序。
四 结语
同乡组织在上海有着悠久历史,并在近代上海城市发展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国民党统治上海以后,上海市政府更加强了与同乡组织等社会团体的联系;(66) 在上海遭遇战争的时候,各同乡团体大都部分担负起救济难民的责任。(67) 而且同乡会的领袖们大都是上海各界精英人物,如潮州旅沪同乡会理事长郑子良不仅是帮会大佬,同时还是上海市鸡鸭业同业公会理事长、南北货同业公会董事长等,抗战时期还追随戴笠积极抗日,(68) 抗战胜利后成为上海滩“国大代表候选第一人”。(69) 其他同乡组织的领袖也大都是上海乃至全国很有影响的精英人物,其能量相当大,一直以来也是市政府治理社会过程中需要依靠的力量,怠慢不得。(70)
但市政府同样不得不考虑难民的生存问题,尤其面对千里来投、口口声声称自己“素怀忠贞”的难民,市政当局也不能将其拒之门外。而此时市政府财政上捉襟见肘,无力多设收容所救济难民;即使是勉强成立的几个庀寒所,不仅容量有限,而且条件相当简陋,无法满足难民基本生活需要。难民们历尽艰辛逃到上海,占居寄柩所等死人托棺之处,与鬼为邻,聊且暂避风雨,市政府无论从道义上还是从法理上都无法动用武力进行驱逐。而且,此时期正处于国共内战之时,国民党统治下的政府如何对待难民,也是国民党能否争取民心的一个重要方面,溃败的军队尚且要护送难民逃亡,而非战区的上海市政府更不可能将难民驱散到街头。因此从1947年10月份难民开始占居上海寄柩所,一直到1949年5月国民党撤离上海,市政府始终没有采取严厉措施驱逐难民。
学界关于抗战之前的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已经有了相当多的研究成果,(71) 但对抗战胜利以后尤其是国共内战时期国民党政府的所作所为仍然缺乏关注。本文从一个侧面对内战时期的上海市国民党政府进行了探讨,虽然此时期国民党在战场上节节败退,其统治下的上海在经济、政治等方面陷入全面衰退与混乱时期,但此时的市政府并没有完全屈服于既得利益集团和有产者阶层。在处理寄柩所风波中,市政当局采取各种或积极或消极的措施,部分维护了难民等弱势群体利益。
在这一事件的交涉过程中,同乡会等社会团体一再声称“现代政府”应该维护社会秩序和私人产业安全,然而他们自身也并不完全按照现代人的法则行事,比如难民占居寄柩所后,同乡组织虽然明确宣称他们触犯了刑法第320条和第335条,“本可诉诸法律”;但他们却又弃法律不用,而再三“呈请有关主管机关请求制裁”,并不断争取各种有权势之同乡向市政当局施加压力,希望通过私人关系或者同乡网络的力量来解决此问题,即仍然采用了传统的抗争手段,并不诉诸现代法律制度来解决问题。(72) 那些由于发生自然灾害而无以为生的生计性难民,在逃难中总是一副弱者形象,而苏北难民因为声称自己是“仗义”来投奔政府,因此,理直气壮地要求上海市政府和地方社会提供救助,完全是一副不肯委曲求全的形象。市政府既要关心社会秩序,保护私有产业;同时更要关注民生安全,难民的生存、生活成为市政府必须努力应付的难题。在这里,各方都高举“现代”大旗,并要求对方处理问题要符合现代行为准则,但各方采取具体行动时又大都并不完全采用现代做法,比如诉诸法律或通过法庭裁决等,而是不约而同地采取了更传统的做法,如通过人际关系网络来向对方施加压力等。作为一个并不现代的“现代政府”,上海市政府手头并无太多可以动用的资源,因而处在“保护私人产业”还是“安置难民”这样的夹缝之中,左右为难,但它并未屈服于强势集团,而是仍然坚持以民生为重,多方周旋,尽力维持难民来之不易的生存机会。
注释:
① 《各公所会馆山庄寄柩所被自称难民占居概况表》,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以下简称沪档),Q1—10—190。
② [美]魏斐德:《上海警察:1927—1937》,章红等译,周育民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41页;[法]安克强:《1927—1937年的上海——市政权、地方性和现代化》,张培德等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24页。
③ 转引自[美]魏斐德:《上海警察:1927—1937》,第41页。
④ [美]顾德曼:《家乡、城市和国家——上海的地缘网络与认同,1853—1937》,宋钻友译,周育民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3页;宋钻友:《同乡组织与上海都市生活的适应》,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第13页。
⑤ 冯筱才:《乡亲、利润与网络:宁波商人与其同乡组织,1911—1949》,《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2期;宋钻友:《同乡组织与上海都市生活的适应》,第9页;郭绪印:《老上海的同乡团体》,上海:文汇出版社,2003年,第27页。
⑥ 上海大同、沪东两寄柩所丙舍多达上千间(《苏北流亡义民请求救济》,沪档,Q109—1—1706—1);1946年上海市卫生局调查认为上海其时各寄柩所等地积存棺柩逾10万具(《上海市卫生局饬令各会馆公所殡仪馆寄柩所等造送存棺柩报告表》,沪档,Q400—1—3984)。
⑦ 王春英:《抗战时期难民收容所的设立及其特点》,《抗日战争研究》2004年第3期;张玲:《战后苏北旅沪同乡团体的救济难民工作》,《档案与史学》2000年第5期;宋钻友:《抗战时期上海会馆、同乡组织难民工作初探》,《上海党史与党建》1995年第1期;罗义俊:《“八一三”时期上海的难民工作》,《社会科学》1982年第8期。
⑧⑩ 《俞叔平为潮惠山庄被流氓用强霸占一案呈请核示》,《苏北难民占居大同及沪东寄柩所请示由》,沪档,Q1—10—190。
⑨ 《处置强占公所山庄难民会议纪录》(1947年12月9日),沪档,Q1—10—190。
(11)(16) 《张伉龙给陈国廉的信》,《陈国廉给吴国桢的信》,《刘维炽给吴国桢的信》,沪档,Q1—10—190。
(12) 《关于苏北难民寄居寄柩所》(1948年1月3日),沪档,Q1—10—190。
(13) 《上海市冬令救济委员会函件》(1947年12月),沪档,Q1—10—190。
(14) 《吴国桢给刘维炽、张伉龙的信》(1947年12月27日),《上海市政府给行政院的呈文》(1947年12月27日),沪档,Q1—10—190。
(15) 《警察局给市长的呈文》(1948年3月11日)等,沪档,Q1—10—190。
(17) 《大同、沪东寄柩所联名信》(1947年12月27日),沪档,Q1—10—190。
(18) 《为殡舍基地被自称难民侵占窃占恳请饬迁》、《为殡舍基地被自称难民侵占窃占续请饬迁》(1948年3月22日)等,沪档,Q1—10—190。
(19) 《为京江公所呈以难民占居打浦路寄柩丙舍呈复核》,沪档,Q1—10—190。
(20) 《沪东寄柩所给行政院呈文》(1947年12月11日),《大同寄柩所给行政院的呈文》(1947年12月11日),沪档,Q1—10—190。
(21) 《吴国桢给刘维炽、张伉龙的信》(1947年12月27日),《上海市政府给行政院的呈文》(1947年12月27日),沪档,Q1—10—190。
(22) 《警察局给市长的呈文》(1948年1月10日)等,沪档,Q1—10—190。
(23) 《吴国桢在潮惠山庄报告上的批示》(1948年3月),沪档,Q1—10—190。
(24) 《上海市冬令救济委员会给市政府的函》,1948年9月4日,沪档,Q1—10—190。
(25) 如锡金公所、四明公所等分别于1948年6月、7月被难民“借住”。沪档,Q1—10—190。
(26) 《碍难照准沐阳县难民请拨四明公所函》(1948年8月31日),沪档,Q106—1—193—55。
(27) 《统筹全国难民救济将成立三垦殖区》,《申报》,1948年8月16日,(二)。
(28) 《上海市冬令救济委员会文件》(1948年11月9日),沪档,Q1—10—190。
(29) 1950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在调查会馆、山庄、寄柩所等场所时发现,仍然有很多难民住在寄柩所内,有些已经居住一年以上(《上海市会馆公所山庄调查表》(1950年8月),沪档,B168—1—798)。
(30)(32) 《警察局为据潮州旅沪同乡会为斜土路潮惠山庄被流氓用强霸占一案请示》(1947年12月9日),沪档,Q1—10—190。
(31) 《郑子良给吴国桢市长的报告》(1948年1月),沪档,Q1—10—190。
(33) 《为地方流氓冒充难民代表强占殡馆乱抛棺柩请予转函社会局及警察机关勒令迁出》(1948年7月),沪档,Q1—10—190。
(34) 《延绪山庄董事长给市政府的报告》(1948年6月23日);《锡金公所董事长给市政府的报告》(1948年5月14日),沪档,Q1—10—190。
(35)(36) 《为被自称苏北难民侵占殡舍、窃占地基、会同续恳鉴核执行迁让》,沪档,Q1—10—190。
(37)(39) 《潮惠山庄苏北流亡义民第六所代表给吴国桢市长的呼吁信》(1947年12月26日),沪档,Q1—10—190。
(38)(41) 《顾义等给市政府的呈文》等,沪档,Q1—10—190。
(40) 《冬令救济积极展开》,《申报》,1947年12月20日(第一张);《血和泪交织画面——几处庀寒所巡礼》,《申报》,1948年1月22日(第四张)。
(42) 《潮惠山庄苏北流亡义民第六所代表给吴国桢市长的呼吁信》,沪档,Q1—10—190。
(43) 《吴国桢对郑子良信的批复》(1948年4月3日),沪档,Q1—10—190。
(44) 《警察局给市政府的报告》(1948年4月12日),沪档,Q1—10—190。
(45) 《郑子良给吴国桢的信》(1948年5月24日),沪档,Q1—10—190。
(46) 《宗濂、吴国桢的批示》(1948年5月26日),沪档,Q1—10—190。
(47) 《遵令制止并拆除潮惠山庄违章建筑》(1948年6月19日),沪档,Q1—10—190。
(48) 《宗濂对警察局呈文的批示》(1948年6月22日),沪档,Q1—10—190。
(49) 《为横行不法、欺骗政府、鲸吞公款、聚党称雄霸占潮惠请求惩处》(1948年8月2日),沪档,Q1—10—190。
(50) 《上海市警察局呈文》(1948年9月22日),沪档,Q1—10—190。
(51) 《为奉令严缉冒称难民代表陈光舟一案呈复》(1948年10月19日),沪档,Q1—10—190。
(52)(53) 《警察局给市政府的呈文》(1948年9月11日),《社会局给市政府的呈文》(1948年9月11日),《吴国桢给上海市参议会的复文》(1948年9月23日),沪档,Q1—10—190。
(54) 《警察局给市政府的呈文》(1947年12月9日),沪档,Q1—10—190。
(55) 《警察局复警备司令部函》,转引自《淞沪警备司令部电文》(1948年3月23日),沪档,Q1—10—190。
(56) 《社会局给市政府的呈文》(1948年4月12日),沪档,Q1—10—190。
(57) 《处置强占公所山庄难民会议记录》(1947年12月29日),沪档,Q1—10—190。
(58) 《此间乐?会馆难民不愿迁出》,《申报》,1947年12月24日(第4张)。
(59) 《为横行不法、欺骗政府、鲸吞公款、聚党称雄霸占潮惠请求惩处》,沪档,Q1—10—190。
(60) 《潮惠山庄给市政府的报告》(1948年1月16日),沪档,Q1—10—190。
(61) 吴国桢对延绪山庄、无锡同乡会、久安寄柩所等报告上的批语(沪档,Q1—10—190)。
(62) 《吴国桢对〈锡金公所报告〉的批示》(1948年5月22日),《吴国桢对〈顾义等给市政府的呈文〉的批示》(1948年4月27日)等;沪档,Q1—10—190。
(63) 《吴国桢对〈陈庆甫等给市政府的呈文〉的批示》(1948年7月1日),沪档,Q1—10—190。
(64) 《市政府秘书处给市长的报告》(1948年9月8日),沪档,Q1—10—190。
(65) 《死人赶活人,寄柩所逐客,驱散难民,警察不忍》,《新民晚报》,1947年12月30日,第4版。
(66) 参见[日]小浜正子:《近代上海的公共性与国家》,葛涛译,第110—117页、第209—278页等处。
(67) 罗义俊:《“八一三”时期上海的难民工作》,《社会科学》1982年第8期;宋钻友:《抗战时期上海会馆、同乡组织难民工作初探》,《上海党史与党建》1995年第1期;张玲:《战后苏北旅沪同乡团体的救济难民工作》,《档案与史学》2000年第5期;张宏森:《论“八一三”抗战期间上海难民救济》,《湘潮》2008年第4期;[法]安克强:《1927—1937年的上海——市政权、地方性和现代化》,第20—21页。
(68) 《潮州大亨郑子良》,http://zx.luwan.sh.cn/shlwzx/InfoDetail/?InfoID=09447f6e-5f6a-48b8-a6e1-784670398037&CategoryNum=023。而同业公会是吴国桢主政上海期间“经济上真正的依靠”,因此市政府对公会领袖更加不敢得罪(吴国桢口述,[美]裴斐、韦慕廷整理,吴修垣、马军译:《从上海市长到台湾省长——吴国桢口述回忆(1946—1953)》,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77页)。
(69) 《潮惠山庄苏北流亡义民第六所代表给吴国桢市长的呼吁信》,沪档,Q1—10—190。
(70) [法]安克强:《1927—1937年的上海——市政权、地方性和现代性》,第177页。
(71) 关于1927—1937年之间国民党上海市政府的相关研究已经比较多,主要可以参见:[法]安克强:《1927—1937年的上海——市政权、地方性和现代性》;[日]小浜正子:《近代上海的公共性与国家》;[美]魏斐德:《上海警察,1927—1937》;[美]易劳逸:《毁灭的种子:战争与革命中的国民党中国(1937—1949)》(王建朗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一书亦有部分章节涉及此一时期的上海市政府,当然该书对内战时期的国民党上海市政府亦有研究。
(72) 《为被自称苏北难民侵占殡舍、窃占地基、会同续恳鉴核执行迁让》,沪档,Q1—10—1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