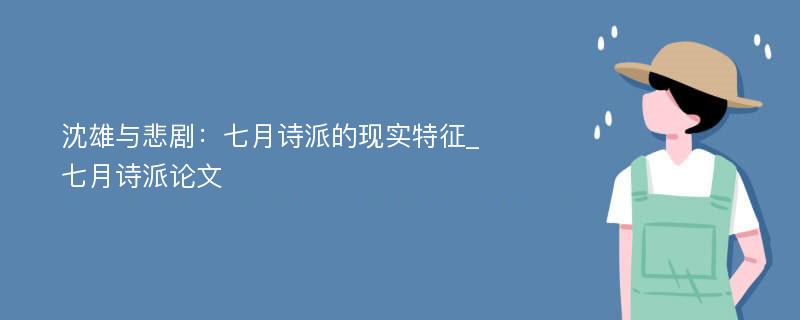
沉雄与悲壮:七月诗派现实主义特征管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实主义论文,悲壮论文,特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06)03-0233-03
经过文学研究会诗人和早期创造社诗人的努力,中国新诗沿着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条道路继续向前发展,再加上西方现代主义的引入,中国诗歌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显得非常繁荣,也使现代新诗由幼稚走向成熟。在这一过程中,现实主义无疑是其中的主要潮流之一。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一翼的“普罗”诗派是现实主义诗歌的主要代表。他们特别强调诗歌的工具作用,自觉学习苏联革命现实主义的理论和创作方法,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面貌,表现了直面现实的勇气。但由于对理想的热烈追求与向往和情感的强烈与炽热,使他们的诗歌充满了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甚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诗歌中的浪漫理想和热情已远远超过对现实的真实描写。他们大多数诗歌中所抒发的革命激情不是来自实际斗争生活,不是建立在发自内心深处或自省的基础上,显得热情有余而厚重深沉不足,缺乏一种内在的感召力,因此缺乏读者的长久支持。同时,这种图解政治式的空洞叫喊也不符合文学创作的规律,因此无法取得更大的成就。
20世纪30年代,重新扛起现实主义大旗的是中国诗歌会诗人。他们有意识地用自己的创作热情把诗与中国现实紧密地联系起来。中国诗歌会的现实主义特征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明显地表现出来:一是长篇叙事诗的大量创作;二是对民间艺术形式的有意借鉴。中国诗歌会的现实主义,是以对体裁的开拓和文学资源的发掘这两个方面来丰富发展的,这无疑是对“普罗”诗派口号化、概念化创作倾向的一种很好的改进,也是中国诗歌会诗人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贡献。
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这种对现实主义的有益探索被中断了。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战争初期那种热情和狂热消退了。人们开始对民族、对文学、对自身进行深刻的反省。这一时期,中国诗坛上出现了两座并峙的高峰,一个是由“九叶”诗派所代表的现代主义诗歌流派,另一个是由七月诗派所代表的现实主义诗歌流派。它们都是在继承和发展此前所有诗歌创作经验的基础上所产生的。七月诗派中的“大多数都是在艾青的影响下生长起来的”①。艾青的诗歌贴近现实和时代,形象生动丰满;注重意象的营造;在形式上大都采用自由体,但着意追求一种内在的节奏美和旋律美。七月诗派的诗人对艾青诗歌某一方面或几个方面的特征加以继承和发展,形成了各自独特的风格。作为一个诗歌流派,七月诗派有很多一致的地方:一是对现实的关注以及强烈的使命感。传统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情怀在七月诗人这里得到了充分的继承和发扬。二是强烈的战斗欲求和主体间意识,这是七月诗派最富有特色的地方。他们努力把诗和人联系起来,把新诗所体现的美学上的斗争和人的社会职责、战斗任务联系起来,强调诗人对现实生活的拥抱和搏击。三是艺术上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但不排斥对其他艺术手法的借鉴。四是沉雄和悲壮的情感表现。七月诗人不屑于表现那种低影徘徊、迷惘失落的情感,而是自觉地把自我和民族联系起来,把个人的情感寄托在民族的命运上,因此诗人的情感也相应地悲壮和沉雄。七月诗派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艺术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可以说是中国新诗现实主义的集大成者,它不仅继承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还借鉴了其他艺术方法,因而是一种丰富复杂的现实主义。我们通过对绿原、阿陇、鲁黎、曾卓这几位代表诗人独特的现实主义特征的分析,从而探讨现实主义在诗歌领域的多元发展趋向和巨大的包容性。
绿原:反讽型现实主义
绿原曾经是一个虔诚的诗的信徒。他梦想着“我要做一个流浪的少年/带着镀金的苹果/一只银发的蜡烛/和一只从埃及国飞来的红鹤/旅行童话/去向糖果城的公主求婚”②,但是,诗人的理想破灭后,诗风也从此变得悲愤和沉郁。但诗人并没有将这种悲愤和沉郁变成空洞的叫喊,避免了将自己真诚高尚的情感流于浅薄;而是用一种冷静克制的态度,对现实生活、人生百态加以艺术的提炼,起到一种很好的反讽效果。如他的《给天真的乐观主义者》、《伽利略在真理面前》、《重读圣经》等诗,在展示生活某一种层面时,追求讽刺与暴露的“刺”的意味,使读者感到它的力。有时,诗人还运用夸张甚至漫画的方法来调动读者的注意力和想象力去辨识和揭露社会病态。绿原的诗不像一般意义上的现实主义作品那样注重具体细节的真实、环境描写等,但诗人仍是在真诚地拥抱生活、关注生活。
绿原的诗中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让人难以界定的现象呢?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是诗人技巧的运用,即反讽手法的运用。诗人故意把生活中一些庄重严肃、悲惨的事戏谑化,使读者在看似荒诞、玩世的背后,体会到诗人深沉的感情。诗人面对那样一种现实,如果只是空喊一些口号或者是刻板的说教,顶多只会一时地煽动一些人的情绪,而不会给我们带来这么强烈的冲击力和震撼力。其二,是诗人“对于客观现实的把握力、拥抱力和突击力”,是诗人对“现实生活的深入和献身”,是诗人洞察现实底蕴的思考力给我们带来的“力”的感染。这也正是绿原的独特之处,是他对现实主义的拓展和创新。
阿陇:主体型现实主义
七月诗派表现出自觉的历史使命感和深广的忧患意识,显示了一种历史的自觉意识。在艺术的探索上,他们打破了传统现实主义的既定模式寻找自己的艺术思维模式、艺术技巧和艺术风格,建构起自己的诗歌艺术世界。作为七月诗派的一员,阿陇的诗歌并没有脱离七月诗派一贯的或者说是最基本的创作特征,即“表现现实生活”。但阿陇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并没有仅仅局限于一般意义上表现生活的现实主义,而是更深刻地拓展了现实主义的一般表现特征。他成功地开创了一种“主体型的现实主义”,张扬了一种个性,显示了他的与众不同。
追求诗的主观与客观、理性与感情的统一,提倡高扬主体的现实主义,是七月诗派一致的倾向。但是,阿陇的诗歌更加鲜明地体现了胡风所说的主观战斗精神,即强调诗人的主体性,把诗人的整个生活实践和创作过程视为“对血肉现实人生的搏斗过程”。这个搏斗过程是主观和客观相克相生的统一过程,经过搏斗主观和客观都得到提升和发展。这往往表现为主体和所描写对象的纠缠胶着状态,要求主体有足够的力量去把握现实,克服阻碍。通过阅读阿陇的诗,我们可以感受到诗人痛苦而崇高的精神面貌。诗人在诗中给我们描绘了战争,战争中的人民,深夜站岗的战士,疲惫却伟大不屈的纤夫,沦陷的孤岛,等等。时代的风云、现实的黑暗在他的笔下得到了充分而细致的描述,这是诗人现实主义性的表层表现。在阿陇诗中更为重要的是深刻细致地表现了诗人在那样一种艰苦的生活环境中的感受。如《再生的日子》,生动地叙述了自己作为一个战士的战场经历。作者亲身经历了战争的残酷,亲眼目睹了真正的流血牺牲,鲜血和战火的洗礼使诗人真正走向成熟,获得“重生”。阿陇诗中写道:“十月二十三日/我再生的日子……从母亲/从天,地间的大的爱/从母亲体现的大的爱我第一次诞生了/沐着血,吐出第一声悍厉的男孩子的啼声。……从敌人/从生、死间的大的战斗/从一团风暴那样猛烈的/灾蝗那样厚密的/那日本法西斯主义底火和铁/我/第二次诞生了/沐着血,我和世界再见/我是一个浑身上下红尽了的人!”这两个“沐着血”显然有着不同的含义。前者是每一个人出生时的必然现象,而后者不仅仅是自然层面,而是诗人亲身走进战场,经历了生与死的搏斗和流血牺牲后情感的升华。这是诗人成长的历程,也是一次伟大的“重生”。但是,成长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它往往需要付出痛苦的代价。诗人以战斗作为他生活的内容和最高目标。诗中写道:“我指着旭日底暴烈的赤光发过誓了/我指着维纳斯底晶莹的眼睛发过誓了……要为大家到人们底废墟堆中寻觅燃烧的火种。”但英雄老去的无奈和壮志难酬的悲愤使他痛苦,诗人只能悲怆地感叹:“我没有时间,我就要老了啊。”无法摆脱身后的阴影是诗人痛苦的另一个原因,诗人这样描述这种阴影:“革命是无可出卖的/胜利是无可出卖的……但是,犹大是立在十二大门徒之中/偎依在上帝底袍袖底阴影里/寄生在人之子底战斗呼吸里。”不被理解的烦恼困扰着诗人,使诗人充满了痛苦和愤怒,但是诗人并没有被痛苦和愤怒所淹没,而是充分发挥主体的意志力和冲击力去搏击现实。这正是阿陇的独特之处:从忠于现实到搏斗现实再到超越现实的“主体型现实主义”。这也从另一个角度拓宽了现实主义的发展道路。
鲁黎:浪漫型现实主义
七月诗派不仅强调主体性和个性主义,理想主义也是七月诗派的重要特征之一。七月诗人大都是有着浓厚的浪漫气质与理想色彩的诗人。他们在泥泞与荆棘的道路上跋涉向前,他们从艰苦的战斗中升华出对生活的热爱、对理想的追求。因此,他们写诗不拘泥于外表的写实手法,而常常带着浪漫的笔法,跃动在诗中的是火一样的战斗欲望与热情。他们大多是站在无产阶级革命的立场上,运用革命的世界观、美学观来认识现实、反映现实,思考和展望历史前景。曾经在解放区生活斗争过的诗人创作更富浪漫气息。气势磅礴的革命现实和远大的政治理想,激发了诗人们心中的激情和自豪感,他们便用瑰丽、夸张的形象来描写革命和革命者,怀着乐观主义的情绪来展望革命的未来,从而使他们的诗篇抹上了浓重的革命浪漫主义色彩。
鲁黎创作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他非常重视对自然景物的刻画描写。他对大自然中的山水草木、日月星辰、雪花、白云、蜜蜂等有着深深的眷恋。七月诗人大都长于自然景物的描写,但是他们对景物的描写主要是为了寄托诗人心中已有的理性思考,因此是有目的地选择适合表现自己思想的景物。鲁黎对自然景物描写的思维过程和其他诗人恰恰相反,他是由景物的触发而引起哲理的思考。如果仅仅从表面上去理解鲁黎的诗作,很多人会认为鲁黎只是在简单地描写自然景物,远离了时代,远离了生活,更与七月诗派一贯坚持的现实主义有一定距离。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诗人的诗作大多写于在根据地生活时期,与国统区和沦陷区相比,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诗人的心情是轻快的。因此鲁黎的诗中有一种恬静、向上、光明的氛围,而没有绿原和阿陇诗中的压抑和挣扎、愤懑和反抗。他在诗中抒发了对解放区新生活的真切感受,把一个光明美好的新世界带进我们的现代诗坛。
理想与追求既是七月诗人的人生图景,又构成了他们诗歌的重要内涵。鲁黎作为其中的一员,这种理想的浪漫主义更加明显。不仅如此,他更把从现实生活中升华出来的希望化做春天的小草,他把诗献给母亲,献给失去的家乡,献给胜利与希望。他的许多诗篇佳句都是在对理想的歌唱中生出光辉的。鲁黎诗作中,作为“非现实”一面的“理想”成分的加重,使他的诗歌不可避免地具有了浓郁的浪漫色彩。
曾卓:象征型现实主义
象征主义在20世纪初传入中国,它与中国传统的比兴手法有相通之处。周作人在《扬鞭集》序里说:“象征是诗的最新的创作方法,但也是最旧,在中国也古已有之。”他提出“象征即兴”的说法。因此,中国作家在运用象征手法时,并不像刻意借鉴短篇小说的写作技巧那样去有意学习,而是一种不自觉的运用。正是因为不自觉,才显得更加浑然天成。在曾卓的诗中,这种不自觉的运用尤其明显。例如“它的弯曲的身体/留下风的形状/它似乎即将倾跌进深谷里/却又像要展翅高翔……”,这可以说是受难而不屈的一代知识分子的象征。他们被不可知的命运吹到“平原的尽头/临近深谷的悬岩上”,但是,他们没有绝望,没有埋怨,只是“孤独的站在那里/显得寂寞而又倔强”。整首诗都是在描述一棵树,没有一句诗是直接抒发感情或对现实人事的描写,但是我们从中却可以感受到一代知识分子的人格力量和追求。《呵,有一只鹰……》通过诗人对自由飞翔的鹰的赞美,我们可以体会到诗人对自由生活的向往和对自在生存状态的追求。在《铁栏与火》中,诗人通过对铁栏中像一团火一样的虎的描写,赞美了一种原始的力和一股难以压制的生命冲动。这几首诗都是通过对某一事物的描述来寄托作者的某种理想,或象征一种生存状态。这种象征手法和中国传统的托物言志手法有一定的相通之处,但两者却又有着本质的区别。托物言志是一种由“物”到“志”的思维方式和写作方式,而象征则是“物志”同一的思维方式和写作方法。因此,仅从表面看,曾卓的诗只是对某一具体事物的描述,是一些简单的咏物诗。这种认识只是一种浅层次的认识,而没有看到表面现象掩盖下的更本质的东西。只有在这些景物中看出诗人的“志”来,才算是真正地理解了这些诗。曾卓的诗已经超出一般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反映论,而带有一种象征色彩,形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象征型现实主义”。
在20世纪最初的20年内,从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写实主义、自然主义、象征主义、唯美主义、未来主义、表现主义、意识流文学,到存在主义先驱者的思想,几乎同时都传入了中国。这些思潮在西方的出现曾经历了300年左右的时间,是历时的,而到了中国,却几乎同时出现,成为共时的。这当然引发了很多问题,但是也有一些有利之处,这就是便于选择和比较,取自己之所需而形成不同的组合,有助于形成多种多样的文学流派,造成异彩纷呈的局面。具体到诗歌领域,最能体现现实主义成就的就是七月诗派。由于不同诗人的个人气质、审美趣味、理想追求的差异,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现实主义类型,如绿原的“反讽型现实主义”、阿陇的“主体型现实主义”、鲁黎的“浪漫型现实主义”、曾卓的“象征型现实主义”。他们以自己的创作从不同侧面展现了七月诗派的现实主义特征,同时也延伸、拓宽了现实主义的内涵。当然,上述诗人的创作都不是仅局限于某一种表现方法,而是多种手法的综合运用,在综合中又显示出其作为独特个体的独特风格。实际上,无论是主体意识的强调、浪漫色彩,还是象征手法的运用,在几乎所有七月诗派诗人创作中都有所表现,只是某一种手法在某些诗人的诗作中表现得更明显。
注释:
①绿原:《白色花·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②本文所引诗歌全部出自绿原:《白色花》,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