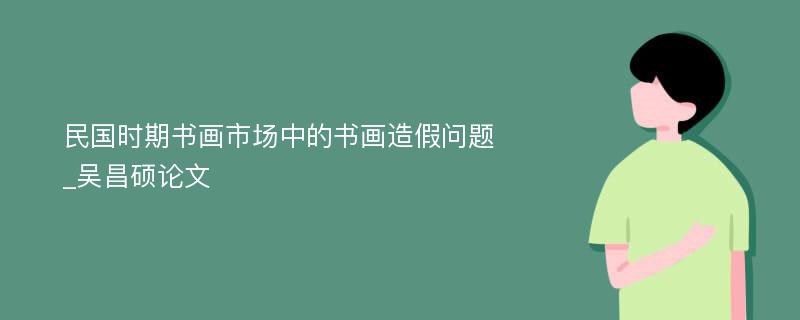
民国书画市场中的代笔与作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国论文,书画论文,市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书画市场在中国起步很早,大致可追溯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当时的书画材料发生了影响中国艺术史发展的重大变革,质量轻、面积小且便于收藏和携带的纸张日渐普及,为书画作品步入市场创造了物质基础。记载书画交易的史料不断被发现。如《魏书·崔玄伯》中记载:“始(崔)玄伯父潜为兄浑诔手笔草本,延昌初,著作佐郎王遵业买书于市而遇得之。计诔至今,将二百载,宝其书迹,深藏秘之。”又如《晋书·王羲之传》中记载:“(羲之)又尝在戢山,见一老姥持六角竹扇卖之。羲之书其扇,各为五字。姥初有愠色,因谓姥曰:‘但言是王右军书,以求百钱邪。’姥如其言,人竟买之。”再如朱和羹所著《临池心解》中所写:“买王得羊,不失所望,宋、齐间人语也……时重大令(王献之)书,而羊敬元(羊欣)为大令门人,妙有大令法。”从这些史料我们可以看出,书画交易在这一时期不仅已经开始出现,还获得了深厚的群众基础,具有一定的规模。然而自宋代以来,在中国书画界占据主流的文人士大夫的书画创作绝大部分是不带功利性质的。高居翰这样描述当时书画家的创作模式:
至少在有教养的中国人中间,存在着一种坚决的主张,认为在所有体面的事务范围内,必须区分开业余兴趣和职业化行为,并且绝对地偏好前者。隐藏在这一“业余理想”背后的论点是,业余爱好者经过修养的心性,会不期然地或根据儒家的正确原则做出超出专门技能之上的决定,同时又能免受物质利益低级动机的干预。即便职业化技巧和专长可能已带来实际的益处,这种态度仍然盛行。①
从这一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在高居翰眼里,文人画创作模式最显著的特点,无疑就是区别于职业化的业余化,他进一步补充说:
业余艺术创作地位的提高也是多个世纪的绘画精英运动较晚的一个步骤,它要将绘画变成上流社会一种正当的文化追求,而不只是手艺人的技艺而已。这些画家的地位不仅使他们免于依靠绘画谋生,而且还树立起强有力的社会约束,不让他们这样做。那么赞扬画家不计物质利益地作画,以及他们因此而享受到相对的艺术独立性,这本身就是很自然的一步,有着一定的正确性。②
由此可见,高居翰对于文人画的业余创作模式对艺术独立性的保持作用,是持赞许态度的。在这种理念的控制下,书画家们不会因为生活的压迫和物欲的诱惑而创作,因此能够更加纯粹地表达自己对于艺术的追求,这也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然而历史是不会停止前进的,当文人士大夫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级在清末民初之际逐步衰落,传统书画艺术的道德保护伞迅速消失,使得书画艺术被毫无保留地暴露在了市场面前。书画作品的物质属性被无限制地放大,而相应的本来居于主要地位的精神属性却变得渐渐不再为人所重,这种突如其来的变化在为书画家们创造了生存空间的同时,也造成了众多负面影响。
伴随着购买需求的不断膨胀,书画市场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书画家们普遍订单山积,工作压力剧增。如吴昌硕在上海成名之后,求画者摩肩接踵,按照每天画三幅的速度计算要画整整三个月才能将去年的画债了却,这种劳动强度对于古稀之人来说无疑是几近残酷了③。李瑞清的境遇则更为可悲,他在夜半临死之前还坚持于晚饭后“手书八联”,把人生最后的气力都花在了应付订单上④。而对于正当年的书画名家来说,像唐驼这样在六年内写对联三万余副,合平均每天十余副,或者一次义卖活动就要卖一万副对联的惊人工作量⑤,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了。只有像余绍宋这样“一日书百张”⑥,或者像张大千这样一个月之内完成包括山水、花鸟、人物等各个画种在内的一百幅展览用画作⑦,才可以用“迅笔”称之。另一方面,供不应求的市场现状又为投机者所利用,使得他们可以轻易地找到试图绕开传统交易方式而寻求“捷径”的买家,从而达到自己经济上的目的。在这种局面下,代笔问题和作伪问题在书画市场的蔓延,自然是不可遏制的了。
一、代笔问题
代笔,指的是在书画家本人认可的情况下,由他人代书画家本人创作的行为。在民国前期,由于大量订单的积压,许多书画家的工作任务已经达到难以承受的地步,这时他们往往会寻求同行或弟子的帮助,来共同“生产”作品以满足市场的需要。另一方面,由于购买者对于创作者缺乏了解,或者出于猎奇的心理,有时他们会提出一些击中书画家“软肋”,使书画家颇为为难、不好应付的要求,诸如请擅长花鸟画的画家画山水,又或是让不通文墨的画家在画作上题长诗之类。当面对这种尴尬的要求时,书画家为了自己的生计以及面子考虑,往往不会拒绝,而是硬着头皮照单全收,这时,求对买主要求真正有所擅长的朋友帮忙,就成了书画家必然的选择。由此可知,正是书画市场的繁荣促成了代笔现象的普遍流行,使其成为民国时期在书画大家间流行的一种特殊创作方式。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有一种代笔是极为特殊的——那就是在书画家因为重病或已经逝世等不可抗拒的原因作用下所无奈采用的代笔。如“王胜之太史逝世,所有已收润资而未着笔之书画,由吴湖帆、冯超然二人或书或画以酬求者”⑧;另如“沈寐叟以书法名海内,鬻书订有润例,各笺扇铺代为收件,及寐叟逝世,已收润资而未交件者,积案累累,均由其门生故旧,一一摹写,以了笔债”⑨。这种代笔行为则并非出于书画家本意,完全是不得已而为之,可视为别品。
按照代笔内容的不同,代笔的形式也多种多样。有些书画家不善诗文长题,辄请他人捉刀。比如著名的“王画吴题”现象,就是王一亭请好友吴昌硕代作长题之意。吴昌硕逝世后,王一亭曾请其弟子王个簃代为作题⑩。再如陶冷月卖画,“题诗大都出于其表叔王佩诤之手”(11)。又如张大千在上海时,其画作的长题均由他的邻居、著名书画家谢稚柳之兄谢玉岑代笔(12)。赵子云作画多借其师吴昌硕曾用的原句,偶有颇见新意的妙句,却多是胡石予代题(13)。除此之外,另一种全幅代笔的方式则更为普遍,即是画作或书作全部由他人代劳,而书画家则只需要在作品完成后署上自己的名款即可。如周钟岳为南京总统府题写府额,一时书名甚噪,求书者颇多,周就请潘伯鹰为其代笔(14)。齐白石曾自谓:“余自四十以后不喜画人物,或有酬应,必使儿辈为之。”(15)钱名山应人之请书写联副,常叫其子钱小山代笔(16)。而“袁观澜因求书者多,常请白蕉代笔”(17)。吴昌硕的金石篆刻,“七十后由徐星洲代刻,八十后,由钱瘦铁、王个簃代刻”(18);而他的花卉代笔人中,甚至有像倪墨耕这样的当时画坛名家(19)。王一亭是吴昌硕的人物画代笔人,“有时日本人欲购买吴昌硕的人物画,吴昌硕画得不好,王一亭就为他代笔”(20);而王一亭的画作,有时也会请高尚之代笔(21)。此类现象中,使用代笔最为频繁的恐怕要算赵叔孺了。据其徒陈巨来坦言,赵一生所刻印章真出其手的不过两千余枚,其余则全部都是徒弟代笔为之,且印风不加统一,甚至是到了“面目都非”犹不加阻止的地步(22)。
职业书画家尚且不以捉刀为意,那些以各种各样的原因偶有挥毫甚至鬻艺需要的名流们则更是普遍使用自己的私人幕僚、秘书代笔了,如“田桐代孙中山,饶汉祥代黎元洪,庞国钧代陈夔龙,曾履川代孔祥熙,冯若飞代张群,任中敏代胡汉民,张斯德代林森,曾仲鸣代汪精卫,易大厂代唐绍仪,陈景钊代叶恭绰,樊光与赵鹤琴代王正廷等”(23)。
事实上,这种代笔行为,简言之就是在书画家“允许”范围内的作伪。郑逸梅曾称自己因不堪求索,不得已而请胡亚光、陈祖范、袁淡如、高锌等人代笔,并自嘲曰“作伪心劳日拙”(24)。可见代笔活动的性质,书画家们是切实了解的。奇怪的是,无论是需要代笔的书画家们还是提供代笔的书画家们对于代笔并没有表现出丝毫避讳之意,我们看刘荣芳润例:
刘荣芳润例 入室弟子刘荣芳,生长纽约,冠游平津,足迹所及,十余万里。比年发陈箧书,冀读万卷,见闻日富,才调益高。早岁毕业于师范,复从老画师傅菩禅游,更不自满,及余门习美术,性既聪敏,所学乃益孟晋,年来余以教务羁身,友好中央作书画金石刻竹者,辄代捉刀,几可乱真,或有誉为出蓝者,余亦自愧。迩因奉母家居,思有以承欢菽水,爰代订润例,以告爱好艺术者。建国二十五年夏岭南陈丽峰叙。(25)
从润例文中可知,陈丽峰对代笔一事丝毫不加掩饰,并且代笔的“几可乱真”竟然成为了陈丽峰用来肯定自己弟子艺术造诣,在为之代订的润例中明确宣传。究其根源,这一现象可能是因为代笔活动最初是在古代文人的书画合作或诗文游戏中发展出来的。当时的文人常常模仿友人的笔法或风格创作书画作品,以供同好猜测玩赏,因此代笔行为多少带有优雅的文人游戏性质。而作为创作的一方,对于这种在今天看来多少不合道德规范的行为是乐于接受的,这种行为还可以在帮助他们完成任务的同时彰显自己的文人士大夫遗风。是故像倪墨耕、王一亭这样在书画界名声显赫的人物,也会时常为他人提供代笔服务。
然而在商业交易中,欺骗毕竟是欺骗,因此在购买者的身上,我们看到了截然不同的反应。如赵叔孺常叫学生陈巨来代为应酬作品,其中不乏来自周湘云、谭延闿、姚虞琴等名流的订单。一次不巧被姚虞琴发现,按理说,姚虞琴也是书画家,对于在书画家中流行代笔的风气自然也应了如指掌,但当他自己转变为购求者时,却表现出了对于代笔行为的不理解,认为代笔的作品是在欺骗他,赵叔孺不应该用代笔的作品来搪塞他,姚虞琴并由此产生对赵叔孺的“大肆不满”。而最为有意思的是,对此赵叔孺认为这是因为代笔的人做得太好,不像他自己那般草率,才“致被识破”(26)。
这种发生在文人阶层内部多少带有矛盾色彩的行为,正是民国时期书画市场处于旧的文人时代和新的商业时代交接点的最佳例证之一。
二、作伪问题
对于任何民族任何时代的书画艺术之进步发展而言,书画作伪活动所产生的负面影响都是最为直接的。它打击消费者的购买欲望,掠夺创作者的市场份额,严重破坏书画市场的正常运行,并使得由书画市场发展带来的物质财富无法实现其推动书画艺术前进的作用;它让艺术家作品的价格混乱,价值衡量标准失去正常的参考尺度,使人们丧失对于艺术品优劣的判断把握能力,也在某种程度上让艺术鉴赏变成一件颇为复杂而麻烦的事务。当然,这一现象的出现与蔓延,和书画市场的产生和日渐繁荣也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书画造假,说明书画市场繁荣,假货有市场有销路”(27)。可以说,正是在市场浪潮中书画作品物质与商品属性的无限膨胀为作伪者提供了最重要的动机,这也是市场给书画艺术发展所带来的最为恶劣的负面影响因素之一。
差不多在中国书画市场诞生的同时,书画作伪活动就已经悄然而至。南梁书法家虞龢所著《论书表》记载,当时“新渝惠倏雅所爱重,悬金招买,不计贵贱。而轻薄之徒,锐意摹学,以茅屋漏汁染变纸色,加以劳辱,使类久书,真伪相糅,莫之能别”(28)。可见早在南北朝时期,伪造书画作品牟利已有一定的发展基础。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古代的书画作伪活动多数都是仿造更加古老的书画作品,很少有模仿当下“今人”作品的。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是在重古轻今的惯性思维影响下,当时的书画爱好者普遍认为古人的作品在艺术造诣上胜今人一筹,伪造古人的作品能够带来更多的利益;其二是书画创作者大都是拥有准统治阶级身份的文人,随时都有可能拥有极大的权力,因此伪造他们的作品要承担一定的风险,而古代作品的作者早已去世,自然也不会追究伪造者责任了。
然而到了民国前期,今人书画市场的繁荣和文人阶级社会地位的没落使得作伪者的两大顾虑完全被打破,加之各种中介活动颇为兴盛,在这种局面下,作伪活动便在书画市场空前繁荣了起来。据姚茫父回忆,当时“书画伪品,多出维扬,金石伪品,多出青齐”(29)。其实,只要有书画市场的地方就一定同时有“伪作”市场,这些公开销售的“伪作”虽然艺术质量往往不高,但却颇具规模。在北京,著名的“伪作”市场自然要数琉璃厂棚铺区。孙殿起在《琉璃厂小志》中这样描述道:
其字画悬满壁间,琳琅满目,古色古香,美不胜观;由师大校迤南,而抵十字路口,字画悬遍。并有临时苇棚,中间挂满古今名人字画书帖,文人墨客,考古专家,往返盘桓,若不胜其看;惟珍贵者殊鲜,其行货则投机者居多数耳。(30)
自然,所谓“投机者”的“行货”,指的就是水平一般的赝品了。无独有偶,另一大书画市场所在地上海也有类似的低档“伪作”市场,《上海鳞爪》一书对其也有详细介绍:
福州路西头三山会馆墙上,每到夜间,常有卖书画者挂满了堂幅轴对,有书有画,有今人作品,也有古人遗笔,五光十色,使人目迷。且售价很便宜,虚头又很多。若辈不在日间做交易,必到黄昏时候才来开张,这是什么缘故呢?据说他们的书画都是冒牌赝品,如在青天白日不容易销脱,故必至夜色迷蒙下才出来做交易。(31)
尽管场面颇具规模,这些低档仿品由于制作粗陋,且艺术水平较差,甚至需要夜色掩护才能脱手销出,可见其对于真正优秀的书画作品来说是不具有什么威胁性的。而真正善于作伪的人,也不会像这样公开在大街上销售伪品,他们大多是和掮客或笺扇店合作,来达到牟利的目的。如无锡荣氏之梅苑落成后,苑主荣德生斥五十两白银巨资托上海笺扇店请康有为书“香雪海”三个大字,制成匾额后悬挂于大厅廊檐之上。直到后来碰巧康有为来游园,这才认出匾文是伪作,于是提笔重写三字,并题诗曰:“名园不愧称香雪,劣字如何冒老夫。为谢主人濡笔墨,聊将题句证真吾。”(32)可以想见,如果康有为不来游园,则伪作之事可能就无从发现了。虽然在这位著名民族资本家的交往圈中,不乏颇具艺术修养的朋友,能看出伪作的应不在少数,但除了康有为本人,恐怕不会有其他人会直接指出这块重金请来的牌匾的问题,这正是借中介暗中销售伪作与公开销售伪作相比的“高明”之处。
当然,最为高超的作伪行为还是那些有职业画家参与的,合制作、宣传、销售为一体的“集团作伪者”,其中比较著名的要数杭州的碧峰居士了。此人名叫陆碧峰,作为一个职业画家,他曾以个人名义刊登润例售画,同时“办一书画社,为客代求当代名家书画,自诩任何不易求得的书画家作品,该社均能辗转请托,如愿以偿。实则该社雇得平素默默无闻的书画和篆刻作手,摹仿伪造,借此骗取润资罢了”(33)。许多著名的书画家都曾因被此人的制作团队仿冒而蒙受损失,这其中就有著名浙籍书画家余绍宋,他曾在自己的日记中两次提到碧峰居士仿造其作品之事:
此间有姓陆名碧峰者,屡赝余画欺人牟利。今日有朱瓒者来,持其友赵昌书求画扇者,书中言春间曾由陆碧峰求到一幅,且已用玻璃板印出。余何由识此人!?所画颇似余笔,此人殊可恨……王鲲徙来谈,杭人陆碧峰又冒余名伪作牟利,昨得朱璜转来赵昌信,知之。当托鲲徙一查究竟。余犹未死,而赝作已出,且公然以玻璃板印行。又不欲登报声明,以自增身份。亦闷人也。(34)
由余绍宋的日记,我们可以零星看到碧峰居士团队作伪手段之高超。作为书画家,余绍宋鉴赏书画的眼光是颇为严格的,其甚至曾对齐白石、林琴南的作品表示过极端的不屑(35)。这些伪造者的书画造诣,可以让这样一位眼光颇高的书画家在盛怒之下仍然不得不承认“所画颇似余笔”,毫无疑问应该是一流的,而他们在宣传上也不惜工本,采用当时先进的玻璃板印刷出画集以辅助销售,无疑也是极具“魄力”的。更为可笑的是在陆碧峰本人的润例中云:
痴云馆书画润格 钱塘陆子碧峰,为杨古韫葆光、刘语石炳照两先生高足,其外祖许迈孙先生以收藏称,筑花圃曰榆园,喜勘订书籍,精赅无比,所识知名之士甚多,一时谈艺者咸集其庐,碧峰耳濡目染,渊源有自,故其平日自娱,诗文之外,尤工书画,长于临摹,逸才孤旨,复异时流。比年以来,薄游南北,治生之资,取给翰墨,天假艺鸣,旨归义取,爰为重订,藉于限制……注意:碧峰书画本属平庸,近今南五省伪冒太多,自民国二十年元旦日起,属画件力摹宋元及四王作品,加盖秘印,一洗平日作品习气,以杜伪冒。(36)
在润例中,当事人还特意额外加了一条“注意”,对外宣称说因为假冒伪作太多,所以竟要用改变作品风格和加盖秘印的方法来告知大众如何区别真伪作品,仿佛自己也是书画伪作的受害者,以“贼喊捉贼”的办法将自己的作伪行为开脱得干干净净,真可以说是用心良苦了。
除了像碧峰居士这样的职业画家,一些书画家身边的人也参与到作伪的行列中。《死虎余腥录》曾记载有好事者冒充“中国道教会”向自号“清道人”的李瑞清诈骗捐款一事。其实李本人并非道士,只不过是在清亡之后,仿苦瓜和尚之意,借取道号表达退世之意而已,好事者的诈骗纯属不通风雅之举。此事的原委,乃是来源于李瑞清弟子,张大千亡弟张君绶秘藏的一封李瑞清回复“中国道教会”的秘信,而这封秘信,竟是由李瑞清的管家誊抄后将副本寄出,而将原本“调包”出来后高价售给张君绶的(37)。由此可见当时伪造风潮之盛。更为夸张的是,连书画界大名鼎鼎的书画名家,也会为了一些蝇头小利而进行伪造时人书画的活动。吴待秋曾向陈巨来述说过一件导致自己与冯超然反目成仇的旧事,他说:
我初至上海时,尝出外交同行联络,与冯氏同时至上海一书画家集会处曰“题襟馆”。冯氏有一次代求我一四尺立幅,墨笔也。某日李平书请我吃饭,见自己墨笔一画变了着浅绛山水了,我着色画照例须加二成,遂至题襟馆找冯氏,要他补这二成款。冯大窘,不认账,于是我与他大相骂了。幸吴缶翁、哈少甫、姚虞琴等三人力劝始止……(38)
在这件事中,显然冯超然是为了独吞着色所加的二成润笔而私自伪造了吴待秋墨笔成品中的色彩,这样发生在著名书画家身上的伪作事件着实让人汗颜。民国时期在书画市场中流行的作伪现象已经发展到何种地步,从这里也可窥见一斑。
单从整体上看,导致书画作品伪作横行的原因的确是市场化的发展带来的趋利倾向,但如果从细致的角度追究,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还可以被分为几个层面,其中最为重要的莫过于法律保护的缺失。由于艺术创作本身的抽象性,使得法律很难找到可以直观考察、并能让民众都了解的真伪参考标准,因此在面对这类案件时法律也往往是敷衍了事,草草结案。比如一则钱化佛作品遭人伪造的旧事:
当时南京路有一家笺扇庄,公然出售化佛的伪画,被化佛所发觉,化佛探囊斥资,把伪画买下,并请该庄出一发票,他拿了回去,把伪画和发票提给法院,向法院控诉,及开庭审判,法官认为书画作伪,自昔有之,既成习惯,无从惩罚……(39)
无独有偶,抗战前夕,徐悲鸿最为人所熟知的奔马题材也遭遇到了被伪造的命运:
抗战前有人发现一些署有“悲鸿”之名作的“奔马”、“八骏”和花鸟作品在出售,此事被查明是任仲年所为,于是徐悲鸿夫人蒋碧薇向法院提出诉讼,但法官宣告任仲年无罪,原因不外是“悲鸿”之名谁都可用,“奔马”等题材更人人可画。(40)
从这两则材料的当事人来看,徐悲鸿在书画界享有盛名,而钱化佛更是辛亥革命的元老,与国民政府高层来往密切,社会影响力都不可谓不高,然而在书画作伪案的判决中,即便有“发票”这样的铁证,法律都难以还他们公道。钱化佛案中法官将作伪称为业界“习惯”自然是推脱之辞,而徐悲鸿案中的判决方才道出其中的部分真相——毕竟要证明伪“悲鸿”就是伪造真“悲鸿”,而不是另一个名叫“悲鸿”的人所署是十分困难的事。在这种局面下,法律对于作伪行为失于惩罚力,无意间还成为了作伪者的保护伞,使得他们的行为更加肆无忌惮。而在诉讼无用的情况下,民间只好自己动手来打击造假行为。如钱化佛就干脆在开画展时“把这伪画加着说明,和自己的画,一同悬挂展出”(41),以宣传辨伪知识。而受碧峰居士侵害的书画家们,则在著名出版人陆丹林的帮助下用更加巧妙的办法还击了作伪者:
他故意开一书画家名单,其中有健在的,也有已逝世的,假说受南洋华侨所托,按这份名单,每人作一直幅,并附尺寸,寄给该社,询问能否办到。那位居士认为这是一注大宗收入,完全包办下来。丹林得此回信,在报上登一文章,带着讥讽说:“某社不惜人力物力,为爱好书画者服务,不仅能求当代名家的缣幅,并在天之灵,在地之魄,亦得通其声气,以应所求,为旷古所未有,敬告海内大雅,如此良机,幸弗坐失……”不久,该社也就自动停业。(42)
尽管最终效果不错,但打击伪作居然要利用民间智慧,还是不能不让人觉得寒心,何况并不是所有的书画家都能有像陆丹林这样的智慧,他们就只能在无奈中任由作伪者侵害了。
尽管是作伪现象的直接受害者,但另一方面,导致伪作横行局面产生的另一层面的原因却正是来自于书画家集团本身。
毫无疑问,绝大多数书画家是痛恨作伪的,他们也想了许多办法来千方百计阻止作伪者得手,在印章上多作文章便是常用的办法。如吴待秋在遭遇冯超然“加色”后,对于自己的设色山水作品极为注意,但凡是他亲笔创作的着色山水,都要在一角押一方“苏林仲子”印,以示与一般墨笔的区别,防止有人再用墨笔上水“加色”赚取差价(43)。然而,在一部分书画家争相提高保密技术的同时,另一些画家则面对伪品表现出“无限的”宽容,这着实令人费解。如吴昌硕,曾当着外人之面将掮客带来的、将“安吉吴昌硕”误写作“安杏吴昌硕”的低级仿品故意认成真迹,还以年老误题为由帮助掮客解释(44)。而齐白石对待赝品的态度,则更加令人称奇。他曾记曰:“弟言厂肆有吾伪作,能有趣。今日随吾同往,吾当购之。”(45)书画家本人竟然要去购买伪造自己的“有趣伪品”,这也的确堪称奇闻了。更为有趣的还要算张大千。他一方面极力试图提高保密技术,“每隔五年,必将所用之印章全部换过,防学生们伪造”(46),另一方面又曾亲自帮助素昧平生的售假者,将伪称合作的假画改成真品。这种自相矛盾的行为究竟原因何在呢?笔者认为原因可能有两点:一是伪作多靠各类中介帮助销售,而书画家也要借助中介的力量销售自己的作品,因此不便与之彻底决裂;另一点则来自于书画家们对于作伪行为认识程度的不足。在张大千这个“作伪大师”的眼里,像为掮客补几笔这样的帮助是对自己的经济效益构不成什么影响的,而真正要防的是学生们的高精度作伪;而在齐白石的眼里,只要画得有趣,无论是谁画的似乎都具有相同的艺术价值,如果伪作画家的作品拥有了能够令他满意的艺术情趣,那么即便署了他的名字也不会对他在艺坛的声望造成什么不良影响。
事实上,任何水平、任何形式的伪作,都会混淆书画家艺术价值的标准,这其中是没有什么区别可言的,而在书画家集团内部对于作伪现象都没有统一、严肃的认识的时候,伪品的流行就更加畅通无阻了。
代笔现象对于书画艺术发展的影响绝不仅仅是造成一时的商业欺骗那么简单,其真正负面效果来自于对书画家探索新领域、弥补自身不足起到的阻碍作用。在代笔盛行的状况下,书画家既已形成依赖习惯,因而再也不愿去寻求对自己“弱项”的新的改进,这对于形式相对抽象、对综合的艺术理解力要求颇高的中国书画来说,其负面作用是非常巨大的。除此之外,代笔现象与模仿的盛行(书画家本身繁重的工作压力)又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一方面,已成名的书画家对于代笔的需求使得他们默认了弟子对自己风格的模仿——即便他们自己也清楚这种模仿是不可能获得大成就的——因而导致模仿之风更加盛行;另一方面,在原作者这种默认甚至鼓励态度的保护下,在平时就已获得代笔资格的一些书画家相对于其他模仿者更有可能转变为作伪者,比如前文提到疑有伪作行为的赵子云,便是吴昌硕常用的代笔人,无论是吴不擅长的山水(47),还是擅长的花卉(48),赵子云都曾参与捉刀,而这种情况一旦出现,对于书画艺术发展的影响就更大了。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对于书画艺术的发展而言,“无论他写的成败,作品总是要反映他的性格、学养和经历的,并间接反映时代风尚与地域影响”(49)。作伪者本身也是其作伪行为的牺牲品,尤其是其中像碧峰居士这样的高手。这些人的艺术造诣,本来或许可以在艺术史上留名,但由于对利益的狂热追求却使自己的才能在无限地对他人的模仿中被磨灭。郑逸梅的老师胡石予擅长画梅,外间多有仿品,一日友人携一卷来访,胡发觉后在画卷上题诗曰:“我画梅花四十春,冷摊发现已频频。不知雅俗难淆乱,婢学夫人惜此人。”(50)诗中最后“惜此人”之句,正是对伪作者艺术人生遭自己亲手断送的惋惜,而这种损失,与伪作带来的直接损失同样巨大,但往往却容易被人忽视。
注释:
①②高居翰:《画家生涯——传统中国画家的生活与工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6页,第6页。
③单国霖:《海派绘画的商业化特征》,《海派绘画研究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01年版,第570页。
④(11)(23)郑逸梅:《艺林散叶续编》,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9页,第149页,第85页。
⑤斯舜威:《百年画坛钩沉》,东方出版中心2008年版,第80页。
⑥陈永怡:《近代书画市场与风格迁变·以上海为中心(1843-1948)》,光明日报出版社2007年版,第159页。
⑦谢家孝:《张大千的世界》,台北徵信新闻报出版社1968年版,第75页。
⑧(13)(18)(29)(47)郑逸梅:《艺林散叶》,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47页,第322页,第51页,第130页,第34页。
⑨⑩(14)(16)(17)(21)(24)郑逸梅:《书坛旧闻》,浙江美术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74页,第54页,第4页,第4页,第21页,第54页,第9页。
(12)(22)(26)(38)(43)(44)(46)陈巨来:《安持人物琐忆》,上海书画出版社2011年版,第34页,第25页,第25页,第52页,第52页,第9页,第35页。
(15)(45)《齐白石文集》,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238页,第316页。
(19)王中秀:《王一亭年谱长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版,第139页。
(20)萧芬琪:《王一亭》,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16页。
(25)(36)王中秀、茅子良、陈辉:《近现代金石书画家润例》,上海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第309页,第273页。
(27)李福顺:《一个造假成风的时代》,见吴明娣主编《艺术市场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12页。
(28)张彦远:《法书要录》卷二,人民美术出版社1984年版,第37页。
(30)孙殿起:《琉璃厂小志》,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60页。
(31)郁慕侠:《上海鳞爪》,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111页。
(32)陈声聪:《兼于阁杂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8页。
(33)(39)(41)(42)郑逸梅:《清末民初文坛轶事》,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85页,第325页,第325页,第185页。
(34)(35)《余绍宋书画论丛》,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267页,第227页。
(37)曹芥初:《死虎余腥录》,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84页。
(40)石三友:《金陵野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03页。
(48)吴晶:《百年一缶翁:吴昌硕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56页。
(49)《熊秉明美术随笔》,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82页。
(50)郑逸梅:《文苑花絮》,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6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