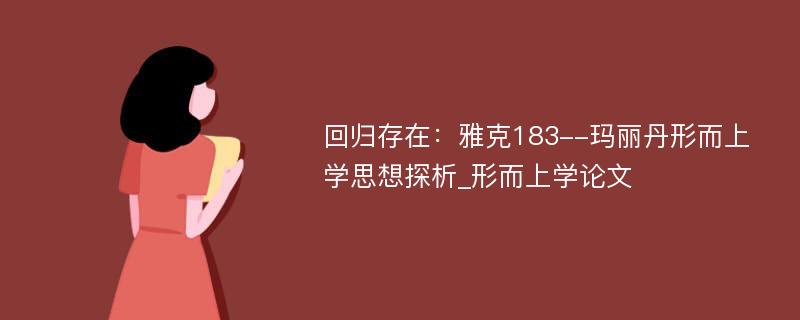
重返存有——雅克#183;马里旦形而上学思想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里论文,形而上学论文,探析论文,雅克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法国新经院哲学家雅克·马里旦(Jacques Maritain,1882-1973)对哲学的最大贡献在于,他运用托马斯·阿奎那神哲学的基本原则,综合其他思想家对托马斯思想的传统诠释,并融合其本人对现实的哲学思考,构建出一个面向当代问题、适应当代思想发展的新经院主义理论体系。
马里旦所处的时代,传统经院哲学的存在论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在马里旦看来,哲学家急于逃避甚至摈弃传统的存在论,以“人本”代替“神本”、将人与上帝对立、以“思想”作为哲学或形而上学的出发点,这些问题所带来的后果是,在实践领域中表现为人的“无根”的存在——精神无助、颓废与堕落;在思想领域则表现为各式各样的非理性主义、虚无主义、无神论、主观主义等思潮。因此马里旦认为,新经院哲学思想家首先要面对的重要问题是人们对“存有”(being; esse)的遗忘和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抛弃,其任务与使命是重返“being(esse)”、找寻人失去的“存在”之根。
一、缘起:“人的形象”丢失在“文明的黄昏”
马里旦认为,从思想因素来看,十九世纪初期,伴随着大卫·休谟的经验主义对因果原理价值的否定、孔狄亚克的感觉主义与康德对理性的批判,形而上学的根基发生了动摇,西方思想陷入困境,西方文明进入“黄昏”时分。与此相伴,中世纪基督教所宣称的“人是上帝的肖像(image of God)”的传统意义在科学主义与实证主义狂风暴雨的冲击下消失殆尽,人之神圣性随之迷失在其“无根的存在”之中。为此,马里旦展开对现代精神的批判,他的矛头首先指向路德、笛卡尔和卢梭。
在马里旦看来,路德“缺乏的乃是理智的力量”,即把握共相、认识本质、接触实在的能力,并且路德在经院哲学上学艺不精,只学会了一些错误的想法、模糊的神学概念和华而不实的论辩技巧。无论是对当时天主教的苦修补赎之路,还是对其自身内在的精神状态,路德都充满怀疑,并从根本上表现出对神恩的绝望,这种绝望后来成为宗教改革的“原动力”。由于路德不能克服自身的罪恶感和欲望,便将全部赌注都押在与其本性全然割裂的恩典的作用上,而他又从一己之体验中推而广之,将自己的命运转化为神学的真理——只要内心确定了对基督的信仰,并且确信一定能获救,你的意志就是你自己的行为规定者,而你所做的一切也无异都是善的。因此,在路德眼里,上帝只是一个盟军、合作者和强有力的伙伴而已。① 马里旦指出,路德所谓的“因信称义”的结果必然是将自我神化、使信仰摆脱理性、将基督教福音归结为内心的体验,其结果是大大激发了现代反理性主义的个人主观主义。
马里旦认为,在笛卡尔之前,已经有了长久而富有成效的有关“理性主义”的准备期——达芬奇、伽利略等人早已为数理方法的不断完善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因此,笛卡尔并非货真价实的“理性主义之父”。不仅如此,就所谓的反思哲学的角度而言,马里旦认为,古人的反思哲学要比现代人深刻得多。在马里旦看来,笛卡尔与经院学术保持了质料上的连续性(material continuity),而在形式的因而也就是决定性的层面上,他则打破了这种连续性。② 值得注意的是,笛卡尔继承中世纪客观本体论的“位格”观念,从而发现“主体意识—我思”的重要性,然而,他却是从思想层面说明人的实体性,以清晰明判的观念作为客观实在的准则,从“我思”说明人之“存有”,人由此而成为“纯意识的存有”。
马里旦指出,笛卡尔思想具有在思想与存在联系层面上的唯心论(idealism)、在理智的等级秩序与知识的意义层面上的唯理论以及在人观上的二元论等特征,其核心则是西方近代哲学科学体系赖以建立的“思维”。“我”就是一个在思维的东西、一个精神、一个理智、一个理性,“我思”与“我在”是同一的,而“直观”、“天赋观念”、“独立于事物”恰恰是笛卡尔所理解的人类知识的特征。在笛卡尔哲学中,人的认识不接受外部事物的制约,相反,外部事物的存在恰恰是思维活动的结果,人类的理智由此变成了事物的立法者。笛卡尔企图使思想独立于现存的事物而仅受制于“它自身内部的需要”,而“一个世界仅仅凭着自身,就关闭了绝对”。③ 马里旦认为,这是一种欲使人类理性的内容成为度量实在的尺度的极端企图与疯狂做法。这种新知识类型必然孕育出一个充满霸气的“自然科学时期”。马里旦将笛卡尔思想视为现代科学深层的原则与源头。
在马里旦眼里,卢梭思想则代表着“以人为中心的人道主义”思想孕育与成长的第三个关节点。卢梭将传统基督教对罪的来源的看法从宗教的层面转为人类历史的自然进程层面,从而得出结论,认为人不是生来就有罪,相反,人的原初状态(原始状态)即是善的,亦即说存在一个人性的理想状态,它处在人类历史的源头。④ 在此状态下,人处于一个“完满的”境地而根本无需任何救赎——上帝根本就是多余的。马里旦认为,卢梭的思想无异将“人类中心论”推向了巅峰。
在马里旦看来,路德、笛卡尔和卢梭三位“改革家”所肇始的哲学革命终于在康德批判的唯心主义那里达到了顶峰。康德的批判源于认识过程中所出现的“二律背反(antinomy)”,他认为,纯粹理性无法认识“物自体”,因此,他将灵魂、自由、宇宙、上帝等这些经院哲学传统实在论的概念都划入不可知的范围。人的认识能力有感官与理智两个不同的层面,感官认识是对可感物质的经验;理智则是精神性的认识能力。为了避免进入先天观念的陷阱和保持经验事物的价值,中世纪经院哲学曾继承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传统,以“抽象”作用说明感性能力与理智的关系,托马斯·阿奎那还特别强调了感性对理智之精神性的“分有”,从而使感性与理智密切为一。然而,自唯名论思想强调认识仅仅是对实在个体的直观,从而冲淡了概念的实在价值之后,抽象作用就成为一种无用的功能,理智与感性由此分道扬镳,不再“合作”。之后,休谟更加否定因果原理中理性的基础,终于促使康德对理性认识严加批判,以认清其条件与限制,这对以理性为主的“主知”的托马斯学派无异是一个极大的挑战。特别是经院哲学形而上学所研究的存有(being; esse)理论经康德批判之后,最终成为一个空无内容的先验范畴,成为经院哲学致命的创伤。马里旦认为,这场所谓的“伟大的哲学革命”并非是一个纯“理性化”的过程,而是将某些原本神圣的东西加以“世俗化”的过程,由此,传统意义上作为“上帝的肖像”的人被彻底地“祛魅”。
马里旦对“人”的哲学理解源自托马斯·阿奎那的思想。托马斯认为,人是由上帝自由地从“无”中创造出来的精神与肉体的结合,上帝是造物主,人是受造物,每一个受造物由于被造的事实而与造物主上帝之间有一种“实在的关系”。然而,上帝不可能是为了要获得什么而创造,而只能是要给予、分赐其美善——因为上帝本身即是完满,是无限的美善。至于说上帝为什么要创造目前现有的这一个特殊的世界呢?这是非人类的理智所能理解的上帝的奥秘——由于人的理智是有限的、不完全的,人类因此无法透彻明白上帝的谋略和计划。因为上帝创造人,也因为上帝要分赐其至善,于是,上帝的至善就成了所有受造物的目的。所有受造物也某种程度地相似上帝,人相似于其始源——上帝,也因此而以相似上帝为最终目的,人在这种“相似”的意义上而成为“上帝的肖像”,就此而言,人对神的渴求源于人的自然本性、自然法则。人的精神性的灵魂由上帝恩赐、与上帝息息相通,因而人分有上帝的神圣之本性,并且天生具有追求神圣的精神渴求,这即是人之存在的形而上学指向。⑤
马里旦认为,路德、笛卡尔、卢梭和康德等思想家期望从人自身得到上帝所能给予的东西,从本质上看,这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人道主义”泛滥的必然结果,它由此而将形而上学的神圣帷幕抛掷到科学主义与实证主义的阴霾天空,人的理性也因此取代了神恩,人由此而成为一种完全独立的、具有绝对自由的、可以以其主体意识为起点建立一切“无根”的存在。这种对所谓“绝对自由”追求的结果,便是人生失去目的、归于荒谬——人可以不再重视生命和尊严;人可以一切以“自己”为尺度排除所有“他者”。而“他者”物化的结果是使人成为一堆纯粹的化学元素。因此,人一旦失去了形上之根、失去了神圣的目的性,所留下的只不过是一堆“可能性”而已。
因此,现代社会文明的危机是源于“神圣的东西与世俗的东西的分裂”,亦即“人是上帝的肖像”的传统意义的瓦解。马里旦坚定地认为,折磨着现代世界的病症是本体的和形而上的,它植根于人心之中。因此,唯有医治人心,才能治好这个病症,从而建构起人类共同体共同的价值理念。⑥
二、基于“完整存在的人”的“以神为中心的人道主义”
雅克·马里旦之所以能将托马斯·阿奎那思想的基本原理与当时的欧洲思想相融合,建立起一个极具创意的“正统的”新经院哲学思想体系,与当时兴起的新经院哲学思潮不无关系。二十世纪中叶的欧洲在经过了前后两次世界大战后,人的精神与心灵遭受了严重的创伤,存在主义的兴起使欧洲思想界充分注意到“行动”、“实现”或“活动”以及事物本性的动态发展的重要性。新经院学者通过研究发现了托马斯·阿奎那形而上学的新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视其为真正的存在主义思想家,并由此展开对其形而上学“存在实现”等理论的探究,以此表达对人之存有的关注。马里旦在其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对个人、对人之存在的思索与反省促使马里旦在以托马斯·阿奎那为代表的经院哲学思想传统里寻求问题的答案。战后的法国盛行存在主义哲学,它强调个人存在的重要性,其代表人物加缪、萨特等人的哲学、文学思想深入人心,马里旦受其影响,开始了对人、人之存在作出深刻反省。此外,当时兴起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也使马里旦对工人阶级在整个社会结构中所扮演的角色、社会地位、历史使命等产生深刻的思考。马里旦积极对社会各阶级进行哲学的反思,他强调“工作”对于“完整存在的人”的重要性,因而重视工人阶级、重视工人阶级的尊严,他认为,此尊严源自人的位格,工人只是其存在的方式,为此他的思想曾被批为“左倾”。马里旦深切地体会到,一个空洞的、名义的、功利主义的、资本主义的世界,就如同一个没有经过发酵的死面饼子,缺乏生机和自身内在的生存发展之力;而要摆脱这样的窘境,就应当将哲学研究的重心放置于对人性的特别关怀上。因此,马里旦寻求从“完整存在的人”(existentialement humaine)的角度来恢复人之神圣性,以寻找对人类早已丧失了的“存有(being; esse)”的把握。
“完整存在的人”指人之整个存在或者人存在的统一性。在马里旦看来,构成人存在的统一性的共同因素是人之“位格(person)”——他由经院哲学思想传统获得启发,提出从人之动态发展来了解“位格人”(从人之行动而理解人之位格)的新主张。在传统经院哲学的概念体系当中,“位格”一词所表达的是个别人的存在,旨在强调具体存在的人的个别特性。从本体论的角度讨论人是传统经院哲学的观点,而存有则无异是“完整之人”的思想基础。
从“存有”的维度诠释“位格”是托马斯·阿奎那关于人的哲学理解的重要内容。托马斯·阿奎那认为,“存在(existence)”是“存有(being; esse)”之完美“实现(act)”,其中,位格与“实现”有密切的关系。上帝的存在即是其实现,人是类比上帝的存在,人只能在上帝中才能完全实现。在此,托马斯强调位格的个别性。⑦ 灵魂与身体分别是实体存在的条件,但实际存在的,是由二者结合而成的组合体。其中,灵魂赋予身体生命并影响身体的活动。由于灵魂本身是实现(the act),使得与其结合的身体成为具体实在的位格之人。⑧ 因此,在托马斯看来,实体最基本的意义就是存在的“个体”,个别实体的意义即指个别存在的人;而实体个别化的方式,就是个人的存在方式,因此,不能将位格转化为其他存在者,它具有其独一无二的特性。⑨ 位格之尊由此得以体现。
经院哲学时代是本体论的时代,是从亚里士多德的形质论(Hylomorphism)⑩ 说明位格之个别性的时代,然而,当时围绕“位格”主题展开的讨论也是相当混乱的。文艺复兴以后,伴随着实验科学的发展以及十九世纪末心理分析学家对人的意识的研究,新托马斯主义者开始注意人的内在生活,主张从“关系”的角度说明位格人的个别性,从心理结构说明人的“行动”,以便发现此行动主体的存在方式。至此,“位格”概念逐渐由传统经院哲学意义上的“个别实体”而成为“意识主体”。
位格之人因其质料而成为主体、藉其理性而能反思其经验与活动,具有内在的、能透过反思而认识“我”与“他者”。在此,“自我”指位格的主体性,由其活动而发现世界。从自我意识的角度讲,“位格”指一个能知觉、能判断、能感受、能知自己活动的“主体”。“主体”借其活动而与世界接触并主动地说明、理解、诠释世界,赋予世界某种意义,并在其中作出选择;同时,世界也因主体之活动而进入主体的意识中,就此而言,主体不但是“在己之存有(being in itself)”,也是“为己之存有(being for itself)”。中世纪经院哲学只是诠释了位格是以理性为本性的个别实体,马里旦则在此基础上强调从内在生活来看位格,即强调位格的“个别意识主体”的意义。
马里旦指出,研究理性与身体如何统一的问题是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马里旦认为笛卡尔所遭遇的就是在此问题上的困境。在马里旦看来,笛卡尔继承了中世纪客观本体论的“位格”观念,发现“主体意识—我思”的重要性,这原本值得肯定;然而,他的错识在于以清晰与明判的观念作为客观实在的标准——从“我思”说明人之存有,由此,人便成为“纯意识”产生的“存有”。虽然,笛卡尔竭尽全力说明人心物之合一,然而,由于他同时强调只有在思辨与科学的领域,心物才化分为二,而在一般的经验中都是二者为一,因此,他的“我思”是极具封闭性的。而从笛卡尔至康德,意识主体渐渐成为一个“封闭的”先验思辨形式和实践原则。马里旦认为,如果主体性仅仅是内在而不是向外呈现、如果主体只指我直接把握的“我的反思”,那么,“我”能经验的只不过是“我的主体性”、“我”所感觉到的世界也只不过是一个脱离自然的世界,而呈现于这个“内心世界”的其他主体则必定成为由自我构成的“我的延续”。(11) 如此极端封闭的自我观念自然会带来以自我为中心的极端个人主义和忽视个人尊严的集权主义。
马里旦强调,位格是一个包含多关系在内的中心。在他看来,位格是有形器的精神体,因此而成为与宇宙、物质世界和其他位格发生关系的枢纽。马里旦称这一关系中心为“在世之存有”(being-in-the-world)。传统经院哲学强调“活动跟随存有”(Act follows being),指的就是活动的本质跟随存有的本质而定。身体是位格呈现自己的“场域”,而世界则是一切能呈现的现象所属的场域。人的“主体意识”与“世界”的媒介是人的身体。马里旦认为,位格所显示的活动可归于两类:认知与决定。从认知方面而言,创造力源自“理解”,“理解”即是把握已知而推论未知——将一切已知的事实置于一个完整的背景中,据此预测一切可能有的事实和可能呈现的现象。在此,由已知而未知,人的认知能力的超越性质得以显现。值得注意的是,传统经院哲学主要是在神人关系的“光照”中探究人的一切,而马里旦是在此基础上从提升人的角度探讨人的问题与人神关系问题,并从人之行动而理解人的位格,使传统思想有了创新的形式。
据此,在位格人反观“已完成”的事件与“待完成”之理想的过程中,人的理性以“追求真理”为终极目的,人的行动则以“善”的实现为理想。而善的完全实行依赖于一个完全公平、合乎正义的社会。即使人在现实世界中找不到或难以建立这样的社会,人对此境界的向往,却也能使现实的行为具有意义。马里旦认为,“人类的政治和社会事业应当追求的最高理想,就是创立一个博爱的国度,这不是意味着希望有朝一日一切人都将得到尘世的完善,彼此相爱如同手足,而是意味着希望人类生活的生存状态和文明结构都更接近完善,完善的标准是正义与友爱……一种真正民主的正义与友爱。”(12) 只有当由终极目的“回望”一个人的“行动”时,才能在此“行动”与终极目的的关系中发现此“行动”的意义与价值。因此,“完整存在的人”的人生历程本质上表现为一种自我超越的轨迹。在此,马里旦将人的神圣性、崇高性指向人生活的世俗结构,以构建世俗生活圣洁化的秩序,这样的一种理论构建蕴含着他对“完整存在的人”的深刻思考。
从“完整存在的人”出发的理论是一种“以神为中心的人道主义”,它基于马里旦对“人的真实形象”的重新发现,它着眼于人的崇高与弱点的方方面面,着眼于上帝栖居其间的、已遭伤害的人类存在的整体性,主张“使理性因超理性而充满生气,并使人开放,让神降临自身。……促发福音的酵母与灵感渗入世俗生活的结构,使现世的秩序神圣化”。在马里旦看来,只有在托马斯·阿奎那的哲学中,才能找寻到这样一种“完整的人道主义”,因为“只有在托马斯·阿奎那的基督教哲学中,才有着心灵的完善,也才有着恢复了其自然的卓越状态的心灵之完善”。(13) 马里旦认为,这种力量足够强大和纯洁,能够有效地影响整个世界,能够使人心恢复秩序并从而凭着上帝的恩典,把世界带回到真理之路上来,而迷失了真理之路,则可能导致世界的解体。
马里旦从“完整存在的人”的角度来构建人道主义,反映出其重构社会精神的宏伟理想,然而这并不能代表他有回归中世纪的愿望。虽然马里旦认为若无上帝的恩典,社会的复兴就只是一场空想,可是他并不期待、也不希望完全返回到中世纪基督教世界的概念中去。因为,现实在变,文化也在变,人道主义的内涵也因之发生变化。从“完整存在的人”的角度来构建以“神”为中心的人道主义的最终目的是重返存有。
三、重返存有
“being(esse)”具有不可界定的特征,它是一个自明的观念。托马斯·阿奎那指出,“being(esse)”的意义来自动词“是(est)”,其本身的意义并非指一个事物的存在,而是首先表示被感知的现实性的绝对状态,因为“是”的纯粹意义是“在行动”,因此才表现出动词形态。“是”动词所表示的现实性是任何形式的共同现实性,不管它们是本质的还是偶然的。“being”的本意是指活动本身,它赋予事物现实性而并非指某一个或一类事物。“being”自身不等于一个事物的存在,它是“纯粹活动”和“现实性”,因此,上帝即是存有自身(Being)。在经院哲学家看来,“being”是一个“自明”的观念,其本身不具有任何限定的本质,而是超越或内含诸种限定的本质。同时,“being”也具有不可界定性,意思是说“being”是一个最为普遍的观念——桌子是“being”、马是“being”、人是“being”、自由是“being”、想象也是“being”;如果神存在的话,也不能不是“Being”。因此,相较于上帝作为存有(Being)的至善(perfection),从类比的角度看,一切经验对象作为万有(beings)的完善性是极小的,然而,这样的一个“极小点”却足以使万有(beings)脱离虚无而进入到现实的世界。
从经院哲学家与新经院哲学的角度讲,“being(esse)”所指出的,是万有(beings)的共同点与共通之处,它是从一切个别的、差异的、分化的事物中抽离出来的最高级和最单纯的抽象,而世间所有的一切限定也莫不与“being(esse)”具有内在的从属关联,即无一物能在“being(esse)”之外存在。由于“being(esse)”是最原初的、最根本的、最不可或缺的、最普遍的生成或实现万物的原理,所以,托马斯主义学派将“being(esse)”视为形而上学的出发点和探讨的根本对象,并且强调“being(esse)”是一个具有“类比(Analogy)”性的理念,从而由形而上学的层面揭示出“有”与“万有”的关联:一方面,万有是类比上帝的存有,而“Being(上帝之存有)”是生成或实现万有(beings)的本根,内在一切又超越一切;另一方面,“上帝之存有(Being)”包罗、融通万有(beings),然而却不抹杀各自作为“类比的存有”而具有的个别性。亦即说,对万有(beings)来讲,“Being”是内在的、不可或缺的、最根本的成分。在此类比性的共同性上,万有在形而上学意义上的会通与共融得以实现。它意味着万物不是彼此无关,无限的“Being”与有限的“being”、精神与物质、天道地道人道融通的形上渠道由此打开。由经院哲学这样一个“完整”的形而上学体系出发,超越的上帝、世俗的人类与物质世界得以找到合适的定位,并且实现其相互关系的合理、持中与圆融的安排。
马里旦关于“存有(being; esse)”的基本理论来源是托马斯·阿奎那的形而上学思想。托马斯认为,哲学是以理性探讨“存有(being)”最基本、最彻底的原因,因此,他的形而上学是以“being”为中心、以“本质(essence)”和“存在(existence)”的关系学说为枢纽的实在论。阿奎那认为,形而上学或存在论所探讨的特殊的固有对象即是“being(to on,esse)自身”,或者称之为“being之所以为being(esse in quantum esse,being as being in jeneral)”。阿奎那在论证“being自身”时,强调“实在”意义上的“being”重于逻辑意义上的“being”。“being”包括“本质(essence)”与“存在(existence)”;“本质(essence)”与“存在(existence)”皆为“beings”。而“存在(existence)”先于“本质(essence)”,“存在(existence)”是“being”之最具体的、个别的、实体的、独一无二的完美“实现(act)”。
在马里旦看来,脱离“存有(being; esse)”即表示人最基本、最重要的形上部分已被切除,而没有形上价值的人与一堆原子毫无区别——如果人已死,知识便失去了理性的载体。同时,由于失去了“being”,人的知识与行动也失去了其理性基础——上帝已死即意味着人的生活失去了信仰。而人类一旦没有了理性与宗教,宇宙的神圣性也将不复存在,相应地,伦理道德因此会失去内在原则——而一旦失去了自然道德律(Natural Law)作为根据,人法(Human Law)也只能沦为“文字游戏”。马里旦得出结论:离开形而上学层次,人不能从根本上实现自己。因此,马里旦强调,从本体论的角度使人之思想回归“being(esse)”,从而重新建构起理性之基础,并从形而上学的层面理解万有(beings)所构成的关系性的整体存在。
“being(esse)”的意义是马里旦建构其“新人道主义”的哲学基础,它的基本思想与托马斯·阿奎那的形而上学思想具有密切关系。而马里旦在其基础上所做的进一步探究,无非是想证明两个相辅相成的问题:一方面,强调上帝“存在”的确定性;另一方面,揭示“作为上帝之肖像”的人原本是作为“类比的存在者”而富有超越性与神圣性,却因为人自己切断了与“上帝”相连的纽带而成为“无根的存在”。
从托马斯“存有的实现(act of being)”思想出发,马里旦认为,黑格尔的理论忽略了“being”的内涵,只注意到其外延,因而忽略了“being”的超越性,“being”也就由此而成为外延最广、不含种差的最高的“类”概念。物之本质差别由其种差而定;种差是“形式”,是“being”所以实现、所以存在的原因。最高的“类”是除去所有“种差”的类。那么,理智所掌握的是没有存在的“being”,这与“无”便没有什么差别了。对于康德的理论,马里旦认为,康德的“being”是脱离存在的先验形式——思想与存在的桥梁一旦断裂,“being”便不再是实在的“being”了。在马里旦看来,克尔凯郭尔的存在主义是一种生存的生存主义(existential existentialism),其本质是宗教性的冲动和要求,是一种信仰之苦痛,是主体性向上帝发出的哭号,其不幸在于:在一种哲学外衣之下发展成为宗教性的抗议。在此,生存者内部的虚无,被生存者本身的虚所取代。而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则是从“无”的痛苦经验中执著于“有”的神秘,马里旦认为,如此学院式的生存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混淆了哲学的智慧态度与宗教的祈求态度,如果将之作为一种真正关于存在(因而是关于生存)的哲学,则是失败的。
马里旦强调,形而上学所研究的不是个别的“being(esse)”,正是从反思经验材料中的模糊“being”来把握其本身,这才是实在的“being”。如果只闻“being”之“声”而不见其“实”,不足以成为形而上学家。形而上学家的理智应具备认识“being(esse)”的习性,而照耀形而上学家的理智之光就是“直观(immediate apprehension)”。所谓“直观”即是理智的“明见(une perception intelllectuelle)”,是不需要任何媒介而与对象直接融合。在此,理智藉此掌握事物的存在,而在主客融合之际,感觉直观的对象以新的形态呈现于理智,这就是“心语(le verbe mental)”,马里旦认为“心语”即是真正的直观,因为它由人的理智直接把握,是单纯的“明见”——它是“无法证明的透视”和“心中灵智之火”,它能在刹那之间照亮心中的寂静。
“直观”意义上的理智的抽象包括三步(以“白莲”为例):第一步,我看到一朵白莲,我对之有知觉,即我知道有某朵白莲呈现于我;第二步,由于我对此朵白莲的知觉,我肯定世上有白莲(白莲精神性的存在);第三步,在理智肯定白莲存在的那一刹那,我体会到我思想中精神化的白莲乃是实实在在地存在于思想之外。在此,理智直观白莲的存在,而这种直观又显然是“抽象”的直观,马里旦称其为“形式抽象(abstractio formalis)”,表示对象的来源并非先天观念或先天形式,而是使实际事物存在的“being”。从“形式抽象”的观点来看,理智首先理解可感“being”如何呈现其可感性,然后理解其“being之为being”及其结构,最后是理解“being”本身。
“beings(ens)”因其为“being(esse)”而成为可理解的对象,而事物的“存在(existence)”即是“act of being”。万有因“其being的实现”才成为具有此本质的实体并成为理智理解的对象。本质虽是可以理解,但是由于本质只是可能的“being(esse)”,其being如果不能实现(act)则没有意义。对于实际存在的万有(beings)本质的理解,可由抽象作用说明。然而,对于上帝的存有即“Being”本身的理解则有困难。这是因为,第一,“Being”本身不可概念化,因为“Being”本身不能是抽象的对象。抽象指“分开”或“脱离”,与“Being”本身分开或脱离即是“无”,而“无”是无法理解的。第二,人的理智不能直观万有(beings)的本质,也无法直观事物的存在(existence)。事物的存在是由感官直观其所呈现的性质,可是,感官并非理解的官能,因此,经院哲学主张,对事物的存在,理智的理解方式是肯定(14),马里旦将此“肯定”称为“抽象直观”。
从根本上讲,马里旦的抽象直观是理智与感觉同时“见”到存在于事物中的存有(being)。为了使这两种“见”合二为一,马里旦认为,必须承认有一种人的理性活动欲发而未发之际的精神性的“前意识(preconscious)”。马里旦主张,位格人行动的根源是意识或“心灵”,不过,“心灵”强调的是意识中的理性因素。马里旦对“意识”的探讨旨在了解位格人的行动以及超越性。因为,在马里旦看来,意识是人最实在、最基本的经验,是人对其内在“经历(the lived experience)”的理会。
马里旦不认为以非理性的因素可以说明人的行为,因为人的行为源自位格的自由选择,他将这种“位格之自由选择”之意义上的“无意识”称之为“前意识”,它指的是人的理性活动欲发未发之际的情况,因此是精神性的状态。马里旦遵循亚里士多德和经院哲学的观点,主张理智与意志活动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而概念的形成,是主动理性(intellectus agens)的“光照(Illumination)”,以及被动理性(intellectus possibilis)的理解与表达相结合。其中,主动理性在未光照前,心灵充满图像及某些源自感官的“前意识(preconscious)”意义上的“自然的知识(natural knowledge)”——这是一块“半透明(translucid)”且肥沃的园地,其中已含有理性的种子。(15) 在此,马里旦强调“前意识”是人的意识在理智活动之前的活动,是在“黑夜(night)”中未成形却仍然充满“最原始生命(primal preconscious life)”的意识,这是人精神性活动及人创造灵感的根源。
从根本上讲,马里旦的“存有直观(或者说直观存有)”是一种“形而上的心态(un habiuts métaphysique)”,它介于神学上讲的启示(revelation)与默观(vision,或称神见)之间。马里旦认为,只有有此体验的人,才称得上是形而上学家。而根据马里旦有关“直观存有”的理论,我们可以发现,比起托马斯·阿奎那,马里旦也许更喜欢使用基督宗教“神秘灵修(mystical spirituality)”的语词来描述其抽象直观的意义,因而强调理智是在其活动静止时才能领会“being”的意义。在此,抽象直观即是思辨理智的默观,而默观的对象是内容丰富的“being”及其实现(act of being)。如此一来,关于“being”之学便成为人的理智所能及的最高智慧。
结语
按照马里旦的主张,事物的本质与主体必须加以区分。事物的本质可以在思想中客观化,而主体却不能客观化。每一个主体都是一个个体的实在(位格人)。人对主体的认识是通过将其作为人的思维客体而获得,因此,不是把主体作为主体来认识,而是将其作为客体来认知。人一旦将自身视为一切认识客体当中的主体、自视为世界的中心,就难免导致个人生存的“主观性”与“客观性”的二律背反:如果你执著于主观性的观点,你就把万物吞噬到自身里面,让一切都为你的独一无二性而牺牲,你就因此被钉死在绝对的自私和狂妄之上了;如果你执著于客观性的观点,那么你就被吞噬到万物里面……而你的所谓的独一无二性也就成为虚假。马里旦认为,只有“上帝”才能解决这个二律背反——如果上帝存在,那么就不是我,而是他才是中心。在此,这个中心不是同某一特定的观察点(例如在某个观察点上看来,每个被造的主体性者是其所知宇宙的中心的那么一个观察点)相关联,而绝对是一个超越的主体性,而一切主体性都要以之作为参照。马里旦认为,只有在这个时候,人才在懂得自己毫无重要性的同时,又懂得其命运具有最高的重要性。
“自我中心”与“整体宇宙中心”常常交织而成就人的两重形象,而作为主体的形象和作为客体的形象,既不可能协调重合,又不可能被抛弃掉。马里旦认为,只有“上帝存在(God exists)”才能解决这个矛盾,而无神论生存主义的悲剧在于:被他人作为一个“客体”来认识永远是被不公正地认识——与自身割裂并受到伤害。只有当被上帝所认识时,人才是作为“主体”被认识。在马里旦看来,上帝要认识“我”,根本无需将“我”客体化,所以,只有在上帝面前,人才是作为主体、而非作为客体被认识;也只有对于上帝,自我才完全敞开。马里旦“完整存在的人”视域中的生存主义不是把自我视为无理性的“感觉之流”、“无用的激情”(16),而是把自我视为有理性的灵魂——它在自我最幽深的隐秘之处,在它最充分的实现之中,为上帝所了解,在它本质的性质方面,又为人的理智所认识。
马里旦在充分强调神恩的同时,也充分肯定人自身的价值,这是其从“完整存在的人”的角度探究“存在”的基本思想特征。在他看来,人始终是“类比”上帝的存有(being; esse),对人的信仰只有建立在超验的信仰之上才会达到完满和永恒,亦即说,对人的信仰要以对上帝的信仰为基础,这是实现其“完整人道主义(以神为中心的人道主义)”的前提条件。马里旦认为,信仰上帝的目的在于建立慰藉人生的理智秩序和社会秩序,从而使人类能够平安地拥有地球,彼此和谐。遗憾的是,近代以来,人们一直在努力挣脱上帝的“牵绊”,继而又不得不在“无根”的生存境域中寻求“人”的地位。世俗化的过程正是“以人为中心的人道主义”成长的过程,它将现代人对上帝的宗教情感渐渐转变成为对人的信仰、对物的崇拜。而历史的流变和残酷的现实又无情地击碎了这种信仰和崇拜,因此,现代人会时常感到一种“无根”的疼痛。
马里旦以适应现代思想需要的原则,以批判现实、批判“以人为中心的人道主义”为前提,在激活传统托马斯主义思想的同时构建起新托马斯主义的形上理论,强调以神为中心,使神道与人道互补而非互相排斥的“完整存在的人”意义上的“新人道主义”,在西方基督宗教文化圈产生了深刻影响(17)。作为“回归基督教”过程中新托马斯主义“与现实对话”、“批判现实世界”等思想运动的重要代表,马里旦主张重返“being(esse)”、主张二元论的统一、主张在神圣与世俗间寻求人之“存在”的内在性与超越性的统一,这是其存在理论的重要内涵。然而,如此的“统一”又何尝不是一种“悖论”式的统一?正如马里旦自己所指出的,引导基督徒去实行基督救赎工作的推动力,深藏于对世界的一种悖论式的理解之中:一方面,基督徒相信自然界是上帝创造并宣布为善的;另一方面,就世界自身陷于肉体贪欲、感官贪婪和精神傲慢而言,它又是基督及其门徒的敌人。因此,生存于这个世界之中的基督徒似乎并不属于这个世界——对这个世界来说,基督徒将永远是陌生人,永远是不可理解的人。这种悖论的张力所引发的后果值得深思。无论如何,马里旦对于现代条件下托马斯主义及天主教神哲学的继往开来起到了先锋与推动作用,其形而上学思想寓意深刻,影响深远。
注释:
① Jacques Maritain,Three Reformers,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955,pp.4-5.
② Jacques Maritain,The Dream of Descartes,New York:Philosophical Library,Inc.,1944,pp.144,146.
③ Jacques Maritain,The Dream of Descartes,pp.168-169,171.
④ 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63-64页。
⑤ Saint Thomas Aquinas,Summa Contra Gentiles,Book One,London:University of Nore Dame Press,1975,p.171.
⑥ Jacques Maritain,The Range of Reason,New York:Charles Scribner' s Sons,1952,p.185.
⑦ St.Thomas Aquinas,Summa Theologica,New York:Benziger Bros.,1948,p.714.
⑧ 邬昆如、高凌霞:《士林哲学》,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6年,第389-390页。
⑨ St.Thomas Aquinas,Summa Theologica,p.718.
⑩ 英文“Hylemorphism”由希腊文Hylē(资料)和morphē(形式)二字所组成。此学说源于亚里士多德,后经经院哲学发展。“形质论”认为,构成自然整体的一切物体均由质料与形式两种本质部分所组成。元素、化合物、植物、动物、人物常被视为这样的自然整体。按照亚里士多德的形质论,实体的个别性源自质料,而普遍性则源自构成人本质的型式。人的本质定义是“理性动物”,因此理性是人位格尊严之所在。理性包括理智与意志;人的一切非理性的部分则是人性中的混浊之气。
(11) Gary Brent Madison,The Phenomenology of Maurice Merleau-Ponty,Ohio:Ohio University Press,1981,p.35.
(12) Jacques Maritain,The Range of Reason,p.198.
(13) Jacques Maritain,The Range of Reason,pp.194,782.
(14) Etienne Gilson,The Christian Philosophy of St.Thomas Aquinas,New York:Random House,1956,p.41.
(15) Jacques Maritain,Challenges and Renewal,New York: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1976,p.57.
(16) 参见萨特的自我描述。
(17) 马里旦以托马斯的思想为基础,针对当时的社会现实建构其自然道德律理论和有关人权思想的原则。由于他对人权思想的贡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邀请他共同拟定《基本人权宣言》的草案,1948年通过后由联合国公布。
标签:形而上学论文; 经院哲学论文; 笛卡尔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文化论文; 上帝已死论文; 传统观念论文; 问题意识论文; 哲学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