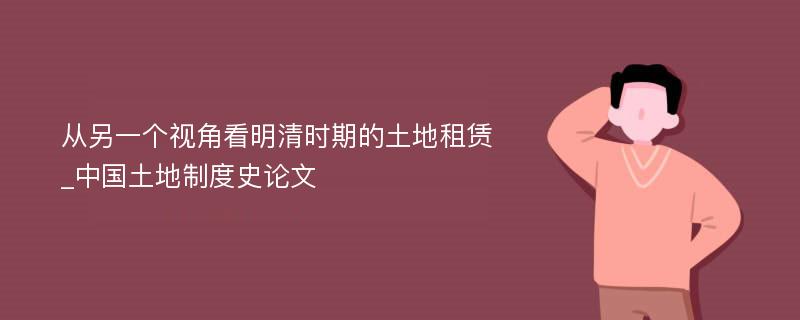
从另一个角度看明清时期的土地租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明清论文,角度看论文,时期论文,土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研究中国历史上的农业生产及社会经济制度,多年来一直有一个主流说法——封建地主经济论。此说直接导出下列几项重要结论:
(一)地主经济制是自然经济。经典著作认定封建经济是自然经济,中国的地主经济既然是封建经济,当然就是自然经济。
(二)中国历史上两千多年来都允许私有财产存在,但是土地产权之转移与土地使用权之让度都不是生产要素市场上的交易行为。地主是兼并之家,土地产权可以流动,但永远是单方向流动,向兼并之家的手中集中,产权转移的方式是巧取豪夺,绝不能算是市场上的交易买卖。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是阶级剥削的手段,更不能算是市场交易。所以,土地作为生产要素之一,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市场。
(三)中国历史上的地主经济有主导性和统治力,整个社会经济就是由此定性。今天的英、美、德、法都有土地租佃制度存在,农村中都有地主与佃农,地主被称为(landlord),意义十分明显,但这些国家的社会经济不被列为地主经济制,就是因为地主们没有主导力及统治力。在中国学术界中,为了坐实地主经济有主导力及统治力,便有人扬言地主们占有全国80%的耕地。
以上这种主流说法,近年来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主流派学者不得不重新检讨此项理论,并作了若干重要修正。
李文治先生首先放弃了封建地主制经济是自然经济的结论。他在一篇论文中计算了明清时代农民经济的商品率,发现商品率相当高,于是他说:“这时以地主制经济为核心的封建社会本质虽未发生变化,但是否仍可沿用自然经济这一术语进行概括,值得进一步讨论”(注:李文治:《论明清时代农民经济商品率》,《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1期。)。这以后又有许多学者由明清上溯,直到秦汉,发现农村的商品率始终居高不下,于是决定将“自然经济”的定义修正为“自给而不必自足”。我们可以说,根据这个新定义,今天英、美、德、法的小农户都是处于自然经济状况中,他们尽量“自给”,但是未能“自足”。
其次,大家对于土地产权与使用权之转移是什么性质,在看法上也有些修正。傅衣凌教授在1980年研究福建土地契约时,发现有“银主”与“钱主”的名词出现,因而承认耕地在市场上的交易(注:傅衣凌:《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编》,厦门,1989年,第246~248页。)。江太新写了一篇论文,专门研讨传统市场的土地流向(注:江太新:《传统市场与土地流向》,《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2期。江太新承认有土地市场交易,但是认为这种交易并未能使土地资源的配置优化,这是因为他不了解经济学上所谓(Parieto optimal)的含义。)。最近更有人指出:“国内学者对地产长期变动趋势缺乏足够认识,主要是对地权变化的动态分析不足,往往简单认为,在土地兼并的推动下,自耕农大量破产,土地分配趋于集中,社会两极分化。”(注:马克垚主编:《中西封建社会比较研究》,上海1997年,第80页。)以上的修正,都只限于土地产权之市场交易,仍然没有人承认土地使用权之转让是市场交易行为,对于生产要素的市场仍然认识不足。
可惜的是,对于“地主经济论”的主导性这一论点,迄今无人讨论,或深入论证,似乎认为这是一个先验的真理,无可怀疑。李根蟠先生最近发表了一篇很有趣的论文(注:李根蟠:《中国封建经济史若干理论观点的逻辑关系及失浅议》,《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3期。)。他将反对主流派“地主经济论”的各项观点归纳为两大派——“市场经济论”及“权力经济论”。他最后的结论是:“我们不必执拗于地主占有土地百分之六七十,七八十才算是封建地主制经济的老观念”。这样的修正,却把“地主经济论”与“权力经济论”融合到一起。我们不计较地主占有土地的比重,不必是80%,或60%,那怕只有20%或10%,只要他们有统治力,有主导权,就可以称为“地主经济制”,如果美国的地主掌握了这种主控权,美国也就变成了“封建地主经济制”。李先生没有正面论证这种主导权的形成,也没有举出实例加以说明,但此文确是触及了经济学上一个有趣的问题——“寻租”(rent-seekingactivities)。经济制度的终极基础就是这种“主导权”,更具体地说,就是经济资源的掌控权。在私有财产制的社会中,这种主导权来自财产权,产权的分配决定了经济决策权的分配。地租之出现及其多寡取决于市场之供需。在没有私产制度的社会中,或是在市场经济的公经济部门,一切经济租(economic rent)则透过其他方式来分配,包括“权力经济论”所提到的“禹作敏模式”。这其中有许多蹊径,就是经济学家爱谈的“寻租活动”。古往今来,莫不如此,只是名称不同而已,古时称“公田转假”或“分田劫假”;今天则称为“官倒”,其为寻租则一。这是理论上的概括说法,可以把不同的观点融合在一起。
仅仅放弃地主占地80%或60%仍然不够。如果占地只有20%或10%,地主的主导权或统治地位既不是来自财产的数量,当然另有权力来源,这样“地主经济论”便与“权力经济论”合流了。在没有统计数据的状况下,“地主经济论”难以敲定地主占地的百分比及权力来源,处于两难境界。我建议不妨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地主制”或“租佃制”都是过于笼统的名词,但是它在实际运作时却有很多详情细节可供观察。我们不妨从这个角度来判断中国历史上的地主究竟有多少主导力或统治力。
我们姑且假设在中国历史上土地已经进入要素市场,有产权交易的市场,也有使用权交易的市场。买卖双方进入市场讨价还价,实力强的一方可占优势,能获得对自己最有利的结果。
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需要把“要素市场”的概念略加廓清,以免引起误解。在商品市场上主要的型态是产权之交换,买者以其对金钱的产权向卖者交换实物的产权。然而要素市场却有两种交换形态。最基本的形态是使用权的交换,买方付出某种代价来换取生产要素的使用权。要取得使用权必须事先言明使用期限,所以使用要素的代价都有时间单位。譬如使用劳动力要付工资,工资是以小时计,以日计,以周计,以月计或年计;使用别人的资金(借贷),要付利息,以日计,以月计,以季计,以年计。依同理,使用别人的土地要付租金,租金也有时间单位,以月计或年计。如果使用期限无限延长,就成为“买断”,也就是买方取得所有权,然后无限期的使用。土地买断时所付之代价就是地价,而不是租金。资金买断时则不再是借贷,而是入股,这就是loanablecapital与equity capital两种不同的资金市场。劳动力买断时所付之代价便不是工资,而是“奴价”,也就是购入奴婢人身,以后永远供主人役使。要素市场原则上都有这两种类型,不过在多数现代国家中,政府以法令禁止奴隶买卖,买断劳动力的市场便被禁掉了。在中国历史上,秦汉以来雇佣市场与奴婢市场都是合法存在的,人们可以从劳工市场上取得劳动力的短期使用权,也可以付出身价购买奴婢的人身所有权,无限期的使用。这两种劳动力市场是平行的,互相置代,供人选择,工资太高则买奴,奴价太高则雇工,工资水平与奴价长期维持均衡,从工资可以推算出奴价,从奴价可以推算出工资(注:赵风、陈钟毅:《中国历史上的劳动力市场》,《台北商务》,1986年,第6章及第10章。)。直到宣统年间清政府才公布禁止买卖奴婢的法令,但婢女(俗称丫头)的买卖,此后还延续了若干时期才断绝。美国,尤其是南方各州,在1860年以前也是雇工市场与奴隶市场平行共存,直到林肯总统解放黑奴的南北战争之后才禁绝了奴隶市场(注:1860年以前美国南方各州与中国历史学家口中所描述的中国古代社会绝相类似,而19世纪的美国西部各州则是“关中模式”的翻版,若能收买到十几个人枪就可以武断乡里,谁的枪法最快最准,谁就是天然选出的警长。学者如果读一遍美国史,或是看过南方各州的历史小说,或是看过几十年前流行的西部武打影片,一定会深感为历史定下发展公式是多么危险的一件事。)。
知道什么是要素市场,就不会再有只承认土地买卖是市场交易而不承认土地租佃(使用权转让)是市场交易这种不合逻辑的观念。从这个角度我们就可以观察明清的耕地租佃市场,来判断作为交易双方之一的地主究竟有多大的主导力和统治力。
首先让我们看一看地租之决定。中国历史上两千多年的租佃制,最普遍的地租形式是分租制。除了地主提供耕牛或农具以及山林种植的情况下,绝大多数是对半均分谷物。在均分制下,地主亲自或派人临场监收,然后将谷物分为相等的两堆,主佃双方拈阄决定各取一堆谷物,双方的机会均等,这是最简单的对分收租方式。如果地主真正有绝对优势,单方面硬性决定收租方式,则可能索取远高于50%的租率,对半均分的收租制度便不容易维持两千多年之久。想来这其中一定有某种制约因素。更重要的是,分租制并不是对地主最有利的租佃制。对分制是主佃双方共同负担风险。如果地主有绝对的主导力,他们一定会将全部风险转嫁给佃户。然而两千多年来地主竟然始终同意分担风险。
近年发现的大量皖南地主的租簿或租佃契约,可以更具体的说明这个问题。例如雍正年间《贵记老租簿》中的第十四号田,其下注道(注:赵冈、陈钟毅:《中国土地制度史》,联经,1982年,第377页。):“此田在水头上,宜做租,不宜监分”。这是证明地主很在意风险因素,在水头上之田的风险大,收获量不稳定,地主希望改成正租制或硬租制,将风险全部转嫁给佃户。但是佃户不愿改为正租或硬租制,单独负担这样高的风险。从租簿历年收租纪录来看,第十四号田始终是采用监分制,未曾按地主之意改变。可见双方协商之后,还是决定双方分担风险。在皖南的地主租簿中常常出现有由正租制改回监分制的例子,细看其注可以发现这些田都是由新佃户接手承种。新佃户因为经验不足,不敢单独负担风险,因而请求地主改回监分制,以期与地主共同负担风险。例如光绪二十年“某氏二房租簿”(注:《中国土地制度史》,第376页。),其中第十三号地便是由正租制改回监分制,其下注明“新佃丘文林”。足证在这类情形,地主也依新佃户之请,分担风险。
明清之际,江南的租佃制正处于转变过程中,由监分制,改成正租制,再改成硬租。正租制是过渡形式,在租佃契约上写明每年租额确数,但届收获交租时地主得视实际年成斟酌照约定之正租额减收若干,称为“让租”,这等于是保留了一些监分制的意味,地主承担一部分风险。不过,让租多寡,决定权操于地主手中,不像分租制那样主佃平分风险。我们可以说此制下地主享有较大的主导权。但从租簿上看,在正租制下,几乎每年多多少少地主都有些让租,可以证明地主的主导权仍受到某些制约。从正租制改成硬租制后,佃户便得“硬交不让”,租簿上再也不出现“让租”之字样。我曾搜集了数十家皖南地主在这段过渡时期的私家租册,将每户地主各号田地收租形态统计下来(注:《中国土地制度史》,第373~375页。),列成一表,表中只有极少数地主是采取单纯一种型态地租,绝大多数是同时各号田地采用不同的地租制。按理说,如果地主有绝对的主导权,控制租佃契约,他们一定选择对他们最有利的单纯一种收租方式。采取不同的租制,正表示地主们不能完全不顾及佃户们的意愿及抗拒。
明清时期租佃制度另一项重要演变是永佃制之发展,不但江南及福建永佃制相当普及,北方的察哈尔及绥远也极盛行。永佃制之出现及推广更能显出中国农村租佃市场的推动力及主导方向。
永佃制发生有不同的来源,各地使用的名词也极庞杂,如“田皮”、“田面”、“田根”、“大苗”、“小苗”等。各地的永佃制是不约而同的发展起来,演变到最后,不但佃户合法享有了对耕地的永久使用权,而且这种权益可以转让、买卖、遗赠甚至典质。它变成了与土地产权相独立的一项产业,也可以说是原来的土地产权被割裂,于是随之出现“一田二主”,“一田三主”等现象。追溯永佃制的起源,主要有下列几大类。
第一个来源是对佃农大量土地加工的补偿。有些情形下佃农协助业主开荒或是整修水利工程,增加了该项土地的生产力,此时所增加的产量应归佃农所得,是佃农劳动贡献的结果。然而这样新增的产量年年出现,这些增产的价值便被资本化(capitapigation),变成一项资产(注:Capitalization的公式及计算很简单。假定一块土地加工以前的年产值是100两银子,佃农加工改善土地生产力后的年产值增加为200两,这额外收入的100两应归佃农所得。如果当时市面一般利率是20%,则这块土地加工后的田皮价值便是500两(=100÷20%)。),当然也应归佃农所享有。这种资本化的过程是中外市场共有的通例,并非中国所特有,不能算是中国地主的恩赐。在佃农有生之年,他可以永远佃种这块土地。如果他不愿继续耕作,则可以把这种受益权转让出去,换得代价。他死后,这种受益权可以遗赠子孙。这种资本化的受益权可以延绵不绝。这种由“工本”转化的永佃权在南方很多,而在边陲地区,如绥远及察哈尔,更为普遍,且都是开荒的后果。受益权的资本化并不限于一次性投入的开荒及整修水利工程之“工本”,有些佃农逐年不断地改善耕地的生态条件或增加土地的肥力,田地的产量也会逐年增加。这种追增的边际产量最后也被资本化,成为有市价的受益权。在南方,有许多肥沃的田地,其田皮的市价往往远超过田骨之价,即因此故。
永佃权的第二类情形是由佃户向地主付出金钱代价,购买而得。最早的实例可以追溯到宋魏泰《东轩笔录》所记载李诚的佃农为其购赎田地的故事,其文曰:
“侯叔献为杞县,有逃田及户绝没官田甚多……内有李诚庄,方圆十里,河贯其中,尤为膏腴府。佃户百家,岁纳租课,亦皆奥族矣……李诚者,太祖时为邑酒务专知官,以汴水溢,不能救护官物……故此田亦在籍没。今诚有子孙,见居邑中……叔献乃召诚孙,俾买其田。孙曰:实荷公惠,奈甚贫何?叔献曰:吾有策矣。即召见佃人百户,谕之曰:汝辈本皆下户,因佃李庄之利,今皆建大第商廪,更为豪民。今李孙欲买田,而患无钱;若使他人买之,必遣汝辈矣。汝辈必毁宅撒廪,离业而去,不免流离失职。何若醵钱借与诚孙,俾得此田,而汝辈常为佃户,不失所业,而两获所利耶?皆拜曰:愿如公言,由此诚孙卒得此田矣”。
南宋及明初,更多的情形是自耕农将其田地售予他人,索价低于市价,但言明永远保留在此田地上之耕作权,因而变成永佃户。与此相类的情形是自耕农将其土地出典,但仍在原业耕作,因典约中未曾定明回赎权之时效期限,只要出典人不赎回其产业,便沦为永佃户。不过,在这种例子中田皮田骨的产权都不明确。总之,佃户付出代价取得永佃权,等于是地主同意将其土地产权割裂,只执其“田骨”之产权。有的时候,业主自动出卖田皮或田面,自己保留田底或田骨,这就好像田主将原来一大块土地分割成两块或数块,分别出售。有的时候田面之分离是出于赠予之行为,地主以田面惠赠给他们的亲戚朋友(注:沈时可:《海门启东县之租佃制度》,成文。),甚至长久服侍的老仆,这就相当于惠赠一小块田产。
有的地区永佃权之出现与发展,既不涉及土地加工之补偿,也不是支付代价购买的结果,而纯粹是该地的乡俗与惯例造成的。南宋时,若干地区的官田租佃已有永佃权的惯例与承诺,承租官田的农户享受佃权保障。两浙地区若干州县学校在买进民田之后,仍让原佃户在该田中继续耕作(注:《江苏金石志》。)。有些民田之地主,也仿此惯例,在买进田地时不更换耕佃户,称其佃户为“随田佃户”。这种乡俗后来便发展成“倒东不倒佃”的惯例。另一方面,法令却保障佃户的退佃权,新业主不得强令原佃户继续耕作,例如绍兴二十三年的一条诏令(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64,绍兴二十三年六月庚午诏。):
“民户典卖田地,毋得以佃户姓名私为阅约,随契分付。得业者亦毋得勒令耕佃。如违,许越诉”。
这类规定都不是由地主发起创立,不表示地主有主导权或统治地位。有的情形,永佃权是由佃户单方面设立的,佃户在同一块土地上耕种多年,便自称有权长此耕种下去,乡俗加以认可,即俗语所谓“久佃成业”(这可能是承认老佃户都有改良土地之功)。地主虽然不同意,却也无可奈何,称佃户为“霸佃”。
最值得注意的是由押租制演变成的永佃制。明清时期押租制最盛行的省份也正是永佃制最盛行的省份,两者渊源密切。押租制是由地主发起创设的,其动机是要保障他们的地租收益。一来,明代时常发生佃农抗租运动,地主便要求佃户预缴一批钱谷,做为抵押品,佃户日后若拖欠或抗交地租,地主便从押租中扣掉。福建省开始流行押租制,据说是在邓茂七领导的抗租运动之后。二来,明代有大量棚民流移各地,租田耕种,这批流民的流动性高,常有农田收获后不交地租而逃离之事,地主便预收押租,以保障收益。
押租制下双方都立有契约,下面试举早期押租的典型契约,可以看出其法律漏洞,以致后来发展演变成永佃制(注:杨国桢:《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93页;魏金玉:《清代押租制度新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3期。):
“某里某人置有晚田一段,坐落某里某处,原计田若干亩,年该苗米若干,原有四至分明,今凭某人作保,引进某人,出赔价纹银若干,当日交收足讫明白,自给历头之后,佃人自用前去管业,小心耕作,亦不得买弄界至、移丘换段之类。如遇冬成,备办一色好谷若干,挑送本主仓前交纳,不得拖欠。不限年月。佃人不愿耕作,将田退还业主,接取前银,两相交付,不致留难。今给历头一纸,付与执照”。
文约中所称“赔价”即押租银或谷,其他地区另有别的名词,意义相同。值得注意的是,此契约明言佃户有自愿退佃之权,退佃时业主要交还押租银;但是业主没有自由撤佃换佃之权,佃人只要不欠租便可继续耕种下去,不限年月。在今天的契约文本中,皆有明定的时效限期,即令是长期时效,也要明确,绝少有使用“不限年月”字样。这就是押租制转化成永佃制的根据。押租银便变成购买永佃权的代价。地主原意恐怕是要给予原佃人长期耕作权,及身而止,但“不限年月”意义含糊,很容易就会被解释为原佃人死后其子孙可以继承的永佃权。通常押租银为数不小,在有些情形下,原佃人请求退佃拿回押租银,但地主因故不能,或不愿,退还押租银,便授意或默许原佃人另找其他佃户来顶替。顶替之佃户要付出相当于原押租银同等之代价给原佃人,所付之代价称为“顶费”。最初,这种承租权之转让恐怕都是经过业主的同意。然而久而久之,地主的“同意权”也被忽略了,该土地的承租权便由各佃户私相买卖转移。至此,佃人便享有遗赠或买卖转手此承租权之自由,它变成了完全独立的一种财产权。
从以上各项实例可以明白看出,地主们未曾有主导权及统治地位。至明清时期,永佃制在各地出现并迅速发展,这项事实变得更加明显。押租制本是由地主主动创制推行的,意在保障自己的收益,然而推行不久便完全失控,押租制最后演变成对地主们极不利的永佃制。
永佃权是土地产权割裂的后果,对地主十分不利。地主在必要时可以将其田产割出一小块卖给他人,以济不时之需,这也是产权之减损与割裂。然而这种方式的产权割裂却是简单明确。田皮田骨式的产权割裂则会引起长远的额外困扰。在这种制度下,地主丧失了自由使用其土地的权利。譬如说,某地主有一块土地,面临小溪,有青山流水,风景优美,他想在此地建造一所别墅,或是认为该地风水好,想改为本家的墓园。如果此块地段的田皮归他人所有,地主若要变更土地用途,必先从享有田皮产权的佃户手中买回田皮,因为这块地是由田皮田骨所有权两造共有的田产①。如果佃户坚持要在该田块上继续耕种下去,地主是无法改变其用途的。也许有人会说,那又有什么关系,不建别墅就是了。但从整个社会而言,如果所有有产权的人都不能自由安排其财产的用途,则人们最大化行为(maximization)或最优化行为(optimization)都会受严重的制约,因为他们无法判断其财产的机会成本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