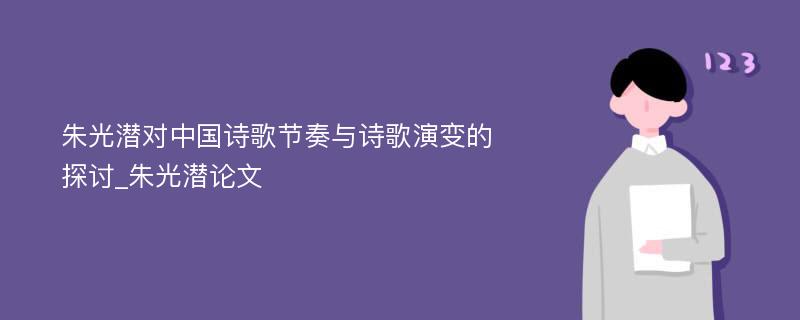
朱光潜论中国诗的声律及诗体衍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体论文,中国论文,朱光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朱光潜先生以治西方美学著称于世,实际上他对中国古典美学,尤其是中国古代诗学也有精湛的研究。他于四十年代初出版的《诗论》(注:《诗论》,1943年由国民图书出版社首版;1948年由正中书局出版增订版;1984年由三联书店出版第三版;后收入《朱光潜全集》第3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出版。),是中国诗学由传统的偶感随笔形态,转向现代系统理论形态的一部具有开创意义的专著,堪称“中国现代诗学的第一块里程碑”(注:参见李黎:《中国现代诗学的第一块里程碑——读朱光潜先生的〈诗论〉》,《读书》1986年第8期。)。 这部著作有许多开人眼界的论述,其中第八章至第十二章五节,在中西诗歌节奏和声韵的多项比较中,探讨中国诗的声律特点及诗体衍变,新见迭出,尤见功力。笔者多年来深感这部分文字极有学术价值,一直翘首盼望有人对它作出切实的评论,并在其基础上作进一步的学术推进。然而,除张世禄先生四十年代在《评朱光潜〈诗论〉》的书评里(注:参见张世禄:《评朱光潜〈诗论〉》,《国文月刊》第58期(1947年7 月出版)。),对这部分内容有所涉猎外,海内外众多的朱光潜研究论著和中国诗学研究论著,对其几乎都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笔者私下曾向多位朱光潜研究和中国诗学研究学者求询,他们都对《诗论》这部分内容所显示出的渊博学识和真知灼见赞不绝口,同时又感慨中国诗的声律是个非常专门化的领域,加之朱先生是在中国与西方多语种诗歌的音律比较中来探讨问题,因而面对它在学术上让人颇有“河伯见海若”之感,自然难免留下“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的遗憾了。本文不揣浅陋,尝试评述《诗论》中的声律论及其相关问题,考察其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缺欠,意在抛砖引玉,一方面引起学术界对《诗论》这部分成果的重视,另方面则期望得到方家的批评指正。
一
声音的节奏,主要于长短、高低、轻重三方面见出。朱光潜指出:“因为语言的性质不同,各国诗的节奏对于长短、高低、轻重三要素各有所侧重。”古希腊诗与拉丁诗都偏长短,读一个长音差不多等于读两个短音所占的时间,长短有规律地相间,于是出现很明显的节奏。而在欧洲各国诗中,似乎并不重视音的长短,而更重视音的轻重,比如英文诗,其音步即以“轻重格”(iambic)为最普遍(注:参见《诗论》第八章,《朱光潜全集》第3卷第155—156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 年出版(下引该书出版社名省略)。)。请看朱光潜引以为例的莎士比亚名句:
To be│or not│ to be:│that is│the ques│tion
轻 重│轻 重│ 轻 重│ 重 轻│ 轻 重 │ 轻
这句话出自莎士比亚戏剧《哈姆雷特》第三幕第一场,是一句剧诗,是英诗中“轻重五步格”的变体。严格说来,朱光潜引这句诗来说明“轻重格”是英诗中“最普遍”现象并不妥当。因为其第四步如依音律读,重音应在第二音“is”上,而实际读时重音却应放在第一音“that”上,并且第五步后还多一音,可说并不是典型的“轻重五步格”诗句。其实,英诗中的音律虽可适当变化,但在十四行诗里,每行均是标准的“轻重五步格”:
And that│my Muse,│to some│ears not│unsweet
轻 重 │ 轻 重│ 轻 重│ 轻 重 │ 轻 重
英诗中的十四行诗都是这样,每行十个音节,这十个音节均按“轻重││轻重│轻重│轻重│轻重”的次序,组成五个音步,所以叫“轻重五步格”。每行诗的声音节奏美,就在这轻重音的交替变化和重复中见出。
与英语诗句重视“轻重格”不同,中国诗句则重视“平仄律”。平仄由字音的声调区别(即平上去入四声的区别)构成。中国诗的平与仄的分别究竟是什么?音韵学家们的回答并不一致;有的说是长短音之分,有的说是高低音之分,也有的说是轻重音之分。朱光潜认为,“平仄的分别不能以西诗的长短轻重比拟”,“拿西方诗的长短、轻重、高低来比拟中国诗的平仄,把‘平平仄仄平’看作“长长短短长’,‘轻轻重重轻’或‘低低高高低’,一定要走入迷路”(注:《诗论》第八章,《朱光潜全集》第3卷第165页。)。这一见解是比较符合中国诗实际的。因为中国诗中的每个音的长短高低,既可以随文义语气影响而有伸缩(如“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这两句诗中的“君”字和“巴”字都是平声字,按说应读长音,但在这里却只能读成短音);有时又受邻音的影响而略有变化(如“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之中的叠音字,按说两字同声同韵,读音也应一样,但实际上叠音字读时都是先抑后扬,在音的长短高低轻重上仍略有分别)。
更为特别的是,在希腊拉丁诗中,一行不能全是长音或短音;在英文诗中,一行不能全是重音或全是轻音,假如那样,诗句就不会有节奏。但是在中文诗中,一句可以全是平声,如“关关雎鸠”、“修条摩苍天”、“枯桑鸣中林”等;一句也可以全是仄声,如“窈窕淑女”、“岁月忽已晚”、“利剑不在掌”等等。这些诗句虽非平仄相间,但仍有起伏节奏,读起来并不拗口。由此可知,平仄有规律的交替和重复,虽然也可以形成节奏,但对中国诗的节奏影响并不鲜明,或者说,平仄的主要功用并不在节奏方面。
那么,平仄在中国诗中究竟起什么作用呢?依朱光潜看,其作用主要是造成诗的音调和谐。“节奏”(rhythm)与“和谐”(harmony )是两个应该分清的概念。节奏主要指声音有规律,和谐主要指声音悦耳。比如磨坊的机轮声和铁匠铺的钉锤声都有节奏而没有和谐,而古寺的钟声和森林的一阵风声都可以有和谐而不一定有节奏。节奏自然可以帮助和谐,但和谐并不限于节奏,它的要素是“调质”(tonequality )的悦耳性。诗歌语言的音乐美,一方面在节奏,在音的长短、高低、轻重的起伏,另方面也在调质,在字音本身的和谐以及音与义的协调(注:《诗论》第八章,《朱光潜全集》第3卷第167页。)。请看白居易《琵琶行》中的名句:
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
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
这里,不仅一系列双声叠音词起到了有助声音和谐的作用,而且平仄声的有规律搭配更是造成其音乐美达到完美境界的重要缘由。比如第一句“嘈嘈”就决不可换仄声字,第二句“切切”也决不可换平声字;第三句连用六个舌齿摩擦音,“切切错杂”状声音短促迅速,如改用平声或上声,效果绝不相同;第四句以“盘”字落韵,第三句如换平声的“弹”字为去声的“奏”字,意义虽相同,可听起来就不免拗。凡是好的诗歌,平仄声一定都摆在各自最适宜的位置,不可轻易相调换,如调换后声音和谐的效果就大不一样。从此例可知,中国诗的平仄是借助有规律的音调抑扬变化,以造成音调的和谐优美。朱光潜说“它对于节奏的影响虽甚微,对于造成和谐则功用甚大”(注:《诗论》第八章,《朱光潜全集》第3卷第171页。),是为确论。
比较《诗论》对“声”的论述和这里的阐述可发现,我们避免了朱光潜反复使用的一个中心概念“四声”(注:《诗论》第八章里有这样几个小标题:“中国的四声是什么”、“四声与中国诗的节奏”、“四声与调质”,可见“四声”是朱光潜论“声”的一个中心概念。),主要原因是他在使用这一概念时出现了重要失误。这一点,音韵学家张世禄于四十年代末就曾指出:
“四声”的声,跟“声母”的声,绝对不可相混;前者是指字调的分别,后者是指字音起首的辅音。朱氏此书第八章论“声”,讲到中国的“四声”问题,有几处不免与“音质”的问题相纠缠起来。如说“中国诗音律的研究,向来分‘声’(子音)‘韵’(母音)两个要素。……现在分析声的性质。声就是平上去入”,几乎使读者要误认“声母”的声和“平上去入”的声为一件东西了!这或许是叙述时偶尔的疏忽;可是朱氏在这一章里所提出的四声“调质”的分别,确是把字调的现象和音质问题混为一谈。他说“四声不但含有节奏性,还有调质(即音质)上的分别。凡读书人都能听出四声,都知道某字为某声,丝毫没有困难,但是许多音韵学专家都不能断定四声的长短、高低、轻重的关系。这可证明四声最不易辨别的是它的节奏性,最易辨别的是它的调质或和谐性”。这里所提出的“调质”,明明说即是“音质”,实在使读者很难了解朱氏所指的“四声”的分别,是属于语音上的哪种现象?是否可以跟“声母”“韵母”上的辨别,混为一谈!(注:张世禄:《评朱光潜〈诗论〉》,《国文月刊》第58期,1947年8月。)
这里的批评言之有据,析理清晰,是很有道理的。朱光潜在谈论“四声”时,确实有时将作为“音调”的声和作为“声母”的声混为一谈了,这是不应该出现的失误。但是,这一概念的混淆,并没影响其基本结论的正确。他的基本结论是:四声(实际就是指“平仄”(注:《诗论》中许多用“四声”的地方,若换成“平仄”,意思没变,却可以避免概念混乱的毛病。不过这问题也颇复杂,也有的学者指出:“四声”所代表的是六朝的韵律论,而“平仄”所代表的是唐代的韵律论(参见日本松浦友久《中国诗歌原理》,孙昌武、郑天刚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97—200页)。)对于中国诗的节奏影响甚微,对于造成和谐则功用甚大。这一看法今天几乎已是学术界的公论,而朱光潜在三四十年代就作了较深入的探讨。因之,张世禄批评他由于概念含混不清,“自然也得不到正确的结论”的话,不免有点过甚其辞。
二
既然平仄的主要作用在于造成音调和谐,而对于节奏的影响甚微,那么,中国诗的节奏究竟是由什么因素决定的呢?
朱光潜指出,“它大半靠着‘顿’”(注:《诗论》第九章,《朱光潜全集》第3卷第172页。)。在中国诗里,“顿”是由音组而形成的自然停顿。汉语一个字为一个音节,四言诗四个音节为一句,五言诗五个音节为一句,七言诗七个音节为一句,每句的音节是固定的。但一句诗中的几个音节并不是孤立的,一般都两个组合在一起形成顿。所以四言二顿,每顿二个音节;五言三顿,每顿的音节是二二一或二一二;七言四顿,每顿的音节是二二二一或二二一二。例如下例诗句,如果我读时拉一点调,就形成这样的顿: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
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
这是按照旧诗读法而划分出来的顿,其中参杂几分形式化的音乐节奏。在通常情况下,顿的划分既要考虑到音节的整齐,又要兼顾意义的完整。因此,上面后两句诗,也可顿成下式:
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
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
由于兼顾了音和意两个方面,较近于语言的自然节奏,有时反而觉得更顺口。
值得补充的是,中国诗音节的组合不仅形成顿,还形成逗。“逗”也就是一句诗中最显著的那个“顿”。中国古、近体诗成句的一个基本习惯,就是一句诗必须有一个逗,这个逗把诗句分成前后两半,其音节分配是:四言二二、五言二三、七言四三。因为在中文诗里,一般多两字成一音组,这两个字就应该同时是一个义组,如果有三个字成一个义组,无论在五言或七言中,它最好摆在句末,这样才可避免头重脚轻的弊病。林庚先生指出,这是中国诗歌在形式上的一条规律,并称之为“半逗律”。他说:“‘半逗律’乃是中国诗歌基于自己的语言特征所遵循的基本规律,这也是中国诗歌民族形式上的普遍特征。”(注:林庚:《关于新诗形式的问题和建议》,见《问路集》第247页。)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有的句子凑成了五言或七言,却仍然不像诗句的道理。譬如下面诸例:
似梅花—落地,如柳絮—因风。
送终时—有雪,归葬处—无云。
静爱竹—时来—野寺,独寻春—偶过—溪桥
对于这几个实例,朱光潜认为它们“在音节上究竟有毛病,因为语言节奏与音乐节奏的冲突太显然,顾到音就顾不到义,顾到义就顾不到音”(注:《诗论》第九章,《朱光潜全集》第3卷第176页。)。实际上,这几例的毛病也在没有遵循中国诗成句的基本习惯,即五言二三、七言四三的“半逗律”,而是写成了五言三二、七言三二二的句式,给人头重脚轻之感,与语言的先抑后扬的普遍倾向相违背。
在谈论中国诗的“顿”时,朱光潜提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观点,即有些中文诗句存在着类似英文诗“上下关联格”(enjambement )的现象。中文诗不论四言、五言或七言,一般一句是个独立整体,如“野树花初发,空山独见时”和“旧苑荒台杨柳新,菱歌清唱不胜春”这两联诗,每一联的前一句与后一句均可分开,并相对独立。这是大多数中文诗句的情况。但是,也有些中文诗,一联中上句和下句虽然分为两句,可在意义上并不能拆开,如“翩翩飞鸟,息我庭柯”;“幸有弦歌曲,可以喻中怀”;“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渭水东流去,何时到雍州”;“天台四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等等,均是形分两句,意为一体的例证。
对于这种把一个意义不能拆开的句子分为两部分,使声音成为有规律段落的现象,朱光潜认为很可拿来与英文诗的“上下关联格”相比较。英文诗(其他西文诗,如法文诗、德文诗也一样)的单位是“行”(line),每行不必为一句,上行的未表达完的意思可以自然转入下行去。譬如莎士比亚的诗句:
…and blest are those
Whose blood and judgement are so well commingled
That they are not a pipe for fortune's finger
To sound what stop she please.
这四行诗实际只是一句,每行最后一字于意义均不能停顿,所以需要连着下句一起读。英文诗在一句未完成的每行末尾既不停顿,为什么又要分行呢?这全是因为“无韵五节格”每行五个音步,上行音步的数目够了,不管意思表达多少,其余意思一律移到下行接着写,以至一句诗可写数行之多。英文诗的节奏如前面谈“声”时所述,与行的关系并不大,主要体现在每行五音步的轻重抑扬的配合上。
中文诗由于以句为单位,在多数情况下一句完了,意义也就完成,声音也就停顿,所以似乎没有“上下关联”的现象。朱光潜指出,“事实上仍是有的”。这有上面引的诸例可以为证。不过,“它与西诗‘上下关联格’所不同者,在西诗行末意义未完成时,声音即不可停顿,必须与下行一气连读,在中诗一‘句’之末,意义尽管未完成而声音仍必须停顿,至少习惯的读法是如此”。“西诗‘上下关联’时上行之末无须停顿,而中诗‘上下关联’时则上一句之末必须停顿,这件事实也足证明顿对于中诗节奏的重要性。”(注:《诗论》第九章,《朱光潜全集》第3卷第179—181页。)
朱光潜这里提出的中文诗中也有类似西方诗“上下关联格”的现象,并对两者的异同特点作了自己的分析,可以说揭橥了中国诗学中一个客观存在而又未被道破的新问题。这显示了他对中西诗歌及诗学修养深厚,咳唾成珠的大家风貌,对于我们认识中西诗歌的特点是很有意义的。
三
中国诗的节奏除了在“顿”上见出以外,在“韵”上也有明显体现。
押韵是字音中韵母部分的重复。按规律在诗歌的一定位置上重复出现同一韵母,就形成韵脚,产生节奏。这种由韵脚而产生的节奏,可以把涣散的声音联络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整体,使前后诗句在声音上互相呼应,贯串一气。
关于中国诗用韵特点的探讨,齐梁以来,代不乏人。朱光潜谈论这一问题的贡献是,把中国诗歌的用韵现象,放在与西方各国诗歌的比较中加以考察,使中国读者既了解了西方诗的用韵情况及其原因,又明白了“韵在中文诗里何以特别重要”的道理。
朱光潜指出:诗与韵本无必然联系,日本诗到现在仍无韵,古希腊诗全不用韵。诗是否用韵,与各国语言的个性密切相关。拿英文诗与法文诗对照,韵对法诗较英诗重要。法文诗从古至今,除一部分散文诗和自由诗外,总体上各种诗体都押韵。但英文诗长篇大著多半用无韵五节格(blank verse),短诗虽用韵较多,但也有不用韵者,就整体言, 英诗无韵的较有韵的为多。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关键在于英文音的轻重很分明,音步又很整齐,节奏容易在轻重相间上见出,无须借助韵脚的呼应。法文诗因为音的轻重不分明,每顿的长短又不一律,节奏不容易在轻重抑扬上见出,所以须借助押韵脚来增加节奏性与和谐感。英文和法文的这种分别,可以说是日耳曼系语音和拉丁系语音的一个重要异点(注:参见《诗论》第十章,《朱光潜全集》第3卷第186—188页。)。
知晓了韵对于英诗和法诗的分别及其原因,就不难了解韵对于中国诗的重要了。朱光潜说:
以中文和英、法文相较,它的音轻重不甚分明,颇类似法文而不类似英文。……中文诗的平仄相间不是很干脆地等于长短、轻重或高低相间,一句诗全平全仄,仍可以有节奏,所以节奏在平仄相间上所见出的非常轻微。节奏既不易在四声上见出,即须在其他元素上见出。上章所说的“顿”是一种,韵也是一种。韵是去而复返、奇偶相错、前后相呼应的。韵在一篇声音平直的文章里生出节奏,犹如京戏、鼓书的鼓板在固定的时间段落中敲打,不但点明板眼,还可以加强唱歌的节奏。(注:参见《诗论》第十章,《朱光潜全集》第3卷第188页。)
中国诗何以重视“韵”?原因与法文诗需要韵的道理一样:主要是音的轻重不分明,音节易散漫,必须借助韵的回声来点明、呼应和连贯。中国诗歌的韵押在句尾,句尾总是意义和声音的较大停顿处,再配上韵,所以造成的节奏感非常强烈。中国诗歌的音乐美,押韵是十分重要的因素。
在探讨中西诗歌与韵的关系时,朱光潜还涉及到一个值得注意的研究线索:
据现有的证据看,诗用韵不是欧洲固有的,而是由外方传去的。韵传到欧洲至早也在耶稣纪元以后。据十六世纪英国学者阿斯铿(Ascham)所著的《教师论》,西方诗用韵始于意大利,而意大利则采取匈奴和高兹诸“蛮族的陋习”。阿斯铿以博学著名,他的话或不无根据。匈奴的影响达到欧洲西部在纪元后一世纪左右,匈奴侵入罗马则在第五世纪。韵初传到欧洲,颇风行一时……。(注:参见《诗论》第十章,《朱光潜全集》第3卷第187页。)
这就是说,欧洲语言中本来并无用韵现象,后来欧洲各国的诗歌不同程度地用韵,主要是受到匈奴族的影响。如此说来,西方诗用韵与中国还存在着某种“事实”的联系。这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一件值得记载的事件,也是中西比较文学里一个十分值得开掘的研究课题。可惜朱先生只是点出问题而没有展开论述,他所提及的十六世纪英国学者阿斯铿(Ascham)的《教师论》也一时不易寻觅,无法判定所论是否有确凿证据。不过,这里毕竟提出了问题,并披露了初步的研究线索,顺藤摸瓜地钻研下去,当会有较大收获,起码可以为中西文学及文化交流史填补上漏写的重要一笔。
四
1948年,《诗论》出“增订版”时续补第十一、十二两章,专门讨论中国古体诗向近体诗演变,即“中国诗何以走上‘律’的路”的问题。这部分成果,是朱光潜学术著述中比较精彩的篇章之一,朱先生自己也较为看重。他晚年向人们告白《诗论》是自己“用功较多,比较有点独到见解的”著作时,曾特别点明:“《诗论》对中国诗的音律,为什么中国诗后来走上律诗的道路,作了一些科学的分析。”(注:《朱光潜教授谈美学》,《朱光潜全集》第10卷第531页; 另参见《诗论》三联书店1984年版“后记”,《朱光潜全集》第3卷第331页。)他探讨“中国诗何以走上‘律’的路”这问题所得到的结论是:
一、声音的对仗起于意义的排偶,这两个特征先见于赋,律诗是受赋的影响。
二、东汉以后,因为佛经的翻译与梵音的输入,音韵的研究极发达。这对于诗的声律运动是一种强烈的刺激剂。
三、齐梁时代,乐府递化为文人诗到了最后阶段。诗有词而无调,外在的音乐消失,文字本身的音乐起来代替它。永明声律运动就是这种演化的自然结果。(注:《诗论》第十二章,《朱光潜全集》第3 卷第220页。)
这三个见解,第二、三两点前人已有不同程度论述,如关于中国音韵研究受佛经翻译和梵音输入的启发,陈寅恪早在《四声三问》中便明确提出,并作了较详细的解说(注:对陈寅恪的看法,近年有些学者如郭绍虞、管雄等提出不同意见。参见郭绍虞:《文笔说考辨》,载《文艺论丛》第三辑,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年版,第303—357页;管雄:《声律论的发生和发展及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影响》,载《古代文艺理论研究》第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8—44页。);关于诗与乐分离后,诗必须在文字本身求音律的看法,刘大白在《中国旧诗篇中的声调问题》里也早有涉猎(注:参见刘大白:《中国旧诗篇中的声调问题》,载《小说月报》号外,“中国文学研究号”,商务印书馆1927年出版。)。对于这些问题,朱光潜虽在有些地方作了自己的阐发,但总体上毕竟是陈述他们的观点。可是,第一点说明中国诗走上律的路,在意义排偶和声音对仗两方面,都受到赋的影响,却是朱先生的发明,最具新意,堪称创见。
自古以来,人们一直认为“赋自诗出”(注:刘勰:《文心雕龙·诠赋》。)。班固在《两都赋·序》里说:“赋者,古诗之流也。”刘勰《文心雕龙·诠赋》说:“诗有六义,其二曰赋。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挚虞的《文章流别论》也说:“赋者,敷陈之称,古诗之流也。”(注:挚虞:《文章流别论》已佚,其论赋之语见《艺文类聚》卷五十六。)这种赋出于诗的看法,当然是不易之论。千百年来,人们尊从此说,似乎只习惯注意诗对赋的影响,而对于赋给予诗的影响则较少考虑,或者说,根本就忽视了这条考虑思路。朱光潜别具慧眼,发现律诗的两大要素,即意义的对偶和声音的对仗,都是最先出现于赋中,并首先由赋家兼诗人的曹植、鲍照、谢灵运等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到诗里,然后再逐渐推广开来,慢慢发展成熟,及至唐朝,终成律诗极盛时代。从此以后,律诗不仅是中国诗歌中影响最大、发展最为充分的诗体,而且对唐以后的词曲及散文演进,都留下了明显的影响痕迹。
本来,在《诗经》等古体诗中,虽然也有对句,如《小雅·无羊》描写牛羊的情况:“谁谓尔无羊?三百为群。谁谓尔无牛?九十其犉。尔羊来思,其角濈濈;尔牛来思,其耳湿湿”,但这种对句似乎只是无意为之,不属有意刻划得来。可是在汉赋里,如枚乘的《七发》、班固的《两都赋》、左思的《三都赋》等,都显然存在有意求排偶的倾向,其中的骈语对句都明显多于散言句式。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赋侧重横断面的描写,要把空间中纷陈对峙的事物情态都和盘托出,所以最容易走上排偶的路”(注:《诗论》第十一章,《朱光潜全集》第3卷第200页。)。这种讲究排偶的风尚,自然会影响到一些赋家兼诗人的诗作,如曹植的诗句“始出严霜结,今来白露晞”;“秋兰被长坂,朱华冒绿池”;“潜鱼跃清波,好鸟鸣高枝”,便俨然是对偶句了。到了谢灵运和鲍照手里,则开始露出全篇排偶的端倪,如谢灵运的《登池上楼》、《登江中孤屿》,鲍照的《代出自蓟北门行》等,都是明显的例证。所以,朱光潜说:“律诗第一步只求意义的对仗,鲍、谢是这个运动的两大先驱(当时虽无‘律’的名称,‘律’的事实却在那里)。在汉朝赋已重排偶而诗仍不重排偶,魏晋以后诗也向排偶路上走,而且集排偶大成的两位大诗人——谢灵运和鲍照——都同时是词赋家。从这个事实看,我们推测到诗的排偶起于赋的排偶,并非穿凿附会了。”(注:《诗论》第十一章,《朱光潜全集》第3卷第205—206页。)
诗不仅在意义的排偶上受到赋的影响,而且在声音的对仗上也受到赋的启发。早在沈约提出“四声说”之前,陆机便在《文赋》里发表了“音声迭代”之说,在中国文艺理论史上首次着重提到声律问题并加以阐述。而陆机所讲的“音声迭代”理论,则是专指词赋而言,诗歌并不包括在内。晋宋之时,陆机的《文赋》、鲍照的《芜城赋》等,都大体已用平仄对称的声调。齐梁之间,梁元帝、江淹、庾信、徐陵诸人的赋,不但意精词妍,句式排偶,而且声音也是“前有浮声则后有切响”了。此时,律赋已连篇累牍,而律诗则凤毛麟角(仅何逊的几首五言可算工整的律诗)。“永明”诗人虽然注重句内各字的声律,但毕竟多属一种理论主张,实践上只是开其端倪,到隋唐时律诗才真正定型。正如宋祁在《新唐书》中所说:“唐兴,诗人承陈隋风流,浮靡相矜。至宋之问、沈佺期等,研扬声音,浮、切不差,而号律诗。”(注:宋祁:《新唐书》第二○二卷“杜甫传论”。)
为什么赋讲究音和义的对称都先于诗?在朱光潜看,这是有一定原因的。他说:
词赋比一般诗歌离民间艺术较远,文人化的程度较深。它的作者大半是以词章为职业的文人,汉魏的赋就已有几分文人卖弄笔墨的意味。扬雄已有“雕虫小技”的讥诮。音律排偶便是这种“雕虫小技”的一端。但是虽说是“小技”,趣味却是十足。他们越做越进步,越做越高兴,到后来随处都要卖弄它,好比小儿初学会一句话或是得到一个新玩具,就不肯让它离口离手一样。他们在词赋方面见到音义对称的美妙,便要把它推用到各种体裁上去。艺术本来都有几分游戏性和谐趣。于难能处见精巧,往往也是游戏性和谐趣的流露。词赋诗歌的音义排偶便有于难能处见精巧的意味。(注:《诗论》第十一章, 《朱光潜全集》第3卷第206—207页。)
中国诗歌的发展,如果说《国风》是民歌的鼎盛期,汉魏是古风的鼎盛期(或者说是民歌的模仿期),那么晋宋齐梁时代可说是“文人诗”的正式成立期。这一由“自然艺术”到“人为艺术”,由民间诗到文人诗,由浑厚纯朴诗风到精研新巧诗风的转变,其中介便是赋的影响。朱光潜这里所揭示的,是从诗体及文体本身衍变的角度,说明律诗这一重要文学现象的产生,在意义排偶和声音对仗方面并非突发事件,而是受到辞赋的流灌和滋养。这一看法新颖而独到,至今少有人论及;也少有人评价,似没有引起学术界的充分注意。笔者以为,只要细心考察、比较汉魏及南北朝时期的辞赋和诗歌,朱先生的观点有大量的事实作根据,是值得认真对待的。
五
律诗和古体诗的最大不同,是在音和义两方面都讲究对仗排偶。但是,西方人也有注重在艺术中对称的倾向,为什么他们的诗没有走了排偶的路呢?朱光潜讨论中国律诗发生、发展的过程和原因时,还在中西语言特点的比较中,考察了律诗在中国产生的语言基础,同时对中西诗歌在排偶对仗上的差异作了自己的分析。就笔者的阅读了解,这是最早从中西语言比较的角度,具体探讨双方诗歌表达特点的文字,可谓是六十年代后西方中国诗学比较研究的代表人物刘若愚、叶维廉等人先驱。
朱光潜指出:中文字全是单音,一字对一音,因而诗句易于整齐划一。如“我去君来”、“桃红柳绿”,稍有比较,即成排偶。可西方文字,不论是英文、法文或德文等,都是单音字与复音字相错杂,意象尽管对称而词句却参差不齐,不易两两相对。例如英国维多利亚时代代表诗人丁尼生(Alfred Tennyson)《公主》(The Princess )里的诗句:
The long light shakes across the lakes,
And the wild cataract leaps in glory.
(长长的金光在湖面摇荡,
野性的瀑布在壮丽飞溅。)
这在英诗中已可算比较工整的排偶,但与中国律诗仍无法相比,原因就在于其意象虽成双成对,而声音却不能两两对称。比如“光”和“瀑”两字,在中文里音和义都相对称;而在英文里,“lihgt ”和“cataract”意义虽相对而音则多寡不同,难以成对,犹如“司马相如”和“班固”都是专名却不能相对的道理一样(注:参见《诗论》第十一章,《朱光潜全集》第3 卷第201 页。 )。 美国斯坦福大学著名教授刘若愚(James J.Y.Liu)在其很受好评的《中国诗学》(ChinesePoetics)里说: “汉语最具特色的声韵美是汉字的单音节性及其固定的声调。一个英语词可能包含一个以上的音节,而汉字却一律为单音节。因此,在中国诗歌里,每行诗的音节的数目与汉字的数目是一致的。”他认为,中国诗所以产生律诗形式,而英文诗无法做到,关键即在“两者语言本身存在重要差异”(注:参见刘若愚:《中国诗学》,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6年版第27—32页。)。这里的见解无疑是精辟的,可是与上述《诗论》中的观点相比,并无出其右者的胜见。朱光潜中西学养之深厚和学术眼光之敏锐,于此可见一斑。
中西文的不同,还表现在两者的语法规则具有重大差异。朱光潜指出:“西文的文法严密,不如中文字句构造可自由伸缩颠倒,使两句对得很工整。比如‘红豆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两句诗,若依原文构造直译为英文和法文,即漫无意义,而在中文里却不失其为精练,原因就在于中文语法比较疏简有弹性。再如‘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两句诗没有一个虚字,每个字都实指一种景象,若译为西文,就要加上许多虚字,如冠词、前置词之类。中文不但冠词和前置词可以不用,即便主词动词亦可略去。在好诗里这种省略是常事,而且很少发生意义的暧昧。”(注:《诗论》第十一章,《朱光潜全集》第3 卷第201—202页。)这里的分析具体而实在,可谓语语中的。我们且以杜甫《旅夜书怀》里两句诗及其英译来加以说明:
星垂平野阔,
月涌大江流。
The stars drooping,the wild plain is vast,
The moon rushing,the great river flows.
——James J.Y.Liu
Stars descend,rimming the endless land,
The moon emerges,on the great river flowing.
——Bruce M.Wilson & Zhang Ting-chen
这两例英译,是笔者比较多种译文选出的最接近原文形式,并能较好传达原意者。然而即便这样,对照原文和译文可以一眼发现,杜诗原句对仗工整,而译作尽管已做出很大努力,仍无法做到两两相对(注:拙著《文学横向发展论》对此有探讨,参见该书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236—243页。)。这不仅因为在英文里音与义的关系较多变化(并非像汉语一字必定一音节,而是一字可能单音也可能复音);更因为英文的语法关系远较中文严密复杂,如上例既需加上“the”、“on ”之类的冠词、介词,又需讲究时态及数的吻合(如第二例译文两句的前半段“Stars descend”,“The moon emerges”)等等。朱光潜说:“单就文法论,中文比西文较宜于诗,因为它比较容易做得工整简练。”(注:《诗论》第十一章,《朱光潜全集》第3卷第202页。)这话讲在“五四”以后推崇西方诗而贬斥中国旧诗的时代,不仅显示了朱先生的学术见识,更显示他的学术勇气。并且,这观点除引起许多中国学人的共鸣外,本世纪以来还被越来越多的西方诗人和学者所接受,如西方诗中的象征主义运动、超现实主义诗歌等,都有明显追求中国诗境的倾向(注:参见叶维廉:《中国现代诗的语言问题》,《中国古典诗中的传释活动》,两文均收入《中国诗学》,三联书店1991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