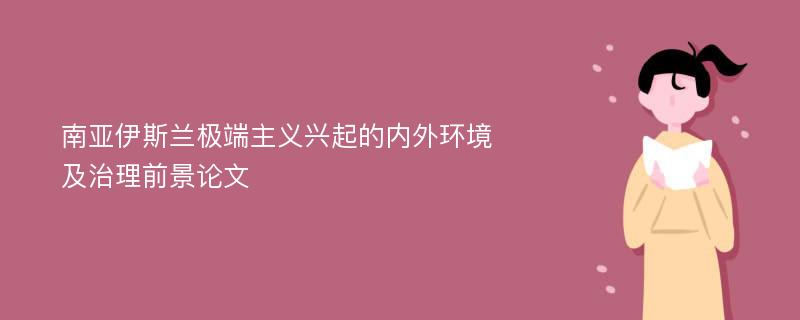
南亚伊斯兰极端主义兴起的内外环境及治理前景
钮 松
[内容提要] 20世纪70年代末,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兴起,构成了南亚伊斯兰极端主义的产生和发展的国际背景。加之深受苏联入侵阿富汗和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影响,以及美国治标不治本的全球反恐战略,尤其是其中东和南亚政策的失败,更成为促进南亚伊斯兰极端主义恶性发展的重要因素。南亚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发展,与地区冲突、国家建构、民族分离主义密切相关,具有跨国性、联动性等典型特征。南亚有关国家围绕打击伊斯兰极端主义加强地区性合作、对伊斯兰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采取不同策略,使得南亚伊斯兰极端主义治理工作取得一定成效,但仍面临诸多严峻挑战。
[关 键 词] 南亚 伊斯兰极端主义 极端组织 恐怖主义
伊斯兰极端主义是当今世界具有全球性影响的问题,影响层面几乎涉及所有拥有穆斯林的国家,涵盖政治、经济、安全等多元内容,对当前国际体系的演进与转型产生了极大冲击。而南亚地区(1) 本文中的“南亚”主要指“南亚区域合作联盟”(SAARC)八个成员国,即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阿富汗、斯里兰卡、尼泊尔、不丹和马尔代夫。该组织成立于1985年。虽然阿富汗2005年才加入该组织,但阿富汗长期以来与南亚地区,尤其是巴基斯坦的联系极为紧密。长期以来,阿富汗习惯上被视为南亚国家。 既是连接东亚、东南亚与西亚北非地区的重要桥梁,也是伊斯兰极端主义向东西双向扩散的重要交汇点。分析、研究南亚伊斯兰极端主义兴起、发展和治理成效,对于全面认识、把握全球伊斯兰极端主义的现状及发展趋势具有重要意义。
一、南亚伊斯兰极端主义兴起发展的外部环境
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兴起,既有伊斯兰世界内部宗教与政治思潮的演进逻辑,也与宗教在现代国际关系中的整体性复兴有着密切联系。随着1492年穆斯林政权在西班牙最后一个据点的陷落,以及恢复基督教统治的西班牙借助阿拉伯人留下的航海技术尝试开辟通往东方的新航路,西方的全球时代开启。1492年是基督教西方与伊斯兰教亚非地区命运的分水岭与转折点。自此以后,西方处于一种持续上升的态势,而伊斯兰世界则在科技、经济、社会等领域的治理上处于整体衰落的局面。尽管在一定时期内衰落中的伊斯兰世界与上升中的西方世界相比仍处在相对的高位,但其整体的颓势无法阻挡,历史的发展脉络已经呈现出与伊斯兰世界辉煌时期相比截然不同的保守态势。
欧洲的兴盛与伊斯兰世界的由盛转衰并非偶然,这恰恰与宗教有着密切关联。西班牙与葡萄牙最早通过开辟新航路走向全球扩张之路,而西班牙的对外扩张恰恰是建立在数百年收复失地运动的基础之上,即从伊比利亚半岛驱逐亚非穆斯林,恢复基督教的统治。西班牙与葡萄牙开辟新航路的动力,除了经济驱动力以外,实则借彻底清除穆斯林统治的大好时机,以超强的基督宗教情怀在新的领域乘胜追击。但西班牙与葡萄牙毕竟仍是由旧式的专制君主所主导,其第一代全球海上霸权逐步让位于资本主义勃兴的“海上马车夫”荷兰,这与宗教情怀所促动的新航路开辟所带来的资本主义的萌芽和海运贸易有着极大关联。这又为“托古改制”的文艺复兴运动以及日后的宗教改革提供了精神、制度和物质的综合基础,英法为代表的殖民主义扩张对全球造成了巨大冲击,在各大洲的诸多文明古国建立了殖民地或保护国,这种屈辱感和危机感对伊斯兰世界造成了巨大冲击。
对于伊斯兰世界而言,欧洲的船坚炮利既带来了某种民族危机,更带来了宗教危机。欧洲历史上以收复圣地为名的“十字军”东征,给伊斯兰世界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与危机感。伊斯兰世界的政界和思想界掀起了诸多的改革运动和思潮,主要包括两种倾向:一种是在国家治理层面效仿欧洲并引入先进器物,一种便是抵制欧洲的影响,主张回归纯正的伊斯兰。由于伊斯兰教并未经历过新教式的宗教改革,因而具有极大张力,包含宗教、政治、经济和社会等诸多领域。诸多伊斯兰思想家将伊斯兰世界的沦落,归结为偏离了正确的伊斯兰教义。欧洲列强的侵入,实际上造成了一种“挑战—回应”的宗教政治思潮的对抗模式。
进入20世纪,欧洲殖民主义列强之间的争端,为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兴起奠定了坚实基础。一战期间,德国为了与协约国阵营对抗,以民族解放为旗号大力扶植英法殖民统治地区的穆斯林采取暴力行动,这被称为“德国制造的吉哈德”。(2) Florence Waters, “Germany’s Grand First World War Jihad Experiment,” Telegraph , August 10, 2014, http://www.telegraph.co.uk/culture/museums/11022199/Germanys-Grand-WW1-Jihad-Experiment.html.有关德国与伊斯兰激进主义的关系,参见:Ian Johnson, A Mosque in Munich :Nazis ,the CIA ,and the Rise of the Muslim Brotherhood in the West , Boston: Mariner Books, 2011。在欧洲列强缝隙中得以生存并被利用的伊斯兰势力逐渐走向壮大(3) 一战期间,与奥斯曼帝国同属同盟国阵营的德国开始打“伊斯兰牌”,借此煽动英法广大殖民地穆斯林的反抗情绪。在塑造“圣战”之类的话语体系与暴力化的发展方面,德国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伊斯兰激进主义的早期源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当时的伊斯兰激进主义的“圣战”行为,实则“德国制造的吉哈德”。此后,伊斯兰势力成为西方国家内部博弈的一种工具,西方实际上长期为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兴起与发展有意或无意地保驾护航。 ,但一直到二战爆发,政治化与激进化的伊斯兰运动仍旧受到普遍的压制。冷战的爆发为伊斯兰主义在战后国际关系中的全面崛起创造了条件,美苏阵营之间的对峙与博弈体现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全方位领域,从宗教视角来看,在很大程度上被解读为有神论与无神论的争端,这实际上为宗教因素参与现代国际关系创造了天然契机。两极格局对于中东地区也产生了难以磨灭的影响,美苏阵营加紧了在伊斯兰世界的拉拢与对抗,这也不断促使伊斯兰世界的诸多民族主义思潮和地方民族主义思潮,逐步让位于伊斯兰复兴主义思潮。
(一)阿富汗战争极大刺激了南亚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兴起
还有一类巴基斯坦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高度关注克什米尔问题,主张通过自身的暴力手段实现把克什米尔并入巴基斯坦,其矛头主要针对印度。“圣战者运动”(HuM)成立于1985年,它从“伊斯兰圣战运动”(HuJI)中分离出来,后者于1980年在阿富汗抗苏战争中成立。1989年苏军撤离阿富汗之后,“圣战者运动”开始将注意力转移到克什米尔问题,并于1993年和“伊斯兰圣战运动”合并成立“安萨尔运动”(Harkat-ul-Ansar)。“安萨尔运动”成立伊始遭到印度的严厉打击,该组织三名重要领导人相继被捕,包括纳斯鲁拉·曼苏尔·兰加尔亚勒、马苏德·阿资哈尔和萨贾德·阿富汗尼。“安萨尔运动”曾试图通过大量绑架行动营救其领导人,包括绑架克什米尔地区的西方游客来对印度政府施压。1999年,阿富汗尼在越狱过程中被击毙,这直接导致了该组织劫持印度IC-814航班,并迫使印度政府释放了阿资哈尔及另外两人。(13) HimanshiDhawan,“ISI Backed Kandahar Hijackers: Plane Crisis Negotiator AjitDoval,” The Economic Times , January 16, 2017.阿资哈尔出狱后于2000年成立了“穆罕默德军”(JeM),其成员大部分来自原“圣战者运动”,其宗旨依旧是结束印度对克什米尔的占领。“穆罕默德军”延续了对印度的袭击活动。
就1979年发生的与伊斯兰教相关的事件而言,伊朗伊斯兰革命、沙特麦加大清真寺事件代表的中东伊斯兰复兴,是影响南亚伊斯兰复兴的重要国际环境,而苏联入侵阿富汗使阿富汗成为全球伊斯兰“圣战”中心,尤其是以阿富汗为大本营的极端组织“塔利班”和“基地”组织,对南亚尤其是巴基斯坦伊斯兰极端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具有直接且深远的影响。苏联入侵阿富汗激起了全世界伊斯兰激进势力的强烈反对,使苏联与全球伊斯兰激进势力之间的武装对抗演变成为伊斯兰极端势力所谓的穆斯林与苏联异教徒之间的“圣战”。伊斯兰极端势力对于苏联入侵阿富汗事件有着不同的解读:一种是伊斯兰教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无神论的对抗,即反抗无神论的苏联及其全力扶持的阿富汗政权。“伊斯兰成为团结各个反对派以反抗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价值体系”,“来自阿富汗以外的伊斯兰世界的‘自由战士’也加入了这场扩大化的宗教政治斗争”。(6) 参见汪金国、张吉军:《政治伊斯兰影响下的阿富汗伊斯兰教育》,《南亚研究》2010年第2期,第75页。 另一种解读认为,是伊斯兰教与东正教的对抗,即将苏联的入侵视为是东正教俄罗斯民族的入侵。(7) Rafael Reuveny, Aseem Prakash, “The Afghanistan War and the Breakdown if the Soviet Unio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 Vol.25, No.4, 1999, pp.693-708.
“纺纱工艺设计与质量控制”课程是一门在大学三年级第六学期开设的课程,学生经过纺纱学和新型纺纱学的学习后,有了一定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时候学生离毕业还有1年时间,他们考虑毕业后将要从事的工作,因此很重视自己能力的培养,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有所提高,此时, “纺纱工艺设计与质量控制”课程采用案例教学法,可以激发学生的潜能,能够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动手能力,提高创新能力和工程实践能力,培养综合能力,进一步锻炼学生分析和解决生产实践过程中出现的问题[5-6]。
苏联的入侵导致全球“圣战者”齐聚阿富汗,在抗苏的旗帜下协同作战,使阿富汗很快成为全球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的大本营,成为吸纳来自南亚、中亚和中东等地“圣战”分子的“坩埚”。通过十年的抗苏战争,本土的“塔利班”和外来的“基地”组织在陷入碎片化的阿富汗不断壮大。美国出于对抗苏联的全球战略需要,大力扶植并武装了诸多以抗苏为名的伊斯兰极端组织。阿富汗的战乱,还为伊斯兰世界逊尼派和什叶派两大教派的冲突提供了斗争场所。除此之外,两大教派阵营还在对美关系上存在斗争,逊尼派伊斯兰极端组织显然与美国建立了抗苏统一战线,美国毫不掩饰对逊尼派伊斯兰极端组织的支持。(8) Steve Coll, Ghost Wars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CIA ,Afghanistan ,and Bin Laden ,from the Soviet Invasion to September 10, 2001, New York: Penguin Press, 2004; George Crile, Charlie Wilson ’s War :The Extraordinary Story of How the Wildest Man in Congress and a Rogue CIA Agent Changed the History of Our Times , New York: Grove Press, 2007.本·拉登便是逊尼派圣战者之一,其创立的“基地”组织虽然思想源头在西亚的沙特,但其诞生及成熟壮大则是在南亚的阿富汗。什叶派伊斯兰激进组织则得到了伊朗的有力支持,伊朗一方面通过两伊战争与逊尼派君主国支持的伊拉克萨达姆政权作斗争,一方面以阿富汗内战为契机,既扩张什叶派的信仰版图,又反苏反美。因此,阿富汗既是伊斯兰极端组织“圣战”的大本营,也是逊尼派和什叶派冲突的主战场,而“基地”组织在阿富汗的创立和发展则成为全球伊斯兰极端主义、国际恐怖主义的渊薮所在,其对南亚乃至全球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影响延续至今。
很多高中学生在做函数的有关习题中觉得抽象难懂,在做题时很难将函数的相关性质相互结合,为了能较好地解决函数中的有关综合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在全面复习函数有关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基础上,进一步升华对函数的基本概念的全面理解,全面把握各类函数的特征,提高运用基础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借助信息化的“动态图”的优势树立函数方程思想与图形的有效结合,使学生善于用运动变化的观点分析问题.
(二)美国对伊斯兰世界的霸权政策加剧了南亚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恶性发展
2.南亚伊斯兰极端主义活动上具有明显的跨国、跨区域性
Adenocarcinomas represent the majority of PC,less than 5% are neuroendocrine tumors. Pancreatic neuroendocrine tumors have specific features and different treatment modalities[3]. In this paper, we will focus only on metastatic pancreatic adenocarcinomas.
从1991年苏联解体到2001年“9·11”事件爆发之前,美国在南亚地区遏制的重点并非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尽管在南亚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界地区活动的“基地”组织对美国发动了一些恐怖袭击活动,但美国仍然保持了极大的克制。不仅如此,美国还与实际控制阿富汗绝大部分国土的塔利班政权保持了良好关系,美国的西亚盟友沙特和阿联酋与塔利班政权建立了外交关系。由此可见,出于在中亚、南亚地区进行霸权扩张的需求,美国与塔利班政权之间并未走向水火不容,甚至存在相互利用的关系。直至“9·11”事件爆发,美国才对塔利班政权施压,要求塔利班交出受其庇护的本·拉登,塔利班政权选择继续庇护本·拉登导致美国发动了推翻塔利班政权的阿富汗战争。
2001年阿富汗战争后,塔利班隐匿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边境地区,并短暂蛰伏后在阿富汗卷土重来,甚至在巴基斯坦攻城略地,与当地盘根错节的部落之间形成联盟,对巴基斯坦政府的统治也构成了极大威胁。塔利班针对阿富汗政府、军警和平民目标发动了较多的暴恐袭击,这意味着塔利班所代表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暴力恐怖主义的要素。随着塔利班在巴基斯坦边境地区的不断壮大,塔利班的巴基斯坦分支于2007年开始自立门户,以“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的名义独立开展运动,并与“基地”组织之间联系紧密。
目前,除了利用个人信息进行电信网络诈骗案外,还存在通过网络精准营销等网络服务形式进行数据盗取和贩卖现象,甚至引发跨境网络诈骗活动。大数据时代数据的流通和使用在为经济增长贡献力量的同时,也为犯罪分子进行新型犯罪活动提供了方便。如何控制?防范?笔者认为有必要进行个人信息保护立法,从源头进行根治,进而从实质上控制犯罪的数量。
随着2003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推翻了萨达姆政权,伊拉克的混乱状态使得失去塔利班政权有效庇护的诸多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从阿富汗转战伊拉克,其中便包括“伊斯兰国”的前身“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该组织的前身“一神教圣战派”便是从阿富汗迁徙而来。而当前“伊斯兰国”从伊拉克和叙利亚也不断向南亚地区推进,重点地区便是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伊斯兰国”向南亚的渗透导致其与塔利班的矛盾加剧,甚至爆发武力冲突,且有愈演愈烈之势。2017年塔利班武装与“伊斯兰国”之间的武力冲突日趋频繁,如双方在阿富汗朱兹詹省交火数日,造成至少52名武装分子丧生。(10) 参见代贺、蒋超:《“伊斯兰国”与塔利班在阿富汗东部交火,上万家庭被迫逃离》,新华网,2017年11月28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7-11/28/c_1122019707.htm[2019-07-02]。 当前,阿富汗塔利班、巴基斯坦塔利班、“基地”组织、“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之间的恶性竞争,以及极端主义组织在西亚与南亚之间的跨境迁徙和流动,不仅对南亚地区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也对美国的中东和南亚政策构成严峻挑战。
美国对伊斯兰世界的战略在“9·11”事件之后主要集中于西亚的伊拉克和南亚的阿富汗—巴基斯坦,西亚与阿巴地区成为美国对伊斯兰世界战略的两翼。美国经常在中东与南亚之间徘徊,即伊拉克战略和阿巴新战略之间协调,但却经常顾此失彼。在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从阿富汗战争转向伊拉克战争,导致阿富汗塔利班卷土重来,而伊拉克的动荡则成为吸纳全球“圣战”分子、孕育“伊斯兰国”组织的温床沃土。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试图将反恐战略重心东移至阿巴边境地区,但伊拉克的持续动荡和叙利亚内战爆发则直接催生了“伊斯兰国”。2015年以来,美俄加大协同打击“伊斯兰国”的力度,但实体组织濒临被剿灭的“伊斯兰国”又继续在包括南亚阿富汗、巴基斯坦在内的广大伊斯兰世界的“边缘地带”进行渗透和扩张。事实表明,正是由于美国治标不治本的反恐政策的游移不定,极大地加剧了中东与南亚极端主义势力的恶性互动和此起彼伏,这也是南亚和中东地区伊斯兰极端主义发展的内在关联的根源之一。
二、南亚伊斯兰极端主义兴起发展的内在原因及其特点
“伊斯兰极端主义”这一概念的普遍使用虽始于20世纪90年代,但其实际上只是伊斯兰复兴思潮中的激进主义的极端形式。如前所述,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发展,与宗教的全球复兴、美苏争霸以及冷战后美国伊斯兰世界战略的失衡有着密切关联,而南亚国家,特别是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在其中扮演了相对重要的角色。具体到南亚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发展而言,除了国际大背景以外,还包括该地区自身的特点。南亚地区的国际关系、族群政治等往往与宗教政治挂钩,再加上受伊斯兰两大教派之间纷争整体性影响的不断加剧,使得南亚伊斯兰极端主义既具有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普遍共性,也有南亚地区的独特个性,其兴起发展有着如下内在原因。
(一)印巴冲突为南亚伊斯兰极端主义兴起创造了空间
受印巴分治影响的巴基斯坦国家建构和民族认同、印巴克什米尔争端等问题,既是滋生伊斯兰极端主义的重要因素,也是伊斯兰极端主义活动的主要空间。
随着印巴分治成为现实,巴基斯坦许多相对较小的民族也不断谋求实现独立,其中孟加拉国得以独立并获得了巴基斯坦的承认,而俾路支人的“建国”则因牵涉国家过多而遥遥无期。
南亚国家众多,民族与宗教多元,这是南亚的基本政治和社会生态。作为南亚地区大国的印度和巴基斯坦,自1947年根据联合国决议分治以来,双方围绕克什米尔的争端演变为数次兵戎相见以及旷日持久的对抗。二战后,《蒙巴顿方案》将英属印度通过宗教信仰的版图进行切割,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信奉印度教的印度和信奉伊斯兰教的巴基斯坦,印巴双方境内的许多信仰对方宗教的信徒集体性相互迁移,这种以宗教划线的分治方案深深影响了巴基斯坦。与印度不同,巴基斯坦完全是一个新的政治实体,巴基斯坦民族主义建构面临民族认同薄弱、境内较大的族群在印巴分治后继续寻求独立的分离主义等挑战。因此,巴基斯坦军人政府和文官政府整体上采取了利用伊斯兰教来塑造国家认同的手段,即打造一个“穆斯林民族”(巴基斯坦立国者真纳提出的概念)为主体的巴基斯坦国家,这既有利于彻底切割历史上的印度元素,也有助于通过共同的宗教信仰来整合各族群。
建国后,伊斯兰团体在巴基斯坦国家政治和社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并在二战后开始的宗教复兴浪潮中不断发展壮大,同时也成为巴基斯坦各政党争夺的对象。20世纪70年代以来,伊斯兰复兴的兴起特别是1979年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对巴基斯坦产生了强烈冲击,许多对政府心存不满的伊斯兰激进组织暴力倾向日趋严重,尤其是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边境地区,成为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等极端组织寻求渗透和扩张的重点。
通过分析研究南亚伊斯兰极端主义兴起、发展的内外部原因及相关极端组织的情况,不难发现其具有如下一些基本特点。
伊斯兰极端主义作为伊斯兰复兴主义思潮中的激进派别,自20世纪70年代异军突起,成为影响当代国际关系的重要力量,这与宗教在现代国际关系中的真正“登堂入室”有着密切关联。(4) 参见徐以骅:《宗教在1979年》,载徐以骅主编:《宗教与美国社会》(第十三辑),北京:时事出版社,2016年,第4页。 全球宗教复兴特别是伊斯兰复兴的标志性事件,对南亚产生了强烈冲击。1979年是宗教深度参与国际关系的转折点,教皇访问波兰、伊朗伊斯兰革命、沙特麦加大清真寺事件、苏联入侵阿富汗等被视为标志性事件(5) Christian Caryl, Strange Rebels : 1979 and the Birth of the 21stCentury ,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3.,而这些重大事件又多与伊斯兰教相关,这也反映了伊斯兰教在国际关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二)少数族群的民族分离主义是南亚伊斯兰极端主义生存的温床
郎西埃用图像性的体制-图像要素和功能之间的关系的体制,意指图像是事物直接记录在其身躯上的意指,是有待解读的事物的可见语言。将语词和图像从可见物和可说物之间做区分。[10]
1.孟加拉国的独立与伊斯兰极端主义
最后,运用大数据技术为企业财务内控管理制度调整提供依据。大数据技术的应用使得企业的数据分析能力有了很大的提升,这对于在财务内控管理中深挖企业的财务漏洞和风险有很大的帮助。通过大数据技术对于企业生产和经营中的财务数据进行挖掘和分析,对于企业财务资源的调配进行全面的审视,找出其中不合理,可以进一步改善的地方,从而帮助企业及时弥补财务漏洞,消弭财务风险,为企业的经营保驾护航。
选取36名于2018年5—6月在我院肝胆外科进行外科学临床学习的广西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专业2015级本科见习生作为研究对象。将其以随机分配的形式分为实验组与对照组,每组各18名学生,见习时间均为4周。两组学生在年龄、性别、基础学习情况对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见表1。
当年印巴分治时,孟加拉人因宗教信仰不同而主要分属印度诸邦和东巴基斯坦,为了打造以伊斯兰教为显著标志且与巴基斯坦有所区别,又能与印度境内信仰印度教的孟加拉人划清界限,1977年齐亚·拉赫曼(ZiaurRahman)提出了“孟加拉国民族主义”(Bangladeshi nationalism),取代了穆吉布·拉赫曼(Mujibur Rahman)建国初所提出的“孟加拉族民族主义”(Bengali nationalism)。“孟加拉族民族主义”从民族上只强调孟加拉民族,是一种世俗的单一民族认同;“孟加拉国民族主义”从民族上涵盖孟加拉国境内的所有民族,其核心认同是伊斯兰教,这也旨在说明印度境内信奉印度教的孟加拉民族不在孟加拉国的国族认同之内。(14) Taj Hashimi, “Bangladesh: The Next Taliban State?” February 9, 2005, https://mm-gold. azureedge.net/Articles/taj_hashmi/bangladesh_next_taliban.html [2019-07-02]. 此后,孟加拉国的国族认同建构实际上与巴基斯坦强调基于伊斯兰教的宗教认同相似,伊斯兰教在国家政治中的地位上升,为各种伊斯兰激进主义势力的兴起提供了条件。
在冷战后的民主化浪潮中,孟加拉国各种伊斯兰政党粉墨登场,各种政治势力频频采用伊斯兰话语来进行政治动员,其中包括曾高举世俗主义和社会主义大旗的“孟加拉国人民联盟”。不仅如此,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也在孟加拉国发展壮大,其典型代表是“伊斯兰圣战运动”(HuJI)。该组织从20世纪90年代初便主要开始在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活动。如前所述,“伊斯兰圣战运动”成立于抗苏战争期间,其目标从把苏军逐出阿富汗发展到把印度逐出克什米尔,1992年“伊斯兰圣战运动”孟加拉国分支“孟加拉伊斯兰圣战运动”成立,标志着该组织在孟加拉国的影响力不断上升。该组织在孟加拉开展了大量恐怖袭击活动,其目标包括推翻政权,建立实施伊斯兰教法统治的政权,并涉嫌于2000年展开了针对哈西娜·瓦吉德(Sheikh Hasina Wazed)总理的刺杀行动。2005年10月,该组织被孟加拉国取缔。(15) Colonel R. Hariharan, “Sheikh Hasina Overlooked Terror Festering in Bangladesh’s Backyard,” Daily O , July 12, 2016.
2.俾路支人的民族分离主义与伊斯兰极端主义
俾路支人主要分布在伊朗和巴基斯坦边境省份,属于伊斯兰逊尼派。俾路支人在伊朗和巴基斯坦都是少数族群,不仅如此,信仰逊尼派的俾路支人在伊朗还处于教派上的弱势地位。二战以后,俾路支人在伊朗巴列维王朝时代处境相对较好,巴基斯坦以伊斯兰教为主导的国家认同中也一定程度整合了俾路支人。随着伊朗伊斯兰革命的爆发,信仰逊尼派的俾路支人的宗教处境出现了巨大变化。随着伊朗强势输出革命,特别是带有两大教派冲突色彩的两伊战争爆发以后,伊朗俾路支人便成为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制衡伊朗的重要工具。20世纪80年代,受伊拉克支持的伊朗“俾路支自治运动”(BAM)登上历史舞台,其目标是寻求伊朗俾路支人的自治地位和经济处境的改善。随着两伊战争的结束,伊拉克对伊朗俾路支人自治运动的支持热情与力度逐步下降,该运动的许多领导人逃亡海湾阿拉伯国家,“俾路支自治运动”走向分裂与瓦解,其中“真主战士”(Jundallah)便是从其中分化出的组织。“真主战士”成立于2003年,属于逊尼派“圣战萨拉菲运动”,除了反对伊朗什叶派神权共和国政权以外,俾路支民族主义运动仍旧是其主要目标,重点是维护其人权、文化与信仰。(16) “Iran Hangs Sunni Militant Leader AbdolmalekRigi,” BBC , June 20, 2010.“真主战士”在伊朗的活动区域在靠近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边境省份,在巴基斯坦境内也开展了许多针对巴基斯坦军政目标的暴恐活动。就俾路支民族主义而言,其核心仍旧是自治运动,在整合伊朗与巴基斯坦俾路支人建立独立的俾路支国家方面,其活动和影响并不明显。
(三)南亚伊斯兰极端主义的特点
20世纪90年代以来,巴基斯坦脆弱的政治和经济环境为伊斯兰极端势力坐大提供了机遇,“巴一些政治、军事力量与极端主义势力相互交织在一起,致使‘9·11’后巴政府的严打举措难以切实施行且收效不大”,“极端势力在巴部落区有比较深厚的群众基础”,使巴基斯坦陷入了伊斯兰极端主义不断恶性膨胀的泥沼。(11) 参见方金英:《巴基斯坦伊斯兰极端主义新动向》,《现代国际关系》2007年第11期,第56—58页。 除了那些主要奉行民族分离主义的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以外,许多巴基斯坦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将矛头对准巴基斯坦什叶派的同时,也针对巴基斯坦领导人和政府目标进行暴恐袭击。例如,“坚格维军”(Lashkar-e-Jhangvi,,LeJ)是一个成立于1996年的逊尼派极端主义组织,它从具有强烈反什叶派倾向的“巴基斯坦西帕·萨巴哈”(SSP)组织中分离出来。该组织的名称来源于“巴基斯坦西帕·萨巴哈”的创始人之一、逊尼派教士哈克·纳瓦兹·坚格维(Haq Nawaz Jhangvi),他领导了诸多针对什叶派的暴力活动并最终于1990年遭什叶派武装袭击身亡。此后“坚格维军”的领导人里亚兹·巴斯拉(Riaz Basra)曾在1999年策划暗杀时任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12) Rory McCarthy, “Death by Design,” The Guardian , May 17, 2002.尽管巴基斯坦政府加大了对该组织的打击力度,但“坚格维军”在数位领导人被处死后依然十分活跃。“坚格维军”与阿富汗塔利班关系密切,近年针对斯里兰卡和阿富汗的目标以及巴基斯坦军警目标频繁发动暴恐袭击,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1.南亚伊斯兰极端主义目标多元交织
1971年,在印度的不断策动下,原属巴基斯坦一部分的东巴基斯坦宣布独立建国。东巴基斯坦得以顺利脱离巴基斯坦,一方面因为东西巴基斯坦之间自印巴分治起便从地理上被印度所隔离,巴基斯坦政府难以对东巴基斯坦进行有效的管治;另一方面在于孟加拉人是东巴基斯坦的主体民族,在印度的煽动与支持下独立倾向不断增强。孟加拉国独立以后,为了与以伊斯兰教为国家认同的巴基斯坦决裂,该国最初采取了遵循世俗民族主义的做法。由于独立之初的诸多困境,孟加拉国新政权的施政成效有限,经济、民生等问题严重,再加上20世纪70年代伊斯兰复兴运动风起云涌,孟加拉国政府很快便转向了伊斯兰教,加强了国家的伊斯兰属性建设。
南亚伊斯兰极端主义的目标主要包括推翻世俗政权、建立伊斯兰教法统治;打击什叶派力量;打造宗教民族主义,谋求自治、独立建国等。以上目标之间并非孤立,许多南亚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往往兼具多重目标。这些目标之间环环相扣,大大增加了治理难度。
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兴起与发展,与美国的中东、南亚政策有密切关联。随着苏军撤出阿富汗、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阿富汗陷入彻底的无序与混战状态,塔利班异军突起并控制了大部分国土。与此同时,本·拉登的“基地”组织在苏联撤军阿富汗以后,其发展便走向一个新的分水岭。1991年海湾战争后,伴随美国军队大规模入驻伊斯兰教“两圣地”(麦加和麦地那)所在的沙特,导致本·拉登及其领导的“基地”组织与美国和沙特王室政权迅速分道扬镳。由于本·拉登不能容忍“异教徒”对伊斯兰土地的入侵,美国取代苏联成为“基地”组织的头号敌人。本·拉登为代表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认为,美军和沙特王室的行为是对伊斯兰圣地的玷污。1999年,本·拉登在一次访谈中指出,美国在沙特阿拉伯的军事存在是其反美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那对整个伊斯兰世界都是一种挑衅”(9) RahimullahYusufzai,“Face to Face with Osama,” Guardian , September 26, 2001, https://www. theguardian.com/world/2001/sep/26/afghanistan.terrorism3 [2019-07-01].。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机构、设施频繁成为伊斯兰极端主义暴力袭击的目标。
南亚地区存在的领土争端、跨界民族和地理地貌等因素,为伊斯兰极端主义开展活动提供了契机,该地区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往往存在跨国、跨地区的复杂联系,或者属于同一个组织的不同分支,其跨国流动性使得对有关极端组织的打击较为困难。尤其是边界地区往往山脉相连,易守难攻,成为南亚国家政府统治的薄弱地带,极端主义的跨境流动日益常态化。
3.相关南亚国家政府对伊斯兰极端主义存在多重标准
其突出表现在对极端组织袭击什叶派的行为采取默许或无视的态度,对极端组织袭击敌对国家则持明显的支持态度。这种分歧和矛盾显然不利于南亚国家形成打击极端主义的有效合作,而长期存在的印巴冲突导致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南亚大国根本无法就打击极端主义进行合作,尤其是印度指责巴基斯坦支持和纵容伊斯兰极端组织袭击印度导致的矛盾,本身就构成了印巴矛盾的重要内容。相关国家利用教派冲突和国家间冲突,将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关切引入这些领域,从长远看其结果往往适得其反,伊斯兰极端主义最终会危害其自身的国家安全。
南亚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发展,与旷日持久的印巴冲突和以孟加拉和俾路支为代表的少数族群的民族分离主义息息相关,后者共同推进了南亚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发展与壮大。再加上南亚伊斯兰极端主义呈现的基本特点,使得南亚地区既促进了全球宗教复兴的发展并影响了美国对伊斯兰世界的战略推进,也极大恶化了该地区自身的政治与安全生态环境。
三、南亚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治理前景
南亚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发展和壮大,尤其是暴力恐怖主义的泛滥,给南亚和周边地区乃至世界都带来了极大的消极影响。第一,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组织和行为,严重恶化了南亚有关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族群和宗教生态,对这些国家的总体国家安全构成了巨大挑战,极大影响了国家治理水平的提升。第二,伊斯兰极端主义与南亚国家间的领土争端、少数族群分离主义运动等关系紧密,严重影响了南亚地区一体化的深入开展。第三,南亚成为“基地”组织、“伊斯兰国”为代表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和暴力恐怖组织全球扩张的“孵化器”,使得南亚地区在全球反恐格局中承受着巨大压力。第四,伊斯兰极端主义对于中国在南亚地区的利益和“一带一路”在南亚沿线的推进构成了巨大威胁。中国与巴基斯坦在推进“一带一路”框架的全方位合作上不遗余力,特别是“中巴经济走廊”具有极大的地缘战略意义,但巴基斯坦形形色色的伊斯兰极端组织对在巴中国企业及公民的暴恐袭击层出不穷,而瓜达尔港所在的俾路支省也面临带有极端主义色彩的民族分离主义运动。(17) 参见王天迷、丁雨晴、徐伟:《外国人进入俾省,需巴政府特批》,《环球时报》2017年6月21日。 此外,也有中国公民因卷入在巴进行基督教传教事件而遭遇巴基斯坦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的袭击,2017年6月2名中国公民被韩国基督教人士带到巴基斯坦进行传教活动而在俾路支省的真纳地区被绑架杀害。(18) 参见王黎明、杜海川:《这对把中国人带到巴基斯坦传教的韩国夫妇,还能神秘多久?》,《环球时报》2017年6月12日。 这使得中巴在协同打击“三股势力”,推进两国发展战略对接上找到了新的合作空间。虽然相关南亚国家出于政权安全的考虑而选择性地对部分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进行了取缔和打击,但整体成效相对有限。尽管如此,南亚国家在国际反恐合作以及促进国内政治和解方面的举措已取得一些成效,对促进该地区治理伊斯兰极端主义创造了一定的有利条件。
在社会治理系统共建共治中,协同治理是创新社会治理最基本的方式,也是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坚持系统治理的具体体现。由社会组织和公众参与的社会协同共治,既是党的领导、政府主导下的社会治理过程,也是多元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基本职能。在新时代,要想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目标,我们必须锐意改革,有所创新,坚持问题导向,把政府治理与社会协同和公众参与结合起来。因此,在创新社会治理中,必须确立多元主体的社会协同的重要地位,通过为社会组织和公众赋权增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多元主体在社会治理系统共建共治中的协同作用。
(一)跨国、跨地区合作是治理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必由之路
目前,印度和巴基斯坦已经正式成为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阿富汗成为上合组织观察员国,这既能促进上合组织新老成员国在打击“三股势力”方面进一步形成合力,又有助于通过上合组织的框架,进一步协调印巴等国在打击伊斯兰极端主义上的分歧。随着冷战结束以后中亚国家的纷纷独立以及20世纪90年代以来伊斯兰极端主义的蔓延,中亚和南亚地区的伊斯兰极端势力严重威胁有关国家的稳定与安全。在此背景下,上海合作组织的前身“上海五国”于2001年正式成立,在2017年吸收印巴加入之前,其成员包括中国、俄罗斯和中亚四国(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并拥有多个观察员国,其核心宗旨是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
2009年6月16日,上合组织元首理事会叶卡捷琳堡例行会议《公报》指出:“本组织成员国应提高在共同应对恐怖主义及其他安全威胁方面的协调水平。地区反恐怖机构应为此发挥核心作用。”(19)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联合公报》,上海合作组织官方网站,2009年6月16日,http://www.sectsco.org/CN/show.asp?id=232[2019-06-30]。 围绕合作打击“东突”等危害地区和平与安全的伊斯兰极端势力,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国际合作程度较高且共同利益居多,而中国与中亚山水相连,利于协同打击“三股势力”的军事行动和后勤补给。不仅如此,中国政府还与时任观察员国的巴基斯坦进行反恐军演。2010年7月,中巴联合反恐军演在中国宁夏举行。2017年,上合组织完成2001年以来的首度扩容,印度与巴基斯坦正式成为成员国。2018年5月,上合组织青岛峰会召开之前,印度与巴基斯坦同意在查谟与克什米尔地区落实2003年便已达成的停火协议。(20) 参见李东尧:《上合峰会前,印巴一致同意落实边境停火协议》,观察者网,2018年5月30日,http://www.guancha.cn/Neighbors/2018_05_30_458356_s.shtml[2019-07-20]。 不仅如此,印度还派出代表团赴巴基斯坦参加上合组织反恐会议,这反映了印巴在加入上合组织以后确实在保持克制,寻求在反恐和打击伊斯兰极端主义等问题上进行合作。同年5月28日,“上海合作组织—阿富汗联络组”会议在北京举行。6月,上合组织青岛峰会顺利举行,这是该组织扩容以后举行的首次峰会。峰会勾勒了未来的发展任务,有利于“结合形势变化推动新安全观在上合组织内达成共识,弥合印度、巴基斯坦加入后在反恐、去极端化中出现的认知差异,以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和可持续安全理念指导上合组织未来安全合作”,并就“阿富汗安全形势恶化问题”等加强合作。(21) 参见许涛:《青岛峰会以新安全观升级上合组织安全合作》,《光明日报》2018年6月16日。
(二)对伊斯兰极端主义和由此发展而来的暴力恐怖主义进行有效区分,采取不同策略应对
2001年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推翻塔利班政权后,在其大力扶持下建立了新政权。随着塔利班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边境地区逐步恢复元气及卷土重来,并对阿富汗政府军目标展开袭击活动,阿富汗问题更加错综复杂。塔利班过去曾庇护本·拉登及其领导的“基地”组织,但两者之间的目标和手段并不完全一致。塔利班是思想极为保守且带有部落遗风的伊斯兰极端组织,其目标是通过武力重新夺回阿富汗并建立实施伊斯兰教法的统治,具有反叛武装的特点。“基地”组织则是全球公认的恐怖组织,“‘基地’组织在全球范围发动‘圣战’,则是以伊斯兰教的名义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及其文化价值观宣战。显然,‘基地’组织只是把‘圣战’作为一种政治宣传和政治动员的工具,企图通过泛化伊斯兰‘圣战’来达到反西方目的”(22) 参见吴云贵:《解析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的三种形态》,《世界宗教文化》2018年第2期,第8页。 。
在盈余管理方面,张灵等(2015)认为上市公司如果聘请具有海外背景的独立董事,会控制和调节企业盈余管理程度。通过理论与实证研究都证实了当其他条件不变时,国有上市公司中具备海外背景的独立董事对盈余管理程度的控制和调节作用更强。原因在于,在国有企业中拥有海外背景的独立董事能够扭转信息不对称现象,切实维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控制好企业盈余管理程度。张灵等(2015)进一步研究提出,企业应合理调整董事会的结构,引进海外背景的独立董事,同时鼓励专职独立董事的产生和发展。
尽管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之间冲突不断,但阿富汗政府也注意区别对待塔利班和“基地”组织,对于“基地”组织进行严厉打击,而对于塔利班则将其视为政治和解的重要对象。2018年2月28日,阿富汗总统加尼表示,愿意在不设条件的前提下与阿富汗塔利班进行和谈,而在此之前他多次斥责塔利班是恐怖组织。(23) 参见杨舒怡:《态度逆转阿富汗政府愿不设前提与塔利班和谈》,新华网,2018年3月2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8-03/02/c_129820376.htm[2019-07-01]。 加尼总统态度的转变,说明了阿富汗政府在对于伊斯兰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认知上越来越务实。同年6月15日开斋节之际,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达成自塔利班政权垮台后的首度停火协议。阿富汗政府于6月7日宣布,从6月12日开始与塔利班停火一周左右,但停火对象不包括“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阿富汗塔利班则于6月9日宣布开斋节期间与阿富汗政府军停火三天。但是,“伊斯兰国”在阿富汗的组织则采取暴恐袭击的方式来予以回应,对楠格哈尔省首府贾拉拉巴德进行汽车炸弹袭击,造成至少26人死亡、54人受伤,死者包括塔利班武装人员和阿富汗安全人员。(24) 参见《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声称制造阿富汗东部炸弹袭击》,新华网,2018年6月17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8-06/17/c_1122996395.htm[2019-07-01]。 故而阿富汗政府依然对塔利班采取以打促谈的策略,2018年6月30日,阿富汗总统加尼在单方面延长停火期结束后,下令重启对塔利班的打击行动。(25) 参见《停火结束!阿富汗总统下令重启打击塔利班行动》,环球网,2018年6月30日,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8-06/12384641.html[2019-07-01]。 这反映了阿富汗政府、阿富汗塔利班、“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等方面在阿富汗的复杂博弈。
通过本综述,我们认识到脂肪不只是传统认为的储备器官,也可能是一个启动能量平衡调节的内分泌器官,因此,是否可以将瘦素作为肝病的常规/辅助监测项目,或作为一种治疗药物(治疗肥胖、不育症,抗肿瘤)等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随着“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大本营的“日薄西山”,其极端分子流散外溢、圣战迁徙、回流问题等会日益明显。“基地”组织与“伊斯兰国”的恐怖竞争也会在阿富汗愈演愈烈。在与国际社会一道严厉打击“基地”组织与“伊斯兰国”这两个国际公认的恐怖组织的同时,加强与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塔利班之间的对话,是阿富汗政府已经做出的正式选择。不仅如此,国际社会也加大了对阿富汗塔利班的对话力度,中国在其中也发挥了相应的作用。2019年6月,阿富汗塔利班负责政治事务的副首领巴拉达尔访华,双方就阿富汗和平进程及打击恐怖主义等进行了会谈。(26) 参见《塔利班高层访华引外媒关注:称中国扩大在阿富汗影响力》,参考消息网,2019年6月22日,http://m.ckxx.net/zhongguo/p/170787.html[2019-07-01]。 同年9月,阿富汗塔利班驻多哈政治办事处主任巴拉达尔及其数位助手访华,与中国外交部主管官员就阿富汗局势及和平进程进行了会谈。(27) 参见辛闻:《中国外交部证实阿富汗塔利班代表团近日来华沟通》,中国网,2019年9月23日,http://news.china.com.cn/txt/2019-09/23/content_75237007.htm[2019-09-24]。
(三)南亚地区去极端化的典型案例: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是南亚地区大国,该国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兴衰与巴基斯坦政府态度的转变存在着直接的联系。巴基斯坦的去极端化措施,既有国际社会去极端化的总体特点,也有基于本国国情的量身打造。巴基斯坦在立法、宗教学校教育改革、对极端分子的改造、反洗钱合作及国际合作等领域,不断探索该国的去极端化发展路径。巴基斯坦往往将去极端化问题与反恐问题统筹处理,即在很大程度上将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相提并论,这也反映了巴基斯坦所面临的极端主义威胁往往有着较强的暴力恐怖主义色彩。
腌出新鲜味:腌渍仔鸡首先要选好料,1只仔鸡,新鲜蒜苗500g,鲜大蒜200g,胡萝卜100g,芹菜段150g,香菜段100g,莴笋片80g,生姜30g,洋葱丝50g,味精20g,白糖10g,盐20g。先把大蒜和生姜拍破,再将所有的青菜料放入盆内,然后用手轻轻搓揉,待流出少许蔬菜汁以后,再放入剩余的调料拌匀成腌汁。把洗净的仔鸡放入腌料盆里,再把腌料填进鸡腹内,然后用保鲜膜密封好放入保鲜柜里,腌渍2小时至鸡肉入味。
具体而言,巴基斯坦的去极端化基于法治基础,通过反恐相关的立法来奠定该国去极端化的法律基础,即通过《反恐怖主义法》《调查与公平审判法》《保护巴基斯坦法》《国家反恐局法案》及其修正案为基础,辅以其他法规,构成反恐及反极端主义的基本框架。巴基斯坦基于对历史上形成的独特的宗教学校的状况,注重加强对宗教教育的矫正,最大限度改变其长期游离于国民教育体系之外的现状。这是从源头上对于极端主义生成所采取的预防措施。巴基斯坦对于所抓获的极端分子的改造措施,则体现了对极端主义所采取的事后“亡羊补牢”之举。
除此之外,巴基斯坦通过加强多领域的国际合作,构建去极端化的国际网络。在阻断恐怖融资方面,加强与国际及亚太地区反洗钱组织的合作,力求促进自身的金融监管改革以达到国际标准。在去极端化合作对象上,注重与南盟的沟通与协调,将巴基斯坦的去极端化视为南亚地区去极端化的组成部分,促进地区协作打击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巴基斯坦尤为注重加强与中国的去极端化合作,积极加入上合组织并热情参与中巴经济走廊建设,通过军事安全与经济发展相结合的方式来促进去极端化的发展。巴基斯坦还高度关注中国在新疆的去极端化成就,重视去极端化的中国方案所带来的启示意义。(28) 参见《访华外国使节盛赞中国新疆发展成就和反恐、去极端化成果》,新华网,2019年7月4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9-07/04/c_1124712289.htm[2019-10-20]。 尽管巴基斯坦的去极端化措施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客观来说仍有巨大的提升空间。巴基斯坦的去极端化只是南亚地区去极端化的一个缩影,未来南亚国家的去极端化离不开各自国内政治经济环境的优化,并加大与大周边国家及相关国际组织的通力协作,在吸收他国去极端化成果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取得应有的成效。
就南亚地区当前针对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治理及去极端化合作的诸多措施来看,该地区在打击包括宗教极端主义在内的“三股势力”上取得了一定成效,特别是印巴加入上合组织以后,上合组织从地缘上对于我国新疆及中亚、南亚等地伊斯兰极端主义的遏制逐渐成片。通过严格区分极端主义与恐怖主义,为诸多极端组织减少暴力行为,参与国家的和平进程、政治进程等提供了契机,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恐怖主义势力。如前文所言,正是由于南亚地区民族、部族、宗教、教派、领土等方面的内外矛盾极为突出,再加上历史上殖民大国和当代全球大国的深度介入,南亚地区的安全治理仍有较长的路要走,各国的去极端化实践仍然任重道远。作为全球伊斯兰极端主义的重要发源地,南亚地区的宗教极端主义治理模式、经验、教训等,对于其他地区也具有理论参考价值与实践借鉴意义。
②锚杆配件:采用高强度锚杆螺母为M24×3,配合高强度调心球垫和尼龙垫圈,采用拱型高强度托盘,承载能力不低于30 t。
四、结 语
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泛滥已成为全球公害。作为全球伊斯兰极端主义若干关键性节点事件的发源地,南亚地区复杂的地理地貌、碎片化的国内政治与族群生态,仍旧是伊斯兰极端组织生存的绝佳土壤。不仅如此,南亚非伊斯兰国家中主导宗教的极端化挑战,也进一步激发了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激烈回应。由于南亚地区伊斯兰极端主义与暴力恐怖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极大增加了该地区去极端化和恐怖主义治理的难度,南亚国家在去极端化方面的地区合作仍然有限,持多重标准的现象仍然明显。
尽管如此,但在多边机制下促进去极端化和反恐合作已成趋势。随着印巴正式加入上合组织,阿富汗成为上合组织观察员国,中国、俄罗斯、中亚与南亚在打击“三股势力”方面的跨地区合作将更加紧密。而未来南亚地区的去极端化实践有力结合该地区的鲜明特点,诸领域多管齐下加强综合治理,将有助于最终取得明显成效。
[作者简介] 钮松,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上海高校智库复旦大学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上海 邮编:200083)
[中图分类号] D815.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484(2019)06-0095-15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全球伊斯兰极端主义研究”(编号:16ZDA096)
[责任编辑:杨泽军]
标签:南亚论文; 伊斯兰极端主义论文; 极端组织论文; 恐怖主义论文;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