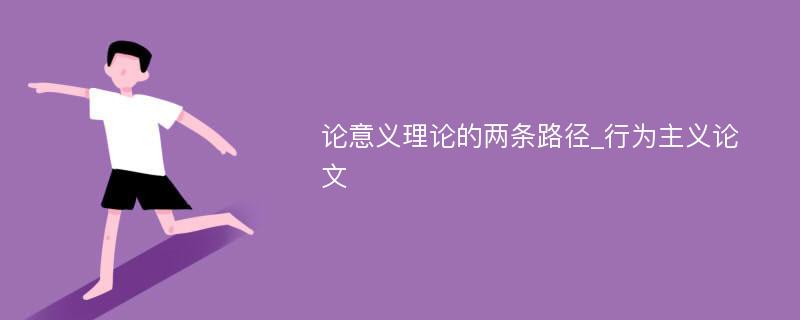
论意义理论中的两条路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条论文,路线论文,意义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意义理论在上世纪后期曾经是哲学讨论的一个核心领域,并成为语言学、逻辑学、认知科学和心理学的交叉研究领域;但它是一个非常复杂而又混乱的研究领域。D.刘易斯在谈到意义理论时指出:“我区分两个主题。首先,可以把可能的语言和语法描述成一种抽象的语义系统,藉此我们把语言中的符号与我们周遭的世界关联起来。其次,通过心理学和语言学事实的描述,任何抽象的语义系统都是被某人或某群体使用着的一个具体的系统。混淆这两个主题只会带来迷惑。”(Lewis,D.,p.19)根据上述区分,关于意义理论的讨论实际关涉两部分内容:(1)意义理论旨在为某个符号系统中的语词和句子指派语义内容,它所要回答的问题是“表达式的意义是什么”;(2)意义理论旨在解释某人或某群体是如何赋予语言中的符号以其应有的意义的,它所要回答的问题是“如何根据语言共同体的成员的心智状态和语言环境来解释被使用的语言符号的意义”。
一、意义理论中的两条路线
D.刘易斯所作区分的价值在于:点出了几个与意义理论密切相关的关键词——语言、世界、心理学与语言学事实以及语言共同体。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看,语言共同体似乎可以包含发生在内部成员之中的那些心理学和语言学事实。有鉴于此,可以恰当地认为意义理论的研究应该是关于语言、世界和语言共同体的。在D.刘易斯看来,第一类意义理论是通过语言与世界的关系来揭示语言的意义是什么,而第二类意义理论是为了解决语言学习与语言共同体的问题。赞成此种区分并非是没有道理的:唐纳兰关于限定摹状词的指称性使用和归属性使用的区分(cf.Donnellan,pp.281-304),以及维特根斯坦在图像论和语言游戏说中的相关论点(cf.Wittgenstein,pp.7-51;参见维特根斯坦,第3-19页),似乎都暗示了这种区分。事实上,这也是20世纪语言哲学讨论意义问题的两条基本路线。路线的不同一定会伴随着论争。意义理论研究中的这种路线论争体现为何者更基本的问题。换言之,这种论争也可以表述为对以下问题的不同回答:到底是语言共同体的成员在习得语言后,通过他拥有的语言能力来给出语言表达式的指称,进而确定语言与世界的关系,还是任何语言学习者只有在正确地建立了名称、语句和对象、事实等语言符号与世界的关系之后,才算是掌握了语言的意义,从而也才能与其他成员进行有效的沟通。如果主张前者,不妨把这种意义理论称之为“语言-共同体”基本论;如果主张后者,可以相应地称之为“语言-世界”基本论。
维特根斯坦的思考在意义理论的研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的研究鲜明地体现了意义理论中这两条路线的论争。在《逻辑哲学论》中,如果问,语言是什么?则答案是:“命题的总体是语言。”(Wittgenstein,p.35)若问命题又是什么?答案是:“有意义的命题是思想。”(ibid)那么思想呢?“思想是事实的逻辑图像”。(ibid,p.19)你对事实说点什么呢?“世界是事实的总体,而不是事物的总体”。(ibid,p.7)在这个问答游戏中,早期维特根斯坦基于语言、思想和世界的逻辑同构关系建立了他的意义理论,因为在他看来,语言的意义或者说命题的意义就是命题所对应的思想或世界中的事实。很显然,《逻辑哲学论》中所建立的意义理论是基于语言和世界的关系确立的,因此早期维特根斯坦的思想可以归于“语言-世界”基本论。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可以归于“语言-共同体”基本论。《哲学研究》在开篇就拿奥古斯汀的语言观开刀。我们是通过“指物识字法”(参见维特根斯坦,§1、6)的方式让孩子学会语言的吗?指物识字法“的确描述了一个交流系统,只不过我们称为语言的,并不都是这样的交流系统”(维特根斯坦,第5页),因此认为“语词的意义就是它所代表的对象”这样一种意义观并不能完全地适用于我们的语言。我们不能单独地看一个语词的意义,而要在这个语词的使用中来考察它的意义,因此,“教孩子说话靠的不是解释和定义,而是训练。”(同上,第6页)语言共同体的成员在学习语言时的活动,以及在这个活动中所关联的心理学和社会学事实,这些因素才是揭示语词的意义时应该最先考虑的。如果上述理解正确的话,后期维特根斯坦的意义观便更倾向于“语言-共同体”基本论。下文将进一步对两条路线上的代表性理论即指称式的意义理论和行为主义的意义理论展开讨论。
二、指称论与意义理论
长期以来,有一种观念在研究语言的哲学家那里颇受欢迎,即认为一个完整的表达式的意义应该是一类特定类型的实体,因此意义理论就是把语言中的表达式和作为其意义的实体一一配对起来,而意义理论的中心任务则是说明可以用什么类型的实体来作为完整表达式的意义。当然,表达式和实体的配对是通过指称理论实现的,而什么类型的实体可以承担这样的任务则取决于理论始作俑者的本体论态度。于是,一个唯名论者会认为能被指称的只有殊相,一个实在论者会认为普通名词也可以指称共相,一个经验论者会认为表达式所指称的只能是原始的感觉材料,而一个观念论者则会认为表达式也可以指称思维中的抽象对象。如上所述,指称理论对于上述形而上学态度和认识论态度是保持中立的。然而,这样的指称理论貌似有强大解释力,却不可避免地伴随着一种危险:如果什么样的哲学态度都可以在指称理论中找到容身之所,那么指称理论也就蜕变成了一个没有实际内容的工具。为了和这种广泛意义上的指称理论相区别,笔者把经由弗雷格、塔斯基等人的工作所建立起来的、解释词项指称的理论称之为“指称论”。
指称论的核心是弗雷格关于“真”和“真值”的讨论,因为弗雷格认为根据语境原则句子才是承担意义的最小单位,而句子的指称就是真值。弗雷格在《思想》一文中探讨了“一个思想的真”与“真本身”。就后者而言,弗雷格肯定不是一个符合论者,因为把真本身看作是反映物与被反映物之间的一种符合关系意味着可以对这种符合关系是否为真再进行追问,从而陷入无穷倒退。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弗雷格指出“‘真’一词的内容是完全独特的,不可定义的”。(Frege,p.327)但是,这是否意味着弗雷格放弃了通过语言-世界的模式来揭示语言的意义呢?并非如此。尽管真本身不是对一种符合关系的断定,但是一个思想的真确实是在进行某种断定。弗雷格区分了思想(思维对语句意义的把握)、判断(对思想的真的肯定)和断定(对判断的表达)。(cf.ibid,p.329)很明显,“真”出现在判断这个环节。但是这种区分却存在着一个很明显的问题:思维是依附于主体的,而思想的真却不是主体所规定的,那么一个依附于主体的思维是如何把握不为主体所规定的东西的呢?事实上,弗雷格在这里实现了两个跳跃:一个是从思维所能把握的东西跳跃到思想,一个是从思想跳跃到思想的真。弗雷格对前者的说明语焉不详,而对后者的解释也存在很大的问题。举例而言,即使某人承认“某朵花是红的”表达了一个思想,即把一个如此这般的对象(某朵花)归属于一个分类范畴(红);但是,当肯定“‘某朵花是红的’所表达的思想是真的”时,他是不是也把肯定理解成把作为对象的某个思想归属于一个分类范畴(真)?弗雷格在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上陷入了左右为难:一方面,弗雷格认识到“我在这个思想上加上真这种性质,这似乎对这个思想没有添加任何东西”(Frege,p.330),因此“是真的”不同于“是红的”这类谓词;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把“是真的”看作一个谓词,从而把思想分别归属于两类范畴“真”和“假”(弗雷格甚至把这两类范畴对象化为真值),却能为语言分析带来极大的便利。
我们现在都知道,从弗雷格以后,人们普遍地认为宣称句的指称就是它的真值,即真或假。现在看来,弗雷格这一指称观至少具有以下三方面的理论优势:第一,真值将我们对句子的认知结果对象化。毕竟宣称句的基本功能就是向不同的主体传达信息,而要认知所传达的信息首先就要弄清楚它们的真假。第二,通过把真值作为句子的指称,我们可以抛弃命题或事实这些含混的概念,进而把数学中的函项概念引入自然语言中的语义分析中来。例如,弗雷格把谓词和命题联结词在语义上都解释为真值函项。(cf.ibid,pp.55-78)第三,确立真值作为句子的指称使得语义上的组合原则变得简单明了。组合原则的基本思想就是整体的值是由部分的值所确定的,因此一个句子的指称也应该是由构成这个句子的语言成分的指称所确定的。因此,尽管在“真本身”的讨论上弗雷格不是符合论者,但是通过句子指称真值这一观点,弗雷格还是可以把各种语言成分和世界中的某类事物之间进行配对:专名配对它所指称的对象;谓词配对满足其所标示的性质或概念;句子配对真值。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弗雷格的意义分析仍然遵从了语言-世界模式,只不过他所描述的是一个由对象(包括抽象对象“真值”)和概念构成的特殊的形而上学世界。
对于弗雷格指称论的彻底批评来自于蒯因。首先,蒯因认为弗雷格混淆了指称理论与意义理论。正如蒯因所指出的:“意义理论的主要概念,除了意义概念本身之外,就是同义性、意思和分析性(根据意义而为真的真理)。另一个概念是衍涵式或条件句的分析性。指称理论的主要概念是命名、真理、指谓和外延。另一个概念是变项的值的概念。”(《蒯因著作集》第4卷,第119页)可是,这两个领域有时候并不是那么严格区分的,因为总是有人倾向于把不同领域的概念拿出来发展成一套自圆其说的体系。较好的自圆其说,如弗雷格的意义理论,不可避免地会涉及指称概念:名字给对象命名,语句指称真值;与此同时,它也会谈论意义理论中的一些概念,例如专名的意义就是对象的呈现模式,而句子的意义就是它所表达的思想,“a=a”和“a=b”有不同的意思。然而,弗雷格在谈到命题态度语句时却指出“that-从句”所指称的不是真值,而是这个句子所表达的思想。(cf.Frege,p.154)但是根据之前的分析,思想是对语句意义的把握,而真值却是语句的指称。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其根源在于,在弗雷格那里,真的断定是基于对思想的把握,但是命题态度语句所表达的思想却包含了主体对另一个“that-从句”所表达思想的态度。以上情形使得确定命题态度语句的真值的难度加大了,因为“that-从句”所表达的思想具有归属于某个主体的特征。例如,如果张三没有获知邓丽君病逝的消息,那么尽管邓丽君还活着是一个假的事情,而且张三也不会相信一个假的事情,但是“张三相信邓丽君还活着”这个语句仍然是真的。很显然,在命题态度语句中,弗雷格指称论的缺陷被放大了:思想是一个远远没有被澄清的概念,因此真值的确定(对思想的肯定)也没有在弗雷格的理论中得到满意的解释。
其次,蒯因对弗雷格指称论的批评还体现在他的指称不确定性论证中。以专名“卡斯特河”为例,它到底是指称某个瞬时的空间片段a,还是指称两天后地理位置与a一致的空间片段b,亦或是与a包含相同水分子的c?蒯因指出,a和b具有同河关系,而a和c具有同水关系。那么,到底“卡斯特河”是指称a或b,还是a或c呢?这取决于说话者所采用的同一性标准。故而,指称式意义理论并不总是像它看上去的那么清楚,它无法回避意义理论中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同一性(同义性)问题。(参见《蒯因著作集》第4卷,第65-77页)
事实上,蒯因的批评不仅对坚持“语言-思想-世界”同构的概念论者适用,它更是指向那些通过“语言-世界”模式解释语句意义的经验论者。指称式意义理论包含了一个基本假定,即语词的所指就是它的意义。按照弗雷格的分析,真值就是语句的所指,故而真值就是语句的意义。然而,人们是如何断定语句的真值的呢?经验论者会认为,断定语句的真值实际上就是要在经验上找到确证它或否证它的方法。为了贯彻这种意义证实论,卡尔纳普更是“详细地规定了一种感觉材料语言,并且指出怎样把有意义的话语的其余部分逐句地翻译成感觉材料语言”。(《蒯因著作集》第4卷,第44页)正如蒯因所指出的,意义证实论的错误在于认为“每个陈述孤立地看是完全可以接受确证和否证的”。(同上,第46页)在类似的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指称式意义理论的错误在于,它认为每个出现在句子中的语言成分都可以根据经验孤立地确定所指,然而蒯因的不确定性论证推翻了指称式意义理论这一基本假定。这就是坚持语言-世界反映论模式的指称论所遭遇的最大挑战:仅仅根据原始的感觉经验,我们既无法确定名称的所指,也无法确定句子的真假,或者说证实与证伪。
三、行为主义与意义理论
行为主义的意义理论发端于美国。其代表人物布龙菲尔德认为:“说话的人用语言形式来说话,引起听话的人对客观环境作出反应;这个环境和对环境作出的反应就是这个形式的语言的意义”。(布龙菲尔德,第192页)蒯因则把采取这一态度的动机阐述得更为清楚:“我们每个人都是从人们相互沟通、交流中,通过可见的谈话动作从他人那里学会自己的语言的。从语言学上说,因而也是从概念上来看,只有那些可公共谈论的、可经常谈论并可用名字标志和学习的事物才是处于最中心的事物。语词首先便是用之于这些事物的。……(然而)外间事物归根结底是通过我们身体的作用而被认知的。我们关于物理事物的谈论的经验意义也是受这个命题限制的。”(《蒯因著作集》第4卷,第199-202页)显然,对行为主义者来说,环境和对环境作出的反应才是研究语言意义的出发点,而揭示说话者(听话者)与外界环境之间的刺激-反应模式,才是研究语言意义的正确方式。在此基础上,蒯因提出了著名的自然主义-行为主义论题(简称NB论题):“语言是一种社会技艺。在开始学习语言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完全依赖于主体间可资利用的关于说什么和何时说的提示线索。因此,除非意义说的是人们公开应对公共社会中可观察的刺激所具有的种种倾向,否则没有任何道理为语言表达配置意义。”(Quine,p.Ⅸ)
较之于指称论,行为主义意义理论摈弃了通过“语言-世界”这样一种反映论模式来揭示意义的途径。反映论的基本模式是将语言表达式与外部世界中的事实或事物相对应,以期揭示它们的意义。行为主义者为什么要放弃“语言-世界”这一反映论的基本思想呢?我们不妨先来看看行为主义意义理论的代表者蒯因是如何走向这一选择的。在反映论的模式中,“事实”这一概念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蒯因对这样一个自明的概念却表达了自己独特的看法:“一个比较规整的计划是设定一些事实作为与真句子整体相符的东西,但这依然是预先布置的勾当。描述世界确实需要大量的对象,具体的和抽象的,但是事实所起的作用不会超过它们对一种符合论貌似有理的支持。”(《蒯因著作集》第6卷,第524页)不难看出,蒯因想要表明事实这个概念与我们对外部世界的描述和解释无关,即与认识上的真假无关。可是,没有了事实,我们是不是就不能谈论语句的真假,不能谈论语言之外的事实呢?并非如此。蒯因认为,尽管不承认事实这类本体论概念的存在,但我们还是可以谈论事实性:“一个规范用语的事实性将随着它与物理学用语的靠近而增加。例如,较之于生物学用语,化学用语更加靠近物理学用语,因而也比前者更加具有事实性。”(Gaudet,p.10)
蒯因区分事实与事实性这两个术语,主要是想摆脱心身二元论的基本假设,进而取得与其自然主义、物理主义的立场一致。在蒯因看来,如果我们使用“事实”来谈论语言外部的实在,那么人们就会很自然地跟随笛卡尔的进路去承认一个与外部实在不同的心智世界。然而,“笛卡尔在本体论上的心身二元论是一种不易坚持的立场,凭借何种机制,心和身中的一个作用于另外一个?”(《蒯因著作集》第6卷,第616页)蒯因通过指称不确定性论证、翻译不确定性论证,强有力地说明了心身符合论以及指称式意义理论都是站不住脚的。一元论显然可以方便地避免上述问题,蒯因的一元论就是他的物理主义:“什么是物理主义?简单地来说,如果用时空区域来描述的物理状态上没有差别,那么在事实上也就不存在有差别。”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蒯因认为,“物理主义就是唯物主义,除开承认数学的抽象对象外,它是直截了当的一元论。”(同上,第565页)如此看来,事实是存在的,至少物理学事实是存在的。那么蒯因为什么还要引入事实性这个概念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考察他对事实的解释:“我们已经论证过,两个相互竞争的翻译手册可以公平地地处理所有的行为倾向,并且在这样的情形下,不存在有所谓的事实以说明哪个翻译手册是正确的。我们这里所说的事实不是一个超验的或认识论上的概念,甚至也无关于证实。它是本体论的,是关于实在的问题,在我们关于世界的科学理论中可以用自然主义的方式把它接受下来。”(同上,第27-28页)真是非常有趣:尽管存在有物理学上的事实,但是它却不是一个认识论上的概念,因为它与真假无关,甚至与证实无关。这显然与传统认识论有显著的差别。
正是通过事实与事实性这两个术语的区分,蒯因划开了本体论和认识论这两个领域。他指出:“我赞成有一个清晰的标准借以确定一个理论的本体论承诺,但实际上要接受什么样的本体论却仍然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对此,最直接的忠告是宽容和实验精神。”(同上,第4卷,第27页)于是,事实和本体论变成了一个选择问题,它不直接关乎于认识上的真假:“我们可以在不损害任何证实的情况下变更自己的本体论,不过这样做时我们就从我们的基本粒子转向了其他某种代理方式……从而重新解释了什么能被称为事实的标准。而事实性这个概念,就像重力和电荷一样,是内在于我们关于自然的理论之中的。”(同上,第6卷,第28页)事实性是内在于科学理论的,因此事实性的标准是可以随着科学理论的变化而变化的。这就是蒯因的自然主义立场:认识论应该在自然科学内部来说明我们是如何获得关于世界的丰富而又正确的知识的。正是在此意义上,蒯因会认为:“也许我们最初的关注是与句子的真及其真值条件相关的,而不是与词项的指称相关。如果我们接受这种态度,指称问题和本体论问题就不再是主要的了。本体论的规定在确定理论语句的真值条件时会发挥作用,但是其他不同的本体论规定也能够同样地发挥这样的作用。(因此)由于指称问题所引发的自然语言的不确定性就更容易被原谅了。”(Gaudet,p.14)显然,对于人们的认知或语句的真假而言,指称问题和本体论上的实在都不是最主要的,当下的物理学理论中所蕴含的事实性概念才是起决定性作用的。这大概就是蒯因拒绝通过“语言-世界”这一反映论模式来解释语言意义的最终原因。
哲学认识论不是凌驾于自然科学之上的,例如告诉我们心身是如何相互作用的;相反,在蒯因的自然化认识论中,认识论本身就作为心理学的一章包含在自然科学之中。蒯因的观点不仅与笛卡尔认识论不同,它与传统经验论者也是不同的,尽管人们通常认为他还是一个经验论者。传统经验论认为理论语句(词项)的意义可以还原成观察语句(词项)的意义;进一步通过观察,由独立于语言之外的客观世界决定这些语句的真值,从而理论语句和观察语句的意义也被确定下来。而自然化认识论拒绝从自然科学外部的客观世界中寻找理论语句和观察语句的意义;外部的实体不是自然科学必须借助的东西,只有在自然科学内部清晰的概念才能预设它们的存在。毋庸赘言,自然主义认识论完全放弃了通过“语言-世界”的反映模式来解决语言的意义问题,因为本体论的假设无助于解释我们是如何获得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的,因而也就无助于解释语言(作为表达知识的载体)的意义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持有行为主义意义理论的人都是自然主义者,因为他们都是秉承着观察和实验的精神,通过自然科学的研究方式来研究人的语言行为,并解释语言的意义问题。
以蒯因为代表的行为主义者放弃了语言-世界模式,那么他们的意义理论又有什么样的内容呢?行为主义意义理论主要是通过“刺激-反应”模式来解释语句的意义。蒯因在谈到场合句的刺激意义时说:“给定一个说话者,说一个刺激σ属于句子S的肯定性的刺激性意义,当且仅当,存在有另一个刺激σ′使得:这个说话者在给予刺激σ′后被问到S,他不赞同S;而他在给予刺激σ后被问到S,他会赞同S。我们只需要把上面定义中的‘赞同’和‘不赞同’互换位置就可以类似地定义否定性的刺激性意义。同时,我们把刺激性意义定义为由肯定性的刺激性意义和否定性的刺激性意义两者构成的有序对。”(《蒯因著作集》第4卷,第226-227页)很显然,刺激性意义取决于语言共同体内的语言学习行为,取决于说话者面对刺激时的心理反应。戴维森把蒯因的这一观点概括为意义理论上的“近端论”。戴维森认为:“我们关于世界的知识直接或间接地依赖于下述因果序列的描述,它的起点是兔子跑过或胃部痉挛这样的事件,通过神经系统的传达到达它的终点——信念。在这个因果链条中,是在什么地方使得我们的信念被给予了特定的内容,并让语词获得了它们的意义?……一个聪明的、为蒯因所赞同的折中做法是把意义和内容与知觉神经的刺激连结在一起。”(Davidson,1990,p.68)戴维森认为,就语言的学习来说,刺激发生在这段因果链的任意地方都是可行的,因为只要有刺激在这段因果链上出现,父母总是可以通过奖励和惩罚使婴儿学会在特定的场合使用合适的语词。但是,就意义或证实而言,刺激发生在这段因果链的哪个地方就不再是无关紧要了。意义或证实出现在因果链的起点可以称为关于意义或证实的“远端论”,反之则称为“近端论”。(cf.ibid,pp.72-73)蒯因显然持有近端论的观点,因为他认为决定一个观察句的意义是它的刺激意义,是主体在某种刺激下对这个句子作出肯定或否定反应的倾向,而不是引起这种刺激模式产生的外部对象或事件。(参见《蒯因著作集》第4卷,第225-229页)
蒯因关于意义证实的近端论遭到了戴维森的批评,因为在刺激模式和外部世界之间存在一条不可跨越的间隙。设想“缸中脑”的思想实验:“被疯狂的科学家所控制的放在容器里的大脑,可以产生他们任意想要得到的世界,尽管客观世界并非如此。”(Davidson,1990,p.74)类似的批评也为语义外在论者(即意义证实的远端论者)所给出,例如普特南的孪生地球论证。在戴维森以及远端论者看来,观察句的刺激意义仅仅是观察者本身对刺激模式的一种反应,它是内在于主体内的,因而不是主体间可量度的。蒯因的行为主义意义理论本来是以反对意义理论上的内在主义的面貌而出现的,但却遭到了和内在主义同样的批评。戴维森指出,蒯因的行为主义意义观实际上包含了经验主义的第三个教条,“不能把图式和内容的二元论、起组织作用的系统和某种有待于组织起来的东西的二元论,变成某种可以理解和可以为之辩护的东西。它本身是经验主义的一个教条,即第三个教条。”(ibid,1985,p.11)当然,蒯因后来解释说,他只是把概念图式当成日常语言的,因此他所设想的东西“不是概念图式、语言和世界的三合一,换言之,我和戴维森一样是借助于语言和世界来进行思考的”。(《蒯因著作集》第6卷,第44页)根据蒯因对刺激意义的解释,语言当然就是观察句,而世界就只能解释为“感官接收器的触发”。然而,诚如之前所论证的,感觉接收器的触发和外部世界存在有间隙,因而刺激模式是如何在主体内和主体间同一的,仍然是刺激意义理论需要解决的问题。正因为如此,蒯因指出他的经验主义不是一种真理论,而是一种证据理论:“如果把经验主义理解成为一种真理论,那么戴维森作为第三个教条归咎于经验主义的那种东西,是被正确地归咎了,也被正确地否定了。……不过,经验主义作为一种证据理论,在排除了两个教条之后,仍然与我们在一起。”(《蒯因著作集》第6卷,第42页)为了反对超验的概念,蒯因用经验主义拒绝了理性主义;为了反对还原论,蒯因用无教条的经验主义拒绝了事实,继而拒绝了真。在进行了这些步骤之后,最后剩下的只有语言以及为语言的意义提供解释的经验证据理论。在这里,我们不禁要问,没有了事实和真的证据理论到底是什么?又是什么理由使得基于这种证据理论的意义理论是合法的?
四、回到经验
指称式意义理论让我们建立了一个“语言-世界”的反映论模式,然而行为主义者却告诉我们本体论上的世界是被假设的——实体是被设定的,而事实也不是充当判断语句真假的真正标准。对于行为主义者来说,世界不论其存在与否,都离我们太遥远;与我们接近的并且能为我们所依赖的只有经验,即感觉接收器的促发。于是,行为主义意义理论构造了一个“语言-共同体”的意义生成模式,但是我们一旦进入这种意义生成模式的细节,就会发现严重问题。在蒯因的行为主义意义理论中,感觉接收器受到的刺激与说话者的倾向之间的关系是澄清语言意义问题的最基础步骤。但是,在明显存在有兔子的场合下,儿童学会自动地发出“兔子”这个词,或者在询问这个词时表示同意,这并不意味着他就学会了对象性指称,也不意味着他就把握了兔子这个概念。当一只兔子出现在儿童面前,他的视觉、听觉、嗅觉、触觉甚至味觉都收到了不同种类的刺激,甚至他可以像蝙蝠或科学仪器那样感受到超声波或红外线的刺激。人类确实不缺乏获取刺激的途径,但是根据接收到的刺激识别出对象却是另一个问题。如果说对象的识别是这类理论的第一个难题,那么人类是如何通过语言学习拥有概念能力的,则是这类理论不可回避的另一个难题。蒯因的行为主义意义理论把观察句的意义建立在说话者对某类刺激模式的赞同或不赞同之上。然而,对说话者自身来说,他是如何对刺激模式分类的?他又是如何把之前的分类方式应用到未来可能的经验解释中去的?这些问题绝对是不可回避的,因为接受刺激的能力每一种动物都有,有时候它们甚至有比人类更强的能力;但是这些动物却不能习得人类的语言,不能拥有人类的概念能力,不能像人类一样去识别对象。
谈论原始的经验是合法的,毕竟任何人无时无刻不在感受着感觉接收器的促发;但是,说这些经验能够构成一种证据并用作构建意义理论的基础,这却是一个值得商榷的看法。与蒯因的态度类似,C.I.刘易斯也认为语言的意义和知识的可靠性只能从原始的经验出发;然而,与之不同时是,C.I.刘易斯强调了原始经验和经验证据之间的差别。他指出:“在我们的认知经验中存在有两类因素,一类是直接被给予的、呈现于心灵的感觉材料,一类是用以表达思想活动所需要的形式、结构和解释。”(Lewis,C.I.,p.38)C.I.刘易斯认为经验知识就是将这些先验概念应用到经验之上而产生的结果;换言之,经验知识就是借助于先验概念而形成的对经验的解释。很显然,原始的感觉经验不能独立地构成经验证据或经验知识。举例来说,我们用“这”来指向一个直接的感官呈现,如一张桌子给我的眼睛带来的刺激,这个过程不涉及真假的问题;但是我们如果用“这只兔子”来指向刚才的感官呈现,就有了真假的问题,因为它涉及句子“这是一只兔子”的真假判断。显然,后者才能构成经验证据或者说它是一种经验知识。正因为如此,C.I.刘易斯说“(经验中的)实在比经验更加规整,因为实在是经过分类后的经验”。(ibid,p.367)事实上,C.I.刘易斯认为任何能被看作是实在的事物都是通过概念加以解释或确定了的某种经验,通过这类实在人们不仅对过去出现的经验材料进行概括,而且能够对未来可能的经验材料做出预测。(cf.Lewis,C.I.,pp.365-368)与之形成对比的是,经验证据与感觉材料之间的区分恰恰是行为主义意义理论没能加以重视的。然而也正是经验证据与感觉材料之间的区别,让蒯因不得不承认条件反射机制不足以解释语言学习的全部。在谈到颜色的相似性时,蒯因说道:“如果对一个红色的圆圈的反应受到了奖赏,那么一个粉红色的椭圆将比一个蓝色的三角形更容易引出这种反应。这个红色的圆圈与那个粉红色的椭圆之间比它与那个蓝色的三角形之间更类似。若没有某种在先的此类性质(颜色)的划分,我们绝不能获得一种习惯;所有的刺激物都会有同等的相似,并有同等的差异。……这些不同性质(颜色、形状等)的划分自身不可能全部被习得;有些必定是天赋的。”(《蒯因著作集》第2卷,第441-442页)
综上所述,无论是指称式意义理论,还是行为主义意义理论,它们都在探索语言和世界的关系。只不过,前者坚持一种反映论模式,因而必须预设本体论上的世界与事实;而后者坚持刺激-反应模式,认为只有此种模式才是解释世界的唯一合法途径。经验证据在这两种理论中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前者而言,经验证据是判断语句真假的依据,继而也是解释语句意义的根据,例如基于指称论发展起来的证实主义意义理论;对后者而言,经验证据虽然与认识论上的真假概念无关,但是作为一种证据理论的经验论却是始终必须坚持的,例如蒯因坚持认为:“经验论的两个基本信条仍然是无懈可击的,而且至今如此。一个信条是:对科学来说,所存在的一切证据就是感觉证据。另一个信条是:所有关于语词意义的传授都必定依赖于感觉证据。”(同上,第404页)于是,不论是坚持“语言-世界”的指称式意义理论,还是坚持“语言-共同体”的行为主义意义理论,感觉经验都是绕不过去的主题。但是,感觉经验到底在语言意义的说明中能起到什么作用?感觉经验到底又是什么?这些恰恰是这两者都没能很好回答而又必须回答的问题。
标签:行为主义论文; 本体论论文; 世界语言论文; 命题的否定论文; 命题逻辑论文; 语言表达论文; 认识论论文; 形而上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