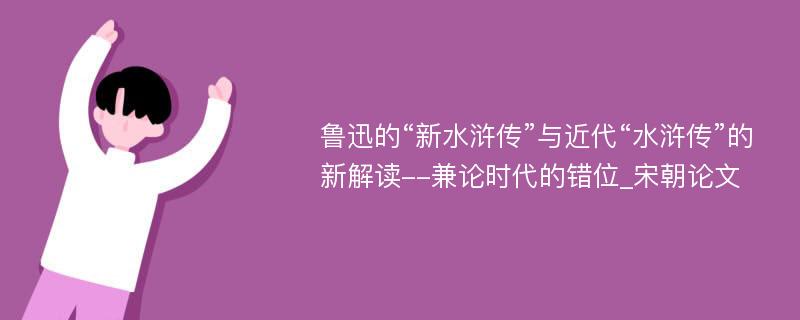
陆士谔《新水浒》与近代《水浒》新读:论时代错置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水浒论文,近代论文,时代论文,陆士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小说(尤其是名著)的续衍现象,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大特色。陆士谔(1878~1944)的《新水浒》(注:本文据陆士谔《新水浒》(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7)。原书宣统元年(1909)七月改良小说社刊。)也是一部续书,该书从贯华堂《水浒》的“惊恶梦”续起,大幅度改变了《水浒》好汉的面貌。不过,续作的改弦易辙,在陆氏的年代并不是孤立的现象,当时的旧书新诠,正好与陆氏该书遥相呼应。本文拟探讨新续和新评两个问题。
故事时间与叙事时间(注:关于“故事时间”( story time),“写作时间”(writing time),请参考Oswald Ducrot & T.Todorov,Encyclopedic Dictionary of the Sciences of Language(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P,1979),p.319。另参 S.Chatman,Story and Discourse:Narrative Structure in Fiction and Film(Ithaca,NY:Cornell UP,1978),第二章。“写作时间”与“叙事时间”有区别。叙事时间可指“叙事时间速度”,关于“叙事时间速度”,实际上与情节疏密度相关。参胡亚敏:《叙事学》(武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叙事时间”一节。用“叙事时间”来分析《三国演义》的例子,可参杨义:《中国叙事学》(台湾嘉义:南华管理学院,1998),页153~159。本文的“写作时间”,是指“小说家实际陈述一个故事、创作一部作品的时间”,参徐岱:《小说叙事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页248。 ):刻意的“时代错置”(注:“时代误置”等于英语的anachronism, 即误将事物放置于该事物未曾产生的时代。莎士比亚戏剧中也有这种情况,参(a)JonsaBarish,"Hats,Clocks and Doublets;Some Shakespearean Anachronisms ",In Shakespeare's Universe:Renaissance Ideas and Conventions.(Aldershot,Hants,:Scolar Press,1996),p.29 ~ 36.( b) Phyllis Rackin, "
Temporality,Anachronism, and
Presence in Shakespeare's English Histories",Renaissance Drama 17 (1986),p.101~123。Rackin指莎士比亚使用“时代误置”可能是故意的。(c)Margreta De Grazia,Shakespeare Verbatim:The Reproduction of Authenticity and the 1790 Apparatus (Oxford:Clarendon
Press,1991),Chapter 3," Situating Shakespeare in aHistorical Period",p.94~132.尤其是p.126~129。)
陆士谔这部续书,不易归类。最突出的一点是:该书将原著人物,放到新时代。说到旧人物新时代这一特色,吴趼人(吴沃尧, 1866 ~1910)的《新石头记》、柏杨的《古国怪遇记》、童恩正的《西游新记》跟陆士谔的《新水浒》可以说是同一类型。这类续书中极为明显的“时代错置”(anachronism)现象, 各种名著四大奇书本身已先启其端。(注:参拙著《四大奇书变容考析》(香港大学哲学博士论文)。)(如《水浒传》出现元化的“行省”(注:《水浒传》第九十一回写“南军连忙报入行省里来”,“冯善同吕枢密都到行省开读圣旨已了”,其中的“行省”是元代独有的建制。参阅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页1247。)、明代的“东昌府”、“兖州府”(注:“兖州府”在洪武十八年方成立,参《明史》《地理志》。东昌则在洪武二年为朱元璋攻克,按惯例,东昌府当在此年成立。)、“子母炮”。(注:石昌渝:《从朴刀杆棒到子母炮》,《文学遗产》1999年2期,页64~77。)
吴趼人的《新石头记》让贾宝玉进入二十世纪(光绪二十七年)的凡尘(注:署“老少年撰”,其实即吴沃尧。初发表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光绪三十四年(1908)十月上海改良小说社出单行本。)。陆士谔的《新水浒》也跟《新石头记》一样,让宋朝人物在清朝活动,只是在形式上还声称故事是发生于宋朝的。事实上,自此体一开,后继者大有人在,如宣统元年“冷血”的《新西游记》写唐僧师徒修成正果后一千三百年,又到了上海。童恩正《西游新记》(注:童恩正:《西游新记》(天津:新蕾出版社,1985)。)也踵步吴趼人和陆士谔的作法,他把《西游记》的三位主角送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把长期受东方传统教育的“出家人”置于尖端科学的薰陶之下。柏杨《古国怪遇记》(注:柏杨《古国怪遇记》(台北:林白出版社,1987)。 按, 书中有1980年序。)甚至让《西游记》四圣及许多神魔进入了不同的时间,写了许多后续故事。
《新水浒》故事发生的时间是北宋末年,实际上却写晚清的社会状况。作者有借小说针砭时局之意。北宋与晚清,时间差距甚远,所以起初读起来颇有点荒诞之感。可以说,小说本身并不著意制造逼真感(也就是不像是北宋末年的故事)。 (注:关于历史感与逼真感,
参考David
Der-wei Wang,"Fictional/Historical Fiction",Studies i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vol.1(March 1985),p.65~66.)
换言之,《新水浒》的“故事时间”(story time)设定为北宋末,实际上却深受“写作时间”(writing time)的支配。书中却处处渗透着陆士谔生存时代的事物。《新水浒》托言朝廷行“变法”(按照神宗时王安石[1021~1086]新法略为变通),形成“新世界”,其实是藉此大写清朝才出现的事物,如电带(页14)、轮船(页43)、铁路(第二十回写卢俊义筑建大名通往白沟的铁路。见页140。)又有邮局、 报纸等。其余如吃鸦片烟(页19),女子革命(页40),吃西餐(页1 48)等等,也是清朝的事。
如果说这一格局是陆士谔独辟蹊径,那是不准确的。实际上,《水浒传》本身何尝不是深受“写作时间”的影响。例如,《宋史》上写明宋江投降,但没有写宋江降后参予伐辽。《水浒传》却写宋江大破辽国,大振国威。李贽(字卓吾,1527~1602)认为“破辽”是作者生于元而愤宋事。(注:李贽的看法,颇获学术界认同。)《水浒传》成书后,又有明遗民陈忱(1613~?)续写《后水浒传》。《水浒后传》成书于康熙初年。小说表面写南宋抗金,其实也寄寓了“抗清的意识”。(注:《水浒后传》已有研究专著,参看Ellen Widmer,The Margins of Utopia:Shui-hu hou Chuan and the Literature of Ming Loyalism(Cambridge [Massachusetts]and London:Harvard UP,1987)。)此书刊于康熙甲辰年(1664),当时台湾为郑成功(1624~1662)后人所据,陈忱写李俊在岛上立国,其寄托不难明白。(丁耀亢的《续金瓶梅》同样也有以宋金交战来影射明清易代之意。)
破辽意识,抗清意识,都是写作时代的意识。
由于《新水浒》故事系于宋代,而实写晚清之事,两者的时间差距相去甚远,所以可能会有许多读者觉得荒唐。然而,四大奇书之一的《金瓶梅》早就这样做了。《金瓶梅》书中的行政系统(内阁、大学士)、监察系统(科道)、司法系统(三法司)、皇家故事(明朝皇帝)、太监系统(镇守、惜薪司、皇庄、砖厂)、地方政制(三司、总督等)、军事系统(提督、总兵、守备)等等,都是“借宋写明”(详参拙著《四大奇书变容考析》)。因此,黄霖在《金瓶梅考论》中说:“明作宋朝纪年,实写明代事实。”(注:黄霖:《金瓶梅考论》(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页49。)
陆士谔的《新水浒》正是这种anachronism的另一个例子。 从这一层看,我们知道小说表面的时代背景(宋代)并不能作为诠释时的参考背景看待。
人物的异变及其时代意义
在内容上,《水浒》好汉的面貌也被陆氏大力改造。《新水浒》处处强调梁山人马是真强盗。这似乎是背离了《水浒传》。
其实,这是宋江故事演变史上非常值得注意的一点。《水浒传》也写了一些梁山好汉“只知利己”的事,但故事的主调还是企图令读者视梁山好汉为正面的人物(如“及时雨”宋江常常赒济他人,鲁智深见义勇为),梁山的宗旨也是“替天行道”,后来为国家破辽,更是“忠义”之举。
《水浒传》这样写,是强说“盗贼”为“忠义”之士。宋江的原型是怎样的呢?原始的公私记载无不视宋江为负面人物,至少是破坏社会秩序的人物。以下是正史中有关宋江的记载:
《宋史·徽宗本纪》: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注:脱脱:《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7),页407。)
《宋史·侯蒙传》:宋江寇京东。(注:《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7),页11114。)
《宋史·张叔夜传》:宋江起河朔,转掠十郡。(注:《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7),页11141。)
私人记载方面:
李植《十朝纲要》:山东盗宋江。(注:李植:《皇宋十朝纲要》([台北县永和镇]:文海出版社,1967),页428。)
方勺(1066~?)《泊宅编》:京东贼宋江。(注:方勺(著)、许沛藻、杨立扬(点校):《泊宅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页99。)
汪应辰(1118~1176)《文定集》:河北剧贼宋江。(注:朱一玄(编):《水浒传资料汇编》(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页5。)
宋江的故事发生于北宋末(约1121),到明朝嘉靖年间(1522~1 566)才有长篇小说刻本(以现存文献所能见来说)。这个故事在几百年之间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宋江由“盗贼”变成“民族英雄”,所以余治(1809~1874)《得一录》评水浒故事为“是非颠倒”:“窃尝谓是非者,天下之定理,是非存而人心于以不死。自《水浒》戏文出,而是非颠倒,定理亡矣!夫英雄、好汉、义士,美名也,以之加于盗贼,颠倒孰甚焉!”(注:朱一玄(编):《水浒传资料汇编》,页526。)
余治说“是非颠倒”,是因为宋江原为朝廷眼中的流贼,水浒故事的流传过程中渐渐将他这一伙人塑造成“好汉义士”。
《新水浒》却处处强调梁山人马是真强盗,藉此鞭挞人性中阴沉自私的一面。在《新水浒》中,梁山好汉原有的本领和特长虽然依旧存在,却用到别的方面去(如林冲在原著中武艺超群,《新水浒》就写他充当陆军学堂的教习。张顺、张横、阮家三兄弟、李俊、童威等人水性好,《新水浒》就写他们开办渔业公司)。这一点,其实是宋江一伙人在历史的长河中衍变的另一种形态。
书中的吴用曾表白:“此后碰着人就可满口‘热心公益’、‘牺牲一己’、‘提创实业’、‘开通风气’、‘竭诚报国’的乱说。有人相信,就可按照着我们做强盗的宗旨,得寸进尺,得尺进丈,敲骨吸髓,唯利是图。”(页35)关于梁山好汉的“强盗面目”,以下举出《新水浒》的几个事例,一看即能明白:
众人下梁山后,蒋敬和时迁在雄州开办忠义银行,最后银行倒闭,两人带走了百姓存在银行中的五十万两银。汤隆、刘唐办铁路,学宋江以退为进之法,一再辞职,反而声誉日隆,目的不过是“骗起钱来亦较他人自易十倍。”宋江设立天灾筹赈公所,借捐款人爱用“无名氏”一点,侵吞不少无名氏的捐款,声名既好,又发大财。林冲开学堂,也是极力设法捞油水,他自供:“一年中教习的薪水,学生的伙食,购买的物件,克扣下来,一总也有好几千银子进益。”(页114)
时迁有一段话,最有代表性:“目下最时髦的莫如我们贼社会,留学生作贼的也有,官场中作贼的也有,好色者窃玉偷香,好名者抄窃文字,即规行矩步的道学先生,亦欲窃取程子之意,……此外如豪士御前窃肉,狂生邻家窃饮,奸雄乘乱窃国,凡古往今来之圣贤豪杰,那一个不是我道中人?”(页53)
可以说,陆士谔将宋江等人还原成原本的“盗贼”了。
但《新水浒》的“盗贼”不是用武力打家劫舍的“盗贼”,而是挖空心思巧取豪夺的“文明盗贼”,《水浒传》中勇字当头的黑旋风李逵,在《新水浒》中是一筹莫展的。
《新水浒》的好汉,人品卑劣,手段肮脏,却还不是最下流的。书中写道:“我们做强盗的心里头杀人放炎,打家劫舍,面子上也杀人放火打家劫舍,他们做绅士的人,满肚皮杀人放火,打家劫舍,面子上却故意做出许多谦恭礼数,文明的样子。”(页20)书中写到皇甫端是兽医,不能医人,作者借萧让之口说出:“军师,如今的人禽兽有甚两样?”(页155)。这“如今的人”,应该是指晚清时期的人。 从这里可略窥陆氏对时代风气的看法。书中各人所经营的新事业,大概反映了晚清时期各行各业的黑暗的一面。《新水浒》的“新”,就新在“讽刺”“鞭挞”。陆氏讽刺时世之意,似比《水浒传》更激烈。
如果我们检讨《水浒》续书的情况,我们就知道,新续离不开时代因素的制肘,如俞万春(1794~1849)的《荡寇志》成于道光年间,大写梁山好汉被惨杀的经过,而俞氏对当时的起义浪潮正是深恶痛绝的。(注:嘉庆、道光间的起事者,的确受到《水浒》的影响。俞灥《〈续刻荡寇志〉序》:“嘉庆中叶,黎民滋事,先大夫奉檄驰办,兵不及发,挺身前往。[……]执二人归,讯之,皆汉人,以《水浒》传奇煽惑于众,适有苛索之事,遂成斯变。”俞灥又记载:“道光初叶,土棍梁得宜,结会万余人,推生员罗帼瑞为‘宋大哥’,将要起事。”这个“宋大哥”,无疑是小说人物宋江。参丁锡根(编):《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页1524,据清同治十年玉屏山馆刊本引录。)再如,民国二十七年(1938)姜鸿飞出版《水浒中传》。(注:姜鸿飞(著),陈烈(校点):《水浒中传(外二种)》(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7)。此册为三书合集,另二部是刘盛亚著《水浒外传》,张家伟校点;程善之著《残水浒》,殷小舟校点。)他有感于“七七事变”,因而让宋江军队去保卫国家。《水浒中传》也和时局关系密切。
宋江故事到了陆士谔手中出现了新变,这是从写作的角度来看问题。其实,从接受的角度看,晚清时期对《水浒》的解读正好跟《新水浒》彼此呼应,基本上是创作性的接受(reception)。 当时一些评论家接受了西方思想,再将这些思想套用到《水浒》之上。有时甚至是按照评论者自己的需要来诠释作品,例如,这个时期出现了“《水浒》是社会主义小说”之论,又有人断定《水浒》有民权、平等、自由等观念,《水浒》作者有“民主共和政体”的概念等等。下面我们探讨一下这一现象。
以新思想诠释旧小说《水浒》
庚子拳变发生后,梁启超有感于国人愚昧,迷信旧小说的人物(如孙悟空、武松等),于是把旧小说打为“诲盗”、“诲淫”,但另一批读者却从旧小说中挖掘到新的东西。
社会主义之小说
黄人(黄摩西)和王无生提出《水浒》是“社会主义之小说”。一九零七年摩西《〈小说林〉发刊词》驳斥《水浒》“诲盗”之见,认为《水浒传》是“创社会主义”。但他没有多作解释。(注: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资料(第一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页253。)
同一年,他在另一篇文章《小说小话》(载于《小说林》第一期,1907)中提出:“《水浒》一书,纯是社会主义。其推重一百八人,可谓至矣。自有历史以来,未有以百余人组织政府,人人皆有平等之资格而不失其秩序,人人皆有独立之才干而不枉其委用者也。山泊一局,几于乌托邦矣。”(注:《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页260。)
另一个重新诠释旧小说的是王钟麒(1880~1913,号无生、天僇生。发表小说评论文章时常署号而不用本名)。(注:颜廷亮:《晚清小说理论》(北京:中华书局,1996),页206。 )王钟麒的小说论著有《论小说与改良社会之关系》、《中国历代小说史论》、《中国三大家小说论赞》。
就在黄人提出《水浒》是“社会主义之小说”的同一年(1907),王钟麒也推出相同的论调。他在《论小说与改良社会之关系》中说:“《水浒传》,则社会主义之小说也。”(注:黄霖(编):《金瓶梅研究资料》,页315。 另参《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页284。)
过了一年(1908),在《中国三大家小说论赞》一文中,王钟麒作了一番解释:
生民以来,未有百八人组织政府,而人人平等者,有之,惟《水浒传》。[……]观其平等级,均财产,则社会主义之小说也;其复仇怨,贼污吏,则虚无党之小说也;其一切组织,无不完备,则政治小说也。(注:《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页346。 原刊于《月月小说》第二年第二期(1908)。马蹄疾(编):《水浒资料汇编》,页438。)
以新思想诠释旧经典,为《水浒》这部明朝小说带来了西方文论家所说的“anachronistic modern meaning”(时代错置的现代意蕴。参看Richard Levin,New Readings vs.Old Plays:Recent Trends inthe Reinterpretation of English Renaissance
Drama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9)第四章第二节“The Problem ofAnachronism”)。
民权、平等、自由观念与《水浒》
一九零五年《新小说》第十五号定一的文章以“或曰”的形式提出“有说部书名《水浒》者,人以为萑苻宵小传奇之作,吾以为此即独立自强而倡民主、民权之萌芽也。”定一本人也同意这种说法:“吾观《水浒》诸豪,尚不拘于世俗,而独倡民主、民权之萌芽,使后世倡其说者,可援《水浒》以为证,岂不谓之智乎?吾特悲世之不明斯义,污为大逆不道。”(注:《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页98。)
一九零七年《新世小说社报》第八期刊出《中国小说大家施耐庵传》认为《水浒》作者有民权思想。文章认为民众有抵抗压迫的权利,甚至也有做皇帝的权利。他最后总结说:“中国之民,罔闻民约之义,发之却有耐庵。耐庵可比卢梭。”(注:《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页304。)
到了一九零八年,燕南尚生在《〈新评水浒传〉叙》中指责金圣叹的批评使《水浒》“纯重民权,发挥公理”的学说湮没不彰。
对于《水浒》“诲盗”之说,燕南尚生表示不能同意。他说:“噫!《水浒传》果无可取乎?平权、自由,非欧洲方绽之花,世界竞相采取者乎?卢梭、孟德斯鸠、拿破伦、华盛顿、克林威尔、西乡隆盛、黄宗羲、查嗣庭,非海内外之大政治家、思想家乎?而施耐庵者,无师承,无依耐[赖],独能发绝妙政治学于诸贤圣豪杰之先。[……]”
然后燕南尚生又从多个角度来看《水浒传》,他认为,《水浒》揭露社会黑暗,则社会小说也,“平等而不失泛滥,自由而各守范围,则政治小说也。”写战争,探情报,叙友谊,赞无畏,讲公德,则又是军事小说、侦探小说、伦理小说、冒险小说、宪政小说。他认为:
要之,讲公德之权舆也,谈宪政之滥觞也,虽宣圣、亚圣、墨翟、耶稣、释迦、边沁、亚里士多德诸学说,亦谁有过于此者乎?(注:马蹄疾(编):《水浒研究资料》,页47。)
《水浒传》者,祖国之第一小说也。施耐庵者,世界小说家之鼻祖也。(注:《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页358。 据马蹄疾(编):《水浒书录》,页141,此书可能仅出第一册。)
燕南尚生的评论,甚为夸张,不甚符合《水浒》原书的实际情况。他所说的发挥“政治学”、“平权自由”、“主张宪政”,都是西方的概念。燕南尚生悍然将这些概念加诸《水浒传》的作者身上,有时甚至到了不顾一切的地步,例如他解说作者的著作动机:“《水浒》者,痛政府之恶横腐败,欲组成一民主共和政体,于是撰为此书。”(注:马蹄疾(编):《水浒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页53。)(所谓“宪政”,是当时流行的话题,陆士谔的《新水浒》组织“梁山会”也说是“立宪政体”了。)(页38)
这种说法,实在是强作解人,借题发挥,是为了呼应当时君主立宪之类的时代思潮。试问《水浒》的作者(注:《水浒》最迟在明中叶已成书。许多论者更认为《水浒》是元末明初之作。)怎会有“民主共和政体”的观念?他在《叙》的结尾说“适值预备立宪研究自治之时,即以[《新评水浒传》]贡献于新机甫动之中国。”这正是他发表《新评》的背景。
其实,燕南尚生本人对于“借题发挥”的做法,也不是一无所觉的。在《新〈水浒传〉或问》中自行供认:“批评云者,借现存之书,叙述一己之胸襟学问而已。”(注:朱一玄、刘毓忱(编):《水浒传资料汇编》,页393。)换言之,他也明白到自己的解释是有主观成分的。
这种《水浒》倡“民权”之说,辛亥革命以后,还有评家继续鼓吹。一九一二年,眷秋《小说杂评》(载于《雅言》):
《水浒》之能冠古今诸作者,正不在此,实以其思想之伟大,见地之超远,为古今人所不能及也。吾国数千年来,行专制之政,压抑民志,视为故常。小说之寓言讽社会,率皆陈陈相因,以忠君爱国为宗旨,即叙述乱君贼臣之事,其结局亦不能为完满之诛伐。自非有应运之君代兴,则绝不敢一言斥及天子。若贼臣之诛,则除假手于君主之外,无他策。至于蚩蚩小民,遭逢乱世,备受千灾五毒,虽未尝不为之太息咏叹,而归罪于君相之言,实不多觏。施耐庵乃独能破除千古习俗,甘冒不韪,以庙廷为非,而崇拜草野之英杰,此其魄力思想,真足令小儒咋舌,民权发达之思想,在吾国今日,独未能普及,耐庵于千百年前,独能具此卓识,为吾国文学界放此异彩,岂仅以一时文字之长,见重于后世哉!(注:马蹄疾(编):《水浒资料汇编》,页414。)
一九二三年七月,许啸天《〈水浒传〉新序》认为《水浒传》要为民众索回“人权”,“胜过卢梭‘民约论’”。(注:马蹄疾(编):《水浒书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页155。)
邱炜萲《客云庐小说话》卷五以为:“《水浒》以慕自由著”。(注:朱一玄、刘毓忱(编):《水浒资料汇编》,页414。)
对于这种以西方思想解释《水浒》的做法,吴趼人有一段公允的评论:“轻议古人固非是,动辄索引古人之理想,以阑入今日之理想,亦非是也。[……]今人每每称其提倡平等主义,吾恐施耐庵当日断断不能作此理想。”(注:原载《月月小说》第1卷。关于吴趼人, 请参颜廷亮:《晚清小说理论》,页101。)
英国评论家克莫德(Frank Kermode)在History and Value一书中的《经典与时代》(Canon and Period)中这样说:“They
believe that the best interpretation,on which valuation must depend,seeks the original intention of the author, and
that valuations which ignore it and consider instead the later or applied senses of an old work-proceed,as some put it,in terms of its significance rather than its meaning-are at least lessauthentic or inauthentic.”(注:Frank Kermode, History
and Value(Oxford:OUP,1988),p.108.)换言之,这一派的意见还是认为:索得作者的原意的诠释,才是最好的诠释;评家的发挥,可信性是比较低的。
结语:
对于续书,有人要求必需和原著贯通协调,不能“无根据”,例如俞平伯对《红楼梦》后四十回的不满,就是不满后部与前八十回不贯通。(注:参拙稿《〈红楼梦〉衍义考析》(1994年香港大学哲学硕士论文)第三章。)至于评释,也有一派理论家极力主张诠释必须以作者的本意为准,如赫施(E.D.Hirsch)。(注:参阅David Newton-de Molina ed.On Literary Intention(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1976)。 另一本专题论文集是G.Isemingered. Intention and Interpretation(Philadephia:Temple University Press,1992)。 这两本论文集中,有人(例如,E.D.Hirsch Jr,1928~)再三强调“作者原意是诠释目标”。雷蒙德·威廉斯在《马克思主义与文学》一书中指出人们常常将作者(author)和权威(authority)联系起来, 这种联系产生了重要影响。参Raymond Williams(1921~1988),
Marxismand Literatur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页192。)
可是,从本文的具体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无论新续还是新解,往往都是别有用心的。宋江的水浒故事,似乎永远无法改变“顺时改易、为人所用”的命运。《水浒》的演变史和成书后各种续书都不断证明这一点。 这恐怕也是许多文学名著的命运。 新实用主义者罗蒂(Richard Rorty )曾经说过一段极有代表性的话:“把文本锤打成符合自己目的的形状。 ”英文原文是这样的:“ The
critics
asks neither the author nor the text about their intentions but simply beats the text into a shape which will serve his own purpose.He makes the text refer to whatever is relevant to that purpose.”(注:Consequences of Pragmatism:Essays,1972~1980(New York:Harvester Wheatsheaf,1991),P.151.)这一番话, 主语是评论家,其实,从陆士谔的续作来看,我们发现:写作也可以是一种“攘为己有”( appropriation )(注:诠释学大师利科( Paul Ricoeur)写道:“Appropriation”is my translation ofthe German term“Aneignung”.Aneignung means to makes one's
own what was initially alien.)的行为。
标签:宋朝论文; 水浒传电视剧论文; 水浒论文; 文学论文; 读书论文; 宋江起义论文; 宋史论文; 宋江论文; 四大名著论文; 西游新记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