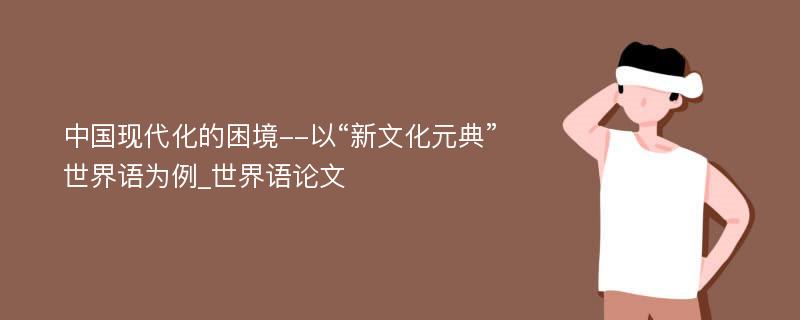
中国现代性的两难——以新文化元典中的世界语吊诡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界语论文,现代性论文,为例论文,中国论文,以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402(2007)05—0045—08
众所周知,20世纪中国现代性的演进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进至一个关键时期。以《新青年》杂志为依托的“新青年派”知识群体在很多层面和领域齐头并进,以期现代性在他们手中绩效斐然甚至大功告成。然而,现代性的“混沌”、多元、复杂乃至纠缠多少让一代先驱“力不从心”。① 本文选取这一时期现代性的一个侧面——世界语命题的讨论——作为展开的由头,从中不难发现中国在借鉴西方资源之时的困窘,这就是标题昭示的“两难”。
一、通向大同的路径:世界语与乌托邦理想的升堂
《新青年》在“文白不争”的情景中陷于左右为难,当白话势在必行而白话文又不堪民族重负之际,倡导者只得将历史的悲情扩张,希望借此掩饰自我的困顿、尴尬、虚无与无奈。于是,寄托希望于世界语并将其作为废除汉字的理由构成了传统语言文学的双刃杀手锏。究其实质,所谓的消灭汉字这种民族文化虚无主义本身就是在现代性面前备感无力的证明,更是一种对现代性的逃避。鲁迅自述当年加盟语言文学革命的心境“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可以说是整个知识群落的心态症候。然而,作为担当道义的现代知识分子,他们不可能将自我的隐遁、逃避、失望心理公诸于众,为此他们寻找到了一种聊以慰藉的“支援意识”。世界语乃是他们现世所能依托的最终归宿——一个神秘、遥远、美丽的乌托邦语言天堂。
必须看到,世界语理想的滋生是在世界主义的大同思想环境下营造的。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当陶履恭看到《新青年》关于世界语的主张并对其执迷提出“忠告”后,陈独秀便身先士卒地予以了“全面”的回答:“‘将来之世界必趋於大同’,此鄙人极以为然者也。来书谓‘世界主义是一事,世界语又是一事,二者未必为同一问题’,此鄙人微有不以为然者也。世界语之成立,非即为世界主义之实现。”陈独秀一是表明了世界语与世界主义在自己眼中的关系;二是流布了世界语为什么要提倡的心迹——为世界大同而将关口提前。在这个“全面”中,陈独秀最后的总结陈词更为关键:“是世界人类历史无尽,则人类语言之孳乳亦无尽。世界语所采用之单语,在理自不应以欧语为限。此义也,迷信世界语者当知之,务为世界之世界语,勿为欧洲之世界语尔。仆犹一言欲质诸足下者,足下轻视世界语之最大理由,谓其为人造的而非历史的也。仆则以为重历史的遗物,而轻人造的理想,是进化之障也。语言其一端耳。”[1] 这第三层意思显然带有建构的唯理主义特征。重视“人造的理想”从“语言”开始,这也正是“积极的自由”或说激进自由主义的基本乌托邦质地。[2] 同时必须看到,世界语说法的出现也不是《新青年》的专利。早在1907年,当无政府主义盛行中国之际就有人把母语与世界语的“水火不容”关系给抬了出来。那时,以吴稚晖等为中心的巴黎中国留学生在《新世纪》杂志上捶胸顿足地咒骂母语,主张改用“万国新语”(即《新青年》期所谓的“世界语”)。一副“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姿态和语气。历史的惊人相似在这里得到充分的证明:如果说《新世纪》是将对清政府专制的咒骂与对将语言文字的诅咒作为同一个仇恨对象加以发泄,那么《新青年》的对传统政治(包括当局)的不满、传统伦理道德的批判、对旧文学的愤恨更是全方位的开战。语言文字的政治工具情怀使得它一开始就夹杂浓厚的意识形态化的诱因。
回到《新青年》杂志,全方位向传统社会开战一方面反映了激进知识群体对现代性向往的焦虑,另一方面也再次印证了传统思维泛起:道统、政统、学统有机统一,从而演绎出新一轮的具有综合、整体模式的新内圣外王主义。世界主义思维模式的形成正是传统乌托邦在现代的翻版。一个值得注意的思想史现象是,《新青年》一方面是极端“个人本位主义”的主张,另一方面则是打破一切阻隔之直通车式的“世界主义”理论。李大钊在《我与世界》中述说的“我”与“世界”的关系其实就是“个人主义”和“世界主义”的关系:“我们现在所要求的,是个解放自由的我,和一个人人相爱的世界。介在我与世界中间的家国、阶级、族界,都是进化的障碍、生活的烦累,应该逐渐废除。”[3] 理论与事实往往既是这样微妙,看来极其相反甚至是“风马牛”的精神现象也往往只有一步之遥。陈独秀也曾在与钱玄同讨论“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的通信中这样说:“吴先生(即吴稚晖——引者注)‘中国文字,迟早必废’之说,浅人闻之,虽必骇怪而循之进化公例,恐终无可逃。惟仅废中国文字乎?抑并废中国言语乎?此二者关系密切,而性质不同之问题也。各国反对废国文者,皆以破灭累世文学为最大理由。然中国文字,既难传载新事新理,且为腐毒思想之巢窟,废之诚不足惜。……至於废国语之说,则益为众人所疑矣。鄙意以为今日‘国家’、‘民族’、‘家族’、‘婚姻’等观念,皆野蛮时代狭隘之偏见所遗留,根底甚深,即先生与仆亦未必能免俗,此国语之所以不易废也。”[4] 主编在认为国语是野蛮褊狭之物的同时也看到了国语转换的艰难性。从陈独秀这段文字中,我们至少可以获得三重重要信息。一是世界主义背景下的世界语之说与无政府主义哲学思想有着根深蒂固的渊源关系;二是所谓废除“中国文字”的命题在本质上是以民主思想的需要或说新型意识形态的建立为依据的。在这个意义上,一切形式的语言文字革命都是意识形态更新不可或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三是文字的革命比起单纯的白话文革命,陈独秀更讲求程序和步骤。这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陈独秀对民主观念理解的偏斜——更注重下层因素和数量因素。
如上所述,早在世纪初年以吴稚晖等一批留法过来的无政府主义者就在自己的阵地《新世纪》上对国语发起了咬牙切齿的攻击。而中经《新民丛报》、《民报》、《甲寅》等杂志,时至《新青年》时期,关于这个世界语与国语关系的讨论几乎还是沿袭了当时的主调。区声白,一位典型的无政府主义者,他在《新青年》与钱玄同关于世界语的积极讨论也多沿用吴稚晖当年在《新世纪》上的只言片语:“有欲将其新名词新术语嵌入于汉语中使用者,更该提倡;如此,则国人与Esperanto可以一日接近一日。吴稚晖先生谓‘近世界之新学理,新事物,若为汉文所发挥不足者,即可搀入Esperanto,以便渐搀更多,将‘汉文’渐废,即为异日径用Esperanto之张本。’(见《新世纪》第四十号)我以为这是提倡Esperanto最切要最适当的办法。”[5] 无政府主义黄凌霜在给钱玄同的信中也还是以十年前的话语为中心:“贵志同号中姚寄人先生将十年前巴黎《新世纪》周报醒先生所做的《万国新语(亦名世界语)之进步》的,末假钞出来。据我的鄙见,这篇文章起头所说的‘万国新语有五大特色,为各国文字所不能及’都是很好的。这篇文章,可算是中国人说Esperanto的先导。我记得民国元年的时候,我的朋友师复先生,创立晦鸣学舍于广州曾将他付印数万份,拿来分赠,看见的人,一定不少,我现在不必再去钞他了。”[6] 这里老牌的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李石曾的理论以及区声白、黄凌霜都纷纷上阵,提起当年之勇。即使新文化运动渐进高潮之际,吴稚晖的“大同”学说仍是《新青年》追逐不放的权威支持。[7] 引证这些的目的在于,对比陈独秀和李大钊关于“家国、阶级、族界”都是“野蛮时代”产物的说法,应该说《新青年》的理论的哲学基础有很大程度的无政府主义性质。不难看出,《新青年》为了自己的“主义”或说意识形态的泛化是不惜一切,也不顾一切的。将无政府主义权且作为立论基础,这多少反映了《新青年》一开始追求现代性的诉求中就蕴含着残缺的因子。无政府主义的破坏、打倒(偶像)意识以及粗暴、简单逻辑给20世纪中国留下了沉重的教训。鉴于《新青年》的语言文字革命不过是借助了这个“暴力”,所以在这里对微妙不作过多的分析。只是要特别指出的是,将中国传统过去所遗留之物作一股脑的“社会”性完全革命,同样是无政府主义的逻辑思维。
其次,笔者要说的是,在追求现代性的价值诉求上,《新青年》一开始是将“语言”和“文学”的剥离作为起点的,这在刘半农的《我之文学改良观》以及胡适、陈独秀的新文学论述文章中可以窥见其端倪。但是《新青年》以民主思想的需要或说新型意识形态的建立为依据的命题最终决定了不可能将这个剥离坚守到底。《新青年》杂志有一个关于世界语的讨论过程值得回味。当读者T.M.Cheng来信这样询问世界语一事时:“至论世界语为今日人类必要之事业,惟以习惯未成,未能完全应用。拜领教言。”主编便以“记者”身份答曰:“世界语,为今日人类必要之事业。惟以习惯未成,未能应用于华美无用之文学。而于朴质之科学,未必不能达意也。”[8] 于是这很快遭到了钱玄同的质疑:“先生认世界语为‘人类必要之事业’,此说弟极表同情。至云未能应用于文学,恐非确论(文学之上加以‘无用’二字,弟尤不敢赞同。然此当是先生一时之论。观大著《文学革命论》所言,知先生于文学之事固视之极重也)。日前孑民先生语我,谓用世界语译撰之书,以戏曲小说之类为最多,科学书次之。是世界语非不能应用于文学也。……世界主义大昌,则此语必有长足之进步无疑。中国人虽孱弱,亦世界上之人类对于提倡此等事业,自可当仁不让。”[9] 面对钱玄同咄咄逼人的气势,陈独秀只好束手就擒。或许是“欲纵故擒”,反正这里的一阵谦逊之后还有一段不能忽视的表白,尤其是对研究《新青年》如何转移视线以突出“民主”意识主题的论题。原信如下:“仆前答某君书所谓‘华美无用之文学’者,乃一时偶有一种肤浅文学观念浮于脑里,遂信笔书之,非谓全体文学皆无用也。世界语犹吾之国语,谓其今日尚未产生宏大之文学则可、谓其终不能应用于文学则不可。至于中小学校以世界语代英语,仆亦极端赞成。吾国教育界果能一致行此新理想,当使欧美人震惊失措。且吾国学界世界语果然发达,吾国所有之重要名词亦可以世界语书之读之,输诸异域。不必限于今日欧美人所有之世界语也,高明以为如何?全部《十三经》,不容于民主国家者盖十之九九。此物不遭焚禁、孔庙不毁,共和招牌当然挂不长久。今之左袒孔教者罔不心怀复辟。其有不心怀复辟者更属主张不能一致贯彻之妄人也。康南海意在做大官尊孔复辟皆手段耳,此伧更不足论!其徒梁任公尝直其名曰康有为深恶之也。”[10] 一个常识性的问题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这不能不说是陈独秀的一个致命“硬伤”。然而,“新理想”以及古典典籍百分之九十九的不容“民主国家”的说法已经让我们明白了主编的制造“硬伤”的苦心,他欲以世界语的转换来切断借以传承专制制度的中介。与此同时,当一个“硬伤”弥合了之后,一个新的“硬伤”裂缝出现了:“新理想”的输入难道能靠自己都承认的“习惯未成”且还是“乌托邦”的世界语来传导吗?也难怪读者张耘在给胡适的信中将这个做法称为“思想紊乱”呢![11]
再次,胡适对世界语的态度是不积极的,就是借主编对白话文为正宗以及“不容商榷”的态度在世界语问题上也出现了缓和。笔者以为,这个缓和本身充分说明了陈独秀这样激进的革命家对世界语的乌托邦色彩也是非常清醒的。就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的趋势和现实而言,尽管困难重重,但毕竟其可行性举手可揽。而通过世界语来促进新型意识形态的塑造,本身就是超负荷的唯意志论式幻想。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新青年》上的文学革命与世界语的提倡几乎是同步进行的。由于刚刚述说的缘故,文学革命则是由于接近现实而且是从中国自身内部的改良下手,因此有近水楼台的优先性和先行性。从此,我们也可以看到“文学”与“语言(文字)”之分分合合的胶着状态——始于分离终于合一。这个超越与回归的悖论一直是伴随新文化元典运动演进的基本思想张力。当陈独秀与胡适在1916年就开始“设计”文学革命时,与之俱来的便是世界语的插科打诨。1917年8月杂志上陶履恭、钱玄同以及陈独秀的讨论已经是满“志”风雨。而随着“文学革命实绩”的显示——白话诗文的“尝试”以及白话小说《狂人日记》的问世,《新青年》自1918年5月号起关于世界语的讨论便几乎湮没了文学改良的声音。在《新青年》5卷2号上,曾有区声白、陶履恭(孟和)的争论以及钱玄同、陈独秀两人关于这“Esperanto”的“跋语”。其中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的争论由此引发了作为杂志编辑的钱玄同和陈独秀的参与。针对陶孟和对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的“两端”怀疑,钱玄同在公开信的结尾也有针对性地呼吁:“我因为怀了这两个意见,所以要提倡Esperanto。声白君对于我这意见如以为然,深愿共同提倡。选学家桐城派反对新文学,我格外要振作精神去做白话文章;我们对于Esperanto,也该用做白话文章的精神去提倡!”[12] 的确如笔者所言,世界语与白话文在一个链条上构成了文学革命的两个阶段。世界语的提倡在当事人看来则是文学革命的深化。在陈独秀与钱玄同、区声白同处一个文化场域并自爱一个思想立场之际,陈独秀最后的陈词还是要极力劝说陶孟和皈依“世界语”的行列:“Esperanto在学术上,尚属因袭的而非创造的;在言语上,尚属人为的而非自然的;孟和先生之不满意于此语也,殆以是故;余亦云尔。弟鄙意与孟和先生微有不同者今之Esperanto,或即无足当‘世界语’之价值;而世界之将来,倘无永远保守国别之必要,则有‘世界语’发生及进行之必要;以言语相通,为初民社会之一大进化;其后各民族间去小异而归大同也,语言同化乃为诸大原因之一;以此推知世界将来之去国别而归大同也虽不全以‘世界语’之有无为转移,而‘世界语’(非指今之Esperanto)之流行,余确信其为利器之一,并希望孟和先生以赞同者也。”[13] 其实陈独秀感觉到了陶孟和的观点正是对自己“人造的”进化理想的否定。这也是主编何以在跋语中“国别”的消失、“大同”的到来,以“世界语”为“利器”作为“劝降”根据的原因。希望归希望,世界语的讨论并不是能靠希望或幻想来完成的。
二、“人造的理想”:世界语与现代性的吊诡
时至1918年8月,正当《新青年》大张旗鼓地为“世界语”张目之时,一位素与胡适之交往甚密的读者朱我农来信公然打出反对世界语的旗帜:“无论那一种语言文字,只有因为文字不合语言,把文字改了的(先生所说,意大利人废拉丁文,就是好证据)断没有用文字去改语言的。如此推想,就知道私造了一种文字(这‘文字’二字是假定的称谓)要世界的人拿他当作日常应用的语言,是万万做不到的。所以,Esperanto断不能当作世界通用的语言,简直是一个无用的东西。”宏观一论之后,接着他又微观地将钱玄同和陈独秀的观点拉来予以纠正道:“两先生又说‘重历史的遗物而轻人造的理想,是进化之障也’,我又不以为然;两先生的意思是称各国语为历史的遗物,Esperanto为人造的理想。不对不对!第一,我们中国的文字,诚然可以认作历史的遗物,但是英美德法诸国的语言文字,是日新月异,当世应用的?断不能认为历史的遗物。第二,语言文字是一种‘公众应用的特别事物’,决不是私造的理想;如果Esperanto是人造的理想,那就万万不能用作语言文字了。所以陶先生既没有重‘历史的遗物’也没有轻‘人造的理想’。”[14] 鉴于钱玄同和陈独秀立场的大同小异,朱我农将陈独秀的语言合而为一了。不过,其中关于语言历史进化观念确是表达的非常明确,也与胡适之的“稳健”观点相互呼应。看看胡适的回信就可略知一二了:“老兄这两次的来信都是极有价值的讨论,我读了非常佩服。我对于世界语和Esperanto两个问题,虽然不曾加入《新青年》里的讨论,但我心里是很赞成陶孟和先生的议论的。此次读了老兄的长函,我觉得增长了许多见识,没有什么附加的意见,也没有什么可以驳回的说话。”驳都驳不倒,自然佩服。这话其实无非也是说给《新青年》其他同仁听的。自己一方面声明“不曾加入《新青年》里的讨论”,另一方面又说“很赞成陶孟和先生的议论”,这则表明了自己的立场。胡适的一贯的(不只是在语言文字上的)“历史进化观念”再次得以彰显:“以上五条,我非常赞成。老兄讨论这个问题的根本论点只是一个历史进化观念。语言文字的问题是不能脱离历史进化的观念可以讨论的。我觉得老兄这几段议论Esperanto不单是讨论,竟可以推行到一切语言文字的问题,故特别把他们提出来,请大家特别注意。”[15]
从最早的《文学改良刍议》到《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再到1918年《新青年》5卷5号的《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胡适的新文学理论都是从本体论的角度谈文学、语言、文字包括文化的渐进、自然进化观。他可以间或在文章中谈到、认可甚至支持“大同”、“世界语”以及个人本位主义抑或社会主义等观念,但在其骨子深处是不可能与其长期为伍的。胡适实验主义的方法论以及自由主义思想使他一开始就对暴戾的无政府主义、激进的集体主义、民粹的社会主义持反感态度。1919年3月15日,《新青年》读者张耘的来信可以说道出了久藏于胸的“心忧”。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上是,从张耘“《新青年》常常收到”的客套中已经可以看出胡适与这位“读者”的关系及其思想路径的默契。他说:“此报主旨似在改良文学。改良文学,今人稍具文学兴味及科学眼光者,多半赞成。惟至如何改良,则主张不一。耘不学,谬想改良应在中国文学自身以内改良,不应出此自身以外而言改良。如某君之主张用罗马拼音,某君之主张用英法文,某君之主张用世界语,均系离此自身而言改良。非改良文学也,直互换文字耳。改良文学与更换文字截为二事。为建设的革命计,吾意只应讨论改良之法。不宜涉及更换问题。《新青年》对于文学果有建设计画,似应主张其一。不应二事并提,徒乱观听,而且造成思想界一种极危险的Anarchy。反对可也。革命可也。而毫无目的的Anarchy到无论在何时何事,均应视为大忌,君以为然否?”张耘在批评了世界语是“造成思想界一种极危险的Anarchy”的倾向后,还批评了许多人的“好高骛远、思想不清”:“我以为今人凡轻视英法德文而极力提倡世界语者,其病因有三:曰愚、懒、妄。惟愚乃信英法德文中好书籍,世界语均有译本;惟懒乃甘取此不通捷径,无所得而不辞;惟妄乃坚信世界不久必大同,大同后必有大同语,而此大同语又必为今日之所谓世界语。三问题混合为一,颇足形容今日中国人思想紊乱情形。主张脚踏实地,做建设工夫者,对于此种愚懒妄传染病,须极力扑灭之。”[16] 正因为张耘的来信为胡适的观点张目,所以胡适的回信是柔中有刚:“张君这封信有许多话未免太过,但他所说的大旨,都狠有讨论的价值,故登在此处,供大家讨论。”“未免太过”为虚,“讨论价值”为实,胡适的跋语未尝不是在实施其拐弯抹角、“欲擒故纵”的文化经营策略。
Anarchy,就是温和的改良主义者担心的无政府主义倾向。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胡适不是不赞成用拼音字母取代汉字,他只是不赞成那种不经实验、尝试、讨论就粗暴地“直接”互换的武断做法。更重要的是,他信奉的是渐进、改良、稳健的“科学”程序。于是就连素称稳健的胡适也坚信汉字必须废除。初到美国,他曾对不假思索就散发“废除汉字,取用字母”之传单者十分反感,但他毕竟不是死守传统的遗老遗少;理解并相信有一天拼音文字取代汉字。[17] 在文学改良取得基本的“实绩”并有稳健的发展事态后,他也有期待到来的蠢蠢欲动:“如果因为白话文学的奠定和古文学的权威的崩溃,音标文字在那不很辽远的将来能够替代了那方块的汉字做中国四万万人的教育工具和文学工具了,那才可以说是中国文学革命的最大的收获了。”[18] 然而,在终极意义上,胡适不会过火,而且会和其他改良的路径一样与陈独秀们发生着程度不同的冲突。世界语问题上他与陶孟和、朱我农等人为一方,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等人为一方的据理力争就充分体现了两条思路的本质区别。
如上所述,与白话文为正宗的不容商榷和讨论不同,陈独秀在世界语问题上或许是接受了白话文的粗暴“干涉”的教训或是由于胡适之的劝说与影响,他这次转向远远没有上次那样陡直,而是放慢了脚步。如果不是钱玄同跟在屁股后面一天到晚地穷追不舍,说不定陈独秀在后来还会像胡适一样漫不经心地谈论世界语甚至只是间或“加入”呢!自从文学革命发生以后,包括像诸如华文横行这类主编完全可以轻松决定的事情都要讨论再三,可见《新青年》是如何在履行“Democracy”的设计了。必须指出,《新青年》的“同仁”意识有不愿意分裂,有意造成一条阵线向恶势力开战的意味。对此,未免将其解释成一定阶段的权宜之计未尝不可。但是最后陈独秀与胡适在《新青年》“色彩”与南下还是北上诸问题上的撕破脸皮则不是这个原因所能解释的(另有专论)。因此《新青年》语言文学革命后期的一些做派还有从深层次上进行思想谱系的知识考古。作为白话文诞生摇篮的《新青年》,其经营者陈独秀从一开始就有着占领平民空间、大众市场的文化民粹主义意识。他主编的《新青年》走的是一条让经典成为时尚的大众化、市场化道路。在文言文当道的时代,他担心的是多数参与的大众化民主政治的孤立;在白话文时代,他希望新型的政治理念能够得以彻底的普及;在世界语时代(乌托邦),他不能不担心会不会前功尽弃?他的文化与政治之双重民粹主义观念会不会由此搁浅?毕竟,现在“功成名就”的白话文还没有完全成为中国多数平民所切实接受。如果由此进行跨越式的发展,我们岂不走向一片荒芜的真空地带?世界语除却是一个带有幻想的至高目标,它还能提供(给民主政治理念)什么呢?对此,即使激进超过陈独秀的钱玄同也不能不承认:“即废文言而用白话,则在普通教育范围之内,断不必读什么‘古文’发昏做梦的话,或可不至输入于青年之脑中;——新学问之输入,又因直用西文原书之故,而其观念当可正确矣。”[19] 白话文尚能进行“普通教育”的普及,而“直用西文原书”,由此进行的“观念可当正确”的“新学问”又当收效若何呢?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尽管心急如焚,甚欲一步到位,但还是“冷静”不少。钱玄同躁情四起:“我再大胆宣言道: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19] 然而,这一附和陈独秀“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的句式,并没有得到陈独秀的赞许,相反倒是一盆冷水:“惟仅废中国文字乎?抑并废中国言语乎?此二者关系密切,而性质不同之问题也。各国反对废国文者,皆以破灭累世文学为最大理由。然中国文字,既难传载新事新理且为腐毒思想之巢窟,废之诚不足惜。……至於废国语之说,则益为众人所疑矣。……惟有先废汉文,且存汉语,而改用罗马字母书之;新名悉用原语,无取义译;静状介连助叹及普通名代诸词,限以今语;如此行之,虽稍费气力,而于便用进化,视固有之汉文,不可同日而语。”[20] 除却在“中国文字,既难传载新事新理且为腐毒思想之巢窟,废之诚不足惜”上达成了整体性思维模式的统一,陈独秀与钱玄同在语言(“言语”)与“文字”上的分歧、在先废“汉文”且存“汉语”的程序是一步到位还是“一步一个脚印上”的不同都使得陈独秀显得有些反常。这也是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可以说是唯一的一次得到胡适附和的地方。在钱玄同和陈独秀的一番对话之后,胡适有一段跋语:“独秀先生所问‘仅废中国文字乎?抑并废中国言语乎?’实是根本的问题。独秀先生主张‘先废汉文,且存汉语,而改用罗马字母书之,’的办法,我极赞成,凡事有个进行次序。我以为中国将来应该有拼音的文字。但是文言中单音太多,决不能变成拼音文字。所以必须先用白话文字来代文言的文字,然后把白话的文字变成拼音的文字。至于将来中国的拼音字母是否即用罗马字母,这另是一个问题,我是言语学的门外汉,不配说话了。”[21] “凡事有个进行次序”是胡适之的一贯主张,而陈独秀间或为之,此为其一例。胡适“门外汉”的自谦也不过是稳妥的说法。陈独秀的暂时不温不火和胡适之的不温不火还是有根本不同的。从实而论,陈独秀的革命家性情和激进做法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受到了学问家胡适之的牵扯和抑制的。同时,胡适之学问家的性情和稳健、周全的性格又是得到了陈独秀的引导和发挥的。不然,《新青年》难成“经典”,陈独秀从而也就难以演化“时尚”。
话说及此,连笔者本人也与诸位一样,还是要追问究竟《新青年》上关于世界语的论争是如何收场的。据笔者的观察,《新青年》最后一期讨论世界语的通信是在1919年2月15日出版的6卷2号上,其中有三篇涉及世界语的文章。一是热衷于世界语的钱玄同与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关于《Esperanto与现代思潮》的通信;二是黄凌霜独撰的《世界语问题》一文;三是周祜和钱玄同关于《Esperanto》的通信。至于以后《新青年》上关于语言的讨论,那都多以白话文、新文学等回归前事的形式展开继续讨论。根据《新青年》随着时代发展而讨论命题也移位变形的特点,世界语问题就此搁浅,继“易卜生专号”之后,遂被“贞操问题”、“马克思研究”、“人口问题”、“工读互助问题”、“劳动节问题”、“俄罗斯研究”等专号代之而起。而最关键的是,《新青年》5卷2号上集中讨论的一次意味深长。在笔者看来,那是“欲休还说”的一次终结论,但不知是何缘故,一直拖了近半年才“弃锣收兵”。那次的《通信》一栏竟然有16人次专门关于新文学和世界语展开讨论,而且都是发起者或关键人物。《新文学问题之讨论》和《论Esperanto》都是两次出现。单单跋语就有6人次之多。如果说这并不是重要的议题,那么他们怎样说则至关重要。当孙国璋来信询问陈独秀作为新文学的关切者何以不置一词时,② 陈独秀8月6日回话如此:“诸君讨论世界语,每每出于问题自身以外,不于Esperanto内容价值上下评判而说闲话,闹闲气,是以鄙人不敢妄参末议也。”[13] “闹闲气”只是“不敢妄参末议”的理由之一。的确,自从《新青年》4卷1号上“不另购稿”的完全“同仁化”以后,轮流编辑的坐庄方法让世界语的讨论已经夹杂着义气之争的成分了。胡适之在8月7日紧紧跟上陈独秀的回话,他草签道:“我对于‘世界语’和Esperanto两个问题,始终守中立的态度。但是现在孟和先生已说是‘最末次之答辨’,孙先生也说是‘最后之答言’了。我这个中立国可以出来说一句中立话:我劝还有那几位交战团体中的人,也可以宣告这两个问题的‘讨论终止’了。”[22] 在孙国璋“最后之答言”、陶孟和“最末次之答辩”、陈独秀“不敢妄参末议”、胡适“讨论终止”之宣告后,本来可能暂告一个段落的争论可以终结,“但”最后的“玄同附言”似乎又带来了新的紧张:“但玄同还有一句话,几个人在《新青年》上争辨,固可不必;而对于‘世界语’及Esperanto为学理上之讨论,仍当进行,不必讳言此问题也。”[12] 虽然是紧张,但有陈、胡两位中坚之中坚做主,即使再延续话题,也只能算是强弩之末了。这也是《新青年》上世界语问题逐渐终结的原因。
需要进一步注意的是,陈独秀毕竟是世界语讨论的支持者,他的少说或说不说不等于没有主见和主张。事实上,他开始的提倡十分严肃,而且与钱玄同有很多共执的成分。这从他回答陶履恭(孟和)的信中可以看到他对世界语美好“大同”理想的向往和执著。[1] 而钱玄同之所以倾力提倡,也不过是因为:“我爱我支那人的热度,自谓较今之所谓爱国诸公,尚略过之。惟其爱他,所以要替他想法,要铲除这种‘昏乱’的‘历史、文字、思想’,不使复存于‘将来子孙的心脑中’,要‘不长进的民族’恋成了长进的民族,在二十世纪的时代,算得一个文明人。要是现在自己不去想法铲除旧文字,则这种‘不长进’的‘中国人种’循进化公例,必有一天要给人家‘灭绝’。”[23] 钱玄同将“历史、文字、思想”归结为“昏乱”的一体,这就是五四新文化元典在情绪上全盘反传统的铁证。陈独秀回答陶孟和的信也道出了一个“不敢妄参末议”者的“良心见解”:“世界语之成立,非即为世界主义之实现。且世界主义未完全实现以前,世界语亦未能完全成立。然世界人类交通,无一公同语言为之互通情愫,未始非世界主义实现之一障碍。二者虽非一事,而其互为因果之点,视为同问题亦非绝无理由。”[1] 将世界语视为世界主义的因果姊妹,自然就会有与钱玄同不二的语言诉求。只是程序和路径上稍有差异。但,这并不耽误共同推进现代性演绎。钱玄同的一段话颇能代表《新青年》同仁的心声,笔者特录如下:“还有一层,同人做《新青年》的文章,不过是各本其良心见解,说几句革新铲旧的话;但是各人的大目的虽然相同,而各人所想的手段方法当然不能一致,所以彼此议论,时有异同,绝不足奇并无所设‘自相矛盾’。至于玄同虽主张废灭汉文,然汉文一日未废灭即一日不可不改良。譬如一所很老很破的屋子既不可久住,自须另造新屋?新屋未曾造成以前,居此旧屋之人自不得不将旧屋东补西修以蔽风雨?但决不能因为旧屋既经修补,便说新屋不该另造也。”[23] 在“旧屋”与“新屋”之间,笔者的看法是:如果画饼不能充饥,那么未免还是先吃下这块不算美味的土煎饼,等画饼成为现实后再吃也不晚。只是我们人类——无论是哪一个种族的人,不可能总是活在希望或说文化的真空(既包括精神文化也包括物质文化)中。
现代性,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界分,在中与西之间起始,在新与旧之间纠缠,新文化元典的同仁们为世界语打造所付出的代价为20世纪中国现代性两难的心路作了生动的历史注脚。回眸历史并眺望未来,在笔者看来,当下的我们对待现代性的态度既不是保守的拒绝,也不应是激进的超越,倒应该是“其命维新”的转换。
注释:
① 张光芒《混沌的现代性——对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总体特征的一种解读》一文中针对目前中国现代性研究存在的“错位”、“误读”、“暧昧”、“浑浊”等问题的批评不止在当下,其实在“五四”时期就不同程度地存在。参见《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② 孙国璋来信说:“独秀先生——余以六月份之《新青年》将为易卜生号,故对于通信栏之讨论,亦遂以他事暂搁。及今思之,余上次通信(载四卷四号)虽感承钱、陶(指钱玄同与陶孟和的通信讨论——引者注)两先生答书,并胡先生跋语,每以未得先生一言,在在令吾人失望。”(《通信·论Esperanto》,《新青年》5卷2号,1918年8月15日)
标签:世界语论文; 陈独秀论文; 钱玄同论文; 新青年论文; 大同社会论文; 胡适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新文化论文; 新世纪论文; 现代性论文; 无政府主义论文; 白话文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