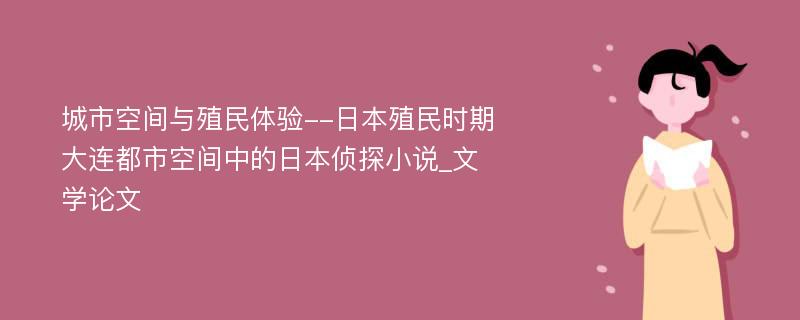
都市空间与殖民体验——日本殖民时期大连都市空间中的日本侦探小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都市论文,空间论文,大连论文,侦探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948(2013)03-0014-07
日本近现代文学很重要的一面就是渗透着深刻的战争记忆和殖民体验,其中,较为突出地体现在与中国东北地区,特别是与东北都市千丝万缕的精神联系上。东北地区的近代城市化进程伴随着帝国主义侵略和殖民统治对地理空间的扩张和城市空间的生产,在这一过程中,大连、沈阳(奉天)、长春(新京)、哈尔滨等相继被兴建或重构,新的城市地貌和景观勾勒出畸形的“繁荣”和现代“摩登”的都市空间。但是,在浮华的幻影背后,充斥着种族歧视、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内在规定了都市空间中殖民者的天堂与被殖民者的地狱的并存。这一异质空间的现代性和与生俱来的矛盾冲突给日本作家带来了深刻的殖民体验,不仅孕育了日本现代主义诗歌的发生、也产生了被称作有“国际野趣”的日本侦探小说、充满谎言的日本儿童文学和记录逃亡的“返迁体验”文学,以及满含“乡愁”的战后中国东北追忆文学等,这些文学都从不同的侧面深刻地折射出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的罪恶。
大连,曾是一个被日本极尽现代技术手段大肆进行都市空间扩张,并被长期殖民统治四十年之久的近代都市,现代“摩登”的都市景象、前卫时髦的都市生活、交织着政治性、文化性、精神性葛藤和矛盾冲突的殖民地都市空间孕育和培养了众多日本著名的文学家和诗人,如五味川纯平、远藤周作、三木卓、清冈卓行、松原一枝、安西冬卫、北川冬彦等都出生在这里或在此度过了人生中最为宝贵的青春时代,并创作了诸多以大连为题材的诗歌或小说。当然,也有很多文学家如夏目漱石、小林爱雄、水上勉等游历过大连,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留下了对大连都市空间的书写。然而,却很少有人知晓,曾经活跃在日本文坛上的侦探小说家们,有很多居然与中国大连这座都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在他们的侦探小说中展现了当时大连的都市空间风貌。这些在异域殖民地都市空间中产生的日本侦探小说由于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生成的一种特殊的文学现象,交织着日本侦探小说家殖民地都市生存体验,因而被赋予了现代性与殖民性对立冲突的双重属性,是纠缠着政治、经济、历史、文化、战争、殖民等多重关系的复杂而立体的存在。对这样的文学加以探究,不仅可以重新审视日本侵略和殖民异国背景下的昭和文学经验,而且还可以重新思考近代以来日本海外体验文学的本质特性。
一、都市空间与侦探小说创作
“都市是现代社会的产物,是人类历史进入现代性的重要标识之一。在高度组织化的现代社会中,工业生产和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带来了人类社会前所未有的空间重组重构,由此催生出真正意义的现代都市。”(谢纳,2012:21)。从18世纪后半期开始,以英国为开端兴起的产业革命,带来的是贯穿整个19世纪欧洲各国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和规模开展的现代都市空间生产、改造和重构。到了19世纪末,欧洲的都市建设已经达到了相当完备的程度。在现代都市空间不断扩张和重组的进程中,融入现代科技与古典艺术的欧式建筑;街灯、林荫道、花圃环绕的花园广场;前卫、现代摩登生活体现的舞厅、酒吧等都市场域与都市空间,与世界各国迅速广泛流行的电影、广播、摄影、列队舞、爵士乐等20世纪都市大众文化共同成为现代主义艺术和文学运动蓬勃发展的巨大推手,催生了各种各样新的文学表现形式。从19世纪初开始,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表现主义、结构主义等一系列现代主义艺术运动和文学运动在世界各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同样,在同一时代、同样背景下产生的侦探小说被普遍认为与现代都市空间的生产与重建所带来的都市文化的迅猛发展密切关联,是新型大众文化、大众文学的代表。日本侦探小说家、评论家平林初之辅就侦探小说的产生与现代都市文化和都市生活的关系作过详细的阐述,他说:“侦探小说必须给予读者以强烈的刺激。与大战前人们的生活相比,现代人的生活节奏急速加快。电梯、出租车、无线广播、飞机,以及其他与之类似的构成机械文明的诸要素,完全渗透交织在现代人的生活当中。以往那些进展缓慢的浪漫主义小说,以及一听就懂的伦理道德说教的教训小说,特别是连汽车、电话都没有的以时代事件为题材的历史小说,早已与现代人的生活割裂开来,那些东西已不能给现代人以任何刺激。而侦探小说在这一点上,更好地满足了现代人的嗜好。”(转自池田浩士,1983:141)在此,平林初之辅揭示了现代都市生活、都市文化、现代机械文明诸要素与侦探小说创作的必然联系。而德国思想家、哲学家瓦尔特·本雅明(ウイルタ一·べンヤミ一,1994:87)则进一步地指出了侦探小说创作与都市空间的关系,他说:“侦探小说的根本性的社会内容便是在大都市的群众当中,个的痕迹的消失。”本雅明将都市空间与生活在都市空间中的个体进行了对比。白天,行走于大都市空间中的“个”的自我被如洪水般的人群所淹没;夜晚,“个”的自我又被高层建筑林立的都市空间所掩盖和遮蔽,在这种“个”的无痕化的都市空间中,不仅潜伏着犯罪的骚动与不安,也为罪犯创造了犯罪的契机。同时,为侦探小说家们扣人心弦地描绘案件始末、丝丝入扣地书写抓捕的曲折过程,提供了重要的创作素材和无限的想象空间。正是由于现代都市空间的不断建构,推动了现代都市建设的不断发展,带来了都市文化的烂熟,使文学家在日新月异的都市空间变革中体验着新型空间感觉经验,极大地推动了侦探小说的发生、发展与兴盛。
同样在日本,如同新感觉派文学的出现、现代主义诗歌的兴盛与东京大地震后急速发展的都市化进程有着密切关系一样,摩登都市的迅猛发展也成为日本侦探小说的发生、发展的必然条件。用小田切进(1965:23)的话来说:“昭和文学史有很多是从关东大地震后的文学动向写起的”。
1923年日本东京大地震后,伴随着“帝都复兴”的重建工程,东京的都市化进程取得了飞速发展。重新建构的东京呈现在人们眼前的是繁华、摩登的现代都市图景,新的都市空间景观如同歌谣中唱到的那样鲜活地呈现在人们的眼前:“东京的中枢是丸内,日比谷公园和两议院,热闹繁荣的帝国剧场,威风凛凛的警察厅”(井上靖等编,1990:27)。而在当时非常流行的歌曲《东京进行曲》中更是形象生动地唱出了东京的摩登都市生活:“伴着爵士乐起舞,饮着甜酒入夜,清晨令人惆怅的细雨中的舞女”(井上靖等编,1990:28),在这样的都市空间中,人们体验着都市文化生活带给都市人的各种感受。当人们在钢筋大理石的都市建筑群中徜徉,在霓虹灯闪烁的橱窗前徘徊,在流淌着爵士乐的舞厅里飞舞,在散发着浓郁西欧味道的咖啡馆里轻斟慢饮,产业革命和商业兴盛使都市人和文学家体验到了都市文化和现代都市空间带给人们的便捷、浪漫和愉悦。“都市空间作为现代生存体验的基本形式,决定了都市人的生存空间体验,同时也决定着文学艺术家的生存空间体验,构成文学的内在生命意蕴。”(谢纳,2012:22)都市空间的生存体验和对空间体验的思考,开启了文学艺术想象的创造空间,刺激了文学艺术家无限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日本迎来了“都市文学”的繁荣。日本文学家们也不断地将对都市的文化感受与生存体验转化为侦探小说的创作元素、题材或素材。如佐藤春夫的《指纹》描写了生活在都市空间中的人,对自我的怀疑和人格分裂;芥川龙之介的《两封信》则揭示了面对都市化的急速发展,人们对自我丧失的不安与恐惧;谷崎润一郎的《白昼鬼语》描写了都市人病态的偷窥癖;江户川乱步的《D坂的杀人事件》对生活在都市空间中的人们,彼此之间情感淡薄现象进行了描写。而《屋檐后的散步者》、《人间椅子》等一系列侦探小说描述了都市中奇怪的幻想和病态的心理。虽然草创期的日本侦探小说存在着表面上追求前卫性,但实质上尚未对西方已经趋于成熟的科学性的实证精神和个人主义思想完全地消化,对复杂的人物内心的剖析和逼真的心理解剖缺乏深度,只能在向怪奇趣味和神秘的浪漫方向倾斜,但是,毕竟日本的侦探小说家们对侦探小说创作给予的热情,对侦探小说理论的探索,对大批年轻侦探小说家的影响与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都市文化的烂熟带来了日本侦探小说的繁盛与发展,也激励着生活在日本海外殖民地的日本文学者开始了侦探小说的创作。这其中,生活在日本殖民地都市大连的日本文学者,也是在大连这座现代摩登都市空间中不断体验着现代都市中各种元素的刺激,孕育了丰富的想象力,激发了无穷的创造力,一部部引人入胜的侦探小说由此诞生了。
二、大连都市空间与日本侦探小说家的殖民体验
正如日本的现代主义诗歌的发生并不是在日本的本土,而是源起于日本的殖民地都市大连一样(柴红梅,2010),当把视角聚焦在“日本侦探小说与殖民地都市大连的关系”时,会发现一个曾被人们忽略的重要问题:二十世纪活跃在日本文坛上的侦探小说家们,有相当一部分人曾有过在日本海外殖民地的生活体验,其中,以曾生活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居多,而且大都与“大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其中,曾生活在大连的日本著名侦探小说家就有十多位,如大庭武年、山口海旋风、岛田一男、樫原一郎、鲇川哲也、南泽十七、西村望、椿八郎、石泽英太郎、加纳一郎等。
那么,大连的都市文化空间如何能孕育出这么多日本的侦探小说家?殖民地都市体验究竟怎样影响了日本侦探小说的创作?在此,有必要做一深入探讨。
大连,自古就是中国的神圣土地,但作为都市自诞生之日起,却不属于中国所有,而是在帝国主义列强的魔掌中被反复蹂躏,特别是在日本的军事侵略和殖民统治之下,历经磨难、饱受沧桑。另一方面,日本殖民者为了永久占领和统治中国东北,为了掠夺更多的资源和财富,也为了满足自身生活的需要,大力开发和拓展中国东北都市空间。这其中,日本殖民统治者历经几十年的经营,使得大连这座都市一度呈现出畸形的“繁荣”和“摩登”的都市景象。著有《大连·空白的六百日》的富永孝子(1999:34)回忆曾经长期生活过的大连都市空间景观时说:“围绕着圆形公园,以重厚的建筑群林立的大广场为中心的景观,与欧洲毫无差异。戴着帽子,身着正装的美丽妇人乘坐马车穿过白色槐花荫下,伴随着蹄音渐渐消失在浪速街和伊势街的深处,这种风景在日本是绝看不到的。”富永孝子不惜笔墨描绘的“大广场”是大连代表性的空间场域,围绕在圆形广场周围的一幢幢风格迥异的欧式大楼堪称摩登都市大连的标志性建筑,很多游历过大连,或在大连有过长期生活体验的日本人都会对这里记忆犹新,这里也成为很多日本文学作品中经常提到的风景。鲇川哲也(1996:11)凭借殖民地大连都市生活原体验而创作出来的侦探小说《佩德洛夫事件》,开篇便生动形象地描绘出国际色彩浓郁但却有殖民地特色的摩登都市大连的都市空间风景:“‘大广场’是这个都市的中心。其周围呈圆弧形状,分别耸立着领事馆、宾馆、银行、警察署等建筑。有轨电车沿着这一线路穿行而过。内圆是个小公园,建造了花坛,放置着长椅。在公园的中心,初代军政官某将军的铜像,摆出一幅得意扬扬的姿态,睥睨着四周。据说是曾经从欧洲归来,单骑横断西伯利亚的勇敢无比的帝国陆军军人。在那里的长椅上坐着年轻俄罗斯母亲和幼儿,她们正在给鸽子扔吃的。”一个欧味十足的“大广场”、各式风格的欧式建筑群、舒缓轻盈的有轨电车、一个个簇拥着鲜花的花坛、洋式长椅、飞来飞去的白鸽、三三两两的俄罗斯人、日本将军的铜像……一幅国际化殖民地摩登都市空间景象即刻跃然纸上。而被称作“大连头号摩登少年”的侦探小说家大庭武年(西原和海,1999:51),对大连都市空间中的一切时尚前沿的事物都非常感兴趣,就连当时世界上非常流行的赛马比赛,也是大庭绝不放过的体验现代摩登生活的方式。众所周知,“跑马场”是现代都市的一种新奇消费形式之一,在那个年代,拥有跑马场的中国都市并不多。这其中,大连较早出现了跑马场,并曾多次举办过国际赛马大会。而大庭的《赛马会前夜》就是以“星之浦”旁边的跑马场和牧场为舞台创作的。可想而知,大庭如果不经常去跑马场观看比赛,体验观看赛马的生活,绝不会写出出神入化的以赛马为线索的侦探小说。而大庭武年(2007:2)的《十三号室的杀人》为读者展现了一幅大连避暑胜地“星之浦”的美景:“那是日本唯一的殖民地都市D市郊外的号称‘月光海岸’的海滨避暑地发生的事情。……‘月光海岸’就是将美国风格的人工设施和大陆自然风情巧妙融合的、东洋少有的异国情调的海岸避暑地。每到旺季,那里是唯一能够吸引满洲支那一代内外有闲阶级,让人感到仿如来到美国本土一样、呈现着豪华和繁盛景象的地方。”藤田知浩(1999:81)对大庭的这段描述评价说:“D市就是满洲的大连市。虽然小说中像医院等都是用阿拉伯字母作以假称,但实际上都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场所。这种真实感不愧是只有在满的作家才能表现出来的。本作品描述了涉及外国人的杀人事件,的确是地道的国际都市大连才有的题材。”不难看出,正是由于有着长期生活在大连都市空间中的切身体验,才使得生活在此的包括大庭武年在内的日本侦探小说家们深切地感受到自己与前卫生活交融,与时尚前沿同步,与摩登世界的连接,现代都市文化空间中的各种摩登元素便自然而然成为小说创作不可或缺的内容。
鲇川哲也1950年发表的《佩德洛夫事件》是日本战后第一本专门发表推理小说的《宝石》杂志“百万元悬赏文学作品大赛”一等奖的佳作。这部作品被认为是日本推理小说界第一部凭借列车时刻表侦破案件的侦探小说。日本侦探小说家江户川乱步(1953:20)曾经这样评价鲇川哲也巧用列车时刻表创作侦探小说的意义和价值:“我小说中择取的犯罪骗术例统括起来有821例,其中‘一人身兼二职’型有130例,很明显出现频率最高。其次是‘密室’骗术有83例。虽然人们都说黑浦是巧用列车或汽车,挤出千钧一发的时间制造不在现场证据的名手。但是他的作品当中利用交通工具制造骗术的充其量也不过9例而已。鲇川哲也发表《佩德洛夫事件》是在1950年,所以利用交通工具制造骗术,特别是列车时刻表骗术,这在日本还是第一部,毫无疑问鲇川哲也就是这个人。”而《佩德洛夫事件》这部小说正是作者根据当时大连“亚细亚”号特快列车真实的列车时刻表创作出来的。鲇川哲也为了证明这一点,还特意附上了当时“亚细亚”号的各趟列车时刻表。因此,小说当中出现的车次、发车时间、行程路线等等一切都与事实完全一致,真实准确。也就是说,如果真像小说当中描述的那样实施杀人方案的话,完全可以做到天衣无缝。日本推理小说家松本清张也有过类似的经历,为了增添小说所描述的事件的真实性,他的推理小说开山之作《点与线》中使用的火车与飞机时间全部是真实的,为了证明这一点,还在小说的后面特意注释加以说明列车、飞机时刻表的出处。就此,王志松(2013:55)指出了侦探小说创作与作家生活体验的关系:很多侦探小说的破案方式,看似偶然,实际上有其必然性,“偶然的灵感往往就产生于他们冥思苦想时的某些生活体验”。而山前让则一语道破了《佩德洛夫事件》这部侦探小说的创作与作者大连都市空间生活体验的关系:“据说因为满铁职员的家属可以免费乘坐列车,所以二十岁左右的鲇川哲也经常外出旅行。看来非常喜欢满洲国中部的哈尔滨,无论冬夏,他总是无数次地去那里。”①正是由于有了无数次乘坐“亚细亚”号特快列车来往于大连和哈尔滨之间的亲身生活体验,鲇川哲也才会对列车时刻表如此谙熟于心,进而促发了他利用列车时刻表创作侦探小说的想法。而日本本土直到27年后,东京申办奥运会的时候才修建了第一条可以与大连“亚细亚号”媲美的特快列车。鲇川哲也的殖民地大连都市生活体验带给了日本昭和文学史第一部巧用列车时刻表创作的侦探小说。
然而,殖民地大连都市空间中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浪漫惬意的街心花园、灯红酒绿的酒吧、摩肩接踵的舞厅、散发着西洋味道的咖啡馆、亚洲时速最快的“亚细亚号”特快列车……所有这些现代、摩登、时尚的都市生活空间并不属于生活在同样都市空间中的被压迫、被剥削、被残害的挣扎在水深火热当中的中国人。大庭武年(2007:272)多次考察大连的中国人居住区后,不无感慨地描述了中国人的生存状态:“满人街绝对是猎奇之地。秩序混乱、凄惨、被压迫的反抗,在那附近只要稍稍猎取,我认为就能挖掘出比小说还怪异的事实来。提起夜晚的满人街,那简直是连江户川乱步都描述不出来的光景。然而犯罪事件反倒不浮于表面化,从黑暗中开始到黑暗中结束的被葬送也浑然不知的人生,在那里如蛆虫一般胡乱地存在着。”很多日本人并不去关注或不愿过多地思考,为什么在灯、光、电闪烁的摩登幻影的阴暗处并存着中国人贫穷、肮脏、偷盗、卖淫、死亡等悲惨和残酷的现实,不去追究,也不可能追究造成这种现实的罪魁祸首。但是,日本人却知道,这种真实光景与这般“摩登的”、“繁华的”,号称“东洋的巴黎”的都市格格不入,形成一种极不和谐的都市风景。因此,自从1905年日本占领了大连,将其变成殖民地之后,日本人不仅要居住在树木繁盛、风景秀丽,依山傍水的好地方,而把中国人排挤到荒凉和偏僻的地带,而且还要严格地划分出日本人居住区和中国人居住区的界限。很显然,这种划分具有强烈的种族歧视和鲜明的殖民压迫特点。日本人侵占了中国东北之后,口里总是高唱着“王道乐土”、“五族和谐”,所谓的“乐土”其实只是日本人自己的乐土,只有日本人才过着悠然自得、富裕幸福的生活,反倒是生活在自己国土上的中国人不得不受尽压榨和剥削。对日本人来说,令他们陶醉的欧味十足的大连都市空间风景带给他们的是难以忘怀的乡愁和甜蜜的回忆,而对中国人来说,那些却是摆脱不掉的噩梦。然而,这不才恰恰是殖民地摩登都市的真实写照吗?殖民地文学评论家川村湊曾对生活在大连或来连游历过的日本作家在描述大连时所犯的通病进行过犀利地批评,他说:
安西冬卫、中岛敦、清冈卓行各自的大连均择取了“近代日本”和“西欧”、支配的“日本”和被支配的“中国”,抑或西欧性的现代主义和亚洲的本土主义的对立和冲突。却忽视了无论是在历史性,还是在政治性上,作为由俄罗斯、日本、中国这三个民族如漩涡状纠葛在一起的中心地,这个城市被形塑起来的本质性条件。
他们并没有看到,比如作为苦力的满人,他们拥有牢固的文化和风俗,是并没有被同化的中国人;他们也不想去看在身边的中国人街上的露天市场和鸦片窑的颓废和黑暗。因此,总是缺失一些要素。……遗漏了努力看清在那里作为政治、文化、语言角逐和葛藤之所在的殖民地的本质。那么,从这样的视点眺望旧殖民地都市大连,最终逃脱不掉偏执的存在于个人内部的乡愁和好奇心的范围罢了。
(川村湊,1990:96-97)
那么,殖民地摩登都市的本质是什么呢?其本质就是那里是东洋人和西洋人聚集的、贫穷和富有对立的、豪华别墅和贫民窟并存的、布满欺骗和犯罪的殖民地摩登都市空间,它弥漫着西洋的味道,但同时也鲜明地呈现出被侵略、被压榨、被剥削、被摧残的掩盖于浮华背后的黑暗与恐怖。
这种渗透着现代与殖民双重属性的都市空间为文学创作提供了独特的现代图景和殖民体验,带给生存在殖民地都市空间、政治空间、日常生活空间融为一体的以“一等国民”自居的日本文学者新型的都市生存经验,由此形成现代性与殖民性双重属性交融的空间意识,孕育了文学家的主体审美经验及艺术创作理念,刺激了日本作家侦探小说文学意识的生成。
三、战争与殖民批判:大连都市空间中的日本侦探小说
如上所述,曾经生活在大连的日本侦探小说家并不少,而且,在他们的侦探小说中,有很多还是以大连为舞台创作的。其中较为著名的包括大庭武年的《十三号室杀人》、《赛马会前夜》、《白杨山庄事件》、《小盗儿市场杀人》;鲇川哲也的《佩德洛夫事件》;石泽英太郎的《烟囱》;加纳一郎的《破裂的旅程》、《黄海大逃亡》、《特快“亚细亚”号杀人行》;宫野丛子的《满洲家书》等。
鲇川哲也的《佩德洛夫事件》虽然在1950年发表,但是,最初创作于1943年,正是日本太平洋战争进入白热化阶段的时候。在这样的战争背景下,生活在中国东北大连的鲇川哲也亲眼目睹了战争色彩浓烈的“伪满洲国”现状,作者在《佩德洛夫事件》中,通过刑警鬼贯的眼睛,借用鬼贯的语言,直言不讳地表达了对战争的质疑和批判:
侧耳倾听,仿佛能听到隆隆的炮声。炒爆豆似的机关枪声来自俄罗斯一侧。到处弥漫着硝烟的气息、血腥的气味。日本兵嗷嗷的叫声和俄罗斯兵呜啦的喊声交错呼应。……
炮弹炸开了,掀起一丈多高的沙尘。到处蠕动着负伤的士兵。当一阵炮声响过之后,他们永远地沉默了。
血腥之风掠过鬼贯的鼻尖。这是残酷的战争造成的悲哀的牺牲者们的鲜血。
(鲇川哲也,1996:105)
虽然小说描述的是1904年日俄战争的情景,但是,鲇川哲也创作这部小说时正是日本侵华战争陷入泥潭化,太平洋战争节节败退,连日本的学生都必须穿上戎装,随时准备出征奔赴战场的时代。年轻的鲇川哲也也是因为学生兵的训练过于严酷而患上了胸膜炎,从日本的学校回到大连,在家休养时开始着手创作《佩德洛夫事件》的。那么,在这种战争背景下,在小说中直言不讳地发表对战争的批判,他的勇气和胆量令人佩服。因为当时在日本的国内,正是采用严酷的手段镇压反战思想的时候,很多曾经反战的文人最终不得不公开宣布转向,或者采取了沉默的态度。在文学界,就连一直被认为是大众文学的侦探小说也被禁止出版发行了。因此,像鲇川哲也公然批判战争的言论,如果是在日本的本土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应该看到,或许正因为鲇川哲也没有生活在日本的本土,而是生活在开放的国际性殖民地都市大连才会有这种想法和胆量吧。笠井杰对此进行了如下评述:
在本国,侦探小说被禁是1930年代后半的时候。大概殖民地的满洲属情报局言论统治框架外的地方。呼吸着作为“文明”殖民地之“先进的满洲”的空气而培育起来的青年,读着横沟正史的历史破案小说和木木高太郎的科学小说,肯定会觉得这些太落后于二十世纪的侦探小说了,于是动笔自己写,想想这一点也不会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笠井杰,1996:113)
正如笠井杰所说,鲇川哲也是生活在日本情报局言论控制范围之外——到处充满着异域风情的国际化港口、殖民地都市空间中——的年青文学者,这里无论在生活上,还是在文化娱乐上,乃至于在交通设施、行政管理等等很多方面远远超过了日本的本土,作为“一等国民”的日本人过着怡然自得、自由自在的生活。这些为在这里孕育起来的作家、诗人们提供了良好的创作环境,从而使他们创作的作品多带有自由主义的风格,于是当时很多人都称大连的这些文学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自由主义的大连思想体系”。这与胸中充满着“建国精神”、“协和理念”,聚集在“新京”(长春)的“日本浪漫派”作家们形成鲜明的对比。文学评论家川村湊(1998:72-73)在评价大连的日本作家作品特点时曾说:“大多数作品表面上歌颂‘五族协和’的同时,却揭示了‘五族’阶层的差别状况和民族心理的葛藤。……隐隐地批评了那些口号的虚妄。”或许鲇川哲也也受到了“自由主义的大连思想体系”的熏陶,能够比较自由地直抒胸臆,得以明确地表达了自己对战争的批判吧。
石泽英太郎的侦探小说《烟囱》发表于1963年,是入选《宝石》“新人二十五人作品选”的佳作。石泽在大连度过了人生最宝贵的幼年、少年和青年时代,他是殖民地都市大连由兴盛走向衰亡的亲历者,亲眼目睹了摩登大连的繁盛与浮华,也体验到了日本失败后到返迁回国前的辛酸与磨难。然而这些波澜起伏的人生经历和历练或许恰恰变成了石泽宝贵的人生财富,使之不断地积淀和酝酿,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的小说创作。针对这一点,评论家桥本雄一(1999:54)曾非常明确地指出了殖民地生活体验对石泽创作的影响。他说:“他始终凝视困苦生活中挣扎和陷入人生窘地的人们的那双眼睛,总是清澈而敏锐。非要说的话,培育这双眼睛的是在近代日本殖民地中的实体验。”
《烟囱》虽然不是石泽英太郎的处女作,但却是以大连为背景,融入了自身真实的生活和返迁的痛苦体验而创作的第一部作品。除此之外还有一部涉及中国东北的、于1966年发表的《凤尾草之行》。从那以后,石泽再没写过有关中国东北或大连的作品。直到晚年石泽患抑郁症自杀前才开始了有关他的出生地和成长地大连的创作,最终汇集而成《别了,大连》,并在他去世后出版。也就是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烟囱》是石泽唯一一部以大连为舞台,特别是以日本失败后,俄罗斯人进驻大连,在这个极为特殊的时代,生活在大连的中国人、俄罗斯人和日本人之间的微妙关系和感情纠葛为题材的侦探小说。由此可见这部小说的特殊性和重要性。
故事描写的是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一直生活在殖民地都市大连,还没有返迁回国的日本人,与当地的中国人和派军队驻扎在这里的俄罗斯人,在同一个工作场所——大连电力公司,共同工作的这一时期发生的日本姑娘美佐子失踪事件。《烟囱》虽然以破解密室中“人间蒸发”的侦探小说形式为依托,但却是以日本战败后的原“日本殖民地”大连为舞台,以“故乡”丧失和身份认同为主题的现实主义小说。小说中的美佐子和作者石泽英太郎一样,同样是出生于大连,生长于大连的日本人,在日本战败后,日本人即将返迁回国的时刻,失去父母的孤儿美佐子对自己的未来无从选择,最终摆脱不掉“故乡”丧失的命运和身份认同的痛苦折磨,在无奈和哀怨中自杀。出生在中国、在中国度过了人生宝贵的青少年时代的二代日本殖民地人都会有和美佐子一样的心态,作家城岛国弘曾就生活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日本人的身份认同问题阐述过一段发人深省的话,他说:
对返迁者来说,在满洲生活的前半生,或许是应该有所补偿的真空吧,不管怎样他们有了个度过后半生的故乡。但是无论我们住在哪里,我们的魂魄并没有在那里,因此永远都是放浪的异邦人。世界史无论怎样凭借只言片语的正义对这种行迹始末加以注解,但是永远涂抹不了扎根于我们内心的地图,这是连我们自己也改变不了的事实。
(城岛国弘,1986:序言)
日本军国主义的军事侵略和殖民扩张最终以失败告终,然而却遗留下了一大堆不可回避的历史问题,而这些必须由被他们抛弃的曾在殖民地生活过的日本遗民承担与抉择,这是多么残酷而又无法摆脱的现实。显而易见,在美佐子心中,大连并不是异邦之都,而是真正意义上的“故乡”。而日本只不过是冠以“祖国”名称的陌生之地罢了。那么什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故乡”呢?“故乡”应该是难以割断的生命的“根”,是精神得以寻求归宿的“魂”。对在大连这块土地上养育起来的大部分日本人来说,大连才是自己难以隔断的“根”,大连才是精神能够得到慰籍的“魂”,大连才是自己内心中真正的“故乡”。然而,如果不返迁回日本,难道能在大连永久生活吗?大连虽是生他养他的地方,可这里终究是中国的土地,是日本人靠侵略的手段掠夺霸占而来的土地,这里一开始就不属于日本人,又何来“故乡”而言?
石泽英太郎把曾为殖民地生活的日本人的“故乡”丧失与身份认同的纠结与痛苦,把对日本的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带给日本民众的沉痛创伤都通过《烟囱》这部侦探小说倾诉和表达出来。或许是由于这种伤痛太深,或许这种莫名的“空虚”和“孤独”过于沉重,致使石泽不愿也不敢再触及心中的那道伤痕。即便在战败后的日本以“满洲”为题材的严肃小说和电影盛行一时的时代,石泽自从创作初期写过《烟囱》和涉及“满洲”的《凤尾草之行》之外,就再也没有写过一篇这方面的小说。直到石泽的晚年,一直沉默的大连,一直沉默的“满洲”,才如决堤的洪水一般倾注而成《别了,大连》的小说集。然而,就像小说集的名字那样,石泽在与大连诀别的同时,也与自己的生命做了诀别,这是对日本的侵略战争与殖民统治最有力的批判。
应当看到,日本许多侦探小说家都是在中国东北地区成长起来的,特别是一些著名的侦探小说家还都曾长期生活在大连,这些侦探小说家作品中的异国情调和大陆风情来源于中国大陆风土,他们的创作灵感和丰富的想象力离不开殖民地大连都市文化空间的培养,这些都潜移默化地融汇到他们的文学创作当中,使之具有了独特的魅力,在日本昭和文学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数量有限,但殖民地大连都市空间中生成的夹杂着现代性和殖民性双重属性的日本侦探小说有了一些对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的批判内容,它让我们看到,大连都市空间中的日本侦探小说并不是人们普遍认为的,只是单纯为娱乐和消遣的不入流的大众读物,它是具有一定的现实主义批判精神的文学创作。特别是像大庭武年的《小盗儿市场杀人》揭示了看似“摩登”、“繁盛”的殖民地都市大连浮华背后的真面目;鲇川哲也的《佩德洛夫事件》则直言不讳地批判了战争的罪恶;石泽英太郎的《烟囱》倾诉了日本遗民“故乡”丧失和身份认同的悲哀与痛苦,间接地批判了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的罪恶。当我们把视角聚焦在“殖民地大连都市空间与日本的侦探小说”的关系时,很多未曾注意到的事情变得清晰明了,中国大连这座都市与日本昭和文学的必然联系和在日本昭和文学史上的作用便会鲜明地凸显出来。
①此评论出自鲇川哲也『ぺトロフ事件』的后序,山前让的注文「人と作品鮎川哲也」。
标签:文学论文; 小说论文; 日本生活论文; 大连生活论文; 大连历史论文; 殖民扩张论文; 大连电影论文; 鲇川哲也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