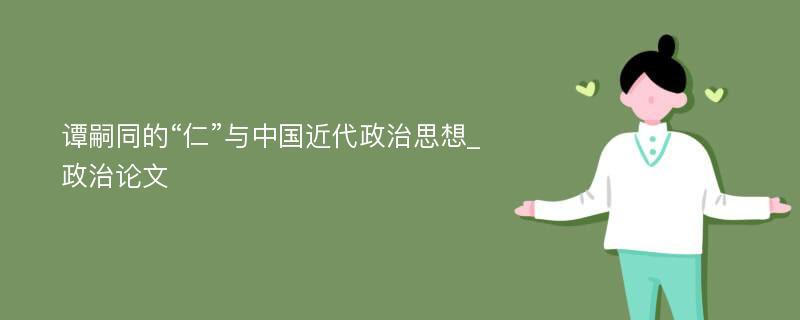
谭嗣同《仁学》与中国近代政治思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近代论文,思维论文,政治论文,谭嗣同论文,仁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63(2001)01-0003-05
清末是中国由古代的君主——臣民的政治文化向近代的民主——公民的政治文化转型的时代。自幼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谭嗣同,面对甲午战争失败的惨烈现实,将关注的视域转向西学,并将积淀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与有限的西学知识融汇贯通,以构筑连通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近代政治文化的通道。本文试图解析谭嗣同《仁学》建构中国近代政治文化的独特思维,为我们合理评价独特而艰难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转型,提供一个有借鉴意义的思维视角。
一 两种类型文化的转换——中国近代政治思维的难点
公民与臣民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是享有法定的权利和义务的主体,而后者则只须履行绝对义务。与之相关,民主——公民文化是指公民对此权利和义务的明确取向、高度自觉,能在这种政治上的权利意识和义务意识指导下参与政治。君主——臣民文化却是指臣民对于忠君义务的取向和自觉,臣民的政治信仰、政治价值、政治态度,就是崇拜、忠于、须从专制君主的统治。在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以后,中国终于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逼迫下进入半封建并殖民地的社会。这时,封建君主统治亦摇摇欲坠,而传统的臣民政治文化仍在竭力维护宗法型君主专制政治。近代以来积极从事政治革命,试图建构民主政治的精英们,则大胆地引进、传播西方资产阶段的天赋人权论、社会契约论和自由、平等、博爱等政治文化理念,并从政治观念、文化意识、社会心理以及国民性等各个层面,展开对以忠孝道德为主要内容的臣民文化的批判和反思,从而揭示这种文化的各种表现以及它维护封建君主专制的实质。在此基础上,谋求实现中国政治文化的转型,即由传统的臣民文化向近代的公民文化过渡。
然而这种转型决非一蹴而就,而是举步维艰。因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转型为近代公民政治文化,是和中、西文化的问题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古代中国在进入文明社会以后从未建立过民主政治制度,君主专制是古代中国的唯一政体形式,与之相应,古代中国亦未产生适应并服务于民主政体的公民政治文化,故而必须对传统政治文化采取一种严厉批判的态度。然而,中国又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古国,中间从未出现过中断。传统政治文化不仅是指一系列系统的政治理论和学说,还包括一种稳定的心理结构、思维方法、价值信仰。因而,它已不是一个人身上可以任意脱换的衣服。而是和中国人联为一体的血肉、骨骼。另一方面,自19世纪4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列强的武力侵略,欧美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以及与之相应的公民政治文化,作为当时的一种先进文化亦随之传入中国。因而在封建专制的中国实行政治制度的变革和政治文化的转型过程中,自然会尽量引进西方近代的民主政治文化。这样,近代知识精英们便处于一个两难境地:既不可能将中国近代政治文化的转型约化为全面摒弃中国传统文化,引进西方文化,而是力图在沟通中西文化的基础上,进行一种创造性的转化,即在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之间构筑一个连通二者的通道,为最终完成政治文化的转型提供既符合时代特征,又契合中国传统文化背景的思想文化。而如何实现这种创造性的转化,则成为近代每一个知识精英必须面对的难题。谭嗣同亦不例外。
二 连接两种类型文化的尝试——《仁学》的政治思维
谭嗣同的《仁学》即是试图解答这一时代难题的有益尝试。甲午海战的失败,使谭嗣同跳出臣民政治文化的窠臼,认为“主于为民开其智慧”(注:《代拟上谕》,《谭嗣同全集》(增订本)550页,蔡尚思、方行编,中华书局1998年6月出版。以下简称《全集》。)的西学是变革中国的依据,主张“尽变西法”,(注:《上欧阳中鹄书》,《全集》168页。)所以他大胆地引进、倡导、服膺西方的民主政治思想,赞扬西方近代的民主平等制度,谭嗣同称颂法国人学问冠绝地球,故能提倡民主,“誓杀尽天下君主,使流血满地球”;(注:《仁学三十四》,《全集》342页。)美国亦不甘落后,“有华盛顿倡民主于前,林肯复释黑奴于后,义闻宣昭,炳耀寰宇。”(注:《仁学四十四》,《全集》361页。)以此为出发点,谭嗣同严厉地批判中国古代的君主专制制度与臣民文化,他说:“二千年来君臣一伦,尤为黑暗否塞,无复人理,沿及今兹,方愈剧矣”,(注:《仁学三十》,《全集》337页。)指责两千年来秦始皇式的暴君“皆大盗也”。(注:《仁学二十九》,《全集》337页,335页。)他们“竭天下之身命膏血,供自盘乐怠傲,骄奢而淫杀”,(注:《仁学三十一》,《全集》339页。)“其残暴无人理,虽禽兽不逮焉”。(注:《仁学三十七》,《全集》349页。)他还历数清朝统治者罪行,指斥他们起于游牧部落,竟将全中国视为牧场,所谓驻防,所谓名粮,所谓厘捐,所谓文字之狱,用尽一切刑名,惨酷压制榨取人民。因此,谭嗣同认为废除君主制制度已成为时代必然。
为此,谭嗣同运用西方“社会契约论”的基本理论,重新阐释君主制的起源以及君民关系,提出“废君权,兴民权”之政见。他说:“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夫曰共举之,则因有民而后有君;君末也,民本也。……夫曰共举之,则且必可共废之。君也者,为民办事者也;臣也者,助民办事者也。赋税之取于民,所以为办事之资也。如此而事犹不办,事不办而易其人,亦天下之通义也。”(注:《仁学三十一》,《全集》339页。)谭嗣同认为君并非天生就存在,只不过是民为协调、处理公共事务而共同选择、推举的普通一民;而且君食民之税,因此君主必须为民办事,如若不然,则会为民所废黜。这样,从根本上戳穿了“君权神授”的幌子,从而使中国传统的政治信仰失去了理论依据。谭嗣同进而认为既然君是由民“共举”的,有民而后有君,那么民是“本”,而君是“末”。他以此为依据,猛烈地抨击被“腐儒”奉为“理之自然”的“事君以忠”和“为君死节”的观点,说:“君为独夫民贼,而犹以忠事之,是辅桀也,是助纣也,其心中乎,不中乎?呜呼,三代以下之忠臣,其为辅桀者几希”,(注:《仁学三十二》,《全集》340页。)将忠君视为“辅桀”、“助纣”。又说:“君亦一民也,较之寻常之民更为末也。民之与民,无相为死之理,本之与末,更无相为死之理”,(注:《仁学三十一》,《全集》339页。)故“为君死节”乃“大悖者也”。民不仅无需“事君以忠”、“为君死节”,而且还认为在发现“彼君之不美”时,可将之罢黜,甚至“从得而戮之”,(注:《仁学二十七》,《全集》374页。)这是作为天下之“本”的民固有的权力。
顺承“废君主,兴民权”之理路,谭嗣同对君主专制制度赖以维系的精神支柱——纲常名教,予以无情地批判。他说:“今中外皆侈谈变法,而五伦不变,则举凡至理要道,悉无从起点,又况于三纲哉!”(注:《仁学三十八》,《全集》,351页。)正是有见于此,谭嗣同对名教纲常的产生作出了具体而深刻的分析:“仁之乱于名也,亦其势自然也。中国积以威刑钳制天下,则不得不广立名为钳制之器。如曰仁,则其共名,君父以责臣子,臣子亦可反之君父,于钳制之术不便,故不能不有忠、孝、廉、节一切分别等差之名,乃得以责臣子曰:尔胡不忠?尔胡不孝?是当放逐也,是当诛戳也。忠孝既为臣子之专名,则终必不能以此反之。”(注:《仁学八》,《全集》299页。)谭嗣同从公民政治文化强调权利与义务密不可分的理念出发,认为君臣父子间的各种责任和义务都不是单方面的,而是双方的,即“共名”,所以君父可以用“不仁”的罪名指责臣子,臣子亦可用同样的理由指责君父。而专制君主为“钳制天下”,将忠、孝、廉、节等各种名分专用于指责臣子,而臣子则没有这种权力,否则被视为“不忠”、“不孝”、“寡廉”、“失节”,这种要求臣子单方面履行绝对义务,而君主独揽各种权力的纲常名教,违背了公民政治文化的权利与义务人人平等的原则。从这种原则出发,谭嗣同审视“五常”之后,说:“五伦中于人生最无弊端有益,无纤毫之苦,有淡水之乐,其惟朋友乎。顾择交何如耳,所以者何?一曰‘平等’;二曰‘自由’;三曰‘节宣惟意’,总括其义,曰不失自主之权而已。”(注:《仁学三十八》,《全集》249页。)他肯定这一伦是因为它体现了民主、平等、自由的公民文化原则。所以他认为朋友不独贵于四伦,而且是四伦之圭臬,如果以朋友之道贯通其它四伦,则四伦可废。谭嗣同试图通过批判、否定“君权神授”与纲常名教,冲决君主专制与臣民文化的网罗,从而效仿西方建构起以民主、平等、自由为理念的公民政治文化。
然而,在这一过程中谭嗣同并未抛弃中国传统文化,而是通过重新诠释儒家的仁学思想、民本观念作为这种民主思想、公民文化的理论依据和思想基础。
“仁”来源于中国古代的儒学。在原始儒学那里,“仁”主要是一个伦理道德范畴。孔子就建立了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仁”是一种道德规范体系,同时亦是一种道德情操和思想境界。儒家学者希望寻找仁道的内在源头和外在依据,他们从人的内在心性中找到仁的源头,从精神权威的天道中找到超越性的客观依据,从而使儒家的仁学走向本体化。谭嗣同直接以“仁学”命名这部重要著作,表明他对“仁”的社会道德意义与宇宙本体意义的双重继承与发展。从人文意义而言,孔子的仁学包含了以人为本和仁者爱人的观念,谭嗣同继承了仁学的这一思想传统,他提出:“‘仁’从二从人,相偶之义也。”(注:《仁学自序》,《全集》289页。)在阐发“仁”的本义时,他是从“二人相偶”的人本观念了发。故而他亦承认“仁”与伦常、礼仪的关系,认为“夫礼,依仁而著,仁则是自然有礼”,“礼与伦常皆原于仁”。(注:《仁学十四》,《全集》312页。)可见,谭嗣同所阐发的仁学,继承了儒家以人为本和仁者爱人的人文意识,为其倡导民主、博爱观念奠定了思想基础。从本体意义而言,谭嗣同以“通”来界定“仁”,认为“‘仁’以通为第一义”,仁具有第一义的通,故而有可能使天地万物、人伦社会不至于产生“隔”和“塞”,从而有利于建立平等、自由的社会政治文化。
与仁学一样,谭嗣同将中国传统民本观念作为建构公民文化的重要理论依据和思想基础。“民本”思想在中国起源很早,《尚书》中已有“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之灼见。历代许多思想家都重视这一思想,先秦时期,孔子提出以“仁”为中心的人本思想,孟子阐发了“民贵君轻”的民本理念,直至明末清初,启蒙思想家王夫之、黄宗羲更是提出诸多颇具“民主性”之政见。王夫之对“一天下之权归于人主”的封建君主制度表示强烈不满,反对那种将天下当作“一姓之私”的封建王朝的“帝统”观念;认为君应“循天下之公”的原则治理天下,必须“以天下之财供天下之用”,“以天下之禄位供天下之贤者”,(注:《读通鉴论》卷三134页,卷二十七1082页,《船山全书》,岳麓书社1988年版。)并从“公天下”的思想出发,提出君权“可禅、可继、可革”(注:《黄书·原极》503页,《船山全书》,岳麓书社1988年版。)的思想。黄宗羲亦认为“天下为主,君主客”,“臣之与君,名异实同”。(注:《明夷待访录·原臣》,《黄宗羲全集》第一册5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谭嗣同将这种强调民的政治地位以及反对君主专制的思想加以继承和创发,使之成为其民主思想必不可少的理论依据。
总之,谭嗣同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底蕴,以西方公民政治文化为模式,试图建构“废君主,倡民主,变不平等为平等”(注:《仁学三十》,《全集》337页。)的政治文化,以连接古代的臣民文化与近代的公民文化,是终实现中国政治文化的转型。
三 “不中不西,亦中亦西”——政治思维的双重“误读”
谭嗣同所建构的这种政治文化,正如人们所评价的,体现出“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思想特点。这是由于,他在融通中与西、古代与近代的政治文化的过程中,表现出了双重的“误读”。
一方面,谭嗣同“误读”了西方的自由主义、民主思想,以传统中国的民本主义政治理想与仁学的价值观念去诠释西方的民主与平等。他说:“西人悯中国之愚三纲也,亟劝中国称天而治;以天纲人,世法平等,则人人不失自主之权,可扫除三纲畸轻畸重之弊矣。固秘天为耶教所独有,转议孔教不免有阙漏,不知皆孔教之所已有”(注:《仁学三十九》,《全集》351页。)他认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早已存在反对君主专制,倡导民主、自由、平等的观念。这种“西学中源”说的观念不仅是为了使西学传播具有合理性,同时也开启了一条以中学解读西学之理路。谭嗣同在继承和发展仁学意义的基础上,诠释了平等、自由理想。宋明儒家在“仁”学中将宇宙之生生不息的本质归之为仁,主张仁者应达到万物一体的境界。程颢主张“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仁者浑然与物同体”(注:《遗书》二上,《二程全集》15页,17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谭嗣同亦肯定仁者与天地万物一体的精神境界,他说:“仁者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注:《仁学界说》,《全集》291页。),并表现为“通天地万物人我为一身”,他认为这种精神境界便是绝对的自由、平等。谭嗣同将这种思想比附《庄子》:“闻在宥天下,不闻治天下”一语说:“‘在宥’,盖‘自由’之转音”,(注:《仁学四十七》,《全集》367页。)并认为只要人人绝对自由、平等,便能实现大同理想。这主有可能将自由、平等建立在儒家个体修身的基础之上,它更多体现为一种个人精神境界上的自由与平等;尤值得指出的是,这种精神境界的思想文化基础是社会群体为本位的价值观念。但是,西方的自由平等是明显不同,它是根据天赋人权的自然法则,认为人人生而自由平等,人生来就有人身权利,即人身自由权,同时,这种自由平等是以不防害他人的自由平等为前提条件的。事实上,这种自由平等是以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资产阶级市民社会为基础的。因而,这样一种平等和自由只不过是商品所有者的平等和自由,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基础上的平等和自由。而且,西方政治文化中的自由、平等完全是建立在个人本位的价值观念的基础之上,完全是一种个人主义的自由、平等。故而谭嗣同以社会群体价值观念为基础,以儒生精神境界的仁学诠释自由平等时,显然“误读”了西方的公民文化理念。
不仅如此,谭嗣同以中国传统民本思想诠释民主时,将民主等同于民本,他说:“孔学衍为两大支:一为曾子传子思而至孟子,孟故畅宣民主之理,以竞孔之志;一由子夏传田子方而至庄子,庄故痛诋君主,自尧舜以上,莫或免焉。”(注:《仁学二十九》,《全集》335页。)尽管谭嗣同也提出“废君主”,但他所主张废除的只是暴君,而不是开明君主。谭嗣同将光绪视为“圣君”,故而在变法陷入困境之时,他深夜造访袁世凯,以死相胁,要求袁出兵营救身陷囹圄的光绪皇帝,“以报圣恩”。变法失败以后,慨然提出:“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注:梁启超《谭嗣同传》,《全集》556页。)最后英勇就义,其报答光绪知遇之恩之意显而易见。可见,谭嗣同继承了历代政治家渴望由开明君主来实施民本政策的思想。正是有见于此,他认为民主即是“君民共主”。而西方的民主是建立在批判封建等级和教会特权的基础上的,将君主视为民主的对立物,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卢梭就说:民主制最凶恶的敌人便是君主制。(注:卢梭《社会契约论》,转引自《卢梭的社会政治哲学》14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因而他们认为,为建立、实行民主制,就应当对君权加以限制,甚至废除。由此可见,谭嗣同的民主思想与西方的公民文化确有不相吻合之处。
在“误读”西方公民文化的同时,谭嗣同亦“误读”了中国古代圣贤的仁学与民本观念,以西方的民主意识、公民文化去理解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
仁学是中学的,体现了鲜明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特点。但是谭嗣同在诠释“仁”的精义时,融进了西学的平等、自由、博爱等西方近代重要的政治原则。谭嗣同认为仁就是“平等”,他在“仁学界说”中反复强调“仁以通为第一义”,(注:《仁学界说》,《全集》291页,293页。)“通之象为平等”。“平等者,致一之谓也。一则通矣,通则仁矣。”使得仁学发生了质的变化,成为一个具有近代人文意义的观念。然而儒家所讲的仁爱是有等级差别的,不是平等的,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之间以及邻里,国人之间的爱是不同的。谭嗣同将这种等差之爱归之于名,他说:“仁之乱也,则于其名也。”(注:《仁学八》,《全集》299页。)所以,谭嗣同的仁学与中国古代儒家仁学的意涵差距很大。
与此同时,谭嗣同还以西方的民主意识阐发中国传统的民本观念。他认为以民为本,就是要赋予民众更多的政治权力,即“兴民权”,(注:《与徐仁铸书》,《全集》270页。)使他们有“共举”、“共废”,甚至“杀戮”君主的权力。然而,自孔子至王夫之以来的一大批思想家,提出以民为本,目的在于警告君主“保民”、“重民”。否则,不利于君主专制统治。故而民本论的终极目标在于维护君主制度,而不是要让民众真正获得管理国家的政治权力。这一切,均可发现谭嗣同在倡导“仁学”、诠释儒教时,亦表现出对本土政治文化的“误读”。
四 文化“误读”的历史合理性
可见,“误读”是谭嗣同政治思想的显著特点。从学术立场看,他们需要解构他的政治思想的构成要素,需对其中学、西学的背景作一准确的分疏。出身于官宦之家的谭嗣同,自幼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五岁受书,即审四声,能属对。十五学诗,二十学文(《三十自纪》,《全集》55页),奠定了他广通中国之书的基础,他自己说:“中国之书当通《易》、《春秋公羊传》、《论语》、《礼记》、《孟子》、《庄子》、《墨子》、《史记》及陶渊明、周茂叔、张横渠、陆子静、王阳明、王船山、黄梨洲之书。”(《仁学界说》,《全集》293页)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功底,使谭嗣同在建构政治文化时,不但运用大量的中国古代哲学术语,而且以中学诠解西学。甲午战争以后,谭嗣同“学术更大变”,“前后判若两人”。(《与唐绂丞节》,《全集》259页)通过与传教士李提摩太、傅兰雅、李佳白及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交往,加之阅读《万国公报》、《湘学报》、《时务报》和一些西学资料,使谭嗣同对西方的政治文化有一定的了解。如他对议院的认识是:“西学之议事办事,分别最严。议院议事者也;官府办事者也。”(《治事篇第五·平权》,《全集》439页)然而,谭嗣同获取西学的渠道极为有限,更由于语言障碍,使他只能获得译介性的非第一手资料,所以他连“卢骚《民约论》之名亦未梦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76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由此可见,他对西方的公民文化并没有系统的了解。然而,强烈的救亡意识,和对社会转型的深刻认识,使得他迫切地参与到新的政治文化建构的事业中。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只能以“误读”的思维方式来构筑一种过渡性的政治文化,以实现臣民文化向公民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诚然,谭嗣同以“误读”思维建构的这种政治文化还显得粗糙,不能满足新的时代对新的政治文化建构的需要。但是,从历史的角度看,这种“误读”有着明显的历史合理性,因为要实现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臣民文化与公民文化、传统文化与近代文化的联结,需要构筑一个连通二者的通道,而文化的“误读”正是为构筑一个这样的通道。应该说,这比他以后的一些思想家张扬全盘西化的民主、自由,确有着更明显的历史合理性。
[收稿日期]2000-10-26
标签:政治论文; 谭嗣同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君主制度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公民权利论文; 仁学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国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