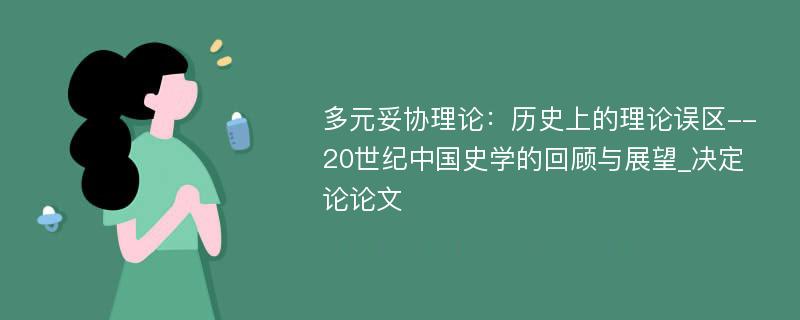
多元折衷论:历史学面临的理论误区——20世纪中国史学的回顾与前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历史学论文,中国论文,误区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多元折衷论(Pluralistic Eclecticism)是当代西方学术思潮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本体论和方法论原则。在本体论上,它强调任何现象或既成结果都是多种因素随机地或偶然地组合在一起,相互影响或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不同的因素组合,造成不同的结果,其中没有任何一个因素是最终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因此也就不可能有决定某种现象出现或不出现的因果必然性的规律。由此决定,在方法论上,它强调不能对研究对象作因果必然性的分析,不能探求因果必然性的规律,只能对引起某种现象或结果的诸项因素作实证性归纳,概括出它们引发某种现象或结果的可能性的模式或趋势。
从科学哲学演变的轨迹来看,多元折衷论是对19世纪盛行的机械的因果决定论的逆反。那种机械决定论确认,可观察到的现象是有其因果必然性规律的。如密尔所言:“自然界存在着这样一些情况相同的事物:它只要出现一次,在条件足够相似的情况下,它就会再度出现。”或者说,“全部的条件,正向和反向的都加在一起,……如果全都实现,结果必定随之而来”(J.S.Mill,A SYSTEM OF LOGIC,1851,P316、345)。这种因果决定论之所以是机械的,是因为:第一,它把“因”和“果”的关系仅仅看作是某种结果和选成它的各项因素或条件之间的关系,把某种结果仅仅看作是促成它的各项平列的因素或“全部的条件”的机械的总和,而没有看到,某个事物之所以呈现出某种结果,首先是该事物“自己运动”的特性决定的,那才是最根本的原因,其次才是各种外在因素或条件对它的影响,使它自身的面貌发生了相应的改变。第二,它断言,在条件足够相似的情况下,就必定出现相同的结果。它使用同时兼有“相似”(similarity)和“相同”(identity)双重含义的“parallelism”一词代替那两个含义不同的词,或把它们等价地使用。这实际上就是假定,只要有了十分相似的条件,就可以预断必然出现相同的结果。然而,这个假定是很难成立的。因为任何类似的原因或结果,类似程度再高也不可能是完全相同的,而如果原因仅仅是类似,结果就更不可能相同。但在19世纪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人们很难注意到那样的因果规律观的漏洞,或者即使注意到,也会认为无关紧要。当时的自然科学,以宏观物理学和牛顿力学为基础,它们的一整套定理与那种规律观并不矛盾,或者说是一致的。运用那种规律观解决当时面临的科学和技术的实际问题,一般也不会遇到困难。当时的世界历史进程,正逢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势不可挡地向全世界推进,政治家和思想家们大都以西方文明已经取得的种种成就为依据,确信全世界的历史必然按照西方理性的方向前进。象兰克那样保守的历史学家也断言,西方的基督新教文明必将在全世界取得胜利。确实也有少数睿智之士持不同的见解,但在大多数精英们看来,那些异议都不足为训。总之,那种机械的因果规律观在当时基本上是独领风骚的。
到了20世纪,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量子力学发现了“不确定关系”,或称为“测不准原理”。它认定,一个微观粒子的位置和动量,或方位角与动量矩,不可能同时具有确定的数值。其中一个量愈确定,另一个量的不确定程度愈大。这对强调确定性的经典力学概念提出了挑战。相对论发现,当物体运动速度接近于光速时,它的质量也会变化,会转化为能量。这对经典力学关于质量不变的设定也是一个挑战。分子遗传学、天体演化学等等新兴学科,也发现了大量变幻莫测、难以把握的现象。面对科学革命中出现的新形势,著名科学哲学家奎恩(W.V.Quine)在《英国科学哲学学刊》上发表文章,断言:“一切都是不肯定的。一切都容许修改。”(W.V.Quine."THE SCOPE AND LANGUAGE OF SCIENCE",British Journal for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VIII〔May,1957〕)20世纪的世界历史进程,也发生了一系列的巨变。两次空前暴烈的世界大战,旧殖民体系的瓦解和第三世界的兴起,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多极化世界格局的形成……,这一切都与19世纪的精英们预言的那种“必然趋势”大相径庭。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巴勒克拉夫在《变动的世界中的历史》一书中写道:“现在,我们充斥着一种不稳定的感情,因为我们感到将跨入一个新时代的门槛,在这个时代面前,以往的经验根本不成其为可靠的指南。”(转引自《当代国外社会科学手册》第112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人们越来越倾向于相信世界变化的随机性、偶然性和非决定论,摒弃因果性、必然性和决定论。19世纪盛行的机械性的因果规律观丧失了存在权利。
研究经济史和史学方法论的美国学者麦克勒南(Peter D.McClelland)在剖析机械的因果律模式的缺陷时,用逻辑语言把它表述为以下形式:
Always,if (C[,1],……,C[,n]),then E,ceteris paribus
或者表述为:
Necessarily,if (C[,1],……,C[,n]),then E,ceteris paribus
上述逻辑语句的含义是:如果出现了原因C[[,1],C[,2],C[,3],……直到C[,n],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拉丁语ceteris paribus),则总是(或者说必然)会出现结果E。这样的因果律模式在逻辑形式上是严密的。它意味着,研究者把他的因果判断的有效性限制在他已知的(或设定的)条件范围之内,他未知或未设定的条件都划入ceteris paribus范围,而且假定它们是不变的。实际上,科学中的原理或定理,几乎全部或隐或显地内含着这样的因果律模式,在它们的数理表述式中,总要用一个常数或系数,而且要设定它是不变的,否则就不能适用。那个常数或系数就是ceteris paribus。这表明,这种因果律模式是富有实际操作价值的,现在的科学也还离不开它。但是,从内容上看,它是有缺陷的。麦克勒南指出:“切近地审视,它仅仅是确认,除非发生某种情况阻止(C[,1],……C[,n])引起E,E就必然随着(C[,1],……C[,n])而出现。其结果是,我们不仅在一个拉丁词句中埋葬了我们忽略的东西,而且连同它们一起也埋葬了我们提出来需要加以解决的问题。”(Peter D.McClelland,CAUSAL EXPLANLATION AND MODEL BUILDING IN HISTORY,ECONOMICS AND NEW ECONOMIC HISTOR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5,P.45~46)他未免说得太严重了。实际上在那个拉丁词句中“埋葬”的,只是他未知或未设定的条件及其可能的变化和变化原因的追寻问题。这些问题也正是现代科学面临的不确定性问题,它无法解决这些问题,只好把它们“埋葬”或搁置起来。
麦克勒南看到了这种因果律模式的缺陷,于是建议把它改写成
Probably,if (C[,1],……,C[,n]),then E其含义是:如果出现C[,1],……,C[,n],就可能出现E。他说:“这一修改的关键之点,在于强调根据那种规律作出的预见和解释都不是肯定无疑的。只要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的推理和解释依赖于那些规律,他们就不能期望达到绝对肯定无疑的推理。”(McClelland同上书,第46页)
麦克勒南的中心思想正是要强调,当今的自然科学都不可能得出完全确定无疑的结论,历史学和经济学这些社会科学就更不该有那样的企求了。一切的研究都只能得出或然性、假设性的结论,不能有更高的要求。这也正是当代西方学术界中最为盛行的学术思潮。它的最鲜明的表达,就是前面引述过的奎恩的两句话:“一切都是不肯定的。一切都容许修改。”多元折衷论就是这种学术思潮的产物。
实际上,在麦克勒南表述的因果律模式中就已经包含着多元折衷论的内容。式中的(C[,1],……,C[,n])和E的因果关系,其含意就是,任何一个结果E都是由C[,1]到C[,n]的多种因素促成的,那些因素没有主次之分,平列地起作用,不存在谁决定谁的关系。probably则表示,那些因素的组合及其变化都是变幻不定、难以确切把握的,由此决定结论只能是或然性、假设性的。
就这样,20世纪的多元折衷论以它的非决定论取代了19世纪的机械决定论,以其对不确定性、随机性、或然性的强调,代替了后者对确定性和必然性的追求。从积极方面来看,20世纪的非决定论的多元折衷论较之19世纪的机械决定论,表现了一种诚实的谦虚态度。它提醒人们要意识到自己的知识和能力的限度,不要固步自封,而要随时准备修改自己的结论。这是有利于防止僵化和促进科学发展的。但是,因此就放弃了对确定性和必然性的追求,特别是因为19世纪的机械决定论的失败就否定对科学的决定论的探索,就不能不说是从一个极端的谬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的谬误。
下面我们具体看看多元折衷论的谬误怎样有损于历史科学的发展。
德国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韦伯主张多元折衷论,认为宗教、经济、政治、文化观念、地理环境、伦理道德等等因素都在历史进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不能单独强调其中某一种因素起最终的决定性作用。他的许多论著涉及到探讨亚洲为什么没有产生出西方那样的资本主义文明,对此提出过众多的解释。例如,他认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亚洲没有产生出西方古代中世纪那样的自治城市,而这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诸如,“它没有象曾经存在于欧洲中世纪的那种城市法,因为它不是一个拥有自己政治制度和特权的共同体;它也没有象曾经存在于西方古代的那种居住在城市并拥有自己武装的军人阶层”。“宗族关系是抑制东方城市居民追求西方意义上的自治的主要障碍”。在另一场合,他又强调,“我们已经指出为什么资本主义未能得到发展的原因,这些原因几乎都来自国家的结构。行政和立法所具有的世袭性创造了一个与专制和宠幸的王国相伴随的不可动摇的神圣传统的王国。这些政治因素阻碍了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最怕的便是没有合理而可靠的行政机构和执法机构,无论在中国、印度、伊斯兰教国家或其他地方都是如此。在西方,皇族的特权可凌驾于普通法律之上,这一原则推动着合理地制定和裁定法律的发展,但这一原则并不有利于中国资本主义立法机构的发展。”有时,他着重强调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如说:“西方国家在古代(直到建立世界性帝国)、也在中世纪和近代,都不得不为资本的自由流通而竞争。中国正如罗马帝国一样,在帝国统一后,为资本而进行的政治竞争消失了。中国帝国也没有海外关系和拥有殖民地关系,这妨碍了在西方古代、中世纪和近代都共同存在过的那些资本主义类型在中国的发展。而妨碍海上扩张的因素部分是由于大陆国家的地理条件,部分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是中国社会一般的政治和经济特点所造成的。”有时,他又着重强调某一个因素,特别是文化、精神方面的因素,是最重要的因素,如说:“合理的工业资本主义在西方是把其重点明确地放在制造方面,它在中国却受到了阻碍,这不仅是因为没有形式上的保护法、合理的行政机构和司法制度以及征税权的具体制度,而且最基本的也是因为没有精神上的基础,首先是植根于中国人精神气质中的中国人的态度妨碍了合理的资本主义的发展,这种态度在官僚阶层以及那些迫切想当官的人当中特别强烈。”韦伯实际上是主张精神、文化决定论的,认为出自基督新教伦理的资本主义精神在促进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方面起了决定性作用。他特别反对唯物史观的存在决定意识的原理,例如说:“资本主义精神(在我们所赋予它的意义上)在资本主义秩序之前就出现了。早在1632年,人们就对新英格兰独特的为追求利润而精打细算产生了抱怨……更无疑问的是,资本主义在……美利坚合众国后来的南部诸州,发展得远不够发达,尽管事实上南部诸州是由大资产者为了做生意的目的而建立的,而新英格兰殖民地则是在小资产者、手工业者和自耕农的帮助下由传教士和神学院毕业生为了各种宗教目的而建立的。在这个问题上,基于唯物主义立场的观点确实是把因果关系颠倒了。”但是,要说韦伯是精神、文化决定论者,他也有充分的理由反驳,例如,他曾说过:“我们首先要注意的是应对西方合理主义过去和现在的独特性的起源加以确定和说明。在每一试图作这样的说明时,都必须承认经济因素所具有的根本重要性,特别是对经济条件加以考虑。但与此同时,对相反的关系也必须予以考虑到。因为,虽然经济合理主义的发展,部分地依赖于合理的技术和法律,但它同时也被那些进行某种实际合理经营活动的人的能力和气质所决定。当精神障碍妨碍了这些活动时,合理的经济行为的发展则同时也会碰到严重的内部阻力。神怪的和宗教的力量以及以它们为基础的伦理的义务观念,过去始终是对行为发生影响的最重要的构成因素之一。”(《文明的历史脚步·韦伯文集》第14、92、94、141页,三联书店1988年版)
韦伯的论述,提供了多元折衷论的一个鲜明实例。面对着涉及众多因素的一个结果,他认为每个因素互相地依赖于其他因素,象一个互相扭缠在一起的连环套,其中每一个环节都对其他环节发生影响,同时也对整个结果施加影响。神怪和宗教力量的影响是“最重要的”,“经济因素”具有“根本重要性”,“精神上的基础”是“最基本的”,“人的能力和气质”是“决定”性的,“经济动机”对“科学知识在技术上的应用具有特别有利的作用”,“合理的法律结构和合理的行政管理结构肯定具有巨大的重要性”,是“必不可少的”……等等。总之,每一个因素的重要性他都说到了,但是不是都说清楚了呢?应该承认,在历史的某些侧面上,特别是在精神、文化因素方面,韦伯的一些论说确有精到之处。但是,言而无据的夸张和缺乏常识的武断也并不少见。特别是,他一再指责唯物史观把存在与意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因果关系颠倒了。然而,仔细看看他的论据,就不难发现,正是他自己,把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弄成了一堆乱麻。他要用那堆乱麻去掩埋历史发展的规律。我们看到,他试图把多元折衷论当作一把万能的钥匙,用它去打开每一个相互作用环节上的锁,却一把锁也没有打开。结果表明,多元折衷论是一把万能而又万不能的钥匙。
以韦伯为代表的这种多元折衷论,决不是孤立现象。前些年,他的著作在冷落了数十年之后重新被发掘出来,享誉西方学术界,以致掀起了一阵阵的“韦伯热”。只不过近年来又逐渐冷下去了,其中一个背景,看来是随着亚洲诸“小龙”的崛起,使他当年对亚洲的“精神气质落后”的种种论断不攻自破了。历史对历史学家真是铁面无私的审判官。
但是,多元折衷论并没有随着“韦伯热”的冷落而冷落下去。它仍然在西方学术思潮中占有主导地位。
我们坚持以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研究,是因为以它为指南,我们才能从繁芜交错、扑朔迷离的历史陈迹中清理出历史运动的轨迹,认清它的来龙去脉,以启迪人们顺应它的规律,以较少的代价去开拓新的历史道路。这是我们研究历史的最终目的所在。多元折衷论的危害正是在于,它在我们奔向目标的旅程中布下了迷雾和陷阱。每当我们走到特别模糊难辨的交叉路口,面临进退维谷的处境时,它就会向我们招手。
例如,我们在探讨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长期延续或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为什么成长受阻时,我们会想到,封建专制政权一贯的重农抑商政策和横征暴敛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这当然是对的。可是,如果我们的探讨就停留在这一点上而不去进一步追寻专制政权为什么能够长期实行那样的政策,而西欧中世纪晚期建立的封建专制政权为什么就实行重商主义政策,就可能陷入迷雾。我们还会想到,地主土地所有制和土地买卖使商人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就总是买地置产,转化成为地主而不是产业资本家,这也许是一个重要原因。可是,西方中世纪后期逐渐盛行的土地买卖为什么反而促进了封建土地制度的衰落和资本主义农场式经营的发展呢?我们也想到,城市历来被封建统治阶级控制而不能发挥工商业中心作用,是一个重要原因。可是西欧中世纪城市原来也大多属于大封建主所有,后来为什么能逐渐形成工商业中心呢?我们还想到,商品经济的发展受阻导致小农自然经济长期凝滞是一个重要原因。可是,明清时期商品经济不是已经把众多小农卷入旋涡,为什么还是没有促进资本主义发展呢?为什么中世纪晚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在促进西欧封建农奴制解体的同时在东欧却反而促进了农奴制的再版或加强呢?还有根深蒂固的重义轻利观念,也许是一个重要原因。可是,在西欧中世纪,基督教神学教义和神甫们的教导,还有宣讲到千家万户的圣徒故事,不也是充满了重义轻利的说教吗?为什么后来的新教伦理和韦伯说的那种资本主义精神终于兴盛了起来而且冲破了它的樊篱呢?还有人口、地理环境……等等原因,我们都会想到,但是认真追寻下去,就发现那些原因或者经不起推敲,或者发现那些原因背后还有更深层的原因。
在陷入互相交错、难解难分的因果连环的困境时,唯物史观启导我们一定要追寻各种各样的原因背后的更深层的原因,一直要追寻到最终决定着其他各种原因是否发挥作用或作用大小的那个终极的原因,那就是作为人的物质生产实践能力的生产力的状况这个终极的原因,只有这样,才能避免陷入多元折衷论的误区,才能达到从扑朔迷离、模糊难辨的历史迷雾中揭示出它的内在规律的目的。当然,我们在深入探究作为人的物质生产实践能力的生产力状况时,就势必要去探寻各种经济、政治、文化、观念、习俗、自然条件……等等多种多样的因素对人们的物质生产实践能力所起的正面或负面的制约作用,但这已不是孤立地去考察那些因素的作用,而是把它们聚焦到对广大劳动者的实践能力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上,去衡量那些作用的性质和大小,这样也才能恰当地估量它们对整个历史进程所起的作用的性质和大小,而不会因此陷入多元折衷论的误区。
标签:决定论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折衷主义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历史规律论文; 经济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