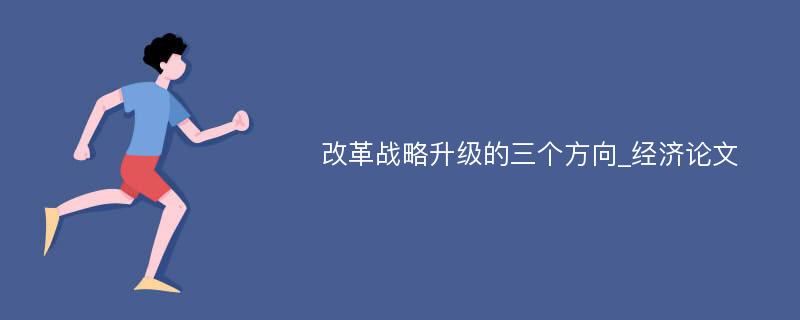
改革战略升级的三个方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向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正面临历史性的战略升级。
前一阶段,制度变革取得了不小的进展,但是,推进的力度、深度和协调度远远不够,还是属于比较浅层的市场化改革。现在面临着三个挑战:(1)微观挑战宏观;(2)自然挑战发展;(3)国际挑战国内。在这种情况下,需要重新审视我们改革的战略格局。总的看,原来改革的战略格局还比较小,属于常规性的配置资源。要把握改革的主动权,必须突破原有改革的格局思路,在更大格局和更高层次上配置资源,这就意味着寻求中国改革的战略升级。在我看来,主要应瞄准以下三个方向升级:
一、瞄准政府自身和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方向升级
前一阶段的经济体制改革,依据的是1992年确立的这样一种目标模式:“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关键是这里边的这个“使”字和“下”字。谁来“使市场”?政府。在谁的“宏观调控下”?政府。一个“使”字、一个“下”字,表明我们原来设计的市场经济体制模式是一种“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体制模式。在这种框架中作为起“主导”作用的政府,是以“理性政府”为假定条件的,前一段改革就在这样一个前提下实施。经过这十几年的实践检验,这种“政府主导型”模式有利有弊。现在经济生活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从制度模式的角度来分析,与此有密切关系。比如说,为什么对于垄断性行业等计划经济体制的核心部分进行体制性攻坚十分艰难?为什么在投资体制改革进程中遇到的阻力和干扰如此之大?为什么国有商业银行的呆坏账率如此之高?等等,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与“政府主导型”模式有密切关系。因此,下一阶段需要由微观向宏观推进,把政府自身体制的创新作为整个体制创新的重点。决策层提出以政府自身体制的创新为重点,是有见地的。建议能否此基础上提升一步,探索一个新型的、有别于“政府主导型”模式的市场经济体制框架。与此同时,要探索新的社会运转和社会服务的新机制,已形成一套与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和文化多元化相适应的新型社会治理模式。
二、瞄准促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创新方向升级
1992年 设计改革目标模式时,虽然联合国早已通过“斯德哥尔摩宣言”和“内罗毕宣言”,并恰好在1992年提出了“人类发展指数”,但在改革的制度设计上对此是体现不够的。当时没有把此纳入新体制的基本框架。这是一个重要的战略缺失。
最近胡锦涛在讲到中国国内“急待解决的八个突出矛盾”时,把“资源能源紧缺压力增大,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制约日益突出”列为第一位,是意味深长的。这个瓶颈是一个战略瓶颈,要打破战略瓶颈,不仅要在结构、技术、增长方式方面做文章,而且要在制度创新上找出路,这就要求我们把如何为可持续发展提供制度保障纳入新体制的基本框架。
比如,为了促进资源的利用和节约,如何推进资源的产权制度改革?十六届三中全会虽然提出建立现代产权制度,但在实践中主要是着眼于企业产权制度,下一步是否应该在资源和环境领域建立一整套包括产权界定、产权配置、产权流转、产权保护的现代产权制度?为了保护资源和环境,如何推进资源的价格制度改革,使各种资源价格充分反映资源、环境和生态的真实成本和供求关系?针对目前社会普遍存在的“短期利益病”,如何用更大的“利益杠杆”,来建立促进“永续发展”的国民经济核算、运行、调节制度?等等。在这里,市场不仅对一般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而且要设法在调节人与自然资源的关系方面发挥作用。这是对原来设计的市场经济体制框架的一个新拓展。
三、瞄准经济全球化的制度创新方向升级
现在一方面是经济全球化的潮流涌动,另一方面国际经济旧秩序依然存在,而且这两者往往纠缠在一起,有时甚至国际经济旧秩序“挟”经济全球化的“天子”而令诸侯,这使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面临复杂的局面,而这种局面在未来五到十年也不可能完全改变。
在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需要积极、主动地改革我们国内现有的体制,尽可能增加新体制的应变性。同时,要看到,按照WTO的规则来行事,中国面临挑战是极其严峻的,它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如何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学会把握国际规则的主动权,特别是要有应对经济全球化、国际经济旧秩序的制度安排。作为一个后起的发展中国家,应该考虑从宏观角度建立一套对外开放和保护国家利益的平衡机制,这都是新问题。同时,随着中国在世界的逐步兴起,也要考虑我们的体制框架如何体现中国在世界上“逐步兴起”的制度保障。这不只是维护国家权益,而是增进国家权益的问题。从进一步扩大开放和维护、增进国家权益的战略高度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