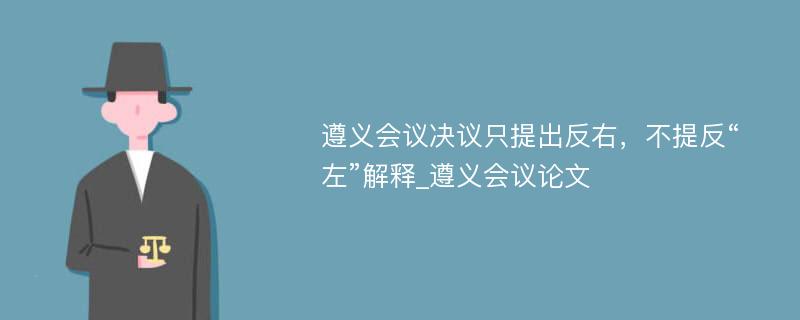
遵义会议决议只提反右不提反“左”释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遵义会议论文,不提论文,决议论文,反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的原因,在党的两个重要历史决议(即六届七中全会决议和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中都作了明确的结论:是由于王明“左”倾错误路线造成的。但是,遵义会议决议中却未提出反对“左”倾的问题,且强调指出:“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一切事实证明我们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而“这种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一种具体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因此,必须要在“全党内”深入开展“反对党内具体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①a]。显然,遵义会议决议中的提法和历史决议中的结论是不一致的。应当怎样认识遵义会议决议中提出的反右倾问题?笔者不揣谫陋,谈点个人的认识,以就教于同仁。
一、从局部的军事路线和现实危险倾向看,遵义会议决议中反右倾
的提法符合当时党内存在着右倾机会主义的具体实际。
遵义会议决议中号召全党深入开展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这是从当时党的军事斗争方面确实存在着“具体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实际情况出发的,而且在战争非常时期,这种右的倾向可以说已构成了党内的最大危险。正如后来周恩来1972年6月10日在《党的历史教训》一文中所讲的:“遵义会议的主旨是纠正军事路线错误,因为当时是在惊涛骇浪中作战,军事路线最紧迫。”[②a概括当时军事斗争中存在的右倾表现,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方面:
首先,从军事领导思想基础来看,过分估计了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反动派力量对于苏维埃革命运动残酷进攻的客观困难,而对自己主观的力量特别是苏区与红军的力量则估计不足。
蒋介石发动的第五次反革命军事“围剿”,较之前四次“围剿”有着一个不同之点,即是在国际帝国主义金钱军火的帮助之下进行的。1933年5月,美国借给南京政府5000万美金(次年改为2000万美金)的所谓“棉麦借款”以及4000万美金的所谓“航空借款”。蒋介石凭借这批金钱购了大量军火,聘请了许多外国顾问,制订了周密的计划,务求消灭红军和苏区。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蒋介石于1933年9月,调集100万军队、200架飞机向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围剿”,其中以50万兵力,分4路“围剿”中央苏区。
面对国民党反动派对于苏维埃革命运动更加残酷的进攻,红军最高军事指挥者李德、博古在反“围剿”伊始至福建事变结束时期,曾采取了“全线出击”、“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左”倾方针,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但是,还应看到,就在“左”倾军事指导思想占主导地位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右的思想倾向。譬如部分人对于能否粉碎这次大规模的“围剿”持有悲观、恐惧和失望的情绪,甚至于许多中国革命的朋友和有些共产党员,也不免抱着悲观的态度。在红军高级将领中亦有人存在着惧怕红军远离根据地作战的右倾错误心理。1934年1月,当蒋介石将福建事变镇压下去而转过头来又重新加紧对中央苏区进攻后,“左”倾军事领导者即由进攻中的冒险主义一变而为防御中的保守主义,以后又在退却中变为逃跑主义,使右倾机会主义在军事斗争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博古在遵义会议上关于反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中,拒不承认错误,并为他们的错误百般辩护。因而,遵义会议决议指出:“这必然会得出客观上五次‘围剿’根本不能粉碎的机会主义的结论”[①b]。
其次,从军事指挥方面来看,畏惧于敌人的堡垒主义,实行右倾机会主义的单纯防御路线及其战略战术原则。
国民党蒋介石在经过前几次“围剿”失败之后,知道用“长驱直入”的战略战术同红军在苏区内作战是不利的,因此,在第五次“围剿”中采用了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企图逐渐消耗红军的有生力量与物质资财,紧缩中央苏区,最后寻求红军主力决战,以达到消灭红军之目的。在这种情况下,红军的战略方针应是决战防御(即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弱点,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彻底粉碎“围剿”。然而,李德、博古在继最初的轻视堡垒主义实行全线出击,结果在硝石、资溪桥、团村、将军殿、建宁、湖坊、温坊等各线,特别是广昌战线连续受挫后,对敌人的堡垒主义由轻视陡然变为恐惧,以单纯的防御路线(或专守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而对毛泽东在反“围剿”期间先后提出的两次正确建议则断然拒绝。其结果,只能是丧失了打破敌人“围剿”的时机,最后,中央红军主力不得不退出中央苏区,实行战略大转移——长征。在指挥红军突围和长征初期,“左”倾军事领导者同样犯了右倾错误,实行即却中的逃跑主义。
再次,从部队战斗情绪方面来看,遵义会议前夕,红军中从一些高级将领到一般战士也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对自己力量估计不足的情绪。
长征开始后部队连续受挫,减员严重,在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后,不到两个月时间,中央红军主力即由长征开始时的86000人减少至不足40000人,并始终未能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加之转移方向不明确,不少干部战士对红军的前途感到心中无数,因此部队混乱现象严重,士气十分低沉。面对红军的危急处境,“博古同志感到责任重大,可是又一筹莫展,痛心疾首,在行军路上,他拿着一支手枪朝自己瞎比划”。当时,“如何巩固提高部队的士气”,已成为完成长征任务的“一个大难题”[②b]。
以上说明,从第五次反“围剿”开始(确切地说是从广昌战役后开始)到遵义会议召开前夕这段时间里,军事领导者的确犯有严重的右倾错误。这时能否振奋士气,克服失败情绪,已经成为红军生死攸关的大事。因此,遵义会议决议号召全党深入开展反对“具体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应该说是合乎当时党内斗争实际的,也是非常必要的,它对保证胜利完成长征任务,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从整体的中央路线和军事领导思想根源看,遵义会议决议中反
右倾的提法和两大历史决议中反“左”倾的结论并不相悖。
我们肯定遵义会议决议中反右倾的提法是合乎当时实际的,并不意味着是对党的两大历史决议中反“左”倾结论的否定,二者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是并行不悖的。
遵义会议决议和两大历史决议的内容,在时间范围和空间范围上都有着很大的区别。前者是一个关于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其内容仅限于总结从1933年9月至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之前这一年零三个月时间内的党中央的军事路线,所提出的“反右倾”是对王明、博古等人的机会主义路线在这一具体历史阶段的军事路线方面的具体批判。而两大历史决议则是全面总结王明、博古等人从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之前期间党的政治、军事、思想等诸方面的路线,所得出的反“左”倾的结论是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和在更深刻的程度上揭示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实质,是一个完整系统的正确结论。即是说,两者之间是局部与整体之间的关系。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王明、博古等人机会主义路线的指导思想是“左”倾错误,而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他们则犯有右倾错误。因为整体与局部之间的矛盾现象是经常存在的。这种现象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史上可谓是不乏其例。譬如大革命时期陈独秀从总的来说是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但在这一时期的工农运动中,也常常有“提出使企业倒闭的要求”,“随便逮捕人,组织法庭监狱”,“随便断绝交通,没收分配工厂商店”[①c]等“左”倾错误的出现。
我们说遵义会议决议反右倾的提法和两大历史决议中反“左”倾的结论并行不悖,还因为二者之间又有着内在的联系。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李德、博古错误军事路线的发展过程有个“三部曲”,这就是《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指出的:“他们始则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继则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最后“又变为实行真正的逃跑主义”[②c]。其第一部曲是“左”倾的,这是总的根源;而后两部曲,则都是“从右倾的观点产生的”。“这种错误,往往有一种‘左’倾轻敌的错误为之先行”[③c]。看起来,这一错误军事路线发展的三部曲是一个奇怪的混合体,但是在“左”倾冒险主义的躯体内却是一种必然的结合,是一种合乎逻辑的发展。因此,从整体的中央路线和军事领导的思想根源看,造成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应该说是“左”倾冒险主义,而不是右倾保守主义。所以,两大历史决议的反“左”倾是从本质上和整体上作出的正确结论,它与遵义会议决议针对部分阶段某个方面而提出的“反右倾”并不矛盾。
三、从当时的党内具体状况和国际背景看,遵义会议决议中只提反
右不提反“左”,既是一种斗争的策略,也有认识上的历史局限性。
怎样认识遵义会议决议中只提反右不提反“左”,即只批评军事路线的具体的右倾机会主义,而对政治路线中的“左”倾不仅只字未批却还予以充分肯定呢?我们认为主要应从以下两大方面理解:
一方面,遵义会议决议中只提反右不提反“左”,不仅如前所述,符合当时党内确实存在着的具体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实际状况,而且也是当时历史条件下采取的一种斗争策略。因为:首先,“左”倾错误的领导者博古、李德等人并不承认自己在军事路线上的错误。不难理解,在他们连军事路线的错误都不能承认的情况下,要其承认政治路线上有错误就更加困难了。其次,当时王明推行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实际上就是共产国际的路线,如果批评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无疑地就是指责共产国际,这样,“左”倾领导者势必会以“反国际”的帽子反攻,从而引起会议的混乱,这样就连迫在眉睫的军事路线问题也难解决了。再次,自从20年代俄共党内开展反布哈林右倾机会主义斗争后,共产国际给各国党的指示,都是以反右倾机会主义作为党内反倾向斗争的中心的。在中国党内,王明等也是以大反右倾机会主义为旗号对党的各级组织实行“改造”和“充实”,从而取得了党的领导权的。那时,在党内只能反右倾不能反“左”倾,似乎已形成一种习惯的看法。因此,遵义会议决议只提反右不提反“左”,不但能使一般的同志容易接受,而且即使犯有“左”倾错误的领导者也因为这一提法符合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而找不出反对的根据了。
对此,张闻天在延安整风期间曾回忆说:“遵义会议没有提出过去中央政治上的路线错误,而且反而肯定了它的正确”,“这在毛泽东同志当时只能如此做,不然我们的联合会成为不可能”。“为了党与革命的利益,而这个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毛泽东同志当时作了原则上的让步,承认一个不正确的路线为正确,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完全正确的。这个例子,可以作为党内斗争一个示范来看。”[①d]
另一方面,遵义会议决议中只提反右不提反“左”,不可否认也有着认识上的历史局限性。由于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以来,“左”倾冒险主义者“在反帝反封建、土地革命、反蒋战争等问题上的若干观点,同主张正确路线的同志们仍然是一致的”[②d];也由于那时王明的危害尚未充分暴露,又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使人一时不易识破他们;还由于当时战争形势紧迫,红军经常处在敌人的包围圈中,不允许会议用较长的时间详细地检讨政治路线。因此,在遵义会议召开时,大多数同志对于“左”倾领导者军事路线的错误是看得比较清楚的,但是他们尚未认识到中央政治上的错误,因而会议认为当时党的总的政治路线一般的是正确的。实际上,党内对于王明路线整个性质的认识,从遵义会议以后又经过长达10年的时间才得到了统一。直到1945年4月,随着整风运动的深入开展,人们认识的逐步提高,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才使全党对于王明路线的整个性质和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形成了一个共识。
当然,在此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说遵义会议决议中只提反右不提反“左”有着认识上的历史局限性,丝毫无损于遵义会议的伟大历史意义,如同要求遵义会议要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好是不切实际的一样,要求遵义会议一次完成对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彻底认识也是不符合认识事物的发展规律的。遵义会议集中全力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实际领导地位,在革命的危急关头,挽救了党和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其功绩如日月经天,作为我党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点而载入史册。
注释:
①a 《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0~21页。
②a 同上,第67页。
①b 《遵义会议文献》,第4页。
②b 《聂荣臻回忆录》上册,战士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227、228页。
①c 刘少奇给张闻天的信:《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中的一个问题》,1937年2月26日。
②c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84页。
③c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98页。
①d 《遵义会议文献》,第80页。
②d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9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