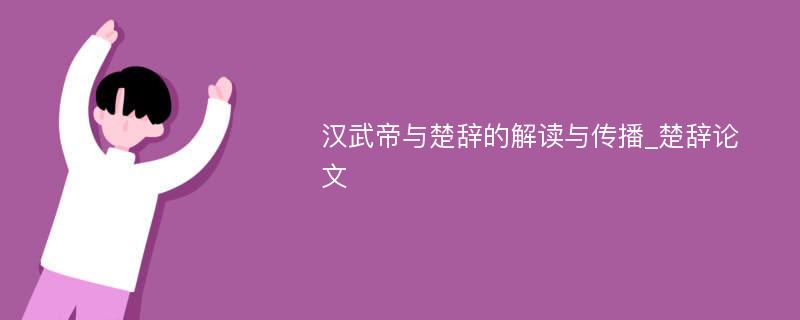
汉武帝和楚辞解读与传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楚辞论文,汉武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刘安《离骚传》:诏令引导下的开山解读
刘安《离骚传》在楚辞学史上具有开山意义,它的产生与汉武帝的诏令引导密切相关。虽此文已佚,但从班固《离骚序》的介绍中可窥见其要点。《离骚序》云:
昔在孝武,博览古文。淮南王安叙《离骚传》,以《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蝉蜕浊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皭然泥而不滓;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斯论似过其真。又说:五子以失家巷,谓五子胥也。及至羿、浇、少康、贰姚、有娀佚女,皆各以所识有所增损,然犹未得其正也。①
由班固载录可知,刘安《离骚传》对《离骚》的解读分总论和词语阐释两部分。在总论部分中,他首先依据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理论,对《离骚》思想内容进行品评,肯定《离骚》的好色与怨诽之情皆能持中,深得《风》、《雅》中和之旨。然后指出,《离骚》体现了屈原在浊世中仍能保持高洁的人格精神,足“可与日月争光”。这一评语,虽是从《渔父》、《涉江》中撷掇而出,② 但它强调个人品格的修养,实际是从儒家注重修身养性的伦理道德角度来解读《离骚》。在刘安看来,人品决定文品,正因屈原品格高洁,才使其文能兼《风》、《雅》之长。那么,为什么崇尚黄老与神仙学说的刘安会从儒家伦理道德角度对屈原及其《离骚》进行解读,而不是从文学或其他角度去解读呢?这显然与《离骚传》产生的特殊政治背景有关。
要弄清《离骚传》产生的政治背景,必先弄清其产生的时间。《汉书》刘安本传云:“时武帝方好艺文,……初,安入朝,……使为《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据此,《离骚传》是在武帝“方好艺文”之际,刘安初次入朝,受诏而作。而刘安入朝的时间,据《史记》本传:“建元二年(前139),淮南王入朝。”《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亦把刘安于武帝时初次入朝系于本年。因此,《离骚传》作于建元二年(前139),是没有疑问的。
必须注意的是,刘安作传的这一年,正是汉武帝第一次尊儒改制在祖母太皇窦太后干预下惨遭失败之年。据《史记》、《汉书》相关记载,武帝于建元元年(前140)以窦婴为相、田蚡为太尉,用《鲁诗》学者王臧为郎中令、赵绾为御史大夫,进行“议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诸侯”、“草巡狩封禅改历服色”(《史记·封禅书》)的儒学改制活动,遭到了“喜黄老言”的窦太后“不悦”和干涉。建元二年(前139)冬十月,赵绾“请毋奏事太皇太后”(《汉书·武帝纪》),触怒窦氏,赵绾与王臧“皆下狱,自杀”(同前),窦婴、田蚡被免职,帮助议立明堂的《鲁诗》大师申公免归,武帝也受到了窦氏“此欲复为新垣平”(《汉书·儒林传》)的严厉指责。可见武帝的尊儒改制活动,引发了黄老与儒学两种思想的一场激烈斗争。斗争的结果,则以武帝失败告终。就在传授《诗经》、辅佐武帝改制的赵绾与王臧被迫自杀、儒学改制失败的非常之时,武帝选择刘安为《离骚》作传,这本身就是一件极富深意的事。那么,武帝诏刘安作传,究竟有何深意呢?
其一,出于个人娱乐抒情的文学需求。汉武帝令刘安为《离骚》作传,有着“爱骚”的本然兴趣,也有着在《离骚》中寻找心灵慰藉的阅读期待。
受汉初宫廷楚声流行的影响,武帝诏刘安作传前就爱好楚辞。刘勰《文心雕龙·辨骚》“汉武爱骚,而淮南作传”之语,就明确指出“爱骚”的艺术兴趣,是武帝诏刘安作传的重要原因之一。又,《汉书》本传载刘安来朝,恰值“武帝方好艺文”;《史记·儒林列传》载申公于建元元年见武帝,亦逢武帝“方好文词”。这就透露出武帝爱骚的具体原因:喜好文辞富丽的作品。而《离骚》“文辞雅丽”、“惊采绝艳”(《文心雕龙·辨骚》),正契合了武帝这一文学趣味。并且,《离骚》抒发的是一位寻求美政理想而终遭失败的改革者之悲愤情感,表达了“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坚韧执着,因此,初次改革遭失败的汉武帝对《离骚》蕴涵的这份情感产生共鸣是很自然的。可以说,《离骚》文本的词采美与情感美与他此时的文学趣味恰好吻合。他让刘安作《离骚传》,据颜师古注:“传谓解说之,若《毛诗传》”,可见是期待通过刘安的解说,能更好地理解《离骚》,领会其词采与情感妙处。又因窦氏不好儒术,慑于其一时淫威,武帝寻找《诗经》以外的文学作品来宣泄内心的悲愤和苦闷,亦属情理中事。对《离骚》丽雅文辞的本然喜好,《离骚》主人公美政理想失败后发出的强烈情感召唤,以及窦太后不好儒术的压力,促使武帝把欣赏的目光投向《离骚》,从而要求刘安为《离骚》作传。
从班固《离骚序》对《离骚传》的介绍看,刘安不仅对《离骚》文本给予了整体性概括,而且对《离骚》中的一些典故和疑难词都作了解释,基本上满足了武帝理解《离骚》文本的阅读期待。尽管班固讥之“犹未得其正”,但毕竟会对他理解作品有所帮助。武帝《李夫人赋》曾多处化用《离骚》词句入赋,如,“释舆马于山椒”,化用“步余马于兰皋兮,驰椒丘且焉止息”;“函荾荴以俟风兮,芳杂袭以弥章”,化用“佩缤纷其繁饰兮,芳菲菲其弥章”;“念穷远之不返兮,惟幼眇之相羊”,化用“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这些说明,刘安为《离骚》作传后,武帝对《离骚》已非常熟悉。
第二,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虽首次尊儒改制活动失败,但武帝并不气馁,企图通过诏刘安作《离骚传》来委婉考察其对中央政府的态度,扩大儒学支持者的阵营,进而加强忠君思想的灌输。这是武帝诏刘安作传的重要原因。
尊儒改制失败后,武帝并不甘心。在元光元年(前134)《诏贤良》中,武帝自称即位以来一直在思考“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业休德,上参尧舜,下配三王”(《汉书·武帝纪》)的问题,说明武帝期盼施行德教、建立三王五帝那样的大一统政治理想并未破灭。又,《武帝纪》载:“建元……五年春,……置《五经》博士。”而窦太后崩于建元六年(前135)五月,可见武帝是趁其年老病重之机,立《五经》博士,提高儒学地位。这也说明武帝并未因改革失败停止“向儒”,而是等待时机,争取尊儒机会。
正是建元二年特殊的政治背景,加上刘安来朝的偶然机遇,共同促成了《离骚传》的产生。如果武帝仅仅是因“爱骚”而要人作传,他完全可以有别的选择。因当时的文学侍从中,至少已有东方朔、严助等人。但面对众多善辞赋的文学侍从,武帝却偏偏选择了刘安,而且选定的篇名是《离骚》,这显然与刘安的特殊身份及其儒道兼综的思想有关。
刘安为武帝族叔,其父淮南厉王刘长于文帝六年(前174)因谋反在废迁蜀道中绝食而死。鉴于吴王刘濞因其子死于景帝棋盘下生怨继而谋反的前车之鉴,且刘安本人在吴楚反时曾欲发兵应之,③ 武帝对刘安言行举止特别关注。更重要的是,刘安名声颇佳,《史记》本传云其“为人好读书鼓琴,不喜弋猎狗马驰骋,亦欲以行阴德拊循百姓,流誉天下。”《汉书》本传又称其“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对于这样一位背景复杂、政治立场不明、广招宾客的诸侯王,武帝不能不严加防范。
另外,作为黄老政治下的既得利益者,刘安有比较明显的黄老思想倾向,并在黄老道家思想统率下兼修儒学。《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下省称“《汉志》”)杂家类著录:“《淮南内》二十一篇”、“《淮南外》三十三篇”。据《汉书》本传:“初,安入朝,献所作《内篇》,新出,上爱秘之。”可知刘安初次入朝就把刚完成的《内篇》献给了汉武帝。所谓《内篇》,就是《淮南内》,亦即今之《淮南鸿烈》。虽《汉志》列其为杂家,然据高诱《淮南鸿烈叙目》介绍,此书是刘安与门客“共讲论道德,总统仁义,而著此书。其旨近《老子》,……其义也著,其文也富,物事之类,无所不载,然其大较归之于道。”④ 可见此书思想虽驳杂,但以道家思想为主导。在全书序言《要略》里,刘安还提出了“权事立制”、守静应变的治国思想,并将其贯串全书。⑤ 如《原道训》云:“圣人一度循轨,不变其宜,不易其常,放准修绳,曲因其当。”“夫有天下者,岂必摄权持势,操杀生之柄而以行其号令邪?吾所谓有天下者,非谓此也,自得而已。”这些言论,表明了王天下者当“一度循轨”,不必“摄权持势”,应继续以黄老思想治国的政治主张。在武帝尊儒改制遭受失败后,刘安献上这部主张以黄老治国思想的著作,其用意十分明显。面对这样一个有思想的诸侯王,武帝不希望他蹈刘濞之辄,而是希望能利用之。因此,他一方面对其所上《内篇》“爱秘之”,一方面又诏令其为《离骚》作传,以期通过让刘安解读《离骚》,考察他对中央政府的态度,争取儒学改革的支持者。
武帝曾诏臣子作对,令其向儒习儒,有史为证。据《汉书·严助传》载,武帝曾赐书严助:“具以《春秋》对,毋以苏秦纵横”,可谓立场鲜明。只是对于刘安这位名誉颇佳的族叔和诸侯王,武帝采用的方法相对委婉。汉武帝的这一番良苦用心并非毫无根据,因为:首先,刘安对儒学并不陌生,代表其思想倾向的《淮南鸿烈》一书,如高诱所云,是“讲论道德,总统仁义”的,在黄老思想统率下兼综儒家思想;他的《屏风赋》化用《诗经》成句,⑥ 还借乔木“表虽剥裂,心实贞悫”来表明对朝廷的忠贞。刘安儒道兼综的思想特质,是汉武帝争取其向儒的基础。其次,王逸《楚辞章句·离骚后叙》称“至于孝武帝,恢廓道训,使淮南王安作《离骚经章句》”,明确指出武帝令刘安作传的目的是借其恢廓儒家道训,扩大儒学影响。这也说明武帝诏刘安作传具有深刻的政治目的。
从班固《离骚序》载录的《离骚传》佚文看,刘安对武帝的心思洞悉明了,并在解读时迎合了武帝的政教期待。王逸《楚辞章句·离骚后叙》说刘安作传,“则大义粲然”,可资为证。既然武帝爱骚向儒,刘安就在总论中将《离骚》与已立博士官的《诗经》并提,抬高《离骚》的地位。并从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理论和注重修身养性的伦理道德观念出发,对《离骚》和屈原给予高度评价。刘安之前,贾谊《吊屈原赋》有云:“历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怀此都也?”认为屈原应弃楚而去,对屈原忠于一家一姓乃至付出生命代价表示不理解。刘安则一反贾谊态度,认为屈原是“蝉蜕浊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皭然泥而不滓”,对屈原坚持理想、不与浊世沉浮而走向死亡的人生态度给予高度肯定。这实际是借肯定屈原向武帝表忠贞。其实,刻意迎合武帝,对刘安来说可谓驾轻就熟。如,《淮南鸿烈·览冥训》中,刘安称:“当今之时,天子在上位,持以道德,辅以仁义,近者献其智,远者怀其德,拱揖指麾而四海宾服,春秋冬夏皆献其贡职,天下混而为一,子孙相代,此五帝之所以迎天德也。”高诱注:“天子,汉孝武皇帝。”⑦《上书谏伐南越》中,刘安赞:“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兽,泽及草木”(《汉书·严助传》)。对武帝政绩仁德给予如此高的评价,足见刘安很注意讨好武帝以争取信任。另,据《汉书》本传,刘安在上《离骚传》的同时,又献《颂德》和《长安都国颂》。虽颂文不存,但据篇名推测,内容应主要是歌颂汉德。它们写作目的与《离骚传》一样,都是讨好武帝表忠心的作品。
刘安《离骚传》的解读无疑大大满足了武帝的需求,所以赢得了武帝的欣赏与尊重。《汉书》本传载,武帝“以安属为诸父,辩博善为文辞,甚尊重之。每为报书及赐,常召司马相如等视草乃遣。”“每宴见,谈说得失及方技赋颂,昏莫然后罢。”说明刘安上《离骚传》等文章后,与武帝的关系一度很好。
在建元二年(前139)特殊的政治背景下,恰逢刘安这样一位身份地位特殊的族叔来朝。诏令者深刻的政治目的和被诏者的迎合心理,促成了楚辞的开山解读名篇《离骚传》的诞生,也确立了以儒家诗教理论来评论楚辞的解读模式。纵观楚辞阐释学史,很少有跳出这一模式的解读,足见其影响之深远。
二 “世传楚辞”:利禄扶持下的解读与传播
与刘安同时活跃在武帝朝中的楚辞解读与传播者还有两位,他们就是严助(亦称庄助)和朱买臣。《汉书·地理志》对此有云:
始楚贤臣屈原被谗放流,作《离骚》诸赋以自伤悼。后有宋玉、唐勒之属慕而述之,皆以显名。汉兴,高祖王兄子濞于吴,招致天下之娱游子弟,枚乘、邹阳、严夫子之徒兴于文、景之际。而淮南王安亦都寿春,招宾客著书。而吴有严助、朱买臣,贵显汉朝,文辞并发,故世传《楚辞》。
这段记载说明,武帝之前,楚辞的创作与传播地点主要在楚地,⑧ 这与王逸“楚人高其行义,玮其文采,以相教传”(《楚辞章句·离骚后叙》)的观点是一致的。在这些“以相教传”的楚人中,就包括严忌、严助父子和朱买臣等人。其中,严助和朱买臣都是武帝中朝官员,他们凭借“贵显汉朝”的政治地位,文辞并发,使“世传楚辞”,对楚辞的解读与传播做出了突出贡献。而他们传楚辞,与武帝的利禄扶持密切相关。
严助是较早进入武帝朝中的楚辞传人。《汉书》本传载:“郡举贤良,对策百余人,武帝善助对,繇是独擢助为中大夫。”王先谦《汉书补注》引齐召南语:“助对策在建元元年。”《西汉年纪》卷十、《资治通鉴》卷十七亦将严助对策被任用之事系于本年。关于严助的楚辞活动情况,除上引《地理志》的记载外,《史记·酷吏列传》又云:“买臣以《楚辞》与助俱幸。”另据《汉书》本传,严助于建元六年任会稽太守,数年后因政绩不佳,上书自责,诏许留侍中,于是“有奇异,辄使为文,及作赋颂数十篇。”《汉志》著录:“严助赋三十五篇。”说明,严助不仅善于应对,而且也善为赋颂,并于晚年成为武帝的专职文学侍从。虽其作品皆散佚,但从《地理志》称之与朱买臣“文辞并发,故世传《楚辞》”之语推测,严助辞赋应多为拟骚作品,且颇有文采。而从武帝“有奇异”则命之为文看,其作品应充满奇异色彩。这也是应诏制作给他的辞赋内容带来的必然限定。
朱买臣是以传楚辞得到进用的。《史记·酷吏列传》载:“朱买臣,会稽人也。读《春秋》。庄助使人言买臣,买臣以《楚辞》与助俱幸。”《汉书》本传亦云:“邑子严助贵幸,荐买臣。召见,说《春秋》,言《楚词》,帝甚说之,拜买臣为中大夫,与严助俱侍中。”这证明,为武帝言《楚辞》是朱买臣得封官的一个重要原因。关于买臣的进用时间,荀悦《汉纪》卷十系于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时严助出使南越成功归来,同年出任会稽太守,于此时引荐朱买臣,较为合理。尽管史书对买臣任职之后的楚辞传播活动记载不多,但据《汉书》本传所载,他对诵书歌讴特别钟情:
朱买臣……家贫,好读书,不治产业,常艾薪樵,卖以给食,担束薪,行且诵书。其妻亦负戴相随,数止买臣毋歌呕道中。买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买臣不能留,即听去。其后,买臣独行歌道中,负薪墓间。
在负薪途中“诵书”、“歌呕”,以致妻子羞之,改嫁他人,但买臣仍依然故我,足证其对诵书歌讴的痴迷。而从《地理志》的记载推测,买臣所诵之书,所讴之歌,必然有楚辞。《汉志》著录“朱买臣赋三篇”,说明他也参加了辞赋创作活动。
就史书记载的总体情况看,虽然《地理志》肯定严助和朱买臣在武帝朝对楚辞的传播作出了突出贡献,但因《史记》和《汉书》主要把他们作为杰出的政治活动家来记载,对他们的文学活动情况介绍不多,也没有载录其楚辞解读作品,故无法窥见其楚辞解读与传播的具体成果。但从他们一位最后成为武帝的专职文学侍从,一位以楚辞得幸用的人生历程看,他们的楚辞解读与传播活动主要是在武帝的利禄扶持下进行的,是为武帝的文学趣味服务的。
三 稳定政权:楚辞传人的被诛与楚辞解读的沉寂
在武帝的诏令引导和利禄扶持下,出现了刘安的《离骚传》和严助、朱买臣的“文辞并发”。然而,这种楚辞解读与传播的活跃局面却随着刘安等三人之死归于沉寂。元狩元年(前122),刘安因谋反,诛;同年,严助因受刘安牵连,弃市。元鼎二年(前115),朱买臣与庄青翟等谋陷张汤至死,伏诛。此后至东方朔《七谏》和司马迁《屈原列传》出现之前,文献中不再有武帝朝的楚辞解读与传播活动的记载。楚辞学史上出现的这段空白,与刘安等人被诛杀有关,更与武帝出于巩固政权的需要冷落楚辞解读有关。要弄清这一点,必先弄清刘安等三人之间的关系。
前文已指出,刘安、严助、朱买臣等都是楚人,都传楚辞。对楚辞的共同爱好,很容易使他们走到一起。三人中,朱买臣与严助是至交好友。据《史记·酷吏列传》:“庄助使人言买臣,买臣以《楚辞》与助俱幸。”又,《汉书·朱买臣传》:“后(张)汤以廷尉治淮南狱,排陷严助,买臣怨汤。及买臣为长史,汤数行丞相事,知买臣素贵,故陵折之。……买臣深怨,常欲死之。后遂告汤阴事,汤自杀,上亦诛买臣。”可见朱买臣因严助引荐而心存感激,他之所以谋陷张汤,为严助复仇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这足证二人关系极亲密。而促成严、朱二人被诛杀的重要原因,就是刘安之死。刘安与严助有私交。据《汉书·严助传》,建元六年(前135)五月,闽越兴兵击南越,汉发兵往救,刘安作《上书谏伐南越》。八月,闽越降。于是武帝派严助谕告刘安,“助由是与淮南王相结而还。”此为刘安与严助首次接触的记载。这说明,是政治上的原因,使刘安和严助结识;也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刘安对时为武帝近臣的严助极力笼络巴结。同传云:“后淮南王来朝,厚赂遗助,交私论议”,可为明证。应该说,刘安与严助的交往,主要是政治上的互相利用,但由于对《楚辞》的共同爱好,他们很容易寻找到“交私论议”的共同话题。而严助也因此成了刘安谋反事件的牺牲品!元狩元年(前122)十一月,刘安谋反,诛,国除为九江郡。其事牵涉面甚广,“党与死者数万人”(《汉书·武帝纪》)。这些“党与”,就包括严助在内。《汉书》本传对此记载:“及淮南王反,事与助相连,上薄其罪,欲勿诛。廷尉张汤争,以为助出入禁门,腹心之臣,而外与诸侯交私如此,不诛,后不可治。助竟弃市。”朱买臣是否与刘安有直接交往,史无记载。但由于严助死是导致朱买臣联合庄青翟谋陷张汤以致被诛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严助之死又因与刘安有私交,所以,刘安谋反可以说是促成朱买臣被诛的一个间接原因。
刘安等三人除私交密切外,都具有强烈的复仇心理。刘安“时时怨望厉王死,时欲畔逆”(《史记》本传);严助于建元六年因“家贫,为友壻富人所辱”(《汉书》本传)而求为会稽太守;朱买臣任会稽太守衣锦还乡,更堪称报恩复仇之典范。⑨ 值得注意的是,《史记·酷吏列传》云:“买臣楚士,深怨,常欲死之。”将朱买臣谋陷张汤的原因与他为“楚士”联系在一起,认为买臣之类“楚士”的复仇性格与楚地习俗的熏染有关。据《史记·货殖列传》,西汉时西楚“其俗剽轻,易发怒”;东楚,其俗类徐、僮,“清刻,矜己诺”;南楚则“好辞,巧说而少信”。总而言之,楚地习俗具有易怒、重言诺、好辞赋、言谈巧辩而浪漫不实等特点。在这种习俗下熏陶出来的“楚士”,多善言辞,重意气、有侠气。从严助、朱买臣二人的行事看,就很有这种“楚士”风范。而这种任侠尚气的“楚士”风范,正是重视君臣伦理纲常、天下为公的儒学思想难以容纳的。刘安因父亲死而谋叛逆,朱买臣因个人恩怨而谋陷国家重臣张汤,就必然招致被诛杀的悲剧命运。
三位楚辞传人,一位是据守一方的诸侯王,两位是武帝的腹心之臣,他们之间有密切交往,重复仇,并皆因政治原因被诛杀,这不能不促使武帝对这一现象给予重视。有其元狩元年(前122)四月《遣谒者巡行天下诏》为证:
朕闻咎繇对禹,曰在知人,知人则哲,惟帝难之。盖君者心也,民犹支体,支体伤则心憯怛。日者淮南、衡山修文学,流货赂,两国接壤,怵于邪说,而造篡弑,此朕之不德。《诗》云:“忧心惨惨,念国之为虐。”已赦天下,涤除与之更始。(《汉书·武帝纪》)
诏令指出,淮南、衡山谋反,乃因“修文学”、“怵于邪说”。是思想的“邪”,导致了行为的“篡”。而淮南王刘安思想的文本载体,就包括了他献给武帝的《内篇》与应诏而作的《离骚传》!武帝对刘安给予这样的指责,其实也是对他自己曾“爱秘”《内篇》、曾因《离骚传》对刘安格外欣赏的否定。所以,在诏令中,他先引《尚书·皋陶谟》之语“知人……惟帝其难之”,以尧舜都难知人,为自己曾欣赏刘安、重用严助等人开脱责任;然后又以心体喻君臣,说明诛杀刘安及其党羽实属不得已。而“涤除与之更始”一语,表明了汉武帝将加强对未来思想领域的控制:要革除刘安的邪说,除旧布新。具体更始措施,诏中对《尚书》和《诗经》的引用已作了表率,那就是,要用儒家经典来端正思想,摈却“邪说”!
淮南谋反案,促使武帝更加重视对国家思想领域的控制。据《史记·三王世家》记载,武帝于元狩六年(前117)分封三子闳、旦、胥为齐、燕、广陵王时,分别赐策训诫。其中,训导封在吴越地的广陵王刘胥不可受“大江之南,五湖之间,其人轻心”的濡染,再度流露出对包括吴越在内的楚人楚俗的提防。另外,武帝赐策燕王刘旦,也因燕地临近匈奴,“其民雕捍少虑”(《史记·货殖列传》),而训导刘旦“悉尔心,毋作怨,毋俷德,毋乃废备”。征和二年(前91)戾太子败,刘旦上书求入宿卫,望得立太子,武帝大怒。据褚少孙《三王世家》补传:“孝武见其书,击地,怒曰:‘生子当置之齐鲁礼义之乡,乃置之燕赵,果有争心,不让之端见矣。’于是使使即斩其使者于阙下。”汉武帝这种“生子当置之齐鲁礼义之乡”的感慨,也体现了武帝在刘安谋反后对统一思想稳定政权的认识:只有儒家诗乐才能端正民俗,使君臣父子有序,稳固刘氏政权,而吴楚燕赵之地的风俗及其诗乐,则无益于此。
刘安等人死后,武帝虽然还创作过《李夫人赋》、《瓠子歌》等骚体作品,但鉴于刘安等人事件教训,他认识到要在政治上统一思想、稳固政权,就必须摈除“邪说”,因而对楚辞的解读与传播必然有所冷落。据史料记载,严助元光中离会稽太守任返中央任侍中后,进入辞赋创作的高峰;而朱买臣自元狩元年(前122)刘安和严助死后,尽管也在朝中任职,⑩ 七年后才被杀,但史书中已没有关于其楚辞活动的记载。这一沉寂局面,应与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后对楚辞的冷落有关。
以上考察充分说明,武帝时期的楚辞解读与传播和武帝的政治权力影响有密切关系。出于个人娱乐和政教需要,汉武帝凭藉政治权力,以诏令引导和利禄扶持的手段,推动了楚辞解读与传播的兴起与活跃;而出于稳固政权的考虑,汉武帝诛杀刘安等楚辞传人,客观上促使楚辞的解读与传播走向沉寂。从楚辞解读在武帝朝的兴衰历程,不难看出,由于中国古代文人对皇权的天然依附性,使他们对文学典籍的解读深受统治者权力的影响。这也再度印证了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一个著名论断:“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德意志意识形态》)当汉武帝从稳定政权和个人娱乐的需要出发,利用政治权力对楚辞的解读与传播进行干预的时候,其时代的楚辞解读与传播就必然地打上了他思想的深深烙印。通过这一个案研究,足见在中国古代等级制度下,帝王凭政治权力可以对文学典籍的解读与传播造成的正、负两面影响。
注释:
①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9页。
②《楚辞·渔父》:“屈原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曰:‘……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淈其糟而歠其酾?……’屈原曰:‘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楚辞·九章·涉江》:“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同光。”
③详见《史记·淮南衡山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081页。
④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叙目》,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页。
⑤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要略》,第711页:“若刘氏之书,观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权事而立制,度形而施宜,原道之心,合三王之风,以储与扈冶,玄眇之中,精摇靡览,弃其畛挈,斟其淑静,以统天下,理万物,应变化,通殊类。”
⑥《屏风赋》:“维兹屏风,出自幽谷。根深枝茂,号为乔木”,化用《诗经·小雅·伐木》“出自幽谷,迁于乔木”;“思在蓬蒿,林有朴樕”,化用《诗经·召南·野有死麕》“林有朴樕”。
⑦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第215页。
⑧据《史记·货殖列传》,第3267—3268页:“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此东楚也。……衡山、九江、江南、长沙,是南楚也,其俗大类西楚。郢之后徙寿春,亦一都会也。”则吴属东楚之地,寿春属南楚。
⑨详见《汉书·朱买臣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792—2793页。
⑩据《汉书·朱买臣传》,朱买臣于元狩元年(前122年)由会稽太守拜为主爵都尉,元狩三年(前120年)免,复为丞相长史。
标签:楚辞论文; 汉武帝论文; 汉朝论文; 诗经论文; 屈原论文; 汉书论文; 历史论文; 朱买臣论文; 史记论文; 西汉论文; 离骚论文; 中国历史论文; 二十四史论文; 后汉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