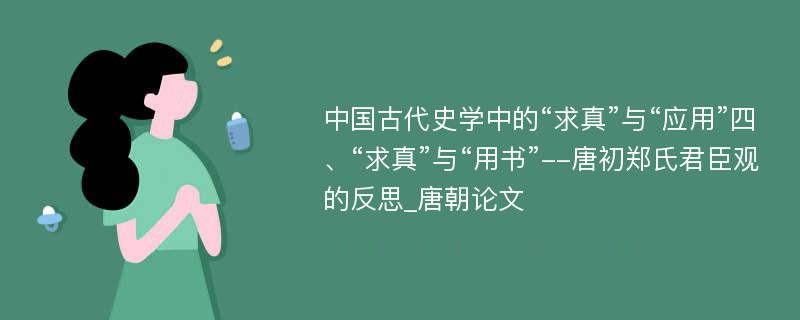
中国古代史学的“求真”与“致用”——4.史鉴在“求真”与“致用”之间——由唐初贞观君臣论政引发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贞观论文,致用论文,史学论文,中国古代论文,君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面临现实中出现的问题,通过回顾与思考,试图从历史中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和答案;或从现实出发,借助历史研究把握事物未来的发展趋势,以便及早作出预测并制定出应对的方案;或从历史成败中汲取经验教训,警示人们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凡此种种皆可称谓“历史鉴戒”,或曰“历史借鉴”,简称“史鉴”。史鉴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优良传统。《诗经·大雅·荡》曰:“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殷商要吸取的教训并不远,即其前代夏朝,夏朝灭亡的教训就在眼前,殷商的子孙应当引以为戒。前事之鉴,后事之师;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这种史鉴思维和认识事物的形式起码在殷商时就已经成熟了。历史鉴戒的思想意识相互影响,递相传承,不仅成就了发达的中国传统史学,也影响着人们的道德观念、修齐治平之学及各种社会关系的调整与有序,维系着传统学术思想与文化绵延数千年不断,而且愈积愈厚。古今学人、政家对“史鉴”传统多有论述与总结,内容十分丰富,若能将之系统整理,便能构成一问新的学问,即“史鉴学”。
历史鉴戒的基础是对历史知识的掌握,而历史知识的获得与掌握并从中汲取有益的启示,离不开“求真”与“致用”两个环节,史鉴与求真、致用,犹如一车两轮、一鸟两翼,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三者原本即是一个整体,缺一不可。善于总结历史以求鉴戒者,必于此三者关系确有恰当处理,使之浑然为一。唐初贞观君臣论政,处处以历史为鉴戒,稽其成败得失之理,揭示人事、立身处世之道,求真致用,借史论政,不仅言辞精辟,而且意蕴深刻,美不胜收,为以后历代君臣所向往,一部《贞观政要》,千余年来传诵不缀。
唐承隋弊,百废待举,又经李唐集团政争内乱,手足相残,唐太宗痛定思痛,深刻体会到一个社会稳定的局面是多么来之不易,如何使天下长治久安?便成了贞观君臣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其实,这本来是一个老问题,唐朝以前的历代统治者对这一问题多少都有过考虑,由于他们所处时代境遇不同,思考问题的态度、方式亦各不相同,效果也不一样。一般来说,效果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对历史的认识与总结,对历史体悟愈深,国家长治久安的道理就愈明确。贞观君臣深识此道,围绕长治久安问题,从各个方面发掘历史智慧。吴怀祺先生将唐代的历史总结归纳为七个方面:即“鉴败莫如亡国”的认识;创业与守成关系的认识;关于“居安思危”的认识;总结盛衰变化的终始之变;“帝王兴运,必俟股肱之力”;“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思想;“以民为本”的理念。(《中国史学思想通史》,隋唐卷前言,黄山书社2004年版)实际上,这些认识、思想、理念,在唐代以前就已经形成了。到了贞观初,社会由乱到治,贞观君臣在重建新的封建君主专制体系和社会秩序过程中,历史上有关治乱、兴衰、成败、安危、始终、君道、政体、任贤、君臣关系等的论题又被一一翻检出来,重新认识、总结,从中获取关于国家治理、社会长治久安的启示、方法和理论。
唐初贞观君臣历经危乱,九死一生与出生入死的考验与阅历,造就了他们博大的政治胸怀与深远的历史眼光。他们借史论政,常怀危惧心理。贞观三年(629),“太宗谓侍臣曰:‘人言作天子则得自尊崇,无有畏惧。朕则以为正合自守谦恭,常怀畏惧……’魏徵曰:‘古人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愿陛下守此常谦常惧之道,日慎一日,则宗社永固,无倾覆矣。唐、虞所以太平,实用此法。’”(吴兢:《贞观政要》谦让第十九)五年(631),“太宗谓侍臣曰:‘治国与养病无异也。病人觉愈,弥须将护,若有触犯,必至殒命。治国亦然,天下稍安,尤须兢慎,若便骄逸,必致丧败。’”(《贞观政要》政体第二)六年(632),“太宗谓侍臣曰:‘看古之帝王,有兴有衰,犹朝之有暮……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魏徵对曰:‘自古失国之主,皆为居安忘危,处治忘乱,所以不能长久。今陛下……留心治道,常临深履薄,国家历数,自然灵长。’”(《贞观政要》政体第二)十四年(640),魏徵上疏,告诫太宗深思“水以覆舟”之鉴,常持危惧心理,曰:“荀卿子曰:‘君,舟也;民,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故孔子曰:‘鱼失水则死,水失鱼犹为水也。’故唐、虞战战栗栗,日慎一日。安可不深思之乎?安可不熟虑之乎?”(《贞观政要》君臣鉴戒第六)唐太宗晚年经常考虑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皇位传承,教导太子也要具有危惧心理。贞观十八年(644),“太宗谓侍臣曰:‘古有胎教世子,朕则不暇。但近自建立太子,遇物必有诲谕……’见其乘舟,又谓曰:‘汝知舟乎?’对曰:‘不知。’曰:‘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尔方为人主,可不畏惧!’”(《贞观政要》教戒太子诸王第十一)这样的危惧心理,使得贞观君臣对人对事对物多能秉持严肃、谨慎的态度,借鉴历史并尊重历史,追求历史的客观性,从历史的真实中发掘其致用的思想意识与价值。
历代君臣大多都能懂得史鉴的道理,亦多论及“居安思危”,然不能达到唐初贞观君臣的思想境界,其主要原因在于贞观君臣能抱危惧心理,居安思危。贞观五年(631),太宗对侍臣说:“今中国幸安,四夷俱服,诚自古所希,然朕日慎一日,惟惧不终,故欲数闻卿辈谏争也。”魏徵曰:“内外治安,臣不以为喜,惟喜陛下居安思危耳。”(《资治通鉴》卷193,唐纪9,太宗贞观五年)《旧唐书·魏徵传》载其上疏,曰:“夫鉴形之美恶,必就于止水;鉴国之安危,必取于亡国。《诗》曰:‘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又曰:‘伐柯伐柯,其则不远。’臣愿当今之动静,思隋氏以为鉴,则存亡治乱可得而知。若能思其所以危,则安矣;思其所以乱,则治矣……《易》曰:‘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诚哉斯言,不可以不深察也。”魏徵一再上言“居安思危”,字里行间颇露战战兢兢的心态,唐太宗也能以危惧的心态接受侍臣的谏争,思考安危的道理,注重自身的修养。他曾与魏徵讨论隋炀帝失国的原因,曰:“朕观《隋炀帝集》,文辞奥博,亦知是尧、舜而非桀、纣,然行事何其反也!魏徵对曰:‘人君虽圣哲,犹当虚己以受人,故智者献其谋,勇者竭其力。炀帝恃其俊才,骄矜自用,故口诵尧、舜之言而身为桀、纣之行,曾不自知以至覆亡也。’上曰:‘前事不远,吾属之师也!’”(《资治通鉴》卷192,唐纪8,太宗贞观二年)隋炀帝口诵尧、舜之言,也知道圣哲的道理,但他恃才自傲,盛气凌人,全无忧惧之心,为所欲为,危亡随之也就到来了。唐太宗“安而能惧”,隋炀帝安则无惧,一治一乱,形成鲜明对比。二人均知尧、舜,唐太宗由尧、舜而知天下所以安,隋炀帝仅仅是口诵尧、舜之言而已。历史是真实的,有人能将其致用,以修身治国;有人只是将其作为粉饰以示风雅。求真与致用只有在严肃的史鉴归纳中得到统一,这也是贞观君臣借史论政给我们留下的启示。
借鉴历史,求真致用,与人的阅历有关。贞观十年(636),唐太宗与房玄龄、魏徵曾就草创与守成难易作过一番讨论,“曰:‘帝王之业,草创与守成孰难?’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对曰:‘天地草昧,群雄竞起,攻破乃降,战胜乃克。由此言之,草创为难。’魏徵对曰:‘帝王之起,必承衰乱,覆彼昏狡,百姓乐推,四海归命,天授人与,乃不为难。然既得之后,志趣骄逸,百姓欲静而徭役不休,百姓凋残而侈务不息,国之衰弊,恒由此起。以斯而言,守成则难。’太宗曰:‘玄龄昔从我定天下,备尝艰苦,出万死而遇一生,所以见草创之难也。魏徵与我安天下,虑生骄逸之端,必践危亡之地,所以见守成之难也。今草创之难既已往矣,守成之难者,当思与公等慎之。’”(《贞观政要》君道第一)房玄龄与魏徵的经历不同,所以对历史的体悟不同,因此在草创与守成难易上会有不同的选择,唐太宗着眼于历史的变化,综合了房玄龄、魏徵的选择,又作出了一个新的选择。由此看来,历史的鉴借与求真致用又是一个不断选择的过程。
历史致用的前提是现实的需要,现实需要什么,又规定着历史致用的选择,不同的需要就有不同的选择。选择实际上也是一个提炼的过程,通过提炼将历史中所隐含的道理揭示出来,人们可以用这些道理解答现实中的问题,或由这些道理指导、警示、劝戒、规范人们的言行,提高人们的道德修养和治政能力,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现实、历史、鉴戒、致用相互打成一片,成为贞观君臣借史论政的各种话题。唐代史学家吴兢将唐太宗与侍臣论政的材料辑为《贞观政要》四十篇,实为四十个论题,即君道、政体、任贤、求谏、纳谏、君臣鉴戒、择官、封建、太子诸王定分、尊敬师傅、教戒太子诸王、规谏太子、仁义、忠义、孝友、公平、诚信、俭约、谦让、仁恻、慎所好、慎言语、杜谗邪、悔过、奢纵、贪鄙、崇儒学、文史、礼乐、务农、刑法、赦令、贡赋、辩兴亡、征伐、安边、行幸、畋猎、灾祥、慎终。所有这些论题基本上都是亡隋之后围绕现实问题所作出的历史思考。其中许多论题是关于个人道德思想修养方面的总结,至今仍有借鉴意义和作用,也有贞观君臣针对治政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向历史寻求解决办法的探讨。现实需要规定着历史借鉴与求真致用,贞观君臣在这方面的探索为后人积累了经验。
唐太宗还善于对历史人物进行心理分析,求得历史真实,并引以为戒,“贞观四年,太宗问萧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对曰:‘克己复礼,勤劳思政,每一坐朝,或至日昃,五品已上,引坐论事,宿卫之士,传飧而食,虽性非仁明,亦是励精之主。’太宗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此人性至察而心不明。夫心暗则照有不通,至察则多疑于物。又欺人孤儿寡妇以得天下,恒恐群臣内怀不服,不肯信任百司,每事皆自决断,虽则劳神苦形,未能尽合于理。朝臣既知其意,亦不敢直言,宰相以下,惟即承顺而已。朕意则不然,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千端万绪,须合变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筹画,于事稳便,方可奏行。岂得以一日万机,独断一人之虑也。且日断十事,五条不中,中者信善,其如不中者何?以日继月,乃至累年,乖谬既多,不亡何待?’”(《贞观政要》政体第二)隋文帝心暗多疑专断,如此愈勤劳,出错的机率愈多,长久以往,必至败亡。唐太宗有鉴于此,诸事大胆委任于臣属,自己仅作些总体把握。一反一正,历史借鉴中的求真与致用,可以说是一个典型范例。
由唐代贞观君臣借史论政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史鉴在求真与致用之间,求真、史鉴、致用是一个有机的联系,在历史研究中,虽有侧重,但不可偏废。求真要着眼于借鉴、致用,致用要以求真为基础,不可违背史鉴的法则。史鉴、求真与致用应以现实问题为前提,用历史研究解答现实问题,历史学便能焕发出无限生机。求真致用,从历史中获取鉴戒,其方法不仅仅是考据、归纳等文本研究,还有历史人物的心理研究,不仅要有高深的学识,还应具备丰富的阅历、谨慎的心理、真挚的情感等。历史的真实或蕴涵于文字之中,或在文字之外,研究历史不仅要懂得文字之内的东西,还要懂得文字之外的东西,懂得文字之内的东西未必真懂,只有懂得文字之外的东西才叫真懂。
具备丰富的阅历,善于思考,既使不识字,也能悟出史事中所蕴涵的真实。后赵石勒目不识丁,“虽在军旅,常令儒生读史书而听之,每以其意论古帝王善恶,朝贤儒士听者莫不归美焉。尝使人读《汉书》,闻郦食其劝立六国后,大警曰:‘此法当失,何得遂成天下!’至留侯谏,乃曰:‘赖有此耳。’”(《晋书》卷105,《石勒载记》)如果不经过血与火的砺练,则不易感悟到历史中的兴衰成败之理。中唐以后,君臣多向往贞观之治,常仿贞观行事,然毕竟缺乏贞观君臣的经历,学习贞观亦仅及皮毛而已。历史求真须用真心去体会,亦须用心致用。
古今或有学者视求真与致用为二物,谓求真不必考虑致用,致用不必计较真实,由此形成好议得失而不辨虚实的学风。清代学者崔述撰《考信录》,曰:“大抵文人学士多好议论古人得失,而不考其事之虚实。余独谓虚实明而后得失或可不爽。故今为《考信录》,专以辨其虚实为先务,而论得失者次之,亦正本清源之意也。”(《崔东壁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崔述考信古史,辨虚实,求真以致用。梁启超论清代学术,谈及学术所受政治的影响,认为文字狱兴,学者转向考据,汉学一枝独秀,清初经世致用的精神衰息。实际上,乾嘉学者讲究“实事求是”,并不废“经世致用”,只是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学术研究的侧重点不同而已。王国维论学问,认为学问无中西、新旧、有用无用之分;顾颉刚云“学问当问真不真,不应问用不用”。学问之真与用,原本为一物,犹物之价值与使用价值。由于人们对之认识不同,遂将之相分,甚至被说成是矛盾对立的两个方面,熊掌鱼翅不可兼得,这实际上是一种不符合实际的偏见。事实上,在历史研究的实践中,确实也存在着实用主义的现象,不问虚实,拿来就用,借喻影射,这些研究者多是囿于学识,心浮气躁,执一端而不顾其它,其违背历史求真致用的法则,自然不可避免,本想达到致用的目的,实际上并不能达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