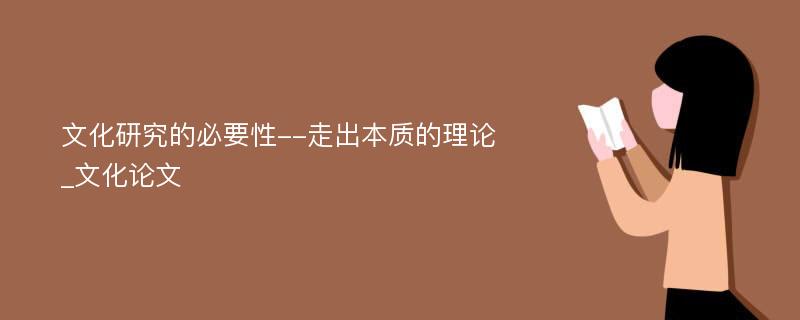
文化研究的必然性——走出本质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必然性论文,本质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伯明翰传统的文化研究传入中国,开始受到学界认真关注,应是1990年代后期的事情。有鉴于本文作者过去曾经是,现在也还是在文艺学的体制之内写过一些文化研究的有关著述,对于文艺学让许多先辈学者忧心忡忡的文化研究转向,可以说是深有体会。某种程度上说,坚持文艺学的文学本位研究,抑或拓边恳土,藉文化研究的因由开辟新的疆域,直接关系到当前文艺学本质论和建构论的考量。霍加特《识字的用途》中,以身说法,叙写了一段特殊的工人阶级的文化史。本文愿汲取其自内而外、深入对象内部的民族志方法,就中国的文化研究如何在不经意的偶然之中,见出未必是偶然的因缘因果,略作探究。
游走学科边缘
文化研究的一个迄今彰显无误的特征,是它始终游走在学科边缘。以1964年伯明翰中心的成立为这门准学科的起点,那么如果说它早期的关键词是异化、意识形态和霸权,它的现状,则已稳稳立定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之中,与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大多数学科结成了同盟。对于美学和文学研究,它提供了背景和语境,对于社会学研究,社会结构、社会制度和社会变革同样也是它的研究对象。从历史上看,文化研究的缘起同哲学和人类学联系密切。哲学是指西塞罗的传统,以文化为心灵和人格的培育,从十八世纪末叶开始,这一传统的重新从个人向公共社会转移,现代性由此成为它的纲领。从马修·阿诺德、F.R.利维斯、T.S.艾略特到雷蒙·威廉斯,文化先是被描述为主要是文学文本中体现的高尚的道德价值,格格不入于个人主义、物质主义和市侩作风,继之在批判视野中将大众文化引入学术,终而把文化定义为一个总体上的生活方式。如是文化不复是高雅文化的专利,而渗透到每一个民族的物质和精神层面。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吉尔兹对文化的定义,由是观之具有代表性。他认为文化涉及到“符号表征的某种历史转换的意义模式,某种根据人们如何交流、永久保存以及发展他们关于生活态度的知识,而以符号形式表达的与生俱来的感知系统。”① 这个对当代文化研究广有影响的定义,应当说尤其适合于文化的信仰、价值和符号分析的社会学方法。它意味文化是规范、是价值,是符号,也是意义和行为。文化研究的社会学视野致力于社会语境中的文化分析,这个语境不可能是别的,它必然是现代性和后现代的语境。
今天文化研究在中国高校里方兴未艾,远未走到穷途末路的盛况,也许可以和上个世纪80年代的美学热做一个比较。美学在中国80年代解放思想,百废待兴的文化氛围中异军突起,当仁不让以一个边缘学科的身份,承担了译介西学,鼓吹启蒙的社会使命。90年代之后美学热退潮,这一方面是因为建构体系,以及客观派、主观派,甚至实践美学、后实践美学这一类高屋建瓴的论争,在更重视实证研究的后现代语境中风光不再;另一方面,美学因为它在西方学科中的相对弱势地位,近年少有纯粹的美学资源给译介过来,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比较来看,中国的文化研究热不妨说只是刚刚起步,很大程度上还处在投石问路的探索阶段。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兴起,毋庸置疑同样具有水到渠成的思想背景。对此汪晖《九十年代中国大陆的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一文中的一个交代,很可以说明问题。汪晖这样描述是时中国学界稍嫌浮躁的理论期待现状:
原来的许多社会意识形态已不能和变化了的社会生活相适应,于是社会上的各阶级或阶级中的某一阶层的代表人物就起来倡导某种思想,企图适应或者抵制变化了的社会生活。如果这种思想确实反映了该阶级、该阶层中部分人的利益、意志、愿望和要求,确实掌握了一部分群众,并在和别种思潮的斗争中产生了影响,形成了潮流,这种思想也就在这个变动了的时代和历史中成了社会思潮。②
可以说,文化研究正是在这一各路思潮相继交锋往来的背景之下,作为一种兼收并蓄,具有极大开放性的交叉学科,进入中国学术语境,并且如燎原之火,迅速蔓延开来的。而它作为一种政治色彩浓厚的学术实践,从另一方面看,又迂回满足了立足于社会批判的人文精神建构需要。此外文化研究作为一门学科建树的西方的理论资源,不是匮乏而是太为充盈,这也是它可以前赴后继,从容发展的一个原因。要之,即便文化研究的热情有一天同样会悄悄退潮,它应该能像美学一样,在我们的学科体制中牢固地确定自己的地位。回顾文化研究的不长的历史,可以说它是在表现为研究方法和策略的同时,形成了一门相对独立的新兴科学。但是文化研究作为方法既千头万绪,各成体统,文化研究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它怎样从哲学、社会学、文学这些传统学科中脱胎而出,以及它如何依然难分难解地呈现着鲜明的跨科学态势,也是可以细加考究的。
就文化研究同文学研究的纷争而言。文学在面临文化研究的挑战之前,她的“强敌”主要是哲学。本文作者在中文和哲学这两个一级学科内供职的时间,几乎对半,所以或有资质评判个中的是非。从历史上看,无论是把哲学比作至高的女神,如五世纪的波爱修;还是把它比作主掌一应小妾的主妇,如一世纪的犹太哲学家斐洛;抑或把它比作高踞在一切婢女之上的婢女,如三世纪的奥里金,都是将哲学当成了女性。可是哲学其实是一位男性。他居高临下,一语破的,明察秋毫,一副将世界把玩在掌中的大家贵族气派。即便需要文过饰非,他也冠冕堂皇,决不露出羞羞答答的可怜相来。反之文学理所当然是一位女性,她颠三倒四,扑朔迷离,经常是南辕北辙,无的放矢,惯于向壁虚造而不善示人以赤裸裸的真理。我们总听到她在絮絮叨叨作自我辩白,忽儿声明她是在如实反映人生,满载着人文关怀;忽而提醒人她原本什么都不肯定,所以从来不曾撒谎。说这些话的时候文学自有一种微妙的魅力,打扮修饰下来,女人味实足,只因她时时提心吊胆,唯恐她的男性上司看不入眼。
但是在当今全球化一体化的市场经济大潮中,文学和哲学,其实是在同病相怜。如果说今天文学自身在日趋分化,它的一部分投靠了专心事奉感官的大众文化,一部分则见异思迁,非要看齐哲学的形而上的高深,该不是夸张其辞。文学何以热衷向哲学看齐姑且不论,文学的文化转向,或者说,文学研究的文化研究转向,却有着不以学人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原因。中国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对于现代性种种继承、批判、反思、重建的努力,我们都不会感到陌生。今天学生畅游网络的时间远较捧着书本的时候为多。年轻一代对于影视作品、流行歌曲、网络游戏的熟悉和亲密程度,远非他们上辈人的童年青年时代所能想象。而假如以图书馆为高雅文化的象征,以影视作品、流行歌曲和网络游戏为大众文化的象征,那么显而易见,大众文化以它喜闻乐见并且鼓励直接参与的娱乐形式,以及它与生俱来的市场机制,无疑是正在跃跃欲试替代高雅文化,出演新的精神导师的角色。文化研究设定大众文化为它的研究对象,由是观之,或者未尝不是学界曾经垂青有加的一种“范式转型”。它肯定波及到传统作为文化最核心组成部分的文学。诗人和作家的名分过去是神圣的,现在诗人一半成了笑谈,作家就这个群体的大部分是在艰难谋求生存而言,早已褪去了围绕在头上的灵光。在这样的情况下,原来从事文学研究的庞大队伍发生分化,不再聚精会神盯住意识形态和审美经验,进而从文化的角度来做一些文学外围的研究,这对于文学和文学研究自身来说,肯定就不是权宜之计了。
大众文化研究
中国的文化研究推究起来,它的起点应是大众文化的研究。这一点和本文作者的文化研究经历大体相吻。我和王毅合撰的《大众文化与传媒》出版是在2000年。当时我们准备写一部比较有系统的文化研究著作,甫有梗概,时任上海三联书店总编辑的吴士余说,可否抽出一部分来,出一个册子?因此就有了这本小书。《大众文化与传媒》可谓国内第一本择要介绍西方文化研究理论的著述。或者因为“新进”的缘故,书中也有不能尽如人意的地方。2001年同样是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了一个读本《大众文化研究》,我和王毅选编。这个读本面世较之罗刚和刘象愚主编的《文化研究读本》晚了一年,但是具有它自己的特点。除了文章出处和注释无一遗漏作了交代,它还是国内非常早的一部解决了版权问题的翻译文集。进入21世纪,中国的知识产权意识已经相当明确,图书引进偷梁换柱,绕过版权的,已基本绝迹。但是涉及文集,同一作者的大抵请作者自选,不同作者的文集则每置之不理,整本书每篇文章逐一同它们版权所有者落实下来的,少有人尝试。这个尝试其实是殚精竭虑的。或者说,它本身是见证了知识版权在中国普及的一个必然过程。
我们的程序是王毅先同选定篇目的作者、出版社、刊物联系,委婉说明这个选本是旨在文化交流,无利可图,企盼对方授予版权。作者的态度总见爽快,无奈版权大都不在作者手里,故还是免不了同出版社交往。出版社是商业机构,它关心的是利润而不是学术。不到万不得已,决不妥协。《大众文化研究》选定了十八篇文章,王毅同十八个版权所有方来回拉锯较量下来,所幸功成过半。剩下来王毅自感无能为力的,一概交由我来交涉。我则坦率告诉对方,这本文集的宗旨是向中国读者介绍西方的文化研究,它是不盈利的,出版社最多保本,假如一定要申求版税,那么它就只有夭折。再进一步,那就坦陈此文集的所有版权拥有者均已经同意赠与,如果对方依然坚持要购买,吾人只有忍痛割爱,撤下有关篇章。这一步可谓置之死地而后生,基本上可以扫清障碍。但即便如此,有一家英国某大学的出版社,硬是不肯让步,非要将它的一篇讨论女性时装的文章,卖上数百英镑。反反复复下来,竟是百无奈何。因为王毅版权意识明晰,不敢含糊,最后竟不得不通知上海三联,撤下已经完成,并且编辑排好的译稿。另外伦敦大名鼎鼎的圣贤(Sage)出版社,也是个难缠的对手。临到最后,它开出的条件是,在文集的“致谢”页上,详细注明Sage的通信地址和网址。我告诉圣贤,当然《大众文化研究》会有一个“致谢”(Acknowledgement),逐一列出赠与它版权的所有出版机构,但是圣贤要把它具体到门牌号码的地址以及网址也排列出来,是不是和上下文的体统不尽相符?但是圣贤再也不肯退让一步。因此细心的读者可能注意到,《大众文化研究》的致谢页上,所有赠与作品中文翻译和在中国发行权利的出版社、杂志社和著作人均是一言带过,唯独圣贤出版社留下了它的地址和网址。今天回顾起来,这个案例如果不能说明别的,那么它至少可以说明,知识产权如何在利益和权利的夹缝之间登陆中国的大众文化研究,本身就是一个值得细细考究的课题。
大众文化是为文化研究的主要对象,这一点学界很少有人提出疑义。问题是大众文化本身如何定义,似乎是大有讲究的话题。一个流行的趋势是,凡言大众文化,必称后现代、后工业、全球化、市场资本和消费主义。如金元浦2003年发表的《重新审视大众文化》一文,虽然不似早年他《定义大众文化》的文章那样,引经据典将大众文化界说得神乎其神,也还是从三个方面来框架了大众文化:1、大众文化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作历史性转型的产物。2、大众文化体现的是现代科技与现代生活。3、大众文化改变着中国当代的意识形态,表明了市民社会对自身文化利益的普遍肯定以及小康时代大众文化生活需求的合理性。陶东风《大众消费文化研究的三种范式及其西方资源》一文则对此评价说,金文捕捉到了大众文化特别是新媒体在拓展公共空间方面的民主化潜力,以及弱势群体利用这种空间的可能性。但是,金文的大众文化定义同样存在问题,比如首先它没有充分估计大众文化的消费文化消极面影响,也没有充分注意大众文化市场和官方的双重体制环境。但是以金元浦和陶东风为代表的一以贯之的主流看法,在本文作者看来是可以推敲的。2003年我和我的学生路瑜写过一篇《大众文化研究在中国》的文章,对迄至当时中国大众文化的研究做了回顾。我们有意识对大众文化作宽泛定义,以我们今天所说的“大众文化”对应英文中的popular culture,那么问题就很清楚了:
有人因此论证大众文化不是通俗文化、流行文化和群众文化,因为它是以生产方式而不是以阶级、阶层作为定义自身的标记。可是英文popular culture,顾名思义,也就是通俗文化、流行文化、群众文化,一如pop arts这个词到今天还译作波普艺术、流行艺术,而不译作大众艺术。因此,问题当在于怎样来看待这大众文化或者说流行文化、通俗文化,以及它在特定的时代里具有怎样的特征。一个例子是坎托(N.Cantor)和沃思曼(Werthman)编撰的《大众文化史》(1968),它源头一直上溯到古代希腊。古代希腊的体育竞技和戏剧,罗马的血腥角斗以及泡澡堂的悠闲从容,都被视为典型的大众文化形式。③
这里都涉及到大众文化的历史渊源问题。这历史也就是俗文化的历史,更确切说当是城市文化和市民文化的历史。由是观之,即便是把工业化批量生产和消费视为大众文化的必要条件,就像当今学者定义大众文化必予声明的那样,那么大众文化的历史也足以上推一百年。但大众文化在中国的扬眉吐气,推究起来也就是十余年间的事情。在此之前,大众文化久被认为是统治机器从上面灌输下来,是商业原则取代艺术原则,市场要求代替精神要求,故与其说是大众自发的文化,莫若说是麻痹大众的文化。这基本上是移植了西方一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始终代表主流声音的大众文化批判立场。而在今天看来,九十年代初叶的中国,之所以对于大众文化的批判和声讨不绝于耳,一个原因或在于知识分子以精英自居,突然发现自己濒临边缘化危机,大众文化如此便是满腹狐疑的最好的替罪羊。
但是此一忧虑后来证明是多虑了。中国在过去的二十年里见证了大众文化如火如荼的勃兴和发展。今天它不但是中国市场经济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且毋庸置疑还是主流意识形态的一个宠儿。藉此而言,同西方语境中大众文化作为统治意识形态的颠覆力量,不可相提并论。总的来看,从上世纪八十年底起,中国的大众文化研究可以说基本上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是谴责大众文化的阶段,炮火的弹药则几乎无一例外是来自法兰克福学派,特别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文化工业理论。第二个阶段发生在世纪之交,表现为西方文化研究和文化理论的引进和翻译。第三个阶段则是文化研究的本土化阶段,它也是当代中国文化研究和大众文化研究现时态的写真。所谓本土化,不仅指出版机构开始将目光转向国内的文化热点,而不是一味盯住西方理论,同时也指文化研究的课程在高校不同院系里纷纷开出,以及,大众对日常生活开始形成的一种“文化”的和“美学”的态度。它的一个直接结果,便是见仁见智、言人人殊的“日常生活审美化”。
日常生活审美化
日常生活审美化成为众说纷纭的学术议题,一定程度上,甚至成为当代中国文化研究的一个自然多有曲解的同义词,可以说是一个极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现象。特别是它直接涉及到高校学制中美学和文艺学专业所面临的文化研究冲击问题,所以格外引人注目。文化研究作为当年英国伯明翰中心的传统,它的主流是所谓的“文化主义”(culturalism),而文化主义的纲领,就是当年雷蒙·威廉斯提出的“文化是普通人的文化”(culture is ordinary)。由此很自然引出日常生活,特别是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话题。可以说,要不要接纳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研究,事实上已经成为传统美学和文艺学立场和文化研究立场论争的一个焦点。
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国内言及这个话题必有引述的两本书之一,是德国哲学家沃尔夫冈·韦尔施《重构美学》,2002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陆扬和张岩冰译。该书原版是伦敦圣贤出版社出版的英文本。从版权页上看,这本书没有德文的底本,这一点同作者的另一本美学著作《审美思维》不一样。虽然作者本人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且长期在斯坦福大学执教,但《重构美学》中的十一篇文章均系从德文译出,并非作者用英文撰写。可以看出,圣贤出版社出了一部作者的自选集,绕过了购买德文版权。转而又向上海译文售出了《重构美学》的英文版权。可见在知识产权的市场上,圣贤的确是游刃有余的。
日常生活审美化涉及许多现实问题,比如说香车豪宅、时尚美人究竟是中产阶级的专利,同劳苦大众十万八千里风马牛不相及,以及充其量退一步也只是小资们的文化和美学呢?还是它们一样是十万八千里之外的农民阶层心向往之的权利?但是显而易见围绕这个话题的论争,始终是具有鲜明的学院派的背景,参与者多为中心城市和高校中有关学科的领军人物,反之在这个圈子之外的评论家较少参入其中。不遗余力倡导日常生活审美化研究的学人,国内比较有代表性的有陶东风、金元浦和王德胜等。理由是日常生活审美化不管是你喜欢它还是不喜欢它,毋庸置疑它已经是今天我们城市生活的真实存在语境,所以同它关系最为密切的美学和文艺学继续正襟危坐对它视而不见,只能是自欺欺人。这是说,今天审美活动已经远远超出了纯艺术和纯文学的范围:
占据大众文化生活中心的已经不是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绘画、雕塑等经典的艺术门类,而是一些新兴的泛审美、艺术活动,如广告、流行歌曲、时装、美容、健身、电视连续剧、居室装修等,艺术活动的场所也已经远远逸出与大众的日常生活严重隔离的高雅艺术场馆,深入到日常生活空间。可以说,今天的审美/艺术活动更多地发生在城市广场、购物中心、超级市场、街心花园等与其他社会活动没有严格界限的社会空间和生活场所,在这些场所中,文化活动、审美活动、商业活动、社交活动之间不存在严格界限。④
对于“日常生活审美化”(the aestheticization of everyday life)这个术语,其话语权考究起来,也耐人寻味。陶东风作为“日常生活审美化”大张旗鼓的推广者,固然有理由申张这个术语的话语权,但是早在2001年,周宪发表在《哲学研究》上解读文化“视觉转向”的《日常生活的“美学化”》一文,已经使用了这个术语,唯以“美学化”而非“审美化”对译aestheticization。所以周宪也有理由申张这个术语的话语权。无独有偶,《重构美学》译稿出版社安排的审读中,一度也将“审美化”改作“美学化”,唯因本文作者感觉“美学化”一语太多学院气,又改回了通俗一些的“审美化”。再往上看,译林出版社2000年出版,是为当今日常生活审美化研究另一个主要理论来源的,英国社会学家费瑟斯通的《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其中一章的标题就是“The Aestheticization of Everyday Life”,只不过中文译作“日常生活的审美呈现”。再往上追究,有人提出还可以上溯到“五四”之后的“新生活运动”。自然,个中讨论语境的差异,不可以道里计。这可见,追究“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话语权,只能是一笔糊涂账。关键是它成了今天中国文化研究的一个热门话题。而在金元浦看来,日常生活审美化中出现的艺术“泛化”现象不是艺术的堕落,反之,艺术与当下生活的生动联系,恰恰是美学“重出江湖”、再度振兴的绝好机会。即是说,当审美性不再是文学艺术的专属性能,而成为商品世界的共性的时候,美学和文艺学自然也要突破原有界限,随生活的转向而拓展新的领地。
但是,日常生活审美化能在多大程度上体现当代中国美学和文艺学研究对象转向之必然?甚至,它能在多大程度上代表文化研究应当关注的主流方向?这绝不是没有疑问的。首先陶东风的老师童庆炳和金元浦的老师钱中文,对他们两位的高足热心阐发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美学内涵,极不以为然。童庆炳借用当年自己老师黄药眠的说法,讥之为那是食利者的文化,与普罗大众毫不相干。故围绕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这一场论争,一般认为是反映了当代中国文艺学阵营老一代专家和中青年学者对文化研究的冲击的不同看法。其实《重构美学》的作者韦尔施本人,对日常生活审美化所抱的批评态度,是显而易见的。他认为这场“审美化”浪潮甚至将我们的灵魂和肉体一股脑儿卷了进去,我们可不是在美容院里残忍地美化着我们的身体,而且这早已不仅仅是女性的专利。对此他讥嘲说,“未来一代代人的此类追求,理当愈来愈轻而易举:基因工程将助其一臂之力,审美化的此一分支,势将造就一个充满时尚模特儿的世界。”⑤ 这类模特儿毋宁说就是所谓的“美人”(homo aestheicus),它替代了不久以前还在出尽风头的知识分子,而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当代英雄”。
这可见,“日常生活审美化”之所以成为一种学术话语,根本宗旨在于对资本主义消费文化的现实展开批判。离开这个批判语境,一切貌似中立的欣赏和分析都将显得言不由衷。诚如韦尔施本人强调说,我们不能忽略这个事实,这就是迄今为止我们只有从艺术当中抽取了最肤浅的成分,然后用一种粗滥的形式把它表征出来。结果是美失落了它更深邃的可以感动人的内涵,充其量游移在肤浅的表层,崇高则堕落成了滑稽。要之,这一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就并非如一些理论家所言,是实现了前卫派冲破艺术边界的努力,相反是把传统的艺术态度引进现实,加以泛滥复制,导致日常生活出现审美疲劳,艺术疲劳,说到底还是镜花水月的一种反照。
由此可见,中国的文化研究一路走来,较之过去一个世纪里的任何一种西学东渐,都更具有理论和实践同步推进的共时性,毋宁说是在一系列偶然事件中,显示了一种必然性。从而将当代中国文化生产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问题、大众文化乃至高雅文化的市场化问题,以及文化研究的体制化问题等等,一并纳入考量推究的视野。但是她也并非没有危机。它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或许因为中国的文化研究尚未抹去她的“文学出身”印记,并且中国的文学批判历来具有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点评式传统,致使迄至今日的文化研究成果,相当一部分还是较为随意的心得和随笔,具有厚重理论背景的研究文献显得稀寥。另一方面,有鉴于中国的文化研究同样开始了效法霍尔的“社会学转型”,重视实地考察的“民族志”方法得以广为传布,但是由此得出的成果,往往同社会学的田野调查大同小异,文化研究的学科特征显得模糊。故此,如何建树具有中国自己特征的文化研究学科,看来本土化并不是唯一的路径,恰恰相反,文化研究的西方理论,特别是伯明翰传统的充分引进和消化,依然是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的。
[本文得到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资助]
注释:
① Clifford Geertz,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New York:Basic Books,1973,p.89.
② 汪晖:《九十年代中国大陆的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电影艺术》,1995年第1期。
③ 陆扬、路瑜:《大众文化研究》,《天津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
④ 陶东风:《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化研究的兴起》,《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1期。
⑤ 沃尔夫冈·韦尔施:《重构美学》,陆扬、张岩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第11页。
标签:文化论文; 大众文化论文; 美学论文; 流行文化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西方美学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哲学专业论文; 文艺学论文; 文学论文; 陶东风论文; 人文学科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