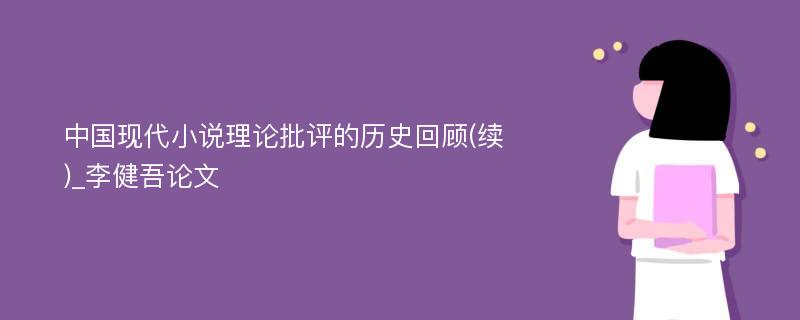
中国现代小说理论批评的历史回顾(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批评论文,理论论文,现代小说论文,历史回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第三时期
一、抗战与民主:现代小说批评的新尺度
八年抗日战争,三年解放战争,民族战争和阶级斗争的新形势引起不少作家文学观念的变化。抗战爆发以后,文学家们以巨大热情投入抗击侵略者的洪流,并自觉地将自己的写作调整到为抗战服务的轨道。茅盾说,“目前我们的文艺工作万般趋向于一个总目的,就是加强人民大众对于抗战意义之认识。对于最后胜利之确信”(《论加强批评工作》)。周扬说,“离开民族抗战的现实,新文学的存在就不能想象”(《从民族解放运动中来看新文学的发展》)。抗战胜利以后,朱自清在《文学的标准与尺度》一文里写道:“抗战起来了,‘抗战’立即成了一切的标准,文学自然也在其中。胜利却带来了一个动乱时代,民主运动发展,‘民主’成了广大应用的尺度,文学也在其中。”朱自清在1947年说的这段话,真实地概括了这十多年间文学观念的深刻变化。
另一方面,为了战胜国内外的敌人,中国共产党在广大抗日民主根据地和解放区,对文武两个战线都非常重视。他们依靠拿枪的军队对敌作战,同时也重视文化战线的建设。在文艺工作方面就提出了一系列的革命观点,诸如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文艺服从于政治,文艺的民族形式,普及第一,文艺批评是文艺界的主要斗争方法,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等等。这些观点,不但在中共领导的地区成为指导文艺运动的方针,而且其影响也遍及国统区的进步文艺界。
民族战争和阶级斗争的新形势所带来的文学观念的种种变化,必然会从广大作家创作题材与主题的选择中反映出来,同时也必然影响到小说批评的标准与尺度。因而本时期的小说批评就出现了以下若干特点。
首先,本时期的小说批评对于描写民族战争和阶级斗争重大题材的小说作品总是予以热情的关注和积极的肯定。在抗战时期,大部分小说作者都从不同的视角来反映这场神圣战争,反映各阶层人民在战争中的命运变化;至于解放区,正如周扬所说,“民族的、阶级的斗争与劳动生产成为了作品中压倒一切的主题,工农兵群众在作品中如在社会中一样取得了真正主人公的地位。”(《新的人民的文艺》)当然,这时期并不是完全没有其他题材的小说,但是在数量上占最大比重的,在读者中产生巨大影响的,还是描写重大题材的作品。同样也正是这类作品引起小说批评家的特别青睐和关注,并热情的加以倡导与弘扬。如在抗战爆发一年以后,茅盾在著名文章《八月的感想》里就热情洋溢地写道:“抗战的高热,刺激了中国巨大的有活力的新细胞,在加速度滋生而壮健起来”,小说也出现新面貌,“新的典型,已经(虽然不多)在作家笔下出现。‘华威先生’(张天翼《华威先生》)就是旧时代的渣滓而尚不甘渣滓自安的脚色,‘差半车麦秸’(姚雪垠《差半车麦秸》的主人公的诨名)正是‘肩负着这时代的“阿脱拉斯”型的人民的雄姿’。在《北方的原野》(碧野)里,我们听见了斗争中的青年战士们的充满着胜利的自信的笑声,青年农民出身的游击队员‘黑虎’,农家孤儿十来岁的‘柱儿’(皆为《北方的原野》里的人物)不都是崭新的人物?……我们又看见‘小弟弟小杜’怎样为祖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小杜是骆宾基的短篇小说《一星期零一天》里的人物),而这位‘小弟弟’正是在炮火里长大坚强起来的战士的典型。”“一定也有人觉得这些典型人物还不免是略具须眉的素描,而不是巍然耸立威仪堂堂的巨像,但是我们决不能否认,新时期的各种典型已经在我们作家的笔下出现了。蓓蕾既已含苞,终有一日灿烂开放。”又如胡风在为丘东平的小说集《第七连》写的“题记”里说:“现在的这一本,在斤两上又何尝轻?展开它,我们就象面对着一座晶钢的作者的雕像,在他的灿烂的反射里面,我们的面前出现了在这个伟大的时代受难的以及神似地跃进的一群生灵。”后来又称赞《第七连》是“真真实实的抗日民族战争英雄史诗的一首雄伟的序曲”;赞扬《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是“中国抗日民族战争的一首最壮丽的史诗。在叙事与抒情的辉煌的结合里面,民族战争的苦难和欢乐通过雄大的旋律震着读者的心灵。”(《忆东平》)
赵树理体现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小说是解放区文学的优秀代表。周扬赞扬他的《李有才板话》“是一篇非常真实地、非常生动地描写农民斗争的作品,简直可以说是一个杰作。”它和《小二黑结婚》《李家庄的变迁》描绘了“三幅农村中发生的伟大变革的庄严美妙的图画”,“这是现阶段中国社会的最大最深刻的变化,一种由旧中国到新中国的变化。”(《论赵树理的创作》)郭沫若也撰文对《李有才板话》大加赞扬。他说:“我是完全被陶醉了,被那新颖、健康、素朴的内容与手法。这儿有新的天地,新的人物,新的感情,新的作风,新的文化。”(《〈板话〉及其他》)此外,解放区的其他优秀小说也都得到很高评价。如茅盾在《关于〈吕梁英雄传〉》里称赞这部小说生动地反映了“人民大众在抗日战争中的英勇斗争。……因为作者正确地把握了人民的立场,所以他笔下的这些并没脱离生产的民兵以及小规模的袭击,不但不使我们有寥落寒伧之感,反而觉得轰轰烈烈,惊心动魄,仿佛看见广大的土地上到处燃起复仇的火焰,使得深入的敌人寸步难行。”又如有的评论者指出《暴风骤雨》是“用农民的语言,农民的生活,表达农民的感情,特别是表达农民的革命情绪,如此鲜明强烈,如此真实,这是解放区文艺创作的一个基本特色。”(韩进《我读了〈暴风骤雨〉》)[(46)]
从以上数例可以窥见本时期小说批评的新动向。抗战与民主,这种批评尺度在以往的小说批评中已有出现,只是没有成为多数批评家评论作品的准绳。到了本时期,在民族战争和阶级斗争十分激烈的时代,它终于被更多的批评家所接受,并被大大地强化了。这是小说批评的富有时代气息的新的价值取向。
其次,本时期小说评论界经常展开对作品作不同评价的讨论与争鸣。对同一部小说出现不同的评价意见,这在以往的小说批评中也曾经有过,但一般都是各抒己见,较少直接思想交锋。本时期可能是受现实斗争形势的影响,或者是由于“文艺批评是文艺界主要斗争方法”理论的导引,小说批评界经常发生具有一定规模的针锋相对的论争,这种正常的争论,往往有利于更深入更全面地揭示小说作品的思想艺术风貌。
张天翼的小说《华威先生》的讨论持续了两年多的时间。1938年4月发表的《华威先生》由于塑造了一个抗日救亡工作中的消极人物,小说发表后又被日本侵略者译成日文用来作为诬蔑中国抗日工作的材料,这自然就会引起对这篇小说的不同的评价。发表文章参加这次争论有林焕平、李育中、罗荪、茅盾、林林、高飞、适夷、周行等多人。有些评论者认为,描写救亡工作中的消极人物,等于对这一工作抹黑;有人认为,讽刺华威先生的“忙忙碌碌”,会使读者将真正苦干的救亡工作者也错认作华威先生。茅盾在《八月的感想》一文里专门以一节来论《华威先生》。他说,由于有些读者误将某些抗日积极分子也讥为华威先生,有的评论者就认为揭露消极现象是“害多而益少”,还是不写为妥。这实际上是倒掉盆里的污水连盆里的孩子也一齐倒掉。如果是这样,“我以为这倒是抗战文艺的一种损失”。对于《华威先生》被日本侵略者所利用,看法也不同。林林在《谈〈华威先生〉到日本》[(47)]一文里,一方面肯定“天翼先生把这种人型刻画出来,是很有慧眼的创造”,一面对小说“资敌作反宣传的资料”又表示担忧,认为这是“减自己的威风,展他人的志气”,因而主张“颂扬光明方面,比之暴露黑暗方面,是来得占主要的地位的”。张天翼发表《关于〈华威先生〉赴日——作者的意见》[(48)]进行辩论,他将华威比作肌体上的某种小疮,“这种病痛之所以能指出,这就是说明我们民族之健康,说明了我们的进步,惟其一天天健康,一天天进步,‘华威先生’这种人物才被我们指得出,拿来‘示众’。”“我认为我们的自我批判,被敌人听见了也不要紧。如要我们自身更健康,故不讳自身上的疾病。”这次论争不在对作品本身的评价,主要在于对作品发表以后的社会效果的不同的看法。
“七月派”作家路翎的小说在读者中有较大影响,但也引起较多的争论。胡风在为路翎的中篇《饥饿的郭素娥》写的“序言”里指出,路翎的小说能“透过社会结构的表皮去发掘人物性格的根苗”。邵荃麟则称赞这部小说“在中国的新现实主义文学中已经放射出一道鲜明的光彩”,指出作品表现了“一种人类灵魂里的呼声,这种呼声似乎是深沉而微弱的,然而却叫出了多世纪来在旧传统磨难下的中国人的痛苦、苦闷与原始的反抗,而且也暗示了新的觉醒的最初过程。”(《〈饥饿的郭素娥〉》)长篇小说《财主的儿女们》是路翎的力作。胡风在为该书写的序言里认为,“时间将会证明,《财主的儿女们》的出版是中国新文学史上一个重大的事件”。鲁芋在《蒋纯祖的胜利》一文里则赞扬路翎的小说是“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感情和意志的百科全书”。但对于路翎的小说也出现不同的评价。胡绳的《评路翎的短篇小说》全面考察了路翎的作品,是这方面的代表性论文。他批评路翎描写工人的小说,认为作者虽然抱着同情来写工人,但写的只是工人的外形而没能写出工人的心,“结果就只能把所了解的知识分子的一套拿出去垫空子了”。路翎曾表白他在创作中寻求的是人民的原始强力和个性的解放。针对这种说法,胡绳批评道:“他们不了解人民的力量存在于人民大众从被压迫生活中的觉醒与可能觉醒中,却反而想去从人民中找什么‘原始的强力’了;他们不了解人民的力量存在于觉醒的人民的集体斗争中,却片面地着重了‘个性解放’的问题。”这次论争主要反映了不同批评者文艺思想的分歧。
谷柳的小说《虾球传》的讨论发生在四十年代末。1948年这部长篇在香港《华商报》上连载。作品描写一个游泳少年富于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由于具有曲折生动的故事情节,色调浓郁的地方景物描写,以及方言的适当使用,小说震动港粤。正如茅盾所说,“一九四八年,在华南最受读者欢迎的小说,恐怕第一要数《虾球传》的第一二部了。”(《关于〈虾球传〉》)1949年春在香港出版的《大众文艺丛刊》《文艺生活》《文汇报》等报刊上,展开了关于《虾球传》的讨论,主要问题有:主人公虾球这个人物的真实性问题,作者对虾球身上的弱点的认识与批判问题,情节发展的偶然性因素问题,描写革命斗争生活的生动性准确性问题,等等,围绕这些问题,冯乃超、周钢鸣、适夷、于逢、林语今等在香港的作家都纷纷发表自己的意见。这次争论较多集中于作品本体的思想艺术评价。
无论是对描写重大题材的作品的热情肯定,还是对小说作品作不同评价的争鸣,本时期的小说批评,都较侧重于作品思想性的探讨,而对作品的艺术性则关注不够。然而作家们发表的许多总结自己艺术经验,谈论自己创作体会的文章,则弥补了这一不足,同时也成为本时期小说批评的新的景观。茅盾的《〈子夜〉是怎样写成的》《我怎样写〈春蚕〉》,巴金的《关于〈家〉十版改订本代序》《关于两个“三部曲”》《以及许多作品的序言,老舍的《三年写作自述》《习作二十年》《我怎样写〈骆驼祥子〉》以及收入《老牛破车》一书的系列文章,叶圣陶的《杂谈我的写作》,沈从文的《我的写作与水的关系》等等,都是产生广泛影响的文章。当然,以前有些作家也曾零星地写过这方面的文章,但本时期无论人数或篇数都是比较多的。在这些文章里,作家们结合自己的小说创作实践,或介绍作品背景,或介绍人物原型,或谈创作动机,或谈构思过程,或总结艺术探索的体会和经验。这不是从批评家或读者的角度的小说批评,而是来自小说作者本身的小说批评。这种文章读来亲切具体,能够给人切实有益的启发,这种文章又为小说批评拓展了新的领域。
二、周扬的小说批评
周扬是一位革命文艺理论家。他积极宣传马列主义文艺理论,认真解释毛泽东文艺思想和党的文艺政策,依照党的文艺方针指导文学艺术工作,因而从四十年代起他就是中国的马列主义文艺理论权威,又是革命文艺运动的实际领导者。在他众多带指导性的文艺论文中,有些是涉及对某些小说作品的评论的,虽然数量不很多,而且主要局限在以解放区小说为评论对象,但却显示出鲜明的特点,并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首先,周扬的小说批评具有非常浓重的政治色彩。由于他在党内的地位和身份,由于对文艺问题发表意见就是他作为领导者的一个工作内容,他在文艺领域里很少作纯学术的研究,他的文艺批评或小说批评总是强烈地表现出为政治服务的色彩,总是鲜明地表现出倡导什么反对什么的指导性倾向。事实上周扬本人就将文艺批评看作领导文艺工作的有效手段。他说:“必须经常指出,在文艺上什么是我们所要提倡的,什么是我们所要反对的。批评必然是毛泽东文艺思想之具体应用,必须集中地表现广大工农群众及其干部的意见,必须经过批评来推动文艺工作者相互间的自我批评,必须通过批评来提高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批评是实现对文艺工作的思想领导的重要方法。”(《新的人民的文艺》)文中的内容和连续使用“必须……”的句式,都充分显示出他作为指导者的地位与口气,而他对文艺批评任务的阐释则完全是政治化的。
强烈的为政治服务的意识,使周扬的小说批评特别重视作品的教育作用。思想教育能提高读者的阶级觉悟和认识水平,是直接为政治服务的重要手段,因而周扬在文艺的认识、教育、审美、娱乐各种功能中特别强调教育功能,将能否对读者起思想教育的作用作为衡量作品价值的重要准绳。对于解放区的作品他是从这一角度给予高度评价的。他说:“这是真正新的人民的文艺。文艺与广大群众的关系也根本改变了。文艺已成为教育群众、教育干部的有效工具之一”。又说:“解放区的文艺,由于反映了工农兵群众的斗争,又采取了群众熟悉的形式,对群众和干部产生了最大的动员作用与教育作用。”(《新的人民的文艺》)《李有才板话》里描写了和农民打成一片的好干部老杨同志,也描写了脱离群众的章工作员。周扬说:“两个人物的对照的描写充满了现实的教育的意义”(《论赵树理的创作》)。即使对国统区的作品,他也十分重视其教育功能。他在《新的人民的文艺》一文里说,茅盾的小说《腐蚀》以及“国统区许多优秀的有思想的作品,都在解放区获得了广大的读者,对他们起了教育的作用。”在评论孔厥的小说《苦人儿》时,周扬也是从教育功能的角度分析其存在的缺点的。他指出,孔厥作品中描写的这个悲怆的故事,由于将男主人公偶然的残废的生理原因作为悲剧的根源,而未能深刻地揭示婚姻制度不合理的社会原因,所以孔厥写的只是一个生理的悲剧。“但也正因为这,削弱了这作品之思想的教育的意义”。(《略谈孔厥的小说》)淡化文艺其他功能,强调和突出其思想教育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就将文艺当作为政治服务的工具,这样的小说批评,其政治色彩无疑是异常浓厚的。
其次,周扬的小说批评十分重视作品思想内容的分析。由于周扬强调文艺的教育作用,他就特别重视挖掘作品的思想内涵,以便从中提取可供思想教育的材料。同时,根据政治标准第一的原则,对于思想性强的作品则给予较高的评价。
周扬注意审视作品的题材选择,特别重视反映重大题材的小说作品。他在《新的人民的文艺》一文里,以自豪的口吻赞扬解放区的文艺作品绝大多数是描写重大题材的;抗日战争、人民解放战争、农村土地斗争和其他各种反封建斗争以及工业农业生产等重大题材是文艺作品描写的主要对象。在他开列的被他认定为解放区优秀的文艺作品中,小说体裁的就有:《吕梁英雄传》《李家庄的变迁》《新儿女英雄传》《地雷阵》《李有才板话》《太阳照在桑乾河上》《暴风骤雨》《小二黑结婚》《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我的两家房东》《高乾大》《种谷记》《原动力》等,周扬认为从这些描写重大题材的作品中“可以看出解放区文艺面貌轮廓,也可以看出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大略轮廓与各个侧面。”在评论赵树理的小说时,周扬认为赵树理的贡献在于中国“农村中的伟大的变革过程,要求在艺术作品上取得反映。赵树理同志的作品就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这个要求”。(《论赵树理的创作》)在评论孔厥的小说时,周扬热情赞扬作家描写题材的转变。孔厥初期小说《过来人》《追求者》都是写知识分子的,经过到边区农村工作,他就写出了《郝二虎》《苦人儿》《父子俩》等农民题材的作品。周扬说:“由写知识分子(而且是偏于消极方面的)到写新的,进步的农民,旁观的调子让位给了热情的描写,这在作者创作道路上是一个重要的进展。”(《略谈孔厥的小说》)
周扬注意审视作品的主题表现,充分肯定描写重大主题的小说作品。他说:“知识分子离开人民的斗争,沉溺于自己小圈子内的生活及个人情感的世界,这样的主题就显得渺小与没有意义了,在解放区的文艺作品中,就没有了地位。”(《新的人民的文艺》)他又说:“主题是确定的,文艺工作者应当而且只能写与工农兵群众的斗争有关的主题。……文艺工作者必须真实地反映群众的要求和情绪,而且站在一定的政策思想水平上回答群众从实际斗争中提出的问题。”(《谈文艺问题》)在他看来,解放区的文艺作品已经很好地体现了上述的要求,因此他在《新的人民的文艺》中以“新的主题”来概括全部解放区的作品。在评论赵树理的小说时,他认为《小二黑结婚》的主题不是讴歌自由恋爱的胜利,而是讴歌农民对封建恶霸势力的胜利,讴歌新社会的胜利,表现的是重大主题。他赞扬《李有才板话》的主题处理:“作者在这里正确地处理了农村斗争的主题,写出了斗争的曲折与复杂性,写出了农村中的各种人物……光明的,新生的东西始终是他作品中的支配一切的因素。”而对《李家庄的变迁》的主题处理则感到不满足。他说:作品以十多年山西政治为背景,涉及山西许多重要事件,“可以看出作者在这里有很大的企图。和作者的企图相比,这篇作品就还没有达到它所应有的完成的程度”。(《论赵树理的创作》)
周扬注意审视作品的人物描写,积极倡导小说作品中描写英雄模范人物。他说:“我们是处在这样一个充满了斗争和行动的时代,我们亲眼看见了人民中的各种英雄模范人物,他们是如此平凡,而又如此伟大,他们正凭着自己的血和汗英勇地勤恳地创造着历史的奇迹。对于他们,这些世界历史的真正主人,我们除了以全副的热情去歌颂去表扬之外,还能有什么别的表示呢?”(《新的人民的文艺》)他赞扬孔厥小说“写出了农村中的新的人物,新的事情”。他评论赵树理小说时指出:“创造积极人物的典型,是我们文学创作上的一个伟大而困难的任务。……(赵树理)无论如何写出了新的人物的真实面貌,那些‘小字号的人物’们可以看作新的农民的集体的形象。”在《新的人民的文艺》一文里,他用“新的人物”来概括解放区文艺作品主人公的基本特色。
周扬通过对小说题材、主题、人物的审察,分析作品的思想内容;同时也倡导作家描写重大题材重大主题和英雄人物,以自己的创作为革命的政治服务。
再次,周扬的小说批评对于小说语言的群众化通俗化给予很高的评价。由于周扬重视文艺的教育作用,他就较多地考虑文艺作品如何顺利地被工农大众接受的问题,对于文化程度不高的读者,语言的群众化通俗化是十分重要的。解放区的小说作者在这方面作了很有意义的探索,因而受到周扬热情的表扬。他说:“解放区文艺作品的重要特色之一是它的语言做到了相当大众化的程度。”他认为赵树理的成功除了作品的思想价值外,还“得力于他的语言,他的语言是真正从群众中来的,而又是经过加工、洗炼的,那么平易自然,没有一点矫揉造作的痕迹。”(《新的人民的文艺》)他也赞扬孔厥小说的语言,“口语的大胆采用更形成了这些作品的一个耀目的特色”,“这些语言是新鲜活泼的,没有空洞概念,也没有故意修辞,从它们,活生生地表达出了农民的真实心理,反映出了新旧思想的对立。”(《略谈孔厥的小说》)
在评论小说语言时,周扬强调不但人物对话要口语化,而且作者的叙述语言也应该群众化。他曾在一篇文章里批评说:“我们的文艺作家一般地都只在描写人物的对话中,采用了民间口语,……但却没有学会在作叙述描写时也运用群众语言”(《〈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序言》)因此他对在这方面做出成绩的作家就特别给予褒奖。在《论赵树理的创作》一文里,他这样评论这位优秀小说家的语言:“他在他的作品中那么熟练地丰富地运用了群众的语言,显示了他的口语化的卓越的能力;不但在人物对话上,而且在一般叙述的描写上,都是口语化的。”在引用了《小二黑结婚》和《李有才板话》的若干语言片断后,周扬说,“从上面的引用,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在作任何叙述描写时都是用群众的语言,而这些语言是充满了何等的魅力呵!这种魅力是只有从生活中,从群众中才能取得的。”
周扬的小说批评,重视小说的思想性和教育功能,无疑是正确的。但相对而言,他对小说的艺术性和审美功能关注不够。虽然他注意到小说的语言,抓住了文学作为语言的艺术的主要要素。但小说语言却远不是一个群众化可以包括的;同样,小说的艺术性也远不是仅语言一项可以包括的。由于周扬的小说批评产生于艰苦的战争年代,这一现象是可以理解的,遗憾的是它作为一种批评模式,对以后的小说批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李健吾的小说批评
李健吾是活跃在三、四十年代国统区的一位文学批评家,他以“刘西渭”的署名发表了一些颇有影响的文章,并先后结集出版了《咀华集》(1936年)和《咀华二集》(1941年)。其中大量的篇幅是对现代小说的评论。
对于文学批评,李健吾有自己的看法,他反对批评家扮演指导者和审判者的角色,认为他的任务主要在于对作品进行鉴赏和分析。他说,“一个批评者与其说是指导的,裁判的,倒不如说是鉴赏的“(《〈爱情的三部曲〉》);又说,“一个批评家,与其说是法庭的审判,不如说是一个科学的分析者”(《〈边城〉》)。另一方面,他的文学批评,他对作品的鉴赏和分析,不同于当时较多批评家通行的社会学批评,他不对作品进行全面的思想艺术分析,只是写下阅读作品的一点感觉,一点艺术鉴赏的感悟,他更注重本人对作品的直观感性的印象。他信奉的是印象主义批评大师勒麦特和法朗士的言论。前者说,批评“所能做的也不外乎把我们对于作品在某一时间的印象凝定下来”;后者说,“好批评家是这样一个人:叙述他的灵魂在杰作之间的奇遇。”李健吾采用的是以印象主义为基本特征的文学批评。在社会学批评占主流地位的三、四十年代,象李健吾这种淡化政治色彩、强调审美功能的文学批评,可以说是别具一格的。
李健吾的小说批评具有以下的特点:
第一,李健吾是站在进步立场从事小说批评的。李健吾的小说评论文章很少涉及政治,也不用革命的词句,但是他选择作为评论的对象都是现代文学中的进步作品,他对这些作品都持热情肯定的态度,纵有批评,也是为了促使其更健康地成长。在他的评论视野里,既有反对封建压迫和军阀统治的巴金、沈从文、叶紫、路翎、罗淑、萧乾、芦焚的小说,也有反映民族战争题材的《八月的乡村》(萧军)、《遥远的爱》(郁茹)。因此,可以说,本时期高扬在许多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中的“抗战”和“民主”的主旋律,同样也回荡在李健吾小说批评的字里行间,他的小说批评同人民大众的时代要求其方向是一致的。他的立场是进步的。
第二,李健吾的小说批评采用的是一种轻松自如的随笔文体。他的文章没有高头讲章的架势,也没有判决教训的面孔,甚至没有清晰的条理和严密的结构,他以亲切的口吻娓娓而谈,以谈天的方式旁征博引,让读者宛如在导游的讲解中无拘束地欣赏优美的景色。例如他评论叶紫的小说,一开始先议论批评家的任务,接着介绍叶紫贫病的飘零生涯,在评论叶紫作品时就纵意而谈,从叶紫作品中湖南的山光水色联系到沈从文;从大革命题材联系到茅盾的《蚀》,从农民题材联系到鲁迅的《阿Q正传》和茅盾的农村三部曲;在谈到“五四”以来以“力”为表征的反抗作品时,联系到鲁迅、茅盾、郁达夫、闻一多、废名、张资平、庐隐、萧红、吴组缃等的作品,李健吾就在这种广泛联系中表达了他对叶紫小说的印象。又如《三个中篇》一文评论了三部中篇小说,作者从女作家郁茹的《遥远的爱》联想到乔治桑的主观抒情的心性;从穗青的《脱缰的马》联想到福楼拜对《包法利夫人》的苦修的期待;从《饥饿的郭素娥》联想到路翎是左拉的“不及门的弟子”,结合三部作品的评析,又对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作广泛的议论。李健吾这种随意而谈的随笔文体,让读者在亲切自如的氛围中聆听他对文学作品的意见。
第三,李健吾的小说批评十分注重对作品作整体的艺术把握。由于他的批评侧重于对作品的印象和感觉,他就不将力量用在细枝末节的品赏,而是把目光集中在整个作品,注重总体印象,从而向读者表述他对小说作品的整体审美感受。他认为路翎的小说,象“长江大河,旋着白浪,可也带着泥沙,好象那位自然主义大师左拉,吸人的是他的热情,不是他的理论”(《三个中篇》)叶紫的小说则给他另一种印象:“叶紫的小说始终仿佛一棵烧焦了的幼树,没有《生死场》行文的情致,没有《一千八百担》语言的生动,不见任何丰盈的姿态,然而挺立在大野,露出棱棱的骨干,那给人茁壮的感觉,那不幸而遭电殛的暮春的幼树。它有所象征。这里什么也不见,只见苦难,和苦难之余的向上的意志。”(《叶紫的小说》)对于沈从文的如诗如画的《边城》,李健吾这样评论:“细致,然而绝不琐碎;真实,然而绝不教训;风韵,然而绝不弄姿;美丽,然而绝不做作。这不是一个大东西,然而这是一颗千古不磨的珠玉。”(《〈边城〉》)带着泥沙的滚滚江河,暮春的烧焦的幼树,千古不磨的珠玉,李健吾用这些精心选择的意象来表达他对这些小说的整体审美感受。
第四,李健吾的小说批评喜欢运用比较的手法来显示评论对象的特色。由于他具有丰富的中外文学知识,对各个作家的风格和特色有深切的了解,他就可以将评论对象同其他作家进行比较,无论中国作家外国作家,无论风格相异风格相似,都可运用自如地比较,在比较中更充分更鲜明地显示评论对象的特色。例如在评论巴金《爱情的三部曲》的文章里,李健吾在阐述不同内容时不断进行了几次比较。他先将巴金同废名比较:“废名先生单自成为一个境界,犹如巴金先生单自成为一种力量。人世应当有废名先生那样的隐士,更应当有巴金先生那样的战士。一个把哲理给我们,一个把青春给我们。”后来又将他同乔治桑比较:“乔治桑仿佛一个富翁,把她的幸福施舍给她的同类;巴金先生仿佛一个穷人,要为同类争来等量的幸福。”在分析巴金的小说时又将他同茅盾比较:“读茅盾先生的文章,我们象上山,沿路有的是瑰丽的奇景,然而脚底下也有的是绊脚的石子;读巴金先生的文章,我们象泛舟,顺流而下,有时连你收帆停驶的工夫也不给。”接着谈两人的共同弱点:“我们今日的两大小说家,都不长于描写。茅盾先生拙于措辞,因为他沿路随手捡拾;巴金先生却是热情不容他描写,因为描写的工作比较冷静,而热情不容巴金先生冷静。”这种反复的比较,将巴金和他的小说的特点从不同的侧面清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又如李健吾在评芦焚时,就将他和萧乾放在一起比较:“但是这两位新人,在文笔上所给的感觉并不一样。萧乾先生用力在描绘,无形中溶进一颗沉郁的心。他的句子往往是长的。他的描写大都是自己的。芦焚先生的描写是他观察和想象的结果,然而往往搀着书本子气,他的心不是沉郁的,而是谴责的。”(《〈里门拾记〉》)此外,李健吾文章里的比较还有许多,如废名和沈从文,沈从文和叶紫,叶紫和茅盾,《八月的乡村》和《毁灭》(法捷耶夫)等,处处都闪烁着相互碰撞中迸发出的艺术的火花。
第五,李健吾的小说批评的文字非常优美。从上面我们的一些引文已经大体可以看到李健吾文字的一些特点。他一般不作抽象的议论,而是将他的意思用准确的比喻或生动的形象表达出来;他曾从事过文学创作,有很深厚的文字功底,同时他又把文学批评也看作艺术创造,因此他的批评文字绝不艰涩,流淌在他的文章里的是优美、抒情、充满诗意的文字。他的批评文章本身就是美文。在评论《八月的乡村》时,他这样描述少年时代的萧军:“一个没有家或者没有爱的孩子,寂寞原本是他的灵魂,日月会是他的伴侣,自然会是他的营养。而他,用不着社会的法习,变得和山石一样矫健,和溪涧一样温柔,人性的发扬是他最高的道德。”(《〈八月的乡村〉》)他这样概括叶紫的小说:“他所能够给的是黑白分明的铅画,不是光影匀净的油画”。(《叶紫的小说》)他这样评论林徽因的《九十九度中》:“作者把一天的形形色色披露在我们的眼前,没有组织,却有组织;没有条理,却有条理;没有故事,却有故事,而且那样多的故事;没有技巧,却处处透露匠心。”(《〈九十九度中〉》)他这样比较沈从文的小说:“《边城》是一首诗,是二佬唱给翠翠的情歌。《八骏图》是一首绝句,犹如那女教员留在沙滩上神秘的绝句。”(《〈边城〉》)在评论萧乾《篱下集》的文章里,李健吾插进了一段文字叙写他读《边城》的感受:“读者,当我们放下《边城》那样一部证明人性皆善的杰作,我们的情思是否坠着沉重的忧郁?我们不由问自己,何以和朝阳一样明亮温煦的书,偏偏染着夕阳西下的感觉?为什么一切良善的歌颂,最后总理在一阵凄凉的幽噎?为什么一颗赤子之心,渐渐褪向一个孤独者淡淡的灰影?难道天真和忧郁竟然不可分开吗?”(《〈篱下集〉》)这种象抒情诗一样美的文字洋溢着巨大的艺术魅力。
本时期的文学批评领域,社会学批评占居主流地位。在多数批评家都在强调文学的教育功能和思想性的时候,在某些批评家以指导者的严肃姿态出现的时候,李健吾的印象式的小说批评,以平等轻松的态度,以优美亲切的语言,引导读者去理解美欣赏美,这是别树一帜的。这样的文学批评对这时期相对忽视作品艺术性的批评倾向,也是一种有益的补充。因此它是很有价值的。但是,在以后的几十年中,李健吾式的文学批评一直被社会学批评的潮流所淹盖,直到八十年代,它的价值才重新被人们所发现和珍惜。
(续完)
注释:
(1)陈独秀《敬告青年》。
(2)周作人《人的文学》。
(3)刘半农《中国之下等小说》。
(4)李大钊《什么是新文学》。
(5)茅盾《现在文学家的责任是什么?》。
(6)《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
(7)《我怎行做起小说来》。
(8)潘垂统《对于超人、命命鸟、低能儿的批评》,《小说月报》第12卷第11期。
(9)化鲁《隔膜》,《时事新报·文学旬刊》第38期。
(10)(18)陈炜谟《读〈小说汇刊〉》,《小说月报》第13卷第12号。
(11)鹃魂《读冰心女士的〈去国〉的感言》,载1919年10月4日《晨报》。
(12)赤子《读冰心女士作品的感想》。
(13)直民《读冰心的作品志感》。
(14)剑三《论冰心的〈超人〉与〈疯人笔记〉》。
(15)敦易《对于〈寂寞〉的观察》。
(16)成仿吾《评冰心女士的〈超人〉》。
(17)《对于〈超人〉〈命命鸟〉〈低能儿〉的批评》。
(19)成仿吾《〈命命鸟〉的批评》,《创造季刊》第2卷第1期。
(20)《批评落华生的三篇创作》。
(21)《〈商人妇〉与〈缀网劳蛛〉的批评》,《小说月报》第13卷第9期。
(22)周作人《沉沦》。
(23)《春季创作坛漫评》。
(24)(28)《评四五六月的创作》。
(25)《读〈小说月报〉第13卷第6号》。
(26)(29)《对〈沉沦〉和〈阿Q正传〉的讨论》。
(27)《〈创造〉给我的印象》。
(30)《小说月报》第13卷第2号。
(31)《评〈小说汇刊〉创作集一》。
(32)《读〈呐喊〉》。
(33)《〈创造〉给我的印象》。
(34)《真善美》月刊第4卷第5号(1929年)。
(35)茅盾《小说研究ABC》。
(36)Bliss Perry《小说的研究》第80页,汤澄波译,商务印书馆1925年初版。
(37)李初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
(38)《流沙》创刊号《前言》。
(39)冯乃超《艺术与社会生活》。
(40)(42)克兴《小资产阶级文艺理论之谬误》。
(41)钱杏村《死去了的阿Q时代》。
(43)《关于新的小说的诞生》,《北斗》第2卷第2期(1932年)。
(44)钱杏村《关于〈评短裤党〉》。
(45)苏读余《冲击云围的月亮》,《现代文学》创刊号。
(46)1948年6月2日《东北日报》。
(47)1939年2月22日《救亡日报》。
(48)1939年3月15日《救亡日报》。
标签:李健吾论文; 小说论文; 文学论文; 现代小说论文; 抗日战争论文; 李有才板话论文; 小二黑结婚论文; 李家庄的变迁论文; 周扬论文; 艺术批评论文; 虾球传论文; 赵树理论文; 茅盾论文; 文艺论文; 华威先生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