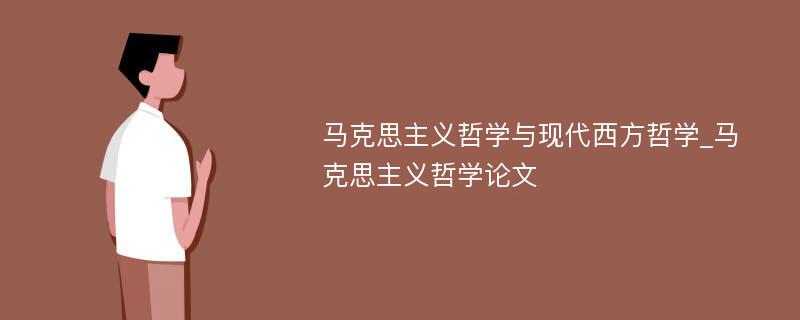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西方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代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关系之我见
我在30年代读过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1942年至1948年上大学期间学得最多的是西方哲学史,毕业论文是关于康德的。1948年至1950年作研究生期间,我仍研究西方哲学史,导师是康德专家郑昕,但实际只上了半年。1949年初北平解放后,我就开始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学习和教学工作,后来就专门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来是西方哲学的组成部分,我在大学期间和后来的工作中也经常接触现代西方哲学,因此对现代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也形成了一些想法。下面就此谈三点看法。
一、西方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直接来源。过去一直讲辩证唯物主义的直接来源是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这话基本上不错,但不很确切。实际上,英国的经验主义(包括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和法国唯物主义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都是很大的。马克思、恩格斯论述英法的唯物主义及其他哲学观点的篇章决不少于论述费尔巴哈的篇章。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曾追溯了英国和法国的唯物主义的历史,他认为法国唯物主义有两个派别,一个起源于笛卡尔,一个起源于洛克,即一派是本土的,一派是外来的。笛卡尔派是机械唯物主义,是真正的法国自然科学的产物,而洛克派则直接导向社会主义。马克思进一步认为英国的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是培根,并从培根追溯到古希腊唯物主义者阿那克萨哥拉和德谟克利特,指出他们对培根的影响。马克思虽然批评霍布斯把培根的唯物主义片面化了,变得敌视人了,但他从中也获得了重要的启发,指出“物体、存在、实体是同一种实在的观念。决不可以把思维同那思维着的物质分开。物质是一切变化的主体。”(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60-164页。)这里的“主体”当然不是指人而是指载体。1847年以后,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92年英文版导言》中大段摘录了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关于英国唯物主义的论述,并作了进一步发挥,指出英国的不可知论是羞羞答答的唯物主义;驳斥不可知论和论证外部世界的客观存在的最有力的根据就是实践。应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两千多年西方哲学的直接继承者,而不仅仅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它诚然是19世纪中叶社会实践、工人革命运动和科学发展的产物,但它不是在这些社会条件的基础上凭空产生的,它的诞生离不了西方哲学丰富的思想资料,它是西方哲学的组成部分,是西方哲学的继续与发展。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之后与其余西方哲学分道扬镳。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是一种西方哲学,但它在诞生和发展过程中开辟了一条与其余的西方哲学迥然不同的道路,可谓泾渭分明,平行发展,呈现出若干本质上的不同之处。具体有以下区别。
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和发展离不开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离不开社会主义运动,它是在西欧工人社会主义运动中诞生的,诞生之后或者是作为思想斗争的武器,或者是作为分析与解决革命与建设实践问题的方法起作用。这就是它的实践性、战斗性、鲜明的阶级性的特点。因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很少写作正面系统阐发其哲学思想的论著,他们的哲学思想多半是在论战性论著或在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论著中阐发的。他们的许多哲学思想甚至只是逻辑地或潜在地蕴涵在他们的政治、经济论著中。马克思曾经想写一本正面系统阐述唯物主义辩证法的书,但终于没有写成。《自然辩证法》是一本正面阐发恩格斯的哲学思想的书,但只是一些笔记、手稿片段和提纲,完整的论文只有少数几篇。列宁也是如此。正面系统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任务是由苏联专业哲学家完成的。而现代西方哲学是学院哲学,是哲学家的哲学,是高高在上、远离社会实践的哲学。当然有的哲学家也很关注社会实践、重视社会发展,有的哲学也对社会实践产生了实际作用,但其主流仍然是忽视甚至否定实践性、战斗性,尤其是不公开宣称其阶级性,甚至标榜超阶级性。
第二,马克思主义哲学总是力求使自己成为科学,它当然有思辨性、论证性,但也强调哲学的实践基础、实证性、客观性。它主张充分发扬人的主观能动性,但强调必须与科学的思想指导相结合。它十分关注有关人和社会的问题,但决不忽视自然界和整个宇宙的问题,因为它深知自然界是人和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客观基础。这就是它的科学性。当然,多数现代西方哲学家都说自己的观点是真理,不说自己的观点是主观臆说,并在实际上也承认哲学的科学性,但一般说来他们是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强调思辨,不讲事实根据,言词晦涩,论述艰深。人本主义思潮强调人文价值,什么是人文价值呢?言人人殊,没有客观标准。科学主义思潮该是强调科学了,但科学主义实际上否定科学,因为他们否定经验的客观性。人本主义也好,科学主义也好,它们都否定世界观,当然也就否定了唯物主义世界观。人本主义口头上不否定本体论(世界观),但它的“本体”只是人的存在或离开了人的存在,不是客观的物质的存在。这样,好像对立的现代西方两大哲学思潮就在否定唯物主义世界观这一点上合流了。我认为,科学始终是与唯物主义一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始终坚持唯物主义。而现代西方哲学的主流是唯心主义,当然也有不少唯物主义者,特别是科学哲学、系统论、信息论的不少研究者的观点是与辩证唯物主义一致的。
第三,与以上两点相一致,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群众性、人民性,易于通俗化;而现代西方哲学完全是精英哲学,远离人民大众,很难通俗化。自古以来还不曾有一种哲学拥有过像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拥有的那样多的信奉者,这当然与共产党在政治上的胜利和党的领导人的提倡有关,但它的特点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它的实践性要求它必须普及,它的科学性使它易于普及。相反,现代西方哲学无普及之意,也难以普及。总之,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虽然都源于西方哲学,但确实走上了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
三、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在20世纪各有其长处和短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长处是坚持了实践性、科学性和群众性,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短处是忽视部门哲学的研究和发展,因而未能使自己建构成充分现代化的当代形态。经过苏联的革命和建设、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和建设,马克思主义哲学始终坚持了它的基本特色和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历史观、认识论,也建设了自己,形成了具有一定逻辑性的科学体系,但它的部门哲学开展得很差,除了自然观、历史观、认识论、美学、军事哲学、人生哲学外,其他丰富多彩的具体领域诸如人学、经济哲学、政治哲学、文化哲学、语言哲学、生物哲学等等,甚至对已有所论及的主体性哲学、实践哲学等都缺乏专门研究,这就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显得单调贫乏,空洞抽象。由于部门哲学研究的薄弱,一个充分现代化的、更加完整和严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体系亦即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形态,难以形成。
现代西方哲学的长处和短处正好相反。它的最大成就是开展了大量部门哲学的研究,哲学领域丰富多彩,百花齐放,除了传统的部门哲学以外,人本哲学、人学、哲学人类学、存在哲学、生活哲学、语言哲学、解释学、逻辑哲学、价值哲学、心智哲学、科技哲学……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但是,他们有一个很大的失误,就是否定世界观,特别是否定唯物主义世界观。科学主义“拒斥形而上学”,反对“本质主义”,怀疑世界的客观存在,陷入相对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泥潭,这就否定了科学,否定了人类的实践活动的可靠性,从而否定了自己。人本主义不反对本体论,但本体就是人的本体、人的存在或精神存在、人的主体性,这种本体也是虚无飘渺、捉摸不定的,最后是脱离人的客观存在的。现代西方哲学各派都认为自己是唯一正确的哲学,都排斥其他哲学,特别是都排斥世界观,尤其是唯物主义世界观,实际每一派别只是一个部门哲学,都离不开世界观,都有其世界观。
在我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可以互补,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观点指导的前提下,现代西方哲学各派都可以改造成为各种科学的部门哲学,从而形成一个丰富多彩的哲学家族。其实,这并不仅仅是一种可能、一种愿望,它已经部分地成为现实。只要回顾一下这20年来中国哲学的发展历程,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互补已经颇为明显。
作为改革开放前奏的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完全是由国内原因引发的,与现代西方哲学没有直接联系,但后来的哲学讨论,则绝大多数与现代西方哲学有关。紧接着真理标准讨论的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讨论诚然有国内的原因,但其受国际人道主义思潮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人本主义)的影响也是非常明显的,法国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萨特一度成为哲学研究的热点。同时出现的主体性哲学、实践哲学或主体性实践哲学则完全是现代西方哲学的中国版。以80年代的电视专题片《河殇》为代表的“彻底反传统”、“全面西化”的思潮曾经盛极一时,其中包括了现代西方哲学的影响。“西化”的思潮后来降温了,但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的影响从未停止过,人学、价值哲学、人权理论、文化哲学、生存哲学、生活哲学、解释学、分析哲学、语言哲学、科技哲学等等的研究和讨论都是由现代西方哲学所引发的。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在实现中国社会全面现代化的过程中,西方的影响和西方哲学的影响从整体上说是积极的、必要的,也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在于如何对待这种影响。像改革开放以前那样把现代西方哲学当作腐朽的意识形态完全加以拒绝,如果要谈,那就是批判,现在还持这种态度的人,我想已经很少了。另一种极端的人,即主张毫无分析地全盘接受现代西方哲学的人也不多。现在有一种不好的倾向,是把某一种西方哲学加以马克思主义化或中国化并以之取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或者确切点说,取代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例如或以实践哲学、或以人学、或以系统哲学,来取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即使这些哲学是科学的,也不能取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因为它们最多是各属一种科学的部门哲学。我认为部门哲学与世界观(关于整个世界的哲学)是不能相互取代的,正如一般与个别、整体与局部不能互相取代一样。因此,如果能把现代西方哲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观点指导下加以科学化,形成若干部门哲学,它们就可以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互补,正如一般与个别互补、整体与局部互补一样。有若干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者已经有意无意地这样做了,对此我是赞同的。
除了西方哲学引发的各种部门哲学外,我国哲学界不少学者还从实际的理论领域或科学分类引发出多种部门哲学,现在一般通称为应用哲学。他们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一般哲学,并以之为指导,建构各种部门哲学如经济哲学、政治哲学、文化哲学、教育哲学、管理哲学、领导哲学等等,我认为这些是20年来我国哲学研究的重大成就。部门哲学是一般哲学与各种基础科学、社会实践、客观世界之间的桥梁。通过部门哲学,基础科学与社会实践可以得到一般指导,有利于提高基础科学的理论深度和社会实践的成功率;一般哲学则可汲取基础科学、社会实践、客观世界的丰富营养,有利于使自身更加丰富、更加完善、更加贴近现实。一般哲学与部门哲学(包括从西方哲学引发的部门哲学)互相补充,互相推动,为21世纪我国哲学的发展展现了一幅无限辉煌、无限广阔的美好前景。
必须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谈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现代哲学关系
中国古代哲学长期以“万物一体”、“天人合一”为主导思想,类似西方近代主客二分式的“天人相分”模式不占主导地位。鸦片战争以后,一批先进的思想家认识到,要想富国强兵抵御外侮,不仅要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科学技术,而且要学习与之相联系的西方近代的哲学思想。他们着力介绍西方近代哲学主客二分式(即主—客关系式)和与之相联系的主体性哲学。例如,梁启超就曾以介绍西方近代哲学“初祖”为题,撰文盛赞笛卡尔和康德的主客二分思想和主体性哲学;谭嗣同则强调“我”与“非我”之分,高扬“心”之力亦即主体性;孙中山明确提出精神、物质二元论和“精神胜物质”的主张。从哲学角度看,“五四”运动的民主与科学这两大口号,就是召唤西方近代主—客关系式的主体性哲学:科学就是要发挥人(主体)的主体性以征服自然(客体),民主就是要发挥人的主体性以推翻封建统治,两者都是强调以主体统一客体。可以说,一部中国近代哲学史,就是学习和召唤西方近代主—客关系的思维模式和主体性哲学的历史。
值得注意的是,西方近代哲学史上伴随主体性哲学的发展而日益突显的是“主体性形而上学”。这种形而上学(其最早的根源是柏拉图的“理念”说)关注超感性的、抽象的概念世界并把它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从而把哲学变成远离现实、令人见而生畏的学问,使人生变得苍白无力、枯燥乏味。因此,我们不能亦步亦趋地沿着西方近代主体性哲学及其形而上学的老路走下去。
正当我们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努力学习西方近代哲学之际,西方哲学史已于19世纪中叶发生了重大转折:自黑格尔死后的19世纪中叶起,西方开始了一个反主体性形而上学的新时代,这也就是我们中国学术界习惯称为“西方现代哲学”的时代,它与近代相对峙。这个时代哲学派别林立,异说纷呈,但大体上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反对抽象性,提倡现实性,要求哲学从抽象的概念王国回到现实的人世,要求哲学与具体的人生相结合,把人生变得富有情趣和诗意。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其他诸多现代哲学派别都是从19世纪中叶开始产生的,都是这同一个时代的产儿,都具有上述反形而上学性和抽象性、主张具体性和现实性的特征。可以说,时代决定了它们是天生的盟友。但是两者在这方面所走的道路又是大不相同的,其中最根本的一个不同点就是:马克思主义以外的其他西方现代哲学派别仍然停留在用不同的方式说明世界这一旧的窠臼之中,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把自己的任务规定为以革命的方法改造世界。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正处在一个革命变革的时代,因此,“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哲学既需要继续学习西方近代的主体性哲学,又需要避免这种哲学所带来的形而上学抽象性;既需要学习西方现代哲学的具体性和现实性,又不能采取西方现代哲学那种只停留在说明世界而不注重以革命方法改造世界的旧观点。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哲学的发展终于在各种西方现代哲学派别纷至沓来之际选择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道路。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有主体性原则,又反对主体性哲学的形而上学抽象性因而具有具体性和现实性精神,更进而主张以革命的方法改造世界。我以为,这些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能在西方现代其他各种哲学纷呈于中国当时思想界的局面中独占鳌头的原因。
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它是中国人民的主体性的一次大解放运动,但很快就受到各种“左”的教条主义的干扰。包括哲学在内,我们在各个方面的进展都大大地被推迟了。单就哲学来说,半个世纪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有如下必须正视的问题。
一、只重认识(知),不重情、意。过去讲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只是讲主体如何认识客体,以便掌握客观规律,征服客体,使客体为我所用;人变成了单纯进行认识活动(包括利用、使用等实践活动)的机器,至于人的情感意欲则被视为妨碍客观认识的主观的东西而加以贬抑,甚至连美学也被认为是主体认识客观事物规律之学的认识论。在那个时代里,谁如果写出诸如恋爱哲学、死亡哲学、民胞物与哲学、潜意识哲学之类的著作,那即使不被扣上资产阶级哲学或反动腐朽哲学的帽子,也会被斥为小资产阶级意识或缺乏阶级斗争观念。其实,正如德国现代哲学家布伯(Martin Buber,1878-1965)所说,人所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因人生的态度而具有双重性:一是“为我们所用的世界”,一是“我们与之相遇的世界”。前者是一种把世界万物当作经验、认识和利用对象的态度,后者是一种以仁爱对待人和物的态度。不认识和利用对象,人固然不能生活,但仅仅依靠这种态度来生活的人“不是人”。布伯的哲学及其表述虽有宗教神秘之处,但他的基本思想却启发了我们:一个只重认识和使用、不重情感意欲上的互尊互爱的人,是不能在灵魂深处与他人赤诚相见(“相遇”)的,这样的人是片面的因而也是抽象的人,而不是具体的、现实的人。一种只重认识、使用而不重情感意欲、不重灵魂深处相见相遇的哲学,必然把人生的意义和空间变得异常贫乏、狭窄和枯寂。
二、只重生产,不重生活。马克思主义哲学重实践,这既是它的内在机制,也是它和其他现代哲学流派重现实、反抽象的表现,是两者的一个结合点。但我们过去所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把实践狭隘地理解为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至于日常生活中其他丰富多彩的活动(例如艺术活动、人与人之间的日常交往以及饮食男女之事)则都被视为卑微的、琐屑的活动而加以贬斥。西方现当代许多哲学流派强调:人类的实践活动不仅像近代哲学所注重的那样,是人与自然作斗争的生产活动,而且包括人与人之间相互交往的活动;我们不仅应当认识到,寻找自然界的普遍性、规律性以发展生产,其目的乃是为了生活,而且更应当认识到,生活的内容既包括消耗自然物,还包括各具独特性的个人与个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的相互理解、相互尊重。与此相对照,过去那种只重生产、不重生活的观点显然是片面的。至于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归结为“以阶级斗争为纲”,则更为错误。马克思主义哲学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我们为什么不能吸取西方现当代其他哲学流派关于“生活世界”的观点以扩大实践的内涵,让人们的生活内容更丰富、更美好呢?
三、讲主—客关系而又不讲主体性。过去所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不外是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以及主体能否认识和如何认识客体,并通过认识、实践以达到主体与客体的统一。这套原理基本上属于西方近代哲学的主—客关系式。然而我们都知道,主—客关系式是“主体性哲学”的思维模式,其重要特征是强调主体性。“主体性”是西方近代哲学的根本原则和专门术语,意指主—客关系中主体的特性:除过去教科书所讲的主观能动性之外,还有个人的独特性包括个人独特的才能、禀赋等,以及自由意志、独立思考、不依赖血统或出身等等。主体性与主—客关系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这一点,海德格尔在《黑格尔的经验概念》一文中已讲得很明确。可是过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却限于主—客关系的框架,而又不讲它所包含的本质环节——主体性。我个人那时讲黑格尔这样一个集主体性哲学之大成的哲学家,也不讲主体性。直至80年代初,我们的学术界才开始讨论主体性问题,而我们当时对西方在几百年前已经建立起来的主体性原则和这个专门术语的本义并不清楚,甚至把主体性理解为主观武断和主观唯心主义。改革开放以前,我们讲的是阶级出身决定人的命运,一切服从组织安排,以及驯服工具论等等,没有人的主体性可言。我想,也许这就是当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讲西方近代哲学的主体性精神的根本原因。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按其本质和本义来说,应该是包含了近代哲学的主体性精神的,尽管它产生于19世纪中叶西方近代哲学终结以后。
尤有甚者,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时产生的西方其他许多哲学流派(这里主要指欧洲大陆人文主义思潮中的一些流派),已经超越(不是抛弃)西方古典的主—客模式和主体性哲学,它们强调主客不分或主客的融合一体(这种一体不同于主—客二分式中的主客统一),有点类似王阳明的万物一体、天人合一的思想,亦即他所讲的“天地万物不能离却我的灵明,我的灵明亦不能离却天地万物”,两者一气流通,无有间隔。为了区别起见,我把包括王阳明在内的中国传统哲学所讲的万物一体、天人合一称为“前主—客式的万物一体或天人合一”,而把上述西方现代哲学所讲的超主—客关系式的主客融合称为“后主—客关系式”。西方现当代哲学流派大多主张主客融合优先于主—客关系,认为前者是第一位的,后者是第二位的。例如海德格尔讲“上手的东西”优先于“在手的东西”,实际上就是这个意思。美国哲学家梯利希(P.Tillich)更明确地断言,“自我”与“世界”的融合一体是第一位的,“主—客关系”是第二位的。而过去我们讲哲学,总是把西方现当代哲学流派所主张的主客融合一体的思想当作主观唯心主义大加挞伐。实际上,这种观点的意思主要是说,人所生活于其中的“生活世界”是人与世界(包括物和人)相互交融的产物,它并不否认离开人而独立存在之物,而只是说这样的独立之物离开了人就没有意义可言。伽达默尔就曾明确说过,他决不否认离开了人的物的独立存在,但我们的兴趣和关心的问题在于:这独立存在之物是怎样显示于我们面前的。这些流派所讲的主客融合一体论,是其重人生、重现实生活、反对离开人生抽象谈论哲学的思想表现,同时也是其注重人与人之间互为主体而非以己为主、以他人为客的平等互尊的思想表现。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应当吸取这些思想以丰富自己的哲学和人生意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哲学主张实践优先于认识,这在某种意义上就包含有主客融合一体优先于主—客关系的思想,它与现当代其他哲学思想(例如海德格尔的“上手的东西”优先于“在手的东西”)是相通的,只是还有待阐发。我们需要从西方现当代哲学那里得到启发,从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本原义深深地加以发掘、发挥和发展。
半个世纪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就其与西方现代哲学的关系方面来说,主要的问题在于把两者绝对对立起来,认为划清界线、着力批判对方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现在看来,这样的“坚持”实际上是孤立了自己,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失去了生命力。时代已经在热切地召唤我们,必须把关注的重点由“坚持”转换为“发展”:只有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而发展的途径之一,正是在于联系当前国际国内的实际,以西方现代哲学为友,吸取它们的优秀思想成果。
从外在的对峙到内在的对话
——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西方现代哲学关系的新思考
近年来,在我国的哲学研究中,西方现代哲学研究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都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然而有趣的是,这两个不同的领域中从事研究活动的学者却常常处在“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状态中,偶尔有一些对话或交流,但与其说它们是学术性的,毋宁说是礼节性的;人们是如此专心致志地在自己的领域中进行耕耘,以致于很少去反思这两个研究领域之间的关系。我们这里说“很少去反思”,表明这样的反思仍然是存在的,但却处在边缘化的状态中,既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也没有产生出任何积极意义上的成果。
据笔者所知,有学者主张西方马克思主义应当从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但这一主张一提出来便遭到了许多学者的批评:按照他们的观点,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异端性质的观点,怎么能把它放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范围中去呢?这些学者的批评意见使西方马克思主义成了卡夫卡笔下的土地测量员,他只能围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城堡”兜圈子,却始终走不进去。
另有学者主张,西方马克思主义应当从属于西方现代哲学,成为西方现代哲学的一部分,但这一主张却遭到了大部分从事西方现代哲学研究的学者的反对。按照他们的看法,西方现代哲学研究具有某种科学意义上的严格性,而任何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当然也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在内)都具有意识形态的特征;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归属于西方现代哲学,势必损害西方现代哲学研究的科学性和纯洁性。显然,这一看法基于双重的误解:一方面,人们把本真意义上的马克思的学说与完全意识形态化的、前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等同起来了;另一方面,即使是西方现代哲学家,他们的观点也不可能完全超越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如杜威之于自由主义传统的意识形态、海德格尔之于纳粹主义的意识形态,等等。不应当把哲学的科学特征与意识形态的特征抽象地对立起来。然而,这种看法虽然与误解相伴,但其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致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亦被逐出了西方现代哲学研究的范围,成了到处飘荡的游魂。
还有学者主张,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看作介于西方现代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中间环节、交叉学科或新的学科生长点。然而,这些新名词并没有真正地把西方马克思主义从学科分类的窘境中拯救出来,也没有真正地消除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西方现代哲学之间存在着的抽象的、对峙的关系。其实,这种紧张的、不正常关系的存在,无论是对西方哲学的研究来说,还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来说,都是十分不利的。
据笔者看来,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西方现代哲学研究的分离与对立至少显露出以下消极因素。首先,在西方现代哲学的研究中,一旦抽去了马克思的学说,这个研究领域便变得残缺不全。众所周知,西方现代哲学大致上发端于19世纪30~40年代,一般认为其肇始人是唯意志主义的代表人物叔本华和实证主义的代表人物孔德。其实,如果我们置身于更开阔的眼界来看问题的话,就会发现,作为存在主义鼻祖的克尔凯郭尔和作为实践唯物主义创始人的马克思都是西方现代哲学的开启者。在《西方哲学史》这部名著中,罗素虽然没有论述克尔凯郭尔在西方现代哲学中的地位和作用,但却专门辟出一章来评述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尽管罗素对马克思的评论是有片面性的,但他还是独具慧眼地看到了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的重要价值及其对整个西方现代哲学发展的影响。他这样写道:“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论点;特别说,它和哲学史家是有关系的。我个人并不原封不动承认这个论点,但我认为它里面包含有极重要的真理成份,而且我意识到这个论点对本书中叙述的我个人关于哲学发展的见解有了影响。”(注: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40页。)按照罗素的看法,在西方现代哲学的研究中,一旦抽去了马克思的重要学说,西方现代哲学发展的脉络就再也没有办法准确地加以把握了。人所共知,波普尔是西方现代哲学领域中科学哲学研究方面最有影响的重要人物之一,尽管他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和《开放社会及其敌人》这两部著作中对马克思的学说取批判的态度,但他坦然承认:“与马克思主义的邂逅是我智力发展中的一件大事”(注:波普尔:《无穷的探索:思想自传》,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4页。)。即使像海德格尔、萨特、德里达这样的大思想家,也深受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影响。在《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中,德里达这样写道:“如果人们不以超越学院化的方式去阅读、再阅读和讨论马克思及其他一些人,将永远是一个错误。这个错误作为理论上的、哲学的和政治责任方面的错误,将会越来越严重。”(注:J.Derrida:Specters of Marx,Routledge 1994,p.13.)在德里达看来,当代西方思想家是无法绕过马克思去思考问题的,不管他们对马克思的学说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他们实际上都已经置身于马克思的学说传统之中,而且只有自觉地、不断地阅读马克思,才能在理论问题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中做出新的创造。总之,西方现代哲学的研究既无法回避马克思的思想遗产,也无法回避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资源。
其次,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如果脱离西方现代哲学这一总体背景,也无法准确地勾勒出自身的发展脉络。如前所述,西方现代哲学滥觞于19世纪30~40年代,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则发轫于20世纪20年代。众所周知,卢卡奇、柯尔施和葛兰西是公认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柯尔施在1930年重版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一书的新增补材料《问题的现状:一个反批评》中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并使之与“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以后,梅洛·庞蒂在1955年出版的《辩证法的历险》、佩里·安德森于1976年出版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中,相继使用了这一新概念,于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潮才广为人知。当我们检视这一思潮发展轨迹的时候,就会发现,它的演化主要有两个内驱力:一是马克思的原始文本(如《资本论》)和新发现的手稿(如《巴黎手稿》、《伦敦手稿》等);二是西方现代哲学发展中出现的新流派。几乎可以说,西方现代哲学中每一个新流派产生后,都会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从而形成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中的新方向。如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韦伯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现象学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派的马克思主义、解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等等。这种相互结合的亲和性表明:一方面,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具有无限的生命力;另一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如果脱离西方现代哲学这个总体上的背景,实际上是无法进行的。
再次,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和西方现代哲学研究处于这种分离的、甚至对峙的状态,我们对有些流派和人物的归属就难以形成一致的意见。比如,法兰克福学派究竟从属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还是从属于西方现代哲学?如果人们把法兰克福学派中与马克思主义相关的部分放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来探讨,把其余的部分放在西方现代哲学中来探讨,这个学派岂不成了支离破碎的东西?同样地,如果我们在研究波普尔、海德格尔、阿多诺、哈贝马斯、萨特、德里达等重要人物时,也把他们论述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放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范围内去研究,而把其余的著作放到西方现代哲学中去研究,这些重要人物的思想岂不也成了支离破碎的东西了吗?
按照笔者的看法,西方马克思主义应当放在西方现代哲学这个总框架内部来进行研究,从而使这两个研究领域从外部对峙的关系转变为内在对话的关系。之所以这样建议主要是基于以下的考量。第一,确保西方现代哲学研究领域的完整性。对这一点,西方学者早就获得了共识。如波亨斯基在1947年初版的《当代欧洲哲学》一书中专门辟出一章篇幅论述“辩证唯物主义”,并强调说:“在欧洲哲学中,辩证唯物主义拥有自己相应的地位”(注:I.M.Bochenski:Contemporary European Philosophy,University ofCalifornia Press 1957,p.61.)。在兰克和施纳德合著的出版于1983年的《哲学史》一书中,作者在论述当代哲学时也辟出专节来叙述“辩证唯物主义”学派(注:J.Rehmke F.Schneider: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VMA Verlag 1983,s.352-358.)。施丢尔希在1989年出版的《世界哲学简史》中的最后部分讨论了当代西方哲学,并辟出题为“今日马克思主义哲学”专章,对卢卡奇、恩斯特·布洛赫、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进行了论述(注:Hans Joachim Stoerig:Kleine Welt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Fischer Verlag 1987,s.620-636.)。这些例子表明,我国的西方现代哲学研究要确保其整体性和科学性,也应该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包含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内。第二,确保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不断地向纵深发展。无数事实告诉我们,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如果对西方现代哲学、甚至对整个西方哲学传统缺乏必要的知识,将不但难以获得创发性的学术成果,而且连准确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的可能性也会消失。事实上,只有依托西方现代哲学这一总的背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才不会流于形式。第三,确保对西方现代哲学家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思想的完整的理解。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叔本华的唯意志主义、孔德的实证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弗雷格和罗素开创的分析哲学,都对20世纪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许多西方现代哲学家或深受马克思思想的影响,或在自己思想发展的某个阶段上对马克思的学说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如果抽去马克思学说这一因素,我们就无法对他们思想的实质和发展脉络作出合理的分析和说明。同样地,如果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背景中抽去西方哲学文化传统和上述西方思潮的影响,我们同样无力勾勒出其思想演化的实际情形。
总之,我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应该成为西方现代哲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分支,这样一来,分别在这两个领域中进行耕耘的学者就将从外在的对峙走向内在的对话,这种对话必将激发起更多的创造性研究的灵感。正如海涅所说,钻石之间的磨擦将会使所有的钻石都发亮。与此同时,西方现代哲学这一研究领域也将因之获得更加丰富的内涵。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有意义的对话何以可能
我以为,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现代哲学的对话问题,需要对话双方一定程度上的相互理解,拥有一定程度的共同语境、共同视域或问题域。按照陈启伟先生的说法,有意义的对话可以有三种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作为知识补充的对话,即把对方作为一种知识对象加以了解;第二个层次是寻求共同点的对话,以便立足于共同的基础,达到互相支持的目的;第三个层次是作为互相辩驳的对话,目的并非是求同,而是互相辩驳,在辩驳中互相发明。显然,只有这三种有意义的对话,才能够获得有意义的结果,达到一定的目的。所谓有意义的结果,在基本的层面上便是通过对话,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现代哲学各派别的对比中确定各自的理论位置,弄明白各自的特征、各种哲学派别之间的同与异;进而彼此从对方那里汲取理论营养,发展自身;而对话的最高境界,则是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相互辩驳,通过辩驳使各自的理论特征清晰化,从而刺激理论的发展。
之所以提出这一对话问题,说明这种对话在以往是缺乏的,这种缺乏又必有其原因,或者说必定因缺少了某些条件。要回答有意义的对话何以可能,无非就是考察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对话才能够是有意义的,而所谓条件,无非是客观的和主观的两大类。我们先分析客观条件。
所谓客观条件,主要是指哲学理论所处时代的社会生活状况。马克思说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黑格尔说哲学是把握在精神中的时代,这两种说法是对哲学理论与现实社会生活关系最为精当的刻画。但是,何为时代?时代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时间跨度概念,而是特定时间段中特定人群的生活方式或实践方式。准此,则处于不同生活方式或实践方式中的人们便在时代上是不同的,尽管他们可能在自然时间上处于同一时间段中。
如果上述命题成立,那么,处于不同生活方式中的人们所把握到的时代精神也便不同,从而这些被把握的东西也就可能属于不同类型的哲学。现在的问题是,这些不同类型的哲学之间有无可能进行有意义的对话?前面说有意义的对话需要对话双方一定程度上的相互理解、拥有一定程度的共同语境和共同视域或问题域,而这一定程度的共同语境、共同问题域和相互理解,一般说来只能是基于共同的、或类似的生活方式或实践方式而形成的。因此可以认为,有意义的对话只能存在于同类型生活方式的同类型的哲学之间,而在基于不同生活方式的不同类型的哲学之间不可能进行有意义的对话。
一般认为,从古到今哲学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或三种哲学范式,即实体性哲学范式、主体性哲学范式和人类学范式或实践哲学范式。从哲学与社会生活的内在关联性看,这三种哲学范式必定与特定的生活方式或实践方式相匹配。自进入文明时代以来,人类迄今已有过两种实践方式,一是自然经济的有机性的实践方式,另一则是工商或市场经济的无机性或构造性实践方式。与前者相匹配的思维方式是一种有机的、笼统的、顺应的方式,亦即一种“实体性”或“本体论”的思维范式;而与后者相匹配的思维方式是一种无机的、构成性的方式,亦即一种“主体性”的思维范式。进而,与探求一种能够克服近代实践方式之弊端的新的实践方式相呼应,产生了一种人类学思维范式,马克思正是这一范式的开创者。然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却并不是始终以这种哲学范式存在的。正如一些论者所指出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50年间已经历了三次范式转换。这一转换可以描述为:从改革开放前的实体性思维范式到80年代以来的主体性范式,再到90年代以来的人类学范式或实践哲学范式(亦有人称之为人学范式或其他类似名称)。为什么中国当代哲学在短短的50年间重演了西方哲学上千年才走完的范式转化过程?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社会生活的发展要求理论与实践匹配。计划经济是一种类自然经济的实践方式,与其相匹配,马克思原本的人类学哲学范式不能不被解释为一种实体性哲学;与市场经济的兴起相呼应的,自然只能是一种主体性解释;而市场经济发展起来之后弊端的显现,则不可避免地会引导哲学回到马克思对市场经济原来所持的一种批判态度的人类学范式。
显然,与不同的实践方式相匹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属于不同的哲学思维范式,因而不同时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便也极不相同。当两者不属于同一哲学思维范式、从而不拥有共同语境和问题域的情况下,要进行有意义的对话是不可能的。我们知道,西方现代哲学所对应的生活方式或实践方式是高度发展了的市场经济类型,因而其所面临的问题便是如何回应这种生活方式所提出的问题。当中国处于一种准自然经济或半工商经济的计划经济的实践方式之中时,与这种生活方式相匹配的哲学所面临的问题便必定与西方现代哲学所面临的问题极不相同。由于缺乏共同的问题域,有意义的对话便难以进行。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与西方实体性哲学的问题域有较多相似性,因而这时的对象便主要是西方的实体性哲学,或者可被解释为实体性哲学的体系。80年代市场经济在中国兴起,使中国人所面临的哲学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与近代西方主体性哲学的问题域有了相似性。因而毫不奇怪,一方面,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急剧地转向了主体性哲学范式,另一方面,对话的对象也变为以笛卡尔、康德为代表的近代哲学。对于西方现代哲学,此时仍处在对之不甚理解或简单批判的独白阶段。
然而,进入90年代之后,由于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市场经济所带来的种种问题显露出来,这就使得作为中国主流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所面临的问题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在社会转型之初,要求从哲学上论证市场经济的合理性,亦即明确弘扬主体性的维度;而在市场经济发展之后,问题便不再是市场经济是否合理,而是如何解决市场经济所带来的问题。这些问题在相当程度上便与西方现代社会的问题有了相似之处或共同之处。而无论是西方哲学还是中国哲学,作为对时代所面临问题的一种深层思考,便也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了共同的问题域。正是这共同的问题域,在客观上使双方有了进行有意义对话的可能性。在寻求解决共同问题的努力中,不可避免地会互相借鉴,互相发明,当然也免不了互相辩驳。
但是,面临某种程度上共同的问题,还只是具备进行有意义对话的抽象的可能性。要使对话成为现实,还必须实现思维范式的转换,真正回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原本的人类学思维范式或现代实践哲学思维范式上。(在笔者看来,西方现代哲学就其总体趋向而言,是一种超越了近代主体性哲学范式的人类学范式。笔者在别处曾论证过,马克思哲学是对于近代主体性哲学的反叛,马克思正是超越了主体性哲学范式的人类学范式或现代实践哲学范式的创立者(注:参见王南湜:《新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理路之检视》,《天津社会科学》2000年第6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现代哲学进行有意义对话的现实可能性,便是实现思维范式的转换。一般说来,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但哲学不会自动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只有通过人们的理论创造才有可能。尽管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已出现了从主体性范式向人类学范式转变的趋向,但是,一则80年代以来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体性解释与主体性解释之间论争的余波尚未消失,在这种情况下,关于马克思哲学是一种超越了主体性哲学范式的人类学范式这样一种说法也就很难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同,而只是一种并不很强的理论声音;另则人类学范式到目前为止基本上还只是停留在一种理论主张的水平上,并未发展出一套足以取代主体性哲学的理论方法,因而要真正实现向人类学范式的转变,还有大量的理论工作要完成。就此而言,笔者赞同“回到马克思”的主张,但不是回到被理解为主体性哲学家的马克思,而是现代实践哲学开创者的马克思。而且,“回到”不能只当作一种态度,而是必须作为一种切切实实的行动,一种从马克思的著作中发掘现代实践哲学理论资源的理论劳作。只有进入这样一种劳作之中,有意义的对话才能够出现。
但是,说原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现代哲学同属现代实践哲学或人类学范式,并不意味着它们是同一种哲学、具有同样的哲学主张:属于同一种思维范式的哲学可能有着十分不同甚至对立的理论主张;而不属于同一思维范式的哲学之间其差异倒可能只是一种简单的不同。事实上,哲学理论之间的尖锐对立,一般说来也只发生于同一种思维范式的哲学之间,如古代的原子论与理念论之间的对立,近代的唯理论与经验论之间的对立。但是,唯其对立,它们之间的对话才更有意义,即更有利于互相发明、互相刺激、互相促进。在现代人类学思维范式内,虽然都强调直接的生活世界的重要性,但马克思对于物质生产实践的重视却与众不同,而这正是马克思哲学之为唯物主义的关键所在。因此,向人类学范式的转换决不意味着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混同于西方现代哲学的某一派别,而是在明确差别与对立前提下的对话。而且,只有明确了差别与对立,对话才能够是有意义的,“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如果抹去了它们之间的差别和对立,将其视为同一种哲学,那么对话也将成为一种自言自语式的独白。
总之,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现代哲学之间进行有意义对话,其客观条件是具有基于相似实践方式的共同问题域,而主观条件则是既转向人类学思维范式,又在这一范式内坚持自身独特的理论立场。
标签: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 哲学论文; 现代西方哲学论文; 主体性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论文; 西方哲学论文; 西方马克思主义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现代主义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科学论文; 世界观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