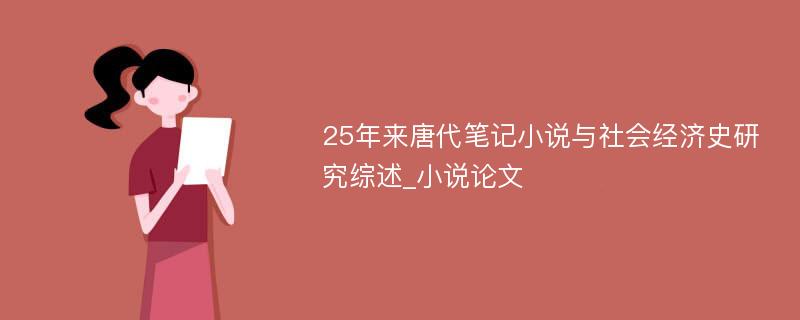
近25年来笔记小说与唐代社会经济史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经济论文,唐代论文,说与论文,史研究论文,年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隋唐五代笔记小说的史学价值,堪与出土文书、石刻碑志相提并论。1920年代,鲁迅先生对小说史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陈寅恪先生“以诗证史”的代表作《元白诗笺证稿》,实际上也是以笔记小说证史的经典之作,向达先生在《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中大量使用了笔记小说中的材料。这些研究促使史学界重新审视笔记小说及其史学价值。
隋唐五代是笔记小说取得重大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发展和变化的重要时期。笔记小说为我们提供了认识隋唐五代尤其是唐代社会经济变化的历史信息。上世纪80年代以来,学者们在关注出土文书和石刻碑志的同时,也逐渐开始重视对笔记小说中史料的发掘、整理,以及对笔记小说本身的研究。隋唐五代小说的研究在20世纪取得了重要成就,《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系列丛书中《隋唐五代文学研究》(北京出版社,2001年)第十六章从文学史的角度对此做了全面的回顾和展望。与文学史领域的研究相比,史学领域相应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却尚嫌不足。
据笔者粗略统计,1980年至2005年,国内以隋唐五代笔记小说为主要史料或主要研究对象的研究论著近30部,论文300余篇。这些研究论著对唐代社会经济问题多少都有涉及,或是较为系统地论述,或是只言片语却有十分精辟的经济与社会背景分析。当前,中古社会经济的变化和发展(或姑且称之为“唐宋变革”)是中古史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深入探讨这个问题,必然需要继续拓展思维和史料范围,笔记小说的价值尤为凸现。因此非常有必要将1980年以来从笔记小说分析唐代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成果加以总结和梳理。
要说明一点,大部分学者都已经不同程度地将笔记小说作为其研究的材料,本文要加以总结和梳理的是专门以笔记小说的角度入手(或者说以其为核心材料)的研究成果。
程国赋以“文学——文化”研究作为立足点与出发点,但在其对唐五代小说文化内涵进行阐释时也结合笔记小说中的相关记载分析当时的经济状况,这集中体现于他的著作《唐五代小说的文化阐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中的第六章“唐五代小说创作与商品经济”。作者对巨商、善于经营的商人、正派商人、胡商等各种商人在小说中的记载和形象都进行了分析研究。此外,他还分析了商业观念对小说创作的影响,以及城市化进程与小说创作风格的通俗化等问题。作者充分吸收了近年来史学界和文学界的研究成果,但有些论述对社会经济现象的背景发掘不够深刻。由于笔记小说基本是以记人记事为主,数字材料非常罕见,因此,20多年来以笔记小说研究隋唐五代社会经济史的成果中,最主要的还是对商人群体以及城市经济与社会的考察。
一、商人群体
唐代的商人群体是唐五代笔记小说中描写较多的人群,因此也是学者们关注较多的一个人群。
学者们主要关注了这样一些问题。其一,小说中人物的工商业者身份认定问题。戚玉成的《荒诞中的真实人生——读唐传奇〈李章武传〉》(《徐州教育学院学报》1987年第1期)认为,从小说中提到“废业即农”来看,女主人公王氏一定是城市小工商经营者(市民阶层)。其二,商人与其他人群的关系。罗立群的《论唐代武侠小说》(《临沂师专学报》1987年第4期)通过对唐代武侠小说的细致分析,认为唐代商业经济发展使得侠与商在物质利益上相互依存,这是唐代侠风盛行的一个原因。惜未见再有学者对二者经济上的交往做更为深入的分析。
胡商是《太平广记》等笔记小说中经常能见到的人物,学者们对胡商的研究成果也颇为丰富,如薛平拴的《论唐代的胡商》(《唐都学刊》1994年第4期),因它们不是专以笔记小说为角度,在此不赘述。韩瑜的《从唐小说中的胡商看唐代中外文化交流》(《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将唐代胡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比较全面地研究了来华胡商的地理分布、胡商与唐代城市商业机制、胡商与“飞钱”、胡商的经营内容、胡商的命运以及胡商给唐代社会经济带来的影响,该文对以往的研究是一个很大的推进。葛承雍的《崔莺莺与唐蒲州粟特移民踪迹》(《中国历史与文物》2002年第5期)继续陈寅恪先生“以小说证史”的思路补充新证,认为蒲州乾和葡萄酒的“乾和”二字是突厥语“盛酒皮囊”的译音,证明蒲州有胡人酿葡萄酒业的存在,文中还指出唐初蒲州地区就有酒家胡,相邻的绛州王绩写有题壁酒家胡诗即为明证。此文发表后,宁强一发表了《崔莺莺:妓女?外国人?》(《光明日报》2003年6月25日B2版)提出了质疑。但笔记小说记载的唐代胡商的经济活动反映了唐代社会经济的发展与中外经济交流的扩大,这一点当不容置疑。笔记小说中对典型商人的记载更是学者们研究的热点。宁欣的《论唐代长安另类商人与市场发育——以〈窦乂传〉为中心》(《西北师大学报》2006年第4期)从窦乂入市与政治世家、经营内容、经营方式与市场发育等方面解读《太平广记》卷二百四十三《窦乂传》,从而探讨了围绕城市生活服务展开经营领域的所谓“另类”商人,并指出这些“另类”商人是研究城市商品经济发展和人口结构必须关注的群体。
二、城市经济与社会
唐代的笔记小说大多是以都市为创作背景的,很多学者注意到了这一点。程国赋对此进行了统计,《唐人小说》所收的68篇唐人小说中有相当部分的作品以都市作为创作背景,其中又以长安为故事发生地点的小说最多(《唐五代小说的文化阐释》,第208页)。赵振祥《论唐代商业经济对文学的影响》(《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也注意到唐传奇的故事多发生在长安、洛阳、扬州、蒲州等繁盛的商业城市。因此笔记小说是研究唐代都市社会经济变化的重要资料。妹尾达彦的《唐代后期的长安与传奇小说——以<李娃传>的分析为中心》(《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国史·六朝隋唐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509—553页),通过对传奇小说《李娃传》的分析,具体揭示长安城市结构的变化,同时兼顾分析当时长安的庶民文化。作者对《李娃传》的情节作了考辨,具体验证了唐代后半期长安地区地域分化的真实情况,他还分析了该故事中天门街竞歌等情节,指出《李娃传》的故事原型就是在唐代以后大众艺术的普及与渗透中形成的。宁欣的《由唐入宋都市人口结构及外来、流动人口变化浅论——从<北里志>和〈东京梦华录〉谈起》(《中国文化研究》2002年夏之卷)一文从《北里志》和《东京梦华录》所描述的唐长安和北宋东京娼妓业及其变化谈起,探讨了流动人口与唐宋城市面貌变化的关系。这是利用小说中的资料具体分析一个特定的人群,并从经济——社会史角度来研究唐宋都城的较有价值的一篇文章。而法国学者雷威安在《唐人“小说”》(《文学遗产》1994年第1期)一文中指出,唐传奇资料证明当时已有职业的说书人。这些都说明笔记小说提供了有关中古时代城市中一些特殊群体的丰富资料,我们完全可以继续深入挖掘中古时代城市的人口流动以及不同群体在城市中的经济活动与社会活动。
上述两个方面是以笔记小说研究唐代社会经济史的最为集中的两个方面。一些学者涉及了当时的阶级或阶层的社会关系与社会地位的层面,其中大家关注较多的是唐代的奴婢问题。王轶冰的《从唐传奇看唐代的私属奴婢》(《锦州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鉴于唐代众多优秀的小说家把目光纷纷对准了奴婢的情况,从唐传奇中撷取其丰富的资料来探讨唐朝盛世时期私属奴婢的来源、役使、地位等情况。此外,雷威安(见前引文)等学者的研究对于这个问题也都有所涉及。
此外,还有学者利用笔记小说研究了颇有现代色彩的问题。郭绍林的《唐代的著作权现象》(《人文杂志》1991年第5期)通过列举唐人笔记小说中的有关材料,说明唐人已经意识到著作权的问题,并开始保护自己作品的领有权和改编权。
如前所述,很多学者虽没有专门从笔记小说的角度入手来研究隋唐五代社会经济,但是也逐渐将材料范围扩大到笔记小说。对此,宁欣在《笔记小说的演变与唐宋社会研究》(《西北师大学报》2002年第5期)一文中,做了比较详尽的列举。例如据作者统计,“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一书,唐宋都城部分注中所引史书177次,其中笔记小说类106次”。在此不一一列举,读者可自行参考。
三、结语
经济史以历史上的经济现象为研究对象,在一定程度上是经济学和历史学的交叉,在经济学日益注重数量分析的今天,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困惑在于是否要进行量化分析。而无论正史的《食货志》还是笔记小说,其所包含的数字材料都比较少,即使有也是比较模糊甚至是错误的记载。因此,从小说中钩稽出的材料一般还比较零散,直接用于经济学意义上的“经济史”的研究有困难。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大部分研究还是集中在商品经济以及各种经济关系方面,而对传统的经济制度等的研究,笔记小说的信息需要经过谨慎的排查,反映的问题也比较曲折。这就决定了将其作为主体研究对象时既需要细致入微又需要放入当时背景之下进行全面分析,同时还应注意视角的转换。
放眼今后的唐代经济史研究,应注意以下问题:
首先,宋代的笔记小说中还有很多关于唐代的记载可以挖掘。唐史是宋人的近代史,宋人的笔记小说数量和质量也胜过唐代的笔记小说,而且有不少关于唐代的信息,因此会有王谠的《唐语林》出现,分散于其他宋人笔记中的材料则需要我们细细爬梳,再联系笔记小说中记载的宋代经济情况,前后比照,相信也会有较大的收获。
利用笔记小说材料的同时,必须借助社会史的研究方法。就隋唐五代的研究实际而言,采取经济——社会史研究的思路似乎比较合适,因此本文将题目定为“社会经济史研究综述”。笔记小说记载了很多社会文化活动,如《李娃传》中记载天门街竞歌一事,但实际上这种社会文化活动背后反映的是经济活动,该故事反映的是街东、街西经济实力的较量。《南部新书》记载了唐代(主要是唐后期)长安城中的多处戏场:“长安戏场多集于慈恩,小者在青龙,其次荐福、永寿”(《南部新书》戊,中华书局,2002年,第67页),那么戏场活动的背后呢?颇有可能存在经济交流,有点类似于今日的文化、经贸活动相互促进的情形。社会民俗文化活动的背后往往隐藏着经济的动机,反映着当时的经济生活。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视角完全可以从社会制度、文化习俗上给经济史甚至经济学提供更广阔的视野。吴承明先生多次强调“研究经济史必须研究社会”、“不能就经济谈经济”(《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84页),说的正是这个道理。
笔记小说大都以都市为背景,是研究隋唐五代的城市,尤其是都市社会、经济问题的重要材料,前面的论述实际上也多以城市为背景。尽管已有很多学者对唐代都市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但笔者觉得从经济—社会史的角度,仍有深入的可能。尤其是可以从笔记小说中继续发掘都市边缘人群如牙人等的社会经济活动,也许会有更多的收获。
利用笔记小说,还需要扩展自己的思维。王家范先生指出:“强调史学必须凭证据说话没错,但殊不知史料本身是不会说话的。只有当史家把考察的视域扩大到‘人与自然’,意识到自然生态环境对人类历史活动的制约关系之后,平日从眼皮底下滑过的生态史料,才会于此时跳出,使我们眼前一亮,顿悟到它们对史学诠释的‘意义’”(《中国历史通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6页)。这实际上指出了思维与材料间的互动关系,即很多问题不因为我们研究而存在。它早就存在了,只是有时需要我们把思维和视域扩展,才能发现它们。比如前面提到的郭绍林的《唐代的著作权现象》一文,想必作者意识到了著作权涉及到巨大经济利益之后,重新来读笔记小说,从而发现了唐代经济史上的“著作权”问题。
总之,我们当以更加积极的眼光来看待笔记小说的史料价值,尤其是其社会经济史料价值,只要我们本着“小心求证”的态度,并不断拓展自己的思维方式和视域,我们完全可以利用它为唐代社会经济史研究开拓出更广阔的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