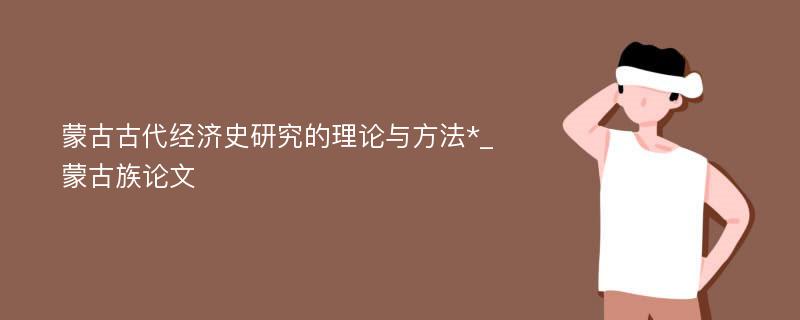
蒙古族古代经济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蒙古族论文,史研究论文,古代论文,方法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摘要]任何经济理论都可成为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而经济史研究究竟选用何种经济理论,则主要取决于理论本身对研究课题的适用性和经济史料的特点,因此,蒙古族经济史研究应重视和运用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尤其要重视和运用马克思在对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一书所作摘录和评注中阐明的观点。同时,结合蒙古族经济史的特点,灵活运用唯物辩证法。这样,我们的研究才会有所突破,才会得出新的结论。
[关键词]东方社会理论 蒙古族经济史 理论和方法
经济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产生于19世纪中叶的欧洲。对于经济史,除作为其依据的历史资料外,其他一切都属方法论,包括各种经济理论〔1〕。然而, 人们得出这个结论却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研究和探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欧美等西方国家的经济史学界,以“德国传统”和“英国传统”占据主要地位。从50年代末起,首先在美国出现了“经济史学革命”,产生了所谓“新经济史学”。这场革命主要改变了经济史的传统研究方法。其特征是充分利用现代资产阶级经济理论来考察经济史,并广泛采用数量研究方法。这样,在克服经济理论与经济史相互脱节方面,在提供量的概念方面,与传统经济史研究方法相比前进了一大步。从此,经济理论与经济史的研究也就能够相得益彰、共同发展了。至于经济史研究究竟选用何种经济理论,则主要取决于经济理论本身对研究课题的适用性和经济史料的特点。古代蒙古社会是属前资本主义社会。因此,对其社会经济结构发展规律进行研究时,应当主要采用马克思主义关于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尤其要重视运用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
一
马克思为了说明东方社会的历史发展,在其垂暮之年,倾注大量心血研究前资本主义社会,作了题材广泛、篇幅浩大的读书笔记,后人称《人类学笔记》。《笔记》的主题之一,就是批判西欧中心主义,强调东方社会的特殊性,承认人类社会发展的多线性。
这一观点,最初是在1877年致《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提出来的。信中写道:“他(俄国民粹派理论家米海洛夫斯基——引者注)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2〕。时隔几年后,即1881年3月8日,他在写给查苏利奇的信中, 再一次重申并阐明了上述观点。他说:在《资本论》中阐述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必然性”,仅“限于西欧各国”〔3〕。 马克思为了写这封信,前后写了三个草稿,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俄国等东方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这一结论可视作马克思对东方社会理论探索的全新成果,是他关于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理论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该理论观点,对蒙古族经济史研究无疑是一个新的视角。尤其马克思在对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一书所作的摘录和评注中阐明的观点,对蒙古族经济史研究具有直接的理论和方法论意义。
“摘录”中,马克思反对柯瓦列夫斯基把亚、非、美洲各古老民族社会历史的演变同西欧作机械类比。他在作摘录时常常把这些类比删除或修改,并且对印度在德里苏丹统治时期和莫卧儿帝国统治时期的土地关系性质作了大段评注。表示不同意柯瓦列夫斯基把印度在上述时期中发生的土地关系变化看作“封建化”的观点,并对柯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⒈纳地亩税,并没有使印度的土地变为封建财产。马克思说:“他们(印度教徙——引者注)不是向国库,而是向由国库授予权利的人缴纳实物税或货币税。纳地亩税并没有把他们的财产变为封建财产,正如impot foncier (法国的地亩税——引者注)不曾把法国的地产变为封建地产一样。柯瓦列夫斯基整个这一段都写得非常笨拙。”〔4〕
⒉马克思认为土地在印度并不具有封建主的司法职能、领地证书和农奴制等重要特征。他说:“别的不说,柯瓦列夫斯基忘记了农奴制,这种制度并不存在于印度,而且它是一个基本因素。……至于封建主……不仅对非自由农民,而且对自由农民的个人保护作用……,那么,这一点在印度,除了教田方面,所起的作用是很小的……;……罗马——日耳曼封建主义所固有的对土地的崇高颂歌……,在印度正如在罗马一样少见。土地在印度的任何地方都不是贵族性的,就是说,土地并非不得出让给平民!”〔5〕因此,当时的印度并不是封建主义。
⒊高度集权的专制君主制不可能产生封建主义。马克思指出:“根据印度的法律,统治者的权力不得在诸子中分配;这样一来,欧洲封建主义的主要源泉之一便被堵塞了。”〔6〕
⒋大莫卧儿帝国在民法方面没有世袭司法权〔7〕。因此, 蒙古人时代, 印度原先的土地所有制关系不仅没有发生什么法律上的变化〔8〕,而且他们的入侵却巩固了采邑占有制〔9〕。
可见,在印度不存在封建主义。蒙古人的入侵也没有改变它,而且在某些方面巩固了它。追其缘由,大莫卧儿帝国同印度一样是一个高度集权的专制君主制国家。大莫卧儿帝国是如此,大蒙古帝国更是如此。据史料记载,蒙古帝国国君对其臣民具有非凡的权威。“任何人都不敢在由皇帝为他指定的地点之外的任何地方居住。”〔10〕皇帝对全国土地具有分封和收回的绝对权力〔11〕。还有帝国的一切财产也“完全都是皇帝的财产,任何人都不敢妄言称道:‘这是属于我的’,或者‘那是属于他的’。而一切都是属于皇帝的,无论是人还是畜类都一概如此。”并就此皇帝曾颁布过“一道敕令”〔12〕。在这种高度集权的专制君主制国家中土地不可能具有封建主的司法职能、领地证书和农奴制等重要特征。因而封建主义也就不可能产生和发展。
二
理论和方法是不可分割的科学内容。迄今为止,科学研究创造并运用着各种不同的具体方法和手段,来认识历史和现实。它们与唯物辩证法不是对立的,而是在科学认识某一过程时对唯物辩证法的具体运用。其运用的形式和界限则取决于研究对象的性质。我们运用唯物辩证法来认识和揭示古代蒙古族经济发展规律时,至少应注意运用以下几种基本方法。
㈠人体与猴体
蒙古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游牧民族。她所创造的游牧文化遗产也不多,加上一些人为的毁灭〔13〕,今天我们所能利用并用于蒙古族经济史研究的史料更不多见。在此情况下,蒙古族经济史研究,在历史断代上从何开始呢?对此,马克思关于确定“人体”、解剖“猴体”的研究方法,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思路和方法。
马克思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这样说道:“资产阶级社会是历史上最发达的最复杂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资产阶级社会借这些形式的残片和因素建立起来,其中一部分是还未克服的遗物,继续在这里留着,一部分原来只是征兆的东西。发展到具有充分意义等等。人体解剖对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14〕在蒙古社会发展史上,能够作为这种“人体”的只有蒙古帝国。原因之一,游牧畜牧业是蒙古族传统产业且是唯一独立的经济部门,而它只有到了蒙古帝国时期才具有了最发达的形式。游牧畜牧业本是人类最古老的、最初的经济部门,但随着人类社会进入文明社会,这种经济部门在世界的绝大多数地方都消失了。然而,它在蒙古高原不但没有消失,反而取得了一定的发展,并改变了人类历史。横跨欧亚大陆、纵横一万余里的蒙古帝国正是这种经济形式的产物。它的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可以从游牧畜牧业这一经济形式的基本矛盾中得到解释〔15〕。原因之二,生活在蒙古高原的蒙古各部在蒙古帝国时期才取得了空前统一的局面,建立了独立而统一的国家,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政策和法律,以新的姿态走上了世界历史舞台,并参与国际事务。
因此,对蒙古帝国社会结构的理解,能够使我们透视已经覆灭的没有文字记载的游牧社会形态的结构和生产关系。因为蒙古帝国就是借这些社会形态的“残片和因素”建立起来的。
㈡生产关系与血缘关系
认识和理解社会结构的关键是生产关系。血缘关系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尤其在蒙古等东方社会。恩格斯说:“有两个自发产生的事实,支配着一切或者几乎一切民族的古代历史:民族按亲属关系的划分和土地公有制。”〔16〕后来他对此作了经典性的概括,这就是两种生产理论。该理论认为,在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社会制度是由两种生产决定的,一方面由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它所产生的社会生产关系决定,另一方面由人自身的生产或种的蕃衍和它所产生的血缘亲属关系决定。商品生产、经济关系愈不发展,社会制度就愈在更大程度上受血缘亲属关系的支配〔17〕。恩格斯的这一理论,长期以来遭到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界中一些人的批评和攻击〔18〕。其实,这不仅是恩格斯的想法,也是马克思的想法。马克思在他晚年的《人类学笔记》中,不但肯定,而且非常重视人类自身的生产及这种生产的关系即血缘亲属关系。他在摘录摩尔根的著作时,同意摩尔根的说法:“血缘家庭是第一个有组织的社会形式。”〔19〕认为在早期人类社会,人本身的生产具有决定意义。这一思想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阐述的原始社会存在有“双重关系”,即“自己生命的生产(通过劳动)和他人生命的生产(通过生育)”的思想,有着惊人的连续性。
可以说,如果不把握这两种生产和两种同是物质性的基本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和血缘亲属关系,就不能真正理解世界各古老民族,特别是东方各古老民族的社会历史。在东方,由于商品生产的不发达,血缘亲属关系和血缘亲属制度曾经十分发达和持久。在古代蒙古社会,商品交换虽然存在已久,但它只是为了满足日常生活需要,以物物交换为主要形式,所以,它还不足以彻底摧毁维系蒙古社会存在的一个重要纽带——血缘关系和血缘亲属制度。虽然它的作用力已非原始社会可比,但终究是可以使人感觉得到的。蒙古帝国时期的“阿寅勒”就是主要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组成的人和家庭的集合。因此,对古代蒙古族血缘关系和血亲制度及其经济内容的研究,对于解开古代蒙古社会结构和财产关系之谜,具有重要意义。
至于蒙古帝国的生产关系,我们研究发现,作为其基础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具有二重结构,即全国土地和部分畜群归国家所有,另一部分畜群归私人所有且是一种不完全的私有制〔20〕。由这种所有制结构决定的分配,当然是一种有利于统治阶级的分配。统治阶级经常以“忽卜绰儿”即对牧场及作为其产品的畜群所征收的1%的租税、 各种临时赋课、1/3的贡赋、各种强制劳动、供养驿站、 围猎等形式搜刮和直接占有生产者的剩余劳动。在这里国家作为唯一而最高地主的身份,充分地被显示出来了。
㈢单线与多线
每一个民族,每一种社会组织、政治制度,每一种文化现象、生活方式都是一定社会经济形态的产物。只有弄清社会经济形态问题,才能揭示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而要弄清社会经济形态问题,又必须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多线与单线之关系,作出正确的回答。
“多线”概念适合说明从原始社会到现今社会主义有若干条发展道路的问题。但是,考虑到世界历史整个进程的主线,我们必须防止将“单线”与“多线”概念僵硬地对立起来。在世界历史单线发展的观念中,很容易夹杂这样一种倾向,即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形态序列似乎可以作为全世界适用的标准。另一方面,多线发展的观念也会导致以另一种方式否定或至少是模糊世界历史进程的主线。我们只有承认社会形态的演进归根到底有条主线的同时,又考虑单线与多线之间的辩证关系,才会对世界历史进程的多样性有一个科学的认识。同样,在古代蒙古族经济史研究中,应承认在蒙古社会形态的演进中有条主线在起作用,同时,也应根据蒙古古代社会经济的特殊性,对其进行多线分析。唯其如此,我们才能避免把蒙古古代历史挤压到单线模式中去的简单做法,同时能够得出一个符合蒙古历史发展的正确的结论〔21〕。
㈣模式法和因素法
在蒙古族经济史的研究领域,人们一般是根据已有的总体结构,如奴隶制和封建制来描述和推导各种经济因素的相互关系和运动的。这种方法在经济学上叫做模式法。其实,这些“奴隶制”和“封建制”等总体结构本身就是机械搬用单线模式来规范蒙古古代历史的结果。如果在蒙古族经济史的研究中导入和运用多线模式,得出不同的总体结构概念,那么根据上述总体结构得出的各种结论就会变得黯然失色的。在古代蒙古社会的经济、政治、历史和自然地理环境等因素的特殊性前面,单线模式日益面临严峻的挑战和考验。可以说,蒙古学研究中单线模式已走到其尽头,很难再有什么新的突破。相反,多线模式在蒙古学领域愈加显示着其适应性和灵活性的优点。
对蒙古族经济史进行多线分析,需要充分占有经济史料。在此基础上,利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考察其各种经济因素的相互关系和运动,然后再界定其总体结构。这种方法在经济学中叫做因素分析法。对此,马克思这样说道:“研究必须充分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22〕可见,因素分析法较适合于古代蒙古族经济史的研究。
㈤地区经济史与民族经济史
在蒙古族经济史的研究领域,有一种观点认为,在内蒙古发现的旧石器文化是蒙古族的。按照史学常识,民族和种族的形成大约在一万年前,而在内蒙古发现的旧石器文化——大窑文化,距今有50~70万年,这是其一。其二,内蒙古地区历史上曾经存在过许多民族,而且他们的活动年代远远早于蒙古族形成时期。何以说内蒙古旧石器文化遗址就属于蒙古族?这里混淆了地区经济史和民族经济史两个概念。我们不能因为蒙古部最后统一和融合了蒙古高原的古代各民族而把发现于蒙古高原的所有古代文化遗存,甚至把旧石器和新石器文化遗存,都当成蒙古族的遗迹。因此,在蒙古族经济史的研究中,应辨别出哪些史料是属于地区经济史的,哪些史料才是属于民族经济史的,然后再将二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这对蒙古族经济史的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除上述方法外,蒙古族经济史的研究还应重视和运用考古学方法。考古学是根据实物材料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学科。它对弄清已经覆灭的社会形态的结构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我们的研究当然不能忽视这一点。本世纪中叶对蒙古帝国首都哈剌和林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了13世纪的蒙古货币和金国货币,还有18~19世纪的日本货币,共230枚〔23〕。这些发现对于说明当时蒙古社会的商品交换及对外贸易状况都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批驳认为古代蒙古人不知道货币的观点〔24〕,提供了有力的依据。
三
综观近十年来的蒙古族经济史的研究成果,研究中无一例外地都采用了单线模式。众所周知,单线模式虽然能够展示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但它却不适合说明东方社会发展的具体历史。古代蒙古帝国地处蒙古高原并建立在游牧畜牧业的基础上,它有着许多不同于西方社会的特点,甚至与东方农业社会也不同。我们应根据其特点采用适合说明它的理论和方法。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突破蒙古族经济史研究中业已形成的僵局,并会得出全新的结论。
本文于1995年8月20日收到。
*该文为内蒙古教育厅科研项目的一部分。
Theory and Method of the Studies of the Ancient Mongolian Economic History
Bao Yu—shan
(Department Politics & Economics,Inner Mongolia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Any economic theory may turn out to be
themethodology of the study of economic history.Which theory isto be chosen for the study of economic history mainlydepends on the suitability of the theory itself to thesubject an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aterialsofthe economic history.Consequently,in the study of economishistory of the Mongols,Marx's theory on the eastern societyshould be given much attention to and applied,those ideas inparticular which clarified in the extracts and comments madeby Marx while reading Kovalevsky's "Possession
SystemofThe Commune Land".Also,materialistic dialectics should beused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ongolianeconomic history. Only in this way can we make greatbreakthrough and arrive at new conclusions in our study ofth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Mongols.Key Words Theories on the eastern society economic historyof the mongols theory and method
注释:
〔1〕吴承明:《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经济研究》,1995年第4期。
〔2〕〔3〕〔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30、268、353页。
〔4〕〔5〕〔6〕〔7〕〔8〕〔9〕〔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69、284、274、284、280、277、 348页。
〔10〕〔12〕耿升、何高济译,《柏朗嘉宾蒙古行纪念鲁布鲁克东行纪》,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4、55~56页。
〔11〕参看《蒙古秘史》第244节。
〔13〕陶克涛著,德柱、乔吉译:《为〈毡乡春秋〉蒙文版所作序言》,《毡乡春秋》(匈奴篇),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页。
〔14〕〔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4 年版,第108、217页。
〔15〕拙作:《游牧经济基本矛盾与蒙古帝国对外扩张》,《内蒙古师大学报》(蒙文版),1995年第1期。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第2页。
〔18〕《马克思主义来源研究论丛》第8辑,商务印书馆,1987 年版,第438~447页。
〔20〕〔21〕参见拙作:《蒙古帝国土地关系及其社会性质》,《内蒙古大学学报》(蒙文版),1994年第3期; 《蒙古帝国畜群所有制结构及其社会性质》,《内蒙古社会科学》(蒙文版),1994年第4期。
〔23〕[蒙古]д·那旺:《古代蒙古历史文物考》蒙文版,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37页。
〔24〕[前苏联]博·雅。符拉基米尔佐夫:《蒙古社会制度史》(汉文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6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