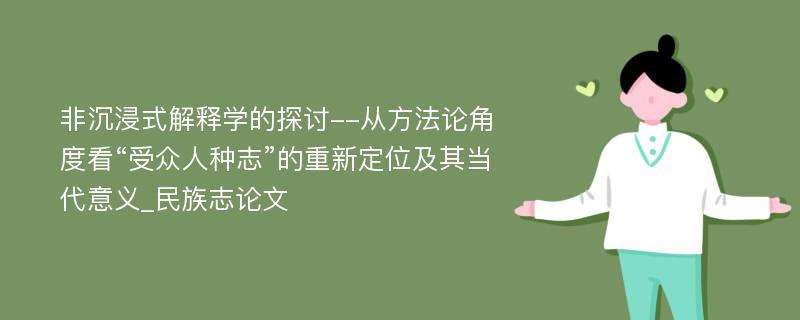
非浸入式诠释性探究:方法论视野下“受众民族志”的重新定位及其当代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受众论文,视野论文,当代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伯明翰学派以戴维·莫利(David Morley)的电视受众研究为代表的媒介受众研究通常被认为在传播学特别是媒介研究学术史上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其理由之一便是认为莫利的研究是将民族志应用于媒介研究的典范,可称之为“受众民族志”研究。一方面,莫利认为自己的研究使用民族志可以“提供一个对这种行为(受众的收视行为)的复杂性有着足够‘厚实’的描述”①;另一方面,正如国内有学者所总结的:“有的西方学者把对受众的接受研究归纳为三个不同的阶段及三种不同的重要范式,即接受研究(reception research)、受众民族志(audience ethnography)和建构主义视野(a constructionist view),从中不难看出民族志在受众研究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另外一些学者则进一步提出传播研究中的‘民族志转向’(ethnographic turn),这更是凸显了这种研究方法的重要历史地位。”② 然而,戴维·莫利的研究是否真的在方法论上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其研究真的是名副其实的“受众民族志”研究吗?笔者认为这是很值得推敲的。本文希图对此作出较为深入的探讨,以厘清其在传播学学科史上的地位及相应的方法论意义。 一、“受众民族志”研究及学界对其的质疑 民族志(ethnography)是“质的研究中一种主要的研究方法”③,但其不同于观察、访谈等具体的资料收集方法,而是一种基于特定研究范式并包括研究设计、经验资料收集、资料分析等一系列研究环节的策略性研究方法。故也有学者认为民族志是质性研究的一种研究策略(strategy of inquiry)。④ 民族志被用于传播学最早见于人际传播领域,称之为“传播民族志”(ethnography of communication)。⑤但早期的传播民族志主要还是被运用于言语社区(speech community)的考察,充斥着浓厚的互动社会语言学气息。而通常认为,这一方法真正被运用于媒介研究领域并在研究范式上产生影响,则主要归功于伯明翰学派后期戴维·莫利的电视受众研究。 自伯明翰学派内部兴起反对弗兰克·李维斯(Frank Levis)式纯文本分析的文化研究的浪潮以来,在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提出不同的几种“文化”定义以及“文化唯物主义”方法的基础上,霍尔总结了文化研究的两种范式:一是以观念和意识形态为核心的结构主义范式,一是以整体生活方式为核心的文化主义范式。⑥莫利即是文化主义范式文化研究的坚定贯彻者,他考虑到民族志在考察人们整体生活方式方面有一定的优势,故而在家庭电视研究中借鉴了这一方法的要素,并被后来者称之为“受众民族志”(audience ethnography)。但事实上,莫利并非一开始就将民族志方法运用到媒介受众研究中,而是经历了一个过程。 在《全国新闻》(Nationuids)受众研究中,莫利首先尝试了使用访谈的方式来收集第一手资料。《全国新闻》是1970年代在英国播出的一个电视新闻节目,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于1975-1979年间对该节目的传播内容和受众展开了研究,其中传播内容部分是考察节目“特定的形式设计、对受众特定的说话方式以及文本组织的特定形式”;受众部分是“探究节目内容是如何被具有不同社会背景的个体解读的,同时试图了解其文化构架在影响个体解读节目中的作用”。⑦莫利所负责的部分是后者,他做出的具体设计是:让来自不同社会背景的受众观看2集《全国新闻》(其中18个组观看一集,11个组观看另一集,每组5-10人),然后在研究者的引导下进行讨论。⑧不难看出,这里莫利主要使用的是由哥伦比亚学派代表人物罗伯特·默顿(Robert K.Merton)所首创的焦点小组法。莫利在事后的回顾当中也专门提到了这一点:“由于时间和资源上的限制,我们没有能够进行语境层面上的研究……节目最初在家庭中被解码和讨论,然后又在其他语境中被重新讨论和诠释。然而,我们并没有对整个过程进行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⑨但他也并不认为这样做会对研究结果造成多大的影响——“但是我认为,这并不会损害我们的研究结果,因为我将假定,解码过程具有可以跨越语境的基本连续性”。⑩显然,莫利的意思是,对于受众的电视节目解码而言,电视节目收看的情境不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从这里可以看出,莫利并没有觉得在原始情境中进行的民族志研究与从原始情境中抽离出来的焦点小组研究有太大的实质性差异。然而,在随后的家庭电视研究中,莫利开始认识到保留原始情境的重要性。 家庭电视研究是由莫利领衔的一项研究,可以说是《全国新闻》受众研究的后续。在1986年出版的这项研究的最终成果《家庭电视——文化的力量与家庭式休闲》一书中,莫利专门用了一章的篇幅来反思上一项研究的不足。(11)他首先承认,《全国新闻》研究“已经引发了一些争议”;接下来总结了研究的若干不足,其中第一条就是:“《全国新闻》受众研究是在受访人小组脱离其家庭环境——也就是说,不在他们‘原生态的’(natural)家庭收视情境当中的情况下完成的,这引起了一些争论。”(12)莫利很快认识到这与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有关:“这种方法(焦点小组)的显著优点在于:它能让我很容易就接近这些已经组成小组的人们。但是同时,这个策略的不足之处是我不能在人们经常所处的看电视的语境中来访问他们。”(13)于是他提出了与上一项研究完全不同并且更具整体性思考的研究目标:“我自己的兴趣是关注人们究竟是怎样观看电视的——也就是看电视作为一项活动其过程是怎样完成的。这就是说,我必须在认识受众对特定类型节目素材的特定反应(这就是《全国新闻》研究所定位的层次)之前先认识观看电视的过程(这一活动自身)。”(14)所以,在家庭电视研究中,莫利放弃了在上一项研究中使用的焦点小组方法,采用了能够尽量在原始情境的“原生态”状态下对媒介受众展开研究的更具整体性和系统性的民族志方法——“这就是为什么在这项新的研究项目中我们决定把整个家庭作为访谈的单位,并且就在他们自己的家里进行访谈——这是为了更好地认识人们在‘原生态的’家庭情境中是如何观看电视的。”(15) 正是基于此,莫利的研究被冠之以“受众民族志”之名,并得以成为传播学研究史上的标志性研究。但不少学者对这一说法提出了质疑。有学者认为,莫利的研究被贴上“民族志”的标签完全是一种误导,(16)最多只能称之为“准民族志分析”(quasi-ethnographic analysis);(17)媒介文化研究学者詹姆斯·拉尔(James Lull)还提出了较为偏激的看法,称:“‘民族志’已经成了在本研究领域被滥用的一个泡沫词汇(an abused buzzy word)。”(18)安东尼奥·拉帕斯汀纳(Antonio C.La Pastina)更是在其《受众民族志:一种媒介接触的进路》一文中认为其被命名为“民族志”的主要原因在于“对于数据的收集与分析而言民族志在修辞意义上已经成为实证主义范式的对立面”。(19) 二、方法论视野下“受众民族志”与民族志的比较及其重新定位 尽管戴维·莫利的研究被贴上“受众民族志”的标签这一举动在围绕实证主义展开范式之争的背景下极可能富有“学术政治”上的意义,然而单就其使用的研究方法而言,却未始不是值得探讨的——究竟其研究方法与民族志相比存在何种差异?此种研究方法是否具有其独特性?都是需要进一步回答的问题。笔者认为,相比于“标准的”民族志方法,莫利的研究至少有以下几点差异: 第一,莫利的研究缺乏研究者在家庭电视受众日常生活实践中的实际浸入(actual immersion)。在民族志研究中,研究者本身虽然是一个局外人(outsider),但却要求其尽量以一个特殊的局内人(insider)的身份深度浸入(immerse)到研究对象的日常生活之中,通过局内人的视角对事件、情境、经历及行动的过程细节进行深入的探究和描述,并提供局内人对事件、情境、经历及行动意义的理解——即体现研究的反身性(reflexivity)。在这一点上,文化人类学家通常采用与研究对象同吃同住的方式达到目标。而以莫利为首的研究者却无法进入到研究对象的日常生活(即无法与研究选取的家庭同吃同住),只能以一个完全的局外人的身份展开资料收集,以至于后来的分析无法将研究者作为一个因素考虑进去。 第二,莫利的研究缺少细节性的参与观察。尽管莫利采用了访谈的资料收集方式,并且将《全国新闻》研究中焦点小组访谈改为以家庭为单位且地点在受众家中的“原生态”访谈,然而对于他曾指出的在研究中要回答的问题——“在收看电视的语境下,哪些家庭成员拥有多少空间以及何种类型的空间?这种空间是怎样组织起来的?电视机和其他的传播技术是怎样穿插在那个空间里的?客厅是围绕着电视组织起来的吗?不同的家庭成员在那个空间里面是不是有着特定的看电视的位置?”(20)——仅仅使用访谈是不够的,还要使用参与观察的方式才能更好地获得答案。但是由于城市家庭的私密性较高,他未能对家庭电视受众进行参与观察,这就与民族志所采用的以参与观察为主、深度访谈为辅的资料收集方法产生了一定的差异。 第三,莫利的研究几乎没有对家庭电视成员日常交往世界的考察。日常交往世界是日常生活世界的最基础的组成部分,是民族志研究者所需要进入的相对于有形现场(field)而存在的无形现场,也可以说是基于社会网络(social network)的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意义上的场域——因为其中往往蕴藏着错综复杂的社会或文化权力关系。只有在研究者浸没入研究对象日常生活并同时结合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方法进行资料收集的情况下,才可能对研究对象的日常交往世界有比较丰富(thick)而准确的把握,而且这两点都恰恰是莫利的研究所欠缺的。故此莫利的团队只能通过研究对象在访谈中的叙述(narrative)或者说自我报告(self-report)来间接了解其社会关系及其与周围他人进行互动的情况,不仅带有较大的不稳定性,而且无法依靠研究者不同感官(经验)渠道获取的信息来加以相互印证。 那么应当如何在方法论上重新定位其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呢?根据前文的分析,需要抓住两个要点: 一是此类研究所采用的方法与民族志具有共同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基础,属于诠释主义范式研究方法中的一种。从本体论来看,民族志作为典型的质性研究方法主要建立在社会建构论(social constructivism)和承认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的世界观基础上;从认识论来看,其基础包括符号互动论(symbolic interactionism)、现象学社会学(phenomenological sociology)、常人方法学(ethnomethodology)和生态心理学(ecological psychology)。其中,符号互动论认为人类是在事物对她们所具有的意义的基础上对事物发生行动,而事物的意义源自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互动。(21)这就意味着个体在特定社会情境下必定会对意义进行建构和解释,而且这一过程是一个能动而非被动的过程。现象学社会学则认为,日常生活世界中的一切,从本质上看都是主体间性的,因而主张社会学回到生活世界的基本事实上,关注社会现象的独特性以及其中的意义特征。而常人方法学提出主张、论证、统计等呈现出的只是一种或然性的成就,有赖于产生它们的那些社会安排;判断一项活动是否具有理性、客观性、有效性、连贯性等等,依据的是随发生该活动的情境而定的或然性标准。(22)生态心理学则认为人类行为是个体的内在因素与外在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应当通过揭示这种相互作用来研究、解释和预测现实生活中的行为和心理现象。不难看到,这些认识论思潮的共同点是,均承认人的活动的情境性及其意义的建构性,并认为对人及其行为的认识应通过互动(相互作用)的方式来予以把握和认识。因此,该种研究方法与民族志一样同属社会研究三大范式之一的诠释主义(interpretivism)研究范式,属于诠释性研究方法中的一种。这也是为什么有学者将之称为大众媒介研究的“诠释性转向”(interpretive turn)(23)的原因。尽管随即有学者对其是否应当被界定为“转向”提出了争议,(24)但其诠释主义的范式特征得到了人类学者和传播学者的一致公认。 二是此类研究所采用的方法与民族志在资料收集方法上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在表层上体现在,所谓的受众民族志研究始终以访谈(某些时候甚至很难称得上是深度访谈)为主要的资料收集方法,而不像民族志采用参与观察与深度访谈相结合的方式。而造成这种差异背后的深层因素则是:原生态情境的剥离。正是因为在研究中剥离了原生态情境,才导致研究者无法采用参与观察法,而只能使用通过访谈也即依靠研究对象叙述(自我报告)的方式来收集资料;也正是因为剥离了原生态情境,研究对象的日常交往世界才只能依靠其自己的视角和叙述呈现出来,而不能由研究者通过亲身进入来加以体验。所以该种研究方法与民族志最大的区别在于后者是浸入式的,而前者是非浸入式的。 在抓住以上两点的基础上可以看到,尽管“受众民族志”与民族志具有共同的认识论基础,但在具体操作层面上的差异完全足以使之成为一种堪与民族志并列的策略性研究方法。就方法本身而言,“受众民族志”一词显然既不够准确,也未能完全反映出这一事实。那么应当如何概括这种研究方法呢? 美国学者凯文·卡内基(Kevin M.Carragee)使用了“诠释性媒介研究”(interpretive media studies)的概念来代替“受众民族志”,并总结了此类研究所共同具有的基本假设和概念基础:主动受众(active audience)、多义文本(polysemic text)和诠释社群(interpretive communities)。(25)不仅如此,他还明确指出其“在将媒介受众置于特定的历史、社会与文化情境方面是失败的”。(26)笔者认为,这一名称虽然较好地避免了该种方法与民族志的混淆,但仍然不够准确。一方面,“诠释性媒介研究”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从卡内基对其基本假设和概念基础的论述来看,其本身是对一种媒介研究取向(诠释主义范式在媒介研究中的反映)的概括而非一种研究方法的名称,英文词“studies”的使用也表明了这一点;另一方面,民族志明显也是属于“诠释性媒介研究”取向的一种方法,不能体现出该种研究方法区别于民族志的自身特点。鉴于此,笔者建议在前文总结的基础上将这一研究方法命名为“非浸入式诠释性探究”(non-immersive interpretive inquiry)。其中,“诠释性”体现其所属的研究范式;“探究”(inquiry)对“研究”(studies)的替换体现出其是一种策略性方法而非研究取向(27);而“非浸入式”则体现该种方法与民族志在操作层面的最大区别。 三、非浸入式诠释性探究方法对于当代媒介研究的意义 从历史的视角来看,非浸入式诠释性探究方法在媒介研究中的使用其实并非肇始自戴维·莫利的家庭电视研究,而是滥觞于1940年代的哥伦比亚学派传播研究和媒介人类学。社会学家、传播学先驱赫塔·赫佐格(Herta Herzog)就曾在1941年的日间广播连续剧研究中使用脱离原生态情境的深度访谈法收集经验资料来研究受众日常生活中对广播节目的使用与满足。(28)此外,著名英国人类学家格雷戈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也曾于1943年发表论文《对电影故事片的文化分析与主题分析》,对当时德国的纳粹宣传故事片(Nazi propaganda fictional film)进行了人类学视角的研究,其资料收集是通过从电影库(the Film Library)获取影片资料以及对一些德国人和对德国文化较为熟悉的社会研究学者进行“逐字访谈”(verbatim interview)来完成的。(29)贝特森指出,对电影的人类学分析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对重要主题(theme)的认识;二是验证这些重要主题是否真正是我们所研究文化的实际特征。具体到方法上,则是一方面通过影片来例证重要主题,另一方面则通过访谈法(interview techniques)来对其进行验证。(30) 从前文比较分析的结果来看,非浸入式诠释性探究方法与民族志相比所缺少的要素或许称得上是一种缺憾,但时至今日仍有不少学者依然选择了使用这样一种带有缺憾的研究方法对媒介和传播展开研究。笔者认为这绝非偶然。对于当代媒介研究而言,非浸入式诠释性探究至少在两个领域有其用武之地。 一是城市媒介研究。众所周知,民族志研究诞生于西方学者为了解人类文化发展的早期阶段而对一些尚处于“蒙昧”“野蛮”阶段的土著民族部落进行的研究和记录,后来成为社区研究的主要方法。正因如此,民族志方法在应用于乡村研究时是非常有效的研究工具,即使是乡村地区的媒介研究也不例外,国内外都有极其成功的研究案例,较具代表性的如柯克·约翰逊(Kirk Johnson)的《电视与乡村社会变迁:对印度两村庄的民族志调查》、郭建斌的《独乡电视:现代传媒与少数民族乡村日常生活》、李春霞的《电视与彝民生活》、吴飞的《火塘·教堂·电视——一个少数民族社区的社会传播网络研究》、卿志军的《电视与黎族生活方式的变迁》以及丁未的《流动的家园:“攸县的哥村”社区传播与身份共同体研究》等。(31)这些研究所选取的考察现场虽然各有不同,但大多数是民族地区的乡村。仅有的特例是“流动家园”研究,所选取的现场是位于深圳市福田区的一个占地0.23平方公里的小型城中村——石厦村,也是一个“类乡村”社区,所以民族志方法在这一研究中也发挥了较好的作用。(32) 但在以城市媒介为研究对象时,民族志方法却有一些难以克服的障碍。城市作为现代性的重要组成要素,其家庭的私密性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民族志在城市媒介研究尤其是城市家庭媒介研究中的运用毫无疑问会受到极大的局限。即便是20世纪初兴起的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城市民族志”(urban ethnography)研究,重点也多聚焦于贫民窟、夜总会、少数族裔聚居区等具有明显封闭社区特征而利于“田野考察”(fieldwork)的研究现场,在这些封闭社区中,受访对象的地理位置相对集中且社会关系具有较强的整体性。这也是为什么民族志方法在现代社会学研究中主要用于研究农村而非城市。而现代城市的单个家庭(一般家庭成员人数为3-5人)作为社区而言,规模实在太小(相比于农村的村庄),多个家庭又相对较为分散,不具有研究的整体性,这也使得民族志方法难以施展。因此,像非浸入式诠释性探究这样近似于民族志而又剥离原生态情境的研究方法就受到了研究者们的欢迎,其在具有小范围日常居住空间(如电梯公寓住户)、小范围日常社会关系(如核心家庭)等特征的城市媒介研究当中成为一种相对合理的选择。除了戴维·莫利的家庭电视研究之外,近年来国际学界不乏选择了非浸入式诠释性探究方法进行的城市媒介研究,其中较为典型的当属斯图尔特·胡佛(Stewart M.Hoover)和柯蒂斯·寇茨(Curtis D.Coats)于2011年发表在国际传播学会(ICA)著名期刊《传播学刊》(Journal of Communication)上的《媒介与男性身份认同:关于媒介、宗教与男性气质的受众研究》。(33)研究采用了与莫利的家庭电视研究十分类似的入户访谈方式,分别对按照“目的性抽样”(purposive sampling)原则在全美范围内通过社会网络招募的30个城市白人家庭(包括19个福音派基督徒家庭和11个非福音派基督徒家庭)中的成人进行了前后各2小时的两段式深度访谈,探析了媒介如何影响男性气质(masculinity)、父权观念以及与家庭和个人的宗教、精神价值观念有关的公民参与(civic engagement)。研究的资料分析以受访者的“叙事”(narratives)为中心,重视研究者对受访者故事的理解(understanding),体现了明显的诠释性研究特征。虽然研究者将访谈地点设定在受访者的家中(也即研究的“现场”),但由于并未深度浸没于受访者的日常生活,显然研究是非浸入式的。即便如此,研究的发现仍然具有相当的价值,从而得以被国际权威期刊所认可和接纳。 二是新媒体研究。不难发现,目前较为成功地运用民族志方法展开的媒介研究基本都集中于以电视为研究对象,而互联网等新媒体的民族志研究却十分鲜见。为何会形成这样的一个研究格局呢?笔者认为,这与媒介自身的社会属性有极大的关系。电视不仅是一种可供多人观看的媒介,而且观看的多人在物理空间上具有共享性。这在早期电视机相对匮乏的时候表现得特别明显,日本学者藤竹晓将之称为电视的“酒家阶段”(34),即家中没有电视的人们集中到拥有电视的家庭去观看电视的阶段。即便在家家户户都置有电视机之后,仍然可以全家人一起共同观看电视,从而形成一个物理上共同在场(copresence)的空间,这在前述的典型民族志电视研究中几乎成为一个必然提到的要点。例如,在郭建斌的独乡电视研究中,曾有专章“在哪里看”描述观看电视的物理空间,并分为“在自家看”“到别人家看”“到集体电视房看”等不同情况;(35)在李春霞的彝民电视研究中,不仅提到“电视被放在家庭中心——‘堂屋’火塘对面的墙边(一般在门的左右),草坝子拥有电视的家庭都是如此,原因是方便大家坐在火塘边看电视”,还专门用一段描述来介绍“草坝子很多家庭收视电视的情境”,并将共同观看电视的物理空间称之为“电视的仪式空间”。(36)所以,电视尽管在现代城市中可能的受众共享空间和共享社会关系会变得更小,甚至完全可以缩小到个人单独使用,但就其根本属性来说,显然是一种在场分享式媒介,这就为民族志研究留下了参与的空间。 然而,另一些媒介却并非如此。例如,伯明翰学派后期著名的索尼“随身听”研究就曾经指出,“随身听作为一种技术产品能够使人们与世界隔绝”,“它可以导致人们越来越个性化和四分五裂”。(37)因此,与电视不同,不能接入互联网的随身听是一种极为典型的个人独享式媒介。而作为互联网终端的个人电脑和手机毫无疑问也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这样的特点,近年来媒体频频曝出类似长辈不满年轻人在饭桌上玩手机之类的新闻(38)便是明证。虽然互联网让更多位于不同物理空间的人得以联系在一起产生大量的远距离社会关系,但其后果之一便是将电脑、手机等终端使用者和物理空间上的共在者区隔开来,使其社会互动的强度和频率都趋于均匀化。遗憾的是,目前的研究对于这一点还揭示得不够,早先杨善华等、(39)罗沛霖等(40)或曹晋(41)关于农民工手机使用的研究,都侧重于关注其在维持社会关系运作中呈现的从一个终端(手机或电脑)到另一个终端(手机或电脑)的分享性,而非在作为获取媒介讯息内容的工具使用时所体现的更为典型的对同一终端(手机或电脑)的独享性;仅仅只有“流动家园”研究,才对同一终端的独享性予以了一定的关注,并特别指出在某些情况下手机是多人共用的。(42)但必须注意的是,这种“共用”并非同时的,而是相互错开时段,换言之,在任何一个具体的时段,手机的使用者都只有一人——也即处于独享状态。新媒体越来越突出的这种个人独享性,使得民族志研究者在对其展开研究时几乎没有参与空间,从而导致长于社区整体性考察的民族志方法在相关研究中越来越难以施展。正如“流动家园”研究的研究者自己所陈述的那样:“当我们想了解攸县出租车司机如何使用手机时,却在研究方法上遇到了难题,通常人类学的观察体验和深度访谈法效果并不好,普通的大样本问卷调查又无法深入。”(43)于是最终采用了通过个别访谈(44)和焦点小组(45)收集资料再进行个案分析的方法。事实证明,这样做的效果反而相对更为理想——“我发现从‘个人经历’入手,让访谈对象讲述他们的生活故事,是了解他们新媒体使用的最佳路径,这也是我对‘情境式研究’的一点体会。”(46)非浸入式诠释性探究由于并不要求在实际浸入的状态下对原生态情境进行直接观察和体验,(47)其资料收集方式以访谈(包括个别访谈和焦点小组)为主,研究对象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分散于不同的物理空间,而在进行资料收集时又可以集中于非日常生活的某个场所,对于作为研究对象的个体个人空间的介入仅仅停留在一个非常浅表的层次上,这使其得以成为一种对个体层面上的媒介使用进行研究时特别适用的研究方法。与城市媒介研究的情况类似,近年来国际学界也有运用非浸入式诠释性探究对新媒体使用展开研究的范例,如美国传播学者迈克尔·塞拉齐奥(Michael Serazio)的《政治顾问的新媒体设计:碎片化时代的选战生产》(48)就采用深度访谈的资料收集方法,通过对以目的性抽样和滚雪球抽样相结合的方式选取的38名担任竞选者政治顾问的受访者进行一对一(one-on-one)的访谈(平均每人访谈时长37分钟),从“文化生产”(cultural production)的视角对选战中的政治顾问如何利用新媒体进行宣传造势进行了探析。 四、结论 根据以上分析,笔者认为从方法论的角度而言“受众民族志”确实是一个不恰当的标签,而应代之以“非浸入式诠释性探究”。后者作为一种策略性研究方法,以去原生态情境化的访谈(包括个别访谈和焦点小组)为经验资料收集的主要方式,与民族志同属诠释主义研究范式,已经成为相对更适用于城市媒介研究和新媒体研究的一种不同于民族志的质性研究方法。 注释: ①[英]戴维·莫利:《电视、受众与文化研究》,史安斌主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年,第200页。 ②蔡骐、常燕荣:《文化与传播——论民族志传播学的理论与方法》,《新闻与传播研究》2002年第2期,第16-22页。 ③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5页。 ④Morse,J.M.,"Designing Funded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Norman K.Denzin & Yvonna S.Lincoln(eds.),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Thousand Oaks:Sage,1994,p.224. ⑤有的学者将其译为“交流民族志”,参见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55页;还有学者将其译为“民族志传播学”,参见蔡骐、常燕荣:《文化与传播——论民族志传播学的理论与方法》,《新闻与传播研究》2002年第2期,第16-22页。笔者认为其是否能够称之为传播学的一个分支还有待商榷,故仍然将之译为“传播民族志”。 ⑥Hall,S.,"Cultural Studies:Two Paradigms," Media,Culture and Society,vol.2,no.1,1980,pp.57-72. ⑦[英]戴维·莫利:《电视、受众与文化研究》,史安斌主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年,第85页。 ⑧[英]戴维·莫利:《电视、受众与文化研究》,史安斌主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年,第103页。 ⑨[英]戴维·莫利:《电视、受众与文化研究》,史安斌主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年,第113页。 ⑩[英]戴维·莫利:《电视、受众与文化研究》,史安斌主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年,第113页。 (11)See David Morley,Family Television:Cultural Power and Domestic Leisure,London:Comedia,1986,Chapter 3. (12)David Morley,Family Television:Cultural Power and Domestic Leisure,London:Comedia,1986,p.29. (13)David Morley,Family Television:Cultural Power and Domestic Leisure,London:Comedia,1986,p.29. (14)David Morley,Family Television:Cultural Power and Domestic Leisure,London:Comedia,1986,p.30. (15)David Morley,Family Television:Cultural Power and Domestic Leisure,London:Comedia,1986,p.30. (16)Carragee,K.M.,"Interpretive Media Study and Interpretive Social Science,"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vol.7,no.2,1990,pp.81-96.Spitulnik,D.,"Anthropology and Mass Media,"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vol.22,1993,pp.293-315.Marie Gillespie,Television,Ethnicity and Cultural Change,New York:Routledge,1995,pp.53-55. (17)Lave,J.,Duguid,P.,Fernandez,N.& Axel,E.,"Coming of Age in Birmingham:Cultural Studies and Conceptions of Subjectivity,"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vol.21,1992,pp.257-282. (18)Lull,J.,"Constructing Rituals of Extension through Family Television Viewing," in James Lull(ed.),World Families Watch Television,1988,pp.237-259. (19)La Pastina,A.,"Audience Ethnography:A Media Engagement Approach," in Eric W.Rothenbuhler & Mihai Coman(Eds.),Media Anthropology,Thousand Oaks,CA:Sage,2005,pp.139-148. (20)[英]戴维·莫利:《电视、受众与文化研究》,史安斌主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年,第159-160页。 (21)See Blumer,H.,Symbolic Interactionism:Perspective and Method,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s-Hall,1969.转引自童星主编:《现代社会学理论新编》,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3页。 (22)[美]马尔科姆·沃特斯:《现代社会学理论》,杨善华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第43页。 (23)Evans,W.A.,"The Interpretive Turn in Media Research:Innovation,Iteration,or Illusion?"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vol.7,1990,pp.147-168。 (24)例如,有学者认为在传播学之前的传统研究取向中就带有诠释主义色彩,如使用与满足取向。参见Evans,W.A.,"The Interpretive Turn in Media Research:Innovation,Iteration,or Illusion?"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vol.7,1990,pp.147-168. (25)Carragee,K.M.,"Interpretive Media Study and Interpretive Social Science,"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vol.7,no.2,1990,pp.81-96. (26)Carragee,K.M.,"Interpretive Media Study and Interpretive Social Science,"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vol.7,no.2,1990,pp.81-96. (27)"inquiry"一词常常在质性研究的策略性方法的名称中使用,如叙事探究(narrative inquiry)、情境探究(contextual inquiry)等。 (28)See Herzog,H.,"On Borrowed Experience:An Analysis of Listening to Daytime Sketches," Studies in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vol.9,no.1,1941,pp.65-95. (29)Bateson,G.,"Cultural and Thematic Analysis of Fictional Films," Transaction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vol.5,1943,pp.72-78. (30)Bateson,G.,"Cultural and Thematic Analysis of Fictional Films," Transaction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vol.5,1943,pp.72-78. (31)参见郭建斌:《独乡电视:现代传媒与少数民族乡村日常生活》,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李春霞:《电视与彝民生活》,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吴飞:《火塘·教堂·电视——一个少数民族社区的社会传播网络研究》,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8年;卿志军:《电视与黎族生活方式的变迁》,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3年;丁未:《流动的家园:“攸县的哥村”社区传播与身份共同体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 (32)参见丁未:《流动的家园:“攸县的哥村”社区传播与身份共同体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64页。 (33)Hoover,S.M.& Coats,C.D.,"The Media and Male Identities:Audience Research in Media,Religion,and Masculinitie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vol.61,2011,pp.877-897. (34)[日]藤竹晓:《电视社会学》,蔡林海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55页。 (35)郭建斌:《独乡电视:现代传媒与少数民族乡村日常生活》,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目录。 (36)李春霞:《电视与彝民生活》,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07-108页。 (37)[英]保罗·杜盖伊等:《做文化研究:索尼随身听的故事》,霍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91页。 (38)如“团年饭上玩手机 放下碗筷找同学 过年不要走过场”,2013年2月4日,华龙网http://cq.cqnews.net/shxw/2013-02/04/content_24106811.htm,2014年7月10日;“玩手机 餐桌上的‘别样’风景”,2012年11月24日,山西新闻网http://www.daynews.com.cn/sxwb/aban/04/1669347.html,2014年7月10日。 (39)杨善华、朱伟志:《手机:全球化背景下的“主动”选择——珠三角地区农民工手机消费的文化和心态的解读》,《广东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第168-173页。 (40)罗沛霖、彭铟旎:《关于中国南部农民工的社会生活与手机的研究》,杨善华主编:《城乡日常生活:一种社会学分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83-100页。 (41)曹晋:《传播技术与社会性别:以流移上海的家政钟点女工的手机使用分析为例》,《新闻与传播研究》2009年第1期,第71-77页。 (42)丁未:《流动的家园:“攸县的哥村”社区传播与身份共同体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283页。 (43)丁未:《流动的家园:“攸县的哥村”社区传播与身份共同体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200页。 (44)如在研究初期对部分出租车司机的车载电话和新媒体使用的调查就采用的是个别访谈法,参见丁未:《流动的家园:“攸县的哥村”社区传播与身份共同体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354页。 (45)如对出租车司机妻子们的ICT使用情况的调查就采用的是焦点小组法,参见丁未:《流动的家园:“攸县的哥村”社区传播与身份共同体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256页。 (46)丁未:《流动的家园:“攸县的哥村”社区传播与身份共同体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355页。 (47)特别需要说明的是,非浸入式诠释性探究只是在资料收集方式上对原生态情境不进行直接观察,而并不是放弃对原生态情境的考察和分析;它仍然可以通过访谈的方式来把握研究对象所处的日常生活情境。 (48)Serazio,M.,"The New Media Designs of Political Consultants:Campaign Production in a Fragmented Era,"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vol.64,2014,pp.743-7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