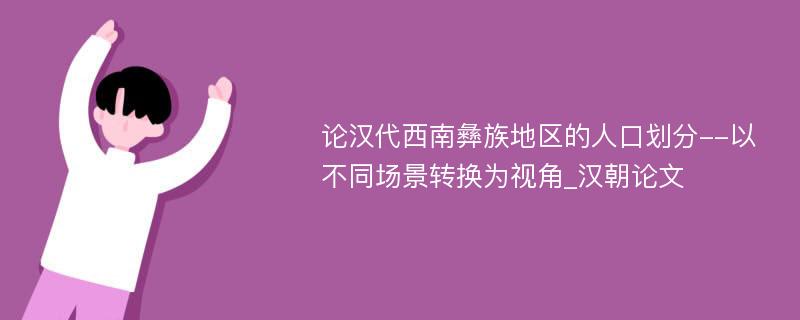
试论汉代西南夷地区的人群划分——以不同场景变换为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代论文,视角论文,试论论文,场景论文,人群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汉代西南夷地区自古部落众多,且各部落在地域分布、生计方式、族源习俗等方面各不相同。长久以来,对西南夷地区人群类别的探讨一直是汉代民族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其中,尤以对汉代西南夷史料中“夷”这一称谓的涵义与语境的讨论最为突出。
蒙默先生指出,汉代西南民族中除了“氐”、“羌”之外,还存在一个“夷系民族”①,这一观点为大多数从事西南民族史研究的学者所赞同或援引。当然,也有学者提出过不同意见,如李绍明先生认为古代西南民族主要属于两大系统,即氐羌族系与濮越族系,并没有一个夷族族系存在。但与此同时,李先生在论证夜郎之地民族族属时又认为“夷”可以用来具体指称氐羌族系的民族②。石硕先生主张在《史记》的语境中,“夷”是对西南各部落人群的泛称,而在《后汉书》和《华阳国志》中,“夷”才演变为一个明确的族属类别称谓,与“氐”、“羌”、“越”并列③。邹立波则认为在整个西南夷地区,“徼”都具有区别人群的作用④。总体来说,以往学界对汉代西南夷地区人群分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夷”之称谓的内涵及变迁、“徼”之人群划分功能两方面,研究场景多为徼内具体族别区分、徼内与徼外人群对比两种。对于其他场景(徼内各郡与徼内外作为整体,政治与非汉族类、文化)下西南夷地区的人群划分则关注甚少。
一 、“西南夷”、“徼外蛮夷”与“郡夷”
自《史记》首列《西南夷列传》后,以“西南夷”泛称汉代巴蜀西南的非汉族群并为之立传等做法为《汉书》、《后汉书》所沿袭。关于汉代“西南夷”称谓的涵盖之地,后世学者众说纷纭⑤。论者多从司马迁所记载的夜郎、滇等九个部落之分布或武帝至东汉明帝时汉朝在西南夷地区所设郡县之范围来确定“西南夷”囊括的区域。事实上,此“西南夷”之范围仅仅是不同时期汉朝所能掌控与了解的西南夷区域,并非时人观念中“西南夷”称谓适用之地区。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司马迁只是列举描述了西南夷众多部族中的九个较大部落,然后以“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概述之⑥。此总括之言为《汉书·西南夷传》所沿袭,到范晔著《后汉书·西南夷传》时,变为“西南夷者,在蜀郡徼外”⑦。此“蜀郡徼外”之“徼”当为“蜀郡故徼”⑧。显然,在两汉及南朝刘宋时期的史家看来,巴、蜀徼外的非汉族群均可被称为“西南夷”。此三史之《西南夷传》只是描述了不同时期史家对该地区的有限认知。当此区域内新的部族为人们所认识和了解后,便会被纳入到新的《西南夷传》中来。如不见于《史记》、《汉书》两书《西南夷传》的哀牢夷在东汉明帝时内附之后,为人们所知晓,关于哀牢的记载便出现在了《后汉书·西南夷传》中。此外,从三史将西南夷郡县区之外“徼外蛮夷”的内附、贡献、犯徼等史事均归入《西南夷传》来看,此类“徼外蛮夷”也被史家统称在了“西南夷”之内。很明显,在汉代,时人观念中的“西南夷”与政府有效控制的“西南夷”所指并非完全一致。三史所载史家观念中的“西南夷”指称对象的范围一直未变,即巴郡郡徼、蜀郡故徼之外的非汉族群⑨。而政府控制下的“西南夷”范围(即西南夷郡县区)则伴随中原王朝在西南的经营而有所变化,如西汉武帝置犍为等郡、东汉明帝置永昌郡等均将不同的西南夷部落纳入到了西南夷郡县区的范围。
在三史作者看来,“西南夷”涵盖之范围是以巴、蜀徼外来界定的。换句话说,巴、蜀之徼将“西南夷”与汉朝其他区域及人群分隔了开来。林超民等先生曾指出:“以前不少学者认为‘西南夷’是指中国西南地区的民族。其实,‘西南夷’的‘西南’不是中国的西南,而是巴蜀的西南。”⑩在这种情况下,巴郡郡徼与蜀郡故徼便具有了划分西南夷人群及地域的功能。此外,在西南夷地区未置郡县之前,巴郡郡徼、蜀郡故徼即是汉朝西南之边徼,分隔着郡县区与“化外”之区。此时,“西南夷”地区与巴蜀徼外“化外”之区、“西南夷”与“徼外蛮夷”两组概念均是重合的,且都由巴郡郡徼、蜀郡故徼定义之。在武帝经营西南夷之初,西汉便于夜郎及其旁邑等南夷地区置犍为郡,在邛、筰等西夷地区设“一都尉,十余县,属蜀”(11)。破灭南越后,武帝更是在西南夷地区大规模开置郡县,“乃以邛都为越巂郡,筰都为沈犁郡,冉駹为汶山郡,广汉西白马为武都郡”(12),以滇王之地为益州郡。永平十二年(69年),东汉明帝在哀牢夷内附之地的基础上设永昌郡。这些郡县的设置使得汉朝西南郡县区的范围大大拓展,巴郡郡徼、蜀郡故徼便不再是郡县区与“化外”之分界,此种分界之职能开始由西南夷地区沿边新设诸郡之“徼”来承担。然而,巴郡郡徼与蜀郡故徼定位“西南夷”之所在的功能却依然在历史中延续并发挥着作用。简言之,伴随西南夷地区的郡县化,当地出现了两种“徼”:巴郡郡徼、蜀郡故徼与西南夷诸郡之徼。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两种“徼外”:巴蜀徼外与西南夷诸郡徼外。一方面,在巴郡郡徼、蜀郡故徼之外,所有非汉族群均被称为“西南夷”,而不论其在西南夷诸郡徼内或徼外;另一方面,西南夷诸郡之徼则将西南夷划分为徼内蛮夷和徼外蛮夷(13)。此“徼外蛮夷”便特指西南夷地区尚未被纳入到汉朝郡县区的非汉族群。
在西南夷地区尚未设置郡县之前,该地区与汉朝郡县区隔以巴郡郡徼和蜀郡故徼,此时,西南夷整体上被视为“徼外蛮夷”。而伴随着郡县的设置、边徼的外扩,西南夷开始被分隔为徼内与徼外两个部分。因汉朝在西南夷地区的郡县设置是陆续进行的,受此影响,“徼外蛮夷”所指人群也因势而变。如前述武帝置犍为郡与西夷都尉、县之后,史载:“(西汉)除边关,关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牂柯为徼。”(14)原蜀郡故徼外的夜郎、邛、筰等部落被纳入到徼内。此时“徼外蛮夷”便用来指代沫、若水与牂柯江外的非汉部落,如尚未归附汉朝的滇、昆明等。待到武帝置益州等郡后,滇、昆明也被纳入到汉政权控制范围中来。之后,“徼外蛮夷”又出现在了武帝所置诸郡郡徼之外,如东汉永平十二年,“益州徼外夷哀牢王相率内属”(15)。而到明帝置永昌郡后,哀牢所居也成为汉朝之徼内。此后,“徼外蛮夷”称呼便又转移到永昌徼外的“蛮夷”身上。如和帝永元六年(94年),“永昌徼外夷遣使译献犀牛、大象”(16);永元九年(97年),“永昌徼外蛮夷及掸国重译奉贡”(17);安帝永初元年(107年),“永昌徼外僬侥种夷贡献内属”(18);永宁元年(120年),“永昌徼外掸国谴使贡献”(19),等等。《后汉书·西南夷传》中记载了东汉时期的一首歌谣:“行人歌之曰:‘汉德广,开不宾。渡博南,越澜津。渡澜沧,为他人。’”(20)关于这首歌谣的产生年代存在一些争议(21),但并不妨碍我们说明问题。此歌谣一方面宣扬汉朝开疆拓土的德行,另一方面也指出边境的拓展并没有消除边徼,边徼以外一直有“他人”的存在。换句话说,只要边徼存在,“徼外蛮夷”便不会消失。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两个结论:一是边徼决定着“徼外蛮夷”之所在。“徼外蛮夷”所指人群因边徼改变而发生相应变化;二是“徼外蛮夷”可以转换为“徼内蛮夷”。转换方式有两种:一是徼外蛮夷所在地域被纳入汉徼之内,前多已言及;二是徼外蛮夷进入徼内居住,如“安帝元初三年,郡徼外夷大羊等八种,户三万一千,口十六万七千六百二十,慕义内属”(22)。相对的,“徼内蛮夷”也可向“徼外蛮夷”转换。转换方式与上述两种方式相反。无论是徼内与徼外的划分,还是徼外蛮夷与徼内蛮夷的相互转换,均是由汉朝西南边徼决定的(23)。边徼的扩张与内缩、“蛮夷”的入徼与出徼都会导致徼内、外蛮夷所指对象发生变化。西南夷地区诸郡之徼成为该地区人群及地域的重要区分标志。
值得注意的是,在记载有汉代西南夷史事的史书特别是《后汉书》中经常出现“徼外”、“徼外夷”、“徼外蛮夷”等词语,却从未发现与其相对的“徼内”、“徼内夷”等称谓。这是由于史家对徼内、外的了解程度不一。邹立波曾对“徼外”、“徼外夷”在不同文献中的称谓形式进行过对比研究。他认为在《史记》、《汉书》、《华阳国志》中,“徼外”多概指地理方位,即与汉有别的“化外之区”,“徼外夷”则概称“化外之地”的蛮夷;而在《后汉书》中,“徼外”多使用在具体的某一蛮夷部族称谓前面,“徼外”、“徼外夷”之前则多添加有郡县等地名限定词(24)。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在汉朝经营西南夷之初,时人对西南夷徼外及徼外蛮夷的地理区位与族属情况所知甚少,便以“徼外”、“徼外夷”概称之(25)。到范晔著《后汉书》时,经过两汉对西南夷地区的开发治理,加上州郡政府和中央朝廷与“徼外蛮夷”政治往来的频繁,人们对徼外部落的认识和了解程度远非司马迁、班固时代所能比拟。于是,便产生了由具体郡县、族属限定的“徼外”和“徼外夷”称谓。而相比之下,虽然史家对徼内夷的族属情况也有一个深入了解的过程(26),但由于徼内为汉朝郡县区,徼内“蛮夷”从一开始便被置归到各个郡县,人们对其所处地理位置是非常清楚的。正因如此,史书中未见作为概称的“徼内”、“徼内夷”,却经常出现“郡夷”、“某郡(某县)蛮夷”等称呼,如“(熹平五年)益州郡夷叛,太守李颙讨平之”(27);“始元四年,益州蛮夷反”(28);“明年(元初六年),永昌、益州及蜀郡夷皆叛应之,众遂十余万”(29)等等。在以上诸例中,“蛮夷”均位于“徼内”,却被冠以比“徼内”更为精确的具体郡县等地名限定词。可以说,由于徼内明确的郡县建制,使得作为概称的“徼内”、“徼内夷”等词在汉代丧失了存在之语境。
“徼外蛮夷”与“郡夷”之异同从其各自称谓即可看出。“徼外”为“化外之区”,“郡”为汉政权辖域,这意味着两者有着不同的政治归属。然两者又同处巴郡郡徼、蜀郡故徼外,均位于汉代“西南夷”概念范围之内。在族类、文化上,他们都与中原汉人截然不同,因而均被称为“夷”。
二、“徼外夷”与“汉人”:徼内外的“夷”、“汉”之分
从非汉族类层面看,徼外夷与徼内郡夷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他们均被中原人视为“蛮夷”,只是居住地各有不同而已。邹立波指出:“‘徼’并不是族群的区分界线,实际上在‘徼之内’同样生活着蛮夷人群。”(30)不过,既然徼内、外蛮夷有着不同的政治归属,且这种归属以“徼”来分隔,这使得“徼”不可避免地带上了政治色彩。此外,不同的政治归属还会导致徼内、外华与夷的区分。在政治场景下,“徼”会自动生成一种分隔华、夷的功能(31),其最明显的表现便是“夷徼”、“蛮夷界”等词的出现。
关于汉代内、外郡的划分。三国吴人韦昭认为:“中国为内郡,缘边有夷狄障塞者为外郡。”(32)其将“边塞”径直称为“夷狄障塞”。类似的词语还有“夷徼”。“(张)嶷知奸计,以重赂使,使杀渠。渠死,夷徼肃清”(33)。此虽是晋朝人的记载,但因塞徼外居住着“蛮夷”而将塞徼称之为“夷徼”的做法恐怕是与前代一脉相承的。如东汉蔡邕就有“天设山河,秦筑长城,汉起塞垣,所以分别内外,异殊俗也。其外则分之夷狄,其内则任之良吏”之语(34)。在蔡邕看来,秦汉长城、塞垣的作用便是将夷狄隔绝于外。晋人崔豹亦有相似观点,其所著《古今注》在解释塞、徼时认为,“塞者,塞也,所以拥塞戎狄也。徼者,绕也,所以绕遮蛮夷,使不得侵中国也”(35)。这里将塞徼的作用直接挑明了。既然塞徼的存在是为了防止蛮夷入侵中原,那么称之为“夷狄障塞”、“夷徼”就不足为怪了。具体到西南地区,前述因夜郎、邛、筰等部落成为汉朝内臣,蜀郡故徼不再作为汉朝西南之外徼。充当“化内”与“化外”之分界的外徼往西、南扩张,“西至沬、若水,南至牂柯为徼”(36)。司马贞《史记索隐》引三国魏人张揖注曰:“徼,塞也。以木栅水为蛮夷界。”(37)此处,设于沬、若水与牂柯江上的外徼被张揖称为“蛮夷界”,用以分隔徼外被称为“蛮夷”的地域与人群,而“徼内”当然为“华夏”、“中国”之地。于是,在此场景中,原先位处蜀郡故徼之外的“蛮夷”(夜郎、邛、筰等)在外徼进一步向外扩展之后不再被视为“蛮夷”,即新扩之外徼成为新的“蛮夷界”。在此外徼的扩展中,夜郎等部落的族属、文化、居地等并未改变,唯一发生变化的是旧有蛮夷之地变成了汉朝郡县之区,该地域上的“蛮夷”在政治上归属了汉朝。显然,所谓“夷徼”、“蛮夷界”的产生与族属、文化等因素无关,夷徼内、外族群的华、夷身份是由其各自政治归属来决定的。在西南夷地区,许多非汉族群因处于徼内(划入汉朝郡县)而被赋予“华”、“汉”等身份。此时,“夷徼”、“蛮夷界”之外才是“蛮夷”,徼内夷则不再被视为“夷”。在《后汉书·西南夷传》与《华阳国志·蜀志》中,徼内莋都夷被称为“汉人”、“汉民”便是显例。
“莋都夷者,武帝所开,以为莋都县……元鼎六年,以为沈黎郡。至天汉四年,并蜀为西部,置两都尉:一居旄牛,主徼外夷;一居青衣,主汉人”(38),石硕先生认为此处“汉人”当作“‘汉朝直接控制之臣民’即‘汉朝统治区域之人’解,非今族属意义上的‘汉人’之意”。他进而指出“汉人”是相对“徼外夷”而言的“徼内夷”,即汉朝直接控制的原沈黎郡境内以筰都夷为主体的少数民族部落人群(39)。陈东则认为“汉人”除包括受汉朝统治的“西南夷”外,还应有撤郡之前来自中原的移民(40)。要了解沈黎郡的民族构成情况,我们需要对其郡县沿革做一番考证。
沈黎郡是在武帝所置莋都县的基础上设置的。在唐蒙出使夜郎并在南夷之地置犍为郡后,“蜀人司马相如亦言西夷邛、筰可置郡。使相如以郎中将往喻,皆如南夷,为置一都尉,十余县,属蜀”(41)。此“十余县”中便包含有莋都县。司马相如因上《上林赋》,“天子以为郎”(42)。在任郎官数年后,因唐蒙发遣吏民开通夜郎道引发巴蜀民众惊恐,武帝派司马相如入川问责唐蒙,事在《史记·西南夷列传》。有学者研究《上林赋》当作于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五月到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五月之间(43),即至早到建元六年,司马相如才被任命为郎官。其第一次出使西南夷当在建元六年之后数年。在司马相如此次出使完成使命回长安向武帝复命后,“唐蒙已略通夜郎,因通西南夷道……治道二岁……是时邛筰之君长闻南夷与汉通,得赏赐多,多欲愿为内臣妾,请吏,比南夷……天子以为然,乃拜相如为中郎将,建节往使……司马长卿便略定西夷,邛、筰、冉、駹、斯榆之君皆请为内臣”(44)。据文意分析,在第一次出使西南夷之后至少两年,司马相如再次被派往西南夷地区,并在此时“略定西夷”。但其时,汉廷在西夷地区并未置郡,而仅设一都尉、十余县隶属于蜀郡。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尉、县并未能延续到汉朝设置沈黎郡时期,“当是时,巴蜀四郡通西南夷道,戍转相饟。数岁,道不通,士罢饿离湿,死者甚众;西南夷又数反,发兵兴击,秏费无功。上患之,使公孙弘往视问焉。还对,言其不便。及弘为御史大夫,是时方筑朔方以据河逐胡,弘因数言西南夷害,可且罢,专力事匈奴。上罢西夷,独置南夷夜郎两县一都尉,稍令犍为自葆就”(45)。“独置”南夷县、尉说明西夷原有的尉、县在此时均被罢除了。莋都县也不例外。据《史记·平津侯传》记载,“元朔三年,张欧免,以弘为御史大夫”,即西夷尉、县被罢除是在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自此一直到南越覆亡后,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廷才在当地置沈黎郡,尔后天汉四年(公元前97年)撤沈黎郡并入蜀郡,置都尉。根据以上分析,莋都夷所在地在武帝时期先后经历了设县、废县、置郡、撤郡、设尉等过程。另从上面年代分析可知,该地从设县到废县只经历了短短几年,废县十五年后才得以置郡,从置郡再到撤郡又只有十余年的光景。短短三十年间,该地行政建制几经变革,这意味着汉廷对当地的统治并不稳固。其中,元朔三年的罢县便是因为西南夷“数反”。元鼎六年撤郡说明当地并不具备独立设郡的条件,而转而设置带有较强军事色彩的郡尉也表明汉廷希望以此加强对当地部落的控制。事实上,这种中央政府与当地部落势力的较量在武帝之前便已开始了(46)。此时的莋都夷无论在族属、文化还是政治认同上并未能融入汉族及中原政权。
在时断时续的郡县设置下,原沈黎郡内居住的民众当以筰都夷为主,也应有少量移居至此的来自巴蜀及中原的移民。在《后汉书》、《华阳国志》两书中,该地民众被统称为“汉人”、“汉民”。而上述可知,莋都夷在沈黎郡撤除时并未能融入汉族,其表现出来的民族性依旧十分强烈。由此,“汉人(民)”之“汉”绝非族属之涵义,而当如石硕等先生所主张的作“汉朝统治区域”解。因两都尉辖地直接承续沈黎郡而来,郡内民众在此间并未脱离汉朝统治区域,所以其民众得称“汉人”或“汉民”。显然,此处“汉人(民)”称呼具有明显的场景性,只会出现在徼内汉朝统治区民众与徼外化外之区民众对称的特殊场景中。此时,政治归属成为判断这两类人群的标准,徼内夷便与徼内汉族民众一起被称为“汉人(民)”。当场景发生变化时,如同属于汉朝统治区域的徼内夷与中原移民对称时,徼内夷便不再被视为“汉人(民)”,而是恢复“夷”的称号。例如建初元年(76年),哀牢王类牢反叛后,“肃宗募发越巂、益州、永昌夷汉九千人讨之。明年春,邪龙县昆明夷卤承等应募,率种人与诸郡兵击类牢于博南,大破斩之”(47)。徼内“夷”、“汉”同时出现,此处的“汉”便仅指代“诸郡兵”或当地汉族民众了。诸如此类的还有“夷汉歌叹”(48)、“夷汉甚安其惠爱”等(49)。这几例中的“汉”均带有明显的族属色彩,而“夷”则指徼内夷无疑。很明显,对于同处汉朝统治区域的人群,政治区分不再起作用,此时族属、文化区分便被重新提及。因此,那种因“徼内夷”在与“徼外夷”对称时被称为“汉人”,便认为他们已从“西南夷”概念中剥离出来,在天汉四年之后乃至东汉以来,均被中原视作“汉人”的说法是值得商榷的(50)。至少在天汉四年以前,徼内莋都夷仅仅是居于汉朝统治区域而已,且汉朝对当地的控制并不稳固,当地部落的民族特性仍旧非常强烈。他们并未能从“西南夷”概念中脱离出来,当场景转入徼内时,莋都夷依然被中原称做“夷”。在《后汉书》和《华阳国志》中,作为徼内祚都夷组成部分的“旄牛夷”、“青衣道夷”均被冠以“夷”之称号(51),其依然被视为夷人部落。
这种因场景转换导致的身份变化在其他西南夷族群中也会发生。在政治场景下,西南边徼被称为“夷徼”,而“夷徼”之外的人群才被视为“蛮夷”,徼内西南夷部落被划入“中国”,称为“华”、“汉”。而当场景转入徼内时,西南夷诸部依旧被视作“蛮夷”,即政治上的“汉人”身份,并未能改变族属、文化上的“夷人”形象。在不同场景与划分标准下,“华”、“汉”等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均具有收缩可变性。由于政治、族体、文化身份的不一致,使得徼内夷实际上处于“华”与“非华”、“汉”与“非汉”之间。徼内夷的这种身份特点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不无关系。如上述沈黎郡位于蜀之西,实际上兼理着“徼外夷”和“汉人”(徼内夷汉)的事务,是蜀郡与“徼外夷”之间的重要缓冲区,也是界于“化内”与“化外”之过渡地带(52)。对于处于这一地带的“蛮夷”人群来说,其身份也介于徼外夷与中原移民之间,因不同的场景与人群划分标准可被分别归入“汉人”或“夷人”序列。
三 徼内的“夷汉”、“民夷”与“夷民”
石硕先生通过与《史记》对比,发现《华阳国志》、《后汉书》中的“夷”的涵义由泛称变为了确指,“夷”成为与“氐”、“羌”、“越”相区别的另一族属类别的人群。他认为这是由于东汉之后中原人对西南夷部落族属面貌、人群系统有了比武帝时期更为深入的认识(53)。石先生的观点对我们理解西南夷地区的族属面貌、“夷”之涵义变化无疑是很有启发的。不过,笔者发现《华阳国志》、《后汉书》中依旧存在很多“夷”作为泛称的例子。与《史记》中对西南地区非汉人群的“西南夷”、“西夷”、“南夷”等泛称不同,《华阳国志》、《后汉书》中具有泛称涵义的“夷”,总是以“夷汉”、“民夷”等称谓形式出现的。在“西南夷”等词中,“夷”是对整体非汉人群的称呼。关于“夷汉”、“民夷”等词中的“夷”、“汉”、“民”的具体涵义,前面论证徼内外“夷”、“汉”之分时已有提及,下面进行进一步分析。
《华阳国志》中出现有“夷汉”、民夷”二词的有以下几例:“郑纯……为益州西部都尉……纯独清廉,毫毛不犯,夷汉歌叹”;“(张翕)迁越嶲太守,夷汉甚安其惠爱”;“梓潼景毅为益州太守,讨定之。承丧乱后,民夷困饿,米一斗千钱,民皆离散”;“刘先主定蜀,遣安远将军、南郡邓方,以朱提太守、庲降都督治南昌县。轻财果毅,夷汉敬其威信”;“(孟)获等心服,夷、汉亦思反善”(54)等。“夷汉”、“民夷”二词分别用来指称益州、越嶲、南中等地域的民众。
《后汉书》中出现“夷汉”、“民夷”的有:建初元年(76年),哀牢王类牢反,“肃宗募发越巂、益州、永昌夷汉九千人讨之”;“汉中锡光为交阯太守,教导民夷”;“(刘)虞初举孝廉,稍迁幽州刺史,民夷感其德化”;“(张鲁)不置长吏,以祭酒为理,民夷信向”等(55)。二词分别指代越嶲、益州、永昌、交趾、幽州、汉中等地辖众。
由上可知,“夷汉”、“民夷”等称呼不仅用于汉代西南地区,在北边及汉中也有使用。在西晋时成书的《三国志》中,“民夷”一词使用更为普遍。除指代上述地域人群外,还有指西域者,如仓慈在敦煌太守任上,对前来贡献与互市的西域杂胡,“使吏民护送道路,由是民夷翕然称其德惠”(56);有指东南诸郡者,如魏文帝曹丕给孙权的策书中有“以君绥安东南,纲纪江外,民夷安业”之语(57)。总的来说,“夷汉”、“民夷”可以用来指称广大不同地域的民众。这说明二词中“夷”之涵义绝不是蒙默、石硕等先生所认为的西南“夷系民族”、“夷族”。即便在西南地区,也存在其他族属的部族,如“南中在昔,盖夷、越之地”(58)。而上述南中、益州西部等例中“夷汉”、“民夷”等称呼显然是对当地民众的总称,其中“夷”的涵义并不限定为特定“夷种”。
以上诸例中“夷汉”、“民夷”所指均是塞徼内某一地域的民众。“夷”与“汉”、“民”显然是不同的两类人。既然他们均处在塞徼内,显然此处之“汉”并非上述与徼外夷对称的带有政治意味之“汉”,“民”也绝非笼统的汉朝统治区域之民。这样,表示徼内“非夷”民众的“汉”、“民”两称谓便只可能是用来指代与“蛮夷”杂居之汉族民众。在汉代,汉族民众有时直接被称为“汉人”,此“汉人”之“汉”明显带有族属色彩。如班彪曾言:“羌胡被发左衽而与汉人杂处,习俗既异,语言不通。”(59)此外,我们还注意到《后汉书·西南夷传》所载章帝招募三郡夷汉平叛哀牢王类牢反叛一事在同书《章帝纪》中记载为:“永昌、越巂、益州三郡民、夷讨哀牢,破平之。”(60)一用“夷汉”,一用“民、夷”,显然,在范晔看来“民”与“汉”所指相同,可以互训。从字面意思上看,“汉”所指当为徼内汉族民众,而“民”则为纳入郡县统治的“编户齐民”。西南夷诸部归附汉朝之后,其民众依旧由原有部落首领统辖,并不入郡县户籍。而当地汉族民众则要在汉朝严格的户籍制度控制之下,向政府服役纳税。正如凌纯声先生所说,“凡隶郡县之民,尽为华夏,部落之众,多属蛮夷”(61)。对于西南夷地区来说,此处隶属之“隶”,当为户籍隶属,而非政治隶属。因徼内“蛮夷”自成部落,不入户籍,“编户齐民”与“徼内汉族”便所指相同,“汉”、“民”得以互称。
古永继先生在分析秦汉时期迁徙到西南地区的中原移民对当地民族构成的影响时指出:“两汉时的史料中常见区分汉人与当地民族的‘郡兵’、‘郡民’及‘夷汉’、‘民夷’、‘夷民’、‘吏民’、‘夷夏’之类记载,说明外来移民已有相当数量,并在当地的民族构成及社会活动中占有了重要的地位。”(62)其实,根据上述分析,“夷汉”、“民夷”等称呼大量出现在东汉及其以后时期,使用范围也不仅限于西南地区。这些称谓可以用来泛指边疆或其他多民族杂居地区的所有民众,其产生有着一定的历史背景。自武帝开置西南夷诸郡后,经过长时间的迁徙实边和当地移民人口的自然繁衍,加上王莽乱后大批中原人士迁入西南夷地区避难等原因,使得东汉时期西南夷地区外来汉族移民数量大增。当地以“夷”人为主的民族构成因而发生改变,以“夷汉”、“民夷”总称当地民众的现象便开始盛行起来。而在东汉中后期之后的其他地区,如西域、幽州、关陇等,无不是因为汉族与其他边疆少数民族的双向或单向迁徙导致“夷”、“汉”空前杂居,使得以“夷汉”、“民夷”概括当地民众成为可能。其中,“夷”用来泛指塞徼内的非汉族群。
值得注意的是,在汉代,“夷”除了用于泛称非汉族群整体外,还被用来确指“夷族”内部的个体身份(63)。在“夷”、“汉”错居地区,“夷族”的王被称为“夷王”,侯被称为“夷侯”,普通民众则为“夷民”。如《隶续》载有汉“繁长张禅等题名碑”碑文,题名名单中出现有白虎夷王谢节、资伟二人,夷侯李伯宣等九人,夷民李伯仁等六人。洪适描述其碑文布局为:“首行云长蜀郡繁张君讳禅字仲闻,其次题掾曹十人及三民姓名。次横之首行云夷浅口例掾赵陵字进德,次夷侯九人邑长三人。第三横邑君三人夷民六人,后云凡世八戸造,末有四行高出两字,题白虎二夷王及丞尉名字。最后两行及其下一横字画差小,似是纪事之辞,惟夷王谢、资数字分明,余皆不可读。”碑文中同时出现了“夷王”、“夷侯”、“夷民”等称呼,且均用来指称具体个人。在此,笔者尤其关注“夷民”一词。在题名名单中还同时出现有“民杜孔茂、民杨伯章、民□伯著”三人(64)。很显然,“民”与“夷民”所指不同。前述“民夷”概念时笔者曾指出“民”、“夷”代指两种不同身份的人群,“民夷”即为二者的合称。当“夷民”意为“夷”、“民”二者合称时,其涵义与“民夷”相同。如前述民夷事例“(张鲁)不置长吏,以祭酒为理,民夷信向”(65),在《华阳国志》中记载为:“学道永信者,谓之鬼卒。后乃为祭酒。巴、汉夷民多便之。”(66)“民夷”与“夷民”均可用来泛指汉中、巴郡等地民众。然在题名碑中,“夷王”、“夷侯”、“夷民”同载,显然分别代表夷族内部不同身份,“夷民”当作“夷族”内部普通民众解。另外,“夷民”与“邑君”同列,而“邑君”为少数民族归义汉廷后所封之官,其所治之民为本族民众(67)。此亦可证明“夷民”的身份。
以“夷民”称呼“夷族”普通民众的现象是值得关注的。该称呼直接表明了“夷民”的双重身份,在族属类别上非“汉”为“夷”,在政治归属上为汉朝之“民”,其身份要异于碑文中同时出现的杜孔茂等三“民”。史书中也有称徼内“蛮夷”为汉朝之民的例子,如益州计曹掾程苞曾对灵帝说:“板楯忠勇,立功先汉,为帝义民。”(68)板楯蛮在这里便被视为汉朝“义民”。此二处“夷民”、“义民”之“民”当理解为汉朝所统辖的民众,与《后汉书》称莋都夷为“汉人”之意相同。特别要引起注意的是,“繁长张禅等题名碑”之“夷民”姓名刻于为汉朝官吏所立石碑之上且与地方官吏同列,板楯蛮因在政治军事上听命于汉朝而得称“义民”,两例均带有强烈的政治归属色彩。惟其如此,“徼内之夷”才可得称汉朝之“民”。洪适在论及题名碑产生之缘由时认为,“东都益部郡县夷汉错居,此必蜀郡太守有德政,繁县夷人共立此碑,尊其官吏,故书之前列”(69)。如此说成立,则“夷民”之身份也为夷人自身所认同。繁县在两汉时期均隶属于蜀郡,程苞所谓板楯蛮则分布在巴郡。在汉代,巴、蜀二郡与西南夷地区均为益州刺史(部)辖域,郡情郡貌一致,无论是在民族的构成及分布还是在对徼内非汉民众的管理上都极为相似。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种“夷民”称呼在西南夷地区也是存在的。
四 余论
通过以上对徼内外各种与“夷”相关之称谓的研究可知,在不同场景与语境下“夷”之内涵与所指称的人群是各不相同的(70)。在汉代巴郡郡徼、蜀郡故徼之外,所有非汉部族均被泛称为“西南夷”,而不论其处于西南夷地区各郡徼内还是徼外;以西南夷各郡边徼为界,“西南夷”又被划分为“徼外蛮夷”与各郡“郡夷”;在政治场景中,边徼具有划分华(汉)、夷的职能。此时,徼内夷连同汉族民众一起被称为“汉人”、“汉民”,“夷”则用来指代徼外人群;在族类、文化对比的场景中,徼内、外非汉族群都被视为“夷”,只有徼内汉族民众才被称为“汉”人;在“夷汉”、“民夷”及“夷民”等称呼中,“夷”均指代塞徼内之“蛮夷”。不同的是,在“夷汉”、“民夷”称呼中,“夷”与“民”是两种相互区别的群体,而在某些“夷民”称谓中,徼内夷本身便被视为汉朝之“民”。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在西南夷地区三类人群(徼外夷、徼内夷、徼内汉族民众)中,史家对徼内夷这一群体的划分最为灵活。在不同场景中,徼内夷可以和另外两类人群自由结合或分化而形成新的群体及称谓。这种情况的出现是由三种因素决定的:一是徼内夷特殊的地理区位。徼内夷位处巴郡郡徼、蜀郡故徼与汉朝西南夷诸郡边徼之间。而此两种“徼”都是史家区分西南夷人群的重要标识,其均会对徼内夷的归属产生作用;二是徼内夷本身的双重归属。徼内夷处于汉政权控制范围内,政治上归属于汉朝。在族类、文化上其又与徼内汉族民众存在较大差异,而与徼外蛮夷有着更多相同或相似之处。这种归属的矛盾性从徼内夷被称为“郡夷”、“夷民”上可得到很好体现;三是“汉”、“民”等词具有多种涵义,每种涵义涵盖的人群各不相同。正是在这些因素作用下,徼内夷的身份便在夷与非夷、汉与非汉、民与非民之间徘徊。而徼内夷身份的不确定性,加上不同时期汉朝西南边徼的扩张与收缩,使得在不同场景下,史家对西南夷地区人群的划分显得颇为复杂。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以上各种与“夷”相关的称谓均是史家对“西南夷”不同群体的客位描述,而并非各群体的“自称”。用美国人类学家郝瑞教授的话说是“国家语境”并未进入各族体的“地方语境”(71)。不过,史家对西南夷地区的人群划分也并非主观行事。上述人群划分的场景与标准在汉代西南夷地区都是现实存在的,即史家对该地区人群的分类是建立在客观事实基础之上的。因此,虽然这种人群分类是一种客位视角,却能让我们更为深入地了解汉代西南夷地区的人群面貌。此外,这些分类还会有助于我们理解郡县建制下该地区不同人群自我认同的变化动因及其特点。在汉代,部落的繁杂和族属的多样性使得西南夷地区的族群认同异常复杂。而郡县的设置、中原移民的移入不可避免地会对各部落原有的族群及政治认同产生影响。王明珂先生甚至认为:“在近代成为少数民族之前,西南各地人群之‘族群性’是相当多元而复杂的。各个族群间以及汉与非汉之间,在认同与文化表征上都有些模糊的边界。”(72)如王先生认为的,在西南夷地区不仅存在各族群彼此的族群认同,因为中原势力(郡县政府、中原移民)的“在场”,还会出现汉与非汉的区分与认同。史家对不同场景下西南夷地区人群的划分昭示了“徼外夷”、“郡夷”、徼内汉族民众三类群体在地理、政治、族属、文化等方面的亲疏异同。以“郡夷”为中介,三者通过以上诸方面相互关联。在现实交往中,当某一方面的相似性被强调时,其他方面的差异会被忽略掉,不同群体便可以此相互结合形成相同的政治或族群认同,从而决定自己的现实举动。这一点在“郡夷”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关于该地区的族群及政治认同情况,请容撰文另述。
收稿日期 2011—01—22
注释:
①蒙默:《试论汉代西南民族中的“夷”与“羌”》,《历史研究》1985年第1期。
②李绍明:《夜郎与巴蜀相关民族的族属问题》,《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③石硕:《汉代西南夷之“夷”的语境及变化》,《贵州民族研究》2005年第1期。
④邹立波:《汉代西南之“徼”与“徼外”夷——从文献记载看史家对西南夷人群的区分》,《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9年第3期。
⑤可参阅前揭邹立波《汉代西南之“徼”与“徼外”夷——从文献记载看史家对西南夷人群的区分》一文相关综述。
⑥(11)(12)《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991、2994、2997页。
⑦《后汉书·西南夷传》,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2844页。
⑧蜀故徼与蜀徼是两个不同概念。在武帝经营西南夷之前,该地“及汉兴,皆弃此国而开蜀故徼”(《史记·西南夷列传》,第2993页)。此时,西南夷地区与蜀郡隔以蜀故徼,蜀故徼也便是蜀郡之边徼。尔后司马相如出使西夷,在邛、莋等部落居地置“一都尉,十余县,属蜀”(《史记·西南夷列传》,第2994页)。天汉四年(公元前97年),武帝又将沈黎郡并入蜀郡。这些举措均会导致蜀郡范围及其边徼发生变化。然而,在三史《西南夷传》中,司马迁、班固、范晔均将后来居地并入蜀郡的莋都夷等纳入到“西南夷”中来叙述。而这些部落先前均是位于蜀郡故徼之外的。这意味着,决定汉代“西南夷”地理范围的是蜀郡故徼,而非随时代发展而有所变化的蜀徼。
⑨《后汉书·西南夷传》仅言西南夷在蜀郡徼外。这当是因为两汉政府主要是以蜀郡为基地开发西南夷,与西南夷地区的交通也多以蜀郡为通道。所谓“巴蜀徼外”在很大程度上即是“蜀郡徼外”。
⑩林超民、秦树才:《秦汉西南夷新论》,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编:《秦汉史论丛》(第8辑),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页。
(13)关于这一点,前引邹立波论文已有详细分析。由于两种“徼”与“徼外”的存在,为阐述方便,本文中所谓“徼”与“徼外”如不作特殊说明,均指西南夷地区各郡之郡徼与郡徼之外。此外,史书中同时出现有“徼外蛮夷”与“徼外夷”,均泛指徼外非汉族群。在本文行文中,两词会随相应史料而选择使用,不再说明。
(14)《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第3047页。
(15)《后汉书·明帝纪》,第114页。
(16)(17)《后汉书·和帝纪》,第177、183页。
(18)(19)《后汉书·安帝纪》,第207、231页。
(20)(22)《后汉书·西南夷传》,第2849、2853页。
(21)《后汉书·西南夷传》系此歌谣于明帝时,即哀牢内附汉置永昌郡之时。任乃强先生认为有误,他指出汉武帝所置嶲唐、不韦二县便已在澜沧江外,此歌不应待明帝时才有。参见常璩著,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88页。
(23)邹立波《汉代西南之“徼”与“徼外”夷——从文献记载看史家对西南夷人群的区分》一文认为范晔划分徼外蛮夷与徼内蛮夷的标准在于该部落“是否已被纳入到汉政权的控制范围之内,是否受汉文化的熏陶,甚至看它是否肩负起缴纳赋税的职责”。这一观点恐过于片面。从我们的分析可知,史家对徼内、外蛮夷之划分完全由“蛮夷”与汉徼的位置关系来决定。至于文化熏陶、缴纳赋税等都只是成为徼内蛮夷之后才有的特点。
(24)邹立波:《汉代西南之“徼”与“徼外”夷——从文献记载看史家对西南夷人群的区分》。邹文对于“徼外”一词的文献对比分析精辟入理。但邹氏将《后汉书》中“徼外”与具体部族、郡县相连所形成的称谓形式视为“徼外”一词出现的新的涵义,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实际上从《史记》到《后汉书》,“徼外”指代“化外”区域和“蛮夷”的涵义一直未变。只是由于时代发展,史家对徼外地理、部落的了解进一步深入,“徼外”开始与具体郡县、族属连称。这种“徼外”称谓形式只是使得其所指代的区域与人群变得更加精确而已,“徼外”一词本身的涵义并未发生变化。
(25)成书于东晋时期的《华阳国志》例外。全书仅见三处“徼外”,一处“徼外夷”,全为泛称。这种情况的出现当是因为常璩是以“本土人”视角描述西南郡县内地理、族类和先贤士女等,对徼外的关注自然不如以中原视角书写的正史(《后汉书》)。在中原视角下,史家较多关注徼外部族与中原政权的政治关系,热衷于宣扬中原王朝的仁德远播,对“徼外”记载的详细程度要高于地方史志。
(26)石硕:《汉代西南夷之“夷”的语境及变化》。
(27)《后汉书·灵帝纪》,第337页。
(28)《汉书·杜周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662页。
(29)《后汉书·西南夷传》,第2853页。《华阳国志》亦有相关记载,但系此事于元初四年(117年)。参见常璩著,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四《南中志》,第237页。
(30)邹立波:《汉代西南之“徼”与“徼外”夷——从文献记载看史家对西南夷人群的区分》。
(31)朱圣明:《秦汉华夷观念与民族意识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09年,第19~23页。
(32)《汉书·宣帝纪》,本始元年诏注文,第241页。
(33)常璩著,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三《蜀志》,第210页。
(34)张烈点校:《两汉纪·后汉纪》卷二四《灵帝纪第二十四》,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465页。
(35)崔豹:《古今注》卷上,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第7页。
(36)(37)《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第3047、3048页。
(38)《后汉书·西南夷传》,第2854页。《华阳国志》中“主汉人”写作“主汉民”。参见常璩著,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三《蜀志》,第142页。
(39)石硕:《汉代的“筰都夷”、“旄牛徼外”与“徼外夷”——论汉代川西高原的“徼”之划分及部落分布》,《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
(40)陈东:《汉代西南夷之“徒”及其去向》,《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9年第6期。
(41)(45)《史记·西南夷列传》,第2994、2995页。
(42)(44)《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第3043、3046~3047页。
(43)龙文玲:《司马相如〈上林赋〉、〈大人赋〉作年考辨》,《江汉论坛》2007年第2期。
(46)司马相如曾言及莋都夷所在地在“秦时尝通为郡县,至汉兴而罢”(《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第3046页)。此外,《华阳国志·蜀志》有“高后六年,城僰道,开青衣”的记载,任乃强先生补注为“高后六年开为青衣县”。任先生甚至认为“蜀王与张若皆已开青衣”。他指出高后六年重开青衣说明当地民族不易接受封建制度,民族特性顽强,所以开置郡县后屡次反叛。上引分别参见常璩著,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第141、198、143页。
(47)《后汉书·西南夷传》,第2851页。
(48)常璩著,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十中《广汉士女》,第561页。
(49)常璩著,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十上《先贤士女总赞论》附《巴郡士女赞注残文辑佚》,第557页。
(50)陈东:《汉代西南夷之“徒”及其去向》。
(51)(53)石硕:《汉代西南夷之“夷”的语境及变化》。
(52)石硕:《汉代的“筰都夷”、“旄牛徼外”与“徼外夷”——论汉代川西高原的“徼”之划分及部落分布》。
(54)常璩著,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第561、557、237、240、241页。
(55)《后汉书》,第2851、2462、2353、2436页。
(56)《三国志·仓慈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12页。
(57)《三国志·吴主传》,第1122页。
(58)常璩著,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四《南中志》,第229页。
(59)《后汉书·西羌传》,第2878页。
(60)《后汉书·章帝纪》,第135页。
(61)凌纯声:《中国边疆民族与环太平洋文化》,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9年版,第137页。
(62)古永继:《秦汉时西南地区外来移民的迁徙特点及在边疆开发中的作用》,《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
(63)此“夷族”代指非汉族群,与作为具体族属类别的“夷系民族”、“夷族”有别,下同。
(64)洪适:《隶续》卷十六《繁长张禅等题名》,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681册,第855~856页。洪适认为此碑书写时代为东汉时期。
(65)《后汉书·刘焉传》,第2436页。
(66)常璩著,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二《汉中志》,第72页。
(67)陈直:《汉晋少数民族所用印文通考》,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编:《秦汉史论丛》(第1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46页。
(68)常璩著,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十下《汉中士女》,第601页。
(69)洪适:《隶续》卷十六《繁长张禅等题名》,第856页。
(70)由于时代关系,在《后汉书》、《华阳国志》的成书年代,史家对西南夷地区人群的了解远甚于《史记》、《汉书》的作者。因而,不同场景的存在与有意识的人群区分在《后汉书》、《华阳国志》中显得更为突出。本文研究的主要史料也来源于二书。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群区分到后汉时期才产生,有些区分场景在西汉时已经形成(巴蜀徼外),而为后世所沿用;另有一些场景下的人群区分在班马时代出现萌芽倾向(徼外),到《后汉书》、《华阳国志》时代则完全表露出来。
(71)郝瑞:《再谈“民族”与“族群”——回应李绍明教授》,《民族研究》2002年第6期。郝瑞教授将中国学术和政治传统中对不同族群的归类视为一种“国家语境”。
(72)王明珂:《由族群到民族:中国西南历史经验》,《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年第11期。
标签:汉朝论文; 中原文化论文; 汉朝文化论文; 汉族文化论文; 史记论文; 后汉书论文; 汉人论文; 中原论文; 武帝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