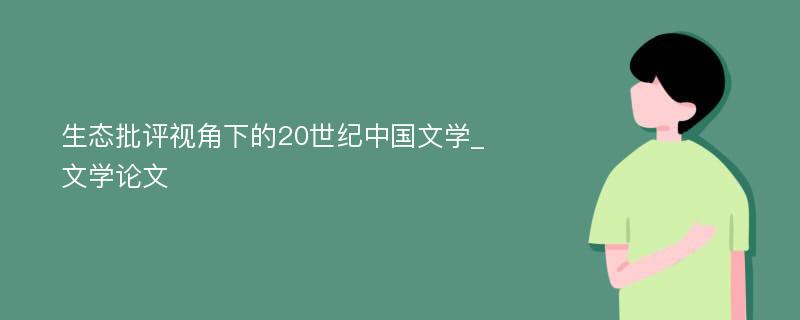
生态批评视阈中的20世纪中国文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文学论文,批评论文,生态论文,世纪论文,视阈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根本上说,人类的生态问题肇端于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产生与发展。在追求物质财富的资本主义价值观驱动下,近代西方社会生产实践(其直接结果是快速的都市化进程)最终必然瓦解人类亘古以来的自然经济体系,导致严重的生态掠夺与生态破坏。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交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52页。)更重要的是,从文化层面看,生态危机是西方之人与自然二分的传统自然观的现实产物,其深层动因来自过于自信的科学主义哲学观和启蒙主义社会历史观。因此,解决人类的生态问题不但需要通过改变社会生产方式来改善生态环境,而且还需要建立一种崭新的生态伦理观,自然观和美学观。1948年,利奥波德提出了著名的“大地伦理学”,这标志着西方思想界对传统自然伦理观的深刻重审。利奥波德明确指出:“大地伦理学改变人类的地位,从他是大地——社会的征服者转变到他是其中的普通一员和公民。这意味着人类应当尊重他的生物同伴而且也以同样的态度尊重大地社会。”(注:利奥波德:《大地伦理学》,叶平译,《自然信息》1990年第4期。)这种崭新的生态伦理思想对于人和自然的传统关系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在此之后,詹奇、卡普拉、拉塞尔、萨克塞和罗尔斯顿以不同的方式阐述了现代生态伦理和哲学思想,提出“以生命为中心”的机体主义自然观,从而为解决人类的生态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法则。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东方的思想传统具有丰富深厚的生态伦理资源,无论是儒家“参赞化育”的机体主义、道家“道法自然”的深层生态学,还是佛教对生命及其生存环境的关切,都隐含着深刻的现代生态伦理精神。(注:详见冯沪祥:《人、自然与文化——中西环保哲学比较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余正荣《中国生态伦理传统的诠释与重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毫无疑问,东西方的生态智慧共同为全球性的环境问题提供了基本的精神资源。
建立在生态哲学及伦理学基础上的生态批评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发端于美国的文学和文化批评倾向,它将文学、文化批评与生态学结合起来,体现了批评家在全球性生态危机浯境下试图构建一种生态诗学体系的深刻动意。美国生态批评的主要倡导者和发起人彻丽尔·格罗特费尔蒂将生态批评界定为:“探讨文学与自然环境之关系的批评。”(注:Cheryll Glotfelty & Harold Fromm,the Ecocriticism Reader:Landmarksin Literary Ecology,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1996,p.xviii.)这个定义已为大多数学者普遍接受。进而言之,生态批评是从自然和生命的角度研究文学与环境的关系,通过发掘文学文本中人与自然、生命本相等生态涵义,从而推动当代的生态文学写作,最终超越人本主义的自然观,在人与环境之间确立一种“新型的伦理情谊关系”(注:霍尔姆斯·罗尔斯顿:《环境伦理学》,杨通进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随着文学中生态人文主义倾向的日益彰显,生态批评也逐渐成为文学批评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当代西方生态批评正以其坚定的生命伦理批判立场和日益完善的学科理论向“生态诗学”(ecopoetics)趋进。
在我国,生态批评也开始引起学界广泛的注意:一方面是西方有关著述的译介和出版,另一方面是对中国传统文学的生态伦理学的发微与重审。运用生态批评审察20世纪中国文学,发掘潜隐于文学史主潮之下的生态主义流脉,对于整体把握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复杂性与悖论性,对于全面揭橥20世纪中国文学的精神传统无疑具有深刻意义。
无人能否认,启蒙、救亡及政治革命等社会历史价值是20世纪中国文学进程的根本动力。肇端于19世纪末的20世纪中国文学自发生伊始就有效地承担了历史的责任,自觉地追求“人的解放”、“社会解放”和“民族解放”等社会功利性目标。这种主导性文学选择的合理性和必然性自不待言,它是20世纪中国文学主动迎取近代以来民族自强和阶级解放等历史中心动作的见证。由此,百年中国文学体现了与20世纪中国现代精神传统的内在一致性,即科学进化的历史观、竞争对抗的自然观和大同理想的社会观。(注:关于20世纪中国精神传统,参见高瑞泉:《中国现代精神传统》,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版。)无论是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鲁迅的“改造国民性”主题和五四文学的个性主义,还是30-40年代文学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救亡话语,或是当代中国的诸种文学主潮,无疑表明20世纪中国文学所着重关注的是社会历史价值的实现,这也是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根本要义。在20世纪中国现代精神传统中,尊重万物生命、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价值观显然被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合理地遮蔽了,它既不可能构成与社会历史价值对话的姿态,也当然难以进入主导性文学视野之中。20世纪中国文学一方面自觉地担负起社会启蒙和民族救亡的历史使命,以显在的方式投入历史变革和民族灵魂铸造的进程,这对于有着“感时忧国”传统的中国文学而言当然是题中应有之义,但另一方面它又不时向历史发出一种逆向性的叩问,并潜隐着一种超越社会历史功利主义的生命忧患,表达了对于自然生命的深切关注,体现出尊重生命、关爱自然的生态智慧。从生态批评切入,我们不难看到20世纪中国文学在历史价值和生命价值之间的艰难选择,并借此发见其自身的伦理及美学缺失。
一
文学史家将20世纪中国文学的起端定于19世纪的最后几年确是大有深意存焉,正是此时期的思想文化初步形成了新文学的社会历史基本价值取向。对于传统士人而言,有限的土地和人口趋向无限增长的紧张,历来是难解的问题,但对于信仰历史进化论的维新派知识分子来说,生态问题从未成为真正的问题。他们相信人类能够不断凭借理性和科学的力量征服自然界,最终实现社会的进步,增进人类的幸福。谭嗣同在《仁学》里以近乎神奇的笔调表达了对于人类的进步及征服自然界的坚定信念:
今人灵于古人,人既日趋于灵,亦必集众灵人之灵,而化为纯用智纯用灵魂主人。可以住水,可以住火,可以住空气,可以飞行往来于诸星诸日,虽地球全毁,无所损害,复何不能客之有!(注:《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66-367页。)
进步的信仰一旦确立,就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历史作用。这种把人作为自然征服者的科学主义价值观成为20世纪中国现代精神传统的主脉,致使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价值观长期以来难以立足。我们很容易从谭嗣同的乐观信仰和后来家喻户晓的“人定胜天”口号中发现20世纪科学主义的强大思维逻辑。同时,由于近代中国社会政治变革的迫切需要,近代知识分子把达尔文那种旨在描述生物圈里“自然选择”的进化论转换成人类社会领域的竞争法则,并试图借此达致启蒙的历史目标。正如本杰明·史华兹所言:“严复对达尔文在生物学上的贡献或他那关于鸽子变种的煞费苦心的学术论文并不感兴趣,他全神贯注的只是含有将达尔文原理运用于人类行动领域的那些内容。”(注:本杰明·史华兹:《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叶凤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0-91页。)在严复那里,“物竞天择”的进化论似乎与生态系统的内在规则全然无涉,而是人类社会与民族的竞争铁律,对此梁启超也深有同感:“人也者,与他种动物同,非竞争则不能进步”,“竞争之结果,劣而败者灭亡,优而适者繁殖,此不易之公例也。”(注:《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众所周知,鲁迅早期正是从严复、梁启超的社会进化论中寻求有效的历史启蒙资源的。这种注重社会人事、轻视自然生态的历史功利主义倾向无疑是20世纪中国现代性追求的重要表征,它与科学主义一起成为制约20世纪中国生态主义发展的两大基本力量。
历史的吊诡也正由此产生。当谭嗣同、严复和梁启超等人高歌科学乐观主义和历史乐观主义的同时,王国维和章太炎则以相反的悲观主义理路对科学和历史的目的论预设进行了深刻的质疑和反思,他们独特丰富的思想成果既是20世纪中国反现代性精神的直接来源,同时也为20世纪中国生态主义提供了难能可贵的哲学理据。王国维认定,现代文明根本是分裂、破碎的。这与科学乐观主义和历史乐观主义的看法迥然不同。“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实是道出了历史与生命之间的分裂性悖论。与叔本华的悲观主义一脉相承,王国维亦意识到作为意志与表象世界的苦难本质:由于芸芸众生的意志是不可遏止的盲目冲动,生命必然陷于无尽的苦痛。王国维由此生发出深沉博大的生命悲悯,他曾作了一首诗《蚕》表达这种悲天悯物的生命情怀:
蠕蠕食复患,蠢蠢眠又起。口腹虽累人,操作终自己。丝尽口卒屠,织就鸳鸯被。一朝毛羽成,委之如敝屣。专专索其偶,如马遭鞭捶。……茫茫千万载,辗转周复始。(注:《静安诗稿·蚕》。)
尽管这种悲观哲学的隐喻与生态主义相去甚远,但它确超越了历史进化论的限定从而具有生命反思的独特气质。章太炎则以“俱分进化论”表明了他对于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与现代社会的悖论的深刻认识。所谓“俱分进化论”,简言之,就是说人类历史发展在道德方面是善恶并进,在生活方面是苦乐并进。章太炎借此对人类片面追求幸福生活的物质主义价值观大加痛砭,并直接针对历史进化论。他说:“人求进化,必事气机。欲事气机,必先穿求石炭(指开采煤矿,笔者注)。而人之所需,本不在此,与其自苦于地窟之中,以求后乐,曷若樵苏耕获,鼓腹而游矣!”(注:《四惑论》,《章太炎全集》第四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54页。)可以看出,章太炎虽然仍从人类的苦乐角度去考量,但他无疑是极力反对人类为求进化而滥采自然资源的。值得注意的是,章太炎的文化哲学思想既来自卢梭的精神滋养,同时有着明显的道家和佛学渊源,其具有近代特征的生命反思的“俱分进化论”因而也必然与中国传统生态伦理血脉相连。显然,20世纪中国生态主义之发轫期就已同时具备两种精神资源——西方的生态自然观和中国生态伦理传统。
二
20世纪中国文学的生命关怀正是在科学进化的历史乐观主义与生命反思的历史怀疑主义之间的张力场中呈现出来的。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天平上,科学与历史的砝码显然重于生态与生命的砝码。然而由于中国现代化进程本身的悖论性发展,同时也由于西方那种质疑启蒙主义的现代生命哲学和生态哲学的引入以及中国生态伦理传统的创造性转换,20世纪中国文学因而也具备了生态主义的基质。
对于五四新文学而言,那种合目的性的启蒙主义价值得以前所未有地张扬,科学进化的历史观、竞争对抗的自然观和大同理想的社会观成为当时主导性的精神坐标。应该说,在民困邦危的历史语境下,文学对思想启蒙、社会改造和民族救亡的积极介入与承担,这种崇高而悲壮的景观我们不应轻言否定。然而也应看到,在统摄于历史功利性要求的主潮下面同时也隐藏着一股异质性的思想潜流。文学中的生态智慧正是在历史的缝隙里萌生的。泛神论、浪漫主义诗学与佛禅伦理和美学是20年代中国文学之生态意识的主要思想来源。在五四作家那里,泛神论一方面为他们打破一切偶像崇拜的个性解放提供了哲学依据,使自我表现获得了独特的表达方式;另一方面也使他们超离了竞争对抗的自然观,从而在泛神的自然中领悟和谐统一的生态大美。如果说郭沫若《女神》的泛神论因其浓重的自我生命色彩而对自然之魅有所遮蔽,那么,同样崇拜歌德的宗白华却对大道贯注的自然天地有着深切的体悟。他在读罢歌德的《游行者之夜歌》一诗后透露出体认自然生机的精神胸襟:“歌德这位近代人生与宇宙动象的代表,虽在极端的静中仍潜示着何等的鸢飞鱼跃!大自然的山川在屹然峙立里周流着不舍昼夜的消息。”(注:《歌德之人生启示》,《宗白华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9页。)冰心、王统照则是通过采撷泰戈尔泛神论的“信仰之华”来表达“自然直感”的,他们的小诗或小说所体现出来的自然万物相互融摄的观念何尝不是对机械自然观的一种强力的反拨?美国生态思想家唐纳德·沃斯特说:“浪漫派看待自然的方式基本上是生态学的,也就是说,它考虑的是关系、依赖和整体性质。”(注:唐纳德·沃斯特:《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侯文蕙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81页。)工业和科学的发展,人类文明的进步,造成了对抗性的加剧及人与自然关系的疏远,因而那种源于卢梭“回归自然”论和谢林有机论自然哲学的浪漫诗学为生态主义提供了可贵的美学营养。19世纪美国作家梭罗的浪漫主义和生态主义的双重实践无疑表明了这一点。五四作家所接受的浪漫主义诗学尽管也发挥着个性解放的启蒙功能,但其显明的大自然崇拜倾向使之最终脱离启蒙主义的历史限定,从而向整体性的生态智慧趋近了。郁达夫是在卢梭思想启发下批判资本主义的,他所痛心疾首的不仅仅是资本家对工人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而且是其对大自然的巨大破坏:
资本主义,更是自然的破坏者。好好的一处山水,资本家用了他们的恶钱来开发,或在山水隈中,造一个巨大的Tank,或在平绿的原头,建一所压人的工场。……所以资本主义和艺术是势不两立的。(注:郁达夫:《艺术与国家》,《文艺论集》,上海光华书局1926年版,第78页。)
郁达夫通过这种卢梭式的激愤之辞表达了对生态环境的关注和对自然生态的深切之爱。郁达夫是一个天生的自然崇拜者,正如他所宣称的:“对大自然的迷恋,似乎是我从小的一种天性。”(注:郁达夫:《忏余独白》,《忏余集》,上海天马书店1933年版,第16页。)徐志摩的自然崇拜倾向也与西方浪漫主义有机自然论密切相关,他是从卢梭、华兹华斯、雪莱和泰戈尔那里寻取田园诗的创作动力的。乔纳森·贝特认为:
在浪漫主义的诗学中,诗不仅在语言,而且在自然中发现,而且是人与自然世界进行感情交流的方式。田园诗具有永恒的力量,是一种常青的语言。(注:Jonathan Bates,From Red to Green,Green Studies Reader,P.169.)
我们从20年代那些深受西方浪漫主义影响的作品中不难寻找到有机自然论的深刻印证。另外,佛教“法界缘起”的整体宇宙观、众生平等和尊重生命的价值观是中国生态伦理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对当代人类的生态理论与实践至今仍具有不可忽视的独特意义。近代以来的佛学复兴从根本上说是历史功利主义的必然要求,宗教改革家们不断强化佛教救济世道的社会功能显然是为了与时代的呼唤同步共生,20年代太虚和尚呼应五四文化启蒙运动而进行的一系列宗教革新便是明证。然而,佛学在迎取历史功利性要求的同时,其固有的生命伦理观念也激发出巨大的生态主义智慧,为人类超越自身狭隘利益的局限性提供了一种远离迷妄的深远洞识。20年代中国文学因而也具有了启蒙个性主义之外的另一种思想形态。许地山从自身生命无常的感受中提升出扩及万物的悲悯胸襟,他的散文名篇《蝉》以广大无边的慈悲心去体认有情世界生命同体的佛法精神,这种“饶益一切众生”的生态伦理观在丰子恺那里更为突出。丰子恺可谓“悲智双运”,他用生命慧观旷观一切众生,用同情眼光爱护一切众生,其《护生画集》和《缘缘堂随笔》足以成为现代中国文艺中发扬佛教生态伦理智慧的典范性文本。佛教这种对众生生命的尊重无疑是20世纪中国文学生态主义极为重要的传统精神来源之一。禅宗“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的直觉观照方式有助于文学将宗教体验引向一种审美体验,使自然山水具有了万象同化为一的生命整体意识,使之包含了生命与环境一体性的生态美学意趣,废名正是在这种自然观的启悟下营造其平淡悠远的小说意境的。值得注意的是,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生态主义的重要思想来源,无论是泛神论、浪漫主义诗学还是佛禅伦理美学,它们往往是相互融摄、交相为用,借此呈现出生机勃勃的理论活力,对20年代以后的文学生态主义也是影响深远。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那种旨在实现国家富强目的的“科学”被提升为关乎人类进步的价值信仰,甚至成为意义世界的基础。科学信仰一方面奠立了20世纪中国现代性的基石,推动着民族自强的诸种历史进程,另一方面又发展成有着独断论色彩的唯科学主义。20年代标志着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公开分裂的“科玄论战”尽管以“玄学鬼”的失败告终,但由此而来的柏格森哲学却很快被知识界广为熟知。与机械进化论截然不同的是,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把生命冲动视为人类和整个自然所共有的本质,一切生物以直觉绵延的力量体现着生命的同一,并不断生成和创化。显然,柏格森这种与科学主义分庭抗礼的哲学思想已经为博大的生命关怀敞开了一条路径。事实上,20年代科学主义大潮之下同时也潜伏着生态人文主义的流脉,这相当耐人寻味。法布尔《昆虫记》的译介显然是当时科学主义信仰的产物,这部昆虫学著作所运用的真理性认识方法无疑支持了“五四”以来思想界的科学价值取向。然而,正如论者所言,《昆虫记》“最重要的是,整部作品充满了对生命的关爱和对自然万物的赞美”(注:秦颖:《〈昆虫记〉汉译小史》,《读书》2002年第7期。)。在中国第一个介绍《昆虫记》的周作人确是从中体认了科学知识之外的万物一体之生命同情心:“我们看了小说戏剧中所描写的同类的运命,受得深切的铭感,现在见了昆虫世界的这些悲喜剧,仿佛是听说远亲的……消息,正是一样迫切的动心,令人想起种种事情来。”(注:周作人:《法布耳〈昆虫记〉》,《晨报副镌》1923年1月26日。)随后,周建人、贾祖璋运用法布尔式的散文笔调写作了一系列生物小品,他们在传播科学知识的同时也揭出“生命的真实细节的美”,从而表达了对生命的敬畏和关爱。
从世界范围看,人类生态问题的产生与工业革命所导致的都市化运动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工业的发展,人口大规模向城市集中,城市性质也由政治、军事、宗教型向工商、贸易经济型转化。都市化进程一方面冲击着传统的自给自足的乡村田园经济,使城乡对立日益尖锐;另一方面又伴随着物质财富的扩张而导致了和谐优美的自然环境遭到严重的破坏。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叶,以上海为中心的现代都市的成熟标志着中国都市现代化发展“黄金时代”的到来。此时期的上海既是政治革命、阶级斗争的策源地,是文化资源的集散地,同时也成为田园主义者的众矢之的。尽管上海的都市化发展客观上推动了现代中国的工业化和商业化进程,但那种通过技术与资本来追逐物质财富的生产方式必然动摇了人与自然的古老关系,必然侵蚀着乡土中国的自然生态。在现代都市物化世界里,乡土中国“古雅的诗意”荡然无存。对此,就连长期浸淫都市文明的刘呐鸥也深有体会,他借小说主人公对到上海来寻找古朴诗意的西方人声称:“你所要求的那种诗,在这个时代是什么地方都找不到的。诗的内容已经变换了。”(注:刘呐鸥:《热情之骨》,《刘呐鸥小说全编》,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39页。)l933年,“生态伦理之父”利奥波德出版了《野生动物管理》一书,孕育了意义深远的“大地伦理”的理论,同年,中国文坛上著名的京派与海派论争也悄然展开。尽管京派与海派之争并非直接指向生态问题,论争的焦点也多集中于文学态度或艺术取向,但究其实质,它反映了乡村与都市两种经济体系制约下的伦理、美学等领域的尖锐冲突,其蕴含的生态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作为京派的代表作家,沈从文的意义不但在于他以城乡对照的文学形式对都市文明展开道德批判,更重要的是他建构了一种独特的“边疆生态学”。沈从文的“边疆生态学”是在地处偏隅的湘西世界里展开的,汉苗杂居边远山区的生命自在状态、楚地神巫文化的余韵以及晋人武陵寻胜的诗情孕育于远离尘嚣的自然山水之中,其和谐、优美而又充满神性的边疆生态构成了30年代都市批判最有效的伦理及美学动力。事实上,这种“边疆生态学”已经成为20世纪文学生态主义的一种重要的存在方式,近年来西藏、云南生态旅游题材作品之方兴未艾无疑证明了这一点。沈从文的生态自觉还体现于对生命自然有机体的深刻认识:“自然既极博大,也极残忍,战胜一切,孕育众生。蝼蚁蚍蜉,伟人巨匠,一样在它怀抱中,和光同尘。”(注:《烛虚》,《沈从文全集》第12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9页。)在沈从文的价值观里,生命是至高无上的尺度:“我是个对一切无信仰的人,却只信仰‘生命’。”(注:《水云》,《沈从文全集》第12卷,第128页。)在“边疆生态学”和生命价值观的烛照下,沈从文以其独特的自然山水观照和生命关怀而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中最饱含生态智慧的少数作家之一。沈从文对20世纪中国文学生态写作的贡献是非常丰富的,当另文专述。
40年代战时中国文学是以民族救亡和民族解放为指归的,相对于波澜壮阔的时代政治风云,自然生态问题当然难以进入主流文学的视野之中。然而,40年代中国文学同时又呈现了前所未有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仅有的一次直接参与的世界性战争,它使吾族置身于跟整个人类命运休戚相关的境遇。战争一方面造成了中国作家颠沛流离的苦难经验,另一方面又成就了这种人生经验的描述者和升华者。40年代文学在文化整合的意义上凸现了文学的生命哲学追求,引领人们看向事物的更深处与时间的更远处。对存在与生命的关注成为40年代中国作家的一种精神导向,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在20世纪中国文学生态意识的形成过程中,40年代开始在国内译介的海德格尔哲学思想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海德格尔认为,人类的技术统治着一切,取代了思想,以致如今人们面临的是一个几乎没有神性的时代,于是思的任务只能是尽可能揭示技术时代的本质以为神性重临作准备。海德格尔正是通过对诗之神性的把握而接近生态主义的:“诗并不飞翔凌越大地之上以逃避大地的羁绊,盘旋其上。正是诗,首次将人带回大地,使人属于大地,并因此使他安居。”(注:海德格尔:《人,诗意地安居》,郜元宝译,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第93页。)40年代冯至正是在海德格尔启示下以神性的眼光发现了“无名”的自然山水——
我是怎样爱慕那些还没有被人类的历史所点染过的自然:带有原始气氛的树林,只有樵夫和猎人所攀登的山坡,船渐渐远了所剩下的一片湖水,这里,自然才在我们面前矗立起来,我们同时也会感到我们应该怎样生长。山水越是无名,给我们的影响也越大;……(注:冯至:《山水·后记》,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7年版。)
冯至的《十四行诗》,无论是《我们准备着》、《我们站立在高高的山巅》,还是《深夜又是深山》,均带着对自然的神性之思,表达了生命在大自然敞开的深层领悟,这无疑昭示着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学的生态关怀达到了一种应有的哲学深度。
三
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近代以来民族自强和阶级解放等历史性要求的最终实现。新政权在强化政治意识形态的同时,一方面把工作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另一方面开始大力推动工业化进程,从而在整个社会形成了战天斗地的历史乐观主义精神。向着明确历史目标并统摄于阶级政治的生产斗争不相信“增长的极限”,以开天辟地的气魄挑战着大自然。显然,在富国强邦的历史要求制约下,生态问题理所当然地被完全漠视了,马寅初“人口论”的境遇无疑证明了这一点。人与自然关系的丰富性被化约为主客冲突的二元对立,盎然生命流衍的大自然成为征服与改造的对象。从历史上看,这种基于生产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单向度历史选择既创造了惊天动地的人间奇迹,也营造了荒诞离奇的神话。在那个时期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大跃进”显然是一个典型的标志,它基于历史乐观主义和政治热情把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夸张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此时期的文学或者遵循着典型化法则去反映历史的必然进程,或者讴歌新时代征服自然、改造社会的伟绩。“五四”以来作为生态主义重要精神资源的泛神论、西方浪漫主义(主要是长期以来被称为“消极浪漫主义”的一脉)、庄禅伦理美学以及现代主义渐渐丧失其存在的合法性,人与自然丰富的精神性联系同样被简约了,在作家的诗化的抒情那里,山水和自然众生最多成为政治性“比德”的隐喻。60年代散文勃兴,从1960年到1963年出版的四十多部散文集,单从集子的名称,我们不难发现作家的“大自然”情结。(注:参见陈顺馨:《1962:夹缝中的生存》,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09页。)然而这些山水自然题材的散文与二三十年代的小品迥然不同,它们显然赋予了山水自然一种关乎“世道人心”的政治性内涵或道德隐喻,冰心和丰子恺的作品概莫能外。冰心的《海恋》依然承袭着早期对大海的那种泛神论式的礼赞笔调,但“曲终奏雅”,文章结尾把自己恋晦的情感升华为反帝的呐喊。曾以佛的悲悯呼吁护生的丰子恺写出了动物题材作品《阿咪》,在表达生命关切之后不忘揭示猫“助人亲善、教人团结”的社会功能。至于杨朔的《荔枝蜜》、《茶花赋》等描写自然风物的作品,其刻意的政治性“比德”则已是众所周知的。无疑,从生态批评的角度切入,我们同样也可以窥见那个时期中国文学的某些规范性特征。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广泛存在于社会各阶层的“新时期”意识,其核心是以“科学、民主”为内容的对于“现代化”的热切渴望。(注: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25页。)城市化进程的展开、科学精神的倡导和个性主义的张扬成为此时期“现代化”渴求的方向标。新时期文学及时地反映了这一激动人心的历史进程:城市与乡村的冲突被上升为“文明与愚昧的冲突”(注:季红真:《文明与愚昧的冲突》,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现代城市已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社会概念,它还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文化概念——它是一种崭新的生活方式”(注:李书磊:《都市的迁徙》,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文学想像中的城市成了瞻望现代化目标的情感触媒;科幻小说的勃兴也表明了近代以来所崇尚的科学乐观主义的历史性回归;“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潮流则突出了人道主义的价值观。在向现代化迈进的时代精神的作用下,文学着重关注的是社会变革、历史反思和人们的内心悸动,已日渐显露的生态问题也因之被遮蔽了。在1977年至1985年的文学作品中,我们很难找到比较完整的自然山水描写,更遑论那种质疑现代化进程的整体性生命关怀了.这确实是耐人寻味的。现代化憧憬和人道主义的历史惯性使文学具有了一种科学理性的品格。此时期的文学创作典型地体现了启蒙现代性的历史维度。
进入80年代中期之后,思想界既极力宣扬启蒙现代性价值,呼唤走向现代化的历史变革,同时也已经开始意识到现代化进程可能带来的生态问题。1984年开始陆续出版的《走向未来》丛书就收有两种关于人类生态问题的著作:米都斯《增长的局限——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困境的研究报告》以及根据F.卡普拉《物理学之道》编译的《现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另外,罗马俱乐部创建者奥·佩西的名著《未来一百页》和池田大作与佩西的对话录《二十一世纪的警钟》以及戴维·埃伦费尔德的《人道主义的僭妄》也相继出版。这些著作描述了人类的生态困境,力图对人类的发展前景作出正确评价,并不约而同地呼吁重新把握人与自然这一最基本的问题。此时期也开始出现了关注自然生态环境的纪实作品(如徐刚的《伐木者,醒来!》)。80年代中国文学及时作出了审美及文化的回应。肇始于1985年的文化寻根是当代中国文学在现代化的历史驱动下,在全球化文化背景下对现代性作出的反思,这种反思在历史和美学的双重意义上,达到了一种深度。尽管寻根文学对启蒙现代性的反思主要是在民族文化或地域文化的层面上展开的,但现代化进程本身的悖论性问题又被重新提出来了,人与自然丰富的精神联系也获得了进一步的确认。寻根文学的外来文化资源显得相当复杂,但不能忽视的是西方生态哲学的启示。“自然的发现”无疑是寻根文学中最具有审美价值的主题意蕴。寻根作家试图超离城市文明进步的轨迹,纷纷发现了属于自己的自然生态地域:“贾平凹以他的《商州初录》占据了秦汉文化发祥地的陕西;郑义则以晋地为营盘;乌热尔图固守着东北密林中鄂温克人的帐篷篝火;张承志激荡在中亚地区冰峰雪原之间;李杭育疏导着属于吴越文化的葛川江……”(注:季红真:《历史的命题与时代抉择中的艺术嬗变——论“寻根文学”的发生与意义》,《忧郁的灵魂》,时代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尽管这些作家观照自然生态地域的内在动机差别很大,而且多限于文化层面上的兴趣,但他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视是显而易见的,他们不但使边疆生态学、浪漫主义和庄禅伦理美学恢复了固有的理论生机,为当代中国文学生态主义的真正形成提供了哲学及文化人类学的资源,而且已经涉及生态危机、大地生命伦理等关键性问题。如李杭育的《最后一个渔佬儿》触及环境污染和资源枯竭问题,张承志的《黑骏马》、《金牧场》等作品以审美理想主义的激情完成了草原生命伦理的信仰仪式。毫无疑问,在中国文学生态主义的形成过程中,80年代的寻根文学具有特别的意义,它一方面接续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学关于生命与自然的沉思,另一方面对90年代自觉的生态文学写作也有不可忽视的启示意义(如贾平凹近期小说《怀念狼》就存留着明显的寻根印迹)。
20世纪90年代是中国文学生态主义的成熟期。在经济全球化和国内发展市场经济的背景下,“技术中心化”和消费主义成为90年代最深刻的危机症候,作为保证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生态保护因而日益引起各方面的重视。应该说,90年代之后,生态问题才作为一个真正的现实问题被提出来。如果说80年代思想界对生态的关注尚限于零星地译介西方生态伦理哲学著作,而且这些思想成果难免被淹没于声势浩大的启蒙话语之中,那么,90年代生态伦理哲学的译介和著述则显示出其整体系统性和现实针对性,并逐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许多西方生态理论代表作也陆续出版(注:此时期译介的西方生态哲学著作有詹奇的《自组织的宇宙观》、拉塞尔的《觉醒的地球》、萨克塞的《生态哲学》和沃斯特的《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等;国内此方面的论著有李章印的《自然的沉沦与拯救》、余正荣的《生态智慧论》和余谋昌的《生态伦理学》以及冯沪祥的《人、自然与文化——中西环保哲学比较研究》等。),这些著作大大丰富了当代中国生态主义运动的理论视野。值得一提的是,90年代思想界对生态哲学的重视与后现代主义思潮有着密切的关系,后现代主义那种质疑启蒙现代性和试图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运思无疑为生态主义提供了解构的逻辑方式,另外,此时期蔚为大观的海德格尔思想也使生态主义获得了文化哲学的支持。伴随着90年代知识谱系的全面转型,生态主义终于成为一股与当代技术主义与消费主义分庭抗礼的力量,其反思人类历史行为、重建人与自然关系的观念体系蕴涵着巨大的理论活力,其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导向也正深刻地影响着当代诸种文化抉择乃至社会实践。90年代生态主义写作是在政府和民间的双重支持下进行的,文化传播界也为之辟出可贵的生存空间(如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以“关爱我们共同的家园”为题编辑出版了生态文学作品“碧蓝绿文丛”)。90年代自觉的生态主义写作主要体现为以下两方面:一是生态报告文学的兴盛。这些报告文学作品直面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危机,揭露人类对自然的破坏,表达了一种强烈的生态忧患。被称为“中国环境文学之父”的徐刚孜孜不倦地关心人类的生存环境,其纪实作品如《中国,另一种危机》、《守望家园》(六卷本)、《地球传》、《长江传》运用大量事实和数据直击当代中国的生态危机,详尽的资料融贯着凝重的历史思考,洋溢着诗意的抒怀,因而成为生态报告文学的翘楚。其他如马役军的《黄土地黑土地》、江浩的《盗猎揭密》等报告文学也产生了较大的反响。这些作品涉及了当代中国生态问题的各个方面,具有震聋发聩的现实警醒意义。二是作为纯文学形态的生态文学的真正出现。在此之前,文学生态主义往往寄植于自我表现的抒情、地域文化的探寻或生命追索的哲理玄思之中,其确定的精神内涵常被他者遮蔽而显得相当含混。而90年代的生态文学则直接切入生态题材,突出地表现人类的生态困境,揭示了人与自然的冲突以及所包含的复杂性,并试图找寻出生态危机解决之途。如果说80年代贾乎凹和张炜之阐发人与自然丰富的精神联系意在探询民族文化的根脉,其自然生态关怀是附着于文化寻根主题的,那么,他们90年代的创作则凸现了生态主义的思想意蕴。贾平凹的《怀念狼》尽管仍残留着文化寻根的痕迹,但那种挖掘传统文化精义的动机已大大减弱,代之的是对作为物种的人与动物之间互存共生关系的深刻审视。在这部小说里,猎狼行为并不是人征服自然的体现,而是被视为自然生态中一个物种和另一物种之间的共生与互证。小说通过展现禁捕所造成的人与狼的物种退化,表达了环保主义时代生态问题的深刻悖论。张炜的《柏慧》以海德格尔式的诗性立场确立了“大地”的形而上意义。主人公从葡萄园来,参与了各种文明活动之后,又回归葡萄园,寻求“大地”的保护,这喻示着人与万物都返回了自身,并在大自然这一母体里建立起一个和谐的世界。在这个意义上,张炜的道德理想主义与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学”有着深刻的一致性。事实上,90年代许多知名的纯文学作家(如李国文、刘恒和郭雪波等)纷纷加入各类生态文学写作,作品数量也相当可观(单是“碧蓝绿文丛”散文卷就收录了二十多位作家的一百多篇生态小品),由此可见生态主义已成为90年代中国文学一股不可忽视的潮流。
在处于世纪之交的1999年,有两个文学现象对于中国生态文学写作而言无疑是意味深长的。一是由《天涯》杂志推出的刘亮程散文所引起的轰动效应,二是湖北作家胡发云的小说《老海失踪》所引出的不尽话题。在民间与官方之间,在作家与批评家、读者之间,生态主义成为一种超乎政治、经济、伦理和美学的共同价值观而被广泛认同。刘亮程的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超越了城乡对立的道德价值判断,以一种博大圆融的胸襟表达了他对这个人畜共居的村庄和大地的感激,对一切自然万物众生的尊重和理解。“任何一株草的死亡都是人的死亡,任何一棵树的夭折都是人的夭折,任何一粒虫的鸣叫也是人的鸣叫。”(注:刘亮程:《一个人的村庄》,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在经济功利主义和技术主义甚嚣尘上的时代里,这种饱含着万物同体的生态智慧的质朴文字能引起普遍的共鸣,这似乎也表明了一种崭新的伦理美学原则正在崛起。胡发云的中篇小说《老海失踪》发表之后立即在读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被誉为“把深刻的生态伦理的思想性和保护生态主义者形象塑造在一起,在中国当代文坛率先创造出了以保护生态为精神旨归的人物形象”(注:李瑞林:《寻找新的“栖息地”——〈老海失踪〉访谈录》,《森林与人类》1999年第7期。)。这篇小说首次以生态保护者为主人公,它以寻找生态主义者老海为线索,直趋“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主题,痛斥现代文明进程中人类的自私、贪婪和狂妄,表达了敬畏自然、敬畏生命的生态主义价值观,无论是在伦理还是在美学上,其对新世纪中国生态文学写作的预示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正如学者所言:“在中国现代性强烈变革现实,与传统决裂的诉求中,也有可能包含着反思现代性的那些思想意识”,“它们是以非常隐蔽而微妙的形式存在于宏大的历史叙事之下的,因而,那些看上去微弱的痕迹就包含着更为深刻有力的韧性。”(注:陈晓明:《现代性与文学研究的新视野》,见陈晓明主编:《现代性与中国当代文学转型》,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3页。)以生态批评的视角审察20世纪中国文学,我们既看到其表现历史中心动作的巨大叙事威力,同时也窥见其中存在着生态主义这种德里达所谓的隐蔽的“踪迹”(trace)。毫无疑问,作为反思历史和科学等现代性价值的生态主义丰富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思想及美学维度,对新世纪中国文学在生态意识、人与自然关系的价值取向上也具有前瞻性的启示意义。
标签:文学论文; 科学论文; 中国文学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生态文化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艺术论文; 启蒙思想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自然观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