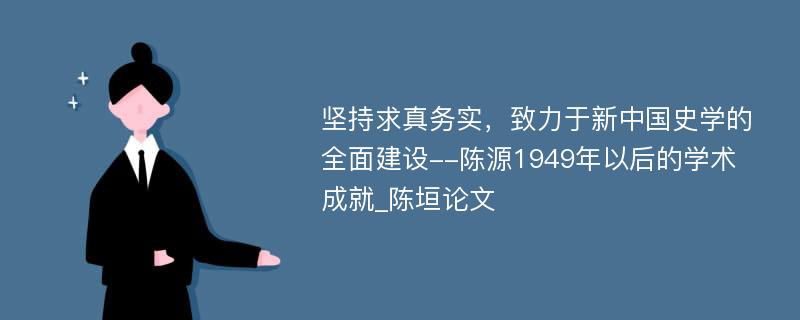
坚守求真理念 致力新中国史学整体建设——陈垣1949年之后的学术建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建树论文,新中国论文,理念论文,学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陈垣(1880-1971),广东新会人,著名史学家、教育家。他一生著述宏富,在元史、宗教史、历史辅助科学等诸多领域具有开拓之功,建树卓越。他治学独树一帜,视野博瞻,考镜精微,创获丰硕。1949年之前,陈垣力作迭出,见重史林,享誉国际,故而学界对于陈垣的学术成就的研究和评论也大都集中于此。相比较而言,学界对1949年后陈垣的学术建树,研讨却十分薄弱,而这不仅是全面评价陈垣个人学术成就的一个缺环,也关乎如何看待陈垣等一大批老一辈史学家在新中国建国后17年间的治学作为,因而是中国当代史学史研究的重要问题。
一、陈垣早年史学研究的根本精神
有的学者认为,陈垣“1949年后除了整理修订旧著外,基本上没有在史学方面再撰新著”[1],甚至在与陈寅恪的对比中,认为陈垣因为晚年服膺毛泽东思想,“学术生命自不得不中途顿折,乃至突然而止”[2]。这种观点简单地把有无大部头的史学专著,作为评价陈垣后期学术成就的标准,有欠公允。况且,陈垣1950年已经70岁,学者于古稀高龄之后,著述减少,能够算做瑕疵吗?对于,一代史学大师,不必苛求其连续不断地新撰专著,更重要的是看他是否坚持精当的治学路径和发扬了学术的根本精神。
陈垣从文献学入手,探得治学门径而自学成家。1917年,他发表《元也里可温考》(后修订改称《元也里可温教考》),得到海内外学界的瞩目。其后,他又陆续发表《元西域人华化考》、《二十史朔闰表》、《中西回史日历》等力作,更是享誉于中外。及至20世纪40年代,先后撰成《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通鉴胡注表微》等大著作,史学成就更上一层楼,产生了深远的学术影响。
陈垣的学术研究能获得空前成功,与其独特的治学方法息息相关,他毕生从事文献考据和历史考据,认为“考证为史学方法之一,欲实事求是,非考证不可”[3]。历史考据无疑是陈垣学术成就的主体部分,《元也里可温教考》、《元西域人华化考》等成名之作,都是历史考据著述。但陈垣的历史考据是建立在宽阔、坚实的文献学基础之上的,其治学本来就是从目录学入门,十二三岁时即按《书目答问》来索求自己需要阅读之书,后来买到《四库全书总目》,则用为治学门径,据此线索泛览群书,逐步打下治学的根基[4]14-15。《中国佛教史籍概论》、《敦煌劫余录》、《四库书目考异》、《明末清初教士译著现存目录》等等著述,均为历史文献考证的硕果,他始终在历史文献的清理和考证上孜孜以求,不断探讨。
历史考证的精确与否,不仅需要广采史料,还需要旁通年代、目录、版本等历史辅助学科知识。陈垣认为,“苟欲实事求是,非有精密之中西长历不可”[5]。他完成《二十史朔闰表》、《中西回史日历》、《史讳举例》、《校勘学释例》等文献学撰述,这些都是通过钩沉史料、稽考文献取得的学术成果,并且成为进一步研究历史的得力工具,嘉惠史林,泽被深远。
陈垣学术研究能取得巨大成就,与其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深沉的爱国情怀密不可分。早在青年时代,陈垣就有参政的经历,其目标是谋求国富民强之道。他从政几近十年,目睹当时政界混乱和腐败,于是弃政治史,致力于教育工作与学术撰著。在日本侵占中国的年代,他坚守民族气节,闭门著书,撰成《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中国佛教史籍概论》、《通鉴胡注表微》等重要史著,字里行间充满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尤其可贵的是他对求真、如实的史学准则始终坚守不移,绝不因自己的思想情绪而在史实上有所轩轾,并不因政治的理念改换个人进行历史考据的治学路径。假如暂时撇开上述著作中隐含的爱国思想,仅就其中的历史考证内容而言,亦为极为精湛的杰作。
综上所述,早在1949年之前就成为著名史学家的陈垣,已经形成自己的治学路径和学术精神,其要点可概况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陈垣的学术造诣建立在坚实的文献学基础之上,不仅时时坚持进行文献学方面考订、整理与研究,而且编辑《二十史朔闰表》等文史工具书,这种繁难的史学基础性建设,表现了陈垣自受辛劳、嘉惠他人,对整个史学界作出奉献的治学宗旨。
第二,历史考据学在陈垣先生全部学术成就中,居于主体与核心的地位,这是陈垣的学术特长之所在。陈垣在史学上的基本治学路径,乃是扎扎实实的考证。
第三,在陈垣的历史考据著述之中,包含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表达出他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极度关注。他在读史、治史的进程中,会对具备民族气节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产生共鸣、多所关注,例如对胡三省《资治通鉴音注》中抵制外族政权统治的精神就比几百年来的无数读者更加敏感,因而能够揭示出前人所未发的蕴义。但是,所有这些研究,仍然都是实事求是的历史考述,而丝毫没有“结论预设”性的牵强、穿凿和曲解。求真、考实,乃是陈垣之根本的学术理念。
以上三点,是为陈垣1949年之前所有学术成就中贯穿的精神实质,考察学者的学术造诣和学术历程,著述的数量固然是一个尺度,但根本的学术精神则更为重要,特别是对于成名的史学家,不能要求其人总是保持创作的高峰期状态,是否坚持科学的治学态度和正派的学术情操,才是最主要的判断标准。
二、陈垣对新中国史学研究的整体性贡献
1949年之后,中国各种社会运动不断,绝大多数学者的研究工作,在时间与精力上都被压缩。陈垣更具有实际上的官员身份,1949年之后参与大量的社会活动,这不能不挤占学术研究的时间,其史学论著的减少,有多重社会因素的影响。但全面考量,陈垣在年龄段大体相仿的史学家中,学术撰述在数量上并非最少,而治史的纯然学术精神,乃卓荦于当时。
对于陈垣的史学成就评析,应当包括:(1)在他主持下承担的集体项目;(2)个人独立的撰述。忽视集体学术项目的观点是十分片面的,这表现为完全不理解新中国建立后学术与文化事业的发展体制。1951年7月28日,在中国史学会成立大会上的郭沫若发言中,就提出中国史学将作出六个转变,其中第二条就是从个人研究转变为集体研究。笔者认为,历史学的发展,个人独立研究、合作研究与集体研究,三者不可偏废。对于一些较大课题,集体研究在组织工作有序、专家悉心主持以及参与成员之间关系得以妥善协调的状态下,具有远远超越个人研究的优越性,对历史学总体上的进步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学术合作介于集体研究与个人探讨之间,只要关系协调、出以公心、互相取长补短,就能够激发出更大的创新思维。时下某些舆论颇有忽视集体研究、甚或质疑学术合作的倾向,这不能排除是受到西方一种狭隘的个人主义学术观念的影响。
陈垣具备杰出的独立研究的学术能力,但更能够以奉献精神从事集体的、公共的学术文化事业。早在1920年,他就被委托担任调查、清点文津阁《四库全书》的工作,撰定《文津阁四库全书册数页数表》。随后担任征集、清理国内尚存敦煌文献以及清查故宫文物的工作,编成《敦煌劫余录》,于故宫内发现整套《四库全书荟要》以及《元典章》等重要典籍。所有这类工作,都属于公益性质的学术文化活动。新中国建立以后,陈垣更将集体性的学术研究置于重要地位,以利于历史学科整体建设的发展。
1951年,新成立的中国史学研究会发起《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编辑工作,陈垣承担了编辑《洋务运动》、《辛亥革命》两个分册的主持和组织工作。这套资料丛刊的编辑,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提供了很大的方便条件。陈垣还主持《册府元龟》的校补与整理工作,在当时可得以利用的文献条件下,以宋版残本校补明刻本,予以影印,这是陈垣以其精深的文献学知识作出的最佳选择,他撰著《影印明本册府元龟序》一文指出,“明人校刻此书之劳不可没。今宋刻既无完本,以明刻初印本影印,亦其宜也。”[6]206陈垣对《册府元龟》的校补,乃亲自动手、认真审定,1959年5月28日复中华书局总编金灿然的信件中,就反映了这种审核重复、搜录阙遗的具体工作[4]746。1961年,陈垣撰《序》的《册府元龟》影印出版。《册府元龟》是北宋真宗时期官修的一部大型类书,达1 000卷。与其他类书不同,本书乃分类抄编历史记述,初始定名为《历代君臣事迹》,实际上是一部分类编辑的史籍,记述范围自上古至宋朝之前的五代时期,其中包含许多极其珍贵、他处已不能得见的史料。强调《册府元龟》的史学价值,乃陈垣所首发,此书之出版对中国古代史的深入研究具有较大的推进作用。
而就在1961年,他又承担了主持《旧五代史》、《新五代史》的校点工作,这是中华书局规划出版标点本“二十四史”的组成部分。而行世的《旧五代史》并非宋代所修原书,乃清朝官方纂修《四库全书》时期的辑佚本,与“二十四史”中其他各书全然不同。陈垣早对《旧五代史》有深入的研究,他指出《四库全书》本《旧五代史》辑佚中过于偏重《永乐大典》,又因时讳多有文字的篡改,舛误率达十之一二,应当利用《册府元龟》等史籍校订和辑补。为此,编辑了《册府元龟五代部分人名索引》、《通鉴五代部分人名索引》、《旧五代史不列传人名索引》等等作为先行准备[4]775,意欲最大限度地恢复这一重要史籍的本原面目,体现了崇高的史学责任感与认真、执著的学术理念。由于社会政治运动不断和“文化大革命”的到来,陈垣未及完成这项学术工作,所有资料以及校勘手稿也被有关部门索取而去[4]847。至2005年,复旦大学陈尚君之《旧五代史新辑会证》出版,此书即发扬光大了陈垣的思路,依据《册府元龟》、《太平御览》、《资治通鉴考异》三十多种典籍增补遗文、重新辑录、删削清人误载、校订文句错讹,纂成《旧五代史》崭新而更为可靠的文本。这固然是作者自己的史学成就,但也证实了陈垣对此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学术意义。
上述几项文献资料和史籍整理的工作,很难作为陈垣个人的重大学术成就,但其中体现了为历史学整体建设奠基开路的奉献精神,是先前编辑《二十史朔闰表》等文史工具书之治史路径的继续和发扬。
与此同时,陈垣还经常为学术刊物、报纸、出版社做义务性的审定稿件工作,审定中不仅毫无保留地提出自己的学术见解和修改意见,而且多曾对偏离史学求真、求是原则的倾向予以旗帜鲜明的拨正。例如1957年在审查《论科学的考据与旧考据的不同》的书面意见中,陈垣尖锐地指出:“旧考据有不科学的,但也有科学的,不能一笔抹杀。故此文题目只能说科学的考据与不科学的考据不同,不能说‘科学的考据与旧考据的不同’。”这篇审查意见虽然篇幅很短,但句句抓住关键,批评了将“旧考据”笼统说成“片面地孤立地看问题”、“从现象看问题”,强调了“不能说旧考据不是科学方法”的主张,建议取消所谓“旧考据”这个词语,甚至提出“文中所谓‘科学的考据’,是否都能符合科学,亦最好再检查一次”[6]471。这些批语的意义已经不止于对一篇论文的审查,而是对于当时学界“宁左勿右”风习的棒喝。在《柬埔寨始通中国问题》一文中,陈垣批评某文章牵强附会,硬将柬埔寨与中国发生联系的历史提前几百年的说法,指出:“两国国交的好坏,不仅在于年代的长短,勉强地把关系提早几百年,未见有什么作用。”[6]467这表明了史事考证必须严谨、求真的主张,坚决反对以主观意图曲解史料的不良作风。这种学术立场,对于按政治理路预设结论的治史偏向,起到了积极的抵制作用,是维护中国史学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应当予以高度评价。
此外,在陈垣1949年之后大量的学术通信中,或纠正报刊载文中涉及史事的讹误,或答复某些机构的历史咨询,或与学者进行史学研讨,或订正年轻学者撰述的偏颇、舛误,或回答一般教师和各行各业人员的请教,均以认真的态度,不避繁杂地答疑解惑,体现出学术上无私奉献的拳拳之心。这如同“润物细无声”的春雨撒向大地,对学术风气和文化氛围的良善影响无法估量。
三、陈垣的治学与从政
陈垣晚年个人作出的学术研究,已有周少川《陈垣晚年史学及学术思想的升华》一文予以评析,认为陈垣“晚年的考据文益臻佳境,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特别是关于历史文献、历史事件的年代问题,考订最为精湛。周文认为,陈垣晚年“依然保持和发扬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这是他的历史考证能够使人心悦诚服的前提和关键。”[7]这些评价虽意在赞誉,但并非溢美。例如《跋胡金竹草书千字文》一文,通过考订清人胡金竹的生卒年,指出这件草书的《千字文》不是胡金竹的手笔,乃为伪造字帖。又如《跋董述夫自书诗》一文,因发现诗末署有万历纪年和“董良史述夫”印,遂经周密考订,指出《明诗综》将明万历年间的董良史混同于洪武年间的董纪(字良史),导致《四库提要》、《明诗纪事》也承讹袭谬,一误再误。诸如此类,周文已作剖析,不再多赘。
据《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二集的收载,1949年之后的纯然学术论文,约有25篇左右,皆为考据性撰述,而且内容以文献的考据为主,解析之精湛细致,非一般学者所能望其项背。例如《书傅藏〈永乐大典〉本〈南台备要〉后》一文仅一千余字,就解说了元代“南台”与“中台”的区别、《南台备要》与《宪台通纪》的关系,从而纠正了清代《四库全书总目》对此书提要的重大错误。随之又对藏书者傅增湘所撰跋文的五大讹误予以辨正,使本书的真实面目原原本本地展现出来,廓清了误解和淆乱。陈垣还指出:“傅先生之意,欲抬高此册声价,遂不觉其言之失检。”[6]367这里的批评虽然只是针对具体的微观问题,但却具有普遍的思想方法意义,在历史研究与文献评析中,常有因作者预存某种欲念而造成研究结论的偏失,陈垣所表达的是在史学研究上,应当反对预设结论、反对先验性预定价值判断,坚持实事求是的理念。又如《两封无名字无年月的信》一文,根据清嘉庆帝的《圣训》、《实录》将两件无题款、无年月的信件,经缜密考证,揭示了作者与事情原委,即清乾嘉时期大学士王杰致门生汤金钊的笔札。第一札写于嘉庆七年五月二十日,乃因其家乡陕西得旨缓征积欠钱粮,请汤金钊AI写作一件谢恩奏折;第二札写于嘉庆七年七月,请汤金钊代作“四、六句”撰写形式的奏折,对皇上的“温谕慰留”表示谢恩,并且再次乞请休致。两封信都是王杰请汤金钊代撰奏折,陈垣将之考证清晰之后,指出此信札因与汤金钊的其他尺牍保存一起,对弄明原委很有裨益,“故凡做档案工作者,不宜将档案轻易分散及移动,所谓秤不离砣也。”[6]485这又涉及了文献、史料整理工作的原则问题。
陈垣的各篇考据之文,理据充沛、论证严密,学术上几于无可挑剔。然而,更重要的是应当解析这些考据文章的总和,透射出怎样的治学精神。陈垣1949年之后的撰述除上文述及的篇目之外,其他如《跋陈东塾与郑小谷书墨迹》、《跋陈鹏年自书诗卷》、《跋陈鹏年书秋泛洞庭诗册》、《跋洪北江与王复手札》、《跋凌次仲藏孙渊如残札》、《跋王羲之小楷曹娥碑真迹》、《谈北京双塔寺海云碑》等等,整体上体现出他对基本文献的极端重视,对考订、整理文史资料工作的衷情投入。而《萨都剌的疑年》、《戴子高年岁及遗文》、《佛牙故事》、《法献佛牙隐现记》、《鉴真和上失明事质疑》等等,体现了陈垣热衷于考释微观史实和历史典故的治学旨趣。与前期的治学路径完全一致,陈垣治学仍然坚持着以文献学考订为基础的历史考据学宗旨,恪守学术上言必有据、不预设结论的实事求是理念。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陈垣同时是一位从政的学者,从1952年一直担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1954年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历任北京市政协常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常委等等。他投身于新中国建立后的一系列议政、参政的社会活动,在多次政治运动中发表过拥护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讲话或文章。这些政治活动、社会活动无疑会占据很多的工作时间、工作精力。然而,对这种现象无论是采取批评还是表示遗憾,都是没有理由的,因为史家或学者参与政治活动或同时就是政治家,自古以来乃屡见不鲜,中国、外国概莫能外。史家接受和信从某一宏观的思想体系,也是完全正常的现象,而宏观的思想体系不一定从根本上影响微观的史学研究,特别是在具体的历史考据事项方面,其关键在于某个史家是否故意按照他所信从和理解的宏观思想来歪曲地塑造历史。清代历史考据学家钱大昕《廿二史考异》等考据专著,本着求真的原则撰述,几乎与其官员的经历没有直接的联系,甚至也无须从他是否归于儒学思想体系的角度予以评析。16世纪的欧洲史家凡·累德(Reyd,1550-1602)就具有这样的史学理念:“我要大胆宣布,我经常以自己的意见和行动支持站在宗教和自由一边的那一派;但我的笔杆子只支持真实情况,既不隐瞒敌人的优点,也不隐瞒朋友的缺点。”[8]无论他实际做到何种程度,这种理念都是可贵的,也是可以力行的。
新中国的建立,结束了神州大地百年的外侮和内乱,建立起朝气蓬勃的社会秩序,预示出光明的发展前景。这一切对于陈垣等绝大多数爱国的老学者而言,无不由衷地欢欣鼓舞。1949年陈垣曾说:“从解放以后,我静心的观察政府的一切措施,一切法令,这是基本上和从前不同了。不用说别的,就看见他们提倡艰苦朴素的作风,没有一点奢华享受的习气,已经是从前所没见过的”,“我们在这样的政府之下生活,还有什么理由能对政治灰心、对政治不闻不问呢?”[9]这是出于肺腑之言,是他拥护共产党领导,并且积极议政、参政的现实基础。建国之初,具有如此政治态度的学者不在少数。再就陈垣乐于接受、服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看,也是十分正常的取向。20世纪50年代之初,不少史学名家实际是第一次认真地领会唯物史观的原理,许多人由衷地感觉到马克思主义体系的深广、严密和系统性。如郑天挺、吕思勉、童书业、齐思和、谢国桢、罗尔纲等等,前此未曾认真阅读马克思主义著述的历史学家,都积极接受和公开赞扬唯物史观,非止陈垣一人惟是。考察20世纪50年代文化界学习马克思主义和思想改造运动中,公开予以抵制的历史学家恐仅有陈寅恪一人,连顾颉刚最后也改变了认识,并且主动地写文章表态,这不能说成是迫于什么压力[10]。倘若无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魅力和影响力,则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陈寅恪完全是个特例,而且较为偏颇,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取得那样大的胜利,即使仅从学术的角度出发,不是也应当对其思想体系“见识”一下吗?
陈垣在1949年后的十几年间,多次在会议发言和报纸发文中拥护历次政治运动,但并未对任何史家施行激烈的批判和落井下石式的打击。多次在会议发言与报纸发文中,强调唯物史观的正确及其对历史研究的指导意义,但他个人的学术研讨,从主题到方法都与早年的治学理路大体一致,因此,诸多发言、诸多报纸发文只是对于立场的表态。当时,历史学界有着极其热门的研讨内容,如关于历史分期问题、古代土地所有制问题、农民战争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等“五朵金花”,讨论风起云涌;再如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问题、新建王朝有无“让步政策”问题等等,争辩如火如荼。在这些主题中,仍有历史考据的用武之地,以探寻一些外围的内容。但是,陈垣撰写的学术文章,无一与当时史学界的中心研究论题相关,这只能解释为他不善于也不乐于从思想理论体系的要求出发来预设研究的主题。在陈垣这里,政治社会的立场与活动、宏观思想理论的信从,是与具体的学术研究分开的。而从社会的时代背景来看,却是绝不认可政治与学术的截然分开,那么陈垣积极、明确的政治表态,就恰好有利于他可以坚持其一贯的学术精神。
陈垣虽然年老和身兼多种职务,仍时刻以学术为怀,这在大量的通信中表现出来,特别是与汪宗衍的来往信件,充满着对于学术研讨的一往情深。汪氏与陈垣为世交,1949年之后汪宗衍居于海外澳门等地,仍保持与陈垣的通信联系,今存陈垣1952年之后致汪宗衍书信70余通,不仅互寄撰述、切磋文献考订,而且陈垣主动提出:“港澳出版有关文史刊物,能寄我者,不吝赐示为幸。”[11]502汪氏遂陆续邮来《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新亚学报》等刊物及多种书籍。1960年4月,陈垣又提出希望得到胡适、傅斯年的论文集,同样在汪氏协助下实现[11] 518。次年,又询问台湾编纂《清史》的情况,汪氏回信予以详细说明,并且抄寄了《清史叙例》全文[11]531-541。此外,还几次询问港台地区大学、学者的情况等等,显示出对整个中国史学文化的关切。1961年与1962年,陈垣公开发表的撰述已基本属于学术论文,极少其他内容,而且数量大增,这是一个显著的变化。自1963年,他的撰述已经完全为学术文章,假如不是政治运动接踵而来且终于发生“文化大革命”,假如不是陈垣年事过高,他将会全力重新投入学术研究,重大成果必可撰成。但是,世事的变动没有再给陈垣提供充沛的治学机遇。
综上所述,陈垣1949年之后的学术建树,与此前的治学在基本路径和精神实质上完全一脉相承、别无二致,在史德、史学、史才、史识等诸方面,都几乎达于尽善的程度,无可挑剔。与陈垣同一时代,还有大批兢兢业业从事学术工作、做出扎扎实实成绩的史学家,如顾颉刚、郑天挺、徐中舒、唐长儒、吕思勉等等,他们似乎沉潜于当时学术“思潮”的表层之下。如何看待这些史学家的学术成就,是当代史学史研究应当认真面对的问题,对陈垣学术精神的客观考量,可以提供一个评价的标准和参照的尺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