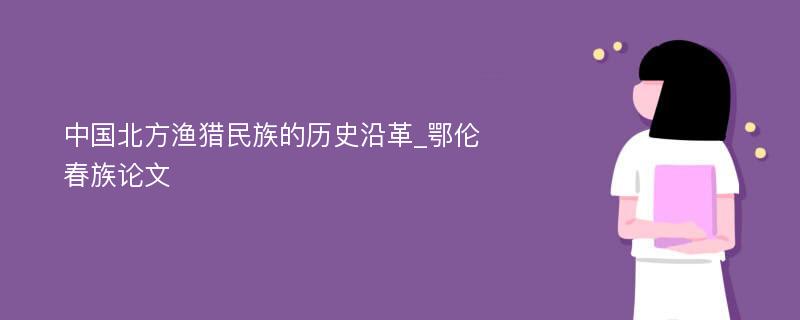
中国北方渔猎民族的历史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北方论文,民族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北方的渔猎民族,习惯上指鄂伦春族、鄂温克族和赫哲族。这三个民族在文化内涵上有诸多相似之处,比如在语言上,同属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支。鄂伦春族和鄂温克族在南迁(黑龙江为界)以前,在族源上很接近,统称为埃文基人。现在,俄罗斯境内仍有3万多埃文基人,主要居住在埃文基自治区。历史上,埃文基人与赫哲人也有亲缘关系。17世纪中叶以前,埃文基人先民分布极为广泛,从贝加尔湖以东,直至黑龙江以北、精奇里江为中心的广大地区,甚至于库叶岛也有埃文基先民的足迹。这样,埃文基人就与赫哲人发生了密切的接触。赫哲先民中的奇楞、撒玛吉尔氏族就来源于埃文基人。
埃文基人南迁后,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称为“鄂伦春”,含义是“使用驯鹿的人们”或“山岭上的人们”;另一部分称为鄂温克,分三部分,含义与山有关,或为“住在大山林中的人们”、“住在山南坡的人们”,或为“从山顶下来的人们”。南迁的埃文基人分道扬镳,分成了两个民族。埃文基人南迁是因为沙俄的入侵。赫哲族也由于同样的原因被分为两部分,俄罗斯称为那乃人,有1万多人。
2000年,中国境内的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赫哲族分别为8196人、30505人和4640人。鄂伦春族主要分布在内蒙古自治区的鄂伦春旗和黑龙江省的5个鄂伦春民族乡及2个民族村;鄂温克族主要分布于内蒙古自治区的鄂温克旗、7个鄂温克民族乡和1个与达斡尔族联合建立的民族乡及黑龙江省讷河市的兴旺鄂温克民族乡;赫哲族主要分布在黑龙江省的3个民族乡和4个民族村。
一、历代王朝对北方渔猎民族的治理
清以前,对这3个民族的治理是比较松散的,任其自我生存自然发展,未采取特别的治理措施。主要原因是中央王朝的势力范围长期无法涉及这一区域。即使在这一区域建立了管理机构,由于其区域浩瀚,鞭长莫及,所以清朝接触这几个民族时,他们刚刚从血缘关系中脱离出来。
从历史记载看,赫哲族与满族先民关系密切。广泛分布在黑龙江中下游流域,包含于肃慎、挹娄、勿吉之中。唐代或渤海国时期则包含于黑水靺鞨之中。辽金时属生女真北支的一部分。元代为女直水达达人的一部分。明代女真人分为三部分,赫哲人先民是野人女真的重要组成部分。明末清初,赫哲族“住松花江、黑龙江两岸者,曰剃发黑金”,“住乌苏里、松花、黑龙三江汇流左右者,曰不剃发黑金……所谓使犬国也”[1]。剃发黑斤与不剃发黑斤原属同一“额登喀喇”,我国的赫哲族和俄罗斯的那乃人主要是剃发黑斤的后裔,被俄罗斯学者错划为乌尔奇人的主要是不剃发黑斤的后裔。过去,赫哲族还有很多自称和他称,主要有那乃(亦称那贝、那尼傲)和赫哲(亦称黑津、黑金、黑哲、赫斤、赫金等,为同音异写)。赫哲作为族称最早出现于康熙二年(1663)三月[2]。
对于赫哲族先民的治理源于唐开元十年(722),唐宣宗封黑水靺鞨首领为勃利州刺史。唐开元十二年(724),唐于黑水靺鞨地设黑水军,两年后设黑水府,再过两年设黑水都督,以本地首领为都督、刺史,派长史监领,因俗而治,对其民生则较少关注。辽重熙六年(1037),设五国部节度使。金收国元年(1115),于松花江下游设胡里改路。元代归属于女直水达达万户府和女直水达达路。明永乐七年(1409),设奴儿干都指挥使司,明弘治年间归辽东都司管辖。
中央王朝对赫哲族进行实质性治理始于清朝。建立前金的女真和建立后金——清朝的满洲族均主要源起于黑龙江中下游流域的黑水靺鞨后裔,也就是后来的生女真或野人女真。努尔哈赤多次提到满族与赫哲本为一家:“尔之先世,本皆我一国之人,载籍甚明,尔等向未之知,是以甘以自外。”[3] 所以,后金——清朝高度重视对赫哲族的治理。清康熙五十三年(1714),建立三姓城,设三姓协领衙门,此地赫哲族编入镶黄、正黄、正白、正红四旗;清雍正五年(1727),设三姓副都统;清光绪八年(1882),于嘎尔当设协领衙门。
清入关前曾对三方用兵,一方是赫哲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达斡尔族等地区,另两方是蒙古和朝鲜,很耐人寻味。从1599年至1644年,后金——清朝对赫哲人居住地区用兵17次,最后一次就俘回人口2552人,分隶八旗。清入关后,仅康熙、雍正年间内迁编旗的赫哲人近60个佐,迁往盛京的有31个佐领万余人,留在吉林的也有1万人,这些被编入“新满洲佐领”的赫哲人成为清入主中原的重要力量。这部分赫哲人后来融入满族中。清朝对赫哲族采取的另一项重要的治理方式是编户,任命赫哲族头人为姓长、乡长,因俗而治。姓长、乡长权力很大,管理生产生活、婚姻、丧葬、司法等事宜:“有不法、不平诸事,则姓长、乡长集于证,公议处置。长(常)法杀人者死。余则视事大小,定班帛服物之多寡,令理屈者出之,名曰‘纳威勒’,至十头为止,小事纳一头二头,大事则纳十头,约值银数两至百两以内。公议云然,两造心服,姓长、乡长始以丈叩地,遂成铁案。否则再议,有至数日数月不决者。”[4] 这是个非常有趣的记载,当时赫哲人的社会风俗跃然纸上。清朝时,赫哲族社会还是有了一定的发展。20世纪初,乌苏里江流域及东部沿海一带,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联系基本丧失其作用,而松花江中游赫哲人氏族组织的作用更为微弱。清末民初,赫哲族社会出现了社会分层,原始民主制逐步弱化。通过占有枪支、马匹和渔具等生产资料入股分成,出现土地出租和雇工现象。如果没有17世纪中叶沙俄的入侵,赫哲族或许可以走上缓慢的民族过程。沙俄的入侵使赫哲族失去了北部广阔的土地,并使其民族一分为二。1909年,撤废副都统建制,设依兰县。1911年,取消了旗制。随后而来的灾难则是毁灭性的。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赫哲族受到日本人惨绝人寰的奴役。1942年,日本侵略者为了将赫哲族与其他民族隔离,以控制和灭绝这个民族,将其赶入深山密林的沼泽地带,分设3个部落。结果是死亡72人,占三部落人口的30.4%。至1945年,中国境内的赫哲族人口仅有300多人,濒于灭绝。
鄂伦春族和鄂温克族的境遇与赫哲族差不多,所经历程更为曲折,也更惨烈。
鄂伦春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17世纪中叶以前,分布于贝加尔湖以东、黑龙江以北精奇里江为中心的广大地区。这一区域历史上曾主要是钵室韦、深末怛室韦人的活动区域,因而被认为是鄂伦春、鄂温克人的先民。室韦人散居于广阔的区域,因地理因素,各部之间并没有紧密的联系。因而,以室韦命名的这个人们共同体集团并不属于一个族系,而分别属于蒙古语族的东胡族系、突厥语族的突厥族系和满—通古斯语族的肃慎族系。其中,东胡族系占室韦人的大部分。鄂伦春语和鄂温克语属于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语言是划分族系的最可靠的依据。衣、食、住、行等生活习惯可以随生存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而语言则是相对稳定的。因此,隋朝时期的钵室韦、深末怛室韦应是鄂伦春人的主要来源,而南临而居的北室韦人亦有可能参与了鄂伦春民族体的历史过程。元朝时鄂伦春先民含于“林木中百姓”和“北山野人”中;明朝含于贝加尔湖以东、黑龙江以北的“使鹿部”中;清初文献曾把鄂伦春人称为“树中人”,清崇德五年(1640),“俄尔吞”作为族称出观于文献中。康熙二十九年十月,才将“鄂伦春”作为同定的族称。
据文献记载,对鄂伦春族先民的治理始于唐朝,室韦都督府管辖室韦诸部。辽朝的室韦部分布于今嫩江上游以北、外兴安岭以南,以黑龙江中上游地区,辽朝设室韦国王府进行管理,辽圣宗时又设室韦节度使,隶西北路招讨司。金朝火鲁火疃谋克管辖外兴安岭以南地区。元朝辽阳行省管辖分布广阔的“林木中百姓”或“北山野人”。明永乐七年(1409),设奴儿干都指挥使司,“北山野人”在其管辖范围之内,弘治年间归辽东都司管辖。以上各朝对鄂伦春族先民都采取了十分松散的治理方式,因俗而治,任其自然发展。
真正的国家治理始于清朝。清崇德五年(1640),清政府将索伦部分编为八牛录(佐),鄂伦春族作为其一部分。康熙八年(1669),在宁古塔将军之下设布特哈(打牲部落)八旗,管理分布于黑龙江中上游的鄂伦春等族。康熙二十二年(1683),从原来统辖吉林、黑龙江的宁古塔将军中析出黑龙江将军,下设八城,分设副都统、总管等官员管辖。对于鄂伦春族,“其隶布特哈八旗为官兵者,谓之摩凌阿俄伦春,其散处山野仅以纳貂为役者,谓之雅发罕鄂伦春。雅发罕鄂伦春,有布特哈官五员分治,三岁一易,号曰谙达。谙达岁以征貂至其境,其人先期毕来,奉命维谨,过此则深居不可纵迹矣”[5]。布特哈总管衙门管辖东西布特哈。东布特哈的鄂伦春族为毕拉尔路,设2佐;西布特哈鄂伦春族为库玛尔路、阿里路、多布库尔路、托河路,库路设3佐,其余均设1佐。雍正十年,鄂伦春族被编为镶黄旗2佐,镶白旗1佐,正红旗1佐,正蓝旗3佐,镶蓝旗1佐。光绪八年(1882),在长期受欺压过重的鄂伦春族的强烈反抗下,黑龙江将军文绪奏请撤销布特哈总管衙门,建兴安城总管衙门专门治理鄂伦春族。光绪十年(1884),兴安城总管衙门建成,设副都统衔总管1位,副总管10位,其中有8位为鄂伦春族。下属库玛尔路设3佐、阿里路设1佐、多布库尔路设1佐、托河路设1佐、毕拉尔路设2佐。光绪十九年(1893)。因实效不大,在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的奏请下,裁撤了兴安城总管衙门,改由黑龙江、墨尔根、呼伦贝尔三城副都统管辖,其中,黑龙江城副都统管理库玛尔路4旗8佐和毕拉尔路2旗4佐;墨尔根城副都统管辖阿里多布库尔路1旗2佐;呼伦贝尔城副都统管辖托河路1旗2佐。副都统和协领均为满族人,佐领均为鄂伦春人。佐领须定期向协领报告佐内情况,他拥有佐内的军事、行政、司法、治安等权力,独揽生杀予夺之权。但在布特哈总管衙门设立之初,氏族长“穆昆达”的地位仍然很高,从氏族的角度管理氏族内部事务,佐领一般以行政职能管理两个氏族。“穆昆达”甚至可以训斥本氏族当佐领之人。清朝末期,“穆昆达”名存实亡。光绪三十四年(1908),设瑷珲兵备道和呼伦贝尔兵备道,分管库玛尔路、阿里多布库尔路鄂伦春族,兴东道管辖毕拉尔路鄂伦春族。民国2年(1912),库玛尔路8佐、毕拉尔路4佐、阿里多布库尔路2佐归黑龙江省督办公署旗务处管理,托河路2佐归海拉尔蒙古衙门管理。
民国时期,黑龙江改设行省,分设县制,但未把鄂伦春族的管理机构合并到县制中,路、旗、佐制同县制并存,不受县管理。这是特殊的管理体制。为了加强边防,民国12年(1923),设立由鄂伦春族组成的“保卫团”,民国14年(1925)改为“山林游击队”,但后来成为日本侵略者、国民党利用的军事工具。“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东北,将原库玛尔路、毕拉尔路、阿里多布库尔路、托河路置于伪黑龙江省民政厅蒙旗科管辖,各路协领公署虽未撤销,但成了有名无实的机构。1934年,伪满洲国将东北和内蒙划分为14个省,伪黑河省管辖库玛尔路和毕拉尔路;伪兴安东省管辖阿里多布库尔路;伪兴安北省管辖托河路。同年7月废除八旗制。名义上仍保留路、佐制度,协领和佐领实为傀儡,日本特务机关派往各地的“指导官”才是鄂伦春族的实际统治者。1938年,日本关东军制订了《指导纲要方案》,对鄂伦春族采取暂时利用、最终消灭的“指导方针”,也就是不开化其文化,持续其原始文化;不使其归农,当作特殊民族实行隔离;构成其独立生活,排除其依存生活习惯等。
清朝对鄂伦春族的治理在政治、军事上是成功的,在经济社会发展上则是失败的。八旗制度牢牢控制了处于氏族社会末期的鄂伦春族,依其原始民主制残余(由此形成的内部凝聚力)、万物有灵观念(由此导致的对死亡的无惧)和捕猎民族骁勇善战的特性,抗击沙俄等国外势力的入侵和平定国内的叛乱、起义及匪患,成为清朝的一支军事利剑。雅克萨之战有565名鄂伦春族士兵参战。光绪二十六年(1900),库玛尔路协领寿廉带领500名鄂伦春族士兵痛击了入侵江东64屯的沙俄入侵者。清朝统治者将鄂伦春族作为平定国内叛乱的一支劲旅,在平定噶尔丹、策妄阿拉布坦、阿睦尔撒纳的叛乱中做出了重要贡献。乾隆、嘉庆年间的阿穆勒塔成为鄂伦春族的英雄,英勇善战,屡建奇功,在收复台湾和抗击廓尔喀侵略者的战争中立有奇功,官至总管,加副都统衔,成为鄂伦春族历史上职位最高、地位最显赫的人物。
除了军事上的成功外,清朝对鄂伦春族的治理是不成功的。比如,由于官私“谙达”的欺骗性剥削和压迫,光绪年间库玛尔路骁骑校烈钦泰聚集各路鄂伦春族,反抗“谙达”的残暴剥削和压迫,要求裁撤布特哈总管衙门。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撤销了布特哈总管衙门,新设兴安城总管衙门,调整了官员。执行了100多年的官方“谙达”制被取消。“楚勒罕”贡貂制也是一种官方对鄂伦春族的欺诈性交易,与对赫哲族“编户”的贡貂与“赏乌林”制相似。民国统治时期,鄂伦春族的境遇更加恶化,私人“请达”和军阀、奸商勾结,对鄂伦春族进行更为露骨的欺诈和压迫。“谙达”们用一些廉价的“现代”用品换取鄂伦春族昂贵的皮毛等物品。在欺诈性交易中,鄂伦春族猎人债台高垒,被勒索骗夺,霸妻夺女。1924年4月,库玛尔路佐领刚通、骁骑校滚都善率鄂伦春民众反抗,人数近400人。迫于压力,统治当局用“收抚”手段平息了这次乱局。应该提到的是清末民初在鄂伦春族部分地区推行过的“弃猎归农”政策。或许是惧于鄂伦春族的强悍,难以驯服,而定居务农则便于掌控和教化,所以,当时的地方当局极力推行这一政策。由于没有考虑到鄂伦春族仍然是一个原始捕猎、采集因素很浓的民族,其心理、生理、文化以及技术能力还无法完全适应定居的农业生活,所以,鄂伦春族“一闻建房开垦,几如害其性命,摇首掩耳,促即奔去”[6]。随后,日本采取了不使鄂伦春族归农的政策。1938年,推行了20多年的“弃猎归农”政策彻底失败。在封闭的原始的和相对民主的捕猎采集生活中,鄂伦春族完全可以过着自给自足的、现代人看似简单枯燥的生活,但也是他们快乐的生活。随着外民族的进入,特别是官、私“谙达”和奸商的进入,产生了极不公平的、欺诈性的交换关系,这个所谓的“交换”,使纯朴的鄂伦春族人反而不可思议地债台高垒,他们失去了妻子儿女,失去了“田园”般的和谐、民主生活,陷入了生存困境,造反也就顺理成章了。日本人的统治更缺乏人性,他们垄断性地收走鄂伦春人的猎品,只提供少量的粮食、布匹、弹药,生计难以维持。历史上强悍的鄂伦春族由于营养不良、疾病蔓延、征战等多种原因,人口大幅减少,面临空前的生存危机。据俄国学者史禄国对中国鄂伦春族人口的统计,1915—1917年,有人口4111人。伪满洲国进行过两次人口调查,1934年为3700人,1938年为2876人。1953年我国进行第一次全国性人口普查时,鄂伦春族人口为2262人。从1917年至1953年,36年间人口减少了45.12%,按照这样的趋势,鄂伦春族濒临灭绝的危险。
一般认为,在迁至黑龙江南岸以前,鄂温克族属于埃文基人的一部分。鄂温克族族称出现较晚。清朝初期,鄂温克一名方见史籍。清初时,索伦鄂温克人分布在黑龙江上、中游流域和精奇里江流域,以及外兴安岭南北广大地区;雅库特鄂温克人分布于勒拿河上游及贝加尔湖以东勒拿河右支流域维提姆河流域;通古斯鄂温克人分布于额尔古纳河和石勒喀河流域。波·少布先生深入研究了鄂温克族历史,我利用他的研究成果,概述一下鄂温克族的历史建制情况。
唐开元二十九年(741)前后,索伦鄂温克先人大致属于分布于黑龙江上游南岸的婆莴部和黑龙江中游北部及精奇里江下游的落俎部。唐朝设置室韦都督府直接管辖黑龙江上、中游,精奇里江下游、嫩江流域和外兴安岭等广大地区。索伦鄂温克先民在唐朝归河北道室韦都督府管辖。辽朝在黑龙江上、中游,精奇里江流域、外兴安岭南北的室韦人区域设室韦王府管辖,索伦鄂温克先民归东京道管辖。元朝索伦鄂温克先民归辽阳行省管辖。明朝索伦鄂温克先民归奴儿干都指挥使司管辖,有11个卫为索伦鄂温克先民的居住区域[7]。
唐朝时,雅库特鄂温克先民居住在贝加尔湖以西、勒拿河上游地区,唐初总章二年(669)归关内道安北都护府管辖,当时属于骨利干地界,唐朝在其西部的叶尼塞河上游设立了坚昆都督府兼管这一地区。雅库特鄂温克先民居住的勒拿河右支流维季姆河流域,也归关内道安北都护府管辖,这一地区属于鞠部地界,具体在烛龙州管辖区域内。唐开耀二年至天宝三年(682—744),雅库特鄂温克先民居住的地区归突厥管辖。贝加尔湖以西的勒拿河上游地区仍为骨利干地界,维季姆河流域仍为鞠部地界,在突厥的版图之内。唐朝天宝四年至大中二年(745—848),雅库特鄂温克先民居住的地区,纳入回鹘的版图。贝加尔湖以西的勒拿河上游地区,以及勒拿河右支流域维季姆河流域,为骨利干地界,由回鹘统一管辖。辽朝时,雅库特鄂温克先民居住的勒拿河上游地区以及勒拿河右支流维季姆河流域,当时不归辽朝直接管辖,而是归属当时与辽朝同时存在的斡朗改部族政权管辖。金朝雅库特鄂温克先民居住的贝加尔湖以西勒拿河上游地区,为豁里、秃麻部地界,勒拿河右支流维季姆河流域,属巴尔虎部地界,后期均被蒙古部统辖。蒙古汗国和元朝时期,雅库特鄂温克先民所居之地为元朝岭北行省辖区。勒拿河上游为布里牙惕地界,统归元朝中央政府的豁里秃麻道牧地。当时雅库特鄂温克人被称为“林木中之兀良哈人”。明朝雅库特鄂温克先民所在的勒拿河上游地区及维季姆河流域属布里牙惕地界,归属鞑靼即北元政权管辖。明末崇祯年间,勒拿河上游地区的雅库特鄂温克人向东迁至勒拿河右支流维季姆河流域游猎。当时称雅库特鄂温克人为“北山野人”[7]。
通古斯鄂温克人也称“那麦塔”、“那麦尔”、“喀木尼堪”等,其活动区域唐至元代史籍无明确记载。通古斯鄂温克人明末至清代居住在贝加尔湖以东至额尔古纳河以西地带。这个地区,唐代是突厥管辖的鞠部地界;辽代为上京道茶扎剌部和斡朗改地界;金代西部由蒙古八刺忽部管辖,东部为泰赤兀部地界;元代时贝加尔湖以东为岭北行省豁里秃麻道牧地,额尔古纳河以西为齐王部地界;明代归奴儿干都司斡难河卫管辖[7]。
清以前,这三部分鄂温克族虽处于各王朝的管理之下,但没有实质性的治理过程,基本上处于自然进化状态,至清朝时期,真正的国家治理才开始。
清朝不仅高度重视对鄂伦春族和赫哲族的治理,对三部鄂温克族也未例外。清入关前,尽管其在黑龙江中下游流域南迁后经百余年的经营渐趋强盛,以建州女真为核心统一了各部,但周边形势并不乐观,稍有不慎就可能改写历史。后金、清初统治者不仅要征服两部的蒙古诸部和亲明的东部的朝鲜,对于黑龙江流域强悍的、桀骜不驯的捕猎各族更不能掉以轻心。这些民族刚从氏族民主制进入地域性的村社阶段,具有极强的军事战斗力和凝聚力,如不收服,必对后金统治和清朝的南下构成致命的危胁。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对捕猎各族的征服和收降,可以补充后金、清朝兵员的不足。后来的事实说明,赫哲、鄂伦春、鄂温克等族不仅成为清朝入关的生力军,而且对于清朝抵御外侵、收复台湾、剿灭叛乱起了重要的作用。所以,后金、清朝对黑龙江流域各族采取了逆者伐、顺者抚的政策。
清初,索伦鄂温克人居住在黑龙江上、中游流域和精奇里江流域。清初索伦部鄂温克人含于索伦部中,当时的索伦部还包括达斡尔族和鄂伦春族,后来达斡尔族、鄂伦春族逐渐从索伦部中析出,索伦部单指鄂温克族[7]。清崇德五年(1640),“俄尔吞”作为族称出现于文献中;康熙二十九年十月,“鄂伦春”作为统一的族称固定下来。这一时间段应该是鄂伦春、达斡尔族从索伦部中析出的时期。
清初除了对以博木博果尔为首的索伦鄂温克人采取收抚政策外,还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征讨。第一次是崇德四年(1639)十一月,出动1万多人的军队,攻破雅克萨城、乌库尔城、铎陈城、多金城、阿萨金城和额尔图、卦喇尔两屯。获男丁、妇女儿童共计6740人。清太宗将俘获的索伦人编入八旗,并将男壮丁派往明边境锦州驻防[7]。崇德五年(1640)七月,第二次征讨索伦部,至崇德六年正月十六日结束,俘获与降服人口为2805人,选拔都勒古尔、达大密、绰库尼、阿济布为牛录章京,管理这部分索伦人。博木博果尔被杀[7]。崇德八年(1643)八月第三次征讨索伦部,共携掠索伦部2817人,男丁补充各旗的缺额,其余赏给出征将领为奴。三征索伦部历时3年零8个月,俘获和降服索伦部14391人,统一索伦部的战争结束。17世纪40年代初,沙俄入侵清朝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流域等广大领土,居住在精奇里江和黑龙江流域的鄂温克人、鄂伦春人和达斡尔人向嫩江流域迁徙。时间在顺治(1644—1661)时期[7]。索伦鄂温克人分布于嫩江两岸及右支流各河的山区,以捕猎为主。清政府按丁编佐,建立了5个“阿巴”(猎场)和3个以达斡尔人为主的“扎兰”(即甲喇,相当于参领),统称为布特哈地区。归理藩院直接管辖,设索伦总管、佐领等。康熙二十二年(1683)以后归黑龙江将军管辖。雍正十年(1732),清政府依据黑龙江将军奏请,在索伦五阿巴、三扎兰基础上,建立布特哈八旗总管衙门。索伦鄂温克人编入正黄旗之外的7个旗,共28个佐。光绪二十年(1894),布特哈总管衙门升为副都统,光绪三十二年裁撤[7]。索伦鄂温克人特别强悍,骁勇善战,被清朝政府充分利用。从康熙二十三年(1683)至光绪十年(1884),驻防或征调的索伦官兵多达40642人次,驻防24处,征调39次,地域多达42处,用以征剿叛乱、土匪、外侵和镇压起义[7]。为清朝的统治和全国的稳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大量壮丁死于征战。
民国时期,索伦鄂温克人主要辖于布西设治局(西布特哈地方)和讷河厅。另外还辖于雅鲁设治局、索伦设治局、克山设治局、德都设治局、克东设治局。
日伪时期,龙江省的讷河县,北安省的德都县、嫩江县是今黑龙江省索伦鄂温克人的聚居区。1932年,日伪统治者将呼伦贝尔原4县改设为旗,组成“兴安北省”,分索伦旗,额尔古纳左、右旗;将原布西设治局、西布特哈总管公署合并,组成“兴安东省”,分设为莫力达瓦、巴彦、阿荣、布特哈等旗,实际由日本参事官进行统治。
乾隆二十八年(1763),500名索伦兵连同家眷921人,由嫩江流域布特哈起程,乾隆二十九年(1764),历经9个月长途跋涉,抵达伊犁驻防,编为索伦营左翼,下设3个佐,为保卫和建设西北边疆做出了历史贡献[7]。
辉河、伊敏河流域的索伦鄂温克人来自布特哈地区,原来在雅鲁河、音河一带游猎。清雍正年间,迁至今内蒙古鄂温克旗境内。雍正十年(1732),在布特哈调至呼伦贝尔的3000名索伦壮丁中,索伦鄂温克有1636名,加上家眷,共2206人。这3000名壮丁编为两翼八旗50佐。右翼4旗25佐;左翼4旗25佐。每翼各设1员总管。移驻呼伦贝尔的共有3部17旗。雍正十年,由京都简派大臣1员,加副都统衔,统辖5总管。乾隆七年(1742),因呼伦贝尔不适宜农耕,24个佐的达斡尔族兵丁被遣回布特哈地区。乾隆八年(1743),大臣改为副都统衔总管,设立总管署。光绪六年(1880),设副都统公署。宣统元年(1909),设呼伦贝尔兵备道。民国4年(1915),成立呼伦贝尔特别区,复设副都统。民国9年(1920),取消呼伦贝尔特别区,设置善后督办交涉员。民国14年(1925),改呼伦贝尔善后督办交涉员为呼伦贝尔道尹公署。民国18年(1929),道尹公署改为市政筹备处。1932年6月,伪满洲国在呼伦贝尔地区成立兴安北分省,驻海拉尔市。1934年12月,将兴安北分省改为兴安北省,直至1945年。索伦左右两翼八旗,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分别隶属于上述行政机构。1945年至1949年,索伦左右旗曾隶属于呼伦贝尔自治省、呼伦贝尔地方自治政府、呼伦贝尔盟、呼纳盟[7]。
唐至清以前,雅库特鄂温克人的建制与索伦鄂温克人大致相同,不再赘述。清初时,雅库特鄂温克人居住在原属蒙古茂明安部落游牧地西侧,勒拿河右支流维季姆河流域。“使鹿部落喀木尼堪地方”,就是指雅库特鄂温克人居住的地方,由于饲养驯鹿,又称使鹿部落。从清崇德元年(1636)十二月二日至崇德二年(1637)五月十六日,清军追剿雅库特鄂温克人,俘获116人,安置于内地,其余雅库特人仍于原住地狩猎,并向清廷朝贡[7]。由于沙俄入侵,清顺治年间,雅库特鄂温克人向东迁至黑龙江左支流阿玛扎尔河一带。在沙俄的进一步入侵下,雅库特鄂温克人再一次向东迁徙,至额尔古纳河与黑龙江汇合口处以东左岸阿玛扎尔河流域,即今黑龙江省漠河以西的地方。在此停留一个时期后,又迁往野兽更多的黑龙江南岸,黑龙江副都统管辖的漠河。也就是贝尔茨河流域,清代称牛尔河、安格林河,即今内蒙古额尔古纳市境内的激流河。嘉庆十五年(1810)左右,游猎于阿尔巴吉河(今额木尔河)与洛乔普河(今老乔布河)之间的索罗共氏族与给力克氏族,在索罗共氏族萨瓦酋长率领下,也由漠河县境内南迁至贝尔茨河(今激流河)流域。5年后,于嘉庆二十年(1815),又返回了阿尔巴吉河一带。道光二年(1822),游猎于洛乔普河(今老乔布河)与杜林河(今大林河)之间的布利拖夭氏族的另一支,也来到贝尔茨河。有清一代,雅库特鄂温克人基本上分为两个部分,一是索罗共氏族与给力克氏族,为一个部落,游猎于漠河境内的阿尔巴吉河(今额木尔河)流域;另一个是布利拖夭氏族与卡尔他昆氏族,为一个部落,游猎于贝尔茨河(今激流河)流域[7]。清末时,雅库特鄂温克人分为3个部落,一是游牧于漠河境内的阿尔巴吉河流域的索罗共氏族,以及从索罗共氏族分化出来的索罗托斯基氏族组成的部落;二是游猎于奇乾境内贝尔赤河以北至乌玛河以南的卡尔他昆氏族和从布利拖夭氏族分化出来的固德林氏族组成的一个部落;三是游猎于奇乾境内贝尔茨河以南至德勒布尔河以北的布利拖夭氏族和一少部分给力克氏族组成的一个部落。清顺治年间,雅库特鄂温克人的索罗共、给力克、布利拖夭、卡尔他昆4个氏族,从黑龙江北支流阿玛扎尔河流域向漠河境内的黑龙江南支流阿尔巴吉河迁徙时,还剩下4个氏族没有跟随南迁。他们与阿尔巴吉河流域的雅库特鄂温克人婚姻关系特别密切。清咸丰八年(1858)中俄签订《瑷珲条约》,咸丰十年(1860)中俄签订《北京条约》,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60万平方公里土地被沙俄侵占。从此,雅库特鄂温克人游猎的阿玛扎尔河流域被沙俄侵占,阿玛扎尔河流域的雅库特人被人为隔绝[7]。
民国沿袭了清末旧制。雅库特鄂温克人游猎于漠河境内阿尔巴吉流域后归瑷珲道管辖;游猎于奇乾境内贝尔茨河流域的,归呼伦道管辖。民国19年(1930),雅库特鄂温克人分别归漠河县和奇乾县管辖。民国年间,雅库特鄂温克人逐渐形成为3个部落。在漠河境内阿尔巴吉市场进行交易的雅库特鄂温克,称作阿穆尔千或漠河部落;在奇乾市场进行交易的称作贝斯特拉千或奇乾部落;在杜博维市场进行交易的称作古纳千或古纳部落[7]。
日伪时期,原在贝尔茨河流域的雅库特鄂温克人归兴安北省额尔古纳右旗管辖。日伪时期,雅库特鄂温克人只剩下贝尔茨河流域的两个部落,以贝尔茨河为界,在北者为奇乾部落,在南者为古纳部落。原在漠河县阿尔巴占河流域游猎的漠河部落的索罗共、给力克两个氏族,因日本入侵者压迫而投奔黑龙江以北阿玛扎尔河流域的雅库特人[7]。
唐至元代文献没有明确记载通古斯鄂温克人情况。明清以后的史料记载比较具体。通古斯鄂温克人明末至清代居住在贝加尔湖以东至额尔古纳河以西的区域,即今俄罗斯国布利亚特自治共和国东部及赤塔州地区的音果达河、尼布楚河、石勒喀河以及乌鲁楞古河、敖嫩宝如金河流域[7]。
清朝通古斯鄂温克人长期与布利亚特人杂居,以游牧为主,兼营猎业。清初在额尔古纳河西岸赤塔州地域内游牧。17世纪中叶,由于沙俄入侵,内迁根河、海拉尔河一带游牧。清政府将“根特木尔的部众”编为3个佐。康熙六年(1667),他们又回到原驻地尼布楚河流域游牧,被沙俄利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社会动荡,居住在额尔古纳河西岸俄境敖嫩宝如金、乌鲁楞古、塔拉其、乌者恩、布如珠地区的通古斯鄂温克人,于1918年纷纷东渡额尔古纳河,迁至中困境内,游牧于莫勒格尔河与特尼河流域,被编入索伦左翼镶白旗中。民国八年(1919)以后,通古斯鄂温克人一直在陈巴尔虎旗管辖之下。通古斯鄂温克人村设有嘎僧嘎(即村长),之上设哈朋等官,之下设催办,这种建制一直延续到伪满洲国。伪满时期,通古斯鄂温克人所在的陈巴尔虎旗一直隶属于伪兴安北省,直至解放[7]。
清以前,北方渔猎民族处于氏族、部落制阶段,历代统治者对其采取因俗而治的政策,放任其自然进化,因而均未进入阶级社会。
清朝时期,对北方渔猎民族采取征伐与收抚和军事上的利用政策。清初,北方渔猎民族成为八旗的重要力量,仅康熙、雍正年间被编入八旗的赫哲人近60个佐,2万余人,这些被编入“新满洲佐领”的赫哲人融入满族中,成为满八旗的主要组成部分。清入关前,编入八旗的赫哲人也很多。入关前最后一次对赫哲用兵就携回男丁720人,妇幼1820人,全部分隶八旗。这些编入八旗(佛满洲)的赫哲人无法准确统计,但从17次用兵的情况看,数量很大,均融入满八旗(佛满洲)中。清崇德五年(1640)索伦部编为八牛录(佐)。雍正十年(1732),布特哈八旗(包括鄂温克族、达斡尔族、鄂伦春族):共61个佐。索伦将十是清朝军事力量的精锐,为其统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因而被清政府所倚重,官至都统、副都统、总管、副总管者比比皆是。
清朝政府比较重视北方渔猎民族的生存状况,清中期以后更为明显。比如对鄂温克族“发放旗地,改旗地为租佃制,明令旗兵归田,大量分发地亩,提倡发展农业,等等”[8]111。在官私“请达”欺凌、蒙骗鄂伦春族,致使鄂伦春族强烈反抗时,光绪八年(1882)清政府撤销了布特哈总管衙门,同时废除了“谙达”制度,以及在鄂伦春族地区推进的“弃猎归农”政策,等等。因此,整个清朝,虽然北方渔猎民族被作为军事机器,并频受官、商的盘剥、欺压,但清政府上层还是想让其脱离原始状态,恢复生产,改善其民生状态。事实上这些民族在清朝完成了民族过程,经济社会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民国时期,军阀混战,社会动荡,无暇顾及捕猎民族的生存发展。尽管在鄂伦春族地区积极推动“弃猎归农”、“抚鄂安边”政策,但由于诸种因素,至1938年,推行了20多年的这一政策彻底失败。民国时期,北方渔猎民族的经济、社会停滞不前,甚至有所倒退。
日伪统治时期给北方渔猎民族带来毁灭性的灾难,几近灭绝。日本侵略者对鄂伦春族采取民族灭绝政策,对赫哲族也采取了类似的灭绝政策。日本侵略者为了将赫哲族与其他民族隔离起来,以达到控制和灭绝的目的,将部分赫哲族赶至深山密林的沼泽地区,设为一、二、三部落。因环境极为恶劣,加之各种疾病蔓延,死亡72人,占人口的30.4%。对于鄂温克族,同样采取民族隔离政策。在日本入侵者的统治之下,很多鄂温克人死于各种疾病。额尔古纳旗的鄂温克人1945年死于肺病者111人。1943年阿荣旗查巴奇因伤寒病死100多人。团结乡一个夏天死了27人,占其人口的30%。更为灭绝人性的是,日本人在鄂温克人身上做细菌试验,辉河的鄂温克人一次就死亡200多人。另一次试验死亡80多人。鄂温克族的人口急剧下降,譬如1899年额尔古纳旗有人口350人,1945年仅剩100多人。阿荣旗团结嘎查“九一八”前还有150人,1945年公剩90人[8]130。
日本侵略者还用强迫、欺骗、利诱等手段将鄂伦春族和鄂温克族编成军事性的山林队。后来在解放战争期间,使解放军蒙受了重大的伤亡。
在日本侵略者统治时期,这3个骁勇善战的神奇劲旅,变成了病入膏肓的羸弱之师,近乎灭绝。比如鄂温克族,1953年时仅剩4957人。我们没有鄂温克族三部分人口的准确数据,但清太宗三征索伦部俘获和降服的人口就有14391人。雍正十年(1732)布特哈八旗的索伦鄂温克人就有28个佐,按常规的300人一佐计算,就有男丁8400人之多。可见,三部分鄂温克人应有数万人之多。鄂伦春族的情况也大致如此。赫哲族最近于灭绝之边缘。1930年著名民族学家凌纯声调查时,松花江下游、混同江南岸和乌苏里江西岸的赫哲族人口近1200人,俄境内为1.1万人。1945年日本投降时,赫哲族人口仅为300余人,离民族灭绝命悬一线。如果历史的轨迹不按现在的方向运转,恐怕这三个民族已经湮没于人类的历史中。
二、历史性的嬗变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北方渔猎各族的情况各异,情况复杂,需采取不同的措施对其安定和扶助。尤其是鄂伦春族的情况最为复杂。呼玛县的“光复军”、爱辉县的“挺进军”等鄂伦春族军事武装拒不下山,与政府抗拒,后经过多次谈判及劝归工作,才解决了此问题。
(一)建国后的建制
建国后,赫哲族主要分布在街津口、上下八岔、七里沁和四排。根据分布情况,1956年将八岔赫哲族村组建为八岔赫哲族乡;1963年,街津口民族村组建为街津口赫哲族乡,组织渔、猎、农业联合生产合作社。1966年“文化大革命”时期,民族乡被撤销,改为人民公社。1959年,大部分赫哲族渔民被编入国营农场,土地大规模开发,野兽资源锐减,赫哲族放弃狩猎,主要从事渔业生产。1980年,八岔、街津口、四排村的赫哲族从原生产队划出,成立了专营渔业生产队。1984年,恢复同江县街津口赫哲族乡、八岔赫哲族乡;1985年,新建饶河县四排赫哲族乡。除这3个民族乡外,还建有抚远县抓吉、南岗、红光,佳木斯市郊放敖等4个赫哲族村。
1951年4月4日,政务院批准成立鄂伦春旗,这也是新中国建立后的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旗。1952年5月31日,鄂伦春旗改为鄂伦春自治旗,下设甘奎、诺敏、托扎敏3个努图克。1953年,全旗共有人口946人,其中。鄂伦春族797人。为一个仅有几百人的鄂伦春族设立自治政府,充分证明新中国重视人口较少民族的政治权利和人权。1959年,自治旗成立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1984年,建立乡政府,旗下设9乡5镇。1988年,旗下设8镇8乡。2003年,全旗有8镇2乡,全镇鄂伦春族人口2322人。800多名鄂伦春族猎民聚居于托扎敏乡、古里乡、乌鲁布铁镇的7个猎民村中。1957年,黑龙江省成立了呼玛县十八站、爱辉县新生、逊克县新鄂3个民族乡,1958年由新鄂乡划出新兴村成立新兴鄂伦春族乡。1958年4月民族乡改为人民公社。1984年恢复民族乡建制,新成立白银纳鄂伦春族乡。目前,黑龙江省共有5个鄂伦春族乡,2个鄂伦春族村。
建国前夕,索伦鄂温克族分布于布特哈旗、莫力达瓦旗、巴彦旗和阿荣旗。1983年10月,布特哈旗撤销,设扎兰屯市。1958年8月,莫力达瓦旗撤销,建立莫立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1958年10月1日,撤销巴彦旗,并入莫力达瓦旗。1958年5月29日,撤销索伦旗,8月1日,成立鄂温克族自治旗。
1948年,雅库特鄂温克族辖于额尔古纳旗境内。解放后,雅库特鄂温克族划为以“乌力楞”为单位的猎区,共5个猎区。1957年,成立了奇乾鄂温克族民族乡,这是雅库特鄂温克族有史以来第一个自治性的国家基层政权组织。1959年,建立奇乾人民公社。1964年,政府将鄂温克猎民迁至根河市以北的激流河上游的阿龙山,从此,雅库特鄂温克族离开了额尔古纳旗,迁入根河市。由于这部分鄂温克人不喜欢阿龙山,又迁至满归以北的敖鲁古雅地区。1965年9月1日,35户雅库特鄂温克猎民迁至敖鲁古雅,同年10月建立满归鄂温克族乡。1967年4月1日,鄂温克猎民建立了东方红猎业生产队。1968年,建立满归镇,实行镇乡合一。1973年,从满归镇行政区北部划出一部分地域,建立了敖鲁古雅鄂温克族乡。2003年8月,敖鲁古雅鄂温克族乡实施整体生态移民,迁至根河市郊,从好里堡镇行政区域西北划出1767.2平方公里的地区。
1945年以后。通古斯鄂温克族归陈巴尔虎旗管辖。1951年实现定居游牧,归属特尼河苏木,下设哈吉、塔拉甘两个巴嘎(村一级行政单位)。1958年,特尼河苏木改为莫勒格尔河苏木。在莫勒格尔河下游的巴彦哈达苏木有500多通古斯鄂温克人,来自额尔古纳河西岸的布如。在今鄂温克族自治旗锡尼河苏木,也有一部分通古斯鄂温克人,来自于额尔古纳河畔的塔拉其地区[7]。
(二)以定居取代游猎。改变生存方式
对于鄂伦春族和部分鄂温克族而言,游猎和游牧尽管保存了其原始文化,但由于外来人口大量涌入地域相对狭小的区域(不同于俄罗斯和加拿大),生存环境受到极大的限制,现在事实证明,这种生存方式不可能存在下去。同时游猎和游牧也不利于发展现代医疗卫生和文化教育事业。为此,各地政府积极推动定居。在定居前,组织游猎、游牧民到各地大城市参观,为游猎、游牧民定居作心理适应的准备,开阔他们的眼界,增强适应新文化的能力。从1953年春天开始,黑龙江省选择了10个定居点,建土木结构房屋313栋,800余间,1953年末全部入住,改变了游猎生活。鄂伦春自治旗从1954年开始建房,1958年完成,共213间,实现了定居。敖鲁古雅鄂温克人2003年8月整体迁至根河市郊,政府为其盖新居31栋,入住62户,实现了定居。定居后的鄂伦春族基本放弃了原始的生存方式——游猎采集业,黑龙江省仅有少数鄂伦春族从事季节性的狩猎活动。敖鲁古雅的鄂温克族仅剩下21人从事驯鹿养殖业。而公务人员、教师、医务人员24人,从事特色养殖业29人,在读学生69人,儿童9人,完全无职业者39人,彻底改变了敖鲁古雅鄂温克人的谋生方式和生存环境。除公务人员、教师、医务人员外,鄂伦春族的农牧业、养殖业、服务业等成为其谋生的主要手段。
(三)经济社会发展成效显著
建国后,国家对北方渔猎民族的发展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在政策和资金上给予较大力度的扶持。如黑龙江省,1978年至2005年。共投入民族专项资金3.4亿多元,2000年以来投入1.5亿元,包括支援经济不发达地区发展资金、少数民族发展资金、少数民族地区补助费等,其中有较大比例投向了鄂伦春族、赫哲族和鄂温克族的经济社会发展事业。这些民族受益更大的是“兴边富民行动”、“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政策以及地方性的“整村推进扶贫”计划等。由国家民委等部门1999年提出、国务院2001年批准实施的“兴边富民行动”,涉及135个陆地边境县,18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人口2100万,其中,少数民族占48%。黑龙江省的鄂伦春族和赫哲族在“兴边富民行动”中加快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在基础设施方面,包括投资1600万元的街津口大桥项目;投资400万元的十八站乡道项目;投资607万元的街律口、八岔赫哲族乡乡道项目;投资168万元的新生鄂伦春族乡乡道项目等。在民生方面,街津口赫哲族村和四排赫哲族村的新居工程等。在社会事业方面,投资172万元的新生鄂伦春族乡科技文化活动中心等。以及教育、卫生、通讯设施等等的投入。鄂伦春族、赫哲族、鄂温克族是全国22个人口较少民族,国家从2000年实施“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加快发展”工程,扶持力度是前所未有的。比如,2005年,黑龙江省民委同省发改委确定了53个发展项目,制订了《黑龙江省扶持人口较少民族专项建设规划(2006—2010)》,列入扶持项目49个,资金3469万元。2000年末,黑龙江省赫哲族村赫哲族户总收入1433万元,其中,种植业收入571万元,牧业收入220万元,而渔业收入只有136万元,结束了历史上以捕鱼为生的历史。2005年,黑龙江省5个赫哲族村的农渔民人均收入接近全省平均水平,比如街津口赫哲族村人均收入3300元,八岔赫哲族村人均收入3900元。2005年,鄂伦春自治旗鄂伦春族村民的人均收入达到2894元,并且全部纳入低保。2004年,黑龙江省6个鄂伦春族村,村民人均收入为2000元,虽然明显低于全省农民人均收入水平,但也是巨大的历史进步。2000年,全国鄂伦春族行业人口为3211人,其中,从事农、牧、林、渔业的为1284人,占行业人口的40%,其他为从事服务业、文化教育、卫生等行业的人口,告别了原始的捕猎采集为生的历史。2005年,黑龙江省的两个鄂温克族聚居村人均收入为2708元。2002年至2005年,黑龙江省民委、省扶贫办投入扶贫资金162万元,用于两个鄂温克族村的畜牧小区的建设工程。2005年,全国惟一的鄂温克自治旗国民生产总值27.4亿元,人均约18899元。在经济发展的影响下,非农业户口人数大幅增加,2000年,鄂伦春族为66.22%,赫哲族为65.13%,鄂温克族为55.21%,都位居全国前9位。分别超出全国平均水平的2.7倍、2.63倍和2.23倍。
民族平等的重要体现是政治地位的状况。这3个民族人口虽少,但在省、自治区和全国人大、政协中都有本民族的代表和委员。2000年,在鄂伦春族的职业人口构成中,国家机关、党群组织和企事业单位担任负责人的有16人(长表数据,以下相同),占整个鄂伦春族职业人口的5.2%;在赫哲族的职业人口构成中,在国家机关、党群组织和企事业单位担任负责人的有15人,占6%;鄂温克族有49人,点3.9%。
民族素质是一个民族发展状况最核心的内涵和指标,也是发展的动力。而提高民族素质的最主要手段就是发展教育。赫哲族教育的发展尤为突出。1999年,街津口、八岔、四排乡的学校达到了省级规范化学校标准。当年4所赫哲族村办学校顺利通过了省及国家“普九”验收,学生入学率、巩固率均为100%。赫哲族聚居区是我国55个少数民族中第一个实现“普九”教育的民族,也是第一个扫除青少年文盲的民族。据2000年的全国人口普查,在全国6岁及6岁以上的赫哲族受教育人口中,有大学专科310人,大学本科165人,研究生7人。其中,大学本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3.6%,超过了全国平均1.14%的水平;同期6岁及6岁以上的鄂伦春族的受教育人口中,有大学专科466人,大学本科181人,研究生12人,均高出全国平均水平;同期6岁及6岁以上的鄂温克族受教育人口中,大学专科1420人,大学本科434人,研究生27人,其中,受大学本科教育人口占总人口的1.42%。文盲人口占1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鄂伦春族为3.48%,赫哲族为3.06%,鄂温克族为3.81%,而全国为9.08%,汉族为8.60%。很明显,在国家的扶持下,这3个民族的教育成绩是显著的,如果考虑到几十年前他们还在从事着原始的捕猎、采集、渔业和游牧业,现在这一成绩的取得是十分了不起的。
三、适者生存法则与迷茫的现实
上述我们扼要介绍了3个民族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所取得的成绩,从中可以寻觅出他们向现代化民族迈进的步伐。从人类第一次现代化的角度看,这3个民族取得的成绩还远远不够。第二次现代化离他们更加遥远,只有他们的精英正在享受着这一人类进步的成果,但是这一切足以令政策的实施者和他们本身感到骄傲。然而始料不及的是,尽管国家出台所有政策的目的都是为了他们的发展,以向这些民族承诺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所宣示的民族平等原则,但还是重复着人类历史上出现过的悲剧,当然这是无法避免的生物进化的自然法则,也就是进化论所揭示的适者生存的法则。15世纪,广阔无垠的南北美大陆全部由以印第安人为主的黄种人所占据,大约有8000万人。1492年,哥伦布到达南北美洲时,生活在现在美国的印第安人有500万人。随着白人的大量涌入,1809年,生活在美国的印第安人仅剩60万。中南美洲欧洲移民远少于北美洲,1835年时有480万移民者,而北美洲为1380万,到了1935年,印第安人在北美只占总人口的1.8%,中美洲21.4%,南美洲为29.2%。美洲印第安人只有少数是因为种族灭绝政策和过度劳累工作而死亡的,那么大多数人为什么会死亡呢?我们可以列出一份白人从欧洲带来的令人恐惧的黑死病(14世纪中叶,曾使欧洲损失了1/3或1/2的人口)、天花、伤寒、霍乱、流感、肺结核、麻疹、水痘、疟疾、百日咳、白喉、登革热、猩红热、阿米已痢疾等。这些传染病对原始的捕猎、捕鱼者就等于灾难。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得过这些疾病,在他们的体内根本没有抵御这些疾病的免疫系统。所以令人恐怖的事情出现了:在北美洲,只有10%多一点印第安人侥幸生存下来。16世纪初,墨西哥中部的印第安人一年就死去40%。1492年,墨西哥的印第安人有2500万,到了1608年,仅剩下100万。1508年,伊斯帕尼奥拉岛(今海地和多米尼加共和国)有6万印第安人,1554年为3万,1570年就只有500人了。曾经创造美洲古代文明的印加人、玛雅人和阿兹特克人就是被流行的各种疾病击垮的。从军事理论而言,刚到美洲大陆的欧洲人是无法彻底征服印第安人的,但是,他们身上携带的各种病毒要比枪炮强大无数倍,美洲印第安人的悲惨命运是注定的,他们没有机会改变历史。
定居后的鄂伦春族、鄂温克族同样面临这样的问题,只是性质完全不同而已。前文谈过,中国政府的定居政策完全是为了这些民族更好的发展,只是因为生物进化的法则是无法避免的,才导致了悲剧的出现。国家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措施,比如建立专门的结核病医院、免费治疗等,将这种灾难降低到了最低的程度。另外,事实上这3个民族历史上已开始接触汉、满、达斡尔等民族,已经在生理上具备了一定的防疫能力。由于上述原因,加之这3个民族与其他民族普遍的通婚,这些民族的人口出现了较快的增长,这与美洲印第安人的悲惨结局是完全不同的。鄂伦春族的人口从1953年的2262人增加到2000年的8196人;赫哲族从1964年的718人增加到2000年的4640人;鄂温克族从1953年的4957人增加到2000年30505人。但是我们还是有必要了解一下“适者生存”法则这在几个民族身上的体现。鄂伦春族是从1953年定居的,定居点的周围是汉、达斡尔等民族,这3个民族自身的免疫系统根本无法抵御周边民族携带病毒的侵袭。定居近30年后的1991年,黑龙江省鄂伦春族总人口的患病率仍然高达45%;结核病的患病率从建国初的10%以上降至3.32%,但仍大大高于全省平均0.64%的水平。1962年,鄂伦春自治旗的结核病患病率为17.2%,1985年为11.86%,1988年降至2.4%。目前全国鄂伦春族的结核病患病仍未降至2%以下。赫哲族定居的历史较早,并与满族先民长期杂居,但是对传染病的抵御能力仍然较低,特别是对伤寒和结核病的抵御能力较弱。建国初期,敖鲁古雅136名鄂温克族人中70%患有结核病,现在的结核病患病率仍然远远高于内蒙古自治区的平均水平。受结核病、酗酒、非正常死亡等因素影响,这部分鄂温克人的平均寿命只有54岁,人口出现负增长。
与生物进化的适应性相比,心理与文化适应和整合更为重要。捕猎、捕鱼、采集文化是人类历史的早期阶段产生的,属于原始文化的范畴。当原始文化与农业或现代文化相接触时,最初的表现是相互之间的冲突与排斥,而且往往最终是先进文化吞噬掉原始文化。然而原始文化并非毫无可取之处或没有任何价值,其实它是所有民族都经历过的一个历史阶段,既有文化遗产保护价值的因素,也有现代文化有价值的借鉴因素。比如,原始氏族制的民主制度、互助机制、与环境的和谐共处意识、纯美的纹饰与造型艺术,等等。关键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原始文化在与先进文化的碰撞中如何保持一种平衡,既能吸收先进文化的优秀成分,糅合、整合进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中,以利在现代社会中生存发展,又能把本民族文化中的精华传承下来,成为民族认同的基础和发展的动力,这一点对落后民族是十分重要的。然而从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看,还没有看到两种文化能够和谐、平衡、有利整合的过程,更多表现为冲突和以强融弱。在这一过程中,原始民族中的大部分人在适者生存法则下被淘汰,能够较好地适应现代文化的人是少数,而他们的后代由于接受了现代教育和大量与外族的通婚,表现出更强的适应性和生存能力,甚至完全融入现代社会。中国的北方渔猎民族未能幸免于适者生存的残酷。1980年至1986年,鄂伦春自治旗的鄂伦春族非正常死亡率很高,其中,乌鲁布铁7人,讷尔克气11人,朝阳13人,古里17人,小二沟4人,托扎敏51人,总计112人。1973年至1979年,一个鄂伦春族公社鄂伦春族的非正常死亡率占该公社鄂伦春族人口的5%。另据对黑龙江省两个鄂伦春族公社的统计,1980年至1982年,鄂伦春族非正常死亡24人,占死亡人口总数的52.17%。另有一个鄂伦春族公社,鄂伦春族人口442人,1982年至1983年,非正常死亡占死亡人口总数的50%。1987年统计,大兴安岭地区鄂伦春族自定居以来非正常死亡人口占该年度鄂伦春族人口的15.78%[9]。为什么有如此高的非正常死亡率,其实就是文化冲突和弱势文化无法适应现代文化的结果。定居前,游猎采集的鄂伦春族尽管生存环境极其恶劣,但他们的生活是自给自足的,人们之间处于平等的、民主的、互助的社会机制中。猎人们是无忧无虑的。但定居以后,他们面临的是复杂环境和人际关系,他们与其他一些人处于不平等的状态,他们不能完全从事他们认为快乐的捕猎、捕鱼和采集生活。传统文化正离他们远去,而又不能适应或不喜欢现代文化,很多人处于两种文化的中间,酗酒便成为普遍的现象,非正常死亡的出现也就很容易得到解释。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定居是一种错误的选择,事实上,如果鄂伦春族当初不选择定居,在人口稠密的中国,必定像有些其他古代民族那样消逝在历史中。
类似的情况目前在国外也普遍存在。20世纪80年代末,加拿大对印第安人给予较大力度的扶持,当时40多万印第安人分散在2260个保留地(目前有50%的土著民族居住在城市),占地660万英亩。目前还有近50万平方公里北方寒冷地区的土地由土著民族直接控制。他们的村落社政府的经费由联邦政府提供;有权参加各级选举,担任各种公务员;有权享受政府设立的一切社会福利措施;在保留地可以免征所得税,部分免征政府销售税;享受免费医疗;资助在保留地建造住房;享受生活补助费;免费上高中、资助大学教育等。即使如此优惠的扶持政策,印第安人的人均寿命当时只有30—40岁,而同期全国为70岁;自杀率是全国平均的6倍,青年人是全国的14倍;暴死率为全国的3倍[10]。而目前加拿大印第安人的境遇也未有多大的改善,土著民族结核病的发病率高出非土著民族6倍;人均寿命比非土著民族低6.4年;严重的酗酒和家庭暴力普遍存在,等等。
对北方渔猎民族的扶持政策是必须的。由于历史因素,没有这一过程就永远实现不了民族间的平等。因为,即使赋予了他们平等权利,他们也没有能力享受。但是扶持政策不能是永久性的,因为这会滋生依赖意识,从而不利于竞争能力和生存能力的形成和增强,消磨创新意识,还有可能成为产生盲目优越感的土壤。
如果说北方渔猎民族为适应现代社会付出了高额的代价,更令人婉惜的是,他们的捕猎、捕鱼采集文化处于加速的消逝中。其中的精华部分,可供现代文化借鉴、吸收的部分也是如此,我们正在失去人类童年时期所创造的纯美、静谧的彩虹。捕猎、捕鱼者也被称之为食物采集者,是旧石器时代人类的一种生存方式。从社会形态上一般经历了母系氏族社会、父系氏族社会到地域性的农村公社(或称游猎公社、游牧公社或村社)阶段。这是人类经历的第一个社会发展阶段,也是今天所有民族部曾经历过的历史。捕猎、捕鱼者的原始生活并非像现代人类想象的那样糟糕,尽管他们的人均寿命很短,但过着田园般的生活。男人们狩猎、捕鱼,提供肉食,承担需要体力的劳动,并负责保护氏族或部落的安全;女人们在住地附近采集各种可供食用的东西,并负责照料孩子和做一些手工制品。男女间是平等的,人们之间互相承担责任,享受着近乎相等的权力和义务,即使是首领也没有特权。建立了一种民主的议事制度。如果不考虑到生存环境的恶劣,有很多生存之道是现代人类梦寐以求的理想。由于环境的限制,捕猎、捕鱼采集并不能养活很多人,所以原始农业出现了,而且经历了漫长的时间。现在,全世界的捕猎、捕鱼者部落大约仅有90多个,而且还在消失的过程中。中国的北方渔猎者就属此列。原始捕猎、捕鱼者创造了那个时代的文化,是我们所有现代民族都曾经历过的文化。这种文化是历史的活化石,它使我们可以了解我们遥远的过去。因此,捕猎文化是人类的宝贵遗产,需要我们保护和研究。原始的东西也并非都是落后的,其中有很多内涵可被现代民族借鉴、吸收。然而,这种原始文化还在加速消逝的过程中。
很多国家意识到了这一点,试图更多地保存这种文化。瑞典曾经不承认少数民族的地位,但强力的压制和忽视往往会带来相反的结果,瑞典的少数民族对自身权力和地位的要求反而更加强烈。1975年,瑞典实施多元文化政策。1997年,瑞典政府开始承认瑞典存在5个少数民族,并制定了统一的少数民族政策。在瑞典的少数民族政策中,其中就包含着语言和文化保持和发展的内容。瑞典少数民族政策确认少数民族享有的主要权利包括:一是平等权;二是充分参与社会生活的权利;三是文化权利,对保存与发展少数民族的文化给予特别的帮助。由于萨米人是土著民族,瑞典还有专门的萨米人政策[11]。1973年以前,澳大利亚曾对土著民族进行大规模的屠杀。后来又对移民实行过同化政策。1973年,澳大利亚实施多元文化政策,承认包括移民在内的土著人和托勒斯海峡人的文化权利[12]。加拿大有100万土著民族,主要有印第安人、麦提斯人、因纽特人,他们是从亚洲北部迁徙过来的,也曾是捕猎民族。加拿大曾实行过民族同化政策,20世纪80年代开始实施多元文化政策。1988年7月12日,加拿大众议院通过了加拿大多元文化法,允许土著民族保存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
新中国自建立起就从法律上承认少数民族的文化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条中,规定国家帮助各少数民族加速文化的发展。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和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第三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第三十八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组织、支持有关单位和部门收集、整理、翻译和出版民族历史文化书籍,保护民族的名胜古迹、珍贵文物和其他重要历史文化遗产,继承和发展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目前,国家正在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古籍整理出版保护。在黑龙江省申报的首批国家级保护项目中,有3项属于鄂伦春族和赫哲族。这3个民族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也受到了国家的重视。黑龙江省民委对鄂伦春语、赫哲语、鄂温克语的抢救(录音、录像)是一项非常有远见的工作。
应该说,中国北方渔猎民族保护、发展传统文化是有充分的法律保障的。然而由于人口数量、社会环境、发展机会、教育体制、通婚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这些民族的传统文化正在加速消逝中。语言正在消亡中。作为他们精神文化的内核的讲唱的历史和文学已找不到传承人,如果想要了解这些,只能看那些整理出版的作品。目前有的所谓“传承人”在用现代人的理念演绎历史和文化,甚至“美化”他们具有重要的人类学与民族学价值的人类文化遗产,创造出来的反而是文化垃圾。具有原始价值观、审美观和宗教观的纹饰、造型艺术正在消失。最具北方渔猎文化特点的桦皮制品也在失去传承人。作为这些民族原始文化集中表现的萨满和萨满教已成为历史,等等。我举两个具体的例子。2001年,对5个赫哲族民族村进行了语言学调查。这5个民族村赫哲族人口为1251人,调查了644人。占51.48%。调查是分完全不掌握赫哲语单词的人、掌握1—99个赫哲语单词的人、掌握100—299个赫哲语单词的人、掌握300—499个赫哲语单词的人、掌握500—999个赫哲语单词的人、掌握1000—1999个赫哲语单词的人、掌握2000—2999个赫哲语单词的人、能够流利地运用赫哲语交流或掌握3000个以上赫哲语单词的人进行的。综合实际情况把掌握299个以下单词的人归为不会说赫哲语的人,其他为会说赫哲语的人。调查结果表明,5个赫哲族聚居村会说赫哲语的人为9.44%,散居区赫哲语的掌握率为零[13]。令赫哲族骄傲的长篇讲唱文学“伊玛堪”已没有传承人。据2003年对新生鄂伦春族村的调查,40岁以下的鄂伦春族很少会讲鄂伦春语,40岁以上能够流利地说鄂伦春语的寥寥无几。已没有人能够完全说清楚鄂伦春族的传统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社会结构、宗教、语言艺术,等等[14]。
北方渔猎民族的原始文化正在消逝,这是不争的事实。那么,未来他们将走向何方?一个失去所有本民族传统文化的民族以什么为基础获得对人们共同体的认同?是已经出版的文献和影像资料还是国家政策的确认或认同,很值得我们深思。目前启动的非物质文化保护工作认识到了传统文化对人类的价值,但对于北方渔猎民族而言,已失去了最佳时机,现在留给我们的渔猎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多是经过“加工”和“美化”的,因而也就失去了它固有的价值。
收稿日期:2007-08-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