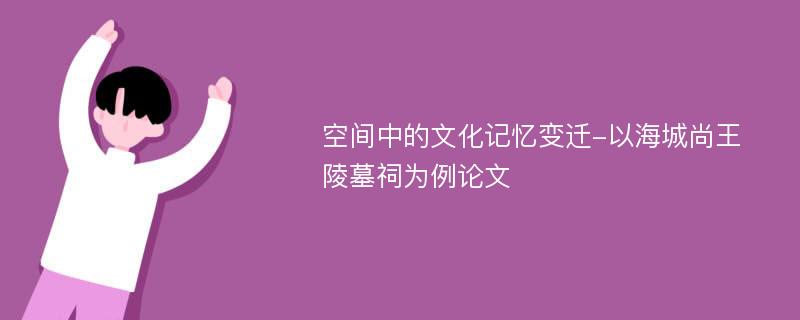
空间中的文化记忆变迁
——以海城尚王陵墓祠为例
金丹妮
摘要: 祠堂作为家族声望、地位、经济实力和家族凝聚力的象征,它的营建是全体族人共同的意愿。祠堂不仅是家族各项活动的空间载体,更是社会关系与文化记忆的载体。尚王陵园从建立到衰败再到重建的几百年岁月中,在塑造后人们文化记忆的同时,也带来文化记忆的变迁。文化记忆中所蕴含着的不仅是对岁月的记忆往事,也是族人们对家族群体的凝聚感与归属感,空间与文化记忆相辅相成,并在新时代下延伸出更多新的内涵。
关键词: 墓祠空间;文化记忆;变迁
引言
宗祠,又称祠堂,是我国古代供奉祖先、举行祭祀活动的场所,它记录着家族的辉煌历程与优良传统,是家族的圣殿与象征。[1]祠堂不仅是家族各项活动空间的物质载体,其中更是承载了家族成员对外、对内以及相互之间的社会关系,并构成了家族特殊的历史记忆。本次研究对象为海城尚王陵及尚氏家族,从陵园建立到衰败再到如今的重建,历经了历史的浮沉与岁月的变迁。尚王陵园是尚氏家族的“记忆的场”,它承载并延续了家族跟随时间与空间所产生的一系列文化记忆,家族又通过产生的文化记忆再次作用回到陵园空间中。从陵园与祠堂的最初建立,到它的衰败与重建,家族的文化记忆也经历了自信、质疑、消退、重振、转型等相应的变化。
面对种种似是而非的说法,很多人无法弄清真相。应该说,这不是老师们的问题。因为语文本色教学,不管怎样系统全面,不管怎样立足实际,它还只是一个教学主张,而不是具体的教学方法。为了推动语文课程改革的深入,也为了更好地满足教师实践本色语文教学主张的需要,我们必须总结出能体现语文本色教学主张的教学方法。
一、家族至上的自信与光荣
康熙二十年,康熙赐尚可喜葬银八千两、房屋地亩万顷,供尚氏家族世代享用,当时整个海城几乎都是尚可喜及后人的领地。尚氏家族身为王族之后,血脉里流淌的不只是王室之血,更是一种家族至上的光荣。建祖庙、修宗祠是发挥家族至上的最显著形式,族人们在这里进行所有的家族活动:祭祖、求子、祈福、编修家谱、人生仪礼、司法决策等等。它是家族的圣殿与象征,记录着家族的辉煌历程与优良传统,使家族的血脉纯正并得以延续。它是祖先信仰的传统,更是族员身份的证明与认同的标签。陵园在家族成员心目中的位置,实际上要远远高于在陵园中完成的各种纷繁的具体功能,族人们通过它对祖先的追溯来探寻自身肉体、精神与文化的“根”,体现的是家族的归属感与历史感、责任感与道德感。陵园将这些心理情感整合,以浓缩的、象征的形式把原本虚幻的心理感受显现出来,使之成为一种实际的力量。陵园的规模越是气势宏大,装潢越是考究奢华,越能彰显家族的地位与实力,它是家族经济实力与声望地位的象征,也是家族所有成员共同的意愿。这段时期里,家族共同的文化记忆是对祖先的忠贞与孝悌,是族员内心时刻流淌着的自信与光荣。
二、质疑与否定
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束,墓祠及家族制度至民国时期逐渐衰落。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文革”的“破四旧”运动让墓祠遭受到了“灭顶之灾”,三百年来一直保护完好的陵园作为封建遗存被大量损毁。往日里威严肃穆的陵园彻底倒塌,只剩下荒芜的破败景象,以及隐隐约约才能找准位置的墙根。除了陵园的破坏,还有土地的改革,土地全归国家所有,家族被批斗,财产全部没收。一时之间,尚氏家族光环不再,自此没落。他们不得不终止一切家族活动,甚至不敢承认自己是尚氏后人,隐姓埋名战战兢兢地过日子,绝大多数人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笔者采访了几位年纪较大的经历过那个时代的老人,他们的记忆只停留在畏惧与恐慌之中。那时他们还比较小,只知道家里没有任何祭祀活动,没有人敢提自己的老祖宗,对于尚姓也比较忌讳,人们对自己的身份产生了质疑,这个曾经让他们光荣无比的身份,如今却成了难以启齿的困窘。陵园作为族人们心灵的庇护所,如今却不再有能力发挥它的功能,人们的家族观念越来越淡薄,陵园也成为一道渐行渐远的风景。在这个时代的族人记忆里,是一种恐慌的担忧,一种逃避的缺失,一种无奈的舍弃。
三、重建与转型
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全球华人掀起了寻根热潮,许多祠堂得以修复,这也为尚王陵园的复建带来了机会。尚氏后人尚德新等人看到祖坟如此破败,心中酸楚。在他们看来,这块地承载着祖先珍贵的情感,是尚氏后人的根,如果不去修复,就等同于放弃了自己的根,于是带领族人们筹资,本着修旧如旧的原则,将陵园依照原貌,于1995年复建了尚王陵园,尚氏家族的所有活动也从此恢复。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中说道:“过去留下了痕迹作为一种铭记,但是空间总是现在的空间,一个目前的整体,而且与行动相互扣连衔接。事实上,生产及其产物乃是同一过程里不可分割的两面。”[2]陵园作为物理空间,不仅是家族文化体系的核心符号,更重新汇聚与凝集当初迁徙至五湖四海的族人们,借助重建的空间也重新生产了社会关系。陵园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所生产,而这些社会关系正是依托于族人们这三百多年来形成的文化记忆。文化记忆作为一种对“过去”在“当下”的再现,族员如今对过去的认识和理解,都是建立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之上的。陵园重新被重视起来,并恢复了曾经认祖归宗、联络同族的功能,不仅成为四面八方的族人们汇聚的场所,为他们重新拾回身份,更将其内部所发生的祭礼文化以新的面貌传承下来,承载了他们的文化记忆。文化记忆的客观化表达是身份固化和群体认同的重要来源,因为群体的整体性意识就建立在这种知识之上,并从中获得形式冲动与规范冲动,从而再生产出自己的身份认同。[3]
乳酸链球菌素又称乳链菌肽,简称为Nisin。它是一种多肽,进入人体后可降解为氨基酸,因此具有无毒、安全的特性,作为天然的防腐剂,它可以有效抑制引起食品腐败的许多革兰氏阳性菌,以延长食品的保质期和提高产品品质,同时也可以满足生产绿色健康食品的需求[1]。
文化记忆的产生与强化需要通过重复性、客观化的社会行为得以完成,不仅有每年在陵园内所进行的祭祀活动,家族人又在学者的帮助和支持下成立了尚可喜学术研究会和沈阳尚氏传统文化交流中心,以试图更正祖先所背负的历史争议。研究会的成立,成为了尚氏家族发展壮大的内在要求和必要手段,尽管仍然争议不断,但是外界人士对历史和尚可喜的重新关注,不仅是对尚氏家族身份认同的重新恢复,也激发了他们继续振兴家族发展的动力。国家政策下的大背景变化,学者们的介入,各行各业的家族精英。社会媒体对历史古迹的挖掘与关注,等等,多方面的因素共同合力唤醒了尚氏家族成员们新时代下的文化记忆。在他们看来,他们的祖先在历史上是为清朝廷做出重大贡献的要员,这种“记忆中的历史”让尚氏族人内心产生了强烈的自豪感与使命感。陵园不仅是族人文化记忆的集中体现,更是彰显了从集体到个人的荣誉彰显。空间与文化记忆相辅相成,并在新时代下延伸出更多新的内涵。
结语
阿格尼丝·赫勒在《现代性理论》中诠释了“家”的定义:“中心被称为家。家是‘很近的’,某种东西离‘家’越远,它就变得越是遥远。”而如何区分“近”和“远”的最简单方式是同一信息的传播长度。假设一个人要告诉另一个人一件事,这件事(对她来说)非常重要;关系越是亲密,传播的长度(路径)就越短,因为“亲密的人”相互理解时不需要语言,而是通过暗示,以一种简略的方式。
如果存在着一个边缘或许多个边缘,如果有不同于我们的传统的传统,如果有不同于我们身份的身份,如果有不能给我们以在家之感、让我成为陌生人或外来者的地方,那么,就有一个中心(或有几个中心)——我们有一个家,一种传统,一个有伸缩性的群体(种族的、国家的或宗教的)身份。[4]换句话说,那个被我们称为“家”的存在,是因为我们与它有着共同的文化传统和文化记忆,在共同的文化传统和记忆中就意味着近,之外的就意味着远。陵园就是家族的“家”,陵园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刻画和书写着族人们共同的文化记忆,它们是同步的,是相互作用的。每一年的祭祀活动,无论距离有多遥远,路程有多艰难,五湖四海的族人们都必须来到陵园里面,共同见证当下情境的文化记忆,因为陵园意味着“家”、“中心”。巴什拉认为:“家宅,就像火、像水,照亮了回忆与无法忆起之物的结合。在这个遥远的区域,记忆与想象互不分离。双方都致力于互相深入,两者在价值序列上组成了一个回忆与形象的共同体。”[5]陵园是被赋予极致想象和记忆的空间,如果人们没有在特殊时刻来到这里,就会造成一种“中心的缺席”的感觉,缺席代表个体无法继续沿袭与群体一致的文化传统,更无法塑造与群体一致的文化记忆,这深处蕴含着的更是族人们为寻求归属感和凝聚感所做的不断努力。
注释及参考文献:
[1]王俊.中国古代宗祠.中国商业出版社:2017.17.
[2]包亚明.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2003列斐伏尔专辑)2003.48.
[3]连连.历史变迁中的文化记忆[J].江海学刊.2012(04).177-239.
[4][匈]阿格尼丝·赫勒.现代性理论.商务印书馆.2005,265-269.
[5][法]巴什拉.空间的诗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4.
[6][匈]阿格尼丝·赫勒.现代性理论.商务印书馆.2005.
[7][法]巴什拉.空间的诗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1.
[8][德]简·奥斯曼.集体记忆与文化身份.陶东风主编.文化研究.1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9]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2003列斐伏尔专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01第1版.
[10]王俊.中国古代宗祠.中国商业出版社.2017.09.
[11]连连.历史变迁中的文化记忆[J].江海学刊,2012(04):177-181+239.
(金丹妮,辽宁大学,辽宁沈阳1100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