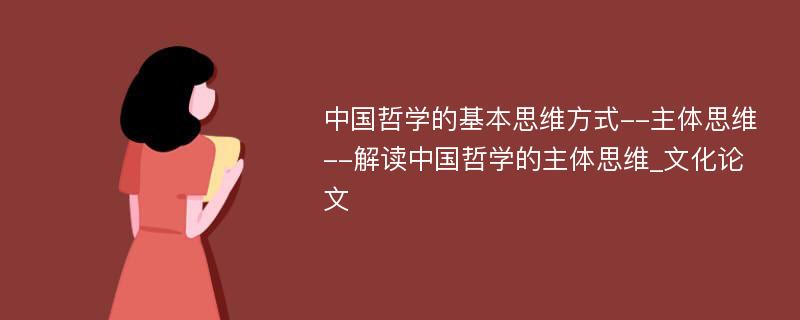
中国哲学的根本思维方式——主体思维——读《中国哲学主体思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主体论文,思维论文,哲学论文,思维方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读蒙培元《中国哲学主体思维》一书,深受启迪。该书从主体思维的角度分析了中国哲学发展的内在规律。“主体思维”在此处不应被理解为西方哲学中的“主体对客体或现象的认识”,而应理解为“主体以自身和自身意识为对象的自我认识”,用作者的话说,是“思维主体的自思维”。
中国哲学这种独特的思维方式是与中国哲学的出发点和价值取向分不开的。一般认为,中国哲学是沿着“天人合一”的模式展开的。“天”乃是指“人之天”,即具于内心的天道、天理、自然之性或佛性。人觉悟到这种“性”,便可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但由于人是行为的主体,觉不觉在人,能否实现“天人合一”亦在人,因此中国哲学乃是以人为主体的哲学,这就决定了它的最根本的思维方式,必然是以人为中心的主体思维。由此可见,作者以主体思维为中国哲学思维之核心内容有其合理性。
由“内圣”之学开出“外王”之道,这是传统中国哲学的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决定了“正心、诚意、修身、齐家”的首要性,只有如此,才能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就此而言,作者从根本上将中国哲学思维方式归结为主体思维亦具有合理性。
这种以“天人合一”为出发点,以“内圣外王”为其价值取向的主体思维在传统文化中有诸多表现。作者从自我反思、情感体验、主体实践和自我超越四个方面加以分析和论述。通过分析,作者展示了中国主体式思维的优缺点,这种分析对于我们更好地继承传统文化,更好地理解中国文化具有深远的意义。
根据天人合一的原则,人的本性被说成是“天道”或“自然”之赋予人者,即内在于人者,这样,人的主体自身就是宇宙的中心,人的存在就成了世界的根本存在,因此,认识自身,也就认识了自然界和宇宙的根本意义。这说明中国哲学思维是以自身为对象的自反思维,是通过自我觉解和自我呈现而把握“道”或“自然”这些本体存在的。据此作者将“自反思维”作为中国哲学主体思维的特征之一。这种以人为主体的思维方式,从一开始便规定了思维的方向和任务,即它探求如何做人的问题,是内向反思自我之本性而不是向外认识事物的自然规律;其最终目的则是实现传统哲学中的“理想人格”——圣贤、真人、至人或佛。这种理想人格虽然在不同时期和不同派别各有不同,但其实现方法皆是同一种思维方式——自我反思和自我超越的主体思维。如果我们说自我反思是出发点和方法,自我超越则是对理想人格的实现。
在儒家,反求诸已在于穷理尽性,一旦穷理尽性,便可把握天道性命,从而实现真我。但由于中国哲学中的“理”、“性”等范畴皆是不可分析、不可言说的整体存在,因此对这些范畴的认识不能采用一般的认识方法。为此,儒家有“至诚”之学。《中庸》:“唯天下至诚,方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又曰:“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这种“至诚”的体道方式其实正是主体思维方式的具体体现。后来,理学继承了这种思维方式,故程颐有“脱然贯通”、朱熹有“豁然贯通”的穷理学说。在道家,“自然”被规定为人的内在本质,要把握人之本性而达到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就要通过自我体验、自我认识,从而掌握内在的永恒的自然之道。老子的“涤除玄览”;庄子的“虚室生白”,王弼的“超言绝象”,嵇康的“游心於玄默”,郭象的“冥然与万化为一”等,皆体现出这种对道整体把握的主体思维的自我超越式特征。后来佛教各派主张“言语道断,心行处灭”式的顿悟求佛方式;南北朝时道生首倡“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把佛性放置于人之内心,而成为人之本性,从而使“明心见性”成了参禅顿悟的重要手段。可见自我反思仅仅是方法,其目的在于经过“悟”的自我超越而达到理想人格。
中国哲学的“内圣外王”的价值取向还决定着中国哲学的主体实践型思维特征。仅仅具有“内圣”之德而不付诸实践,不去教化社会,让人们效法,是不可能开出“外王”之道的。因此,古代哲人皆重视切身践履,以做一个实实在在的圣人。故荀子说:“学至於行之而止矣。”(《劝学》)孔子亦要求其弟子“讷于言而敏於行”,孟子要求人们“先立乎其大者”。后来,宋明理学继承了这种思想。《朱子语类,卷十三》:“学之之博,不如知之之要;知之之要,不如行之之实。”道家同样亦很重视在实践中体验人生道理。庄子《庖丁解牛》揭示出,要自由自在地生活在人世间而不遇到困难,唯一办法就是现实体验。这种体验所得在某种程度上的不可言说性,被玄学发展为只重心领神会的“超言绝象”之学,被佛教发展成“随处体认佛性”“顿悟成佛”的参禅方式。中国哲学这种注重现实体验的特征,成为中国人注重在现世实现人生理想的哲学基础,它促使人们自觉地去实行道德修养,处理好现世人事关系,达到一个和谐自然的社会环境,为自己找到一个“安身立命”之地。道家思想的传播,佛教的禅宗流派之兴盛皆可从中国人的这种现实关怀找到根据。但这种现实关怀亦容易流为社会之弊端,如魏晋时的享乐主义,各代的官僚结党营私等。
中国哲学是以人为主体,以人为认识对象的思想体系。人是有情感的动物,这就决定着“情感体验”乃是中国哲学主体思维的重要特征。根据“天人合一”的哲学出发点,天人相通,人有情感,自然会推及事事物物以至苍天皆有情感。人们把自己之情感,投射到自然界及社会群体,从中体验人生之乐。孔子的“曾点之乐”便是以审美形式表现出的道德体验,它具有强烈的社会内容,映射了孔子“老者安之,少者怀之,朋友信之”的理想。庄子的“鱼之乐”则可谓道家的情感体验的典范。以往学者常从认识论角度解释之而得出庄子乃不可知论者的结论,其实,这种观点是不全面的。该书作者为此指出:“这根本不是一般认识论问题,而是一个情感体验的问题。在这里,人与自然不是认识上的相对立,而是人把自己投入到自然界或“切入自然”,从中体会自然之乐。把这种乐投射到鱼的生命活动中,就会感到鱼也有一种乐,鱼之乐乃人之乐之体现。纵观历史,我们可以发现这种思维特征在中国文化中举足轻重的地位。杜甫诗中的“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芙蓉泣露香兰笑”,范仲淹《岳阳楼记》中天气的阴晴不同与人心的忧喜之别,关汉卿《窦娥冤》中的天人感应,曹雪芹《石头记》中的木石姻缘,以及现实生活中的山岳封禅,河流祭祀,或喜或忧,展示给人们一幅巨大的情感体验式画卷。如果说吴均《与朱元思书》再现了庄子心境逍遥的境界;张载之《正蒙》则是对孔子“曾点之乐”的切身体验之所得。佛教禅宗的情感体验方式继承了道家的体验方式。后来,宋明理学家集儒释道之大成,融合道德体验与自然情感体验於一体,这就是理学家体验到的“仁者万物一体”之境界。
当然,中国哲学的情感色彩更多地还是表现在人与人的关系上,至少儒家如此。儒家以“孝悌”为立身之本,由此推出仁、义、礼、智、信等范畴,以追求一种“天下一家”的大同世界,由此而形成儒家注重道德教化而轻视法制的传统;但中国之大一统之观点,中国人之追求社会和谐的人生指向亦应归功於儒家。
总之,作者通过对中国哲学主体思维特征的论述,揭示了传统的“天人合一”式哲学思维乃是通过其为主体——人进行自我认识和自我扩充而达到的,人由生来具有而未自觉的“天人合一”状态,经过自我认识和自我扩充,从而达到自觉的“天人合一”状态,无论儒家的穷理尽性,道家的反朴归真,还是佛教的明心见性,都不过要人们觉悟到人与自然,或我与非我的和谐统一,都旨在去除物我之界限,达到万物一体的“乐”的境界。这种以人为主体和对象的哲学思维特征,贯穿於中国各家思想体系之中,人们通过对人类自身之反思而进一步实现其社会和自然性意义,因此,作者归结主体思维为中国哲学思维方式之核心,存在着中国文化渊源上的合理性与发展上的必然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