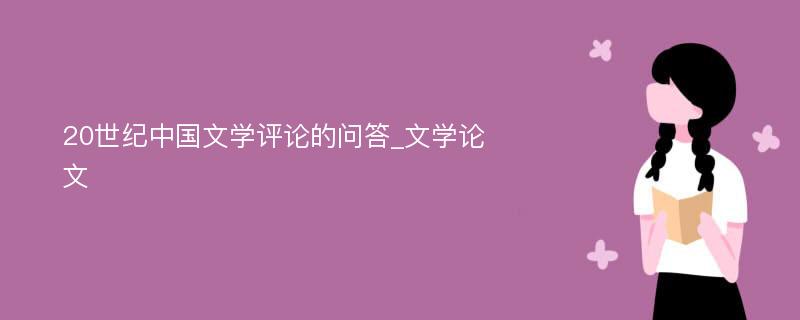
关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回顾的问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二十世纪论文,中国文学论文,问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问:际此世纪之交,我国文坛回顾二十世纪有种种不同的见解,请问您有什么样的看法?
答:我注意到这些不同的见解,要回答这个问题,我觉得有必要拿二十世纪文学跟它以前的文学、特别是十九世纪的我国文学作一番比较。
中华民族有悠久的历史,创造过许多辉煌的文学时代,涌现过像屈原、司马迁、陶渊明、李白、杜甫、苏轼、辛弃疾、关汉卿、曹雪芹等伟大作家。但是到了十九世纪,以文言为主要表达媒介的我国文学由于内容的陈腐和形式的僵化,已日益不能适应社会生活发展的需要。在我国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过程中,龚自珍的启蒙文学也好,曾国藩和桐城派的古文运动也好,还是王闿运等的“同光体”也好,都无法挽救旧文学的衰颓。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梁启超、黄遵宪等才提出“文界革命”和“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的主张。维新派在推动我国旧文学向新文学转变的贡献,固然功不可没。但“五四”前,文学革命的倡导者仍然感到有“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陈独秀:《文学革命论》)之必要。整个中国文学从陈腐的旧观念、旧形态到充满省略的新观念、新形态的转变,是在二十世纪完成的。这真是几千年来我国文学最伟大的划时代的革命,是实现我国文学走向现代化,也是使我国文学从少数贵族和文人的小圈子走向最广大的人民大众的革命。这场革命使我国文学从内容到形式、从生产到消费无不产生翻天覆地的变革。当然,这变革又是与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的变革联系在一起的,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联系在一起的。毛泽东早就对这场新文化和新文学的运动作出高度的评价。1940年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二十年来,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证之整个二十世纪文学,这个评价实在不过分。
如果从二十世纪世界范围再作一个比较,我们会看到,就文学而言,世纪初我国文学是落后于许多国家的现代文学的。不但不如欧美的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如俄罗斯和日本。因而从文学反映现实的广阔视野和丰富的形式技巧来说,要使我国文学新生和蜕变,就不能不学习和引进这些国家的文学及其经验。这是合乎后进国家总向先进国家学习的历史规律的。要看到,没有这种学习与借鉴,是不可能产生二十世纪中国新文学的。这不是什么耻辱和无能,恰恰表现了不甘耻辱的自强。我们知道,俄罗斯文学的很高成就正是由于向法国文学学习和借鉴才获得的。在这学习过程中,艺术构思与表现手法受到外国文学的启发,乃至出现某些模仿,并不奇怪。俄罗斯文学借鉴法国文学也有这样的现象。只是为了表现本国本民族的生活内容,并用本民族的语言书写,那么这种借鉴就是有益的,就像鲁迅的《狂人日记》受到果戈理的影响,但它毕竟是中国作家的新作,从内容到形式都被赋予了中华民族的特色。至于从文学所生存的社会历史与思想文化背景而言,二十世纪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产生了强大的社会主义运动和多个社会主义国家,还产生前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压迫被奴役的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和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争取自身平等权利的斗争。而二十世纪的中国不仅长期处于战争的旋涡,而且处于上述多种运动与斗争的前沿地位。在此特定情势下,我国文学虽然刚从长期的封建主义传统中摆脱出来,它却很快便在上述系列运动和斗争中超越了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而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我国二十年代的革命文学、三十年代的左翼文艺运动、四十年代的人民根据地文艺运动和新中国的文艺都是世界社会主义文艺运动的一部分。它和整个社会主义文艺运动一起为推动二十世纪历史的进步和人民的解放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整个二十世纪下半叶,我国文学艺术都属世界性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部分。就其所表现的思想境界而言,共产主义提倡为全人类彻底解放而无私奉献的精神,正超越只求个人解放的旧人文主义精神。因为人类的解放包含着个人的解放。共产主义理想的崇高性就在这里。
所以,无论从纵向或横向的比较来看,都应该承认,二十世纪我国文学实在作出了伟大的贡献。在诸多文学先辈和至今仍然活跃于文坛的广大作家的努力下,二十世纪文学不但完成了我国从旧文学到新文学形态的历史性转变,而且实现了人类思想史上意义深远的超越,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意识形态跳到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还使文学走向广大人民的心灵,使读者的精神境界变萎靡、柔弱、悲哀、彷徨、暗淡为强奋、雄放、豪迈、坚定和明朗,重铸了中华民族的灵魂,从而为我国二十一世纪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而宽阔的道路。即使在这过程中,我国文学也产生过种种的支流与逆流,社会主义文学运动中更有“左”的错误的危害,那也掩盖不了文学主流发展的上述历史作用和意义。
问:您能否更具体点说明二十世纪我国文学的历史贡献?
答:在我看来,这种贡献至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它确立了以审美为主要特征的多层本质的现代文学观念。大家知道,我国历史上长期都把文章视同文学。曹丕的《典论·论文》虽提到“诗赋欲丽”,触及审美的特点。但他所举文类仍包含奏议、书论、铭诔等等。诗文之外的小说、戏剧反长期被排斥于文学正宗,视为难登庙堂的末技。直到二十世纪初王国维才明确认识文学的审美特征,指出“美术中以诗歌戏曲小说为其顶点”(《红楼梦评论》)。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也说:“由纯文学上言之,则以一切美术之本质,皆在使观听之人,为之兴感怡悦。”从二十世纪初到今天,我们已经明确认识到文学属于社会的审美意识形态,是以语言符号作为表达手段的艺术,也是通过形象反映社会生活、表现人们思想情感的艺术;尽管有些文学作品看不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性,但从大多数作品所构成的文学整体而言,它作为最重要的艺术之一,确具有社会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性。对文学本质特征的上述认定非常重要。它对于提高文学创作的审美自觉和作品的艺术魅力、社会功能,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第二,它大大拓展了文学的表现内容和形式。二十世纪我国文学题材的拓展从天上到地下,从历史到现实,从神仙鬼怪到未来的科学幻想,从人们的显意识到潜意识,可以说真正是“包罗天地,晖丽万有”。人的性格、行为、心理,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都得到前所未有的广泛而深入的描写。而文学的品类和形式更发展为繁多的家族,无论诗歌、小说、戏剧、散文,都有许多的分蘖(如小说就有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和微型小说等篇幅形式的划分,还有社会小说、言情小说、心理小说、哲理小说、伦理小说、推理小说、科学幻想小说之分;散文也涵盖小品、随笔、杂感、速写、报告文学、传记文学、回忆录等等),还出现了影视文学、童话等新的品种。可以说,经过百年的引进和努力,凡是世界上有的文学形式,我们也都基本有了。而人家所没有的,例如旧体诗词以及相声、快板、鼓词等曲艺和传统戏曲形式,我们仍在发展和丰富。在这种内容和形式的变化过程中,从写贵族到写平民,从用文言到用白话,应是最重要的变化。
第三,它不断提升了文学的精神境界和社会功能。康有为曾抨击十九世纪的旧文学“吟风弄月各自得,覆酱凝薪空尔悲”(《与菽园论诗兼寄任公、孺博、曼宣》)。虽然那时的先进文人渐有民主意识,从西方开始学到某些新思想,但主流文学仍充满封建主义意识和奴化思想。“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打倒孔家店,提倡民主和科学,并且呼唤“人的文学”,但在列强侵凌、军阀混战、阶级对立的社会环境中,抽象很多,就靠《离骚》《九歌》和《天问》,便足以使他千古不朽而位列伟大。作为伟大的思想家和诗人,毛泽东的成就在二十世纪的世界上有几个人能与他比拟的呢?他的思想,包括他的文艺思想之具有世界广泛的影响,他的豪迈雄放的精美诗词更是脍炙人口,誉满海内外。而鲁迅,毛泽东是这样评价他的:“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毛泽东是在延安认真读过《鲁迅全集》后作这样的评价的,我以为,今天我们还没有理由去改变这种评价。单是鲁迅所创造的阿Q的形象, 就足以与哈姆莱特、堂·吉诃德、奥勃洛莫夫等闻名世界的文学典型相并肩,都属于对人性弱点的最深刻的发现、发掘和最成功最独特的艺术概括。自然,无论是毛泽东还是鲁迅,都有他的局限和不足。毛泽东甚至犯过严重的错误并给我国二十世纪文学的发展带来过损失和灾难。但“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历史上的伟大人物无不可以挑剔出他的缺失。而伟大人物之所以伟大,则在于他的贡献毕竟大于他的缺失。如果攻其一点,不计其余,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那恐怕不是评价人物包括作家的公正的办法。
至于说到经典作品,我对于称文学作品为“经典”,不是很赞成。但二十世纪还是有许多可传之后世的好作品,也不妨称之为“经典性作品”。当然是否真正是具有恒久生命力的好作品,还需要经过历史、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反复检验。个人的看法不过是一家之言。近几年已经有学者编选过不止一本冠名“经典”的作品选。人民文学出版社还请专家学者投票甄选百年优秀作品,我也被聘为评委,参加投过票。我觉得像鲁迅的《呐喊》《彷徨》,郭沫若的《女神》《屈原》,茅盾的《子夜》,巴金的《家》,老舍的《骆驼祥子》《茶馆》,夏衍的《包身工》《革命家庭》,田汉的《义勇军进行曲》,曹禺的《雷雨》《日出》,闻一多的《红烛》,冰心的《寄小读者》,艾青的《火把》《归来的歌》,光未然的《黄河大合唱》(歌词),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贺敬之的《白毛女》《雷锋之歌》,郭小川的《向困难进军》《望星空》,孙犁的《风云初记》,杜鹏程的《保卫延安》,梁斌的《红旗谱》,柳青的《创业史》第一部,姚雪垠的《李自成》,还有新中国成立后涌现的许多著名作品,都是深刻反映社会现实,有力地表现时代精神,而且艺术上也富于创造和感染力的。这些作品都不仅是十九世纪的中国难以产生,也是二十世纪的其他国家所难以产生,它们真正可以构成二十世纪中国的“时代的镜子”。有的青年朋友往往拿外国的某一作家和作品来比较,断言我国的就比不上人家。或者认为中国的作家作品没有得到诺贝尔文学奖,也就自我菲薄。其实,许多伟大的作家和作品都没有得过诺贝尔奖,列夫·托尔斯泰就是,而有的获奖作家却入不了文学史。1986年我参加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当代文学国际研讨会就听瑞典皇家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教授发言说:“如果鲁迅和老舍的作品当年就译成瑞典文,他们也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可现在他们都去世了,而诺贝尔奖是规定只颁给在世的人物的。”诺贝尔奖虽然具有世界性影响,但评委的视野难免会有局限。所以不能说没有获奖的人中就没有伟大的作家。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中有很多作家还缺乏更多的人去加以深入研究,可能其中还有伟大的作家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当然,一个国家在百年内也不可能出现很多伟大作家。否则伟大也就显不出伟大了。而影响广泛的杰出作家却远不止一个、两个。
问:那么,您认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是不是也有缺失呢?
答:这方面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例如有人认为主要的缺失是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太密切,政治对于文学的干预太多。也有人认为中国知识分子太软弱,缺乏独立的人格,缺乏艺术上精益求精的追求,过于浮躁。还有一种看法,认为中国作家缺乏自己的思想体系,也缺乏艺术的独创性,只是引进别人的,等等。说起来都不是没有一定道理。情况确实相当复杂。从历史上看,出现文学辉煌时代的社会机制也是复杂的。政治家爱好文学、关心文学,会有助于文学的繁荣。但能否出现大作家又不是政治家的意志所可左右。我国历史上建安文学的兴起,固与曹操父子爱好文学分不开,但建安七子无不生于乱世,而且有的人如孔融还被曹氏所杀。盛唐时代出现李白、杜甫和许多名诗人,这可能与当时的科举要考试诗文有关,唐玄宗李隆基也爱好文学和艺术。但李、杜都未当成大官。实际上他们不少佳作都写于安史之乱前后。中唐之季,白居易前期有不少好诗,当了大官后反而写不出好诗来。可见,要说清楚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并不容易。就二十世纪文学而言,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也是复杂的。不能绝对地说文学脱离政治就好,与政治关系密切就不好。如果说要吸取经验教训,我倒认为政治家、政党和政府还是应该多关心文学,宏观上多为文学的繁荣创造条件,但我也赞成政治家或政党、政府微观上不要过多干预文学艺术的具体创作。邓小平同志说得很对:“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但我不认为文艺与政治保持密切的关系就绝对是坏事。文艺与政治保持密切的关系,可以说是中国文学的一个悠久的传统。从屈原起直到鲁迅,直到今天,都仍然如此。因为中国知识分子总是忧国忧民,而且还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即使“人在江湖”,也要“心存魏阙”。陶渊明虽然归隐田园,不为“五斗米折腰”,却还要抱着“桃花源”的政治理想。李白求官不成,浪迹江湖,似乎潇洒得很,实际上由于政治抱负未能实现,一直有失落感。我看,中国知识分子包括作家关心政治,关心人民大众的福祉和疾苦,总想参与政治,乃至用文学作品表达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人民的心声,这是个好传统。这也是历史上许多伟大作家所以伟大的一个重要条件和标志。恩格斯说:“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和喜剧之父阿里斯托芬都是有强烈倾向的诗人,但丁和塞万提斯也不逊色;而席勒的《阴谋与爱情》的主要价值就在于它是德国第一部有政治倾向的戏剧。现代的那些写出优秀小说的俄国人和挪威人全是有倾向的作家。”(《致明娜·考茨基》)可见,西方文学史上的情形也如此。这些作家的伟大跟他们鲜明的政治倾向正分不开。如果一个作家连关系人民死活的政治都不关心,那他很可能只不过成为供人逗乐的侏儒式人物罢了。所以,问题不在于要否与政治保持密切的关系,而在于政治倾向是否有利于历史进步,是否有利于广大的人民。二十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尽管也有站在人民对立面、站在反动统治阶级一边,乃至当汉奸的,但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包括其中的作家,或先或后都站到人民一边,为人民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作出自己的贡献。从邹容到秋瑾,从鲁迅到左联五烈士,为救国救民和为人民革命而献身的作家难道还少吗?即使闻一多、朱自清那样的民主主义知识分子,他们的民族气节和铮铮铁骨,难道不都足以彪炳千秋吗?笼统地责备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和作家软弱,乃至品格不好,是与历史实际不符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所以有很高的价值,跟它产生的优秀作品中的进步的、与人民相一致的政治倾向正紧密相关,也与许多作家在历史传统的继承中,在革命斗争的烈火中,在与人民群众的结合中不断铸造自己的崇高品格分不开。如果说经验,这条正是很重要的经验。而疏离政治,躲到象牙之塔里去吟花咏草,抒发一己之悲欢的唯美主义作家,他们的作品即使不乏一定的审美价值,也确为文学的百花之坛增添某些彩色,但仅靠他们,毕竟撑不起世纪的文学大厦。给他们戴上“伟大”的桂冠是很难的。
问:从您上面所说的意见中,我感到您似乎有自己很坚持的价值取向和标准,是吗?
答:是的。但我以为在文学评论和研究中,谁都有一定的价值取向和标准。在价值取向和标准方面既有个人性,也有集团性(包括阶级性和民族性)和时代性。或者说,既有普泛性的取向和标准,也有特殊性的取向和标准。价值体现与物的一种关系,即物能够满足人的何种需要?因此,价值既取决于物自身的质的规定性,又取决于人的需求选择。文学艺术的质的规定性,已如上述。而人的需求选择,则因时代的进步而有所差异。别林斯基说:当今的诗人“已经不能生活在幻想的世界里面了:他已经成为当代的现实疆域里的公民;一切发生过的事情必须生活在他里面。社会已经不愿意把他看做是一个娱人的角色,而要他成为它的精神和理想生活的代言人;成为能够解答最艰深问题的预言家;成为一个能够先于别人在自己身上发现大家共有的病痛、并且以诗的复制去治疗这种病痛的医生。”(《阿波郎·迈科夫的诗》,《别林斯基论文学》第24页)。这可以说是现代人的要求比较高的文学价值观。自然不排除有些人只要求文学满足自己的娱乐就行了的价值取向。应该说文艺批评取向和标准是由批评者的世界观、人生观、审美观为思想背景所构成的价值体系。思想背景近似的,价值取向和标准也近似,如果思想背景全然不同,价值取向和标准必然产生差异。但不同中也还可能有相同之处。毕竟人类在进步的历史过程中,对于真善美的追求是很普泛的。何者为真为善为美,开头人们会有意见的分歧,但通过交流和沟通,许多方面又会逐渐一致起来。所以,我以为,这方面还需要多交流多讨论。我希望听到更多同行们的不同见解。
标签:文学论文; 鲁迅论文; 鲁迅的作品论文; 中国文学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艺术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读书论文; 文艺论文; 作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