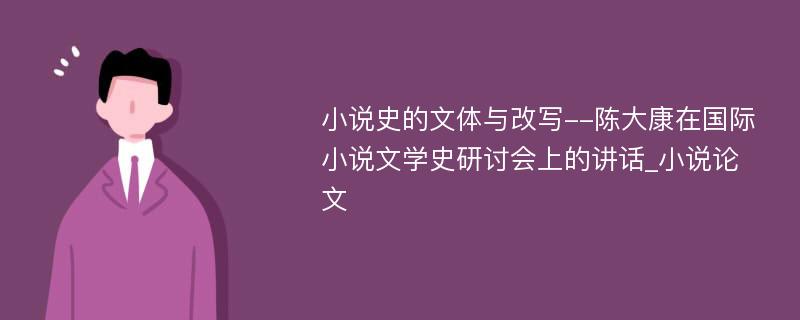
“小说史”的体例与重写——陈大康在“小说文献与小说史国际研讨会”上的演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小说论文,体例论文,重写论文,文献论文,国际研讨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之后,各种小说史恐怕已有百部,体例多为作家作品分析的组合。这样便于读者了解重要的作家作品以及相应评价,也自然勾勒出一条史的线索。可是数十年来都是这般体例,难道就没有另一种写法?而且,究竟何谓“小说史”?上述体例能涵括小说史应有的内容吗?
被搁置的疑问
小说史上颇有些悖于文学常理的现象。这些奇怪现象汇合成一种责难,似在无声地发问,为什么在七十余年的研究中它们一直被搁置于一旁?
小说史上颇有些悖于文学常理的现象。如按文学发展规律,优秀作品问世后一般都能迅速传播,可是从《三国演义》到《红楼梦》等最优秀的小说,从问世到广泛流传都有几十年甚至一二百年的时间差。优秀作品的问世理应会刺激创作繁荣,可是《三国演义》与《水浒传》问世后却出现近二百年的创作萧条。按文学发展规律,有重大影响的优秀作品会促成新的创作流派,如通俗小说第二个创作流派神魔小说就是在《西游记》影响下形成。但此作问世于嘉靖后期,后来的神魔小说却集中出现在万历三十年前后,那条规律居然要潜伏半个世纪,而讲史演义的形成与开山之作《三国演义》的问世竟约相隔两个世纪!文学史上新流派的产生一般都得力于功底深厚且有创见的文人,可是上述两个流派的形成,却首先得力于书坊老板,他们还曾长时期地主宰创作领域。文学贵在独创,明代小说情形却正相反。作者们长时期地在改编正史、话本、戏曲与民间传说的圈子里徘徊,有的还整回地抄袭他人,直到明末才出现少量文人独创的作品。奇特的现象还有。自冯梦龙的“三言”问世后,短篇小说创作日趋繁荣,至清康熙朝作品总数已逾六百。然而随后百余年里,短篇小说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若观察通俗小说数量的分布,又可看到令人惊讶的不均衡:前期曾有近二百年的创作空白,而作品总数的大半,竟又密集于晚清三十余年。这些奇怪现象汇合成一种责难,似在无声地发问,为什么在七十余年的研究中它们一直被搁置于一旁?
被搁置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以作家作品分析或论述的组合为体例时,这些现象不会进入研究者的视野,而小说史之所以采用这样的体例,又有其历史原因。古代小说研究首先须得钩稽相关资料,辨析认定作者生平经历、作品成书年代、情节本事源流以及各书版本嬗变等;其次是分析探讨具体作品艺术上的成败得失与思想倾向。这两个层次的研究有一定基础后,宏观考察才能开始。由于较长时期停留于单个作家作品的研究阶段,原有的思维方式因惯性而伴随着一起进入了小说史研究领域。于是一种误解油然而生:仿佛前辈学者从资料考证到艺术、思想分析等方面已有研究或涉及,现在只需按年代顺序与题材分类等综合整理现有成果,即可撰成一部小说史论著。这样的论著自然不会去解释上述种种似是奇特的现象,或者说,是这些现象暴露了小说史论著体例的缺陷。而且,依此体例撰写,面貌必然大同小异,所谓“小异”,只是论及的作家作品有多少之分,篇幅有长短之别,分析的深入细致各有差异而已。
最后还须指出,在这体例中,对各作家作品的分析也有相对固定的模式,即将研究对象置于一定的时代背景中考察,并据此探讨创作的成败得失、思想倾向及其与社会种种联系,这种模式可以归纳为“社会——作家——作品”。运用这种方法的分析自有其合理之处,但运用的固定化限制了多角度、多侧面的审视,更不必说勾勒解释古代小说的行进轨迹了。
小说史应是创作史
“小说史”定义为“小说创作史”更为合理,须知某阶段作家作品甚少乃至全无,也同样是一种需探究原因的创作态势。若视小说史为“小说作品史”,那么创作空白就无法进入研究视野。
上述奇特现象都应属“小说史”的内容,但作家作品分析对此无法解释,这证明了“小说作品史”观念的狭隘,也表明了并非将研究具体作家作品时形成的思想与方法移用于全体就可称为宏观研究。显然,“小说史”定义为“小说创作史”更为合理,须知某阶段作家作品甚少乃至全无,也同样是一种需探究原因的创作态势。如明初《三国演义》、《水浒传》、《剪灯新话》问世后,创作出现长时期停滞。若视小说史为作品分析的有序组合,那么创作空白就无法进入研究视野;若以“小说创作”为研究对象,那么不管状态如何,都须说明其成因。更正定义意味着撰写体例必将相应变化,而要切实发现并解决问题,还须经历拓宽视野、更新观念、改进研究方法与扩建理论体系的过程。
从整体中抽取作家作品作分析是小说研究的必经阶段,但抽取不可避免地要伤害甚至割裂整体间的筋络,小说史研究应特别注意那些曾被暂时舍弃的种种联系,因为古代小说整体并不等于所有作家作品的简单叠加,宏观研究须遵循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原则,重点应是构成整体的各部分间种种有机联系。有个典型的例子:以往对熊大木评价历来不高,因为他的《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只是《精忠传》等的白话改写,《南北两宋志传》又将《五代史平话》全数抄入。然而,当时《三国演义》、《水浒传》刊行不久,读者热情欢迎通俗小说并要求读到新作,文人却囿于传统偏见不屑于创作,熊大木的四部长篇小说就相继问世于稿荒严重之时。由于文化与艺术修养的限制以及强烈的牟利动机,这位书坊主只能出产粗率之作,但读者的饥渴使它们问世后即不断被翻版盗印,并刺激了其他书坊主跟进。从嘉靖年间仅有几部作品,到万历后期创作初步繁荣的过渡阶段中,这些作品壮大了通俗小说声势,并刺激后来者投身创作。倘若没有熊大木等人,通俗小说在嘉靖中到万历初的五十余年里就几无新作可言,刚开始启动的创作连锁反应就又会出现较长时间停顿。很显然,只有把握诸种“联系”,方可全面了解那些作品的价值与意义。由此还引出一个命题,即作品对创作发展的价值并非自然地与其文学价值相对应,而在作家作品分析阶段,这区别是难以发现的。清中叶李海观的《歧路灯》可从反面证明这一点。这部长篇小说思想与艺术均不见弱,可是它在两个世纪里仅靠抄本存世,当然无法对古代小说创作发展产生积极的意义,因为它与其后的作家作品都无“联系”。
“联系”的追寻与确定,还可帮助化解疑团。如明中叶文言小说的简陋稚嫩常使人疑惑不解:明人为何不学习借鉴前人的优秀作品?如果察寻明中叶作品与前人之作间的“联系”,可以发现两者的互相隔绝。《世说新语》自南宋刊刻后直到嘉靖十四年才首次刊出,《夷坚志》刻于嘉靖二十五年,此时四百二十卷只剩五十一卷了,《太平广记》刊行是嘉靖四十五年。子部小说类作品大多有这样的遭遇。尽管历史积蓄雄厚,可是前代优秀之作只有收藏了一二百年的宋版或抄本,一般人无缘得见,明中叶文言小说创作的基础实是薄弱得很。对“联系”的追寻不仅弄清了当时创作状况的成因,而且还可帮助纠正一个误解,即作家创作时未必定能受前人之作的影响。
“联系”的追寻与确定不能只局限在创作领域,前面所列种种反常现象,已证明文学发展规律在这个领域常要走样变形,唯一合理的解释是还另有摄动力在。这就需要检测小说发展的各个环节,从创作一直追踪到读者的反响,包括作品到达读者手中的方法与途径;同时又考察读者群体的反响如何制约后来的创作。这一不断反复的盛衰起伏历程,可用公式“创作——传播——创作”概括。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开始将传播问题纳入小说研究时,曾遭到“这不是文学研究”的批评,可是若拒绝越界探索,文学领域的一些问题恐怕始终无法解决。
明清小说的双重品格
小说不像诗词赋曲那样有多种传播途径,一部数十万字的作品口诵笔录都不易,而且就算有几十部抄本,又能供多少人传阅?小说,特别是通俗小说,须有印刷出版业支撑方能充分发展,双重品格因此而形成,这是解释种种悬疑的一把钥匙。
文学作品只有广为传播,才能充分体现价值,产生与本身相称的影响,并激励或启迪后来的创作。但小说不像诗词赋曲那样有多种传播途径,一部数十万字的作品口诵笔录都不易,而且就算有几十部抄本,又能供多少人传阅?因此,小说,特别是通俗小说因本身特点的限制,须有印刷业支撑方能充分发展。
于是作家创作到读者阅读这一完整过程明显可分成两个阶段。创作生产精神产品,这是以往小说研究的主要内容;作品经书坊刻印成书流向各地时,它仍是精神产品,同时又是实实在在的商品。一部作品付诸刊行就意味着被投入了商品生产,必然得接受这方面的法则与规律的支配,它的艺术水准、思想倾向等文学因素,常被书坊主转化为可估量的经济价值,该精神产品的价值须随商品价值的实现而实现。明清小说发展是精神产品与商品相结合的不断再生产,而若将各部作品的创作与传播都置于那不断再生产的过程之中,那么又可以发现,就在精神产品生产的同时,商品生产的因素往往已或多或少地融于其间。尚友堂主人眼红于冯梦龙“三言”,就央求凌濛初编撰《拍案惊奇》;该书销售情形如同预想,于是凌濛初又编撰了《二刻拍案惊奇》,而冯梦龙的编撰其实也有“应贾人之请”的成分。色情小说的涌现是更突出的表现,情痴道人在《肉蒲团》第一回里就公然宣称,他写这部小说就是“要世上人将银子买了去看”。甘于寂寞、苦心孤诣地追求艺术创造的作家毕竟是少数,而且他们作品的出版、传播以及对后来创作的影响都无法摆脱商品生产、流通法则的制约,因此从整体上看,还是得承认小说在明清时既是精神产品,同时又是文化商品的双重品格。
双重品格发现后,过去往往混同使用的“问世”与“出版”概念就应该严格区别。“问世”是精神产品完成的标志,“出版”意味着商品生产的结束,作品可以在较多读者中流传;前者表明小说史上增添了新作,而惟有后者方能保证产生与该作品相称的社会反响,从而影响后来的创作。这两个概念被严格区分后,《西游记》与在它影响下形成的神魔小说流派之间半个世纪时间差的问题便迎刃而解:《西游记》直到万历二十年才首次由世德堂出版,其后神魔小说接连刊行,终于在万历三十年前后形成流派,其间并无令人诧异的时间差。从明初到嘉靖年间通俗小说创作极度萧条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当时的印刷业还不足以支撑小说创作的发展与繁荣,明代印刷业的大发展要到嘉靖年间,而这正是通俗小说重新复兴之时;晚清小说创作之所以极度繁盛,当时西方先进的印刷技术的引进是重要原因。小说异于许多文学体裁之处是对于物质生产具有相当大的依赖性,双重品格因此而形成,这是解释前所述种种奇特现象的一把钥匙。
小说发展遵循的是文学与商品交换规律糅合为一体的法则,出版环节对创作的影响与作用要比我们想象大得多,在明代嘉靖后期到万历中期约半个多世纪里,还出现过创作由熊大木、余象斗等书坊主及其雇佣的下层文人主宰的极端事例,小说史上色情小说泛滥等许多不良现象都与这属于本质性特征相关联。然而,不能因此就对双重品格取简单的否定态度,实际上它对小说发展确曾起过积极的推动作用。
首先,它在最大范围内壮大了小说的声势。书坊的介入,改变了只有抄本在小圈子中传阅的状况,否则,闭塞会使许多潜在的作家想不到去撰写小说,即使创作也难以借鉴以往的成败得失,这就可能导致创作的萧条乃至空白。其次,商品供求法则不断调节读者与作者的关系。供不应求时,书坊采取种种措施刺激创作以满足读者需要,反之则改变择稿标准,迫使作者变换创作题材。各流派的崛起及式微的原因并不都能被商品法则涵括,但确由它的调节而显现。再次,书坊为招徕顾客,一般都乐意恳请名士评点或撰写序跋,借其声望抬高作品身价,而撰稿者也常借此分析总结作品特点,从而为小说理论的发展增添了新内容。通过点点滴滴的积累,古代小说理论终于形成较全面又颇具民族特色的体系,它反过来又推动了创作。最后,商品生产、流通法则在客观上保护了小说的生存与发展。封建统治者曾几次严厉禁毁却无法实现预期的目标,其中最直接的原因便是竭力维护财源的书坊主的顽强抵制。封建统治者动用了国家机器,而书坊主则恃广大读者为后援。封建统治者遭到的是双重失败,既无法消灭广大群众喜爱的文学样式,也无法消灭给书坊主带来丰厚利润的特殊商品。
小说史的重写
发现小说的双重品格后,需把握的种种联系骤然增多,小说史其实是作者、书坊、创作理论、文化政策和读者等相关因素联系与作用相交织的有序运动过程,需要设计诠释功能更强的研究模式。
发现小说的双重品格后,需把握的种种联系骤然增多,于是需要设计诠释功能更强的研究模式。若以产生直接、重大且又持续的作用为标准,那么不可小视者大体上是下列五种。
首先是作者,对此无须赘言。其次是书坊。书坊主时刻关注读者的兴趣爱好及其变化,其择稿标准及变化是流派盛衰的重要原因,他们对趣味低下作品的泛滥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为争取更多读者以牟取更大利润,他们想方设法降低书价,形成“市井粗解识字之徒,手挟一册”的传播局面。封建统治者禁毁小说时,书坊主为维护利润直接与之周旋、抗争并最终使该政策流产。再次是伴随创作而发展的理论。创作受到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小说观的制约,在嘉靖至万历前期,只有演述史实、以忠孝观念教育百姓的作品才被认可,于是将正史通俗化的讲史演义便占主流地位。李贽等人自万历后期起在理论上提高小说地位的努力,促进了创作的迅速繁荣,梁启超提倡“小说界革命”也是类似的典型。理论反过来也受创作的制约,后者是它存在的前提并每每促进了它的发展。第四是封建统治者的文化政策。清初中央政府接连令禁小说,曾导致半个世纪的创作萧条。明代有相反的例证。官方最先刊刻《三国演义》与《水浒传》,使之摆脱仅靠抄本流传的困境,从理论上肯定小说功用与地位的也正是统治集团中的某些成员,这是创作能步入繁盛的重要原因。最后是读者。众多读者类似的选择会形成强大压力,并通过书坊实现巨大的强制性影响。沟通作者与读者的主渠道书坊只以畅销为标准作单向迎合,某些阶段受世风浸渍的读者口味也不值得称道,但从长期发展趋势来看,小说全靠读者支持才能生存与发展,广大读者的要求总体上也健康合理,众多读者的共同要求是诸因素中最强大深远的力量。以上五个因素又都交叉影响、互相制约,形成一股合力影响了小说的发展。
以此模式作观照,小说史其实是各相关因素的联系与作用相交织的有序运动过程,对此不能套用固定的公式作解析。如人们习惯以排中律作判断,一部作品要么是改编,要么是独创,非此即彼的归队反而导致了混乱。其实,再拙劣的改编中多少有独创的成分,最优秀的独创作品《红楼梦》中改编的内容也不能算少。曹雪芹将《五色石》的“补天”思想、《平山冷燕》的“山川秀气尽付美人”的见解都化入作品,也采用了《金云翘传》的构思与情节,更整段移用了《定情人》的文字。冯梦龙据许浩《复斋日记》115字的记载写成近万言的《陈多寿生死夫妻》,这似不能称为改编,但称独创同样不妥,因为框架、情节与人物全依原作。文学领域里诸如改编、独创一类内涵明确而外延不确定的模糊概念比比皆是,硬套排中律而引起的争论也因此时时可见。
从改编到独创,是通过从明初到清中叶四百年的不断量变而完成。小说史上确有渐进过程的中断与质变,如《三国演义》与《水浒传》的问世,是通俗小说从诉诸听觉到供案头阅读的飞跃。然而在传统影响笼罩下,许多变化却是缓慢的渐进。如文体上,明中叶风气是无诗文羼入不得言小说,有的小说中诗文篇幅比例已逾50%。随着对小说作用、地位及其创作方式的认识逐渐深化,非创作必需的诗文羼人相应减少。《刘生觅莲记》等已降至20%,而《丽史》等已只占10%。自明末以降,创作已不在意诗文的羼入。与此相类似,从明末到清初,拟话本中“头回”也是逐渐减少乃至消失。这些事例都证明了渐进是小说史上极重要的变化形式。
在某些历史阶段,创作演进又以平庸之作迭出为主要表现方式。如清初才子佳人小说艺术或思想均无甚高明,但它们却形成“团粒结构”似的群体,若无此铺垫,后来也不会出现《红楼梦》。小说史上类似情况还有不少,若因子庸而舍弃,就无法解释某些重要的历史现象。除研究的完备性以及平庸之作群体的中介过渡意义之外,平庸之作不断大量出现且确能广泛流传,其实与当时社会氛围、创作整体水平以及读者群审美情趣等相适应,这正是制约创作发展的重要因素,因而也应是研究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面对复杂的小说发展形态,只要能解决问题,各种研究模式与方法都可以去尝试。这里之所以论述了一些思想方法,只是感到目前对此有必要作强调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