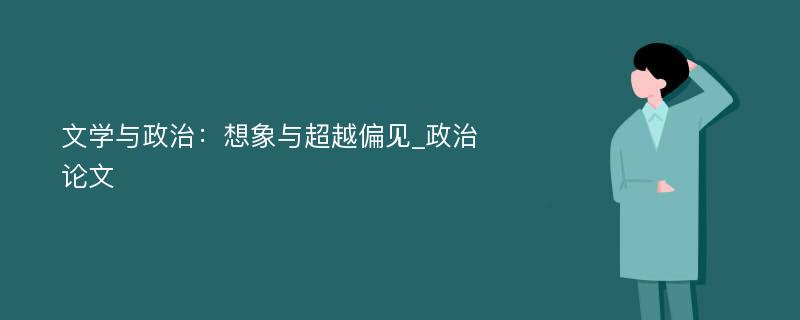
文学与政治:可以“想象”与超越偏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偏见论文,政治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63(2011)07-0144-07
关于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讨论,在百年来明昧交织的社会文化景观中从未间断过。既往的论述,由于纠缠在复杂的人事关系、历史恩怨中,往往多了情绪的表达,少了学理的深入阐释。如何心平气和地将两者关系拉入到常态的学理视域内加以考察,或许才是理顺两者关系的开始。但更为根本的是要认识到文学与政治的本质特性,它们都是对于一种美好生活的期待,这才真正建构了它们的连接,并因这种连接的复杂性产生它们之间的张力关系,使得政治因为有了文学的助成而强化了自身,文学因为有了政治的内涵而丰富了自身。但文学还是文学,政治也还是政治,二者并没有因此而泯灭各自的界限。
当代中国的文学与政治关系论述一直发生着变化,大致可以概括为:文学对政治的依附关系(从属论、工具论)、文学与政治的疏离关系(关系论、平行论)、文学与政治的暧昧关系(多元论)。“从属论”意指文学从属于政治,是政治斗争的工具。“从属论”萌芽于20世纪国难当头之际,梁启超、鲁迅、胡适等人已经意识到文学在社会改革过程中的作用,胡适的实用主义文学思想使文学与现实政治的关系更为亲密。30年代左翼文学的形成与巩固是文学“从属论”成型期,但是有意识、有目的地将文学与政治结合起来的理论阐释还在孕育之中,“这一时期主要强调了文学与政治结合的必然性,但对于两者结合后发挥什么样的作用,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结合等问题未能清晰的阐释,同时也缺乏相应的实践活动,使得当时的理论阐述不甚明了”。①真正系统地论这种关系的是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以及新中国成立之初文艺界的大部分左翼人士对这一权威文本的神话式阐释。《讲话》认为文艺应该为人民服务,为革命战争服务,为现实的政治服务,强调文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政治功用,艺术功能退居次位。彼时的政治观点、立场成为解释与评价文学现象的标准。政治以介入文学构形的方式完成政治“成规”的建构,并使大众认同、理解、支持并加入对这一政治“成规”的规范与完善的行为中去,文学从文本到构形完全被意识形态化了。那么,文学的审美效果也“必然是一种统治的效果:个体向主导意识形态的臣服,即向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的臣服”。②
随着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到来,文学“从属论”受到质疑,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似乎被放置到了一个正常的视域内加以讨论,中国文论开始了“向内”转,其视野无疑转向了“从属论”忽视的文学的审美特性、自主性和独立性研究。在此期间,借助西方的理论与方法,形成了影响甚大的“主体性原则”、“审美原则”、“形式原则”等新的文学标准。文学于是站在了政治的对立面抗拒其规训与收编,具有强烈的虚幻性和批判性。不可否认,这种做法对矫正传统的文学与政治关系论述中忽视文学审美特征的致命弱点确实有所补益,然而,若是就此来界定文学的性质会失之偏颇。强调文学的审美独立性和自足性,并不能证明文学与政治之间就没有关联,也不代表文学不具有政治性,更不能说明文学不会成为政治实现自己目的的工具。这种做法不过是回到审美的乌托邦中去了,而这个乌托邦因没有摄入政治养分而显得轻飘,难免成为一种自慰的幻景。在阿多诺看来,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文学“领域也像经验世界一样是一种现实存在”,强调文学世界与现实经验世界的疏离,“意味着对该领域的一种先验性肯定,而无视艺术作品的内容会是多么的‘悲惨’”。③
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文化研究,促使中国文论发生分化。主要在于文学存在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物质飞速发展,带来的不是精神的富足,而是社会问题的层出不穷,精神危机在消费时代成为潮流,一种文化救赎或新启蒙思路的产生势在必然,文学是这一思路发展的最好的突破口。文学研究意欲突破原有思路与文化研究结合在一起。尽管中国式的文化研究不具有西方文化研究所具有的强烈政治批判意识,不构成某种否定性,以至于被称作无政治指向性,④但由于其本身的政治胎记仍然导致了文学研究的泛化,文学内部研究一时失宠,文学消亡论成为普遍的理论认同。在此情形下,对文学理论的本体认识也逐渐发生了动摇,导致了关于文学理论边界的激烈讨论。结果,文学与政治关系因文化研究的第三者插足而再度出现了文学的再政治化论述,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又在理论上被重新提出。不能说文化研究对于文论的介入就已经处理好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就已经提出了更加清晰的理论命题,但促使人们重新思考这个问题,却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研究的新思路。
其实,我们不应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建立在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思维之上,简单地将文学与政治关系或定义为文学依附于政治,或定义为文学独立于政治,或以多元论取消两者辩证结合的可能性。因此,超越形而上学的二元对立思维,用一种融洽彼此的具有阐释张力的观点与思维来重新界定文艺与政治的全面、合适、辩证的关系,就显得尤为必要了。
亚里士多德说:人在本性上是政治动物。这个说法揭橥出政治乃是人的本质属性之一,人通过政治来实现自身建构,人在政治中展开,并在政治中丰富;政治也因人而成其为政治,离开人的存在,政治也不存在了。因此,无论是理念层面的政治,还是具体权力制度运行的政治,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人而存在的,为人的价值实现而运转。
具体说来,政治为人类规划并提供某种美好生活的未来计划与理念,这往往建立在对现实政治生活的批判否定之上,⑤并通过构想形成一套理想的政治哲学,以寄寓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渴盼。这里的中心问题是以“追问最好的政治制度、正确的生活、公正的统治、威信、知识和权利的必要影响”来解决“人的天性、人在神与兽之间的位置、人类精神及灵魂的能力,以及人的身体的欲求”等问题,⑥不难看出,政治哲学的最终目的乃是对人类生活进行美好的设计与想象,它以人的存在为根本出发点,对人类存在秩序进行想象性的探索。沃格林说:“就主题而言,政治科学并不玄妙,它离日常生活并不遥远,所关注的是人人都会问的那些事情的真理。什么是幸福?人怎样生活才幸福?什么是美德?什么是正义?”⑦当然,美好生活的想象往往是在理念政治(政治哲学)的层面上获得充分体现的,虽然在具体的政治制度实践中也存在着对于美好生活的承诺,但这种承诺常常不能全部实现。由此来看,事实上,政治是人的一种必要的生活方式。着眼于现实政治秩序的变革,有利于完善我们的实际生活。但对具有乌托邦性质的政治理念的想象,对我们仍然具有吸引力,它能为现实政治的革新提供参照与引导,而它本身所代表的改变、不确定、激情和充满美好诗意的生活理念,虽然无法完全实现,但坚守它,却是人类生存下去的理由。
作为“人学”的文学,无疑也是关乎人的存在的叙事,是对人的情感、心理、日常生活等的审美关注,它通过叙事想象,使得人类可以超越现实的生存秩序,在想象的文本中构造美好生活的图景。正如钱谷融所说:“一切艺术,当然也包括文学在内,它的最基本的推动力,就是改善人生、把人类生活提高到至善至美的境界的那种热切的向往和崇高的理想”。⑧也如周作人所说:“个人以人类之一的资格,用艺术的方法表现个人的感情,代表人类的意志,有影响于人间生活幸福的文学”。⑨所以,文学与政治的起点和最终归属,都是以人为本的,在为人类谋求(想象)某种美好生活的层面上,两者殊途同归,一言以蔽之,都是为了人类更好地活着。
因此,文学和政治之间在想象一种美好生活的层面上关联起来了,这个层面是两者产生融合的根本处与起点处。这种想象可体现为政治自身关于一种社会生活理念的想象、文学对这一社会生活理念的想象、文学对政治的想象、政治对文学的想象、文学想像与政治想像的整合与冲突等主要方面。⑩必须指出,这样因想象而构成的关联性,是一个相互勾连、相互缘起、相互影响的整体。文学想象政治时可以是没有逻辑和没有概念指引的,它根基于现实并超越这一现实,以审美的方式建构起一个形象化的世界。但对于任何一种政治蓝图的政治想象,必然是历史逻辑的延伸和历史概念变形的体现。但若以价值论视之,二者同时指向一种美好生活则是相同的。若以功能论观之,两者具有的想象性在否定现实的同时往往具有改造现实的作用,尤其在革命战争的时代,(11)这也是它们的相似之处,只不过两者的具体实施过程和最终效果有所不同罢了。
首先,文学和政治共同指向一种好的生活的想象具有一定的否定性,这是对现实政治秩序或日常生活的不满。孔子提出的“克己复礼”、“大道为公”的“大同”社会想象,是对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的现实不满和对未来社会图景的重新设计。(12)康有为在《大同书》中说:“总诸苦之根源,皆因九界”,于是提出“破九界”的大同社会构想,(13)这是对彼时中国传统政治制度混乱状态的一种价值重估。至于陶渊明的桃花源,则是对置身的社会政治现实的彻底否定,于是便想象出另一种日常生活模式,传达出诗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郁达夫说:“古今来这些艺术家所以要建设这无何有之乡,追寻那梦的青花的原因,究竟在什么地方呢?约而言之,不外乎他们的满腔郁愤,无处发泄,只好把对现实怀着的不满的心思,和对社会感得的热烈的反抗,都描写在纸上;一则在生前可以消遣他们的无聊的岁月,二则在死后可以使后起者依了他们的计划去实行。”(14)因此,在想象一种好的生活时,文学的想象和政治的想象,都不可避免地具有某种否定现实的倾向。
其次,文学与政治在想象一种好的生活时具有超越性。这种想象具有超出现实政治秩序和日常生活叙事的功能,它超越一时一事、一己一国,不限制于现实的琐碎与细节,它是对现实的超越也是对现实的补充,亦是对现实的批判,是用想象的方式试图为人类在现实生活之外设计种种希望的幻景。这种超越性体现为一种精神追求,是主体对未来更好的存在状态的意识趋向。就像柏拉图为人类构建的理想国一样,他超越现实,以一种想象性的范式建立起最好城邦的典范,尽管这个美好典范的适用性不强,但为超越现实生活,追寻美好生活或快乐生活提供了一个可供想象的环境。(15)马尔库塞在论及文学时说:“伟大艺术中的‘乌托邦’从来不是现实原则的简单否定,而是它的超越的持存,在这持存中,过去和现在都把它们的影子投射到‘满足’之中”。(16)文学与政治的想象也具有这样的“持存”性质。主体超越现实的意向活动在这种超越的环境里得以展开,而超越本身创造的图景,成为人类向往与追求的图景以发挥他们的生命热情,从而在这种超越性的图景中流连忘返。
其三,文学和政治想象出来的某种社会生活样式具有不可完成性,只能趋近,却无法实现。无论是孔子的“大道为公”、康有为的破“九界”,还是诗人们的桃源梦,都不可能付诸实施,但在构建现实的政治蓝图时却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17)也可能会成为群体的实际政治目标。虽然经由一次次社会变革,“不可能”的生活构想向“可能”的现实转变,这“可能”的现实却远不令人满意,仿佛离“不可能的好生活”仍然距离遥远。但这种“不可能的好生活”仍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所有的现实可能性大都是从这种想象中的不可能出发的。一是导向对往昔时代的怀念,通过对过去生活的想象来解构现实的生活秩序。如孔子的“克己复礼”,陶渊明的桃花源,杜甫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都是如此。一是指向未来,通过预设一种生活场景达到对现实生活的反动,进而否定现实生活秩序的合法性。如康有为的“大同”设想和《尚书》里的“百姓昭明”、“协和万邦”的构想就是例证。(18)这两个方向的想象模式,总的说来意在希望在现实的政治秩序之外,构造另外一种社会生活图景,实现合理的生存。不过,无论是回顾往昔,还是指向未来,其创设的不可能的生活图景一旦“可能”,想象力便告结束,人类生活达到终点,那就停滞不前了。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
文学想象和政治理念想象的最终旨趣是以想象一种好的生活为本质归宿的。一方面文学叙事的想象是在寻找一种好的生活景象,无论它是以反面的批判性想象方式出现的还是以正面的叙事形式出现的;另一方面,政治在理念上的构想,也是在想象一种比现实更为完善的政治秩序。虽然两者在想象力上存在着强弱之分,但两者同样具有想象性是不容置疑的,这为我们探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提供了本体论意义上的考察视点,有助于我们在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纷繁复杂中建立论述的逻辑基点与评价标准。
循着这个思路,我们认为落实到具体的政治生活和文学创作中,两者同样以一种相互想象的关系而存在,在对对方的想象中看到自己的存在,在对对方的想象中彼此生成自己的存在格局。在日常生活中,两者也必须以这样一种相互想象、相互参证的态度来反照自身,进而生成自身、完善自身,如果它们的关系是相互拒斥的或一方依附于另一方,那么就不正常了。因此,两者在相互想象中生成的关系模式,是文学与政治关系回归常态的体现。
我们先来看文学是如何影响政治的具体运行的。通常的观点总认为文学对政治起着消极的解构作用,是政治的威胁,柏拉图构建“理想国”时驱逐诗人,就出于这种政治目的。略萨也说过:“虚构小说是对任何政权的永久腐蚀剂,文学永远是一种阴谋活动。”(19)或者认为两者根本就老死不相往来。事实上,文学对政治建构的作用是不容小觑的,解构不过是二者关系之一个层面而已,即便解构,这在本质上也是为了更好的建设。因此,政治必须意识到文学对其的积极影响,伊格尔顿就认为“文学的‘经验’”有利于“意识形态事业”,(20)“诗必须成为对现实矛盾的一种意识形态解决方式”,(21)那么,政治对文学产生想象应从哪些方面开始呢?
文学文本为政治提供了想象的依据,经典文学文本往往成为政治规划的蓝本,也即是文学的叙事影响着政治“成规”设定。一些在今天看来是文学作品的,可能在中国古代就是政治制度实施的纲领,体现了具体的政治主张。如在《宋史·赵普传》中就流传着“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以今天的标准很难界定《论语》的学科归属,可以将之视为哲学或政治学著作,在中国古代将之当作制定政治准则的参考(甚至蓝本)本是事实,也可以说它是属于文学的,我们惯常将它作为文学作品来读,这时候,它所具有的文学想象性可能是其产生巨大的政治想象与阐释张力的原因所在。其他如大臣的上书或讽谏文字往往就极具文学性,却又极具政治性,《古文观止》中的《宫之奇谏假道》、《出师表》、《陈情表》、《谏太宗十思疏》、《为徐敬业传檄天下文》等文章,都是以充满着文学想象的方式来设计政治的版图的,即便放到今天,也同样具有政治的参照意义,可是今天我们只将之作为文学作品来读了,无形中为建构当下政治生活失去了一个很好的资源。尤其是那些具有乌托邦性质的文学作品,其建构的想象性社会存在秩序,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建构现实政治规则的想象性资源之一。
文学作品中所隐含的时代情绪往往成为改变政治运行的风向标。民众往往以文学的方式直接或曲折地表达自己对社会现实的看法,尤其当政治压抑成为一种流行的政治运作手段时,民众的声音便藏匿在文学想象的海洋里,这样的声音其实就是政治实施效果的隐喻。这种非理性的情感表达在塑造意识形态的版图时意义重大。伊格尔顿认为,英国文学的兴起恰恰暗合了统治阶级的需要,到维多利亚时代,宗教作为一种无限强大的意识形态已经不再能赢得“群众的感情和思想”,因为“宗教是一种极其有效的意识形态控制方式”,“它是情绪的和经验的,因而能使自己和人类主体的最深处的种种无意识之根缠结在一起”,“它提供一种极好的社会‘黏合剂’”,同时,它“也是一种安抚力量,它培养驯顺、自我牺牲和沉思的内心生活”,它的衰落自然让统治阶级惊慌不已。然而,正如伊格尔顿指出的那样,“幸运的是,另一种极为相似的话语就近在手边:英国文学”。“当宗教逐渐停止提供可使一个动荡的阶级社会借以融为一体的社会‘黏合剂’、感情价值和基本神话的时候,‘英国文学’被构成为一个学科,已从维多利亚时代起继续承担这一意识形态任务”。也就是说,英国文学的兴起,一方面包裹着强烈的意识形态的因素,另一方面,现实政治的运作又不能无视这一文学情感的表达,于是便顺水推舟,将之纳为政治版图中的一员,这样一种吸纳与其说是政治对文学的避让,毋宁说是政治对文学的利用,究其根本乃是文学的情感走向影响了政治策划的走向。因为,“文学主要依靠情感和经验发挥作用,因而它非常宜于完成宗教留下的意识形态的任务”。(22)所以,统治阶级借着文学的情感走向而重新想象自己的制度路线时,一方面认识到,“审美是每一个社会关系的根源,是人类得以结合的源泉”,(23)因此,对社会的统一性而言,“只凭借理性是不够的,必须用爱和感情将之激活,它才有可能成为调控社会的力量”;(24)另一方面,政治“迎合”文学的情感表达时,也利用了这一情感表达,实质上是将“社会权力更深插入被征服者的身体中,这是一种极为有效的政治霸权模式”,被霍克海默称为“内化的压抑”。(25)但在现实的政治语境里,文学的情感表达往往是与政治不兼容的,这不是说文学本质上的“反动性”使之有意与政治疏远,有时却是统治集团将文学的情感表达视为异端,有意把它排除在政治视野之外,并从消极的立场上认为它是不利于政治统治的,而这种认识恰恰是没有真正看到文学的情感表达之于意识形态建构的重要作用,只一味地夸大了彼此的不相协调的一面。
事实是,文学作品往往代表着人们对政治文明的真诚召唤,是特定政治历史处境中人的情感的真实表现,在这种表现里藏匿着大众的愿望、理想、无遮掩的爱恨与生存的悲苦疼痛,这些情感音符通过文学作品表达出来,隐含着大众群体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因此,这种召唤是可以为现实政治共同体的完善提供参照的,政治不必对文学的情感召唤不屑一顾,以至不可容忍,而应该积极主动地面对文学中的各种情绪,并以之作为政治策划的参照资源之一,因为“在各门艺术与科学中,只有文学在内容和方法上不受任何限制。……文学的虚构维度对战略家来说不可或缺,因为他们在必须作出决定的时候不可能知道所有的事实、因素和某种形势的潜在结果”,所以“伟大的文学作品的价值在于,它们尽管不忽视理性思索,却向留意的读者传达国家内部事物或国与国之间事物的未充分发展的方面”,(26)这些方面无疑可作为政治规划的资源之一的。但如果政治不重视或排斥文学的情感作用,以至于达到“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地步,那么,这个时代精神气象也必定是消极颓废的、灰暗浮躁的和污浊憋闷的。伊格尔顿说:“一个已经停止重视文学的社会是一个致命地关闭在曾经创造和维持了人类文明中的最佳成分的那些冲动之外的社会”。(27)这是认为文学“是一个深陷在意识形态危机中的社会的最终指望,它以抚慰代替批评,以情感代替分析,以维持代替颠覆。如此一来,诗的含义与其说是一种具体的文学实践,不如说是一般意识形态的运作模式”。(28)因此,政治以积极的姿态对文学的情感叙事展开合理的想象,并将这一想象落实在具体的政治实施过程中,方为明智之举。
再来看文学对现实政治的想象。虽然在实际的文学生活中,文学可以不理会政治,可以不对之产生想象,但这种远离政治的文学想象必须是自然而然的文学行为,而非主体故意为之。因为,故意的远离事实上是没有远离,反映出的恰恰是文学和政治紧张关系的存在事实,而这一远离使得文学与政治之间的联系变得简单而又漫漶不清。我们认为,一方面,文学可以不想象政治;另一方面,文学可以或者应该想象政治。区分是否将政治作为文学想象的资源的立足点应在于文学自身是否需要这一资源,这一需要与否的前提和主体的情感表达需要是紧密关联的,和文学的审美价值本身须臾不离。当创作主体的情感表达需要政治内容的支撑时,便可以在文学创作中想象政治;当情感表达不需要政治内容的渗入时,文学和政治也可以暂时“分手”。这样一种关系状态的形成是立足于主体的审美情感表达而顺其自然生成的,而非反常态的人为的设计与规定。
事实上,现实政治对丰富文学想象起着积极的作用。韦勒克认为,文学是一种社会性的实践,这种实践实际上取决于或依赖于社会背景、社会变革和发展等方面的因素,因为人类各种活动范围都是相互联系的。(29)鉴于这样一种联系的存在,文学与传统观念、生活习俗的联系便是存在着的,文学与政治的联系不能轻易否决。政治成为文学想象的资源本在情理之中,政治资源可以是正在运行中的现实政治效果,也可以是已然的政治事件。托洛茨基指出,认为艺术能“绕过当今时代的各种巨变,这是可笑的、荒谬的、愚蠢至极的”,“艺术直接或间接地反映那些制造或体验这些事件的人们的生活。如果大自然、爱情、友谊等与时代的社会精神没有关联,那么抒情诗早就不存在了”。(30)文学离不开政治,只要创作者生活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其创作就或多或少地带有时代烙印。陈平原认为文学与政治有关联,有时候是出于文学自身的需要,政治毕竟是人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发生在政治领域的‘革命’,更是充满激情、想像力与冒险精神。对于文学家来说,人生百态,没有比‘革命’更富有刺激性与诱惑力的了。”进一步来看,“如果能将社会责任、启蒙立场、文学想像,以及语言、细节、风格等,很好地协调,未必不能成就一番事业。也就是说,假如有自己的思考与立场,拒绝充当政治家的‘传声筒’,小说家的积极介入现实政治,直面时代以及人生的重大话题,并不是坏事。”(31)文学积极介入政治倘以情感表达之需为前提,这种介入未尝不值得提倡。刻意地将文学与政治的鸿沟拉大,不食人间烟火的意图使之有失却厚重、丰富的可能,因此一切表达了人类美好生活愿望的政治,都是文学可能表现的对象,也是能够表现的对象。当然,即便是不那么追求美好生活的某种现实政治秩序,也同样是可以作为文学想象的对象的,而这种想象更具有批判的张力。
总之,文学可以成为政治想象的资源之一,文学也对政治产生想象,在相互想象的召唤中形成相互生成、相互缘起的关系。政治借助对文学表达的想象来完善其制度设计,文学通过对理念政治或现实政治的想象来丰富自身,进而生成一片绚烂多彩的审美天地。所以,我们必须杜绝政治对文学一贯的疾言厉色之态,事实上政治完全不必对文学如此痛恨和绝望;至于文学,也须正视其与现实政治血脉相通的存在事实,不以语涉世俗而产生紧张兮兮的耻辱感,倘若此,文学便也可以充满血气、大大方方地高歌猛进了。
注释:
①刘锋杰:《从“从属论”到“想象论”》,《文艺争鸣》2007年第5期。
②埃蒂安纳·巴利巴尔、皮埃尔·马歇雷:《论作为一种观念形式的文学》,出自[英]弗朗西斯·马尔赫恩编:《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刘象愚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8—59页。
③[德]阿多诺:《美学理论》,王柯平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
④旷新年:《文化研究这件“吊带衫”》,《天涯》2003年第1期。
⑤[美]唐纳德·坦嫩鲍姆、戴维·舒尔茨:《观念的发明——西方政治哲学导论》,叶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9页。
⑥迈尔:《为何是施特劳斯?》,见[美]施特劳斯等《回归古典政治哲学——施特劳斯通信集》,朱雁冰、何鸿藻译,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第vii页。
⑦[美]沃林格:《没有约束的现代性》,张新樟、刘景联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2页。
⑧钱谷融:《当代文艺问题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7、89页。
⑨周作人:《新文学的要求》,《艺术与生活》,岳麓书社1989年版,第23页。
⑩参见魏朝勇《民国时期文学的政治想象》,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第24页。
(11)参见马尔库塞《新感性》,选自刘小枫选编的《德语美学文选》(下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46页。
(12)[美]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翁贺凯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页。
(13)康有为:《大同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52页。
(14)郁达夫:《文学上的阶级斗争》,《郁达夫全集》第10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9页。
(15)刘小枫主编:《信仰与政治哲学——施特劳斯与沃格林通信集(1934-1964)》,谢华育、张新樟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41页。
(16)马尔库塞:《审美之维》,李小兵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79页。
(17)参见拉塞尔·雅各比《乌托邦之死》,姚建彬译,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第231页。
(18)《尚书·尧典》:“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
(19)[秘鲁]巴尔加斯·略萨:《谎言中的真实》,赵德明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83页。
(20)(22)(27)[英]特里·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5、21—25、31页。
(21)(28)[英]特里·伊格尔顿:《历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马海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9页。
(23)(24)(25)Terry Eagleton,The Ideology of the Aesthetic,Australia:Blackwell Publishing,1990,p.24,p.26,p.28.
(26)Charles Hill,Novel Ideas,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10/08/13/novel_ideas.
(29)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01—115页。
(30)[俄]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刘文飞等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页。
(31)陈平原:《怀念“小说的世纪”——〈新小说〉百年祭》,《书城》2003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