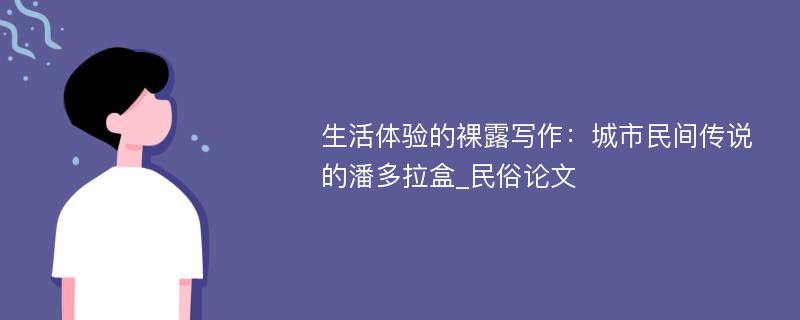
生命经验的裸写:都市民俗志的潘多拉盒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潘多拉论文,民俗论文,盒子论文,生命论文,经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注民俗的人免不了有几分乡土情结,总想着从别人的文字里找到似曾相识的山水人情。翻开主要是抄录方志、乡土志的《中华全国风俗志》,却多少有点儿尴尬。其中,抄录的《曲阜县志》有言:“韩宣子谓周礼尽在鲁,汉高祖谓守礼仪之国。今时代虽远,而冠婚丧葬,一禀《曲礼》。古道犁然,宛乎周情孔思焉。”①在纷繁的舆论界,天主堂和孔庙俨然比肩而立的这座东方圣城,周情孔思余味真的悠长?安歇这些周情孔思的古城墙呢?城门口拿把蒲扇,打鼾、品茗、话古的老头儿哪去了?那些晚上张牙舞爪的古松古柏又放哪儿了?
以个人喜好和今天的事实来衡量这本记录过去、功德无量的类书很不厚道。问题是,今天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民俗志?能安抚无论是学者还是读者乡土情结的民俗志到底是什么样的?近些年来,具有现代学科问题意识和作为一种研究范式的民俗志的理论探讨和实践成果颇丰。②尝试继承方志、风俗志和民族志传统的新型民俗志,又多少被这些传统不同程度地割裂,或偏向某一类。在记述策略上,即将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大型丛书“中国节日志”就欲进一步整合志书传统和民族志传统之间的裂缝。但是,具有可读性、资料性和理性认知的“裸写”和“如何裸写”仍然是关注现实的新型民俗志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
没有冗长沉闷的理论堆砌,铺开自己真挚的乡情“裸写”是《乡村医生·父亲:乡村医患关系的变迁(1985—2010)》(后文简称《乡》)这篇优秀硕士学位论文给我们的一个答案。回到自己熟悉的生活环境,观察、反思和阐释,加上质朴、深情的语言,这似乎见惯不惊,没有什么特别,但却打开了一个关于民俗志的“潘多拉盒子”:面对隐而不言或欲说还休的种种尴尬,民俗学者该何从选择?如果关注现代性的都市民俗学是频频回首的乡土民俗学发展的应有之路③,那么这个民俗志的潘多拉盒子也就是都市民俗志的潘多拉盒子。
一、裸写:“把理论思考化于无形”?
人类学小说《金翼》对《乡》的影响,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明晰可见,甚至《乡》也可以视为一部小说。组织《乡》的是主题不同又以时间连贯的八个篇章。没有花哨或柔情的语言,只是质朴无华地叙写记忆中的日常琐事,作者生命经验中那种深沉的乡土情感流贯始终。乍一看,这是《金翼》的高徒!就连作者自己也申明,“把理论思考化于无形,余虽不能至,心向往之。”④这一基本定位使得《乡》有别于当下学院论文就一点经验事实“深描”成篇,然后穿靴戴帽,却又常常削足适履甚至张冠李戴的理论与事实不合的“八股”文风。“裸写”使得看过《乡》的人都为之叫好。
《金翼》和《乡》之间最大的区别,也正在于“把理论思考化于无形”的裸写。读过《金翼》的人,脑子里难免会被烙上社会均衡论的印子,这也是林耀华在书中反复用对人物命运的评论言明,并不时以设问句引导,又在尾章谆谆阐释和论述的。⑤换言之,当年社会学界时髦的社会均衡论不仅是《金翼》形而上的指导思想,更是其骨架。这样的骨架十分规整,把情节都归纳其中,人物也纷纷扮演着人类学中的角色,或典型或平凡,但一切都仿佛发生在一个舞台上,还是“一个灰砖飞檐下的四方古戏台”。遗憾的是,这个古戏台因缺乏戏剧性的冲突和张力,略显沉闷、老气,似乎一切都自然而然,顺理成章。
与之不同,《乡》更像是“一本书边儿泛黄了的简装书”,朴实无华,自带一种光晕。“人情与赊欠”、“放下锄头就看病”、“病人兼客人”这样简洁立体的篇题,交错讲述着一个社会基层中寻常又典型的作为乡村医生的父亲起起伏伏的生命经验。它跨越了近三十年,更跨越了京鄂两地的城乡阻隔和父女两代的心理距离。随着这本带了年份的简装书慢慢翻开,渔村、父亲、父亲出诊时的路、“我”与弟弟上山采药的路、人与人之间那种不必言明却可通感也渐渐褪色的乡情、医患情,都浑然一体全景式地呈现在读者眼前。
一篇文章、一本书想做什么和做到了什么的差距,全在读者的感觉。借“灰砖飞檐下的四方古戏台”和“书边儿泛黄了的简装书”这组阅读感受,我们要说明:《金翼》的“理论思考”观点鲜明,框架规整,像个军警一样规矩着全部的情节,“无形”无非是小说这一体裁和平实语言合谋的假象。当均衡论不仅内化在情节中,更在论述和篇末反复提点,怎能说它“无形”呢?《金翼》于理论,只是穿脱马甲的区别。《乡》中娓娓道来的乡村医生的“越轨”、医患关系的变迁、规章制度的尴尬等都不乏精准的分析与深入的思考,但其扑面而来的质朴乡情衍生的情感上压倒性的阅读共鸣使“理论”的延伸和反思化于“无形”。医患关系的变迁和乡村医疗保障制度的名实分离,无论在新闻界还是学术界都已不是新鲜事,可在个体生命经验的情感叙述中,《乡》使之焕发出了本雅明所追思的也是久违了的“光晕”⑥。
当然,拿一篇硕士论文和大名鼎鼎的《金翼》相比有“小题大做”的嫌疑。但从重叙写、纪实的学术写作而言,比较二者还是有必要的。《金翼》以理论构建为要旨,事实被结构成一部作为表达工具的小说。《乡》是个人生命史,回忆和书写中弥漫着生命经验和浓郁乡情。⑦如此,我们所需的民俗志,是要规整出一个观点,还是高水平地抒一次情?
二、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阐释学还是资料学?
不可否认,中国民俗学长期是作为资料学因而也是工具而存在的⑧,至今也未能摆脱这一窘境。作为民族志的孪生兄弟,钟敬文先生在其系列著述中强调的都是具有现代学科意识的民俗志的“资料性”。⑨对这些以“科学”为名的记述作品,保罗·拉比诺(Paul Rabinow)提供了另一种可能:田野过程也可以呈上台面。1973年,拉比诺出版了《象征支配》,1977年出版了《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不管读者的反应是多么震惊和不悦,拉比诺解决了自己对于其哲学导师理查德·麦基翁(Richard McKeon)的反问:“思想还可能是别的什么吗?”⑩至少,民俗志还可能是对过程的阐释,是一次对自我的绕道反思。
因为兴趣在于说清事实的作者无意追问民俗志“还可能是别的什么吗”这种问题,《写文化》与《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等反思民族志的经典著作在《乡》的参考文献中是缺席的。《写文化》给民俗学最重要的一击是,民族/俗志本身的魅力已经被迫让位于女性主义、权力等话语对它的种种解剖,甚至沦为这些语词的注释。相较资料学而言,从遥远的摩洛哥开始,《写文化》所代表的对民族志的反思已经往另一个可能的方向走了很远,且态度决绝:“无论如何,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在原有的民族与地方之调查领域中,民族志不会再回到档案功能。”(11)《写文化》是一本颇狠的书,连令人啧啧的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的“阐释”都被揪着质问成了“阐释癖好”,而“谁告诉格尔茨了?——整个民族怎么可能仅仅拥有一个主体性?”(12)的质问更是掷地有声!
既然回不去了,还要接受劈头盖脸的质问,最终连远赴重洋辛苦筹建起来的权威性都被肢解了,民族志还有别的出路吗?有,如果它本身就是一场实验!《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做了一次尝试——虽然是马后炮式的。毕竟它首先是一次田野,其次才是一次反思,但这已经足够让当时学界震怒。遥远的摩洛哥化解了《金翼》和《乡》留下的“理智与情感”式的取舍,因为它直接跳出了必须要写田野事实的圈子。
在《乡》的“前言”中,有在一定程度上“填补空白”的自白。这是针对叙写对象当代乡村的医患关系而言,并非针对将理论化为无形的“裸写”。就广义的民俗志,民间有心有识之士对某一民俗事象的记述往往比学院派作品更形象自在。当年,在初次看到奉宽的《妙峰山琐记》时,一度因调查、编著了《妙峰山》而自豪的顾颉刚深深地被其材料的精密、确实震惊,自叹其《妙峰山》“质料的单薄”,仅“小巫”而已。(13)这种状况似乎延续至今。在《旧京风情》“自序”中,侯长春明言,民俗史是由各个时期千万“好事之人”汇集、整理而成的形式各异的“文”与“象”两类资料,《旧京风情》也仅仅是为北京民俗文化做一点“拾遗补缺”的事儿。(14)无论是学界还是民间,文人雅士、闲云野鹤大抵延续着旁征博引、反复印证诠释的经学传统,这不稀奇。令人感慨的是,《写文化》、《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这套汉译人类学名著丛书的“总序”依然锁定了偏向资料学的意义:“磨砺我们找‘事’,说‘事’的本事”。或许,就在手边的摩洛哥离中国民俗学的传统和现在,都还遥远。
在我们认同的好的民俗志中,充沛的情感、质朴的叙事、丰富的事实和深入的反思是显性的。因为我们对理论已经厌倦。厌倦的原因是什么呢?理论无罪,理论套用的过盛有罪。平庸无罪,阐释不足制造的平庸有罪。如果“不言自明的事实和无用的真相”、“深层意义上的他者”离我们的学术传统太远也太过颠覆,那在实验民俗志和资料学民俗志之间,有没有过渡性的中间路线?更立体的阐释不仅是一种方法,也是一种切实的态度。把民俗志所要面对的事实,从资料的层面上往上拉,使之更有阐释的纵深空间。这也即为何在《空间、自我与社会》中,作者无意澄清“天桥的把式—光说不练”正确与否,而是关心今天声称自己是天桥艺人传人的人“为什么对这句传衍近百年的俗语反感”(15)。同样,相对于《乡》中对“村将不村”的忧心忡忡和“牧人者慎之”的义愤下连环式的发问,下述诘问显然更沉得住气:“我们该怎样去理解共产党的党政体制以及它所连带的无可否认的弊端?怎样去进一步发挥它的积极性,而又同时改进它的众多弱点?”(16)情感可以煽动人,可以构成一个强大的气团,却无法磨成一根尖锐的针。这跟伤痕文学永远不如后现代小说来得尖锐一样。或许“情感”和“理智”真的只能二选一,正如黄宗智评价乡村建设时,少了些忧患,多了点讽刺。他鲜明地意识到“一个带有讽刺性的事实”:中国共产党做到了20世纪前半叶晏阳初和梁漱溟未竟的事业,但改革开放期间却又再现了“乡村建设”的号角。(17)不可否认,同样是讨论乡村建设,讽刺性事实和情感性事实之纵深度不可同日而语。
无论是《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空间、自我与社会》还是《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尽管可以划归到不同的学科名下,但其阐释的深度和立场却有一致性。它们合力证明,在传统全景式书写之外,还存在另一种可能。
三、群众的眼睛,雪亮
在谈及民族志描述中对颠覆因素的掩饰时,被引用得十分坦荡的赫尔墨斯的传说仿佛要言明民族志的真相,但这个传说本身却是说不明白的:“当赫尔墨斯承诺绝不说谎,也不承诺说出整个真相时,宙斯表示理解。”(18)在民俗志的圈子,是不是也有些得到“理解”而未经言明的“真相”?
群众的眼睛,雪亮。这种雪亮绝不只体现在对央视大楼“大裤衩”、国家大剧院“鸟蛋”之类的换喻调侃上。在面对云游客、克非等非学院派人记述旧北京天桥的精深资料时,当下研究者明显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19)这就有如下问题:如果如侯长春一样的“好事之人”和有识之士已经完成了文象俱佳的民俗志写作,“文学性”、“声情并茂”并标榜客观、科学、理性的访谈是否还有必要?
在情感上和高明程度上,不少学界作品大概难以与邓海帆的《陋巷人物志》媲美。这本将工笔画、旧体诗、回忆小品熔融一体的书画志,完全撑得起于是之“序”中“生动鲜明,呼之欲出”的评价。作者写粮店小学徒的“打油诗”云:“幽巷角,槐荫下。送粮去,得空暇。思昏昏,睡沉沉。梦甜甜,笑吟吟,口水流,鞋乱丢。粮袋破,鸡儿乐。管他娘,睡一觉。”紧随其后是作者的回忆,“我亲眼见到,在背静的胡同里,那个小学徒送粮食到主顾家去,在粮袋上竟睡着了。我很替他担心,也很同情他的遭遇。”(20)在这本“稍得假日,偶涂部分陋巷人物,缀以芜词”的不言民俗志的民俗志中,学者们孜孜追求的“事”随处可见。
对于那些岌岌可危或者已经消逝的民俗,曾经和它们一起生活并共建生命经验的亲历者是最好的发声体。他们心怀“情感”就足矣。这是至今包括《荆楚岁时记》、《东京梦华录》、《燕京乡土记》、《忆往说趣》这些古今凭吊、感怀忆旧之作的魅力所在。从这个角度而言,《乡》可以做得更彻底:完全抛却“民俗学者”的立场,单纯作为其中一员,将更多的乡言乡语七嘴八舌地融入其中。当然无论是从现实角度,还是就是否回到“单纯作为其中一员”的立场而言,都很难。但是,为什么回不去?在回去与回不去之间,这次田野是如何进行的?对作者自身的认知又有何影响?是否也存在“深层意义上的他者”?个人记忆是以什么角色,在多大程度上参与到这次民俗志写作当中?对各方资料,尤其面对争议涉及“谁做得更厚道”之类的道义问题的资料,又是如何取舍的?(21)这项工作即使作者本人不适宜做,也值得读者思考。
“群众”给学者带来的威胁,在都市民俗学方面更明显。都市里,白纸可以写作,网络可以写作,手机可以连载,微博可以直播,课桌、过道、厕门、电线杆、过街天桥、广告橱窗、咖啡屋、茶馆,处处都可涂鸦。在《讲故事的人》中,本雅明对前工业社会古典经验(Erfahrung)在现代社会的衰落充满忧患。(22)实则相反,经验(绝不仅仅是本雅明所强调的从零开始的“经历Erleben”)在都市生活中随处可见,且人人都可以表达、宣泄。如果只是停留在资料学的层面,学者恐怕永远落后于群众的高明。《背包十年——我的职业是旅行》和《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等著作更是让这种感觉步步逼近。都市生活虽然多元,但很难逃脱所谓现代化的基本模式。一本都市青年旅行的自传,已经不需要像介绍一把油纸伞的制造过程一样,细腻得面面俱到,因为现代生活的很多方面都不言自明。它的写作方式也应该立体、精炼、灵活和不拘一格。以这样一个开放的定义来看,自传体小说和旅行志都完成了既定任务。如此,都市民俗志或许是一个转机,逼着我们走出资料学的困境。
妹尾河童以他精准的速写和率性的文字,描绘、记述下他眼中的印度。(23)作为异国的晚辈,无业青年小鹏在不知不觉中承继了妹尾河童的“游记”,他且歌且行的十年环球旅行记录夹杂着地方风物和个人对时间、生命、生活与爱情的体悟。没钱没资本的穷游经历,从杂志编辑到王府井乞讨的随性,他没有太多“诉苦”,没有对窘境的遮掩。(24)尽管无心插柳,这样一本和民俗学八竿子打不着的书却很难拒绝在“都市民俗志”书架之外。与其去跟随书写,民俗学者不如讨论这样一本游记从单纯的个人博客赢得大众关注,到被结集出版的过程,以及这一过程反应出的共建乌托邦的下意识共谋——作为读者的都市青年面对现实和理想的落差,选择在精神上追随小鹏这样的冒进分子,从而建立起一个都市里自在生活的乌托邦。
一部好的都市民俗志,不仅仅是描述都市人何以生活,而是深入他们的精神世界,言说他们的挣扎妥协,和在此心态下衍生出的一系列新兴甚至荒诞瞬间又不会消失的现象。旅行,到底是个安全的概念,但身体的自残、暴露和任性消费就不见得获得宽容了。如果民俗学者不甘于只是分析都市民俗志,不如书写这些看似荒诞有悖道德的都市中不为民俗的“民俗”。像福柯给疯癫以存在的合理性一样,把荒诞的变正常,把正常的变荒诞比传统的把陌生的变熟悉,把熟悉的变陌生更理所应当。
《给未出生孩子的信》的作者不是平民,而是强悍的女记者奥里亚娜·法拉奇(Oriana Fallaci)。再伟大的女人也难免怀孕,她怀孕了,孩子的爸爸逃避不在身边。她并不要求也不想他在身边,甚至在其来探望时,还硬生生将之赶出门外。更荒诞的是,她和她的孩子谈起了一场“恋爱”,还思考孩子是否在篡夺她自由生活和工作的权力。直到在胎儿八个月大的时候,她拒绝休养生息,奔波不停,孩子流产了。(25)法拉奇很聪明地设置了一场道德审判。在审判中,孩子的爸爸,她的父母和朋友都列席。一个女人跟她的孩子抢夺对生活的自主权?女人和孩子的关系在道德伦理之间,究竟该如何说明?面对这个问题,我们大多数时候要么没有意识、能力去说明,要么无暇顾及。对此,法拉奇做了一次很好的尝试。当然,法拉奇没有理由为民俗学做啥贡献,并声称她的写作与思考是民俗学的、现代的、都市的与女人的。
与法拉奇的经典道德拷问不同,台湾邻家女孩弯弯脚踏实地的多。从奶茶店店员到配音员,花店打工妹到周刊记者,她始终在尝试一种新的生活方式。(26)再聪明的访谈者、局外人,也很难再现这种“体验”式的生活。在铁饭碗和不断跳槽于市井各个行当之间,都市生活到底有多少可能性?都市生活的多元具体到个体,又该如何定义?是不同人的多元化还是一个人身上的多重可能性?这些应该都是关注现代性的都市民俗学的领地。归根到底,资料学已穷途末路,都市民俗学要么去深描挖掘更深层的“事实”、“资料”之下的因果关联,要么就以身试法,去做一次实验性的都市民俗志。
如果在情感和高明程度上敌不过,那“真实”总该是个筹码吧?《采访本上的城市》是记者王军继《城记》之后再次对北京城交通和建筑格局变迁的追溯。多次访谈记录和对政府、民间、商业多重力量如何参与其中的梳理,道出了一个连贯的过程:从汽车浩浩荡荡进入城市,大马路热闹地建起,到胡同拆迁,见缝插针的异形建筑,开始支离破碎的城市天际线高高低低,终至失去了平衡。王军谈到作为一个记者,他是“唯以事实为目的,非以事实为手段”(27)。其实,他对真实的处理方式和民俗学者没有本质上的差别。(28)何况,绝对的真实通常只是理想!这种亲缘关系,在都市民俗志如何与“他者”划清界限而彰显自身合法性和独特性上,制造了朦胧的困境。于是,“重塑‘原型’”、“辨识真相”不得不甘居末路,而让位于过程和“异文”。(29)
面对书写权力的下放、网络资讯的欢畅、学科边界的模糊,作为资料学的民俗志失声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解决方式,中国民俗学肇始时期的歌谣运动就已经回答了:发动群众搜集资料,学者的工作是“学术的”与“文艺的”。(30)至于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言语写老百姓的“事儿”,是志在启蒙的知识分子和芸芸众生之间抹不去的距离。青涩时期的韩寒有句话还是可取:潮流就像火车,追是追不上的。豪迈伟岸的夸父逐日,道渴而死,如永远不能将巨石推上山顶的西西弗斯。
四、尴尬的有机知识分子
“民俗专家”的位置是尴尬的,这在学院派与非学院派之间没有差别,非遗专家亦如是。(31)在其志业中,民俗的拥有者民众永远是民俗学者一个心结。下述文字颇有代表性:
居陋巷七十余年,每忆儿时,巷口门前,所见所识之人物,虽时隔多载,音容举止,依然目前。其中多数为劳动人民,奔波街巷,劳苦终日,困窘坎坷,默默终生。儿时天真,深抱同情。鲁迅先生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旨哉斯言。季世细民,苟活终日,实不审何所以争也。但善良淳朴,知耻乐业,提携扶持,关怀互助,邻里闾户,煦煦穆穆。日下俚俗,犹遗古风,何任其泯灭而无传?况时过境迁,行业习尚,多已泯失,不为人知,更不能不记之。蓄此意有年,丙寅溽暑,稍得假日,偶涂部分陋巷人物,缀以芜词,聊遣寂寞,虽遗笑方家,在所不计也。(32)
因民众“愚、弱、穷、私”(33)而“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又因其“善良淳朴,知耻乐业,提携扶持,关怀互助,邻里闾户,煦煦穆穆”而心仪不已。这是多数四顾茫然又感怀伤时的智者一贯取态,只不过是偏执一端或首鼠两端的站位不同。于是,真做起和民众有关的工作来,与顾颉刚首次调查妙峰山一样,非要找点借口(34),“稍得假日,偶涂部分陋巷人物,缀以芜词,聊遣寂寞”,还要给自己壮点儿胆,“虽遗笑方家,在所不计也”。自“士”开始,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取态是明确的,一以贯之的。
对民俗的态度又如何呢?“日下俚俗,犹遗古风,何任其泯灭而无传?况时过境迁,行业习尚,多已泯失,不为人知,更不能不记之。”资料学的立场显然,也张扬了知识分子舍我其谁的使命感、责任感。这种“责任感”,从杜甫的“垂死病中惊坐起”,到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再到于是之所言的“爱国主义”,浸入骨髓,不绝如缕。
传统的儒生、士和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站位意外地诠释着意大利人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有机知识分子”的内涵。(35)在汉译人类学名著丛书的“总序”中,专门知识介入社会的激情溢于言表:“专家作为第三方叙事对于作为大共同体的现代国家在内部维持明智的交往行为是不可缺少的。”同样,陈平原也把中文这个学科立意在介入社会,将之视为一种“积极参与当代思想文化建设的力量”(36)。如同士之于古代中国,专家是现代民族国家制造的一个群体,更是一个“阶层”。这样一个阶层的合法性由国家给予,除传统的“为民正义”之价值观,还不时强调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语言学来写作。其实,这整个链条都是制造出来的,但面目模糊的民众仅仅是环环相扣的链条环中的空穴。
在精英主义和有机知识分子传统的夹击下,与其张扬和民众的感情多么笃厚,不如宽泛一步,摆明平等态度。一个老百姓和一个公务员,无论他们作为“研究对象”,还是“合作者”亦或是“报告人”,他们都是“我”视野中“无差别”的人,怀抱各自的生命经验,从不同层面展演着“人的价值”。民俗学或者更具体的民俗志书写,最终的落脚点还是人的价值——站位只是出发点,情感只是疏通的路径。好的民俗志不在于出发的时候给自己贴了什么标签,而是和其他记录“人的价值”的作品殊途同归。
与张承志心怀天下,又慈悯地直接为弱者鼓与呼的硬汉写作不同(37),虽然在赫塔·米勒(Herta Müller)和法拉奇这些轮廓分明的女人的作品里看不到对受苦人的讲述和弱势群体的道义之言,但后者同样对“人性”、“大众”给出了深刻冷静的表达。2010年,赫塔·米勒的系列作品在中国出版。她期待中国读者通过对西方文学的阅读和体验,丰富自己的当下生活,对人性的省察与对社会现实的感知具有了“另一种技巧”。笔锋一转,她写道:“我宁肯你们把我视为您身旁的一个普通写作者,你们都可能是我诸多书中人物的命运共同体。我们以相似的姿势飞翔,也极可能以相同的姿势坠落。”(38)
每个学术圈子都有自己的视域,深入一种文化或传统亦难免画地为牢,故步自封。或许在民俗志写作上,我们也该探寻“另一种技巧”。至少在都市民俗志的写作中,讲述一只鸟的前世今生已经不能说明相似的飞翔姿势了。纵然是在一个胡同里,五柳先生的胡同和卖包子大婶的胡同,王世襄的蛐蛐、北岛的蛐蛐与当下市井百姓还在玩的蛐蛐,到底还是不同的。不见得非要去深情地牵起卖包子大婶的手,但对人性的省察却可以让我们更加坦然平和地去接纳她。相比今天四处泛滥的情义文化,这种“无情”态度说不定更切中实际。
五、平民的、人道的与自私的
1986年,在庄孔韶前往黄村做田野时,黄村人似乎并不知《金翼》为何物。(39)
这并不奇怪。林耀华写《金翼》时,就摊明了这是一部人类学小说,还是用英文写的,他不指望黄村人去读。但同样的事情到了民俗学,就有点尴尬。我们在写作民俗志时被鼓励用老百姓的语言,要让老百姓也看得懂。事实上,《乡》的命运与昔日《金翼》的命运并没有太多的不同。至今,装订整齐的《乡》安静地摆在图书馆密密麻麻的硕士学位论文中,少有人问津。在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乡》的编号开头是2011。在它之前有2010、2009,一直往前,也会一直往后。
在谈到“平民文学”时,周作人倡导“应以普通的文字,写普遍的思想与事实”“乃是对于他自己的,与共同的人类的命运”。就是以今天的标准,这也像极了民俗学的申明,但同时周作人也明言:“白话也未尝不可雕琢,造成一种部分的修饰的享乐的游戏,那便是虽用白话,也仍然是贵族的文学。”(40)结合中国知识分子葛兰西式的站位和《乡》的束之高阁,在民俗学专业学位论文里的摊煎饼的老大妈、自己也用“迷信”表述自己的香头、在渔村里颠簸的乡村医生和即将到来的被深情书写的更多“小”人物的生命经验,无非是一篇一篇地被有不同倾向的老师品读,然后被行政人员装订摆放在书架上,等待着为数不多的后生们有闲情时来随手一翻。如此,这感情也不必要一定要“浪费”了罢!
周作人不乏聪明的自我放逐与闲置是很自然的事儿。他这个人太自然了,肯说实话。虽然写了平民文学并且研究里巷歌谣,他也说:“我以前是梦想过乌托邦的,但觉得这种生活在满足自己的趣味之外恐怕没有多大的觉世的效力,人道主义的文学也是如此,虽然满足自己的趣味,这便已尽有意思,足为经营这些生活或艺术的理由。现在所爱的乃是在那艺术与生活自身罢了。”(41)中国的知识分子往往要以社会大义为己任,为了躲避非大众即小资的分类学,打着周作人牌子的大多数人又做不了周作人做的事。自己的趣味都没有,更无从谈觉世的效力了。
每个时代的学者都有自己的喜好,诸如“用自然,质朴的语言去描述与分析他们,而让读者自己从中去领会与评价这些人的悲喜”(42)。真正的学者都有自己的性格。朱光潜写后门大街时,说它是“一个怕周旋而又不甘寂寞的人”的良友。(43)拉比诺感慨摩洛哥人始终不明白人为什么要独自散步,所以他才能和穆罕默德坐在无花果树下,聊各自文化,感受深层意义上的他者。在别人的喜好和自己的喜好之间,周作人说的很坦荡,“虽然满足自己的趣味,这便已尽有意思”。所以,不是所有民俗志都要做传统意义上“平民的文学”,而是什么样的人写什么样的民俗志。
在说没有多大的“觉世的效力”时,周作人又添了一句实话“人道主义的文学也是如此”(44)。《乡》完全可以算作人道主义的文学,而且就其作为一篇硕士论文归入档案束之高阁的事实,它也没有多大“觉世的效力”。在中国传统的儒道文化下,我们通常只在道义的框架里面转圈。《乡》能够写得规整丰富,却不能叫做“淋漓尽致”,因为《乡》中父亲的形象始终是正面的,他踩在乡情、医德、个人在国家和时代变迁中的起伏之上,虽是处在弱势群体中勤勤恳恳的小人物,却可以被“大书”。与之相应,母亲的形象是一个贤内助,无论辛苦平顺都甘心照顾家小,还理解父亲行医中种种得失。甚至连“我”和弟弟,也因为父亲是医生,是乡村“公共知识分子”的代表,也在默默坚持上课不迟到。全文中的情感充沛不假,但仔细读来,其实也颇为平淡。这里的平淡不是指内容,而是思维的跨度。思维的跨度通常是超越具象与事实的,但又是真切可感的。例如,福柯的监狱,不但长宽高俱全,有着空间和时间,还是全景敞视主义的。相对而言,《乡》在一团和气的平面上展现的父亲近三十年的人生旅程,是一条没有冲突以及起伏的时间线。
当然,讨论不能忽略“何为人道主义文学”这个基点。法拉奇给那个没有出生孩子的信可以算么?将一颗热土豆视为一张温馨的床可以算么?在中国,这些提问会被视为怪诞,至少是不正常的。我们可以接受《乡》这种温吞的人道主义,却没有足够的包容去接纳新近触碰既定“人道主义”界限的尝试。2008年,徐童的《麦收》以妓女鱼为中心,辐射到她生活圈子——从北京到河北老家——中的各色人等。“真实”、“人道”、“平民”这些概念,反而在这种遭到社会广泛拒斥的纪录片尝试中看得更清。在道学家和人道主义者之间,是“在这里”到“去哪里”或者“去那里”的距离——由问题寻找答案比陈述更重要。如此看来,民俗志不如“自私”一点!奈吉尔·巴利(Nigel Barley)曾说:“事实上,许多人类学家选择重返生活极不舒适。……诸此种种,都让你重新审视自己。或许如此,人类学到头来说终究是个自私的学科。”(45)
圈子里的人怎么说,争论已经过盛。不如看看圈外人如何一语道破访谈和我们所说的“田野”的窘境。十多年前,在“田野”重回学界并被学界如明星般大力抬举和炒作时,张承志有些尖刻却也真实地写道:
一个叫做“调查”的词正在流行。是的,这个词汇已是天经地义的科学术语,无论怎样与文化的主体,即民众,从地位到态度地保持着傲慢的界限。与之孪生的另一个词是“田野”。把人、文化主体视为“田野”,是令人震惊的。……表述者与文化主人的“地位关系”,是一个巨大的命题。
……
我不大信任所谓民俗学或人类学,比如,我总怀疑背负着极为血腥的侵犯原住民的历史的欧美民族学与人类学,究竟有多少深度。它们与人认识真理的规律相悖。受欧美影响而展开的中国民俗学人类学,说透了并没有提出过什么值得重视的认识。(46)
在一次采访中,温普林这么评价:“我一向认为这种方式是种危险的陷阱,访问者可以先入为主地设定谈话的基调儿,决定了把你作为哪一类货色推销给大众,而被访者呢,也完全可以利用访谈者,编点儿瞎话蒙人。而且这种谈话很可能产生误导,使不能明辨是非的读者误入歧途。”(47)
张承志和温普林都太过悲观了!巴利是作为一个正常的人类学家进入田野的,却以一个“天真的人类学家”的形象走出田野,并且以悲喜交杂的“一场不同寻常的毛毛虫瘟疫”开头,写起自己的田野汇报。在因为毛毛虫瘟疫的“喜感”咧嘴笑的时候,我们也不得不正视他的这一条转变线索和他要借此表达的反思。在《天真的人类学家·序》中,赵丙祥将巴利比作了“捣蛋鬼”,这个命名与《天真的人类学家》这本书的处境、意境都极为吻合。它或许不能作为一部严肃的学术著作,但巴利却是个伟大的人类学家。金小凤也是如此评价温普林的:他有时候正经,有时候不正经,但很少时候是假正经,大多数时候是假不正经。
简单说,周作人、巴利和温普林无非就是明人冯梦龙强调能发名教之伪药的山歌的“情真”和今人巴金所说的“真性情”而已。只不过简单的事最难做了,索性按自己的喜好,回答自己的问题。民俗志,何妨自私而为?
六、尝试:边界与实验性
这个世界是在“混沌”中生成的,本雅明命名的散发着光晕的古典神话、史诗大抵如是说。福柯写癫狂也是在这种情境之下:“在那里我医生不像医生,病人不像病人,倒使我能够以一种客观的、开放的眼光来看待问题,不受常规的羁绊。”(48)只有在规整的分类面前,另一些奇怪的“边界”才能显现出来。赵丙祥也如此给巴利证言:“这正是知识捣蛋鬼的价值和意义。”(49)所以,不是去田野,而是自己出发“发现”田野;不要田野里的人奇怪,他们正常,你“奇怪”就可以了。田野并无定法,是太过强调理论的学界把田野弄得僵硬、机械,让人望而却步、如履薄冰。其实,心甘情愿地“被人牵”比“牵别人”更重要。(50)《银翅》里提出的直觉主义、“反观法”都是如此。
当下,作为群居的女大学生卧谈的基本话题,其婚恋观并不明晰,反而有被污名化的嫌疑。我们发现了这一有趣也严肃的田野,结果陷入了“正常”与“不正常”的沼泽。起初,在宿舍卧谈时,孔雪只是听。后来,出于明确也是自私的“学术”目的,她开始引导九零年前后出生的室友系统地说对相亲、恋爱、结婚、孩子这些婚恋关键词的看法。结果,我们渐渐发现,童年经历、本科学校和城市风物、家庭氛围对每个人婚恋观的影响。但这依旧是条寻常的路子。在她怂恿室友献身参与京城大学之间玩命式的相亲联谊活动时,这几个每天晚上都喊着要风风火火找男朋友的室友断然拒绝了。再到卧谈,她默默按下手机的录音键时,问题越来越多也越发杂乱。首先,这样得来的资料可不可以用,怎么用?其次,卧谈中,她一方面在引导,一方面也必须贡献其个人的经历才能让谈话继续。在话题比较敏感越来越隐私时,录音键到底是按还是不按?三两个月间断的录音已经让每个人的“婚恋档案”显形了,单纯的分析整理没有问题,但也没什么“意思”。当试探性地也是忐忑地表示可能对室友起个化名进行学术写作仍然有的种种顾虑时,她的另一位“拉拉”朋友却兴奋异常,说:“你一定要做我们这些女同性恋的亚文化啊!一定要把我写进去!”
但是,在这个带有学术私情的整个卧谈的过程中,室友们总体认为孔雪“不正常”。因为她坦率地说出了自己下述论调:婚姻是一种畸形的制度,爱情是被“制造”出来的,孩子和伦理道德之间有黑洞;孔老二断言的“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和叔本华觉得大多数女人是种本性“低劣”的生物很有先见;求婚、结婚、新婚虽然幸福,但到底是“套子里的人”。基于此,一位室友反过来将她定义为“解构主义的女性主义者”。于是,“不正常”的她看“正常”室友的婚恋观觉得有趣,“正常”的室友觉得她怪异。再加之拉拉朋友,涉事三方中的每一方在他者眼中都是有趣的,抑或不停地被他者进行着“正常”或“不正常”的命名、建构。女大学生如此,男大学生又是怎样的风景呢?在男女的交流对视中,无论个体还是群体,双方又是如何给对方命名的呢?还有他们的长辈、兄长以及所置身的社会对此将会有怎样的言与行?正常到不正常究竟有多大的解读空间?如同古今、内外、左右、男女、上下、真假一样,它能否成为都市民俗学的一个基本话题?
《乡》虽然题名曰“父亲”,但并未忽视与父亲两位一体且相互涵盖的“母亲”,并将“父亲”、“母亲”这两个最寻常不过却久违了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制造了出来,使离开乡土的无根的都市读者多少都有点家园的感觉。这也是“裸写”的《乡》的亮点之一。数十年来,中国人的“父亲”,至少被罗立中的《父亲》占去了二十分之一。有趣的是,在组委会审核的《父亲》时,因应时政,要求罗立中在《父亲》耳后加了一支笔,以体现新时期农民大众中“父亲”的文化身份。这并非反讽与冷幽默。现实当中,大街上的哪一位父亲又何尝不是被加上各种时代的、传统的、政治的符号,并被它们驱遣着主动塑造自己?悖谬的是,这又是一个驱逐“父亲”的年代,是“青少年文化”大行其道的年代。(51)人们不仅放弃了父子文化链条,“母亲”同样被抛弃。职业女性、剩女、宅女、天天练琴的乖乖女、一夜成名的超女、绯闻女星、站街女、留守妇女、打工妹、拉拉、同妻等等五彩缤纷,点染着当代女性的谱系学,亦是苦心经营的显学。乡土社会的“妈妈令”同时在形而下和形而上两个层面远离了民俗学。都市子民欢天喜地也是懵懂地跨入了“无父无母”的时代。面对这样一个时代,关注现代性的都市民俗学又能做些什么?
个体的塑造不仅是被动的,同时也是主动的,既表现为行为,也表现为言语。活跃于当下的有机知识分子都在勉力重塑自己的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的谱牒,或严肃或诙谐,或低沉或高亢。(52)与此不同,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茅盾编的《中国一日》就是要再现1936年5月21日,阴历四月初一这一天的中国人的生活。(53)数年后,声名鹊起的才女张爱玲的参差笔法只写现代性都市市井“非英雄”的诸相、音声与传奇。(54)无意中直接承继了七八十年前茅盾和张爱玲各自开创的传统,在“实验性”的领域里,当下一些先锋群体和杂志对“小”人物日常生活记述的尝试显然更有意义。
《我们·People》是一次大众的摄影实验的结果。在2011年的3月25日,由豆瓣发起,无数民间的普通人和摄影爱好者在自己所在城市的某一个角落按下快门,以这种偶然的方式呈现那一天那一刻普通中国人的生活和生存状态。3月25日这个时间的选择,没有深意,就因为“是个极其普通的日子”。编者“我们”最大的愿望是,“即便在若干年后,人们还能拿着这本书,说:‘看,那个时候是这样的。’”(54)截至2013年3月初,87辑图文并茂的《老照片》和网易新闻坚持了228期的《看客》大抵都有此意。
与此相类的还有《肖像》。《时尚先生》2010年9月刊的主题是18岁到100岁的“中国男人”的肖像,历时两个月,跨越北京、南京、深圳、香港、厦门、丽江等十余座城市。作为月刊,有限篇幅让每个人的肖像下角只有三五句话的空间可供言说。不过,如此一个实验性的立意,其空间却可以被每一个读者延伸。编辑叶三是带着困惑也带着不贴标签的立场完成这个专题的:“这说明什么,我没有想明白。正如《肖像》这个专题的初衷一样,我们力求呈现,避免贴标签,避免概括……每个人都是自己的肖像,我们仅有权观看——但在这难能可贵的观看过程中,能认识他们中的每一个人,已足够让我感激。”(55)
这种观看的态度在民俗学看来是亲切的,甚至与人们对民俗志的基本定位如出一辙!不过,依托画面的“呈现”又和民俗学拉开了一定的距离。启发依旧存在:如果画面的冲击和言简意赅的自白已经独特地展现了当代“都市人”的生活和生存状态(即便是瞬间的),那么一篇“专业”都市民俗志的长篇大论不见得比它们的诠释更有意义。跳出学科的小圈子之后,以文本、影像、音频以及行为等多种载体呈现的都市民俗志怎样站稳脚跟、安身立命,才更有意思?如同斯芬克斯之谜,这仍然是待解难题!
注释:
①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上编),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1页。
②刘铁梁:《民俗志研究方式与问题意识》,《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刘铁梁:《“标志性文化统领式”民俗志的理论与实践》,《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
③廖明君、岳永逸:《现代性的都市民俗学:岳永逸博士访谈录》,《民族艺术》2012年第2期。在对瑞士民俗学理论的评介中,户晓辉也指出了中国民俗学这一转向的应然,参阅户晓辉:《建构城市特性:瑞士民俗学理论新视角》,《民俗研究》2012年第3期。
④朱清蓉:《乡村医生·父亲:乡村医患关系的变迁(1985—2010)》,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8页。
⑤林耀华:《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庄孔韶、林宗成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207—214页。
⑥“光晕”也译作“光韵”等,是本雅明揭秘以照相摄影、电影为代表的现代可机械复制艺术品“不足”的核心概念。原始艺术中独一无二的、本真性的,以巫术、宗教仪礼为基础生发并具有膜拜价值和即时即地的这一特质,正是仅具展示价值的可机械复制艺术品所拒斥与驱逐的。参见[德]瓦尔特·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王才勇译,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年。
⑦当然,《乡》不仅是受了《金翼》的影响。1940年代,杨堃等在燕京大学指导的系列书写当年北平民俗的学位论文是其另一精神来源。刘铁梁教授近些年倡导的“标志性文化统领式”的民俗志同样对《乡》影响深远。在相当意义上,燕京大学那些学位论文的共同点除了作者们自己强调的局内观察法,就是把理论思考化于无形的裸写。
⑧艾伯华对五四时期到1960年代民俗学在中国的工具性角色有非常好的梳理和阐释,参阅Wolfram Eberhard,“Introduction:The Use of Folklore in China”,in Studies in Chinese Folklore and Related Essays,published by Indiana University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Language Sciences,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Folklore Institute Monograph Series,Vol.23),1970,pp.1—16。当下中国民俗学的工具化使用,可参阅岳永逸:《反哺:民间文艺市场的经济学——兼论现代性的民俗学》,《思想战线》2010年第5期。
⑨相关梳理参阅岳永逸:《空间、自我与社会:天桥街头艺人的生成与系谱》,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第228—229页。
⑩[美]保罗·拉比诺:《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高丙中、康敏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中文版“自序”,第1页。
(11)[美]乔治·E·马库斯:“中文版序:《写文化》之后20年的美国人类学”,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高丙中等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9页。
(12)Vincent Crapanzano,“Hermes' Dilemma:The Masking of Subversion in Ethnographic Description”,in James Clifford and George E.Marcus (eds.),Writing Culture: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6,pp.76,74.
(13)顾颉刚:“序”,奉宽:《妙峰山琐记》,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1929年,第4—7页。
(14)侯长春:《旧京风情》,中国电影出版社,1992年,第1页。
(15)岳永逸:《空间、自我与社会——天桥街头艺人的生成与系谱》,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第292页。
(16)黄宗智:《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法律出版社,2010年,第79页。
(17)黄宗智:《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法律出版社,2010年,第95页。
(18)Vincent Crapanzano,“Hermes’Dilemma:The Masking of Subversion in Ethnographic Description”,in James Clifford and George E.Marcus(eds.),Writing Culture: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6,p76.
(19)岳永逸:《空间、自我与社会——天桥街头艺人的生成与系谱》,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第8页。
(20)邓海帆:《陋巷人物志》,国家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第6—7页。
(21)这也是在天桥的后续研究中,岳永逸进一步探讨并试图回答的问题。参阅岳永逸:《老北京杂吧地:天桥的记忆与诠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第1—37页。
(22)[德]本雅明:《本雅明文选》,陈永国、马海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291—315页。
(23)[日]妹尾河童:《窥视印度》,姜淑玲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
(24)小鹏:《背包十年——我的职业是旅行》,中信出版社,2010年。
(25)[意]奥里亚娜·法拉奇:《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毛喻原、王康译,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
(26)弯弯:《可不可以不要铁饭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
(27)王军:《采访本上的城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371页。
(28)关于媒介田野和学术田野的关系及进一步探讨,可参阅岳永逸:《学术田野与媒体田野:直面灾后族群文化的传承》,《民族艺术》2008年第3期。
(29)岳永逸:《老北京杂吧地:天桥的记忆与诠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第27页。
(30)《歌谣》第1号第一版、第二版,民国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
(31)岳永逸:《擦肩而过的走阴》,《新产经》2013年第2期。
(32)邓海帆:《陋巷人物志》,大象出版社,2003年,第1页
(33)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3页。
(34)顾颉刚:“妙峰山进香专号引言”,《妙峰山》,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1928年,第1—10页。
(35)[意]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36)《东方早报·上海书评》编辑部:《两百年的孤独》,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第6页。
(37)张承志:《常识的求知:张承志学术散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
(38)[德]赫塔·米勒:《一颗热土豆是一张温馨的床》,刘海宁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页。
(39)庄孔韶:《银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1—20页。
(40)周作人:《艺术与生活》,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4—8页。
(41)周作人:《艺术与生活》,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2页。
(42)乔健:“序”,岳永逸:《空间、自我与社会——天桥街头艺人的生成与系谱》,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第2—3页。
(43)朱光潜:《后门大街》,《论语》半月刊1936年第101期。
(44)周作人:《艺术与生活》,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2页。
(45)[英]巴利:《天真的人类学家》,何颖怡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40页。
(46)张承志:《常识的求知:张承志学术散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第4、5、139页。
(47)金小凤:《小凤丢手绢——寻问当代26位先锋人物》,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第2页。
(48)[法]福柯:《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严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2页。
(49)赵丙祥:“序”,[英]巴利:《天真的人类学家》,何颖怡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xiii页。
(50)岳永逸:《老北京杂吧地:天桥的记忆与诠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第284—308页。
(51)甘阳:《通三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65—77页。
(52)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北岛、李陀:《七十年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
(53)茅盾编:《中国一日》,生活书店,1936年。
(54)张爱玲:《传奇》增订本,山河图书公司,1946年。
(55)本书编辑部:《我们·People——2011.3.25民间记忆》,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序”,第2页。
(56)叶三:《肖像》“作者手记”,上海三联书店,2010,第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