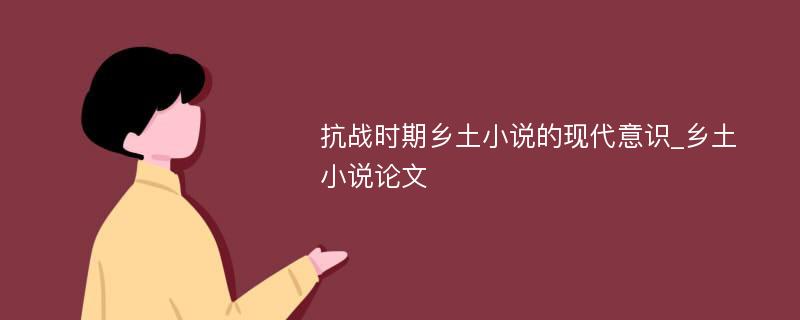
论抗战时期乡土小说的现代意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战时期论文,乡土论文,意识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乡土小说在抗战时期,得到了很大发展,“一九三七年以后,中国现代文学进入了一个以乡村题材占统治地位的阶段。”(注:李欧梵:《论中国现代小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85年3期。)长篇的数量与容量远远超过二三十年代,张天翼、沙汀、碧野、姚雪垠、田涛、王西彦等三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作家在四十年代显示出了强大的艺术创造力,他们的关怀点主要是苦难的乡村。不过,这时的乡村,已不仅仅是三十年代左联乡土小说农民阶级受压迫而终于觉醒最终走上反抗道路的故事模型依托。随着作家对乡土的进一步了解和融入(由于战争和流亡),对乡村真实状况的认识和思考,这一时期的乡土小说显示出与二三十年代不尽相同的风格和价值取向。这里,本文拟通过对抗战时期部分乡土小说的梳理来探索抗战时期乡土小说的现代意识。
一
抗战初期,作家们(包括老中青)虽被战争逼得流离失所,但仍然都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这场全民的抗战运动。原因之一在于他们把战争看作一场火的洗礼,一切丑恶的落后的东西和现象将被扫灭,中国也许会得以新生,抗战在他们看来,是中国的一次新的“风凰涅槃”。作家柏山激动地说:“呵!战争!感谢你。毁灭了旧中国的一切,创造了新中国的人!”(注:彭柏山:《晚会》,选自《〈七月〉、〈希望〉作品选》,人民文学出版社,86年。)的确,“侵略者的炮火给中华民族带来了灾难,也……使之调动了平时无法调动的诸多健康力量,帮助中华民族进行了一次全面的‘体检’,进行了一次有效的排毒工作。”(注:郭志刚:《论三四十年代的抗战小说》,《文学评论》,95年4期。)而对于乡村,当时就有人看到:“中国在抗战中有了文化的进步,甚至在一百年来的无数次风暴中没有受到显著影响的最僻野的山村,在这三年中也发生了自觉的激荡”。(注:胡绳:《战争与文化》,《夜读散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96年12月。)在这种情况下,以一种全新的眼光来观照农村、农民的生活和抗日活动,使之与民族的解放事业同步,既不以左联时期文学阶级斗争的眼光,也不以京派作家居高临下的观赏眼光,也不尽以20年代人道主义眼光,而是从民族解放给农村带来的变化出发,一方面,描绘出农民遭受的苦难,暗示他们反抗的可能性:如田涛《沃土》写北方沃土上的仝云庆一家将近一年间的辛劳苦难与不幸,沙汀《淘金记》、《还乡记》通过冷静观察,细密剖析,绘出了四川农村农民的生存现状;另一方面,挖掘出埋藏于农民身上的原始的伟力(那是抗战的后备军);碧野的长篇《肥沃的土地》中战争并未出现,“书中没有暗示这一大事(抗战)在农村中起了什么‘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情景”,(注:茅盾:《读书杂记》,选自《小说研究史料选》,黄俊英编选,四川教育出版社,88年6月。)但碧野笔下的主人公破箩筐无疑是乡村新兴力量的代表,他强壮有野性敢爱敢恨,敢于打破常规,敢于炫耀自己的力量,不满足现实的安排,作者成功地写出了蕴含于农民体内的原始粗犷然而分外强大的力量;艾芜《丰饶的原野》的主人公之一刘老九,路翎《燃烧的荒地》的主人公都是在危急的时刻显示出了自己强大的力量,不再是可怜的任人宰割的顺民。两类作品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对农民灵魂实质的提问,但并不能因此否认其中的现代精神。的确,乡土文学最为优秀的现代性传统,集中表现在“对愚弱民魂
的揭露、批判和改造要求上”。(注:朱寿桐:《中国新文学的现代化》,南京大学出版社,92年10月。)但是在民族即将沦亡的中国,争取民族的独立和抗争,并在这一过程中进行民魂的改造,同样具有现代意义。可以看到,抗战期间涌现的一些乡土小说表现出对农民一些先天弱质根性的宽容,甚至还有对农村落后封建思想文化,宗法制的认同(而非二十年代乡土作家毫不留情的批判)。如《差半车麦秸》的主人公其实是个落后保守封建自私的农民,但因为参加了抗日游击队,他的劣性都成了可爱的笑话。《沃土》里着重展现作家故乡的“人生形态”,对仝云庆的封建保守只是实录,批判意识少而又少。《丰饶的原野》对具奴性的沉默的邵安娃和具阿Q双重性格的赵长生,作家也不忍下笔批判。《淘金记》里的劳动群众麻木愚昧,“一点愤怒、反抗的情绪都没有。”(注:唐弢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但并不能根据对劣性的宽容否认其现代意义。宽容并不等于漠视,正因为作家们对抗战的期望使他们认为战争能“荡涤劣根”,《差半车麦秸》、吴组湘《山洪》、穗青《脱缰的马》里的主人公克服弱质逐渐走上思想转变的过程,都是作家的美好愿望及期待。诗人艾青的一句“让没有能力的、腐败的一切在炮火中消灭吧;让坚强的、无畏的、新的在炮火中生长而且存在下去。”(注:艾青:《忆杭州》《选自〈七月〉、〈希望〉作品选》,人民文学出版社,86年。)可以看作是作家的共同心声。
然而,希望通过战争使乡村发生立刻的质变的美好愿望和期待很快被作家发现只是一个乌托邦。除了血与火的战争场面外,对于抗战,内地乡村感到的只是拉伕、驻军、逃难、破产、暴发户以及那并未有根本改变的乡村社会秩序。美好的愿望与事实相悖,不能不令作家感到震惊和失望。突变显然成了泡影,抗战进入了相持阶段,痼疾渐渐暴露,作家开始重新捡拾起对社会的批判态度,揭示出一系列抗战期国统区的黑暗现实。在四十年代的国统区,这可以说是一个大趋势,鸳鸯蝴蝶派的张恨水以写国难小说声名重振,他的《八十一梦》以嬉笑怒骂的荒唐形式,以严峻的现实主义态度,谛现苦难深重的社会人生;右翼作家王平陵也写了一些作品,如《进城》、《重庆的一角》,表达了对发国难财的暴发户的不满。乡土作家的笔触伸向更广阔的乡村和小镇,沙汀在四川小镇的其香居茶馆里为读者上演了一幕征兵丑剧;在客家杉寮村里发生了官绅结合囤米积粮,勾心斗角的事件(易巩《杉寮村》);以及发国难财者的“持久战”理论;还有未曾松动,反而加剧的农民的苦难,艾芜《石青嫂子》中石青嫂子辛勤开垦耕种多年的土地忽然被宣布非她所有,《故乡》中农民因挤兑风潮而纷纷陷入绝境。暴露与讽刺小说的一度兴盛一方面说明作家的热情和急切,另一方面却又暴露了作家的思想深度不足。总体看来,乡土作家们对黑暗现实的揭露,其意义仍停留在三十年代左联乡土小说的高度,延续着茅盾等人的社会剖析派小说风格,只是比之较为具体化,不再限于图解概念。但由于思想欠缺,对社会的观感流于平面,现代意识反而淡化了,其后果虽然揭示出了一些真实的客观存在的现象,但却没有能因此向前推进一步,不论是作者还是作品本身,落入了晚清谴责小说“笔无藏锋”的窠臼。如《故乡》描绘了故乡小镇上侵吞捐款的女校长,私办银行的教育局长,存心挤兑的商会会长,以及他们道德的虚伪和沦丧、乡村里主人公的放高利贷盘剥佃户,六亲不认的母亲等人的群丑图。但也仅限于描绘,主人公(一个革命青年)既未能与母亲决裂,也未能看清故乡的真面目。与之相似,我们看到的是暴露与讽刺作家们大多放弃了现实的深入挖掘探讨,而挑选了较平面化的生活作为创作题材,而这些题材的根本缺陷在于它触及不到社会和灵魂最深处,而只是导致了表面的刺激和政治上的高压政策,或者又重新引入反映阶级压迫和抗争的主题。作家们以为贴紧现实的作品却因为消解了现代性而成了对社会的浮光掠影式的描绘,同时也就注定了其意义
的时效性。由于“对暴露和讽刺了解上的肤浅,限制了这一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发展。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这一文学思潮开始走向衰落”。(注:刘增杰:《文学的潮汐》,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这里的“肤浅”,不仅仅是指对“暴露与讽刺文学”理论上的限制和误解,还在于这些作品本身的缺乏深度,即热情有余,思想不足。
二
相比于一般的讽刺暴露文学,沙汀的《兽道》就实在不同凡响,它以遭洗劫过的乡村为背景,展现了乡村的人文情态,作家深刻地揭示出乡村环境封建文化根深蒂固的持久性,及其自私残酷无人道。战争劫掠带来的是物质和生命的灾难,在某种程度上是暂时的,灾难过后,亟待解决的是重建新的秩序,但是正如曾在纳粹集中营里渡过少年时期的捷克作家伊凡·克里玛认识到的那样:“剥夺别人生命和自由的人是可恶的和不可容忍的,然而从被剥夺的人的经历中也许并非必然生长出真理和正义:因为极端的经验可能使人的判断力发生倾斜。”(注:崔卫平:《布拉格精神》,《读书》97年10期,三联书店出版。)伊凡这一判断建立在肯定“剥夺”这一行为发生之前的人们的判断力正常或健康的基础之上,是因为战争使人的判断力(主要指人们的思想道德模式)变得不正常。而《兽道》的作者清醒地意识到被劫掠前乡村人民的思想道德模式是不正常的(也就是说是非现代性的),作者也和抗战初期的作家一样,渴望经过劫掠后的乡村能建立起一种相亲相爱的同情、团结的健康的人文关系。但事实却令作家无比失望,劫掠并不能使被劫掠者“必然生长出真理和正义”。乡村延续了战前的道德模式,老妇在劫掠中受了痛苦,但共同经历了劫掠的乡村人却先是表示出貌似同情的惊讶,这惊讶中还有一种心理的满足,随后,健忘的乡村人忘却了劫掠者,却盯住了老妇的一句为救女儿无可奈何求饶的话而百般责问和取笑,终于使老妇的精神完全崩溃以至疯狂。这是祥林嫂的故事在四十年代的重演。战争并未能令乡村重建新的健康的人文关系,相反,原有潜在的民族的劣根,因有战争而得到了充分的舞台展现机会,进一步发挥着“吃人”的功能。认识到这一点是需要勇气和眼光的,而更重要的在于作家的现代意识。一旦作家将眼光滑入深层现实就不自觉地回到了“对愚弱民魂的揭露、批判和改造要求上。”作家王西彦可以说是一直追随着鲁迅的乡土小说作家,他一直探索以现代意识来关怀乡村,也即用现代思想模式来对照批判封建思想模式和民族劣根性。他的长篇《古屋》中这一思想更为显明。一方面,作者常制造《圣经》诵读者“我”与快乐主义者孙尚宪的辩论,显示孙生活的清高与脱俗,看起来是一个西方自由主义和老庄思想在中国的结合体。但另一方面,快乐主义信徒孙尚宪作为封建家长(一个“浪子回头”的败家子),毕恭毕敬地行使着作为封建家长的权利,扼杀了一个又一个年轻的生命,就是这样的人自称快乐主义者自由主义者,
以伊璧鸠鲁派标榜。这具有强烈的反差效果,“古屋”里出现西方个人主义者到此被发现只不过是一个玩笑而已。作为封建家长的威权的诱惑远远大于做一个自由主义者,孙尚宪的精神压迫与统治导致了哑巴侄儿媳妇的发疯,撞墙自杀,侄女与人私奔,廖慧君在朋友的帮助下勇敢地出走。小说“真实地揭露了一个官僚地主家庭的罪恶和它的本质。”孙尚宪惨淡经营的封建家庭分崩瓦解,这个家庭中受压迫的女人都勇敢地“出走”,这出走以后的路,虽仍不显明,但也已不像鲁迅小说的子君出走之后那样悲惨,因为有与古屋为邻的女教师为参照。《古屋》不能算是王西彦的成功之作,但却一直延续着他早期的批判意识和超前眼光。
《兽道》、《古屋》都是通过人物命运来透视战争时期乡村文明的实貌达到批判的目的。不光国统区流亡作家,身在解放区的作家也不例外。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慎重提出了一个超越于普通战争的问题:战争在多大程度上能改造人们的封建思想,涵义与《兽道》相似而感情更加急切。孔厥《受苦人》也指出政治解放并不等于妇女解放。小说中的女主人公贵儿不仅在政治上是受苦人,在阶级压迫缓解之后,面临的是又一重的精神痛苦,新的上层仍然默认她与未婚夫的婚约,因为未婚夫是与她一样的受苦人,解救他的苦难则必须以牺牲贵儿的幸福为代价。阶级的压迫可以推翻,而阶级的压迫造成的心理惯性却使人们因循了原有的思维方式。作家隐隐约约地意识到了这种解放的不彻底性和悖谬,这是具有超前意识的。孔厥的另一篇小说《凤仙花》中,“我”代表了新的统治秩序,扮演了救世主的角色,将凤儿从后爹的封建压迫中解救了出来。这里,新的上层与封建家长以一方说服,一方同意的方式取得了一定的妥协。而《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将妇女解放等同于政治解放,以为妇女解放能通过政治解放达到目的,三篇小说同出于一位作家手笔,也正说明作家思想的矛盾与模糊,他虽然意识到了危机,却没有勇气进一步面对批判。作家的现代意识混合在政治意识中,只能偶露锋芒。尽管如此,在政治解放呼声远高于妇女解放呼声的抗日根据地,这微弱的现代意识也是难能可贵的。
同时,战争的大环境也是对知识分子自身的一大考验,借此,知识分子也反观了自己。《古屋》中的“我”经常读《圣经》也是一种现代性思考方式,但是对于“我”诵读圣经,我们产生的印象只是“我”是一位较消极的避世者,对于现世似已灰心,已无可相信。可是,《圣经》与佛道不同,它并不是可以借之作为避世的工具。“我”虽然时常沉溺于此,然而也渐渐地被拉回到现世,古屋里的女性的出走使“我”对自己思想大于行动的劣性有了一定认识。艾芜《故乡》写一位革命知识青年余峻廷返乡十余天内发生的事件。余峻廷怀着一腔宏图大愿改造故乡,可在故乡只呆了十余天就带着满心失落和失望离开了故乡。小说解剖了革命知识青年对现实的隔膜,理想虽完美,然而幼稚不坚实、易热情冲动也极易灰心泄气、行动软弱等一系列弱点。沙汀《困兽记》“真实地反映了国统区进步知识分子共同的抑郁、愤怒苦闷和追求。”(注:唐弢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从而也进行对自身的批判和反思。
乡土作家对自身和对国民性的认识和批判反思并不是个别的现象,它应和了当时文坛的一股反思浪潮。近年来由于对个体作家研究的深入,一般认为沈从文,萧红等作家抗战时期较注重对民族文化传统和国民性的批判。其实,那些孜孜于写“与抗战有关”的乡土文学作家也常对自己和现实产生类似的困惑和反思,这是有其思想、时代和文化背景的。早在三九年,当时还年轻的评论家胡绳在一篇文章中就指出:“文学家在创作中深深地发掘着人的性格,当他发掘得越深,他就越走进哲学上的各种范畴,这种范畴正是现实的生活的反映。”(注:胡绳:《战争与文化》,《夜读散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96年12月。)的确,作家坚守着自己的文化、哲学观念和现代意识就必然使作家对固有的现存的文化进行反思和对照,也更容易看到现存文化的缺陷,而达到对现实生活的真正的反映。这都说明,作家的现代意识在抗战时期并未消失,而是继续存在并随着时代的不同、环境的复杂而有所发展。
三
如果说王西彦、丁玲等通过对国民生存状态、女性命运的阐释达到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延续了20年代的乡土文学的现代批判意识,孔厥则是揭示了政治解放呼声高亢下对女性解放的忽视,其现代意识是属于四十年代的。那么同样写四十年代的女性,于逢、易巩作品中的女性却以一种逐渐觉醒的姿态出现,在某种程度上延续了人的解放、人性解放主题。
于逢、易巩都曾是革命文学作家,其作品主要也还停留在暴露与揭露方面。但是,他们从女性命运入手,认识到女性不仅受阶级的压迫,还受到来自封建思想模式的更一层压迫,在作品中他们更注重写女性不仅仅是阶级意义上的觉醒,还有来自个体意义的女性的觉醒。两篇“堪称双璧”的作品《乡下姑娘》、《杉寮村》都以战争时期农村生活为背景,并以客家妇女为主人公。《乡下姑娘》中军队在韫玉山庄驻军给山庄带来了变化,何桂花从麻木地受苦受累开始了缓慢地生命骚动,由起初的任由丈夫婆婆压迫凌辱开始了一定自觉的意识和行为的反抗,生命由压抑到骚动到一定程度的解脱,她终于大胆地和勤务班长在山坡上野合了,虽然这在勤务班长看来,只不过是极普通无趣的玩弄女性,满足性欲而已,但在何桂花,却是人的自我觉醒的标志。生命觉醒使她不再甘于韫玉山庄受压迫凌辱的非人生活,她勇敢地想趁军队转移时逃走,走上一条自新的独立的路。这说明《乡下姑娘》的主题意义并不在全民抗日、民族解放,暴露与讽刺等时代主题(虽然这在小说中都存在),还有“命运般的历史重压下人的生命觉醒”。(注: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细究起来,乡土小说中农村妇女形象并不缺乏,鲁迅笔下的中国农村妇女受压迫的多重和深重,即不仅有封建四权的压迫,自身的愚昧也是不能觉醒的原因。奇怪的是这一深刻命题延续到《鼻涕阿二》、《为奴隶的母亲》就出现了断层。京派乡土作家把农村女性作为美和纯洁至善的化身来歌颂,且不说渡口守候的翠翠,即如自己受愚昧野蛮的封建旧俗的毒害并且继续以之害人的萧萧,沈从文也充满了赞赏。罗淑《生人妻》里的妻子作了还债的工具,她虽已有一丝自主的情感意识,不愿意被卖给丑怪的新丈夫,但做到的也只比祥林嫂大胆了一步,逃回夫家,却又陷入了更加无路可走的境地。而“乡下姑娘”何桂花的反抗虽然也告失败,但她的生命意识、个性意识却已经渐渐觉醒。茅盾当时就指出:“何桂花这一个人物假使不能说是我们现在所有的农村妇女典型人物中写得最好的一个,那一定是最有力的一个。”(注:茅盾:《读〈乡下姑娘〉》,选自《小说研究史料选》,黄俊英编选,四川教育出版社,88年6月。)于逢的贡献正在于他敏感地捕捉到了抗战给韫玉山庄带来的变化,尤其是农村妇女个体意义上的觉醒。
如果说,于逢写出了“命运般的历史重压下人的生命觉醒”,易巩《杉寮村》则揭示了“生存危机面前女性的自立精神”。(注: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主人公黄青叶“一贯继承着客家婆婆的勤劳、倔强、朴素的优良传统,以及能够独立独行的男子气概”,为了生存,她不再与她的婆婆那样死守着田地而加入为军队挑货物的行列,她“警惕的像头猎狗似的,整天睁大眼睛,竖起耳朵,到处探询可以赚钱的门路”。她也不像她婆婆那样安于“穷和饿”,而希望靠着自己力量(主要是体力)在恶劣的环境中顽强地生存着,她完全不像以往的农村妇女那样任劳任怨,认命麻木地接受着苦难,成为时代、制度的牺牲品,而是勇敢地反抗着命运,包括后来大胆地将稻田改种蕃薯。生命力的强悍可与路翎的郭素娥相媲美,不过郭的饥饿里包含着性的成分,黄青叶则还在生存方面,相对于时代,这也许更真实一些。与黄青叶类似的女性形象在易巩的《珠江河上》再次出现,只不过这时的主人公是一位“艇家婆”,她对生活不满便痛快的咒骂,当看到两个艇妹在警察的命令下拼命追拿抢米者时,她的咒骂更加厉害,对抢米者有着强烈的同仇敌忾感,并且骂“我跟她们去抢一份还好!”“祖先的灵位打瞌睡么?枉我早晚奉香灯了!你以后再不灵圣,就一个一个把你们破掉了当柴烧。”这是何等大逆不道的思想,一位泼辣、强悍、不信命运的农村妇女形象活生生地展现了出来。可以看出,艇家婆是黄青叶形象的继续。
作家在战火纷飞的岁月仍不忘对女性命运的关注,并指出了农村女性在四十年代的一种新的可能性。五四浪潮时期出走的娜拉大多是中上层的知识女性,四十年代抗日大潮则促进了下层的乡村女性生命的觉醒。何桂花和黄青叶以后的道路虽然并不明朗,但她们已不再如祥林嫂的麻木,郭素娥的盲目了。她们和从古屋出走的女子一样,独立的自我个体意识已经确立。几个女子的觉醒过程是在战争期间进行的,可以说,抗战之于这些女子,是相类于五四之于五四女子的。作家把眼光聚焦于女子,进一步(也可以说是重新)提出了妇女问题,人的解放首先是妇女的解放,对人物命运的关注和思考无疑是抗战时期乡土小说现代性的一大证明。从作家的角度看也说明新一代的年青作家也具备较独立的现代意识。对“人的解放”主题有了与三十年代不尽相同的进一步的思考,同时,他们的思考与五四时期“人的解放”呼声也不是简单的重复,“人的解放”的对象、内容、结局及背景都有了大的变化。四十年代作家具有五四作家的现代意识与独立的思索能力,却较少五四乡土小说家的悲观色彩,他们拥有把握现实的自信。五四作家标举“人的解放”的作品,多以失败或颓丧苦闷告终,四十年代乡土小说中“人的解放”作品人物命运虽然也有悲哀,但结局总是略带亮色的。
通过对抗战时期一部分乡土小说的梳理及其现代性思考,不难看出,司马长风所说的抗战时期是小说“凋零期”的视点是不够完备的。而在一些乡土小说史著作中,对抗战时期的乡土小说大多涉及不深,且受五四乡土小说特征左右,以为抗战时期乡土小说丢弃了批判传统,是“变调”的乡土。近年来,由于对个体作家如萧红、骆宾基、端木蕻良等研究的深入,他们的乡土小说受到一定重视,但对于总体特征的把握似嫌不够,本文就是在这一考虑下而写,认为抗战时期乡土小说对中国现代乡土小说的意义不可抹杀。一方面,战争初期,它强调在民族解放的斗争中争取对国民的改造以及阶级意识的觉醒;一方面,战争中后期,它延续了五四乡土小说的批判国民性意识。前面说过,这并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五四运动二十年后中国知识分子的进一步反省和深入思考。同时,它让五四“人的解放”主题由中上层知识分子转入下层农村妇女的个性解放。这是五四及三十年代乡土小说所未涉及的,自然具有创新和开拓意义。总之,应当充分认识抗战时期乡土小说的独特意义,排除偏见,使它成为现代乡土小说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否则,我们的现代乡土小说史就不可能完整和科学,也不可能正确认识抗战时期乡土小说所具备的现代意识和独特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