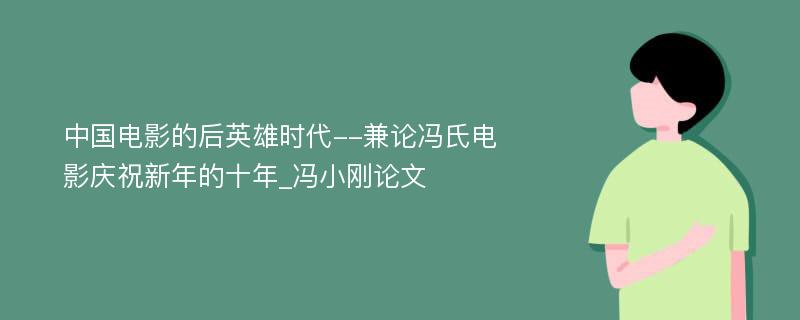
中国电影的后英雄时代——兼论冯氏电影的十年贺岁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电影论文,英雄论文,时代论文,电影论文,兼论冯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奥斯卡·王尔德曾言:“所有蹩脚的诗都是真诚的。”这并不等于说:所有伟大的诗都是不真诚的。但是起码有一点毋庸置疑,伟大的诗作几乎都依靠比喻——“不但是对词汇本义的转换,而且还对先有喻义作再转换。”[1]作为比喻载体的现象——电影艺术,在它从脚本到后期拍摄成型的制作流程中,除了技术层面的问题之外,构成整部电影灵魂的是它的幻象表现。这种幻象存在于编剧的意识层面,最终落脚于导演的镜头语言。但幻象不是纯主观的,它或多或少受到外界环境的干扰或熏染。它是客观世界反映在主体意念之上,并经过艺术加工之后的某种投影。“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胡适语),同样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电影。百年的中国电影,前后六代的电影导演在不同话语背景中将他们对历史与现实的诉求、精神与现世的羁绊投影在不同的电影影像之中:“第一代导演郑正秋、张石川初创电影形态,以言情与武打挣扎在早期资本上海的票房商海;第二代导演蔡楚生、孙瑜受命于国家危机,沉沉的影像深切地寄托着人民的苦难;第三代导演崔嵬、谢晋周旋在历史漩涡,其影片每每映照社会政治的起伏跌宕;第四代导演张暖忻、谢飞劫后重振,于现实与艺术之间摸索电影的本体皈依之路;第五代导演陈凯歌、张艺谋置身启蒙大潮,以对老中国的形塑折服了世界影坛;第六代导演张元、王小帅侧身商业时代,城市素描在他们的电影中飘然浮现。”[2]在这代际延续的谱系中,不论是哪一个时期的电影导演,在他的作品中我们都可以读到有关人与外在环境,即社会的命题:从《火烧红莲寺》中读到人如何以侠义征战于现世;从《渔光曲》中读到人如何以信念栖息于梦境;从《芙蓉镇》中读到人如何以任性逃离于混沌;从《人·鬼·情》中读到人如何以任情出入于幻境;从《红高粱》里读到人如何以蛮荒苟活于俗尘;从《站台》中读到人如何以破碎挣扎于虚无。无论是栖息或挣扎,我们都会发现电影悄悄建构起了人与社会的矛盾张力场——一端是人本主义、一端是民本主义。
以人本主义为核心的电影,导演倾向于表意或象征,以强烈的视觉冲击来取代原本常态的叙事结构;以民本主义为核心的电影,导演倾向于写实或浪漫,以传奇的浪漫故事来取悦大众的审美情趣。长久以来,中国电影导演往往是两条路线必择其一而从之,只不过有时体现在电影中的程度或深或浅而已。为什么人本主义与民本主义一定要成为悖论?在滚滚红尘之中是否可以做到既“任情任性”又不忤逆世情?在冯小刚十年的贺岁电影中观众惊奇地发现,他让这二者婚媾并开出美丽的花来。当然这场婚礼的双方,必须有一方做出改变。就像张爱玲所说,婚姻不需要热情,而需要虔诚。虔诚意味着放弃个人固有的自由,心甘情愿走入围城。在这两者之中,民本主义的基础是大众,大众是不会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所以如果要让二者兼容必须改变人本中的某些元素,如纯粹的艺术性中要掺杂商业化运作模式;开天辟地的英雄要受藏污纳垢的世俗情绪浸染。由此,在中国电影史上,以冯小刚十年的贺岁电影为代表,开创了一个迥异的电影时代——后英雄时代。
后英雄并不是非英雄或者无英雄,而是英雄的世俗化、烟火化。它以打破英雄的“高大全”模式为前提,以拉近英雄与凡人的距离为手段,在“藏污纳垢”的民间社会重新树立起一个真实的阿喀琉斯。不论是《甲方乙方》中,借了女朋友给人圆爱情梦却又担心女朋友跟人跑了的姚远;《不见不散》中,见了美女就忘了装瞎子的刘元;《没完没了》中,有绑架之心却无绑架之胆的韩东;《大腕》中,搞了超级豪华的葬礼却被送入疯人院的尤优;《手机》中,盛名之下却在情欲之中纠缠的严守一;《天下无贼》中,深陷污渠却不失良知的王薄;《集结号》中,言辞粗俗却重情重义的谷子地还是《非诚勿扰》中,情场坎坷却桃花不断的秦奋,这些俗尘中的阿喀琉斯都有一个共通性:消解崇高、拒绝宏大、追求残缺。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共同代表了后英雄时代中人物的精神气质。
一、消解崇高
康德曾对崇高感有这样的解释,“以某种方式对我们的感觉想象力施加暴力的知觉可以引起精神上的重新振奋。”[3]它往往对某种事物产生同敬畏和敬慕相似的朴素的或者消极的快感,是一种严肃认真和令人激动而不是游戏的和平静的审美感应。如面对万里长城,我们会敬慕其巍峨壮观,从而产生对历史压迫的厚重感和激动兴奋的精神快感。如果投影中国电影史,前后六代电影导演的镜头或浓或淡地都会迫于这种暗影重重的民族恢宏影像,而使得作品中的人物潜意识里将崇高视为神圣不可侵犯并沦为一种道德说教。这种伟岸的民族影像摇曳不定,时而晦暗,时而明朗,时而欢愉,时而阴郁。而在冯小刚的电影中从《甲方乙方》到《非诚勿扰》都在消解这种由政治、历史、传统道德所带来的严肃与认真地说教模式,甚至于经常调侃这样抽象的道德说教,让观众对他们投以既轻蔑又同情的微笑。如《甲方乙方》中钱康每次在帮客户完成一个梦之后,都会习惯性地开会并作总结发言:
这次时间短、困难多,但还是拿下来了。一是扩大了影响,二是锻炼了队伍。缺点是应变能力不够,事先对困难的估计不足,责任在我。送给大家几句话,计划充分,分工明确,大有希望,早点歇着吧。不要喝酒,不要玩牌。
《天下无贼》中黎叔:
说了多少次了,要团结,要看到别人的长处。这次出来,一是通过实战考察队伍,二是考察新人。
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啊。
在冯小刚电影中,开会这一场景不管是“好梦一日游”的“蹩脚”公司还是高智商、低情商的“三只手团伙”,都无非由如下两组人物构成:颇具理论功底的领导和玩世不恭的虾兵蟹将。后者采用貌似恭敬实则戏弄的心态去聆听前者教诲。虽然形式严肃,但已然变了味道。开会的时候,有人暗中打着自己的小算盘,有的干脆就没有听见所谓的指示,更有的甚至于插科打诨,油腔滑调地篡改会议的主旨。特别突出的是《手机》里费墨给《有一说一》栏目组开策划会。费墨的一番长篇大论分别被手机打断了三次,从“火车”、“萝卜”、“狗熊”到“玉米”,费墨自己都不清楚要说什么,相反严守一的那段插科打诨的总结性发言格外吸引人:
肯定是一女的打来的。费老,对面说什么我给您学出来。(学着男女两种语调):开会呢?对。说话不方便吧?啊。那我说你听。行。我想你了。噢。你想我吗?嗯。你昨天真坏。嗨。你亲我一下。(停顿)那我亲你一下。听见了吗?
开会的不严肃态度是现代人自由性情的外部呈现,但更多反映出对开会这一形式的内心抵触情绪。长久以来中国人习惯说一句话,“开会研究研究”。曾经有很多电影、电视剧作品批判讽刺过这种“喜开会、善表决”的“民主”决议体制,如电视连续剧《家有九凤》随处可见让当事人回避而其他的人参与、讨论事关当事人切身利益大事的片断。随着历史的发展,会议已经逐渐消解了它的权威性与严肃性。冯小刚则把原本崇高的集会形式用调侃的方式进行解构,在谈笑间便以日常消解崇高,用随意消解经典,成为一种崭新而重要的艺术风格。
消解崇高还表现在消解绝对权威的道德教条。这种一元性、模式化的创作在40年代的“抗战电影”,五六十年代的“十七年电影”,60年代的“文革”电影中尤为突出。当时的影片侧重于“讲故事”和情节的发展变化,以戏剧化的“起、承、转、合”连缀人物,人物形象成类型化、简单化、脸谱化的特点。所有的人都要服从一种秩序,尊崇唯一的道德理念。如人道主义就是救死扶伤,完美女性就是圣洁无瑕,世间人情就是风和日丽、鸟语花香,而这些在冯小刚的电影中都不同程度进行了消解。如《甲方乙方》一个因恋爱而绝望的人让他在一天内被“美丽的公主”垂青并陷入爱河,当梦醒之后结果一场空,这到底是害了他还是帮了他?钱康引出重症患者需要注射吗啡以化解疼痛的例子,来解释“任何一服药都不能包治百病。”“道德不是空泛的,脱离对象,孤立存在的”。把一个自杀的人从悬崖上哄骗下来虽只是权宜之计,但是既然走下悬崖了就有不再走上去的可能,这又何乐而不为呢?在《不见不散》中,刘元有对脱衣舞女的一番辩白:“脱衣舞怎么了?都得会劈叉折倒立一条腿轻轻松松一抬就得一人多高。这不是任何人都可以胜任的工作。不能因为职业的关系就臆断从业之人的品性。”在《天下无贼》中王薄也曾经非常斥责王丽不告诉傻根生活的真相,“你为什么要让他傻到底。生活要求他必须要聪明起来。作为一个人,你不让他知道生活的真相,那就是欺骗。什么叫大恶,欺骗就是大恶。”
消解崇高,并不是没有道德操守和行为规范,而是强调在这个多元的时代,没有一成不变的道德,只有一成不变的修行。如果你信奉纯真、善良、美好的品行并不断加强自身修养,人格的完善工程便会呈螺旋式上升态势。一个人的修行渐趋完善,那么一个民族的品性便会臻于完美,这应该也是为什么在冯氏贺岁片中,最后都会给我们留有一抹亮色的主要原因吧。明天总是美丽的,亦同《非诚勿扰》中秦奋看向未来的眼睛。
二、拒绝宏大
宏大叙事(mata-narrative),来自于法国哲学家利奥塔《后现代,关于知识的报告》中的重要术语。它指征任何一种艺术形式都:“有某种一贯的主题的叙事;一种完整的、全面的、十全十美的叙事;常常与意识形态和抽象概念联系在一起;与总体性、宏观理论、共识、普遍性、实证(证明合法性)具有部分相同的内涵,而与细节、解构、分析、差异性、多元性、悖谬推理具有相对立的意义;与个人叙事、私人叙事、日常生活叙事、‘草根’叙事等等相对。”[2]此种叙事话语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电影创作群体中曾风行一时。它以压倒性的政治强势随意点染艺术价值,不论是电影画面的构思还是人物形象塑造都离不开十全十美这一主题。从“样板戏”电影中的英雄(如《智取威虎山》中的杨子荣),重拍片中的英雄(如《平原游击队》中的李向阳),到革命时代的英雄(如《闪闪的红星》中的潘冬子),合作社时期的妇女英雄(如《李双双》中的李双双),他们或舍生取义,或朴实无华,或活泼机敏,或泼辣爽快,不论何种性格特征,都是美丽的化身,正义的代名词,殊不知英雄也有“狗熊”的时候。
荷尔德林曾言,人应该诗意地栖息在生活中。每个人都是诗人,每个人都曾做过成为英雄的美好幻梦。但是按照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电影的思路,英雄只能活在王国维先生三境界的第一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那种曲高和寡,真有如“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的无奈与寂寞。到了80年代第五代中国导演开始,英雄情结开始幻化成一种寓言,不论是陈凯歌的《黄土地》、《孩子王》深沉的现代对传统秩序的质询,还是田壮壮的《盗马贼》和张艺谋的《红高粱》厚重的民间对上层建筑的颠覆,他们所有定格于荧幕上的动作都是一个“在路上”的奔跑姿态。他在寻觅英雄灵魂归栖,在奔向理想中的天堂,但最终依然不出离于王国维先生的第二个境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当我们转身背离宏大的叙事话语去寻找英雄,突然发现“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英雄不在峰巅也不在谷底,他不是“云深不知处”,而是“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回归自然”的英雄少了精英气,多了烟火气,而这也正拉近了与民众的距离。在冯氏贺岁片中所有的人物脱离不了一个“小”字:小善良、小恩爱、小谎言。但“小”并不意味着没有“大”哲学。这些人来自民间,纯属草根,没有太高深的文化背景,却能敏锐地“把出”刚刚过去这一年中国人群体的脉搏,并开列一剂剂方药。如1997年《甲方乙方》中梦想与现实的转换;1998年《不见不散》中活着与死去的辩证;1999年《没完没了》中金钱与爱情的取舍;2002年《大腕》中荒诞与严肃的悖论;2003年《手机》中真实与欺骗的纠缠;2004年《天下无贼》中正义与邪恶的论战;2007年《集结号》中荣誉与尊严的置换;2008年《非诚勿扰》中戏谑与真诚的邂逅。小人物都能对症下药,如《甲方乙方》、《没完没了》是一剂“文火慢炖”的中药,细心调养力保实效。
姚远一边给巴顿往下扒做戏的军服,一边告诫他:
过过瘾就行了,和平年代真巴顿也得老老实实在家待着,撒野警察照样抓他。(《甲方乙方》)
刘元告诉挣钱不要命的女友李清:
我不像你似的挣钱没够,我觉得享受生活的每一分钟是最重要的。这才是十年美国生活的最大收获。(《不见不散》)
露茜与尤优看到彪哥沉痛悼念泰勒,说:
“他和泰勒的感情好像比我还深呢?”“废话我给钱了。”(《大腕》)
费墨告诫严守一:
“手机连着你的嘴,嘴巴连着你的心,你拿起手机就言不由衷啊。你们这些手机有好多不可告人的东西。”“手机是手雷。”(《手机》)
经常有人质问,为什么冯小刚能开创中国电影的贺岁市场并引领着它走过了10年风雨?答案不言而喻。拒绝宏大,如同卸下了千斤枷锁,使得冯氏贺岁片无需为伦理服务(如三四十年代的伦理电影),无需为政治服务(如抗战电影),无须为意识形态服务(如改革主旋律电影),在商业化和艺术化的制衡中从容地服务于大众,既哗众又取宠,虽献媚但不谄媚,“鱼和熊掌,二者得兼”。
三、追求残缺
老子曾言:“大成若缺。”(四十五章)又言:“道冲而用之或不盈”,(第四章)“洼则盈”。(二十二章)他认为万事应该讲究盈缺之道,和谐之理。“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谿”(二十八章)[5]。故欲致其圆,必由其缺;欲达其全,必由其断,“宁缺毋滥”之理便在其中。这种圆与缺的辩证在中国电影史中也无时无刻不存在着。成长于百年动荡的历史背景之中,前后六代中国电影导演都经历了剧烈的身心冲击和思想裂变。不论是屈从于特定时代主旋律还是变相游走在历史罅隙之间,每个导演都在建构美丽的幻梦,但梦终究是要醒的。与其害怕美梦不成真,索性不做梦。如果我们放逐高蹈的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笃定残缺,质疑完美,便会发现镜头具有无限延展的空间,也留给观众无穷言说的可能。比如战争题材的代表作《英雄儿女》,王成的形象完美无瑕,高大无比,使得观众对其仅能褒扬而无有针砭或质疑的可能。“人无完人”,一个人如果太完美,则失真至极。这种塑造人物求全求圆的现象,在任何一代电影导演的镜头中都有投影。如《啼笑姻缘》中的情定终身,《马路天使》中的纯真性灵,《青春之歌》中的大义凌然,《城南旧事》中的童贞谐趣,《荆轲刺秦王》中的重情重义,《洗澡》中的痴迷固守,每一代导演都把他们心中美好的幻梦投影在电影镜头的某一个角落,使得导演把这些完美的生命作为自己艺术的栖息地,蜷缩于此,就如同朱湘的诗,“我情愿拿海阔天空扔掉/只要你肯给我间小房——/像仁子蹲在果核的中央,/让我来躲避外界的强暴”。这样的躲避是固守精神家园的最后方式。但如果走出圈地,以接纳异己之胸怀投身社会洪流中,既任运随缘又不随波逐流,也不可不算是一种保持艺术品性的行之有效的方式。冯小刚导演便是深陷世俗泥淖且怡然自乐、以自我解嘲的方式行走江湖的得道之人。当我们将传统的仰视英雄的眼光收回,以平行的视角来审视冯氏贺岁片的草根英雄时,便会发现他们跟俗人并无二致,甚至有时比俗人还要粗俗,但粗俗并不庸俗,这便是残缺的妙处。
1.残缺之一——虚实相生
严沧浪在《沧浪诗话》中曾提到有关虚实相生的经典论述:“……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像,言有尽而意无穷……”[6]冯小刚非常善于在有限的镜头里无限拓展言外之意,使得欣赏之余产生“景有限而意无穷”之感。冯氏贺岁片往往以做梦开头,以解梦结束。如白日梦(《甲方乙方》)、电影梦(《大腕》、《不见不散》)、少年梦(《手机》)、战争梦(《集结号》)。而导演表达意图的点睛之笔就在这解梦的一瞬之间。电影《手机》中,少年时候的严守一通过电话传得最远的一个声音是“牛三斤,你的媳妇叫吕桂花,吕桂花让问一问,最近你还回来吗?”并从此走上以说话混饭吃的主持行业,一鸣惊人;但最终也是因为话的言不由衷而葬送了自己的前途。影片的最后,同样的声音穿透历史的围墙再次回响,由此衍生出无限思索的空间。梦境是虚幻的,所有的美好回忆无非是自我安慰;生活是实的,每个人生故事都有一个缺憾的尾巴才楚楚动人。
2.残缺之二——喻庄于谐
冯氏贺岁片的语言往往会成为该年流行语。例如《天下无贼》中“黎叔很生气,后果很严重”;“IC、IP、IQ卡,通通告诉我密码。”《大腕》中“什么叫成功人士?成功人士就是买什么东西都买最贵的,不买最好的。我们做房地产的口号是:‘不求最好,但求最贵’”。这是独具特色的冯氏语言,在嬉笑怒骂之间调侃了社会上严肃的命题。特别像《集结号》中连长谷子地,他因指导员牺牲,一气之下枪杀俘虏,哄抢衣服,被记大过一次,禁闭三天。可依然不思悔悟,说“好容易摸到炕沿,就差脱裤子了,吃饭着什么急。”王金存冲锋的时候“衰”了,谷子地没有摆出一副革命英雄的架势批评嘲讽,反而说“就是神仙也得衰啊”。冯小刚经常用一种故作庄严的姿态把小人物当大人物来看,用通俗的语言来写高雅。这种反常态的目光,内敛而幽默的语言让人物外在的语言与内在的观点、事情的表象与真相构成悖论结构。使人物在粗俗的语言游戏遮荫中若隐若现地露出崇高的本真性情。一旦观众参悟出此种“真”便会为之动容,在嬉笑中感到惊悸。他的影片中每一个人物都不完美,但是在观众的心目中都是完美的身影,这个从残缺到完美的转换需要我们自己去完成。
2008年的岁末,冯小刚携着他的贺岁影片《非诚勿扰》如期而至。走过了10年的贺岁路,或者再走10年的贺岁路,冯小刚都依然如《甲方乙方》中的姚远自我介绍那样。1997年,中国贺岁电影开始了它的试营业,经营了10年,当时的姚远在10年后的秦奋看来似乎已不再“遥远”:
我梦想有一天,有一样东西可以解决所有的分歧,大地鲜花常开,孩子们重展笑颜。21世纪什么最贵?和谐……
“英雄不问出处”,生于斯并老于斯是人命定的曲线,不管他是英雄还是凡人。只是在从摇篮到坟墓的旅途中,冯氏贺岁片让我们在每年的岁末看到一条以真情真意划出的最动情的曲线,随着新年的雪花一起消融在岁月的长河之中。
标签:冯小刚论文; 中国电影论文; 英雄时代论文; 不见不散论文; 手机论文; 天下无贼论文; 大腕论文; 电影节论文; 集结号论文; 甲方乙方论文; 没完没了论文; 喜剧片论文; 爱情电影论文; 剧情片论文; 战争片论文; 综艺节目论文; 中国电视剧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