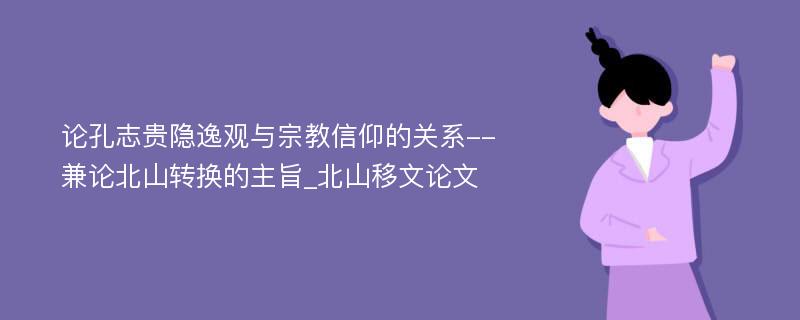
论孔稚珪的隐逸观念和宗教信仰的关系——兼论《北山移文》的主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隐逸论文,主旨论文,宗教信仰论文,北山论文,观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孔稚珪《北山移文》嘲讽士人周顒的隐仕无常:先是隐居于钟山草堂,然而征召甫至便欣然出山,职满还京时又企图再访北山隐舍。《北山移文》指出周顒亦官亦隐的实质是缨情荣爵而非志在山林,这一观点,显然与当时盛行的朝隐风尚迥异其趣,体现出对出处同归的玄学思想的批判,突出了隐逸作为士人节操的道德意义。当我们分析孔稚珪在佛道论争中对家族传统信仰的态度时,便能进一步看出孔稚珪对士人节操的追求和对传统儒学观念的执著,孔稚珪的隐逸观念与其宗教信仰有着人格和学理上的一致性。因此《北山移文》并非毫无寄托的调笑戏谑之文。
一、孔稚珪《北山移文》中的隐逸观念
1.《北山移文》与周顒仕宦经历的关系
《文选》吕向注对《北山移文》的本事有以下说明:“钟山在都北。其先周彦伦隐于此山,后应诏出为海盐县令,欲却过此山。孔生乃假山灵之意移之,使不许得至,故云《北山移文》。”吕向注所陈述的周顒事迹,实际上并不符合事实。其一,据《南齐书》、《南史》,周顒从未出任过海盐令[1](PP178-185),其二,吕向注认为周顒隐而复出,而《南齐书》本传曰:“于钟山立隐舍,休沐则归之。”可见隐舍是周顒在任职于京城期间建筑的。张云璈《选学胶言》也认为草堂是周顒“官国子博士、著作郎时,于钟山筑隐舍,休沐则归之,未尝有隐而复出之事”[2]。
正因如此,有学者提出了孔稚珪的《北山移文》“只是文人……对朋友开开玩笑、谑而不虐的文章”[3](P82),并无严肃的思想寄托的看法。笔者认为,《北山移文》与周顒的实际仕宦经历确实不完全符合,但是进一步寻绎文意可知,《北山移文》中促使“草堂之灵”对“周子”发出移文的契机,是周子欣然出山之后、任职期满返京时又打算再过钟山。周子离开草堂后并不是一去不返,而是时作归来之态,这种态度就很接近史书中周顒在仕宦的闲暇归往隐舍的记载。《北山移文》所要批判的,正是周顒亦官亦隐的生活方式。在朝隐的社会风尚大行其道的南朝,孔稚珪的隐逸观念,显然极为独特。
2.孔氏隐逸观念的道德内涵
江左五代,作为名士风流的重要标志、与玄学清谈同时盛行的,是士人的希企隐逸之风。[4](PP188-210)而名教与自然合一的玄学理论的兴起,使得隐逸一事完全打破了在朝在野的界限,士人只要澄怀无欲,在行迹上则既可入仕,亦可隐处。于是隐逸志趣与现实荣利的矛盾涣然冰释。此时隐士之不尚峻节成为社会认可甚至称道的行为。从隐逸的初始意义来看,避世离人、不食朝禄是隐士应该保持的节操,而晋宋之际最为著名的隐士如戴顒、宗炳、周续之、雷次宗等人却广交达官贵人并受其丰厚馈赠。随着“隐节”的失落,隐逸行为所蕴含的傲视王侯、淡泊名利的道德内涵也丧失殆尽。在朝士人则大倡亦吏亦隐之风。构筑郊居以养情志,是士人实现隐逸志趣的方式之一。当时包括周顒在内的许多士人都建有郊居、隐舍,居官得暇,便去小住几日。隐士不尚节操,居官而有隐舍,这两种隐逸形态都淡化了隐逸的道德意味,而《北山移文》中“夫以耿介拔俗之标,潇洒出尘之想。度白雪以方洁,干青云而直上”等文,却突出隐逸作为士人节操的道德内涵,“岂其终始参差,苍黄反复……乍回迹以心染,或先贞而后黩”数语,表明了对变节改操行为的愤慨。
孔稚珪隐逸观念的独特之处,首先表现在他对隐逸的道德内涵即“隐节”的强调。这与孔稚珪师从的江东士人对他的影响有关。与孔稚珪同族别宗的孔祐、祐子道徽、道徽侄子总以及孔稚珪的道法师傅褚伯玉,都以隐居不仕、终始无亏著称于世(《南史·隐逸传》)。孔稚珪的友人、吴郡顾欢丧母后隐居剡县天台山,亦固守“志尽幽深,无与荣势”的节操。
3.孔氏隐逸思想与玄学批判
南朝隐逸风尚的玄学基础是名教与自然合一思想,因此,孔稚珪对亦官亦隐士风的批判,便隐含着对“名教与自然合一”的玄学思想的否定。在此,有必要首先考察一下其中蕴含的玄学思维方式。在名教与自然合一这一哲学命题的形成过程中,玄学家们采用了老庄的“得意忘言”、“动静一如”、名辩的“辩同辩异”等多种思维方式加以阐述论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辩同辩异”的思维方式。在“得意忘言”的思维方式下,自然与名教之间存在着本同末异的关系。而在“辩同辩异”的思维模式下,名教与自然、仕与隐原本就是一回事。史载王衍、阮修对话曰:“阮宣子有令闻,太尉王夷甫见而问曰:‘老庄与圣教同异?’对曰:‘将无同。’太尉善其言,辟之为掾。世谓‘三语掾’。”
这一记载提示了名教自然合一理论与名辩“辩同辩异”思维的关系。《晋书》卷九四《鲁胜传》载其《墨辩叙》曰:“名者所以别同异,明是非……是有不是,可有不可,是名两可。同而有异,异而有同,是之谓辩同异。至同无不同,至异无不异,是谓辩同辩异。”可见“辩同辩异”思维的实质是将相对性绝对化,走向齐同是非。清谈名士正是通过反复辨析名教自然的同中有异、异中有同,认识到同、异的相对性,从而由“辩同异”走向“辩同辩异”,得出了圣教与老庄至同无不同的结论。
郭象注《庄子·逍遥游》对此有更明确的论述:“夫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世岂识之哉!徒见其戴黄屋、佩玉玺,便谓足以缨绂其心矣。见其历山川、同民事,便谓足以憔悴其神矣,岂知至至者之不亏哉!”这段论述的前半部分“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仍然不脱“得意忘言”的思维模式,然而后半部分以为圣人即便居山林之中也不会憔悴其神,则意味着圣人之隐居山泽,也与身在庙堂无异。在此,山林与庙堂都在得到了肯定的同时又被否定了,于是名教与自然不复有心迹本末之分,从而达到了真正的“同”。“岂知至至者之不亏哉!”一语,很明显地带有受名辩“至同”、“至异”概念影响的痕迹。
由于资料的限制,孔稚珪本人批判玄学的理论已不可详考。我们可以通过考察孔稚珪的友人顾欢的相关言论,追溯孔稚珪隐逸观念的学术背景。关于孔稚珪与顾欢的交游,史书中记有“会稽孔稚珪尝登岭寻欢,共谈四本”(《南史·顾欢传》)一事。据《南齐书》本传,顾欢为吴郡盐官人,博学能文,曾师从豫章雷次宗,研习玄儒。他还是著名道士,曾作《夷夏论》以尊道抑佛(说详下)。顾欢有研习玄儒的学术经历,他的学术倾向却是崇儒抑玄。他曾反思玄学的重要命题“四本论”曰:“兰石危而密,宣国安而疏,士季似而非,公深谬而是。总而言之,其失则同,曲而辩之,其途则异。何者?同昧其本而竞谈其末,犹未识辰纬而意断南北。群迷暗争,失得无准,情长则申,意短则屈。所以四本并通,莫能相塞,夫中理唯一,岂容有二?四本无正,失中故也。”魏晋士人对才性关系有同异离合四种看法。“四本论”的具体内容,今已不得而知,仅就思维方式而言,才性同异合离四论的并行不悖,是魏晋玄学吸收名辩的“辩同辩异”的思维方式的结果。顾欢认为:“群迷暗争,失得无准……所以四本并同,莫能相塞。”这就揭示出“四本论”的根源在于齐同是非的思想方法。他的“夫中理唯一,岂容有二?四本无正,失中故也”之说,阐明了他反对同遣是非、要求重建是非标准的观点,这就完全否定了“辩同辩异”的思维方式。如前所述,“辩同辩异”是名教与自然合一思想的思想基础,因此,顾欢反对才性四本并存,便从根本上否定了出处同归这一命题的方法论根基。顾欢著《三名论》以批驳《四本论》。与顾欢共谈四本的孔稚珪,必然在顾欢《三名论》的影响下,否定名教与自然合一的玄学理论及其中的“辩同辩异”思维。这一独特的学术倾向,构成了孔氏批判“吏隐”士风的理论依据。
二、孔稚珪对家族传统信仰的坚持
在孔稚珪的隐逸观念中,崇尚隐士节操与批判自然与名教合一的玄学,是在逻辑上互为因果、密切相关的两方面。他本人对士人节操是如何躬行践履的、对包括玄学在内的主流学术思潮持何种态度呢?永明末年,在孔稚珪写作《北山移文》之后,竟陵王萧子良劝诲孔稚珪奉佛、孔氏坚持其家传道教信仰一事,为我们提供了考察这一问题的良机。
1.崇道抑佛与人格节操
南齐文惠太子、竟陵王萧子良均笃信佛教,广泛召集宾客,大力鼓吹佛理。萧子良为了敦促士人回心奉佛,甚至以官位荣势相利诱。如范缜坚持其神灭无佛之论,萧子良令王融转告曰:“以卿之大美,何患不至中书郎,而故乖剌至此,可便毁弃之。”(《南史·范缜传》)正因如此,西邸宾客中公开表示反对佛教并且始终不改其志者,范缜之外寥寥无几。相反,像沈约那样出身于天师道世家、却在宋齐之际顿改旧志者,比比皆是。孔稚珪的选择却与时尚有别。在致萧子良的信中,孔稚珪首先表达了自己不能舍弃家传道教信仰的志向、关于佛教义理是否有悖于儒家仁义孝悌的疑惑。萧子良答书则肯定了佛教思想与儒家道德的一致性,在信末有“栖心入信者,前良不无此志……君若以德越往贤,圣逾前修,智超群类,位极人贵者,自可逍遥世表,以道化物,高尚其怀,无求自足而退仿前良”等语,又暗示了孔稚珪若继续执迷不悟,则很可能为此付出仕途偃蹇的代价。面对萧子良的循循善诱,孔稚珪在答书中仍然反复表示,他不忍背弃家传的道教信仰:“门业有本,不忍一日顿弃。心世有源,不欲终朝悔遁。”但另一方面,萧子良的佛教并不违背儒家的说法,使他对佛教的态度不无改变。他表示愿意依照其表兄、吴郡张融的“通源之论”,并尊佛道二教。
值得探究的是张融通源之论的实质。宋齐两世,佛道二教的论争十分激烈。宋末元徽中,顾欢著《夷夏论》,表面上会同二教,实质上崇道抑佛。其说既出,袁粲等奉佛名士纷纷著文反驳。南齐永明末年,张融又在《门律》中提出了佛道“通源之论”,其说云:“道也与佛,逗极无二,寂然不动,致本则同。感而遂通,达迹成异。”(《弘明集》卷六)。“通源之论”会通二教,似乎于佛道不偏不倚。然而奉佛士人周顒对此却大为不满,他追问道:“所谓逗极无二者,为逗极于虚无,当无二于法性耶?将二途之外更有异本?”他所关心的是:佛道通源,是同归于佛,还是本同于道?张融的回答是:“法性虽以即色图空,虚无诚乃有外张义。……所以苦下之翁且藏即色,顺其所有不震其情,尊其所无渐情其顺。”(《重与周书并答所问》,《弘明集》卷六)“苦下之翁且藏即色”一句,认为老子思想中原本包含了即色之义,只是为了教化的权便,蕴而不发而已,这便透露了张融以道统佛的用意。“通源之论”的实质是在会通二教的幌子下,张大其崇道抑佛之论。孔稚珪不仅吸收了“通源之论”,还对佛道二教同符的理论做了进一步的阐述,这些阐述同样透露了他崇道抑佛的倾向。道家在终极本体观念上与佛教的异同,是张融、周顒的论争中悬而未决的问题。孔稚珪承认“道之论极,极在诸天”,但又指出这不过是道家用以教化的权便方法:“然寻道家此教,指设机权,其犹仲尼外典,极唯天地,盖起百姓所见二仪而已。”继而他又引《老子》“有物混成,先天地生”一说,认为这正说明了道家对终极本体的认识与佛教无异:“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已是道在天外,稍不以天为道也……佛竟不止于罗汉,道亦于天未息。甫信道之所道,定与佛道通源矣。”姑且不论孔稚珪的理论是否真正把握了佛道二教的宗旨,耐人寻味的是孔稚珪在这封表达其并尊释老的答书中,反复论证的却是道家之“论极不止于天”的问题,这充分反映出他对于道教徘徊不已的心态。
借助于“通源之论”这一思想资源,孔稚珪保持了家传的道教信仰。在荣利与志向的冲突面前,孔稚珪尽其所能地守住了自己的宗教意志和家族传统,显示了他的人格节操。值得注意的是,张融之创立“通源之论”,是受到了孔氏家学的启发。孔稚珪自云:“民门昔尝明一同之义,经以此训张融,融乃著通源之论。”(《弘明集》卷一一)。此外,“通源之论”与顾欢《夷夏论》也是一脉相承的。在会稽孔氏、吴郡张氏、顾氏之间存在着一个江东旧族的文化圈子,他们以尊道抑佛、崇尚儒学(包括士节等儒家道德)为共同的文化特征。
2.佛道信仰之争与新旧学术之别
宋齐两世是否弃道从佛,还折射着士人对玄学思潮的态度。佛教成为门阀社会的主流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佛教与老庄玄学的契合。以《般若学》的流传为例,汤用彤指出“夫《般若》理趣,同符《老》《庄》。而名僧风格,酷肖清流,宜佛教玄风,大振于华夏也”[5](P108)。事实上随着佛玄进一步交融,佛教已自然成为玄学的一部分。与宗教信仰中的佛道之争相对应的,是学术思想上的儒学、黄老等旧学与玄学新说的对立。首先,佛道论辩与儒玄对立密不可分。顾欢作《夷夏论》,指出尊道抑佛的根据是夷夏之辩:“佛教齐乎达化,而有夷夏之别……舍华效夷,义将安取。”(《南齐书》本传)华夷之别本是儒家传统观念。而在玄学思潮的冲击下,忠义士节、夷夏之辩等旧儒学,早已为门阀社会的主流文化所忽略。顾欢之崇道排佛,与其崇儒抑玄有着很大的关系。
其次,以黄老道家思想为基础的道教,在学理上亦与佛教背后的玄学迥异其趣。周顒批驳通源之论,指出“知有知无吾许其道家。惟非有非无之一地,道言不及耳,非有非无三宗所蕴”。显然佛教的“非有非无”,不同于黄老道家的“知有知无”,而与玄学齐同是非的旨趣颇为接近。周顒之奉佛,与其学术上的尚玄是密切关联的。
因此,孔稚珪之坚持家传道教信仰,还反映了他对玄学等主流文化的疏离。孔稚珪在家族信仰问题上表现出的士人节操和崇儒抑玄,与《北山移文》中的隐逸观念极为契合。《北山移文》确实寄托了他的人格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