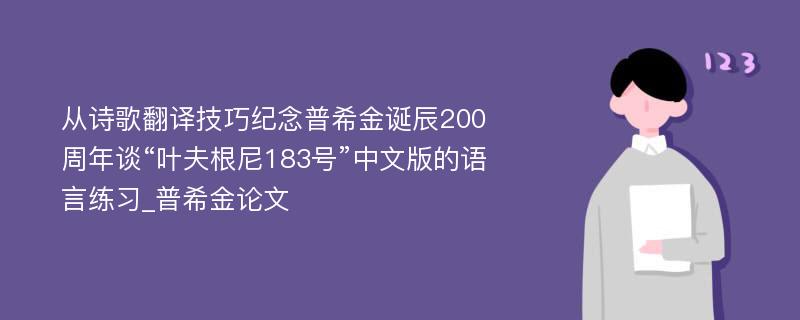
从译诗技巧的角度探讨《叶甫盖尼#183;奥涅金》中译本的语言锤炼——为纪念普希金诞辰200周年而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普希金论文,中译本论文,诞辰论文,而作论文,角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普希金的代表作《叶甫盖尼·奥涅金》(以下简称《E·O》)迄今为止我国已出版七个中文译本。纵观前译,翻译的总体水平在不断提高,但若从世界文学名著的高度来要求,前译本无论在韵律处理上,还是在译文语言的锤炼上,真正做到内容与形式的完善统一,还有不小的距离。我们总结和发扬前译的成就,承认并披露前译的缺陷与不足,目的只有一个:让后译者取长补短,接过前译的接力棒继续跑下去,用集体的智慧和力量,将一部接近完善的世界名著定本早日奉献给中国的广大读者。
笔者在另一篇论文中曾经谈到过韵律和节奏对于诗歌的重要性。如果把韵律和节奏比做诗歌的呼吸和脉搏,那么优美的语言便是诗歌的载体和灵魂。诗的语言被普希金称之为“神的语言”(《E·O》八章5 节),他认为诗和散文有严格的区分,恰似岩石和浪花,冰与火之迥然不同一样(《E·O》二章13节)。他在《E·O》第三章13节中还说,“我宁愿降低身份,去写朴素的散文。”可见诗的语言不是普普通通的语言,它简洁、凝炼、含蓄、隽永,它需要经过诗人的神笔加以“千锤百炼”。
诗歌翻译同样要求译者在语言锤炼上下功夫。难怪有人提出:诗译者最好他本人就是一位诗人。往往相同的思想、相同的意思,在不同译者的笔下,便写出各不相同的译文来,从而产生各不相的艺术效果。
Я зто потому пишу,
Что уж давно не грешу。
(一章29节)。
译文A 老实说,我所以写这几行,
因为我早已不再荒唐。
译文B 我所以在这里要这样地写,
因为我早已不再犯这种罪孽。
译文C 我为什么要写下这些话,
因为我早就不做缺德的事。
三种译文意思完全一样,但饮文A诗味浓郁, 其余两种译文读起来淡如白水。
在《E·O》中常有妙语警句出现,翻译这些妙语警句时,应努力做到用词洗炼、含蓄、有韵味。
Прнвычка свыше нам лана;
Замена счастцю оца
(二章31节)
译文A 上帝本来没给人幸福,
“习惯”就是他赏赐的礼物。
译文B 上天让我们习惯于各种事物,
就是用它来代替幸福。
两种译文孰优熟劣,勿须评论,读者自明。
世上所有的译者恐怕都会宣称自己是忠于原著的。但是,仅仅在字面上保持一致,并不就是忠于原著。译诗最忌一字不差地逐字对译,重要的是看原诗的主要实质、诗的意境、形象等等是否得到很好的安排和表达。前苏联诗人兼诗译家马尔夏克关于如何译诗有过一段精辟的论述,他说:“……逐字逐句地译诗是不行的。我们对译诗的要求是严格的,但我们要求的准确,是指把诗人真实的思想、感情和诗的内容传达出来。有时逐字准确翻译的结果并不准确。……译诗不仅要注意意思,而且要把旋律和风格表现出来,……要紧的,是把原诗的主要实质传达出来。……常常是这样:最大胆的,往往就是最真实的。……好的译诗中,应该是既看得见原诗人的风格,也看得出译者的特点。”(注:杜运燮:《穆旦著译的背后》。)
在结束《E·O》全书的最后一个诗节(八章51节)里,普希金满含激情,用抒情插笔的形式,表达了他对昔日友人的怀念和对人世沧桑的感喟。他看到过去的好友有的被沙皇杀害,有的流放到远方,《奥涅金》写完,旧人却已星散,于是发出这样的感慨:
О,много,много рок отъял!
这一句诗蕴含了诗人多少伤心和惋惜之情!有人译成:
噢!多少东西都被命运剥夺!
也有人译成:
噢!这样的人有多少被命运糟蹋!
这里被糟蹋、被戕害的是人,是社会精英,因此,第一种译文译成“东西”显然不妥。第二种译文无疑是正确的,然而文字不够简洁凝炼。请欣赏另外两种译文:
呵,命运淘尽了多少浪沙!
啊,命运摧残了几多春光!
这两种译文虽然在文字上与原文并不一致,然而所表达的意思却和原文一样,收到了“异曲同工”的效果。这两份译文的特点是:
第一,文字简炼,节奏感鲜明;
第二,生动、形象、富有感染力。换句话说,它们象诗,读起来有诗味。
由于汉俄两种语言在表达习惯上存在很大差异,因此在将俄诗译成汉语时,需要做一些技术上的处理,如将长句破译成数个小短句,或将叙述的顺序作适当调整;有时为了使原作的形象和实质更准确、更鲜明地表达出来,不得不加一些字或减掉一些字,或者如刚刚引过的那句诗那样,另外营造形象,等等。
请欣赏下面一段诗:
从前,清晨的微风总是
吹动着这简朴的坟莹上面
挂在松树低垂的枝头上的
一个神秘莫测的花圈。
(七章7节)
将四行诗译成一个特长的汉语句子,读起来好费劲,即使在散文中,这样的译文也很难称得上是优美的,更不必说在普希金的诗中了。请对比下面译文:
在这朴素的坟墓上面,
松树垂下了它的枝叶,
常常,树枝上挂着花圈,
在晨风里轻轻地摇曳。
这样译诗,不仅脉络清晰,语意畅达,而且饶有诗意:“在晨风里轻轻摇曳。”破成数个小句之后,读起来节奏鲜明,音韵和谐,同原诗一样押的是abab交叉韵。本来原文在“花圈”之前有一个形容词таинствеиный,译者略去未译,因为若在“花圈”之前加上个“神秘莫测的”作修饰语,会破坏译诗的和谐与匀称。对于这种处理方法,译者查良铮先生有他一整套的译诗理论作为依据。他说,“译诗必须有个总体观点,有了这个总体观点,译者就会看到,并不是诗中的每一字、每一词、每一句都有同等的重要性;对于那些原诗中不太重要的字、词或意思,为了便于突现形象和安排形式,可以转移和省略……这样做要忍受局部的牺牲。但虽说牺牲,也同时有所补偿,那就是使原诗中重要的意思和形象变得更鲜明了,或者说形式更美了一些。”(注:杜运燮:《穆旦著译的背后》。)
当该加字的时候,查先生会巧妙地加字:
И так они старели оба,
И отворилисъ наконец
Иеред Супругом дверъ гроба
И новый он приял венец
(Глава Ⅱ,36)
奔HTK〗就这样,两夫妻老了下来
日月荏苒,丈夫先临到大限,
墓门无情地为他打开,
他终于戴上冥冠,离开人间。
译者在第二行加了“日月荏苒”,一方面说明两夫妻很快便衰老下来;另一方面在形式安排上也更美了些,读起来跟第一行一样,有鲜明的抑扬顿挫节奏。尤其是第四行“离开人间”四个字加的十分精彩。大家知道,在俄语中主要信息往往先说出来,次要信息在后,而汉语恰好相反,主要信息常常放句子的末尾。加进去的四个字,从意义上说,是对“戴上冥冠”的一个补充说明,从修辞效果上看,加进去的四个字使整段诗读起来意满气足。对比另一种译文,就给人一种言犹未尽的感觉:
(死神)为他启开了坟墓的大门,
于是他戴上了另一个花冠。
“戴上另一个花冠”到哪儿去?做什么去?语意并不清晰。
为了说明加字的妙用,在这里再补充一译例。众所周知,普希金写了大量的情诗,而讴歌女人的秀足是普希金情诗的一个内容。
Дианы грудъ,ланиты флоры
Прелестны,Милые друзья!
Однако ножка Терпсихоры
Прелестней чем-то для меня
Она,пророчествуя взгляду
Неоценимую награду,
Влечёт условною красой
Желаний своевольный рой
Люблю её,мой друг Эльвина,
Под длинной скатертъю столов,
Весной на мураве лугов,
Зимой на чугуне камина,
На зеркальном паркете зал,
У моря на граните скал.
译文A
花神的面颊,狄安娜的胸脯
亲爱的读者,自然够美妙,
但是舞蹈女神的一双秀足
却更能让我神魂颠倒。
它给眼睛打开喜悦的门,
任你去遐想,妙趣无穷,
它的美不可捉摸而蕴藉,
不知引动了多少痴情。
呵,你那一双脚,爱丽温娜!
或者踏着春日的草原,
或者露在桌边的台巾下,
在海岸的悬崖,冬日的炉边,
或者从光滑的大厅掠过,
它多么激动我的情波!
译文B
亲爱的朋友!福罗拉的面容,
狄安娜的酥胸,实在美妙,
可是,忒耳西科瑞的脚踵
更有点儿让我神魂颠倒。
它,能够给我的目光
送来一种无价的报偿,
以它合乎规范的美丽
勾起我心头蜂拥的希冀。
我爱它,我的朋友爱尔维纳,
春天,它踏上绿色如茵的草原,
冬天,它贴着壁炉温热的铁板,
席间,它放在餐桌的长台布下,
它踏着明亮的地板步入大厅,
它踩着花岗石岸,伫立在海滨。
这一节诗描写的是舞蹈女神忒尔西科瑞的一双诱人的秀足。这里引的两份译文,代表两种不同的翻译风格。译文B比较忠实于原文, 一字、一句都不肯舍弃,叙述顺序也跟原文一样,然而比起译文A来, 应该说译文语言有些拘谨、生涩:
合乎规范的美丽——不可捉摸而蕴藉的美
勾起心头蜂拥的希冀——引动多少痴情
其余各行的诗句也不如译文A简洁、洗炼。尤其是, 不该为了押韵而将ножка(秀足)硬译为“脚踵”。
原文从10到14行诗直译过来是:
在餐桌长长的台巾下面
在春天草地的嫩草上面
冬天在壁炉的铁板上,
在大厅如镜般光滑的镶木地板上,
在海边悬崖的花岗石上
译文A用简洁、洗炼的语言将这些诗行重新加以组合:
“跟着春日的草原”(将“嫩草”略去未译),
“冬日的炉边”(将“铁板”省去),
“海岸的悬崖”(将“花岗石上”省去),
“光滑的大厅”(将“镶木地板”省去),
译者在省掉对表达诗的实质内容不关紧要的字、词的同时,用“踏着”,“露在”,“掠过”等加以巧妙穿插,使整段诗形成一个完整的画面,尤其是将原文的12、14两行合并成一行译出,而在文章的末尾加进一个感叹句:“它多么激动我的情波!”
这一句加的相当妙:虽然这行诗在原文表层结构里找不到,但是在原诗的字里行间却包含着:加进这一行诗既可与译文A的第8行“不知引动了多少痴情”相呼应,又可以使整节诗意满气足,从而将普希金对舞蹈女神的秀足心醉神迷之情渲染得淋漓尽致。
也许有人要问:是不是译者在翻译中可以随意加字,任意发挥呢?当然不是。翻译不同于创作,译者不可以离开原著而随意发挥。加字有两个条件,一是所加的内容必须是原著深层语意中所包含的,而不是译者强加的或臆造的;二是加字以后更好地传达了原诗的内容和实质,而不是相反。两个条件缺一不可。
鲁迅先生说过:“凡是翻译,必兼顾着两面,一当然力求易解,一则保持着原作的丰姿。”
俄国语言大师契诃夫说过:“语言是风格的基础,是风格的灵魂,是整个风格棋盘上的将帅。”作品的语言风格译出来了,整个作品的艺术特色、它的丰姿,也就再现了。由于原著的语言风格要靠译者的笔来传达,因此,译者的文学修养和中外文语言水平,以及驾驭诗歌语言的功力如何,对于译文的质量至关重要。一部翻译作品可以说是译者的文学修养和中外文水平最真实的答卷。
不同的作家语言风格自然不同,就是同一位作家,在不同的作品里,在一部作品的不同场合,其语言风格也不尽相同,在翻译时一定要认真阅读,仔细推敲,努力把握作品的褒贬雅俗,弄清作者的喜怒爱憎、用词习惯和特点,以及修辞上的种种细微变化,然后用等值的表达手段加以再现。
《E·O》既为长篇小说,自然会有情景描写。情景描写是为展示主题、塑造人物服务的,其重要作用不容忽视。通过景物描写和人物画像,使故事情节具体生动,使画面鲜明形象,使人物富有个性,给读者以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如临其境的感受。描写情节的语言应力求简洁、生动。请欣赏这一段情节描写:
В сей утомительной прогулке
Проходит час-другой,и вот
У Фаритонья в переулке
Возок пред домом у ворот
Остановился.К старой тетке
Четвертый год болъной в чахотке,
Они приехали теперь.
Им настежь отворяет дверь,
В очках,в изорванном кафтане,
С чулком в руке,седой калмык.
Встречает их в гостиной крик
Княжны,простертой на диване.
Старушки с плачем обнялись,
И восклинанья полились.
这次令人疲惫的旅行
又过两小时终于完成。
马车在哈里顿教堂旁
拐进一条狭窄的胡同,
在一家大门口停下来,
她们总算来到姨母家中。
开门的是一个卡尔梅克人,
白发苍苍,戴一副花镜,
穿着破袍子,手提着一只袜子。
客厅里郡主连声欢迎。
只见她躺在沙发上,
已经患了四年痨病。
两个老妇人抱在一起,
叹息不已,老泪纵横。
(七章 39—40节)
这一节主要描写的是达吉亚娜母女俩的马车进入莫斯科后,又沿着大街小巷,颠簸了一两个小时后,终于抵达姨妈家,以及两位老姊妹阔别多年后喜相逢的情景。所引译文叙述简洁、生动,又能抓住这段诗的特点:经过七天七夜的旅行,总算来到姨母家中。其它译本都没有强调这一点,而且有的译文语言显得重复拖沓:
这儿住着个年老的姨妈,
她们这次正是前来找她,
她在家里害痨病已经四年。
接下去,译文先点出“开门的是个卡尔梅克人”,然后再详细描写他的外表长相和动作状态。这样处理自然、得体,读起来又顺口,合乎汉语表达习惯。若换一种译法,效果就不一样:
一个白发苍苍,戴着眼镜,
穿着破衣衫,提着一只袜子的
卡尔梅克人过来给他们开了门。
在描写两个老姊妹喜相逢的情景时,译者未译成“看到他们,欢喜得连声叫喊”,也没译成“郡主惊喊一声,将她们迎进屋里”,只用“连声欢迎”四个字,便概括无余了。接下去,他未译成“两位老太太哭泣着紧紧地拥抱”,只说两个老妇人“抱在一起,”然后是“叹息不已,老泪纵横”,既简洁朴实,又生动感人,可以说是绘声、绘色、绘形、绘景。
尤其精彩的是,译本将“已经患了四年痨病”一句,从原文的第六行巧移至第十二行译出,跟在“只见她躺在沙发上”一句后面,以说明她没有走到门口迎接远方贵客的原因。从这里可以看出,译者对原著的理解的深度和善于处理译文的功力和匠心。
人的心理活动是通过语言来表达的,因此刻画好人物的关键在于写好人物的语言。翻译人物对白时,译文语言要口语化,要切合人物的身份,要体现人物的个性特点。成年人和小孩子说话的口气有别;普通农妇之间的聊天跟上层贵族太太小姐之间的交谈,又会有所不同。请欣赏下面一段人物对白:
译文A“别是爱上了谁?”“有谁呢?
布扬诺夫求婚,她一口回绝,
佩图什科夫也是一样。有个骠骑兵
贝赫金在我家住过一个时节,
他可真迷上了达妮亚,
殷勤献媚,竭力巴结,
我寻思,这回该妥了吧?
哪有的事!又吹咧!”
“她婶,那有什么难的?
到莫斯科去!那里有的是空缺,
那可是待嫁姑娘的集市。”
“唉!他大伯,没进项,去不起哪!”
“去一冬总好对付,
不什么,先从我这儿借。”
(七章 26节)
译文B“她是不是在恋爱?”“爱谁呢?
布雅诺夫求婚,一无所得。
伊凡·彼杜什科夫也遭到拒绝。
骠骠兵倍赫金来我家做客,
对达妮亚真是一见倾心,
向她献尽了多少殷勤!
我想:这下子也许成功了,
哪有这种事!结果还不行。”
“老太太,何必为这事苦恼?
莫斯科是少女云集的地方!
听说那里求婚的人真不少。”
“噢,我的老爷,收入有限啊。”
“绰绰有余了,在那儿过个冬天,
要不然,我借给你一点钱。”
译文A用通俗易懂的现代口语, 将前来串门的乡村女邻和地主太太之间的谈话译得亲切自然,生动逼真,其口吻可以说恰如其份。而译文B却充满书生气和学生腔:“是不是在恋爱”,“一无所得”, “遭到拒绝”,“也许成功了”,“结果还不行”“绰绰有余了,在那儿过个冬天”……
在小说《E·O》中普希金常常以书中一个抒情主人公的身份对周围的社会和各种文化现象做出评价,随时随地抒发自己的见解,倾吐自己的心怀,这就是《E·O》中别具一格的“抒情插笔”。翻译这些抒情插笔时,要注意把着眼点放在对诗人情绪的传达和感情的渲染上面,不仅要述意,而且要移情。
请欣赏这一段抒情插笔:
Придет ли час моей свободы?
Пора,пора! —взываю к ней;
Брожу над морем,жду ногоды,
Маню ветрила кораблей.
Под ризой бурь,с волнамн споря,
По вольному раснутью моря,
Когда ж начну я вольный брег?
Пора покинуть скучный брег
Мне неприязненной стихии
И средь полуденных зыбей,
Под небом Африки моей,
Вздыхать о сумрачной Росснн,
Где я страдал,где я любил,
Где сердие я нохоронил.
(一章50节)
可到了我的自由之时?
自由!自由!我不断向它呼唤;
我在海岸徘徊,等待天时,
我招呼每一只过往的船帆。
什么时候我才能获得自由,
逃上那茫茫无际的海路,
站在风暴里,和巨浪博斗?
去吧!离开这乏味的国度
和险恶的气候,我要浮过
南海的浪涛,在我的非洲的
赤热的天空下,想着俄国。
我将为它沉郁的土地叹息:
是在俄国,我爱过,痛苦过,
是在那儿,我的心早已埋去。
(一章 50节)
这段译文出自诗译家兼抒情诗人查良铮先生的手笔。译者以诗人的才情、抒情的笔调,将这段抒情插笔译得跟原著一样充满激情,生动感人。普希金当时遭受沙俄流放,暂住在里海边上的敖得萨;他受人监视,心情苦闷,一度产生过经由海路逃离俄国的念头。引诗一开头便提出:可到了我的自由之时?”接着诗人便急切地喊出:Пора!пора!(直译:到了!到了!)这充分表达了普希金对自由的渴望和自信。查译文把握住了诗人的情绪,用“可到了”三个字,将诗人渴望自由的急切心情准确地表达了出来。对比另一译文:
我那自由的时刻是否即将来临?
句子有些冗长,一冗长便显得苍白无力;听语气,对自由的到来似乎又不那么自信。
有人将原诗第8行照字面译成:“我该离开这寂寞的海岸了, ”而查先生却译成:
去吧!离开这乏味的国度。
这行诗读起来节奏分明,铿锵有力。原来前者只在述意,后者却重在移情:由于译者在“离开”前加了句“去吧!”,而将诗人决心逃离俄国,去寻求自由的心情刻画得入木三分。
诗的最后两行,查译文处理成两个排比句,读起来诗味浓郁,颇富感染力。
这一节诗查译文在文字处理上有许多独到之处:
1、第二行的两个Пора没有如某些译本那样译成“是时候了”,而译成“自由!自由!”,着重渲染了诗人对自由的渴望,同时也跟“不断向它呼唤”一句形成呼应之势。
2、第8行加了“去吧!”,第11行加了“想着俄国”,这些内容虽然在表层结构中没有,然而在深层语意中却已包含。加进去后各有其作用:“去吧!”加强了“离开俄国”的决心,增强了诗的节奏感和艺术感染力;“想着俄国”加进去后,一方面表明诗人即使离开俄国也会总惦记着她;另方面,第11行用了“俄国”,第12行的сумрачной Росснн就可以译为“沉郁的土地”,而不致犯重复的毛病。尤其高明的是,译者在“叹息”之后加了个冒号,以说明诗人何以要为俄国叹息:这里毕竟是他生长过,有过爱和恨的故土。
3、最后两行诗中原文以两个где开头, 查先生译为“是在俄国……是在那儿”而没有译成两个“在那里”,又一次显示出译者用词灵活、不落窠臼、追求变化的译风。
著名的学者王佐良教授一次在谈到查良铮先生译诗成就时,推崇他为近代译坛上与戴望舒齐名、最成功的诗译家。(注:马文通:《谈查良铮的诗歌翻译》。以上引文均参见《一个民族已经起来》,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通过多年的翻译实践,查先生总结出一整套自成体系的译诗原则。他常说:“考察一首诗,首先要看它把原作的形象或实质是否鲜明地传达了出来;其次,要看它被安排在什么形式中。”又说:“译一首诗,如果看不到它的主要实质,看不到整体,只斤斤计较于一字、一词,基至从头到尾一串字句的“妥贴”,那结果也不见得是正确的。”
可见,译诗要善于抓住诗的实质,同时又要经过自己的思考,找出既同原著等值,又合乎汉语表达习惯的表达方式。
请看这一段诗:
Ей нравится порядок стройный
Олигархических бесед,
И холод гордости спокойной,
И эта смесь чинов н лет.
译文A她欣赏名流们的清淡,
慢条斯理,语调平稳,
冷冰冰的从容傲岸,
显贵长者的盛气凌人。
译文B她喜欢权贵人士的倾谈
所表现的有条不紊的顺序,
喜欢那安然傲岸的冷淡
和这种官职与年令的混合体。
(八章7节)
普希金经常带领缪斯出席社交界的各种聚会。这一节诗写她(指缪斯)对上流社会某些权贵人物的评论意见。他们谈起话来慢条斯理,不痒不痛,从容中透出冰冷的傲气,好一副权贵和长者盛气凌人的面孔。译者A吃透了原意,抓住了诗的实质,通过自己的消化理解, 完全用自己的语汇、自己的表达方式,写出自己的诗文。其中“慢条斯理”,“语调平稳”,“从容傲岸”,“盛气凌人”等几个关键词语选得好,既简洁又形象。尤其是用“显贵”来译“чннов”,用“长者”来译“лет”,更是恰切,精当。至此,一个活脱脱的人物形象便栩栩如生地勾画了出来,使人读了如见其人,如闻其声。
而译文B虽然同原文一字一句都不差,连脚韵都跟原文完全一致, 然而读过之后,蚀没有给人留下清晰、深刻的印象,自然不会产生生动感人的艺术效果了。什么叫“有条不紊的谈话顺序”?什么叫“官职与年令的混合体”?由于译者没有抓住诗的实质,只好寻求字面上的对应,然而,诚如查良铮先生所言,即使从头到尾一串字句的“妥贴”,那结果也未必就是正确。
本文侧重于从译诗技巧的角度来探讨译诗的语言锤炼,至于有些《E·O》译文文白杂揉,文理不通的译例甚多,如“黑暗的幸福”,“透明的昏暗”,“单调而多彩”,“早市汹汹,噪音悦耳”,“欢乐嚷嚷,科学喧喧”等等,就不必在这里浪费笔墨了。
关于如何译诗,是一个颇值得探讨的大课题,而且各译家都坚守着自己的译诗原则,因而表现出自己所独有的不同译风。要求所有的译者都遵循一种模式不是明智之举,且有悖于“双百”方针。然而,一首诗、一部书译得好还是差,总还是有个客观标准的。笔者在这里阐述的只是个人的“一管之见”,难免出现厚此薄彼、评论失当之处,诚恳地欢迎专家学者和读者朋友不客气地提出批评与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