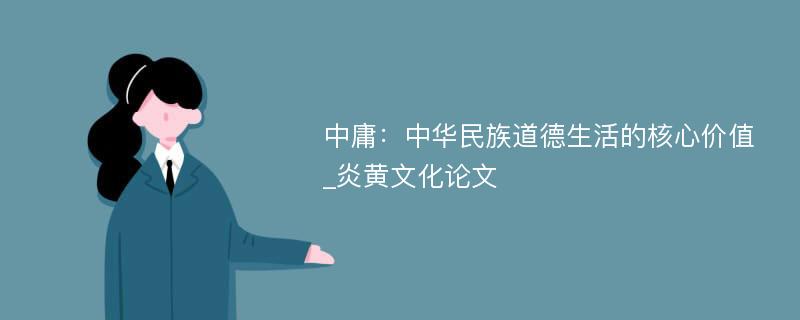
中庸:中华民族道德生活的核心价值观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庸论文,中华民族论文,价值观念论文,道德论文,核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13)05-0048-05
如何探寻与发掘中华民族道德生活的核心价值观念,关乎对中华民族道德生活的整体把握与深度体认,对中华文化品性和特质的整全感知与价值认同,无疑是一个需要全面深入研究而又研究得很不够的重大理论问题。通过“致广大而尽精微”的思维求证以及诸子百家的理论反观,无论是在其显性的行为考察还是隐性的精神索解方面,我们都可以发现,讲求与遵行中庸之道,践行并修养中庸之德,始终是中华民族道德生活的主流价值观念以及中国人孜孜以求与勉励为之的伦理价值目标与生活信念。可以说,中庸之道与中庸之德塑造着中国精神,并因此成为中华民族道德生活的灵魂,是其区别于其他民族道德生活的核心要素与价值基质。
一、“中正”“中庸”是“中国”“中华”的文化伦理蕴含
“中国”“中华”不特是一个地理学与政治学概念,指中原、京畿和国家政权,更是一个伦理文化的概念,指“中正”、“中庸”与“礼仪教化”。杨雄《法言·问道》设宾主问答:“或曰:‘孰为中国?’曰:‘五政之所加,七赋之所养,中于天地者为中国。’”[1](P358)其中“中于天地者”,除了指政治意义上的天下之中外,更是指伦理意义上的中正中、庸之道,即贯通天地、不偏不倚的大中至正之道,亦即“中国之道”。
胡塞尔曾指出,“欧洲这个称呼指一种精神生活和一种创造性的统一体——包括它所有的意图、兴趣、关怀和烦恼,包括它的规划、机构和制度”[2](P946)。与此相对应,“中国”一词在实质上是指一种尚中、用中、守中与持中的精神智慧及行中正、贵中和、主中道的伦理文化精神。“中庸之道”对于中国与中国人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其在某种程度上规定着中国与中国人的内涵和特质。如梁启超将“道中庸重和谐”视为中国的“国性”与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认为与欧洲人好走极端,讲绝对,因之种族、宗教纷争不已有别,中国人以道中庸、重和谐而“纳种种民族、种种宗教,而皆相忘于江湖,未或龃龉破裂”,“其所贵者厥惟秩序,务使其所包含之种种异质,与随时变化之环境相应,常处于有伦有脊的状态”[3](P31—32)。林语堂在《中国人》一书中指出:“中国人如此看重中庸之道以至于把自己的国家也叫‘中国’,这不仅是指地理而言,中国人的处事方式亦然。这是执中的,正常的,基本符合人之常情的方式。”[4](P119)
崇尚中正之道的源头,可上溯至中华民族人文始祖伏羲,他在开辟鸿蒙的过程中“因夫妇,正五行,始定人道”[5](P51)。伏羲之所以能够“始定人道”,源于其“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式的上下求索。正是这种效法天地之道以确定人道的求索路径,奠定了中华民族尚中取正的价值建构基础,同时表达了中华远古先民以“人道”得以无愧地立于天地之间的原初含义。所谓“中”,其实就是一个贯通天地以取其中的意义建构和价值法则。伏羲的人道始定已预制着中华民族立足天地而论人与人道的致思取向及价值建构路径。古史传说的炎黄时期,这种路径不断明晰并向社会生活运演,在“混合殊族”的治理需要中得以强化,初步形成了推崇中正之道、崇尚中正之德的文化传统。《黄帝四经》将中正与法度、道理合而论之,并指出,“天定二以建八正,则四时有度,动静有立,而外内有处”。“明以正者,天之道也。适者,天度也”;“王天下者”效法天地之道,就是要“行中正”,“称以权衡,参以天当”,“应化之道,平衡而止”[6](P126—127,131)。而这种权衡、应化之道即一种恒常的中正之道:“正者,事之根也。执道循理,必从本始,顺为经纪。禁罚当罪,必中天理。”[6](P107)唐虞时期,华夏人道观念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尧、舜被后世视为“圣人”及儒家“道统说”的奠基性人物。尧、舜、禹三代授受均以矢志中正之道为“心传”、“法宝”。为了巩固这种“尚中之德”的地位,并使其传至千秋万代,古人将这种治国的中正之道用于国名,以“中”字称之。“中国”之谓,其义即行中道,尚中德。柳诒徵指出:“唐、虞之时所以定国名为‘中’者,盖其时哲士,深察人类偏激之失,务以中道诏人御物。”“唐、虞之教育,专就人性之偏者,矫正而调剂之,使适于中道也。以为非此不足以立国,故制为累世不易之通称。一言国名,而国性即以此表见。其能统制大宇,混合殊族者以此。”[7](P33)以“中”命国名,表达了远古先圣将“中”提升为国家精神与治国理念,并欲传诸千秋万代的价值观。
中华民族精神及其价值观念是同“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效法天、地、人、物之路径探求与致思取向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并在长期的历史与文化进化中积淀、内化为一种“执两用中”“无偏无党”“无过不及”的道德智慧与德性。可以说,崇尚中庸适度的伦理观念,向往、追求和谐中正的伦理生活,实现内圣外王的人生理想及天下有道的价值目标,一直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传统及其伦理文化的基本精神。
二、中华民族道德生活以追求与践行中庸之道为核心
中庸所确立与规范的道德生活,是一种效法天地之道而成就人道,并以人道来与天地之道相配、相参,进而使人得以无愧地立于天地之间的有意义、有价值的道德生活。其借助并通过命性道教与庸言庸行来表现和实现,并以尽性知天、体天恤道、率性修道为精神要义,其宗旨是使人在天地之间堂堂正正、顶天立地地做人。
崇尚中正,主张“允执厥中”,信守中庸之道,是中国人文精神或中国之道的核心。钱穆指出,“中庸之道”是大道,亦是人道。“惟其中国传统,特重此中庸之道,故中国传统思想,亦为一种中庸思想。”[8](《自序》,P2)当然,这种思想与价值观从根本上说来源于中国人的生命活动而其所主张的生命态度正是“中庸”。所谓“中庸的生命之道”,不单指思想和认识活动,而且涵盖了思想认识活动在内的更为广泛的整个生命实践活动。
中华民族的道德生活是在中庸之道的指导和追求中展现出其特色及优势的,中庸之道向人们“打开了一个生存的视域:天下或天地之间——它构成了中国人生存世界的境域总体”[9](P12)。中庸之道所确立与规范的道德生活是存乎“天地之间”的道德生活,是一种效法天地之道而成就人道,并以人道来与天地之道相配相参的有意义和价值的生活,既体现了对天地之道的尊重、效法,又“以人为依”,主张发挥人之主体能动性与内在价值。中华民族道德生活传统是中华民族在漫长的生产生活实践中不断地法天法地与上下求索的产物,是中华先哲立于天地之道、万物之情不断地进取以继其事,退处以修其身的结晶,也是远古圣人明乎乾坤之道而昭明四方、化成天下的表征与确证。中华民族道德生活是一种借助并通过命、性、道、教来表现和实现的道德生活。“所谓性者,中之本体也;道者,中和之大用也;教者,中庸之成能也。”[10](P68)因此,体天恤道、率性修道成为中华民族道德生活内在精神要义,激励人们通过体认天命、修养性情、接受社会教化来达到与道德合一的境界,使其在天地之间堂堂正正、顶天立地地做人,最终得以“无愧于天地”——实乃“中”字的伦理深蕴。
中国人的道德生活与中庸之道有着一种内在的确证关系,中庸之道是中国道德文化的一以贯之之道与中华民族道德智慧的核心。“刚中而应,大亨以正”,“无偏无党”,“无党无偏”的大中之道,不仅“符合中国精神”,而且是“王天下的平坦大道”[11](P12—13)。商汤时,左相仲虺在劝勉成汤的诰词中指出:“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义制事,以礼制心,垂裕后昆。”[12](P231)所谓“建中于民”,即建中道于民,立中正之道于世,这是王者的责任。周灭殷后,周武王向箕子询问治国之道,箕子据《洛书》详细阐述了“洪范九畴”,史官记录其言,遂成《洪范》。《洪范》代表着中国的“永恒哲学”,与《周易》所代表的“变易哲学”共同构成了中国哲学的基本架构[13](P154—163)。《洪范》第五条提出“建用皇极”。“皇极”即是大中至正之道,是一个国家必须遵行的。其实,不唯《洪范》推崇“大中至正”之道,以此为治理天下的根本大法,专以探讨天下治乱兴衰之变易法则的《周易》亦重于中道或中正之道,《周易·乾》指出,“龙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谨,闲邪存其诚,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认为“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是圣人所应有的行为,也是每一个有道之士所须效法和学习的。《易经》的六爻二、五之中正内蕴着尚中求正的精神取向。若阴爻处二位,阳爻处五位,则既“中”且“正”,称为“中正”,在《易》爻中尤具美善象征。
中华民族伦理价值观是围绕中庸或中正之道而展开的,中庸可谓其核心或枢纽。诚如王夫之所言:“天下之理统一于中:合仁、义、礼、知而一中也,析仁、义、礼、知以中也。合者不杂,犹两仪五行、乾男坤女统一于太极而不乱也。”[10](P59—60)孔子祖述尧舜,十分重视尧、舜、禹政治授受中所体现的“允执其中”思想,并将其与文武之道特别是周礼结合起来,纳仁、礼于中道之中,发展了中正之道与中庸之德,建立了一个以仁为主、仁礼结合的中道伦理思想体系。中庸是内在之仁与外在之礼的统一,构成了仁与礼的本质和原则。仁与礼从内外两方面使道德生活处于一种中和状态。在孔子那里,仁是礼的内在根据,仁道的外化即为礼,统一于中道。仁作为内在德性,礼作为外在规范,各有其不可取代的地位和价值。它们也深化和拓展着中道的空间及范围,赋予中道以更加丰富而深刻的伦理内容。虽然在《论语》中孔子直接提到“中庸”的地方不多,但间接阐述中庸之道与中庸之德的地方则比比皆是,如“过犹不及”,“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等等。曾子以“忠恕之道”为孔子“一贯之道”,其实,“忠恕之道”恰恰是中庸之道的集中体现。“中庸的具体内容,实即忠恕”,“而忠恕即是‘庸德之行,庸言之谨’,即中庸的实践”[14](P71)。如果说“忠恕之道”主要是立足于人的精神动机讲践行中道的话,那么,中庸之道则是立足于人的行为实践讲求适中合宜。可以说,中庸是仁的内在生命。此外,礼是以外在规范的方式使人的行为具有“中”的特点,体现了中庸的原则和要求。在以仁作为中庸至德的人性根据后,孔子进而提出,要达到这种至德还须具备两个要素:智和勇。智表现为一种明辨是非、把握中庸的理性能力,没有这种理性能力,就无法达到仁,自然也就无法达到中庸。孔子之中庸强调时时用中,事事合理,这就必然要求这种理性的认识能力。勇代表一种意志品格,表现为一种勇往直前的坚韧毅力,但其并非鲁莽,而是对道义的信守与坚持。孔子所倡导和推崇的中庸是仁、智、勇的统一,只有将三者统一起来,才能成就中庸德性。不但如此,儒家所讲的其他道德原则规范和德目也是围绕中庸而展开的。
三、中庸之道贯穿于中华民族道德生活的各个方面
中庸之道实际上是一种源于道德形上学的“性命道教”,具有理论伦理学和道德哲学的深刻蕴含,以及规范伦理学和美德伦理学及实践伦理学的多重意蕴,贯穿于道德意识、道德规范与道德行为诸方面及社会的道德评价、道德教育、道德理想与道德人格诸领域之中,是一个由“贵中庸”、“致中和”、“行中正”而连接起来的道德价值体系。正如王夫之所言:“古之圣人,本其性至善者而尽存养省察之功,为内治密藏之极致,乃以发为日用之所当为者,皆得夫大中至正之道,而无过不及。存之为诚,称之为知仁勇,发之为言行动,施之为礼乐刑政。于是功化之极,与天地合德,而民物受治焉。其内外合一之至德,名之曰中庸。”[5](P104)中庸之道有体有用,无论圣凡皆可在体认的同时践行,在践行的同时深化认知,身体力行,拳拳服膺,从而达到知行合一、诚明合一。
中庸之道兼具命、性、道、教诸内涵,其所建构的是一种道德形上学或道德哲学。它作为一种道德本体,是从深厚、高明、悠久的天地之道抽象、提升出来的,是中华先哲“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大其心体天下万物”的智慧结晶。中庸原天以启人,尽人以合天,彰显出“天人合一”的价值特质。大中至正既是天道天德,亦是人体恤天道天德而成就的人道人德。“天道不遗于禽兽,而人道则为人之独。”[16](P405)不遗于禽兽的天道在禽兽那里只是一种自发的本能,不可能产生对天道的体恤与辅佐。是故只有人所独有的人道才能体天恤道,“存人道以配天地,保天心以立人极”[17](P57)。
中庸之道在具体的道德生活中表现为规范伦理学意义上的,人们必须遵守不可须臾离开的基本的道德原则或规范。为此,中庸要求人们为人处世、待人接物遵循大中至正之道,直道而行,公正无私。中正之道源于天道的“刚中而应,大亨以正”,是人对乾道变化、万物各正性命所参悟到的人生之道及应遵循的道德法则。中正含有适中、合宜及恰到好处等意义。如《乾·文言》:“刚健中正,纯粹精也。”《讼·彖传》:“利见大人,尚中正也。”中正之道是无偏无党之王道的价值凝结,表达着中庸之道为原则规范与价值目标的内在要求,包含了不偏不党与公平正义、中正无私、无过无不及等意义。这种“中道”要求人们“不以私爱失其正理”[18](P112),内蕴着“公道”与“义道”的要求。如果说“公道”是“中正之道”的目的性与实质性的要求,那么,“义道”则是过程性与形式上的要求。“公道”是道的普遍性与公正性的集中体现,彰显出道的无私与包容之品格。《说苑·至公》曰:“不偏不党,王道荡荡,言至公也。古有行大公者,帝尧是也,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得舜而传之,不私于其子孙也。……此盖人君之公也。夫以公与天下,其德大矣。推至于此,行之于彼,万姓之所戴,后世之所则也。”[19](P343)“义道”因其适宜、合理、正当的含义而与中庸之道相辅相成,而时中之道集中表现为“义道”。尚公而行义,是中庸之原则性要求。
中庸之道还表现为一种德性伦理学意义上的道德品质或君子人格,此即“中正之德”或中庸品德。中庸要求将文与质有机结合起来,只有内在德性与其外在表现形式实现了适当的配合,才能成为君子人格。君子之道德生活是文明之形式与质朴之内容的和谐统一,言行举止既“发乎情”,又“止乎礼”,简约而有文采,温和而不失条理,在平凡的追求中彰显着伟大。孔子将“中庸”视为“至德”,这种“至德”首先体现为公允地坚守中正的原则,并以无过无不及为特征。中庸之道须由中庸之“德”来开启,而中庸之“德”则展开为一个由浅而深、由疏而密的动态过程:由修道者“智、仁、勇”之“三达德”到君子在“诚之”过程中打开的“诚”,再到圣人无息的“至诚”之德,建构了一个“三达德”、“五常德”及“至诚之德”的美德伦理体系,为人们修德达善提供了一个难得的范本。
中庸之道大虽地表现在人们的实践活动中,成为实践伦理学或行为伦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庸”之原义,就是人们在其日常生活之中,无论是言行,还是待人接物,都能坚持一种中正而不偏激的态度。一方面,中庸之道从人际关系的最小单元——夫妇开始而遍布一切,一般人皆可知可行,不可须臾离开,千万不能以为高远难知而畏缩不前,乃至自暴自弃,这是就中庸之道的平实简易而言;另一方面,中庸之道也有其高明俊伟之处。如深究精研,便可发现,其包罗天下大理及天下万物,即便是圣人也有所不能知,其不能行的地方,故而千万不能因其简易平常就轻视冷落之,不求深造,应深刻地体悟中庸之道所包含的内在机理和高明俊伟之处,并加以持久不懈地身体力行。“中庸之道,圣以之以合天,贤以之以作圣,凡民亦以之而寡过。”[10](P91)各种不同道德境界的人都可在遵循中庸之道的过程中有所收获,在践行中庸之道的过程中实现精神境界的攀越与提升。中庸之道贯穿于人们的言行举止、视听言动等方面。中庸既指“切中伦常”的必要性,亦指“切中伦常日用”的过程与实践活动,是通过“庸言庸行”和日常生活而表现出来的。故有学者指出:“正是通过切中一个人生活的日用伦常从而不断地关注于达到‘中’的境界,最终才会导致那种最为集中和凝聚的富有灵性的经验。”[20]吕坤《呻吟语》既从道统意义上盛赞中道,认定“除了个中字,更定道统不得”,又从日常生活中谈论中道,认为其体现在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或问:‘中之道,尧舜传心,必有至玄至妙之理。’余叹曰:‘只就我两人眼前说,这饮酒不为限量,不至过醉,这就是饮酒之中;这说话不缄默,不狂诞,这就是说话之中;这作揖跪拜,不烦不疏,不疾不徐,这就是作揖跪拜之中。一事得中,就是一事的尧舜。’推之万事皆然。又到那安行处,便是十全的尧舜。”[21](P40—43)人们正是在视听言动、举手投足的日常生活中实践和体验着中庸之道,从而不断发展和完善着自己,创造着人生的价值,在成就自己的同时,更好地改造世界,实现成己与成物的有机统一。
中庸集中正之理、则、德、行于一体,既体现于平常日用,显现于实际的伦理生活之中,又为天命之所当然,不断激励、敦促着人们明德达善,止于至善。
中庸之道强调在做人和道德生活方面把握中正适度的原则,并力求在行为上一以贯之,避免过激与不及的行为。中国人厌恶做人和道德生活方面的“过与不及”两种极端,欣赏处世中正平和、适宜合度。中国人的道德生活是在中庸之道的指导和追求中展现其特色与优势的。中庸之道锻造了中华民族道德生活的精神架构,是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念与伦理品质。中华民族道德生活因始终坚守无偏无党的中正之道,追求天下为公与和谐为贵的伦理原则,将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化为立身处世的准则与风范,并怀有一种修齐治平和内圣外王的价值关注,故而实现了道化的规范建构与德化的美德建构之间的相耦相协,既使中华伦理文化内部保存了源于多样性的活力与互补性,又有助于中华伦理文化的长期稳定发展和延续,避免了由于根本价值冲突而可能造成的灾难性毁灭与悲剧性衰落。罗素指出,“中国是建立在比我们西方人更加人道、更加文明的观念基础上的”,“中国人的显著优点是对生活的目标持有一种正确的观念”,并认为,“中国人的某些无与伦比的优秀道德品质”正是“现代社会生活最最迫切需要的”[22](P36、38、50)。罗素所谓“对生活的目标持有一种正确的观念”及“无与伦比的优秀道德品质”,即指中正和谐的观念与道德品质。他基于对西方文明崇尚竞争、战争与对立而造成的种种灾难性后果而判定,如果世界人民特别是西方人能够真诚地采纳中国文明的中正和谐之道,并在现实生活中加以贯彻执行,我们所处的世界肯定比现在有更多的欢乐与祥和;如果源于中华文明的中正和谐之道不能主宰世界,世界则是没有前途和未来的。这些断语和言论,从一个层面确证了中华文明之中正和谐之道所具有的世界意义。
[收稿日期]2013-02-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