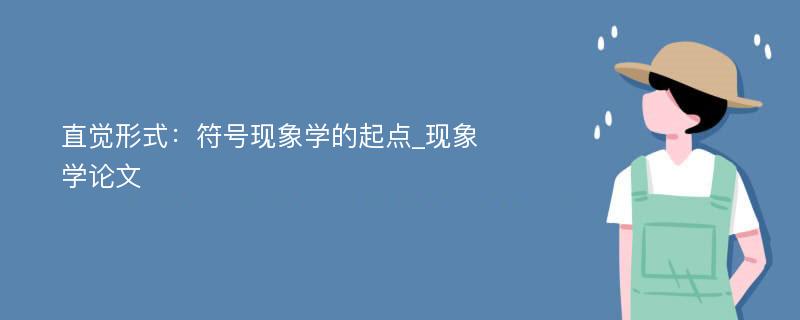
形式直观:符号现象学的出发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象学论文,出发点论文,直观论文,符号论文,形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何为“形式直观”? 意义问题,意义与符号的关系,是20世纪初以来的各批评学派共同关心的课题,这可以说是当代思想的核心问题,符号不仅是意义传播的方式,更是意义产生的途径。符号学作为集中探研意义的学问,更关注意义的形式问题。意义必用符号才能承载(产生、传达、理解),符号只能用来承载意义。德里达说,“从本质上讲,不可能有无意义的符号,也不可能有无所指的能指”①,没有不承载意义的符号,也没有无需符号承载的意义。本文讨论的“形式直观”问题,目的是回答意义是如何产生的:意识面对的“事物”是如何变成意义对象,又如何进一步变成意义载体,也就是意向性是如何把对象变成符号的。这个过程,在本文中称为“形式直观”。因为它直接卷入了意识、意向性、事物、对象,它在意义活动中的基本功能,是符号现象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皮尔斯从19世纪后半期就在符号学论域内思考现象学问题,他到晚年才知道胡塞尔,并且只是在笔记中提了胡塞尔的名字,实际上胡塞尔的现象学比皮尔斯晚出②。由于皮尔斯集中于思考符号学理论,其现象学体系相当特殊,他的讨论基本局限于贯穿符号学的“三性论”③,他甚至在“现象学”(phenomenology)与“显象学”(phaneroscopy)等学科名称上摇摆不定④。 最早结合两个学派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梅洛-庞蒂的“生存符号学”,近年在这个方向努力的有拉尼根和索乃森等⑤,但是至今学界并没有形成一个清晰的符号现象学论辩体系,甚至未能清理出一个基本的论域。笔者认为,符号现象学应当如皮尔斯所考虑的那样,是符号学理论的一部分,是从当今的符号学(而不是现象学)运动的需要出发,重建符号学哲学基础的努力。看起来本文与现象学有所异议,实际上只是吸收了现象学的一些基本概念与方法,试图回顾并丰富皮尔斯的符号现象学,而没有任何重写现象学的企图,也没有任何“反驳”胡塞尔的想法。在个别问题上,例如在符号与事物的关系上,似乎与现象学有所争论,实际上只是论域不同。 意向性,就是意识寻找并获取对象意义的倾向,是意识的主要功能,也是意识的存在方式。意识的“形式直观”,是意识获得意义的最基础活动。形式直观的动力,是意识追求意义的意向性。意识把“获义意向活动”(noesis)投向事物,把事物转化成“获义意向对象”(noema),在这个过程中获得意义。 这一对源出希腊文的术语,中译歧出极多,有“意识活动—意识对象”、“意向活动—意向对象”、“意向性活动—意向性对象”等。对“noema”的翻译,又有“对象”与“相关项”之分,所谓“相关项”,即是“意义”的另一种说法。实际上,“对象”并不等于“意义”,二者还是应当区别开来。这对词的希腊词根“nous”,指的既是“心灵”(mind),又指“认识”(intellect),这些译法的分歧,来自原概念的多义性。 事物面对意识的意向性压力,呈现为承载意义的形式构成的对象,以回应此意向,意义就是主客观由此形成的相互关联。本文把“noesis”称为意识的“获义意向活动”,而把“noema”称为“获义意向对象”(为行文简洁,本文经常会称作“获义活动”和“获义对象”)。所用的译法,虽然长了一些,或许更清楚明了:由于意识对意义的追寻,才出现这一对关键范畴。 本文把获得意义的初始过程,称为“形式直观”(建议英译“formal intuition”)。所谓“初始”,就是第一步,即皮尔斯所谓“第一性”。意义活动不会停留在这一步。皮尔斯认为符号活动必有三个阶段:符号的“第一性”(firstness)即“显现性”,是“首先的,短暂的”,例如汽笛的尖叫;当它成为要求接收者解释感知,就获得了“第二性”(secondness);然后出现的是“第三性”(thirdness),只有到那时,“我们会对于我们所看到的事物形成一个判断,那个判断断言知觉的对象具有某些一般的特征”⑥。意义活动不会停留在初始阶段,意义的积累、叠加,构成第二性的认识记忆;意义的深化,构成第三性的理解与筹划。 本文只讨论意义活动的初始发生,也就是说,只局限于形式直观所涉及的第一性阶段。皮尔斯明确声称:“就我所提出的现象学这门科学而言,它所研究的是现象的形式因素。”⑦形式直观也是一种直观,但与胡塞尔现象学的出发点“本质直观”不同。二者相似的地方只在于对“意向性”和“直观自明性”的理解,胡塞尔说:“在直观中原初给予我们的东西,只应如其被给予的那样,而且也只在它在此被给予的限度内被理解。”⑧意识之“形式直观”之所以成为意义活动的根本性出发点,原因有二:第一,“直观”的动因是自明的,意识的“追求意义”本性,是获义意向活动之源;第二,作为直观对象的“形式”,如皮尔斯的定义,是“任何事物如其所是的状态”⑨,即对象最基本的无可遮蔽的显现。 胡塞尔现象学讨论的关键点是“本质直观”(essential intuition),即“观念直观”(ideation)。本质直观被给予的不仅有感性个体,而且有关系范畴及本质观念。究竟直观是否能通过观念化抓住事物本质?符号现象学并不讨论这个问题,因为符号学关心的是意义的生成和解释,至于由此获得的意义是否为事物本质不可能在形式直观中考虑。皮尔斯建议把符号现象学直观的范围,缩小到对象初始的形式显现:“关于现象学的范畴和心理事实(脑或其他事件)之间的关系,它又极其严格地戒绝一切思辨。它不从事、而是小心翼翼地躲避进行任何假定性解释。”⑩他建议把对事物的进一步理解,推迟给形式直观之后的经验认识累积去解决。这不是符号现象学“有意扭曲”现象学。作为意义理论基础的符号现象学,只是回顾并吸收现象学的一些方法,应用于符号学的基础建设。它与现象学在一系列关键性问题上,看法可以不同,因为各自的论域很不同。 意识的这种初始获义活动是一种直观,是因为意识的题中应有之义,就是寻求意义。为什么意识寻找意义?这一点无需辩护,甚至无须证实,因为它是意识主体存在于世之必需,皮尔斯称之为心灵与“真相”天生的亲近(11)。意识的存在不可能不追求意义,因为人生存于一个由意义构成的世界之中,只要意识功能尚在,就一刻也不可能停止意义的追寻。意识的获义活动能否如意地获得“真相”,则是另一回事,需要另外讨论,但是追寻意义的活动本身,是意识存在于世的方式。 因此,形式直观作为初始获义活动,是自我澄明的。也就是说,主体意识产生获取意义的意向性,这个需要,以及这种能力,是自我的内在明证性的立足点,也是符号现象学的起点根据。获取意义的意向活动,无需他物作为其根据。与之正成对比的是:对象给出意义回应,却不是自发的,而是获义意向施加压力的结果。 只有追寻意义的意识,才是不变的出发点。一旦人的意识不追寻意义,意识就中断,意识就是追寻意义的精神存在。《孟子·告子上》:“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12)孟子这段话说得很清楚:感觉并不是意义的首要条件,意识(“心”)的意向性功能(“思”)才是。“思而得之”的,是对象世界,对象是“思”的产物,而意识对意义的这种追求,是“天所与我”的本能。 并非所有的心理活动都是意识的体现,精神病患者、错觉幻觉者、失去知觉者,一旦他们的意识不再持续地追寻意义,就不具有意识。在这个意义上,睡眠的确可以被看作死亡或精神病态的预演,睡眠中断了意识对意义的追寻,只有靠梦,朦胧模糊地、断续挣扎地维持获义活动。 形式直观不可能取得对对象的全面理解,任何深入一步的理解,就必须超出形式直观的初始获义范围。无论什么事物,都拥有无穷无尽的观相,所谓“一花一菩提,一沙一世界”。在特定的初始获义活动中,只有一部分观相落在意向的关联域之内。例如,我们看到某人一个愤怒的表情,这个感知让我们直观到愤怒这个意义,但是此人愤怒的原因,此人如此愤怒的生理心理性格机制,却远远不是一次形式直观能解决的,需要许多次获义活动的积累,才能融会贯通理解,也很可能永远无法“正确地”理解。皮尔斯指出:认识累积,才有可能“把自己与其他符号相连接,竭尽所能,使解释项能够接近真相”(13)。认识理解,必然不再局限于初始形式直观,而需要进一步的符号意义活动。但所有进一步的理解,首先需要第一步的形式直观来启动。 形式直观是意识与事物的最初碰撞产生的火花,没有这个意义反应,就不会有此后的链式认识活动,就没有符号学的所谓“无限衍义”(unlimited semiosis),不可能进入属于认知过程第二性的理解,更没有属于第三性的范畴分辨与价值判断。皮尔斯认为真相是每个符号的最终解释项。但是无限衍义使符号过程不可能有终结,因此“真相”只是吸引我们持续认知努力的目标,我们的每一步认知能接近这个目标。对事物的认识,可以逐渐加深,逐渐扩大,甚至进而深入事物的本质,但是这些不是形式直观所能做到的。 那么,究竟什么是意义?胡塞尔一再强调:意义并不是意向对象,相反,意义总是意向性活动。因此,当自称继承胡塞尔意义理论的赫施说“一切意向性对象的一般属性就是意义”(14),有论者认为是违背了胡塞尔的原意(15)。笔者认为,意义可以定义为这样一个双向的构成物:意义是意识的获义活动从对象中得到的反馈,它能反过来让意识主体存在于世,因此,意义就是主客观的关联。这样一个定义符合海德格尔的看法:“在领会着的展开活动中可以加以勾连的东西,我们称之为意义。”(16)“严格地说,我们领会的不是意义,而是存在者和存在。”(17)而且,意义也是主客观互相构成的方式:不仅是意识构成对象,而且意识由于构成意向对象从而被意义所构成。梅洛—庞蒂的话“景象用我来思考它自己,我是他的思维”(18),点明了意义关系中的相互建构原则:对象必然是意识的对象,而意识也必然是对象的意识。 王阳明《传习录》的名言“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19)把意识追求意义的关键层次,说得相当清楚:“身之主宰便是心”,自我的主体存在就是自我的意识;“心之所发便是意”,意识的主要功能就是发出意向性;“意之本体便是知”,这种意向性的根本目的就是获得意义;“意之所在便是物”,获义意向性的压力让事物变成对象。 很多学者注意到王阳明这段话与现象学遥相呼应,二者异同之处,也得到不少辩论(20)。笔者认为这段话更适合于符号现象学的形式直观论:王阳明所说的“意”不是纯主观的“心”,而是心发出的“意向性”;“物”可以被理解成“对象”。王阳明还有一段话,支持本文这种理解:“凡意之所用无有无物者,有是意即有是物,无是意即无是物矣。”(21)如果没有获义意向性的压力,事物不会成为对象,而一旦有“意之所用”,即“有是物”。 但是形式直观的意义定义还有个回应过程,我们可以沿着王阳明的话,再加一句,“物之应意便是心”。王阳明也清楚地了解这种意义回应构成意识的过程:“目无体,以万物之色为体;耳无体,以万物之声为体;鼻无体,以万物之臭为体;口无体,以万物之味为体;心无体,以天地万物之是非为体。”(22)对象给予获义意向性的意义回应,反过来构成意识。它们的关系形成(心灵)意识→(获义)意向→(对象事物给予)意义→(心灵)意识,这样就完成了一个意义构成主客观的循环。 二、获义对象是事物还是符号? 获义意向活动的对象,究竟是事物,还是符号?这是符号现象学不得不面对的一个大问题。笔者在《符号学》一书中提出符号的定义是“被认为携带着意义的感知”(23)。既然意义必须通过符号才能表现,形式直观创造的“对象”,就应当既是符号,亦是事物,更明白说,是“以符号方式呈现的事物”。事物在形式直观中呈现为对象,就是为了提供携带意义的观相。 事物呈现为对象,对象提供感知作为符号,这过程的两端(事物与符号)在初始形式直观中结合为同一物,是意向对象的两个不同的存在于世的方式。二者的不同是:事物可以持续地为意识提供观相,因而意识可以进一步深入理解事物,而符号则为本次获义活动提供感知,要进一步理解事物,就必须如皮尔斯说的“与其他符号结合”。因此皮尔斯非常明确地说:“品质的观念是现象的观念,是单子的部分现象。它与其他部分或构成成分无关,不涉及其他东西。我们绝不考虑它是否存在……经验是生活的过程。世界是经验的反复灌输。品质是世界的单子成分。”(24)他的意思是说,符号是个别意义活动中的存在,而事物是持久的意义活动中的存在,事物有回应意向活动的持续性。但是,如果我们只局限于讨论特定的、一次性的初始获义活动,那么事物给出的对象观相即是符号,事物在形式直观中成为符号。 有不少讨论符号的现象学者,强调区分事物与符号,主要是因为他们把符号看做意义的替代,或看作得到意义后进行传送所用的工具。胡塞尔认为符号是直观之后的“非直接”意义,并非第一性的,他认为“直观行为”与“符号行为”是两种不同的表象,取决于“对象究竟是单纯符号地,还是直观地,还是以混合的方式被表象”(25)。他认为直观表象是“本真的”,而符号表象是“非本真的”,也就是次生的。正因如此,舍勒反对卡西尔把人定义为“使用符号的动物”,而要求“从符号返回事物,从概念的科学和满足于符号的文明返回到直观地经验到的生活”(26)。 有些叙述学家,也认为直接感知经验并不是符号,例如普林斯完全否认梦是符号构成的叙述(27)。在他看来符号文本必须媒介化,能给别人看,而经验的“心像”本身,除非用其他符号表现,无法与人分享;吉尔罗也强调“正在做的梦是经验,不是文本”,她的理由却是“(媒介)文本有边界,形成整体结构”(28),经验的心像不构成符号文本。 但是也有论者发现这二者的区分并没有那么清晰。文化哲学家霍尔提出:人类面对的是两套“再现体系”:“一是所有种类的物、人、事都被联系于我们头脑中拥有的一套概念或心理表象”;而第二个再现系统是符号,即“我们用于表述带有意义的语词、声音或形象中的术语”(29)。霍尔实际上承认:既然“事物的概念与心理表象”与各种符号一样,都是用来“再现”意义的,那么它们至少在意义活动中很难区分。 笔者认为,事物与符号的确有本质区别,上面已经谈到,它们的意义持续性非常不同。只是在特定的初始获义活动中,二者无法区分,因为此时事物呈现为符号。对象对获义意向提供观相以构成意义,这种观相来自哪一具体事物,在形式直观阶段并不一定能区分,也并不一定要区分。一个苹果的鲜红,一个蜡像或一幅画面上的苹果的鲜红(某些人只承认后两种为符号),一样可以引向“新鲜”、“可食”、“可观赏”等意义;一个笑容,在人脸上,在照片上,在视屏上,都可以引向“和蔼”、“可亲近”等意义。一个人醒来时听到清晨农村一天开始时的各种声音,这究竟是身处农舍听到的自然声音,还是有人在放录音,给他的意义并无二致。这不是说事物与图像这样的人工符号之间难以区别,而是说在初始形式直观中,这两者无从区别。 符号现象学与现象学的这种分歧,起源在于对符号本质的理解。主张事物不同于符号的学者,可能心底里认为符号是靠“一物代一物”被用作意义替代的:有了意义,需要传送,才需要符号。这个误解从符号学形成之初就已经出现,皮尔斯曾指出:“(维尔比夫人提出的)‘表意学’(significs)比符号学的范围小了一些,因为‘表意’(signification)仅仅是符号的两个主要功能之一。”(30)另一个主要功能就是意义的接收。大半个世纪之后,福柯对符号学的误解如初,他说:“我们可以把使符号‘说话’,发展其意义的全部知识,称为解释学;把鉴别符号,确定为什么符号成为符号,了解连接规律的全部知识,称为符号学。”(31)福柯明显说的是索绪尔符号学,实际上在皮尔斯的理论中,符号学的重点落到意义的解释上。近年符号学的发展,重点更落在接收这一端。 意义并不出现在符号之先,凡有意义时,就必然已经有符号承载这意义。苹果“新鲜”的意义,并不一定在用另外的媒介(例如图像或视屏)来传送时才需要符号,苹果自身成为意识对象,就是鲜红的观相成为符号的结果。不是一定要到感知被“媒介”携带并传达的时候,才成为符号。实际上,当意识感知到事物的某个观相,就把事物变成了认识对象,也就是说,在意识的“共现”(appresentation)中,片面性的观相,就已经成为事物的符号,这两者之间已经出现了部分指向整体的符号表意关系。既然“符号”的定义是被认为携带着意义的感知,那么观相反馈意义给意识,它就是一个符号。正因如此,“真实的”苹果与苹果的蜡像或照片,在初始形式直观中,意义功能可以相同。当我们把符号学的重点从发送者移到接收者,把接收者看成面对对象的意识,事物与符号的分别,在形式直观中就暂时不存在。 胡塞尔曾相当详细地讨论过蜡像馆中蜡像与真人的区别,他说“一旦我们认识到这是一个错觉,情况就会相反”(32)。因为到此时,我们才会意识到二者“质的”区别。那么,在认识到错觉之前,二者的意义是相同的。美术史家贡布里希的下面这段论述,也在强行区分事物与符号:“植物课上使用的花卉标本不是图像,而一朵用于例证的假花则应该算是图像。”(33)标本是真花,而这位植物课老师手里拿的是假花。但是对于课堂上学生进行的这一次获义活动而言,假花(符号)与真花(事物),如果形式相同,初始获义会有什么差别呢?除非有人已经看出形式不同,那样就是对象不同导致意义不同。 甚至观相的明显差异,在特殊的意义活动中也能暂时搁置,条件是主观上看不出不同点:花卉画能把鸟弄糊涂;美人画能让柳梦梅堕入情网(这是感情引发的超常识认同);听到曹操说“梅子”,见到梅子的画,闻到梅子的味道,与看到梅子、尝到梅子,意义效果也会很相似;在现场看足球,与看电视现场直播,甚至看重播(只要不事先知道比分),所获得的意义是相同的。有人可以说二者很不同,电视上感觉不到现场的气氛,但是电视也给我们现场看不到的细部,现场与转播如果提供的观相相同(例如在我这种“伪球迷”眼中),形成意义就相同。 因此,事物与符号,在形式直观中,没有根本性的区别。奥格登与瑞恰慈在讨论意义的定义时指出:“我们的一生几乎从头到尾,一直把事物当作符号。我们所有的经验,在这个词最宽的意义上,不是在使用符号,就是在解释符号。”(34)胡塞尔其实也清楚事物与符号在意义活动中潜在的同一性:“最终所有被感知之物,被虚构之物,符号性地被想象之物和荒谬,都是明证地被给予的。”(35)德里达在批评胡塞尔的符号理论时指出:“如果把符号看作一种意向运动的结构,那符号不就落入一般意义上的物的范畴?”(36)而德勒兹的声明更为明确:“事物本身与事物被感知其实是一回事,呈现同一个形象,只是各自被归为两种不同的参考系统。”(37)这种“归于参照系统”,须待事后的进一步认识。 意义必然是符号的意义,符号不仅是表达意义的工具或载体,符号也是意义产生的条件:有符号才能出现意义活动。意义形式直观所面对的事物,在这时候也让有关的观相呈现为符号,让自己成为符号所指的意义。在意识的获义活动中,事物与符号无区别,原因非他,因为落在获义活动中的对象,已经非事物本身,而是获义活动所需意义的提供者。 三、形式还原 所谓“还原”,就是简化成最基本的要素。意识要获得意义,意向活动必须排除所有与获义活动无直接关联的因素。上面已经说过,事物在获义意向性的压力下,被还原为提供意义的观相所组成的对象。形式还原的第一步就是“悬搁”:获义意向活动把事物的某些要素“放进括弧”,存而不论,排除在外。事物与符号,在形式还原中无从区别,因为意识的形式直观,首先悬搁了对象的“事物性”(thingness)。 在意义产生过程中,事物失去事物性。皮尔斯对此的解释比较清楚:“现象学与它所研究的现象,在多大程度上和实在相符合这个问题没有关系。”(38)他在另一处进一步说明:“红色的品质取决于任何人实际上都看到了它,因此在黑暗中红色就不再是红色。”(39)鲜红的颜色和形状说明苹果的存在,而在黑暗中,红色消失,我们知道苹果的颜色也只是在记忆中。此时形式直观只能依赖于别的观相,例如触摸圆润,嗅闻香甜。因此,在初始获义意向活动中,对象失去事物性,被形式还原成符号感知。甚至,在符号学中,关于意识是否能掌握事物本质的考虑,即“本质直观”的可能性,也在被形式还原暂时悬搁之列。 在所有的获义意向活动中,事物必须靠形式还原才能具有意义给予能力。意识中最初呈现的一切都是感知表象,皮尔斯在讨论第一性的“现象的性质”时,称之为“显象素”(phaneron),即“此时此刻在心灵里的显现”。“显象素”既是事物又是符号,因为“显现”的只是部分观相。经过这种形式还原,主体意识面对的事物,就降解成为携带意义的符号感知。获义意向活动的对象,本来就是意向性的构造物。意识要获得意义,第一步是“面向事物的形式本身”,获义意向划出事物被感知的范围,这是获得意义必要的前提。 意向活动的投出不仅有方向(投向某个对象),而且对相关的观相有所选择。这种选择“悬搁”了与本次获义活动不相关的观相,忽视不期而然落入感知的“噪音”,并且把相关观相分解成“背景区”、“衬托区”与“焦点区”。事物的形式被意向性如此处理,意向性显得像个手电筒,只照亮事物形式的一部分,把它变成对象,而且聚焦于更小的一部分,在此获得最多的意义,其余都被悬搁,被当作噪音、当作背景、当作衬托。把意向性比作手电筒,过分空间化,不适用于多样化的(例如嗅觉、味觉方向的)获义活动,但是它比较生动地说明了意向性如何把事物变成对象,激活出意义来,而且让对象呈现一种“非匀质”状态。 在意识追求意义的过程中,每一个事物,都有可能呈现有关观相,而成为意义的符号载体;反过来,每一个符号载体,也可以因为所携带意义消失,而降解为不携带意义的事物。由此,每一个事物,每一个符号,都是表意性与物性复合的“符号—物”双联体。哪怕是人工制造的最彻底的“纯符号”,例如言语、文字、图画、标记、纸币等等,都有物的成分。符号的这些物成分(例如涂抹可以遮盖,纸币可以点火),一样具有物的无穷观相。既然任何物都是一个“符号—物”双联体,它就可以向纯然之物一端靠拢,完全成为物,此时它与意义活动无关;它也可以向纯然符号载体一端靠拢,不作为物存在,纯为表达意义,或更确切地说,纯为本次意义活动提供符号载体。人在付钱时,使用事物的观相携带的符号意义,纸币的物品质,例如纸币的硬度,不参与本次具体的意义活动,除非纸币过于破烂使其意义可疑。任何符号—物都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滑动,因此,绝大部分物都是偏移程度不一的符号—物,其使用部分与表达意义部分的“成分分配”,取决于特定的获义意向。 从这个基本理解出发,可以看出,被形式还原成为获义活动对象的符号—物,可以有四类: 第一类是自然事物(例如雷电,例如岩石),它们原本不是为了携带意义而出现的,它们“落到”人的意识中,被意识符号化,才携带意义:雷电被认为显示天帝之怒,或预兆暴雨将至,岩石可以看作矿脉标记,或自然界鬼斧神工。 第二类是人工制造的器物(例如石斧,例如碗筷,例如食品),原本也不是用来携带意义的,而是使用物。这些事物,当它们显示“被认为携带意义”的观相时,也就是被“符号化”时,就成为符号:石斧在博物馆成为文明的证据,食品放在橱窗里引发我们的食欲。 第三类是人工制造的“纯符号”:完全为了表达意义而制造出来的事物,例如语言、表情、姿势、图案、烟火、货币、游行、徽章、旗子、棋子、游戏、体育、艺术等等,它们不需要“符号化”才成为符号,因为它们本来就是作为意义载体被制造出来的。上文已经说过,它们在一定场合也可以降解为物。 第四类是看起来几乎无任何物性的“纯感知”,例如心像(错觉、梦境等),“应有感知而阙如”造成的“空符号”(如沉默、无表情等),它们作为符号存在,是因为它们也是“被认为携带意义的感知”。梦中的家乡让人情可以堪,音乐中的休止,绘画中的留白,都是携带意义的符号感知。 既然任何符号—物都不外乎这四类,而这四类都可以变成符号来表达意义,它们表达意义的部分都只是符号,而不是事物,那么在表达意义的时候,上面的分类中,“原先的”事物,与“原先的”符号,没有本质差别。符号现象学探究如何获得意义,要做的是“形式直观”,就不必、也无法区分这四者何者只能为物,何者只能为符号。 在形式还原时,要悬搁事物的事物性,也需要悬搁符号—物与本次的意向活动不相干的诸种观相。因此,被获义活动选择出来构成对象的,不是事物本身,而是事物的特定观相。事物不需要全面被感知才携带意义,让事物的过多观相参与对象之形成,反而成为获义的累赘,因为噪音过多。形式还原并不使符号回归事物自身,恰恰相反,符号因为要携带意义,迫使对象“片面化”,成为意义的简写式。 这种片面化,是获义活动之必需:若无关品质,不仅可以忽视,而且必须忽视,不然意义活动就会遇到困难。如果汽车按喇叭,你听到马上会躲避,甚至不去看汽车一眼,此时符号就使整个事物极端片面化,只剩下喇叭声音这一感知;而当朋友向你炫耀豪车,此时你就会注意到标牌的样式和车身的光鲜:这当然也是片面化,是另一种片面化。因此,初始获义意向活动要追寻意义,事物就只剩下与意义相关的观相组成对象。正因有这样一个意向性选择,事物在意向性压力下还原为符号。 所以符号载体不仅不是物,甚至不是感知集合,而只是与获义意向活动相关的某个或某些观相的临时显现。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同一事物可以承载完全不同的符号。例如一个苹果,意义可以有关美味、有关水分、有关外形美等等:同一个苹果,在被不同意向性激活后,显现的观相不同,产生的意义不同。 这就是为什么本文一再强调,事物与符号感知,在形式直观中,对意识而言是等值的。只不过事物是可供进一步认识的无穷观相的寄宿地,可以持续地回应需要意义累加才能形成的理解活动。继续沿用上面举过的乡间晨音的例子,如果我听到此“天籁”后起身,看一看嗅一嗅摸一摸,事物的其他观相就成为新的符号,回应我的新的获义意向活动,此时事物不同于符号的“意义持续性”就显示出来了,意识也就渐渐接近“真相”。意义一旦累加,我就可以进一步理解农村田园生活,或是进一步理解CD音响。到这个时候,前者被称为“事物”,后者被称为“符号”,或许才有道理。 注释: ①(36)雅克·德里达:《声音与现象——胡塞尔现象学中的符号问题导论》,杜小真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0页,第30页。 ②施皮格伯格说皮尔斯“很熟悉胡塞尔的逻辑学”(参见施皮格伯格《现象学运动》,王炳文、张金言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52页),他没有提出根据。皮尔斯晚年的笔记中两次提到胡塞尔的名字,但是对胡塞尔的学说没有任何说明(Cf.Charles Sanders Peirce,Collected Paper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1-1958,Vol.4,p.7; Vol.8,p.189)。 ③参见纳桑·豪塞《皮尔斯、现象学和符号学》,保罗·柯布利编《劳特利奇符号学指南》,周劲松、赵毅衡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98-110页。 ④(11)(13)《皮尔斯论符号》,赵星植译,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8页,第15页,第15页。 ⑤Cf.Richard L.Lanigan,“The Self in Semiotic Phenomenology”,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emiotics,Vol.1,No.4(2000):91-111; Goran Sonesson,“From the Meaning of Embodiment to the Embodiment of Meaning:A Study in Phenomenological Semiotics”,in Tom Ziemke & Jordan Zlatev(eds.),Body,Language and Mind,Berlin:Mouton de Guyter,2007,pp.85-127. ⑥科尼利斯·瓦尔:《皮尔士》,郝长墀译,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25-27页。 ⑦⑩(24)(38)(39)Charles Sanders Peirce,Collected Papers,Vol.1,p.284,p.287,pp.310-311,p.287,p.418. ⑧(35)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李幼蒸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84页,第53页。 ⑨Form is “that by virtue of which anything is such as it is”.Cf.Max Fisch(ed.),The Writings of Charles Sanders Peirce,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1-1993,p.371. (12)焦循:《孟子正义》,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796页。 (14)E.D.Hirsch,Validity in Interpretation,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7,p.218. (15)R.马格欧纳:《文艺现象学》,王岳川、兰菲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年版,第113页。 (16)(17)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熊伟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85页,第186页。 (18)Maurice Merleau-Ponty,“Cézanne’s Doubt”,in Galen Johnson & Michael B.Smith(eds.& trans.),The Merleau-Ponty Aesthetics Reader:Philosophy and Painting,Evanston,IL: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93,p.59. (19)(21)(22)《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6页,第8页,第108页。 (20)参见林丹《境域之中的“心”与“物”——王阳明心物关系说的现象学分析》,载《江苏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 (23)赵毅衡:《符号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页。 (25)(32)胡塞尔:《逻辑研究》第二卷,倪梁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52页,第491页。 (26)施皮格伯格:《现象学运动》,第400页。 (27)Gerald Prince,“Forty-One Questions on the Nature of Narrative”,Style,Vol.34(2000):317-327. (28)Patricia Kilroe,“The Dream as Text,The Dream as Narrative”,Dreaming,Vol.10,No.3(2000):127. (29)斯图亚特·霍尔:《表征:文化表征与意志实践》,徐亮、陆兴华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22-23页。 (30)Charles Sanders Pierce,Collected Papers,Vol.8,p.378. (31)Michel Foucault,The Order of Things:An Archeology of Human Sciences,trans.Alan Sheridan,London:Routledge,2002,p.33. (33)E.H.贡布里希:《视觉图像在信息交流中的地位》,范景中选编《贡布里希论设计》,湖南科技出版社2001年版,第111页。 (34)C.K.Ogden & I.A.Richards,The Meaning of Meaning,New York:Harcourt,Grace & World,1946,pp.50-51. (37)吉尔·德勒兹:《电影I:运动—影像》,黄建宏译,(台湾)远流出版公司2003年版,第1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