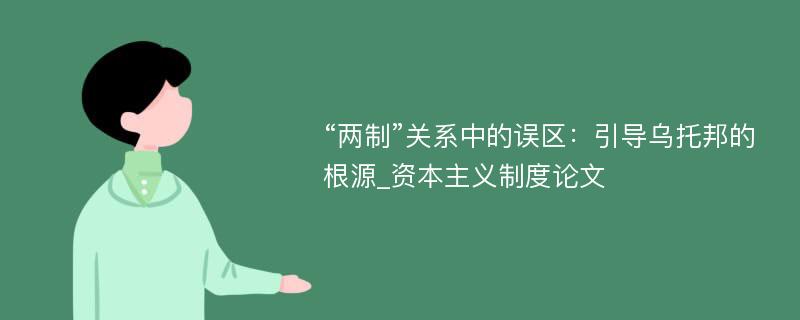
“两制”关系上的认识误区——导向空想的一个根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空想论文,根源论文,导向论文,误区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何认识资本主义及其“两制”的关系,始终是社会主义者面对的一个重大问题,但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社会主义者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存在误区。16至19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全盘否定资本主义,主观地割断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历史联系,否认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基础,因此他们的理想社会只能是空中楼阁。20世纪的社会主义者为了抵制资本主义的侵蚀,拒绝利用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但又急于赶超资本主义,因此也曾空想萌动。尽管二者存在本质的区别,但在“两制”关系上的认识误区,使它们都陷入了空想的怪圈。
1978年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冲破了姓“社”姓“资”的思想束缚,为“两制”关系重新定位,终于给中国的发展带来了无限生机。实践证明,只有正确认识“两制”关系,才能从根本上杜绝空想。
(一)
16至19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全盘否定资本主义,主观地割断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历史联系,否认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基础,因此他们的理想社会只能是空中楼阁。
首先,他们不能辨证地历史地评价资本主义。1516年,当资本主义尚处于萌芽时期,莫尔就预见到资本主义的弊病,提出消灭一切私有制,并描绘了一个理想社会——《乌托邦》。我们首先肯定莫尔的政治洞察力和远见卓识,但莫尔对资本主义的评判使用的是道德标准,而忽略了历史标准,从而完全否认资本主义的历史作用。在他的笔下,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同样丑恶,都应该被推翻。其实,当时这两种制度正处在完全不同的发展时期,封建主义已日薄西山,而资本主义则刚刚破土而出,生气蓬勃地处于上升时期,对这两种既不同质又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制度各打五十大板,起码是不公平的,也是不科学的。自莫尔之后,空想社会主义者在批判资本主义时,运用的几乎全是道德标准,对资本主义的历史作用基本忽略,因此也就无法对其作出辨证和历史的评价。
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最深刻的,但同时他们又从人类历史发展的高度,肯定“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P277)。可见他们在评价资本主义时,坚持的主要是历史标准,而非道德标准,因为“共产主义者根本不进行任何道德说教”[2](P275)即使需要进行道德评价,也应该把其置于历史评价的基础之上。
其次,他们否认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历史联系。莫尔从“羊吃人”的现象预见到资本主义的弊病,从而根本否认资本主义的存在价值,不承认资本主义文明是他推崇的理想社会之基础。摩莱利和马布利同样否认资本主义与未来社会的联系,摩莱利认为要切断私有制的根,必须回到原始自然状态去。马布利则认为“在他们的这种处于萌芽状态的社会里有最完美的平等。”[3](P252)他甚至提出限制生产的主张,企图以禁欲主义来实现所谓的平等和幸福。19世纪初的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虽然认识到资本主义是封建制度与未来社会制度之间的一个“中间的和过渡的体系”[4](P252),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的一个暂时阶段,但是,却始终没有进一步认识到这个“暂时阶段”是必不可少的,是为社会主义奠定基础的阶段,否则他们的理想王国就不可能实现。正因为此,他们仍然没有突破空想的局限。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是用世界历史的眼光,来看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关系的。马克思早在1850年就指出:“只有工业资产阶级的统治才能除掉封建社会的物质根蒂,并且铺平无产阶级革命唯一能借以实现的地基。”[1](P402)列宁则把资本主义看作建立社会主义的唯一基础,指出“开发资源、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真正的和唯一的基础只有一个,这就是大工业。如果没有资本主义的大工厂,没有高度发达的大工业,那就根本谈不上社会主义,而对于一个农民国家来说就更是如此。”[5](P301)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地基”和“基础”,这就是经典作家对“两制”关系的正确评价。资本主义不但为社会主义准备了物质条件(社会化大生产),而且还准备了阶级条件(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有着割不断的历史联系,这就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不管你主观上是否承认,它总是客观地存在着。
最后,他们忽略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现实基础。他们主观排斥资本主义这个现实基础,热衷于“发明一套新的更完善的社会制度,并且通过宣传,可能时通过典型示范,从外面强加于社会。这种新的社会制度是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空想的,它越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越是要陷入纯粹的幻想。”[2](P724)
马克思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6](P33)这段话揭示了两个深刻的道理:第一,人类社会每一种新的生产关系都是在旧社会孕育成功的,它产生的现实基础就是它将取代的那个社会形态。同样如此,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也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胎胞里产生并成熟的,而在其日益壮大的过程中,吸收的正是资本主义为它提供的各种养料。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决不是空中楼阁,而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作为一种文明,社会主义也只能是资本主义的继续,而不可能是以往文明的中断。第二,衡量新的生产关系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是否成熟的主要标志是生产力水平,这是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社会形态更替的普遍规律。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越是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存在条件就越趋成熟;资本主义社会所容纳的全部生产力一旦发挥殆尽,社会主义就会水到渠成。“如果社会主义在经济上尚未成熟,任何起义也创造不出社会主义来。”[7](P218)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不是人们头脑中杜撰的理想社会,如果忽略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而拔苗助长,只能陷入可悲的空想。
(二)
20世纪的社会主义者为了抵制资本主义的侵蚀,拒绝利用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但又急于赶超资本主义,因此也曾“空想”萌动。尽管他们与空想社会主义者有本质的区别,但在“两制”关系上的认识误区,使他们同样陷入“空想”的怪圈。其主要表现为:
第一,两大阵营的对峙导致全面否定资本主义。马克思指出:“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来”,这样“就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苦难而取得它的全部成果”[8](P129)。即经济落后国家尽管有权利选择“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但却不应该拒绝承袭资本主义所创造的“一切肯定的成就”和“全部成果”,因为这是建立社会主义所必须具备的条件。现实的社会主义都来自经济落后国家,有的是不发达的资本主义,有的甚至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借鉴资本主义的成就和成果是它们承担的共同任务。但是,当社会主义制度一诞生,就遭到了资本主义的干涉和遏制,两大阵营的严重对峙,使社会主义视资本主义为“洪水猛兽”,千方百计设置壁垒,以防止资本主义的侵蚀,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去借鉴和利用资本主义,从而对社会主义的“合格”标准心中没底,导致过渡时期相对短暂。短暂的过渡时期并没有垒起坚实的生产力基础,而对共产主义的美好憧憬,又使人们加速推动历史的车轮。现实和理想的巨大差距,终于促发了空想的萌动。
第二,“资强社弱”的现状,促发社会主义的“赶超”冲动。资本主义制度是建立在封建主义衰落的基础上,发展的氛围相对宽松;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之中,所处的环境非常压抑。资本主义所拥有的现代化先发优势,以及“中心——外围”的国际分工体系,始终处于强势地位。社会主义的优越感与“资强社弱”的现实形成了极大的反差,赶超资本主义就成为社会主义的既定目标。但是,资本主义已经有几百年的发展历史,社会主义则刚刚喷薄而出,双方的实力悬殊,赶超谈何容易。但是,社会主义者相信政治勇气可以弥补经济实力的缺憾,只要执政党的使命感与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相结合,就能创造出人间奇迹。前苏联从斯大林以重工业为重点发展战略、赫鲁晓夫的15年赶超美国乃至戈尔巴乔夫的“加速战略”,都是为了在短时间内赶上并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结果却事与愿违。我国“大跃进”的目标也是为了在钢产量上赶超英国,动用了9000万人大炼钢铁,尽管如期完成了1070万吨钢的既定指标,但其质量却大打折扣。社会主义“赶超”的愿望无可非议,但由于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既定目标非但没能如期实现,反而导致了急于求成、超越发展阶段的“空想”萌动,教训是何等深刻!
第三,忽略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基础,断章取义地搬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以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研究对象,所制定的一些基本原则也主要是为它们度身定做的。现实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同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情况存在巨大反差,但社会主义者却无视这个反差,断章取义地解读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原则,把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当作神圣不可动摇的定理。由于忽略了本国国情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盲目追求高起点,必然出现拔苗助长的“空想”萌动,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诚然,空想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空想萌动,决非简单的重复,而是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在“两制”关系上的认识误区,却使它们不约而同地陷入空想的怪圈。
(三)
世界社会主义的历史证明:“两制”关系上的认识误区,是导向空想的一个根源;而要彻底告别空想,必须为“两制”关系重新定位。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母体,经济落后国家尽管在社会制度上回避了这个“母体”,但却不应该拒绝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也无法人为割断“两制”的历史承袭关系。社会主义者只有走出“两制”关系的认识误区,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大胆利用资本主义,才能彻底告别“空想”,使社会主义始终循着科学的轨道前进。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就是明证。
首先,经济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间,应该与资本主义的发展水平成反比。也就是说,生产力越落后过渡的时间就越长。按照马克思设计的革命程序,社会主义制度应该首先建立在经济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改变了这一程序,使一大批经济落后国家率先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可以越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进入社会主义,但这不等于说,这些国家可以把应该在资本主义阶段完成的历史任务从自己的发展进程中一笔抹去。相反,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必须用相当长的时间,集中力量完成生产社会化、商品化、工业化和现代化,以及相应的民主法制建设和科学文化建设任务,过渡时期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须的。列宁指出:“资本主义愈不发达,所需要的过渡时间就愈长。”[9](P183)只有经过适当的过渡时期,才能使社会主义的根基牢固,才能获取社会主义的“合格证”。
其次,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大胆地利用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其目的不是为了复制资本主义,而是为了超越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在长达50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创造了许多文明成果,我们“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和商品经济一般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国外的资金、资源、技术、人才以及作为有益补充的私营经济,都应当而且能够为社会主义所利用。”[10]历史使经济落后国家超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因此必须自觉地有选择地利用资本主义,为过渡到社会主义创造条件。我们为了实现对资本主义的超越,必须首先向它们学习。正如列宁所说:“没有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没有战胜资本主义的保证”。[11](P10)只有敢于和善于利用资本主义,利用好资本主义,才能建立“合格”的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对资本主义的超越。
最后,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异,不应该成为“两制”关系的障碍。“两制”关系的历史证明,“两制”间的对峙和斗争主要源于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异。其实,各国人民都有选择自己发展道路的权利,不同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是一种客观存在,我们“应尊重各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承认世界多样性的现实。世界各种文明和社会制度,应长期共存,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12]特别在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当代世界,一些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大问题,已经突破了社会制度的界限,需要全人类的智慧和努力才能解决,这就使“两制”间的合作和支持成为现实。而经济全球化又使各国经济的开放性和互补性日益增强,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都在尽可能地吸收借鉴对方的先进文明成果,以谋求自身的再发展。可以预见,在新的世纪里,“两制”之间的关系总体上可能仍是和平共处,我们应该“以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为重,不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扩大共同利益的汇合点,妥善解决分歧”[13],实现共同发展。
标签: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国家社会主义论文; 文明发展论文; 社会主义阵营论文; 经济学论文; 经济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