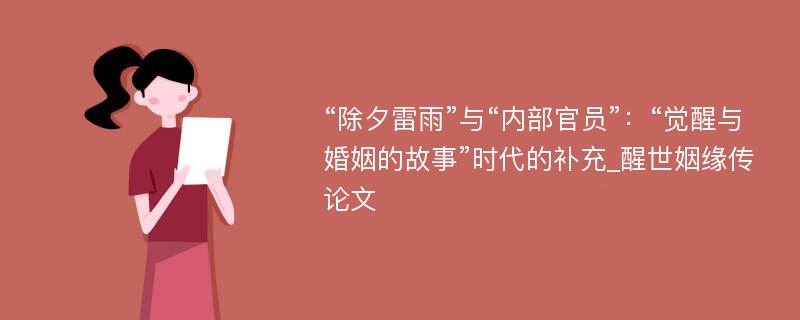
“除夕雷雨”与“内官”:《醒世姻缘传》成书年代补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成书论文,雷雨论文,姻缘论文,除夕论文,年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学界对《醒世姻缘传》的成书年代一直争论不休,概括起来,主要有“崇祯说”、“顺治说”、“康熙中后期说”等三种说法。另外,林辰先生曾提出“乾隆说”,这显然属于误断,因为雍正六年(1728)日本的《舶载书目》已经著录了此书(注: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页238,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关于成书年代的上限,小说中所写到的有关李粹然的事迹是极有力的内证。三十一回:“天地的心肠,就如人家的父母一样……他那指望他做好人改过的心肠,到底不死,还要指望有甚么好名师将他教诲转来。所以又差了两尊慈悲菩萨变生了人,又来救度这些凶星恶曜,一位是守道副使李粹然,是河南怀庆府河内县人,丙辰进士。”孙楷第先生据《河内县志》、乾隆《淄川志》、康熙和光绪《滋阳志》、《嘉兴府志》、《潞安志》等考定:“粹然任济南道,的是崇祯初年事,倘小说作于崇祯以前,即无粹然任守道之事。然则谓此小说之作,至早不得过崇祯,乃极有把握之论断。”(注:孙楷第《一封考证醒世姻缘的信》,亚东版《醒世姻缘传》附录,广州出版社,1996年版。)这一“极有把握之论断”已得到学界公认。至于具体成书年代,孙先生认为“当在康熙间”(注:孙楷第《一封考证醒世姻缘的信》。);胡适先生以作者为蒲松龄为前提,认为在“康熙四十二三年——蒲松龄六十四五岁时——还没有完成”(注:胡适《〈醒世姻缘传〉考证》,亚东版《醒世姻缘传》附录。)。建国后,路大荒先生首先对蒲松龄说提出异议(注:路大荒《聊斋全集中的“醒世姻缘传”与“鼓词集”的作者问题》,《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副刊,1955年9月4日。),动摇了书成于康熙中后期的前提;随后王守义先生明确提出“《醒世姻缘传》当作于明末崇祯朝”(注:王守义《〈醒世姻缘〉的成书年代》,《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副刊,1961年5月28日。),彻底否定了胡适对此书作者和成书年代的结论。
80年代以来,对《醒世姻缘传》的研究逐渐升温,成书年代始终是焦点问题之一。刚开始的时候,主要是延续胡适“康熙中后期说”和王守义“崇祯说”两种意见,比较起来前者占明显优势。1979年版的《辞海》倾向此说;孙楷第先生《中国通俗小说书目》1982年再版时仍坚持“书为留仙作说比较可信”,也就是说坚持成书于康熙年间;徐北文先生为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时所写的《简论》中亦持此说;李永祥先生虽然比较笼统地说“成书必在清初”,却认定“作者当为蒲松龄”(注:李永祥《蒲松龄与〈醒世姻缘传〉》,《中华文史论丛》,1984年第1辑。)。一些坚持认为作者为蒲松龄的学者,对成书年代往往比较笼统地称为“清初”,这个“清初”其实是指胡适所说的康熙中后期。“康熙四十二三年”距明亡已经有六十来年了,再称清初显然不合适。而且,另外有些学者认为成书于顺治年间,也简称“清初”。这样,表面看起来说的都是“清初”,其实相差了三四十年。为了便于区分,不妨分别以“顺治说”和“康熙中后期说”称之,与此相适应,我们将学界一般所说的“明末说”改称为“崇祯说”。
随着研究的深入,作者为蒲松龄的说法已基本被否定,“康熙中后期说”也就站不住脚了,而在“崇祯说”和“顺治说”之间仍难以定谳。
“崇祯说”的主要思路是考证作品中一系列事典都符合明末的社会现实而不露清朝的痕迹;以徐北文、徐朔方、李永祥、孙玉明、徐复岭等先生为代表的明确主张“顺治说”或反对“崇祯说”的学者们的主要思路和方法则是在作品中找出一些“清代的痕迹”,这种思路和方法无疑是正确的。不过,到目前为止,几乎所有文章中提到的“清朝的痕迹”都不能说明问题。曹大为先生曾撰文对徐北文、徐朔方、李永祥等先生提出的有关“关圣帝君”、“典史稽察狱囚”、“捐纳”、“条鞭之法与赋役流弊”等问题分别作了有力的反驳(注:曹大为《〈醒世姻缘传〉作于明末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4期。),只是对“除夕雷雨”一条的解释显得勉强。就目前讨论的情况来看,对“崇祯说”最具挑战性的有两点:一是“除夕雷雨”一事;二是有关“内官”的事。笔者在博士学位论文《〈醒世姻缘传〉研究》中,在广泛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对有关成书年代的种种说法进行了详尽的辨析,最后的结论是同意“崇祯说”,具体来说,大约成书于崇祯十二年至崇祯十七年之间。限于篇幅,本文仅提供对“除夕雷雨”和“内官”两条材料的考辨。
一、关于除夕雷雨
第二十七回:“十二月还要打雷震电”,“癸酉十二月的除夕,有二更天气,大雷霹雳,震雹狂风,雨雪交下。”
《济南府志》载,崇祯癸未十六年,“除夕,雷雨大作”。孙楷第先生据此认为,小说中的“除夕雷雨”“虽时代不符,当即此年事”。学界大都同意此说。力主成书于“崇祯说”的曹大为先生亦以此为“小说中最晚的一个能够准确分辨出年代的事例”,从而认为“最后定稿的时间不会早于崇祯十七年”;徐朔方先生则主要利用此例反驳曹先生的“崇祯说”。在曹先生很有说服力的驳辩文章中,只有对此例的解释显得牵强,在承认了此事发生在“崇祯十六年除夕”的前提之下,将其解释为“这必定是崇祯十七年一、二月间作者又对全书作了一次细微的修改或誊清,于是很自然地把这件刚刚发生的事情,随手加了进去”,这种推测虽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到底缺乏说服力,因为正如徐朔方先生所说,书中穿插了许多有关明末时俗的只言片语,不能说其它的是原有的而只有“冬雷”这一件是“随手加了进去”的。
我认为,关于冬雷的讨论,从孙楷第先生开始就已进入误区,即认定小说写的一定是“崇祯十六年除夕”的事。孙先生的原文是这样的:“除夕雷雨,事诚怪诞,除崇祯十六年外,别无其事(唯崇祯十三年正月朔历城雷电雨雪,事相仿佛,但非除夕)。此虽年代不符,可确认为崇祯癸酉事。”(注:《一封考证醒世姻缘的信》。)在以后的讨论中,孙先生此说被作为一个无需论证的前提,其实,这一论断是大可商榷的。我们从两个方面来加以论述。
第一,从虚构的层面来说,“除夕雷雨”不一定是写崇祯十六年的事。小说虽然可以有相当程度的写实性,有些甚至可以当史料来读,但不可能像考证历史一样,对其中的人和事一一坐实。在《醒世姻缘传》的二十七回、二十九回和三十一回集中写了八月霜、除夕雷、洪水、干旱等种种灾异。据史籍记载,明成化以后,天灾不断。在传统天人感应的哲学思想中,这是上天示警。小说称“作孽众生填满贯,轻狂物类凿良心”,“祸患无突如之理,鬼神有先泄之机”,正是对“天谴”观念的附会。一般认为,最为严重怪诞的灾异之一就是“冬雷震震夏雨雪”,《汉乐府·上邪》将它们与“山无陵”、“天地合”、“江水为竭”一起,当作根本不可能出现的自然现象。而在文学家看来,越是怪诞的事情越能表达某种特定的主题,因此往往利用虚构,《窦娥冤》的“六月飞雪”即是典型。尽管西周生所写的一连串灾异大都有迹可寻,但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要求作者所写的都是实际发生的事情,因为《醒世姻缘传》是小说而不是有关某个地区的灾异纪实,二十九回“冯夷神受符放水,六甲神按部巡提”写水灾就极诡异荒诞。为了强调众生罪孽之深,上天警戒之重,他完全可能像关汉卿虚构“夏雨雪”一样虚构一个“冬雷震震”,而且是在“除夕”。曹大为先生也许是由于严谨的史家意识,认为“除非西周生是能够呼风唤雨的神仙,否则就不可能在崇祯十七年以前杜撰出这件千百年难遇的怪事,稿成之后不久,又居然得到应验”(注:曹大为《〈醒世姻缘传〉的版本流传和成书年代》。)。其实,正如“六月飞雪”一样,在文学家那里这种“杜撰”是完全可能的。至于文学家杜撰的千载难遇的怪事得到“应验”,也是很正常的,震惊世界的“泰坦尼克号”事件就与它发生之前一位作家虚构的故事有惊人的吻合,以至于许多遇难者家属怪罪作家不该写这谶语式的小说。
第二,从写实的层面来说,“除夕雷雨”也不一定是写崇祯十六年的事。在孙先生的原文中,括弧里的内容——“唯崇祯十三年正月朔历城雷电雨雪,事相仿佛,但非除夕”——似乎一直未引起重视。既然根据“事不同时,人相异地”的原则,年代可以不符,日期何必要完全相符?“除夕雷雨”固然怪诞,正月初一“雷电雨雪”同样难遇,何况除夕和正月初一只有一天之差,在传闻中很可能将“初一”传为“除夕”。历城同属济南府,西周生所写的“除夕雷雨大作”如果一定要坐实的话,完全有可能是指“崇祯十三年正月朔历城雷电雨雪”事。而且,与“雷雨大作”比起来,历城的“雷电雨雪”与小说中“大雷霹雳,震雹狂风,雨雪交下”的描写似乎也更接近。
综上所述,“除夕雷雨”不能落实为崇祯十六年的事,因此也就不能作为小说中最晚的一个能够准确分辨出年代的事例,它不足以动摇“崇祯说”。
二、关于内官
三十九回写汪为露“挦得那个模样通像了郑州、雄县、献县、阜城京路上那些赶脚讨饭的内官一般”。
孙玉明先生认为,“从这句话来推测,可能是明王朝被推翻后,内官们无以为生,只得在外赶脚讨饭”。(注:孙玉明《丁耀亢是〈醒世姻缘传〉的作者吗》,《蒲松龄研究》,1993年3-4期合刊。)
笔者曾同一些其他论者一样,认为此条对“崇祯说”极具挑战性,现在终于找到了可靠的反证材料。这要从宦官的来源说起。宦官的来源在早期大概有两条,一是由于战争的掳掠,二是来自籍没罪人的家属。后来,需用日多,又增加了两条途径:一是由宫中的执事太监回自己的家乡招选,二是一些人自宫来投。在宫中未派人招选时,有些人家为了入宫求职,自行净身再设法请求入宫。这也有两种情况,一是有些父母迫于生计,又受了一些人的诱惑,把自己的孩子净了身,这一类年龄多较小;二是一些人净身做太监以求摆脱困境,这一类中有些人已经成年甚至已经成家,明末臭名昭著的魏忠贤就属这一类。他原本是市井无赖,因赌输了钱无法偿还才自宫求职。自宫求职属于一种无序的自发行为,宫里太监需求量有限,自宫者却源源而来,群聚京畿,惹是生非。明代宦官用事极久极盛,自宫求职者也为历代之最,到宪宗成化年间几乎多到泛滥成灾的地步,以至不得不诏令禁止(注:参见温功义《明代的宦官和宫廷·序》,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明宪宗实录》:
成化十一年(1475)十二月,礼部奏,“近有不逞之徒,往往有自宫其弟□子侄,以希进用,聚至四五百人,告乞奏收,群众哄然,阻遏无计”。奏入,有旨:“此辈逆天悖理,自绝其类,且又群众喧扰,宜治以重罪。但遇赦宥,锦衣卫其执而杖之,人五十,仍押送户部,如例编发海户当差。自后有再犯者,本身处死,全家计边防充军。礼部仍移文天下禁约。”
十三年三月,自宫以求用者积九百馀人,礼部以闻,上曰:“此辈以规避差役,违禁自宫,锦衣卫其执杖之,人三十,遣还当差,有再犯者,必罪不宥。”
十六年六月,礼部进自宫者至千馀人,喧扰官府,散满道路,乞照旧例,令巡城御史锦衣卫五城兵马等官逐回原籍宁家。
二十一年正月,周洪谟等疏言:“自宫求进称为净身人者,动一二千人,虽累加罪谪,旋得收用,若不痛惩,无有纪极。今各王府累求内使,宜量以赐之,否则,仍发原籍原卫。今后宜依先年枷项放遣先例,勿复收用。”
《明世宗实录》对此亦有记载:
嘉靖十一年(1532)五月记载,“时自宫无票帖未收者尚数千人,先是,正德二年(1507)九月,申男子自宫之禁,令锦衣卫五城兵马限三日尽逐出之,有潜留京者,坐以死。时宦官窃权者,泽及九族,愚民尽阉其子若孙以图富贵,有一村至数百人者,虽严禁亦不之止也。”
由这些材料可知,在成化至嘉靖年间,民间或为规避差役,或为贪图富贵,有很多人自宫求职,聚集京城,散满道路。数十年间,朝廷一再严禁、重罚,非但未能禁绝,反而愈演愈烈,从成化十一年的四五百人到成化二十一年已动辄一二千人,至嘉靖十一年未收用者有数千人,甚至一村就有数百人。这些人中,固然有规避差役、贪图富贵者,但是,“根本的原因是人们生活日益贫困,无以为生者太多,才会有人不惜自残其身,或伤及子孙”(注:温功义《明代的宦官和宫廷·序》。)。万历以后,许多地方天灾人祸,人们无以为生,有些地方“饿死者道相枕籍”、“割尸肉而食”(注:清康熙《续安丘县志》。),还有些地方甚至有“母食死儿”的惨剧(注:诸城举人陈其猷所绘《东人大饥指掌图》中有“母食死儿”的内容,“见者鼻酸”,见《明神宗实录》卷542,《明实录》,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影印本。),在这种时代,自宫求职谋生的人更多。《万历野获编》卷六“内监”“丐阉”条载:
余入都渡河,自河间、任邱以北,败垣中隐阉竖数十辈。但遇往来舆马,其稍弱者,则群聚乞钱,其强者,辄勒马衔索犒,间有旷野中二三骑单行,则曳之下鞍,或扼其喉,或握其阴,尽括腹腰间所有,轰然散去。其被劫之人方甦,尚昏不知也。比至都城外依然。地方令长,视为故常,曾不禁戢,为商旅害最酷。因思高皇帝律中,擅阉有厉禁,其下手之人,罪至寸磔。而畿辅之俗,专借以搏富贵。为人父者,忍于熏腐其子,至有兄弟具阉而无一人入选者,以至为乞为劫,固其宜也。按宋制,凡愿自宫者,先于兵部报名,自择旺相吉日阉之,兵部纪其日上奏验明,待创愈,纳之内廷。其后宦者得官,即以阉之日为诞辰,一切星壬算命,竟用此日支干。今世用事大珰,却不闻有此说。然而报名就阉,自是令甲所载。无奈浸寻至今,略不遵行。朝廷每数年亦间选二三千人,然仅得什之一耳。聚此数万残形之人于辇毂之侧,他日将有隐忧,不止为行役之患也。
由此可见万历年间自宫现象较嘉靖时更烈,聚集京城的“未收用者”已由“数千人”发展至“数万”,而且直接说明了这些人的谋生方式是“乞”或者“劫”。《万历野获编》卷六“内监”“二中贵命相”条还有一条材料:
内竖辈得志,多无忌惮。如梁师成之父苏子瞻,童贯之父王禹玉皆是。然而苏、王子孙终得其力。且二公亦因而昭雪,自是怪事。近日王笠川进士继贤,少年励志读书,以欲念烦炽,去其外肾,遂作宦者状,声貌全如妇人。辛丑登第后,诸阉骄于御前,指王名云,吾曹中已有甲榜,宣力于外者矣。上询知其故,亦为启齿。群阉出外抵王寓,称贺不绝,求附气类。王大恚,避入西山,其作令清苦,故是乐巴一流人也。
这里,王笠川自宫之后并未入宫做太监,但无论是沈德潜还是宫内的太监显然都是把他当“内监”看待;在第一条材料中,沈德潜明确将隐于断壁败墙中的自宫者称为“阉竖”。“内监”、“阉竖”与“内官”是同义词,可见,在人们心目中,自宫者无论是否进宫做太监,都被看作“内官”。何况西周生在小说中用到“内官”一词,强调的是“没有胡须”这一生理特征,在这个意义上,“内官”、“内监”、“阉竖”完全能够互换。因此,我们认为,《醒世姻缘传》中所写到的“郑州、雄县、献县、阜城京路上”有许多“赶脚讨饭的内官”这一现象完全可以用大批自宫者流落京城“为乞”这一历史事实来解释,就算如孙玉明先生所推测的,在明清易代之际有无以为生的“内官”流落在外“赶脚讨饭”,它也不能作为成书于清初的证据。
标签:醒世姻缘传论文; 崇祯论文; 中国古代史论文; 文学论文; 历史论文; 读书论文; 康熙论文; 蒲松龄论文; 明朝论文; 明朝历史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