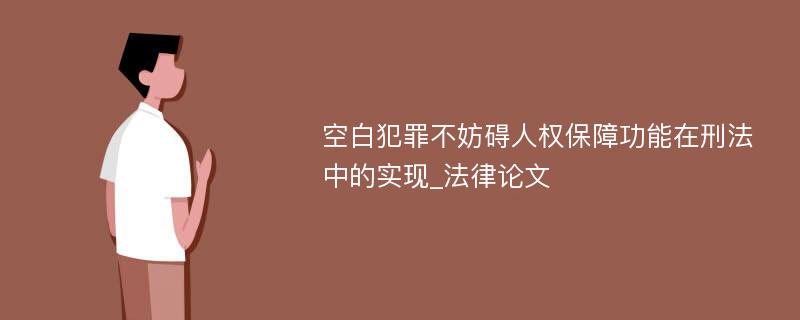
空白罪状并不妨碍刑法人权保障机能之实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罪状论文,刑法论文,机能论文,人权论文,空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924.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140(2007)01-0021-05
空白罪状是随着社会公共事业范围的不断扩大,顺应由自由法治国向社会福利法治国的转换,行政犯日趋增多的状况而出现的一种罪状表述方式。它表现为立法者虽在刑法罪刑规范中明确规定了法定刑,却将部分犯罪构成要件委诸给刑法之外的其他法律规范予以补充。这种以其他规范性文件为补充的立法方式是否违反罪刑法定之法律专属性原则?是否不利于防止国家权力尤其是国家行政权力对公民自由的恣意干涉呢?空白罪状对犯罪构成要件之“空白”规定是否违反了罪刑法定主义的明确性原则?是否不利于国民对自己行为的预测呢?在当前“人权入宪”和罪刑法定原则法典化的背景下,这些问题的解决关涉到人权保障在刑法中能否得以实现,以及空白罪状这种罪状表述方式能否在刑法中继续存在,并随着行政犯的增多而增加是否可行,因而非常重要,本文拟对此进行探讨。
众所周知,罪刑法定主义从思想的启蒙到原则的法律确认,始终贯穿着人权保障的思想,始终以限制国家的刑罚权,保障公民的人权为己任,人权保障是罪刑法定原则的核心。“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nullum crimen sine lege,nulla poena sine lege)是罪刑法定原则的经典表述。根据这一表述,罪刑法定之人权保障的要义在于:一方面基于民主主义思想的要求,从法律主义的角度,犯罪与刑罚必须由民主制定的法律规定,易言之,必须由国民的代表机关即议会制定的法律来规定,以防止国家权力的恣意行使;另一方面,基于保障国民自由的自由主义的要求,对犯罪与刑罚必须由法律事先采用明确的规定,以使国民了解进而准确预测自己的行为何时构成犯罪[1]。据此,判定任何一种犯罪与刑罚的立法模式是否符合罪刑法定,是否有利于人权保障机能的实现,应看其是否符合罪刑法定主义的法律专属性原则和明确性原则。
一、空白罪状符合罪刑法定的法律专属性原则和人权保障的民主、法治要求
为了限制国家刑罚权,避免行政机关(通过制定行政法规)擅立刑事规范,保障公民自由人权的实现,现代法治国家要求奉行法律专属性,强调犯罪与刑罚必须由民选代表机关制定的法律来规定。
对于法律专属性的理解,意大利刑法学界存在相对主义与绝对主义的对立。绝对主义者认为意大利宪法第25条明文规定,不依“法律”规定不得处罚任何人,因此,在刑法领域中只能由法律来规定犯罪与刑罚,不允许任何第二性法源。换言之,在刑法中不仅不准其他机关代理立法,也不允许用行政法规或习惯来补充刑法规定,“因为只有完全排除行政方面的干扰,狭义的罪刑法定原则才能发挥它的保障功能”。为了缓和宪法规定的严厉性提出的概念,意大利公法学者主张对法律专属原则作相对理解,他们认为,古往今来的任何立法者都不可能制定详尽无遗的法律,在社会生活变化急速的现代国家里,立法者更是只可能规定行为规则的“主线(linee maestre)”,让等级较低的渊源来决定具体的内容,即允许行政机关在法律规定的基本原则范围之内制订、完善具体的行为规范。在上面两种对立的主张之间,意大利刑法学界的通说采取了一种折衷主义的态度,即在刑法中是否允许存在非法律性规范作为渊源的问题上,坚持刑法渊源绝对的法律专属性,否认任何行政规范具有作为刑法直接渊源的效力,但在是否允许行政法规或习惯法来补充完善刑法规范的问题上,则认为在一定条件下应当承认非正式性法律对刑法规范的补充作用。自1966年第26号判决开始,意大利宪法法院开始阐明一些指导法律与法规相互关系的基本原则,明确地认为应在一定程度“削弱”法律专属性原则的绝对性。意大利宪法法院通过一系列判决强调:(1)对刑法规范的法定刑部分,应采取绝对的法律专属性原则,行政机关无权决定或选择刑罚,因为严格的罪刑法定原则要求“只有国家的法律(或具有同样效力的规范)才能够规定用哪种刑罚来惩治那些必须给予刑事制裁的违法行为”,因为“人的尊严和自由是……具有特别价值的法益……不允许行政机关在这方面有任何自由处置的权力”;(2)刑法规范的禁令(罪状)部分应采取构成要件“足够明确原则”,即法律“必须明确规定应由非立法机关来确定的前提、性质、内容和范围”。换言之,在刑法规范的罪状部分,宪法规定的刑法“法律专属性原则”只有相对的意义,只要符合“足够明确原则”,行政法规对刑法规范的补充,就不违背宪法规定的精神。至于在什么情况下行政规范与刑法规范的关系才符合“足够明确原则”,意大利刑法学界认为,空白刑法规范中规定了犯罪的法定刑,而由行政法规来补充确定具体的罪状,可以说在原则上符合法律专属性原则[2]。法国学者对于法律专属性原则的理解,也认为本义上的法律,即字面形式意义上所指的法律,是指由立法权力机关(国民议会与参议院)表决通过的成文法。但除此之外,由执行权力机关发布的法规,即行政性法令与条例,也是刑法的实际渊源,也是犯罪的“法有规定”的构成要件,只不过它们在价值和效力要低于本义上的法律。法律不仅可以规定哪些行为是犯罪,而且可以规定刑罚;条例只能对犯罪作出规定,条例无权确定刑罚。在条例仅仅是具体规定如何使用法律的情况下,条例中规定的制裁事项,应当从法律本身中去寻找[3]。
总之,刑法学界目前的主流观点是从相对意义上来理解法律专属性,它只强调制裁规范必须由民选代表机关制定的法律来规定,但至于法律制定后根据什么来解释适用,那就不再是立法的问题,而是法律补充适用的问题。因而,空白罪状在刑法已将罪刑关系确定之后,指示参照其它法律法规来补充适用,并未违背刑事立法权只能由最高立法机关行使的民主、法治原则,并不妨碍人权的实现。更何况这些补充规范尽管不是由立法权直接运作而制定的法律,但它们是经过了法律的授权,其规定的内涵同样受立法权的监督,在实质上仍是受制于立法权的规定,故同样属于罪刑法定之“法定”[4]。正如我国台湾学者指出:“按照罪刑法定主义之所‘法定’,应指国家立法机关通过实施之法律所订定者而言,不包括行政机关颁布之命令在内。惟如系以法律授权由行政机关以命令补充法律所未具体规定之事项,形式上虽为行政命令,实质上因系基于法律之授权,仍为法律之作用,与单纯行政命令之价值应有不同,不能认为违背罪刑法定主义之原则,空白刑法即系基于此项原则所为之命令。”[5] 因此,空白罪状在实质上与罪刑法定原则不相违背,并未与其人权保障理念相左。
在我国,以行政法律法规补充空白罪状之“空白”并未违背民主法治原则。我国自1997年修订刑法之后,将所有原行政法律中规定的罪名和法定刑条款统一到了刑法典之中,目前暂不存在附属刑法规范。至于直接在行政法律之外的其他行政管理法规中规定罪名及法定刑的做法,我国从未采用。所有的行政犯罪都是由刑法规定的,我国立法机关也从未授权行政部门制定行政犯罪方面的法规。空白罪状之“空白”参照行政管理法律法规来确定不过是在法律制定出来之后的法律解释适用问题。这与“非由民主制定的法律”而是由其他行政管理法规直接规定犯罪与刑罚不是一个层面上的问题。由什么规定犯罪与刑罚是第一层次上的问题——立法问题,以什么为依据对刑法所规定的犯罪与刑罚进行补充适用,则是在法律制定出来之后第二层次上的问题——法律补充适用问题。不可将国家立法机关行使刑事立法权制定法律与对法律的补充适用混为一谈。因此,在刑法分则罪刑条文中规定空白罪状并未违背民主法治原则[4]。其次,作为空白罪状补充规范的行政性法律以及行政法规、行政措施和决议、命令也是人民群众意志的体现。行政性法律是由代表人民意志的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并不违反民主法治原则。行政法规则是国务院在宪法的授权之下根据宪法和法律制定的,并且内容与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相一致,否则无效,因而根据宪法和法律制定的有效行政法规是人民群众意志的体现。
二、空白罪状符合人权保障要求的罪刑关系的明确性
为了限制司法权的恣意扩张,切实保障公民的人权,罪刑法定主义要求立法者为公民提供一张清晰明确的罪刑关系“价目表”,使公民的行为具有可预见性。明确性原则是罪刑法定原则的派生原则之一,它要求立法者规定犯罪的法律条文必须清楚明确,使人能够确切了解违法行为的内容,准确地界分罪与非罪,以保障该规范没有明文规定的行为不会成为该规范适用的对象[6]。20世纪初美国宪法判例亦提出了“由于不明确而无效的理论”(void-for vagueness doctrine)。据此,罪刑即使法定,但内容如不明确,依然无法防止刑罚权滥用,罪刑法定主义保障公民自由的目的依然无法实现。封建专制主义制度下的罪刑擅断之所以得以猖獗,很大程度就在于法的不明确性、法的含糊性。故而有法律格言:“没有法律的状态比有不确定的法律要好”(Melius est jus deficiens quan jus incertum),即与其制定不明确的法律,不如不制定法律。言下之意,不明确的法律比没有法律更糟糕[7]。马克思也曾经指出:“法律是肯定的、明确的、普遍的规范,在这些规范中自由的存在具有普遍的、理性的、不取决于个别人的任性的性质。”[8] 总之,没有法的明确性就没有权利的保障。
那么,空白罪状之“空白”是否违背了罪刑法定之明确性呢?对此,我们回答是否定的,理由如下:
首先,罪刑法定之明确性总是相对的。正如意大利刑法学者指出:“‘明确’本身就不是一个确定的概念,所谓‘构成要件的明确性’也只能是一种立法政策的方向,甚至在一定范围内可以说是一种理想”[9]。更何况,随着社会的发展,加之立法技术的不足、语言文字本身的模糊性等,有些在当时看来是明确的内容,在以后也有可能出现歧异。因此,期盼法律的绝对明确,要求刑法成为任何人都能读懂的、任何争议都不存在的法律,那是过于幼稚的想法,世界上也没有这样的刑法。基于此,有些国家的宪法法院或最高法院对如何判断某一法律条文是否符合明确性原则提出了相应的原则性标准。美国最高法院认为,刑法规定是否含混,应以刑法的规定是否能够充分明确地就禁止的行为表达警告的意思,且对于普通智力的人能够事先理解为准。例如,“不得在街上、公园或公共场所或任何公众出入的建筑物内游荡”的规定中,“游荡”(loiter)一词,即系无明确的定义。再如,新泽西州1934年刑法典第4条规定的“gang”一词既可理解为一群有组织的犯罪团伙的成员,亦可理解为一群有组织的工人,其含义就是不明确的。日本最高裁判所大法庭1975年9月10判决时指出,判断某个刑罚法规是否含混、不明确,“应根据具有通常判断能力的一般人的理解、在具体场合能够判断某行为是否适用该法规为基准来决定”[10]。意大利宪法法院则在具体认定某一规范是否违反明确性原则时总是持极端谨慎的态度,因此常常宣称“犯罪构成的明确性并不等于(一定要)采用(多少有点完整的)描述性罪状”,运用“约定俗成的概念或者可以作客观理解的社会伦理价值”并不与明确性原则的要求相悖,只要“这些概念在法官所处的社会环境中是众所周知并被普遍接受的”[9] 28。
由此,刑法条文在对明确性追求中只能在不走向如下两个极端当中求得平衡:一是详细的罗列式规范;二是纯粹一般性的规范或包含模糊因素的规范。因为,前者会割裂概念的完整性,很难发挥法律规范在引导社会文化价值方面的作用,并且易生法律漏洞,破坏法律的确定性;后者致使法律规范没有具体或确定的内容,刑法蕴含的行为规范和裁判规范的功能都会受到侵损[9] 26。
就罪状的描述方式而言,采用叙明罪状方式固然详细地描述了具体犯罪构成要件,而空白罪状则留有“空白”,但“空白”不意味着不明确,“详细”也并不意味着就明确。判断一个刑法条文明确与否,应该对该条文使用的语言进行全面整体地分析,而不是只要有详细罗列就一定明确不含糊。比如,我国《刑法》第384条“挪用公款罪”详尽地罗列了挪用公款进行非法活动、营利活动和其他个人用途的行为情况,并且针对三种不同用途规定了不同的定罪条件。咋看起来,似乎清楚明确。仔细分析就可发现其实不然,其法条并不明确,甚至缺乏可操作性。首先,何谓非法活动?挪用公款归个人进行非法活动,是仅限于构成犯罪的违法活动,还是仅限于一般的违法活动?或者是既包括犯罪活动也包括一般的违法活动?在理论和司法实践存在不同的理解。营利活动这个概念就更加宽泛,不好界定了。更何况,营利活动与非法活动之间存在一定的交叉。营利活动有非法与合法之分,非法活动也有营利与不营利之别。此外,法条表述的挪用公款用于其他用途,“超过3个月未还的”,此处的“未还”就更令人费解,真不知此处的“未还”是指案发前就一直未还,如果案发前已还,即使挪用已超过3个月也不再追究刑事责任还是指不管案发前是否已还,只要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超过了3个月就要追究刑事责任?此外,《刑法》第384条针对不同用途,对挪用公款行为分别规定了不同的定罪标准,固然体现了对不同危害程度的挪用公款行为区别对待的原则,但却缺乏了司法实践的可操作性。试想如果某人一次或者多次挪用公款,分别用于多种用途,司法机关能否准确查清每一种用途的数额呢?即使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可以查清,其必要性、合理性如何呢?对于挪用公款罪的罪状设置,笔者十分赞成有学者提出的“删除不同用途的规定,只概括规定挪用较大数额的公款”的修改建议。由此可见,尽管我们要求法律语言必须明确,不能含糊不清,但也不能因追求法律的明确详细而导致法律的臃肿累赘或漏洞增多。“简短是法律之友,极度的精密在法律上受到非难”(simplicitas legibus amica et nimia subtilitas in jure reprobatur),因此。要避免过于繁琐冗长,导致法律漏洞或空白、法律条文交叉矛盾的现象出现。正如美国学者弗里德曼指出,法律起草人懂得法官专横“解释”的权力,总是将语言像网一样收得很紧,尽量给条文加上各种保留和限制,试图将同义词堆积起来,尽量堵住所有的漏洞,把门栓好,结果往往使法律条文成为镶嵌物、拼渣物[11]。与之相反,我国刑法中有些犯罪虽采取空白罪状的方式,但在内容上却十分明确。例如,《刑法》第340条规定:“违反保护水产资源法规,在禁渔区、禁渔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捕捞水产品,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该条是以行政管理法规——《水产资源繁殖保护条例》作为补充规范的。该法规第7条、第8条、第9条、第10条和第11条分别对禁渔区、禁渔期、禁止使用的工具和方法作出规定,内容十分明确。由此可见,罪状设置的明确性并不意味着必须详尽描述,概括、简单并不意味着就不明确,就会产生歧义。空白罪状只要明确规定出要参照的法律法规亦同样可以使人清楚明确地理解犯罪的具体构成要件。
对于空白罪状的明确性问题,日本最高裁判所判例指出,“在新宪法之下,得以命令规定罚则的情形,必须以基本的母法有具体的委任规定之意旨者为要件。”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对此也指出,“刑罚命令之委任立法,必须由立法者明白表示授权之意旨,包括授权之内容、目的及范围,均须精确加以确定;就其可罚的要件及处罚的种类,在授权的母法规定中,均以明白可以预见,而非全由授权的行政命令始予制定。”[12]
就我国刑法中的空白罪状而言,哪些法律、行政法规、规章等能够成为空白罪状的补充规范是由刑法明文规定的,即只有当空白罪状的刑法规范明文规定“违反……规定”、“违反……法律”、“违反……法规”等时,这种法规的相关内容才能补充空白罪状的构成要件。同时考虑到空白罪状的补充规范所涉范围的广泛性,我国《刑法》第96条规定,“本法所称违反国家规定,是指违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和决定,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规定的行政措施、发布的决定和命令。”此外,2001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刑法》第228条、第342条、第410条规定的“违反土地管理法规”作了立法解释,即“违反土地管理法、森林法、草原法等法律以及有关行政法规中关于土地管理的规定。”据此,我国空白罪状之“空白”是有明确的授权和范围界限的。比如,我国《刑法》第343条第2款规定破坏性采矿罪是“违反矿产资源法的规定,采取破坏性的开采方法开采矿产资源,造成矿产资源严重破坏的”行为。根据刑法指示参照的《矿产资源法》第29条规定:“开采矿产资源,必须采取合理的开采顺序、开采方法和选矿工艺。矿山企业的开采回采率、采矿贫化率和选矿回收率应当达到设计要求。”第30条规定:“在开采主要矿产的同时,对具有工业价值的共生和伴生矿产应当统一规划,综合开采,综合利用,防止浪费;对暂时不能综合开采或者必须同时采出而暂时还不能综合利用的矿产以及含有有用成分的尾矿,应当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防止损失破坏。”据此,在实践中,如使用不采取合理的开采顺序、开采方法和选矿工艺,致使矿山企业的开采回采率、采矿贫化率和选矿回收率达不到设计要求的行为应视为破坏性采矿行为。
三、结语
空白罪状这种随着行政犯增多而出现的罪状表述方式,尽管表面上存有“空白”,即它是在刑法已将罪刑关系确定之后,指示参照其他法律法规来补充适用的,然而此种“空白”参照行政管理法律法规来确定不过是在法律制定出来之后的法律解释适用问题,而非由其他行政管理法规直接规定犯罪与刑罚的立法问题,因此,在刑法分则条文中规定空白罪状并未违反罪刑法定主义的法律专属性原则,也并未违背人权保障的民主法治要求。同时,其内容也并非不明确,能够成为空白罪状补充规范的法律、法规和规章都是由刑法明文规定的,人们依然可以据此预测自己的行为范围,知悉自己的权利界限,实现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总之,空白罪状并未违背罪刑法定主义的精神实质,并不妨碍刑法人权保障机能之实现。
标签:法律论文; 刑法论文; 罪刑法定论文; 法律制定论文; 刑法基本原则论文; 立法原则论文; 行政授权论文; 宪法的基本原则论文; 日本宪法论文; 行政立法论文; 宪法修改论文; 宪法监督论文;
